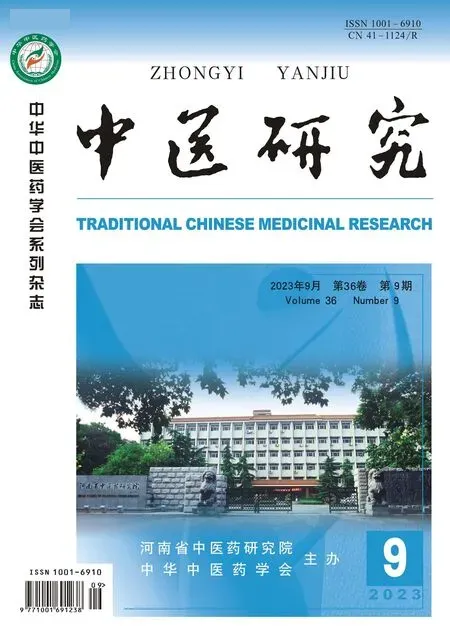同病异治的理论渊源与后世影响*
钱会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
同病异治理论发源于《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篇》《素问·病能论篇》分别明确提出“同病异治”的概念,并进行了阐释。书中的其他文章如《素问·异法方宜论篇》《素问·诊要经终论篇》《素问·汤液醪醴论篇》《素问·示从容论篇》等均有论述,亦进行诸多阐述和发挥。《黄帝内经》的阐述奠定了同病异治的理论基础,使其成为中医学重要的治疗法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代医家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其内涵,推而广之,指导临床应用。该理论对拓展临床疾病的论治途径、启迪方药的药理研究思路及传承和创新中医学理论均有重要意义。
1 同病异治之理论渊源
同一种疾病因其发病的地域环境、时间、疾病所处阶段或类型不同,所表现的证候也不同,故临床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同病异治已成为中医学治则治法的重要内容。回溯历史长河,从《黄帝内经》探究其渊源,主要阐述有以下方面。
1.1 地域环境不同
《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曰:“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即气候环境与人的体质状态不同,故临床采用不同治法。王冰注解该句曰:“西方北方人皮肤腠理密,人皆食热,故宜散宜寒。东方南方人皮肤腠理开,人皆食冷,故宜收宜温。”认为西北气候寒冷,而人之皮肤腠理致密,且多食热,故而体质多内热,临证治宜散其外寒、清其内热;东南气候炎热,人之皮肤腠理开泄,加之人多食冷,易生内寒,故治宜收涩其表而温其内寒。该论述以南北气候、饮食的不同,以及对机体影响的差异明示了同病异治理念与基本原理。《素问·异法方宜论篇》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相同,皆愈,何也。”明示答案为“地势使然也”。张介宾注曰:“地势不同,则气习有异,故治法亦随而不一也。”该篇将自然区域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方,描述地理位置、气候、水土、物产不同,人们的衣食起居、生活习惯对体质有不同影响,故形成五方人体质之不同,且导致五方区域的常见病不同,而临证治疗亦不同。东方之人,多患痈疡,治以针石;西方之人,其病生于内,治以毒药;中央之人,多患痿厥寒热之病,治以导引按跷;北方之人,多患脏寒、满病,治以灸焫。其原理为“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黄帝内经》之论可谓因地制宜理论的萌芽。喻昌在《医门法律》中列专题“申治病不审地宜之律”明言“凡治病不察五方风气,服食居处,各不相同,一概施治”为“医之过”。此亦从人与天地相参的视角,关注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综合考察气候、饮食等对人体体质与发病的影响,以及宜采取的相应治疗措施。
1.2 发病时间不同
因脏腑有其所主时令,故疾病发病季节不同,所涉及的主要脏腑不同,临证治疗亦不同。《素问·诊要经终论篇》曰:“正月二月,天气始方,地气始发,人气在肝。三月四月,天气正方,地气定发,人气在脾。五月六月,天气盛,地气高,人气在头。七月八月,阴气始杀,人气在肺。九月十月,阴气始冰,地气始闭,人气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复,地气合,人气在肾。”此论的切入点是不同季节与物候之间的差异,脏腑所主时令及邪气入侵的脏腑不同,治疗不同。诚如《素问·诊要经终论篇》曰:“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说明四时不同,针刺治疗核心点与方法亦不同。《难经·七十四难》曰:“春刺井,夏刺荥,季夏刺俞,秋刺经,冬刺合者,何谓也?然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荥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经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肾。”此以五腧穴针刺应四时变化为例,表明脏腑主时不同,论治取穴不同。该论立足于时令变化,重视气候因素对人体脏腑及发病的影响,提出不同季节治疗的脏腑不同,此亦是因时制宜思想的生动体现。
1.3 疾病所处阶段不同
疾病处于不同阶段,其病变机制与特点亦不同,故治疗方法各异。《素问·病能论篇》曰:“有病颈痈者,或石治之,或针灸治之。”此述及临床颈痈之治,明示治疗用具与措施的选择有不同,究其原理,指出“痈气之息者,宜以针开除去之,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即颈痈同病异治乃基于疾病的阶段不同,气血状态不同,正如姚止庵注曰:“治之有异者,以痈原各有所宜故也。”以颈痈的论治为例,其病变的时期、病理机制等不同,故治疗不同,归纳而言“此所谓同病异治也”。宋代《圣济总录》记载,治疗痈疽影响气机者,宜针疏导开除;而对于气盛血聚者,则宜使用砭石、针刺泻之,“若然则砭石九针之用,各有所利”。此述及九针的施用各有其适应病证,提示临床善治“血脉之变,痈肿之病者……当审轻重而制之”。在此进一步阐释经文之意,说明虽同为痈疽,但临床因病之轻重、病变性质不同而采用不同治法。从疾病不同发展阶段角度进行考察,疾病处于病变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病理变化特点,故治疗方法与处理措施宜有所不同。此亦蕴含了因病制宜的理念。
2 同病异治的后世影响
同病异治理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在历代医家的运用发挥中,同病异治理论得以践行并不断发展。同病异治在中医理论的构建与临床运用中具有重要价值,为临床疾病辨治分析的丰富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2.1 病机不同,治疗不同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的“燥胜则干”指出燥邪偏胜以干燥为病理特点。清代喻昌在此基础上首创秋燥病名,并提出“燥属火热,易伤肺之阴液”,创制清燥救肺汤。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专论秋燥之治,提出“秋感燥气,右脉数大,伤手太阴气分者,桑杏汤主之”,由于该病为本气自病之燥证,“初起必在肺卫”,治以辛凉之桑杏汤清气分之燥,并注明服法为顿服,若重者则可以再次服用,其原理在于“轻药不得重用,重用必过病所”。若“感燥而咳”初始津伤不重者,以桑菊饮主之。若属“燥伤肺胃阴分”,治以甘寒之沙参麦冬汤,并指出较桑杏汤、桑菊饮的适应证而言,沙参麦冬汤所治病证“病深一层,故以甘寒救其津液”;若属“燥气化火,清窍不利”,则以“清上焦气分之燥热”的翘荷汤主治;若燥热较盛、阴津损伤,治以辛凉甘润之喻氏清燥救肺汤。以上论述明示,虽同为秋燥之邪致病,因其病位深浅、病机轻重变化不同,故治疗不同。此亦同病异治理论在秋燥论治中的践行实例。
2.2 病位不同,治法不同
《素问·汤液醪醴论篇》提出“开鬼门,洁净府”,认为水湿停聚体内,可通过发汗、利小便进行治疗。《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进一步明确发汗与利小便的适应证,即“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其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同样是水液代谢障碍所致水肿,其病位在上、在表者,当发汗乃愈,病位在下、在里者,则利其小便,体现病位不同、其治各异的思想。《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曰:“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同为溢饮,其邪在表,当以汗解之,其中大青龙汤证兼里热,治以发汗散饮兼清里热;而小青龙汤证则兼里寒,治以发汗兼温化水饮。《医宗金鉴·辨温病脉证并治篇》亦结合温病与热病特点,明示温病、热病无汗者,宜大青龙汤;时无汗、时有汗者,宜桂枝二越婢一汤;有汗者,宜桂枝合白虎汤;内热者,宜防风通圣散;表实者,倍用麻黄;里实者,倍用大黄。辨治要点在于“量其病之轻重,药之多少而解之”,且提示临证“当审其表里,随其传变所见之证”。
清代叶天士《温热论》曰:“大凡看法,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并将其作为温病的辨证纲领。“在卫汗之可也”即邪在卫分,当予辛凉轻剂银翘散;“到气才可清气”指若邪在气分,则予辛凉重剂白虎汤;而“乍入营分,犹可透热,仍转气分而解,如犀角、元参、羚羊等物是也”“入血则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如生地、丹皮、阿胶、赤芍等物是也”。此凸显温病病位不同,治疗不同,并警示“若不循缓急之法,虑其动手便错耳”。此乃同病异治实践运用之范例与思维模式,亦创新发展了温病理论。
2.3 病性虚实不同,治疗不同
《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曰:“胸痹心中痞,留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虽同为胸痹,病性虚实不同,临证治疗有温通、补虚之不同。若痰浊壅塞、气滞不通,宜枳实薤白桂枝汤,通阳散结宣痹;若属中焦阳气虚衰,宜人参汤,温中益气助阳。《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曰:“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宜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可见虽病同为支饮,但因虚实性质不同,故治法与方药有所不同。
2.4 体质不同,治疗不同
《素问·示从容论篇》曰:“夫年长则求之于府,年少则求之于经,年壮则求之于脏。”明示年龄不同、体质不同而治疗不同。清代俞震《古今医案按》曰:“若南京人患伤寒,用麻黄者十有二三。若江北人不用麻黄,全然无效,况直隶陕西乎。”此以伤寒之治为例,说明南京人、江北人、陕西人等因生活地区不同,人之体质有异,故使用麻黄的情况截然不同。俞震进而援引赵献可之论,提出“太阳之人,虽冬月身不须绵,口常饮水,色欲无度,大便数日一行”,治以“芩、连、栀、柏、硝、黄”;“太阴之人,虽暑月不离复衣,食饮稍凉,便觉腹痛泄泻”,治以“参、术、姜、桂”。究其机制,“此两等人者,各禀阴阳之一偏”。此论以体质不同为依据,强调“立方用药,总贵变通”,认为临证不仅要关注人的疾病,还要重视患病之人体质状况的调治。清代冯兆张《冯氏锦囊秘录·伤寒夹惊变惊》亦以小儿伤寒夹惊变惊的病理特点为例,指出“伤寒门中杂症,惟此小儿多犯,而与大人异治”,认为夹惊者因邪热乘心,热极生风,手足为之动摇,精神为之恍惚,患儿症见痰壅气喘、口噤目窜等变惊之候,痰热在上焦横扰者,治可“即吐之”;若三焦俱客者,治可“即下之”。清代徐灵胎《医学源流论》曰:“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以人体的体质差异为立足点,阐述了病虽相同,因其体质状态不同,故治疗不同,亦可谓因人制宜观念的体现。
以上论述为现代“同病异体”命题[1]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亦为基于以人为本、因人制宜思想的个体化诊疗提供了理论依据。诚如王琦院士所述:“充分注重人的个体差异性,进行个体医疗设计,采取优化的、针对性的治疗干预措施,使之更具有有效性和安全性,并据此拓展到个性化养生保健以及包括人类生命前期的生命全过程,从而实现由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的转化。”[2]
3 同病异治的现代运用
同病异治理论是现代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论治思路发微,为疑难病的辨析治疗拓展了途径,亦为方药治疗机制探索提供了启迪。
3.1 同病异治,丰富常见病论治思路
著名医家秦伯未论热病之治,提出发汗退热、调和营卫退热、清气退热、通便退热、催吐退热、和解退热、表里双解退热、清化退热、清营解毒退热、舒郁退热、祛瘀退热、消导退热、截疟退热、滋补退热等不同治法[3],体现了依据热病之病位、病性、主证不同,采用不同治法。此为同病异治应用于热病治疗的范例。徐经世认为,热病的外感和内伤须分而论之,外感热病有传染性、非传染性之分,治疗须分阶段,感受“戾气”则可发生疫病。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邪首侵于肺,治当宣透;少阳不和,治宜和解少阳;阴虚热病,治宜滋阴清降;气虚血亏,治宜甘温除热;肝郁血瘀,治宜疏清泄热[4]。针对崩漏病证,北方医家临证着重于本为肾虚,标为血瘀,治以活血化瘀以止血,兼补肾健脾,因北方患者体质较强、腠理致密,故活血化瘀力度较大,且在用药剂量上也相对较大;南方医家则着重于本为肾虚,标为气阴两虚兼血瘀,临床治疗着眼于滋阴益气以止血,兼补肾健脾、活血养血,因南方患者体质相对较弱,腠理疏松,且体质多为阴虚,故虽有瘀血,仍以滋阴益气为主,活血化瘀为辅,用药剂量也相对少[5]。当代医家施小墨认为,因患者体质不同,即使同病,受损脏腑亦有差异,所以强调根据体质及所处地区、气候、季节、生活习惯、饮食等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使“各得其所宜”[6]。虽同为心病,但其证有虚实,表现各异,可伴焦虑、抑郁等,且病因病机不同、症状有异,临证治疗以同病异治为指导,宜注重辨证论治,再辅以心理疏导[7]。眩晕原因多端,基于无风不作眩、无痰不作眩、无虚不作眩、无瘀不作眩之原理,论治紧扣风、痰、虚、瘀不同病机,临证治疗分别采用平肝潜阳、息风止惊、燥湿祛痰、健脾益气、活血化瘀等不同方法[8]。同为湿邪所致泄泻,证候有湿热证和寒湿困脾证的不同,肠道菌群失调变化亦不同,治疗有清利湿热与温化寒湿之不同,为探索泄泻同病异治提供了肠道菌群视角的客观依据[9]。刘爱民治疗湿疹围绕湿热蕴肤的核心病机,审湿求机,提出风寒束表、湿热蕴肤以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加减,阳虚外寒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减,湿热蕴肤以龙胆泻肝汤加减,脾虚湿蕴以参苓白术散加减,风热夹湿、侵犯肌肤以消风散加减等,其辨治湿疹的临床经验彰显同病异治之精髓[10]。冯蓓分别运用清解湿热、发汗解表与温阳固表、养血祛风论治荨麻疹,体现同病异治之思路[11]。
3.2 同病异治,拓展疑难病辨治途径
白塞氏病属于中医学“狐惑”范畴,根据病机特点与症状不同,临床治疗可分别采用通腑泄浊畅气机、活血祛瘀通络、滋补肝肾之阴等法,其治既有核心重点之不同,又有遣方用药之差异,体现同病异治的思维模式[12]。石国喜[13]紧扣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虚实病机,辨为肝胃不和、浊毒内聚、气滞络阻、阳虚饮停、阴虚燥结等,临证分而治之,亦是同病异治之践行。中医证候代谢组学研究可获得不同证型下的差异代谢物及通路,基于同病异证的肺系疾病代谢组学运用,可为中医临床诊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理论支持,是同病异治探析之例[14]。顾少蓉[15]根据不同病因病机论治不孕症,其中宫寒不孕、冲任受损、胞冷不孕,治以调补冲任、温肾暖宫;肝郁不孕、冲任失调,治以疏肝解郁、调理冲任;湿热阻络不孕、胞脉阻塞,治以清热化湿、化瘀通络。
3.3 同病异治,对方药药理机制研究之启示
同病异治理论对于方药的网络药理学研究,尤其是不同或多种方药在同一疾病的运用机制阐发,不乏启迪与借鉴。通过网络药理学网络化联结与分析方法,构建抗阿尔茨海默病常用中药复方开心散与生脉散“成分-靶点”调控网络图,提示中枢神经炎症调控是复方开心散与生脉散抗阿尔茨海默病的重要生物学机制[16]。茯苓杏仁甘草汤与橘枳姜汤干预冠心病,与该复方中相同化学成分对应的靶点作用相关[17]。青蒿鳖甲汤及补中益气汤治疗癌性发热的分子作用,与正向调控一氧化氮生物合成、DNA转录、酶结合、平滑肌细胞增殖等生物过程有关[18]。以上论述为运用同病异治理论探索方药作用机制提供了有益借鉴与思路启迪。
4 小 结
同病异治理论源于中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历代医家结合临床实践不断丰富完善,使其成为中医学治则治法的重要内容。同病异治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对同病异治理论的深入认识与灵活运用,该理论对临床常见病治疗途径的拓展、疑难病症的论治及中医方药的药理机制研究等具有借鉴与启迪意义,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