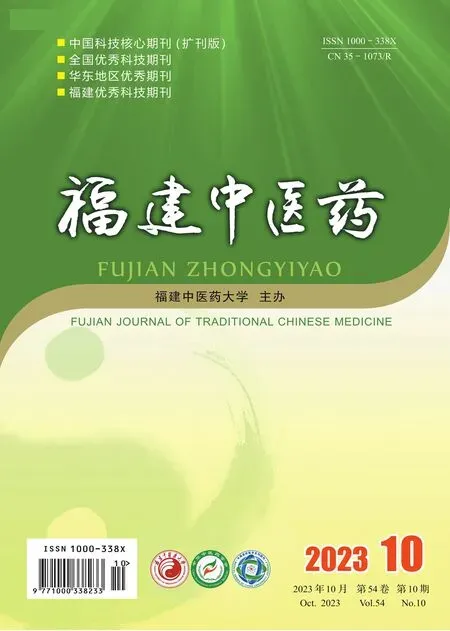齐鲁儒医形成和发展之历史沿革
刘亚楠,姚鹏宇,林智善,付革利,王亚歌,赵彦蕊,陈思馨*
(1.滨州医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0;2.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山东工程技术研究室,山东 济南 250102)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齐鲁大地,是儒医的重要集聚区和发源地之一。从儒及医,医弘儒学,独特的儒医思想融入齐鲁医家的骨子里,儒脉与医脉相谐相合,形成了齐鲁医家的精神内核,造就了齐鲁医家独特的学术风格。“儒医”是齐鲁医道文脉传承的基础,是地域学术特色的体现,对于塑造齐鲁医学流派的特色至关重要。
1 齐鲁儒医的形成背景
1.1 齐鲁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山东地处黄河流域下游,是中华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龙山文化起源于此,华夏文化一脉相传,对后世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齐鲁文化著称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春秋战国时期。此时建国于山东地域上的齐、鲁两大国,对促进华夏文化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
1.2 齐鲁儒医的形成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 孔子为鲁国文化的杰出代表,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儒家学说对医学的影响很大,其经典著作《易》之阴阳、《尚书》之五行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石。《史记·儒林列传》载:汉初以《诗》著称者三人,齐鲁有其二;以言《尚书》显名者六人,齐鲁居五;以言《礼》受禄者八人,齐鲁半之;以言《易》得位者八人,齐鲁得六;以治《春秋》至大官者八人,齐鲁分六。太史公曰:“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细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山东之所以自古多良医,是以山东自古多文学之士,谓之“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
2 齐鲁儒医形成和发展脉络
2.1 春秋两汉 林则徐曰:“文是基础,医是楼。”中医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和基础。春秋战国时,齐、鲁两国皆为文化发达之地,数千年历尽沧桑,经久不衰,以其根深蒂固故也。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秩序更迭变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繁荣的文化背景为中医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在学术交流的鼎盛时期,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首的儒学,与医道不断发生着碰撞交流。西汉初期,齐国名医如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显学,亦成为医家兼修之学。儒医交融,兼修相长,儒医兼修、通儒知医之士不乏其人,仓公即是其中之一。《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言仓公虽事医,亦善儒学。淳于意以医闻名京师长安,名垂青史2 000 余年,其所著之医案,开古今中外医案之先河。
2.2 魏晋隋唐 魏晋隋唐以来,非精儒者难列廷位,诸如王叔和、徐熙等医家均系朝廷官员,儒学造诣均颇深。晋代王叔和“性度沉静,通经史”,为儒学修养极深之人,其编撰《脉经》一书不仅论脉言医,更有着深厚的医学人文精神,展示了其遵循“仁义孝亲”的人生价值观,践行着“仁爱慈悲”“利泽生民”的儒医价值观[1]。南北朝时期的徐熙医学家族,世传7 代,13 人,历时200 余年,医术噪于朝野,名闻天下。徐之才即为其中之一,其行岐黄之道,博经史,通《礼》《易》,解天文,精医术,才学之至,名噪文苑,堪称一世宏才。法医学家和凝,举进士,名列十三,官至太子太傅,著有《疑狱集》10 卷,为验伤验尸、评判冤狱发挥很大作用。羊欣出自仕官之门,其博览善书,兼善医术,好黄老之学。魏晋隋唐的齐鲁医家儒学功底深厚,文人知医或文人业医者数量增加,“儒医”成派已现端倪。
2.3 宋代 宋代儒学盛世,儒医合流。“儒医”一词经常出现在医药或非医药典籍中,被世人称道和尊崇。《宋会要辑稿·崇儒》曰:“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2]被誉为儿科圣手的钱乙,博览群书,晚年仍手不释卷。其内外兼修,知行合一,出仕朝廷,官至太医丞,既服务于达官显贵,也救治黎民百姓[3]。同样与钱乙齐名的宋代医家董汲,弃儒从医,善治小儿病,“尤精于豆疹”,为小儿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中医学在宋代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由儒及医、儒医融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4 金元 金元时期少数民族当政,在文化和医学上均学习中原文化,学术环境较为宽松,有利于医学创新。鉴于外族统治的歧视和耻于事夷的儒家风骨,齐鲁儒士们本着“济天下、利苍生”的愿望,大量进入医学领域,以实现济世救人的理想抱负。历史上首位注解《伤寒论》的医家成无己,家世儒医,性识明敏。医学博士纪天锡,早年弃儒从医,以医名世。程鹏善医卜,乐施与,于自家建立书院,资助求学者。元代李浩,其父及祖父皆以儒显,李浩喜医方术,治病如神,其子初习儒术,奉旨承父业,掌管御药局。金元时期的齐鲁名医多为儒者出身,均有着良好的儒学底蕴。
2.5 明清 明清时期,齐鲁儒医群体成为从医者之主流中坚,不仅在数量上远超前代,在身份认同、医典道统、医疗执业、济世关怀等方面均体现出鲜明的职业及群体特征[4]。此时期涌现出大批儒医,如“世传儒业,敏而好学”的瞿玉华、“弃举子业,因母习医”的张星纬、“弃政习医,济世活人”的王象晋、“身兼六艺,以文治医”的王玉珂等,皆卓然杏林,声名远播,影响深远。还有诸多儒医医家不胜枚举,其中,齐鲁儒医中极具名气的当属刘奎与黄元御。刘奎自号“松峰老人”,贡生出身,精于伤寒温疫诸症,师古而不泥古,著有《松峰说疫》,且擅长古文诗词。黄元御出身诗书门第,少有奇才,且负大志,初攻儒术,后因目病误治,遂弃儒学医,以其医术精湛、治多奇验而名闻乡邑。由此看出,习儒成为明清医门之径,故明清时期医儒关系以互融互显为主流[5]。
3 齐鲁儒医的主要特点
3.1 深受孔孟思想影响 齐鲁大地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其儒家文化底蕴深厚且氛围浓厚。齐鲁医家们在思想上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行事上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道准则,具备深厚的经、史、子、集文化基础。齐鲁儒医们受教育水平相对于其他地区的儒医更高,多数有着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儒学根基,具备极强的阅读和理解能力[6]。有很多医家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便深受儒学的影响,如生于小仕宦之门的瞿玉华家族,世传儒业;张銮幼承家教,师事诗书世家贾振基;黄元御生于诗书门第,其祖上为名门望族,自幼勤奋好学,聪慧过人,自云:“诸子百家之论,率过目冰消,入耳瓦解。”足见其博通经史,才华横溢。
3.2 善于学习他人长处 医圣张仲景云:“勤求古训,博采众长”。历代医家皆以仲景之言勉励自己,齐鲁儒医们亦是如此。如清代医家刘奎,博采历代名家之说,善于向当时名家请教,加之平素留心搜集民间疗法,故对于疫病怪疾,以简便良方及针灸奇术皆能奏效。再如高宗岳,出身于三世医家,自幼喜读医书药典,精心研读历代医籍,是时西学东渐,遂兼习西医,故其学识宏富,术兼中西。马益良出身世代书香,博通经史,工诗词,擅书法,精医术,淹贯诸家学说。荆中允学识渊博,才思敏捷,其对药物的研究能融会百家,博采众长,除推崇《神农本草经》外,对历代各家本草之长,均能如实评价并取其精华。由此可见,齐鲁儒医们涉猎百家,广撷博采,为齐鲁医学乃至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3.3 擅长著书立说 齐鲁儒医们不仅有着丰富的临证经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有助于将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很好地总结下来以传后世。他们文笔优美且擅长理性思维,可及时总结临证经验,使之上升成学术理论,有助于中医学的发展和传播。齐鲁儒医们勤于著书立说,著作甚多,其中,徐氏家族著述较多,计43 种,222 卷,涉及杂病、妇科、儿科、方药、针灸等。其中徐叔响著书16 种,达160 卷之多,历史上颇为少见,堪称医林之一绝。再如荟萃古今名医学说、集其大成为一家言的“一代宗师”黄元御,亦可谓“高产作家”,其著作共13 部,其中医学著作12 部,现已出版11 部,是中国传统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完整注解《素问》《灵枢》《神农本草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的医家[7]。
3.4 精于治疗儿科疾病 齐鲁医家医术精湛,各科均有涉猎,经查阅古籍发现:齐鲁儒医们多为儿科专家,尤擅长治疗痘疹、斑疹等,活小儿无数,并留下诸多著作及名方。其中最具名气的当属“儿科圣手”——钱乙,是我国中医儿科较早的奠基人,其著作《小儿药证直诀》及创制的六味地黄丸、异功散、益黄散、导赤散、泻青丸等方剂名垂千古,功效卓著。正如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中云:“小儿经方,于古罕见,自乙始别为专门……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再如与钱乙齐名的宋代儿科专家董汲,弃儒从医,善治小儿病,尤精于痘疹,其著有《小儿痘疹备急方论》,对小儿痘疹的证候作了简要说明,并附方17 首,为我国较早的痘疹专著。诸如此类儿科专家还有韩茂贵、王廷宾、荆中允等30 余位医家,不胜枚举。
4 结 语
“儒医长河,群星璀璨”,纵观齐鲁儒医的历史沿革,从先秦到明清经历的漫长历程,儒医辈出,薪火相传,齐鲁儒医这一群体的诞生及其文化影响为中医学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儒及医,代有传承。“儒医文化”是山东地区中医药的特色标签,儒、医一脉,仁爱济世,传承千载,山东的儒医文化已经成为地域医学的特色标签。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们应紧抓中医药发展史上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传承并创新儒医文化,为中医药学发展注入更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