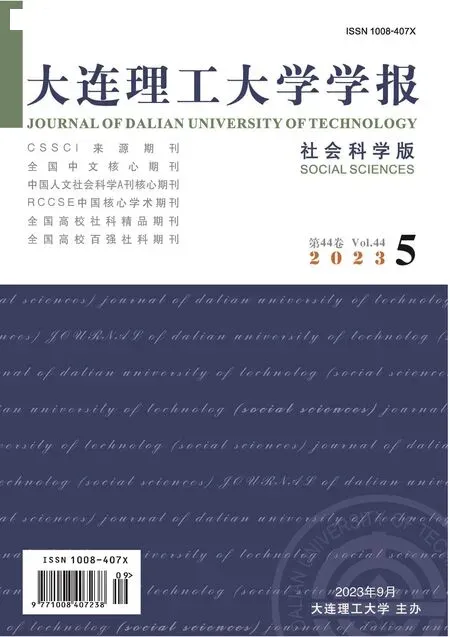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数字劳动
——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
邓 伯 军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网络空间公共安全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1106)
一、引 言
在所谓的“知识信息”社会中,主导技术已经从传统的工业技术转向计算机技术(Computer Technology)、互联网技术(Internet Technology)、云计算(Cloud Computing)、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大数据(Big Data)等现代信息技术,技术的数字化与生产的社会化日益融合,数字化劳动、数字化资本、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流通、数字化消费成就了数字经济新形态。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切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过程,并对资本主义的劳动与资本关系进行重构,劳动的数字形态和资本的数字形态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回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的结构性矛盾,就构成政治经济学批判面对的重大课题。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产业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将生命主体的生产性劳动界定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前提,“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而另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1]224-225。这样,劳动就成为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只有生产性劳动才能创造出资本的生产力和资本的价值关系,正是生产性劳动完成了从非商品生产关系向商品生产关系的转化,搭建起以物化逻辑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建制,这种以物化逻辑为基础的社会建制确立了生命主体的独立性,却也因外在化对象与生命主体的分离造成了物的拜物教。信息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是以数字劳动为基础的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数字资本主义使劳动的普遍性进一步抽象为数据算法,劳动的物化逻辑变身为劳动的数据算法,社会生产关系不再被还原为物,而是被还原为一种数值关系。机器大工业时代以物为中介的社会建制变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以数据为中介的社会建制,这种用数据算法所架构的资本主义社会建制以数字化形式有效而精准完成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却也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拜物教形式——数字拜物教。从以一般劳动为核心的机器劳动到以一般数据为核心的数字劳动,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处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问题域之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依旧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题。
二、基本概念界定
劳动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主导生存方式,劳动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起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阐述了劳动的双重性及其张力关系,通过劳动的链条将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连接起来,实现了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向变革世界的实践哲学的历史性转变。数字劳动是信息时代的主导生存方式,数字技术对劳动的全方位渗透,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劳动形式、劳动成果均以数字化形式表现,就需要在劳动价值论视域下对数字劳动概念进行再解读和再解释。学术界数字劳动理论研究主要有“受众劳动” “非物质劳动” “物质劳动”3种研究范式。“受众劳动”范式认为数字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由单一性转变为多重性。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Smythe)首次提出“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ur)概念,认为广告商从大众传媒公司购买到受众劳动力,受众群体为广告商进行免费劳动。“寄生于广告的大众媒体的受众是一种商品,他们被不自觉地出售给广告商们,原因在于他们能为广告商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2]达拉斯·斯迈兹认为,所有的非睡眠时间都构成劳动时间,受众劳动是工厂劳动的延伸。哈里·克莱弗(Harry Cleaver)认为,社会将变成生产社会,工厂将变成社会工厂,工人将变成社会工人,社会关系只剩下生产关系[3]。“非物质劳动”范式主张数字劳动是创造知识、信息、沟通和情感反馈的文化劳动。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首次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并将其界定为“生产商品的信息与文化内容的劳动。”[4]蒂奇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首创“数字劳动”的概念,认为数字劳动是“免费劳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是指知识性消费行为转化成为额外的生产性行为。“免费劳动”是自愿行为和无酬劳动同在,享受和剥削并存。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认为非物质劳动意指创造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形式,劳动形式的变化使生产性时间与非生产性时间越来越难以区分。他们指出:“在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主义下,工作日和生产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的划分越来越不明显。”[5]145“物质劳动”范式强调数字劳动的物质属性,数字劳动受到资本的控制与剥削,依然具备劳动的二重性特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重新审视信息时代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问题,认为在数字媒体技术和内容的生产中资本积累所需要的所有劳动都属于创造数据商品的生产性劳动,同时他也阐述了数字劳动的剥削机制,认为数字劳动是异化劳动,包括数字劳动力的异化、数字劳动工具的异化、数字劳动对象的异化、数字劳动产品的异化。总之,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数字劳动的研究表明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时代的解释力,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野,推进了政治经济学与传播学的融合。同时也要看到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数字劳动的泛化理解,因为依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只有带来资本增值的数字劳动才是真正的生产性劳动。
资本的生产关系是在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劳动者的劳动变成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1]232。马克思不但深刻剖析了机器大工业时代产业资本的生产性劳动本质,而且还前瞻性地提出“一般智力”概念,开启从早期产业资本到知识资本理解的序幕。“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6]数字资本是当代资本主义增殖与运作的新形态。学术界对数字资本的核心本质的探讨主要有“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集体智力”(Collective Intellect)、“一般数据”(General Data)3种代表性研究路向。“一般智力”是诸众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由认识、技术和知识构成的总体性的非物质关系,这种非物质关系一方面让诸众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为资本主义社会机器运行服务;另一方面也汇聚成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控制的潜能,让诸众具有了反抗资本权力的砝码。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以白蚁为例在个体智力和“一般智力”之间做出类比,“在蚁群中,单个白蚁与其他白蚁之间有信息素交流。尽管没有一只白蚁拥有很高的智力,但白蚁群构成了一个无中心的一般智力的体系。这就是建立在交流基础上的蚁群智力。”[5]91“集体智力”是诸众自身的思想能力和潜能本身,是以“认知范式” “对话演绎” “语言游戏”等方式存在于活生生的主体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中。维尔诺(Paolo Virno)认为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的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一般智力”,而是以“集体智力”为主导的“认知能力存储系统”,在后福特时代,集体智力“包含了形式和非形式性知识、想象、伦理倾向、心智和‘语言游戏’”[7]。在维尔诺看来,“集体智力”已经超越了客观化的知识力量,而成为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建制的普遍性的本体力量。“一般数据”是数字资本主义中资本的一般形态,是由数据和云计算形成的庞大的关联体系构成的一种客观性的力量,并被数字资本家作为榨取利润的新的客观性力量。蓝江认为,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一般数据基础上架构出来的体系。一般数据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事实,成为最一般性的量,如果货币构成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通货,那么,一般数据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最普遍的价值。信息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都被它所中介、所赋值、所架构”[8]。质言之,随着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物性的劳作塑形转变为信息时代计算机虚拟平台上的代码的编程设计,对资本核心本质的探讨从生产性劳动走向“一般智力”,试图通过“一般智力”而不是通过生产性劳动来发现资本对生命政治的霸权,这势必陷入概念预先设定的思维框架中。事实上,数字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攫取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内核并未根本改变,因此,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依然处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逻辑框架之中。
三、数字劳动条件
正像马克思所言,“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1]215交换价值确立的基本前提是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交换价值本身和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的前提是:他人的劳动能力本身是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活的劳动能力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或劳动能力对自己的客体性的关系——成了对他人的财产的关系;一句话,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成了对资本的关系。”[1]505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通过对私有产权的确证,完成了劳动自身与其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过程,劳动者只有通过劳动以劳动的客体化形式来取得和证实自身的社会权利,劳动者成为丧失劳动的客观条件但拥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劳动的客观条件获得独立的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价值形式,表现为统治和支配活劳动的对象性劳动的权力。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以物权的形式来确证了劳动主体的独立性,任何劳动主体都必须以物的形式才能在市场化的世界中得以存在,这样,具体生命的劳动主体就被物化为劳动力,才能获得一种能够与他人进行交换的平等权利。劳动主体的独立化确实把劳动主体从人对人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不管这种统治和从属关系的性质是氏族制的、农奴制的或是封建制的,劳动主体毕竟以物化的形式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同时也能发展出“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之间的生产关系”[1]114。也就是说,劳动力所有权的私有制建构对于瓦解等级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对于“平等观念的形成和平等原则的产生也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9]。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以物权的形式确证了劳动条件的独立化,劳动的客观条件以价值的形式,与那些已经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并与成为交换价值生产者的劳动力相对立,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的分离过程表现为劳动客观条件本身的独立化过程。劳动条件的独立化过程“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它自身创造出来的东西,既表现为劳动能力自身的客体化,又表现为它自身被客体化为一种不仅不以它本身为转移,而且是统治它,即通过它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1]444-445总而言之,生产性劳动一手创造了纯粹主体的劳动者的雇佣身份,也就创造了自己的贫穷,另一手创造了自身的对立面——资本,也就为他人创造了财富,双手创造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和支配权力。“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1]447这就是“物的依赖阶段”的劳动主体与劳动客观条件的二律背反。无论是以物权形式对劳动主体独立性的确证,还是以物权形式对劳动条件独立化的确证,都是以物为中介所架构的社会建制,所谓“物”并不是具体的物,而是物的抽象形式,也就是说,能够用量化指标计算的可公度性的物,表现为物的价值形式,即价格,而价格则是物的交换价值的体现。更为准确地讲,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物化,而在于量化,是物的量化形式架构了机器大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建制。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以数字技术重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以“非物质劳动”为特征的数字生产方式,实现从劳动主体到劳动条件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劳动主体和劳动条件都被数字资本重新组织和架构,为数字资本所重新定义和赋值。这就要求依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准确界定数字劳动的生产性质。依据马克思生产性劳动的基本标准,“只有直接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而消费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10]520。数字劳动不是互联网用户的网页浏览、网络社交、网络购物、网络消费等所谓的“玩劳动”,互联网用户的“玩劳动”制造的“数据”充其量是具有潜在使用价值的数据资源,而这些数据资源绝大部分属于非结构化的数据资源,需要互联网企业依据互联网数据标准与规范,对这些非结构化数据资源进行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系列结构化处理操作,从而使杂乱无章的非结构数据成为真正具有交换价值的结构化数据。因此,真正的生产性的数字劳动是指互联网企业对数字进行加工的生产劳动,是在互联网背后从事对数据资源进行采集、管理、清洗、规范、挖掘、整理、分析的价值创造的生产劳动。因此,“把互联网用户行为过度解读为给资本主义生产带来剩余价值的剥削性劳动,而忽视了互联网产业背后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力投入,使其数字劳动理论不能科学地解释互联网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与剩余价值问题。”[11]数字资本主义以数字资本重塑了劳动主体,生产性数字劳动是生产数字资本的劳动,是数字劳动过程中实现数字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数字劳动,是在数字劳动过程中为数字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字劳动。数字劳动主体之所以作为生产性劳动者,是因为数字劳动者在对数据的采集、管理、清洗、规范、挖掘、整理、分析过程中再生产出了数字资本,而数字资本家正是通过占有数字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数字劳动的生产性逻辑只会再生产出雇佣身份的数字劳动者本身,而绝不会使数字劳动者成为资产者,也就是只会使支配数字劳动的权力增大,只会使数字资本的生产力提升。“数据商品的‘交换法则’与数据私有化及其价值增殖的资本的‘生产逻辑’,那么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会形成更大的、更隐蔽的‘社会权力’,必然会带来对数字劳动者更深层面的规制与异化。”[12]数字资本主义以数字资本重塑了劳动条件,物理化的劳动条件被数字化为数字空间存在,数字化平台、数字化资源、数字化工具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数字劳动条件,数字劳动者登陆的数据平台是他人的数据平台,加工的数据原料是他人的数据原料,运用的数据工具是他人的数据工具,数字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数据原料、他人的数据工具和他人的数字劳动的结合,表现为他人的数字财产,即数字资本。数字劳动条件是数字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的,再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数字劳动条件的客观存在,而且是这些数字劳动条件作为独立的价值,即属于数字资本家的价值,而同数字劳动主体的生产性劳动相对立的存在。因此,并不是数字劳动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数字劳动主体的实现条件来实现,相反,数字劳动主体仅仅作为把数字劳动条件当作与数字劳动主体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来增殖和保存的条件,而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数字劳动主体作为与数字劳动条件相分离的纯粹的主体则需要出卖自己的数字劳动能力才能得以生存。无论是数字资本对劳动主体的重塑,还是数字资本对劳动条件的重塑,都是以数据算法为中介所架构的标准化处理,数字技术的发展加深了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程度——在时间上强化,在空间上扩大。最终结果就是数字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可能会减少,但是无酬劳动时间却呈现增长趋势,数字资本家在剩余价值分配中所占相对比重呈现增大趋势。这样,数字技术就开拓了资本积累和增殖的新场域,以数据算法所担保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的有效治理成为现实。数据的运算规则真正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关系的支配性力量。
四、数字劳动产品
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13]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产品才会转化为价值形式,劳动产品因成为价值形式而成为资本,劳动的生产性也会变成资本的生产力。“劳动(活的、合乎目的的活动)转化为资本,从自在意义上说,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因为这种交换给资本家提供了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以及对劳动的支配权)。”[1]267资本是作为与劳动对立的资本,劳动是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劳动,“资本和劳动就只是作为不同的物质存在方式上存在的相等的交换价值来相互交换”[1]282。资本以劳动作为前提,资本不是从来就是资本,只有劳动者本身丧失交换价值,也就是劳动者是自由工人,资本才能把劳动作为纯粹的使用价值,对象化的劳动才具备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也就是说,资本只有把劳动作为非资本存在,即把劳动的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资本通过获得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使自身具备了增殖的可能性。“作为奴隶,劳动者具有交换价值,具有价值;作为自由工人,他没有价值;只有通过同工人交换而得到的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才具有价值。不是工人作为交换价值同资本家相对立,而是资本家作为交换价值同工人相对立。工人没有价值和丧失价值,是资本的前提和自由劳动的条件。”[1]249劳动以资本为前提,只有劳动产品作为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时才转化为资本,才表现为统治和支配活劳动的资本,才能成为与劳动者相对立的独立的异己力量。也就是说,劳动产品以自为存在的价值形式表现为他人的财富,成为支配劳动者的统治力量。劳动者注入生命力量的对象化成果既表现为劳动能力自身的客体化,又表现为通过它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14]157扬弃劳动产品对劳动主体的异化必然要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来实现,即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来扬弃异化问题。“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4]189
数字商品是由互联网企业的劳动者运用数据技术对由数字终端用户产生的杂乱无章的非结构化的数据原料进行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之后的结构化的数据产品,被数字资本家所占有,用来为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效率化配置提供市场服务,使数字资本家完成对整个数字资本运转链条的掌控,成为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数字商品的完整形态。数字商品不等于数据原料,数字商品是对数据进行价值化提炼后以数据集合形式存在的信息资产,数字商品具有5V特征: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价值)、Veracity(真实性)。在互联网上每时每刻都进行着产生数据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但其目的并不是要生产数据商品。网页浏览的目的是休闲,而不是生产休闲数据;网络游戏的目的是娱乐,而不是生产娱乐数据;网络购物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生产消费数据;网络聊天的目的是社交,而不是生产社交数据;网络支付的目的是商务管理,而不是生产金融数据;网络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而不是产生学习数据。因此,数字商品的价值不是由达拉斯·斯迈兹笔下的互联网用户“受众”创造的,而是由互联网企业的数字劳动者创造的。“数据商品的生产过程,即从数据库的建立到数据的清理、分类,再到数据的挖掘,甚至是机器学习算法的编写,都需要耗费相当长时间的人类劳动。”[15]数字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商业资本提供商业营销和市场咨询服务,为产业资本提供生产计划和产品结构咨询服务,为金融资本提供市场预期和风险投资咨询服务,为政府机构提供产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为事业单位提供行政职能和公益职能咨询服务等。在数字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数字劳动者不仅在必要劳动时间再生产出自身劳动力价值,而且在剩余劳动时间为数字资本家无偿生产剩余价值,更严重的是数字资本家借助“摩尔定律”提高工作效率榨取数字劳动者的相对剩余价值。这体现了数字资本家对其所雇佣的数字劳动者的剥削关系。这种新型的数字剥削仍然处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问题域之中。数字资本家利用其数字技术优势,将数字产品作为资本从深度和广度上对其进行综合开发,数字信息就在数字空间的虚拟流动,形成一般数据的流动空间,数据的流向决定着资本的流向,最终将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以一般数据形式被整合纳入数字秩序框架之中,形成以一般数据为核心、以数字产品为载体的完整的数字产业链条。这就是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动被数字资本所主宰的命运,这是对数字劳动更深层次的异化,即数字异化。当然,“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14]182因此,就要建立数字资本的公有制架构,以数字资本的公有制来扬弃数字资本私有制对数字劳动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
五、数字劳动本身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因劳动本身的客体化发展而历史地生成的,劳动若缺乏任何客体,劳动只能作为纯粹的主体,劳动就是绝对的贫穷,对象性财富就在劳动视野之外;劳动只有收获客体,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劳动具有价值的可能性,才能成为对象性财富的源泉。劳动本身的客体化使劳动者凭借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的那种对象性交换,以物权方式确证了劳动者独立的主体地位。“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只是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的那种对象性的交换,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1]196但是,这种以物权担保的人权却是以“物化”为代价的,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是确证自己,而是创造出他自己的对立面;劳动成果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人;劳动者越是努力,他越是贫穷。劳动者本来是通过劳动创造物化世界来确证自身的独立性,但是劳动所创造的物化世界却反过来成长为奴役劳动者的现实力量。劳动本身的客体化也调动了潜藏在劳动本身上增殖价值的可能性,催生了与劳动本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性的资本世界的形成,通过劳动本身创造力的持续释放,对象性的资本世界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庞大的存在。“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1]444也就是说,劳动本身的客体化通过释放劳动的创造力,劳动能够创造出比自身劳动力价值更大的价值,使资本能够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来获得自身生产力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成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也就是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手段。劳动本身的客体化过程是一个实现现实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去现实性的过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述,“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观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劳动作为创造价值或增殖价值的单纯可能性返回到自身,因为全部现实财富,现实价值世界以及劳动本身得以变为现实性的现实条件,都成了同它相对立的独立的存在。孕育在活劳动本身中的可能性,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劳动之外,但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1]446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要通过劳动把自身的劳动能力生产出来,同时还要生产出同活劳动本身相对立的资本;反之,资本家要把资本家自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还要生产出与其相对立的活劳动本身。“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等等。”[1]450-451
数字劳动的客体化创造了数字劳动本身,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对立面——数字资本。正是数字劳动再生产自己的对立面——数字资本,从而也再生产出数字劳动本身。这就是数字劳动的自我异化过程。数字劳动的客体化推进劳动本身的升级换代,数字技术作为先进的生产力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劳动方式,混杂了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分化了实体劳动和虚拟劳动,模糊了雇佣劳动和免费劳动等。数字技术改变了数字劳动创造价值的时间条件,模糊了劳动时间和休息时间,模糊了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模糊了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等。数字技术改变了数字劳动创造价值的空间条件,模糊了劳动场所和生活场所,模糊了私人场所和公共场所,模糊了实体场所与虚拟场所等。在某种意义上,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从传统的基于雇佣劳动的福特制生产模式向基于隐性劳动的后福特制模式转变。从毛里齐奥·拉扎拉托以“非物质劳动”对劳动方式变革的指认,到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以生产性时间和非生产性时间的边界模糊对劳动时间变革的确证,到霍华德·莱因戈德(Howard Rheingold)以“电子小屋”[16]对劳动场所变革的描绘,都能看到后福特制时代数字劳动本身的自由度扩大,劳动方式的自由、劳动时间的自由、劳动场所的自由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不限方式、不限时间、不限空间的数字劳动本身就是新型的奴役机制,从邱林川的“i奴”(I Slave)[17],到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的“睡眠的终结”[18],到马里安·克莱恩(Marion G.Crain)等的“离身劳动”(disembodied labour)[19],我们都能看到数字劳动本身的异化,数字资本越过雇佣劳动界线染指免费劳动,越过工作时间界限侵入休息时间,越过工作场所边界进入生活领域,数字资本几乎将劳动主体的全部社会生活领域都纳入资本管辖范围之内。数字劳动的客体化创造了强大的数字资本世界,数字技术作为先进的生产力深刻变革了资本的存在形态。数字技术改变了数字资本的活动空间,数字资本凭借数据技术优势,对虚拟的网络空间的圈地,对公共数据的瓜分,对私人数据的侵占,形成一极是“信息富有”和“数据烟囱”,另一极是“信息贫困”和“数据荒漠”,造成严重的数字鸿沟现象。数字技术改变了数字资本的运行方式,数字资本遵循从数据采集到数据处理再到数据应用的循环路径,数字资本凭借其数据聚集优势,掌握数据信息的准确定位和运行方向,在互联网空间实现数据资源的精准配置的同时,也会形成数据的垄断和数据的操纵,诱发新的剥削形式和异化形式,甚至成长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支配性力量。数字技术改变了数字资本的生产方式,数字资本建立了以一般数据为核心的数据资产管理架构、数据资本模型架构、数据技术平台架构等数字产业链条,数字资本成为数字寡头。这样,一极是掌握了数字平台的数字寡头,一极是达拉斯·斯迈兹(Dallas Smythe)所说的“受众”,而中间的数字劳动者则沦落为尼克·戴尔·怀特福德(Nick Dyer-Witheford)所提出的“赛博无产阶级”(Cyber-Proletariat)[20]。如何解决数字劳动客体化形成的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的两极分化现象?单纯的数字技术批判无法命中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的结构性难题,只有重新回到数字生产领域,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寻找数字剩余价值积累的秘密,探寻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矛盾的解决方案。这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解剖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意义。
六、数字劳动关系
在资本与劳动的等价交换中,资本换来的是能够创造价值的活劳动的使用价值,也就是换来了劳动的生产力,这种劳动的生产力能够使资本保值和增殖,从而变成了隶属于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劳动换回的是劳动的生产力的价值,这种劳动力价值能够实现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家作为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作为劳动力所有者,作为买者和卖者相互对立,他们在法律意义上是独立的权利责任人,资本家和工人只是平等的商品交换者,双方不存在任何统治和服从的隶属关系。从表面上看,资本与劳动是一种形式上的隶属关系。随着劳动者对自身劳动的生产力的所有权的让渡,“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1]450劳动从交换过程进入生产过程,意味着劳动的生产力成为可变资本,劳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不以劳动者意志为转移的条件,表现为资本的存在形态;劳动的科学知识表现为以社会发展精神成果应用于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的运用;劳动的生产成果表现为他人的财富,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连同劳动一起并入它自身。”[10]539也就是说,从活劳动的生产力转化为对象化劳动的生产力,活劳动表现为对对象化劳动的实质意义上的隶属。“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10]385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深刻地变革了劳动方式,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开始表现为社会劳动过程,一方面是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劳动的生产力为资本的生产力发展奠定基础,劳动的生产力为资本提供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是资本的生产力表现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发展推进了劳动的生产力的社会化,资本的生产力为扬弃劳动对资本的隶属提供现实条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本身就蕴涵着扬弃雇佣劳动的因子,意味着就会发生从雇佣劳动走向社会劳动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其现实条件,为之提供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这个由革命发展起来的与工人相对立的劳动生产力、生产条件与交往关系中,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就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10]547
数字技术的进步给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带来新的变化,数字资本家就是掌握能提取、控制、分析各种数据的数字平台企业。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将其划分为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产品平台与精益平台5种数字平台,“平台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产生,并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21]。数字劳动者就是基于数字平台对由互联网终端用户所产生的各种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进行加工和再加工、处理和再处理、分析和再分析的数字劳动者。这主要是互联网行业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人员所从事的技术性劳动,主要包括软件开发、程序编制、网站设计、数据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安全、数据处理、数据挖掘、数据分析等。数字劳动者是受雇于数字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数字劳动者通过自身数字劳动的生产力推动数字资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同时也使数字劳动为自身生产力所创造的数字资本所异化;数字资本家通过数字资本的生产力推动数字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化水平提升,同时数字资本的生产力为扬弃数字劳动的异化创造条件。互联网终端用户的劳动即“受众”的劳动属于消费性活动,而不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数字空间上的每一次网上冲浪,每一次网页浏览,每一次网络游戏,每一次网络购物,每一次网络聊天等等都在无形中为数字资本家提供数字劳动,这些数字劳动所形成的绝大部分属于离散型数据,只有被数字资本结构化处理后才会形成可伸展、可预测、可共享的数据资源。因此,“从整个数据产业链可以看出,互联网用户劳动制造的‘数据’只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原材料’,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性劳动,要使这些原材料经过加工变成可按照不同目的分类打包销售的‘数据商品’,则需要大数据完整产业链的生产与加工。”[11]47
总而言之,数字资本主义是基于雇佣劳动的社会建制,虽然产业资本家变成了数字资本家,产业工人变成了网络劳工,工业产品变成数字产品,但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本质没有改变。数字劳动是在数字资本的逻辑框架下进行的,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就发生在数字商品的创造过程中,数字劳动已经成为数字资本的要素,是数字资本实现价值增值的手段,是数字资本剥削逻辑在虚拟数字空间的延展。因此,就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回应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结构性矛盾,创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概念和分析范式,彰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面向数字社会的学术生命力。
七、结 语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消解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劳动方式,生成信息时代的数字劳动方式,数字技术解构产业资本的存在形态,生成数字资本的存在形态。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所言,“一方面,不断崛起的数字资本主义强有力地推动资本的重新积累;另一方面,它也有可能引发天翻地覆的矛盾与张力。”[22]数字异化和数字垄断等引发的社会剥削和社会压迫归根到底是资本逻辑全面扩张所带来的恶果,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激化的结果,集中体现在数字生产的社会化与一般数据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依然是剩余价值规律。正如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3]目前,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暴露出从数字劳动条件、到数字劳动产品、到数字劳动本身,再到数字劳动关系全过程异化,数字劳动条件包括各类数字平台、数字工具、数字资源等本来是用来确证劳动者自身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却沦落为数字劳动者谋生的手段[24]。数字劳动产品包括各种数字终端、数字资产、数字服务等本来是数字劳动者的自身本质和内在需要的实现,却表现为数字劳动对象的丧失和数字劳动者的非现实化,数字劳动者与自身的数字劳动产品之间形成一种异己的关系。数字劳动本身的客体化进程激活了数字劳动的创造力,实现了数字财富的爆发式增长,却也创造更为精准的数字资本的控制机制,沦落为智能化的数字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数字劳动关系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当代资本主义表现形式,数字生产力诱发了数字劳动关系的新的剥削形式和异化形式,但是数字生产力的进步也为数字劳动关系的解放创造了条件。总而言之,要克服数字劳动的异化,必须“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观关于资本与劳动的结构性矛盾依然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键。因此,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剖析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和数字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数字劳动异化和数字资本剥削问题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