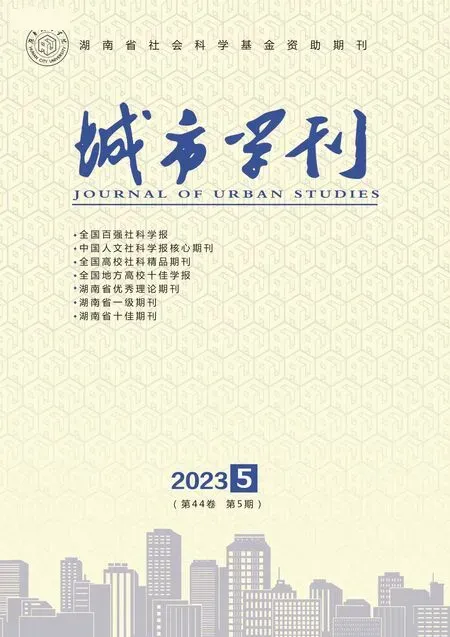湘桂边苗族汉话的完整体标记及其来源探析
沈 敏
(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长沙 410081)
一、湘桂边苗族汉话概述
本文所谓“湘桂边苗族汉话”主要指分布于湖南与广西交界处绥宁、城步、龙胜、资源等县青衣苗人所说的一种目前系属尚不明确的特殊汉语方言。各县乡苗族人对该方言自称不一,主要有“苗话”“人话”“平话”“伶话”等说法。虽自称不同,但这些散落在不同县乡的苗族人使用的汉语方言极有可能是同源的。李蓝、胡萍、姜礼立、王巧明等均认为应是同一方言的不同变体。[1-4]
关于这种汉语方言的性质,我们基本同意李蓝的说法,认为其是湘桂边青衣苗人弃用苗语转用汉语且不断迁徙的结果,是一种少数民族汉语,可简称为“民汉语”。其语言的整体面貌已是汉语,但语言持有者不是汉族,语言的深层还保留着一些原语言的成分。从语言区域来看,这种“民汉语”处在湘桂边多种汉语方言的包围之中,语言接触频繁。长期以来与湘语、西南官话、赣语等深度接触,还可能受到湘南土话的影响。李蓝综合考察城步青衣苗人话的语音系统、社会属性及底层现象后指出,这种特殊的汉语方言既不能归入吴、闽、粤、客、赣、湘等传统的南方方言,也不能归入平话或湘南土话。[1]
本文对苗族汉话体标记的调查涉及绥宁关峡、城步兰蓉、龙胜伟江、资源车田等四个乡镇。要统一称说各点苗族人所操的这种具有同源性质的汉语方言,借用某点自称的“平话”(如绥宁关峡)或“人话”(如龙胜伟江)显得代表性、概括性不够,且其中“平话”易与一般意义上的广西平话相混;“人话”之名虽是多个点的自称,但也显得颇为奇怪,甚至容易引发语言歧视的误解。多个县乡的苗族人也自称其语言为“苗话”,“苗话”虽覆盖性强,但易与“苗语”相混,不能揭示其作为汉语方言的语言身份。鉴于该语言的性质是湘桂边各地苗族人所转用的汉语方言无疑,为称说方便,姑且将其合称为“湘桂边苗族汉话”。按照“一县一点”原则,本文选取绥宁关峡、城步兰蓉、龙胜伟江、资源车田等4 个点进行调查,基本覆盖湘桂边苗族汉话各个片区。
二、湘桂边苗族汉话主要的完整体标记①
据调查,②湘桂边各苗族汉话点使用频率最高的主要完整体标记如下:绥宁关峡为“呱[kuo33]”,城步兰蓉为“呱[kuɑ44]”,龙胜伟江为“哇[uɑ44]”,资源车田为“咧[le44]”。湘桂两地苗族汉话的完整体标记有差异:广西境内伟江和车田差别较大,一个用“哇”,一个用“咧”;湖南境内关峡和兰蓉两个苗族汉话点均用“呱”,只是语音上稍有差异,与绥宁话、城步话、新化话等老湘语的完整体标记几乎是一致的。这些标记均表示事件的完成或动作的实现,功能上接近于普通话的词尾“了”:
(1)关峡:昨日我买呱五本书。昨天我买了五本书。
(2)兰蓉:我打烂呱一只碗。我打破了一个碗。
(3)伟江:你临时食哇药,食不得茶。你刚吃了药,不能喝茶。
(4)车田:我食咧夜饭。我吃了晚饭。
在句法位置上这些体标记一般紧跟动词,但伟江苗族汉话的标记“哇”有一种较特殊的句法位置是其他苗族汉话点和普通话“了”所没有的:
(5)伊去北京哇好久哇?他去北京多久了?
(6)我来桂林哇三年哇。我来桂林三年了。
在“主语+来/去+处所宾语+时量补语”的句式中,伟江的“哇”既可位于“来/去”之后,也可位于处所宾语之后,且以位于处所宾语之后为常。普通话这种句式中一般不用“了”,若要用则只能将“了”置于“来去”之后,而不能说:
(7)*他去北京了多久了?
(8)*我来桂林了三年了。
(一)标记的情状及界限特征
苗族汉话中的这几个体标记在用于终结情状时,既可用于达到完成阶段的事件,也可用于尚未达到完成阶段的事件。如:
(9)关峡:上半日我□sai33呱本书,还麻□sai33完。上午我看了一本书,还没看完。
(10)兰蓉:我昨□ti55写呱封信,麻写完。我昨天写了封信,没写完。
(11)伟江:昨日我去望哇场戏,只是冇望完。昨天我去看了一场戏,但没看完。
(12)车田:伊上半日写咧数学作业,但是冇写完。他上午写了数学作业,但是没写完。
以上各句均为尚未达到完成阶段的事件。也就是说,湘桂边苗族汉话的“呱”“哇”“咧”等标记更注重从外部整体上观察动作行为的实现,而不太注重事件是否达到完成的阶段。这一表现与新湘语不少方言,如长沙话、益阳话等使用的完成义标记“咖”不太一样,“咖”不能用于以上这类句子,一旦用“咖”就“不能通过后续句再将事件内部进行分割”。[5]如:
(13)益阳:*我昨日写咖一封信,但是冇写完。[5]
“呱”“哇”“咧”均可用于尚未达到完成阶段的事件,也就是说它们并不像典型完成体那样要求达到有结果或结束的阶段,似乎比湘语中的“咖”更不像完成体而更接近完整体。
从体标记对事件的有界性要求来看,苗族汉话中的完整体标记既可用于有界事件,也可用于无界事件。这一点也与湘语的“咖”不同,夏俐萍指出,现实句中“咖”要求搭配有界事件,体现在句子层面,包括要求有数量短语、强调性时间副词,或用于连续事件等。[5]如:③
(14)长沙:
a.我吃咖一杯水。我喝了一杯水。(有界)
b.*我吃咖水。我喝了水。(无界)
(15)沅江:
a.他将将买咖菜。他刚刚买了菜。(有界)
b.*他买咖菜。他买了菜。(无界)
(16)湘阴:
a.他写咖作业就回去得。他写了作业就回去了。(有界)
b.*他写咖作业。他写了作业。(无界)
以上三例中a 句通过数量短语、时间副词、连续事件将事件有界化,用“咖”是合法的;b句不采用这些有界手段,均为无界事件,用“咖”便不合语法。苗族汉话中的“呱”“哇”“咧”等标记则可以用于无界事件:
(17)关峡、兰蓉:我食呱水。我喝了水。
(18)伟江:伊写哇作业。他写了作业。
(19)车田:伊要咧菜。他买了菜。
在这一点上,苗族汉话的完整体标记与普通话词尾“了”以及湘语中的另一个完成义标记“哒”相似。
此外,从现实相关性来看,“呱”“哇”“咧”等均可用于“他去年学了几个月,后来又没学了”一类的句子。以关峡、伟江为例:
(20)关峡:伊去年学呱几个月,背□san22麻学呱。他去年学了几个月,后来没学了。
(21)伟江:伊去年学哇几条月日,背哋冇学哇。他去年学了几个月,后来没学了。
句中“学呱/哇几个月”这一事件在基点时间之前已经发生和完成,但并不强调对现在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说不具有典型完成体所包含的“现时相关性”。这一点与湘语“咖”及普通话词尾“了”相似。
(二)标记的语法化程度
范晓蕾采用“句法适配度、使用强制性、隐去自由度”三个参数来确定词尾“了”的性质,认为以上参数与“了”作为成熟体标记呈现正相关。[6]句法适配度指词尾“了”搭配动词及宾语的范围,范围越大句法适配度越高。使用强制性指某环境表有界事件又无句尾“了”时必须加上词尾“了”,且词尾“了”不能替换为动相补语。隐去自由度指词尾“了”隐省后不改变句子的命题义与合法性。我们也可从这几个参数来看苗族汉话完整体标记的语法化程度。
1. 句法适配度
一般认为,“动词—结果补语—动相补语—体标记”是汉语体标记演化的主线之一。董秀芳认为,汉语虚化完结成分有两类,一类与“得”义有关,一类与“失”义有关。因为语法化的“语义滞留”原则,虚化前的词汇语义往往会制约动相补语及其进一步演化而成的体标记的使用。[7]夏俐萍将其称之为“扩展源意义”。因为扩展源意义的制约,“多功能语法标记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搭配成分受限、结构歧义甚至进一步发展出主观积极义或消极义等特点。”[5]苗族汉话的“呱”“哇”“咧”等标记在非现实情状中与动词的搭配受到限制,以下以“脱/穿”“撂扔/□tɕie55收(关峡)、□nai55收(车田)”两组意义相对的动词为例来进行说明,其中“脱”“撂”代表消除义动词,“穿”“□tɕie55收”“□nai55收”代表获得义动词。关峡和车田苗族汉话的“呱”和“咧”在非现时情状中还保留着相当于结果补语“掉”的用法,与动词的搭配也受到限制。
关峡:
(22)a. 只要脱呱□ma33□xa53嘅衣,就会感冒。只要脱掉外套,就会感冒。(条件句)
b. 只要穿起□ma33□xa53嘅衣,就麻会感冒。只要穿上外套,就不会感冒。
(23)a.我想脱呱个顶帽哩。我想脱掉这顶帽子。(意愿句)
b.我想戴起个顶帽哩。我想戴上这顶帽子。
(24)a. 捉个滴东西撂呱!把这些东西扔掉!(祈使句)
b. 捉个滴东西□tɕie44起!把这些东西收好!
车田:
(25)a. 只要脱咧外衣,就会感冒。只要脱掉外套,就会感冒。(条件句)
b. 只要穿起/紧/嗮外衣,就不会感冒。只要穿上外套,就不会感冒。
(26)a. 我想脱咧□o²¹³咧帽哩。我想脱掉这顶帽子。(意愿句)
b. 我想戴起/紧/嗮□o²¹³咧帽哩。我想戴上这顶帽子。
(27)a. 担□o²¹³哋东西撂咧!把这些东西扔掉!(祈使句)
b. 担□o²¹³哋东西□nai55起/紧/嗮!把这些东西收好!
不难看出,苗族汉话这类标记在条件句、意愿句、祈使句等非现实句中还保留着类似结果补语的用法,且常与“脱”“撂”等具有消除义的动词结合,据此可推测这些体标记的原型意义或与董秀芳提及的“失”义相关。而“穿”“□tɕie44收”“□nai55收”等获得义动词不能与“呱”“哇”“咧”等搭配,一般只能与另一个准完整体标记“起”搭配。车田苗族汉话比较特别,有3 个平行的结果补语“起”“紧”“嗮”均可搭配获得义动词。在现实句中,“呱”“哇”“咧”等作为体标记,表示行为事件完结或实现。此时与动词的搭配范围显著扩大,句法适配度大大提升。仍以关峡、车田点为例:
关峡:
(28)□mei21底死呱个讨饭食嘅。那边死了一个乞丐。(消除)
(29)我滴伊屋里住呱三个月。我在他家住了三个月。(中性)
(30)伊得呱顶红帽哩。她捡了一顶红帽子。(获得)
车田:
(31)□o²¹³边死咧□dai²¹³叫花哩。那边死了一个乞丐。(消除)
(32)我是伊屋□ie55住咧三条月日。我在他家住了三个月。(中性)
(33)伊得咧顶红帽哩。她捡了一顶红帽子。(获得)
以上各例中,“死”是消除义动词,“住”是中性义动词,“得”是获得义动词,“呱”和“咧”均可搭配,扩展源意义的影响几乎已经消失。而湘语中的“咖“哒”在与有界事件搭配时,仍然可以看出其扩展源意义的影响,即“咖”的消除义和“哒”的获得义,使它们在一些方言点中对所搭配的动词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5]如:
(34)宁乡:他失咖/*哒一只包。他丢了一个包。
他得哒/?咖一只包。他得了一个包。④
(35)湘阴:他失咖/*哒一只包。他丢了一个包。
他得哒/咖一只包。他得了一个包。
(36)韶山:他洗咖/?哒一上午衣服。他洗了一上午衣服。[5]
(37)长沙县:他今日子穿哒/?咖一件新衣服。他今天穿了件新衣服。[5]
从以上各例中仍可看出“咖”倾向搭配消除义动词,“哒”倾向搭配得到义动词,不过在不同方言点、不同动词后体现出这种倾向的强度不太一致。而苗族汉话中“呱”“哇”“咧”则可在以上每一个例句中使用,已看不出选择倾向。从这一点来看,苗族汉话完整体标记的语法化程度似乎略高于湘语中的“咖”“哒”。另从动词情状类型来看,根据戴耀晶对动词的情状类型分类,[8]我们发现:苗族汉话中的“呱”“哇”“咧”等完整体标记可以与少量心理感觉类静态动词和一般的动态动词(含动作动词和结果动词)搭配,也可与兼有静态和动态性质的动词(含姿势动词和位置动词)搭配。
(38)伟江:我去年就认哩哇老王。我去年就认识了老王。(静态动词)
(39)关峡:伊咳呱几日呱。她咳了几天了。(瞬间动作动词)
(40)兰蓉:我半日食呱两碗饭。我中午吃了两碗饭。(持续动作动词)
(41)车田:伊屋□ie55死咧两□dai²¹³鸡。他家死了两只鸡。(瞬间结果动词)
(42)伟江:门口徛哇好多人。门口站了很多人。(姿势动词)
(43)车田:墙□ie55挂咧一幅图。墙上挂了一幅画。(位置动词)
从以上各例可知,除属性、关系类静态动词(如“是”“姓”“等于”等)之外,苗族汉话中的“呱”“哇”“咧”等标记可与心理感觉类静态动词搭配,如(38);可与大多数动态动词搭配,如(39)(40)(41);也可与多数兼有静态和动态的动词搭配,如(42)(43)。其与动词情状类型的句法适配度接近于普通话词尾“了”和湘语的完成兼持续标记“哒”,而明显高于湘语完成义标记“咖”。
2. 使用的强制性
此处主要考察“呱”“哇”“咧”等完整体标记能否被其它动相补语替换而意义不变。据我们考察,在苗族汉话中,可能与完整体标记替换的动相补语有两类,一类表完结,相当于陈前瑞体貌系统中的“完结体”,如苗族汉话各点均有的“起”“完”“好”等;一类表结果,相当于陈前瑞体貌系统中的“结果体”,意义接近普通话的“着(zháo)”“到”“见”,[9]各点差异较大,如关峡有“滴”,兰蓉有“到”“紧”,伟江有“哩”,车田有“起”“紧”“嗮”。在表有界事件的现实句中,除了车田点,其它苗族汉话点的完整体标记均不能直接替换为表完结的动相补语,即使用上表完结的动相补语,完整体标记仍然不能少:
(44)关峡、兰蓉:a.伊食呱两碗饭。b.伊食完呱两碗饭。他吃了两碗饭。
(45)伟江:a.伊食哇两碗饭。b.伊食完哇两碗饭。
(46)车田:a.伊食咧两碗饭。b.伊食完两碗饭。
关峡、兰蓉、伟江完整体标记替换成“完”以后,句子不成立,“呱”或者“咧”需要强制使用。唯有车田点的“咧”可以替换为“完”,且不需要再用“咧”。但这是因为车田苗族汉话中的“完”的语法化程度高于关峡、兰蓉和伟江,(46)b 句中的“完”已演化为一个表示事件完结的体标记,[10]所以可与“咧”互换。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实句中,在“食”这类具有隐约消除义的动词之后,完整体标记“呱”“哇”“咧”是强制使用的,不可与表完结的动相补语直接替换。
苗族汉话完整体标记与表结果的动相补语的替换关系则是另一番景象,在获得义动词之后,几乎都可替换为表结果的动相补语。例如:
(47)关峡:a. 伊打呱个野猪。b. 伊打滴个野猪。他打了一头野猪。
(48)兰蓉:a. 伊打呱个野猪。b. 伊打到/紧个野猪。
(49)伟江:a. 伊打哇个野猪。b. 伊打哩个野猪。
(50)车田:a. 伊打咧□dai213野猪。b. 伊打起/紧/嗮□dai213野猪。
这说明,苗族汉话这类标记使用的强制性还受到动词语义的影响。在“打”这类具有隐约获得义的动词之后,完整体标记通常可替换为表结果的动相补语。一般来说,如果这些完整体标记之前是中性义动词,则很难用其它动相补语替换,使用的强制性最高。比如“伊看呱/哇/咧一场戏他看了一场戏”中的完整体标记一般就不能再用其他表完结或结果的动相补语替换。
从隐去自由度来看,“呱”“哇”“咧”在现实句中作为完整体标记时,无论句末用何种助词,均不能隐去不用。
总之,苗族汉话动词后虚化成分“呱”“哇”“咧”在性质上存在“结果补语—动相补语—体助词”的连续统。从句法适配度、使用强制性、隐去自由度三个方面来看,4 个苗族汉话点的核心完整体标记内部一致性较强,语法化程度也较为一致,均明显高于湘语的“咖”,接近于普通话词尾“了”。
三、湘桂边苗族汉话核心完整体标记来源探讨
从标记来源看,湖南境内绥宁关峡、城步兰蓉两个苗族汉话点的核心完整体和已然体标记均用“呱”,与周边的老湘语如绥宁长铺话、城步儒林话、新化话等使用的完整体标记完全一致,应是青衣苗人转用或借用老湘语体标记的结果。
龙胜伟江点的“哇”,不见于湖南境内的湘语,也不见于桂北西南官话(如桂林话)和入桂湘语新化话。“哇”是否苗语底层词呢?我们认为应该不是。在伟江苗族汉话中,“哇”音为[ua44]。而相关文献所记录的苗语主要完成体助词多为ʑ声母系,且没有u 介音。如:
坝那语:ʑa44[11]
矮寨苗语:ʑa44[12]
黔东苗语鱼粮话:ʑɛ55[13]
黔东苗语养蒿话:ʑaŋ55[14]
我们认为伟江点的体标记“哇”与老湘语的“呱”同源,极有可能是语法化过程中语音弱化、“呱”k 声母脱落的结果。彭逢澍、[15]李冬香、[16]胡萍[2]等均认为湘语中表完成的体标记“咖”“呱”等都来自“过”。⑤“过”属歌部,据王力的构拟,“过”的韵母先秦为“uai”,汉至晚唐为“ua”,宋至清代均为“uo”。[17]如此看来,“呱[kua]”是保留了“过”汉至晚唐的古音,“咖[ka]”则是“呱[kua]”u 介音脱落的结果。语音弱化是语法化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吴福祥指出语法化过程往往伴随音系形式的减少或销蚀(erosion)。[18]赵日新则论及处于弱化位置的音节通常会发生的变化包括“复元音单元音化、主元音央化、声调零化或促化、声母浊化或脱落,以及‘零’化等。”[19]我们认为,伟江苗族汉话的“哇[ua]”正是“呱[kua]”声母脱落的结果。
声母脱落在方言中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语音弱化现象。唐作藩《湖南洞口县黄桥镇方言》中记载的洞口话完成标记“呱”(唐先生记作“瓜”)就有[kua21]和[a21]两个读音。[20]湖南常德方言有完成体标记“啊[a]”,[21]李冬香认为其与“咖[ka]”“呱[kua]”同源,[16]显然是声母脱落的结果。在我们调查的车田苗族汉话中,“起”作为实义动词或动词性语素时发音为[tɕhi33],作动相补语或体标记时声母脱落,读音为[i33],是语法化导致声母脱落的典型例证。车田点近指词为[o²¹³],而关峡点为[kou²¹³]、伟江点为[ko213],周边湘语和赣语多为[ko]系近指词,[o²¹³]显然也是声母脱落的结果。
移民史也可以用来证明“呱”“哇”同源。李蓝曾指出,“根据当地的口碑传说,龙胜的青衣苗都是明代从湖南城步移民到广西来的。”[1]我们在龙胜县伟江乡调查时,据当地石姓苗族人介绍,石氏族谱记载他们是从湖南城步迁徙到广西龙胜定居的。果真如此,那么源自湖南城步的龙胜伟江青衣苗人很有可能早先也使用“呱”,后来声母脱落成为“哇”。这种脱落过程我们还可以从三个苗族汉话点的对比中看到动态演变的痕迹。且看:
(51)五团:我食呱饭呱。[1]
(52)马堤:我食呱饭哇。[1]
(53)伟江:我食哇饭哇。
城步五团、龙胜马堤和伟江均属湘桂边苗族汉话的西片。从地理位置来看,五团属湖南城步,受湘语影响大,完整体标记和句末已然体标记均用“呱”。伟江属广西龙胜,处于大山包围的深谷中,与外界接触较为困难,两个标记均已脱落声母成为“哇”。马堤则处在五团和伟江之间,其标记格局是句中完整体标记仍用“呱”,句末已然体标记脱落声母成为“哇”,正好呈现出一种中间状态。据此我们推断,城步五团、龙胜马堤和伟江三个点之间完整体和已然体标记的共现模式演化趋势如下:
V 呱O 呱>V 呱O 哇>V 哇O 哇
再来看车田点的“咧”。从语音形式看,车田点的“咧”[le44]在湘桂边苗族汉话中显得颇为“另类”。因为缺少历时语料及文献佐证,我们只能通过跨方言、跨语言的语音及语法意义比较进行推断。“咧”的来源有两种可能:
一是来自桂北西南官话中的“了”。车田苗族汉话长期与以桂林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及以新化话为代表的入桂湘语接触。当地苗族人除了会说苗族汉话之外,同样可操不标准的桂林话和新化话。如果作横向比较,车田的“咧”与桂林话完整体标记“了”很相似,有可能是西南官话强势影响所致。杨焕典所记桂林话完整体标记为“了”,记音为[nɤ54]。[22]而据伍和忠调查,桂林市区官话n、l 相混,属自由变体。[23]我们在桂林市的调查也表明,新派桂林话完整体标记“了”的声母多用边音l,读音为[lɤ0]。抛开声调因素,车田的“咧”[le]与桂林话的“了”[lɤ]只是韵母开口度大小的差异。
二是来自苗语底层助词。前文曾提到苗语主要的完成体助词一般都是[ʑ]声母系的,但也有语音及语法意义上接近“咧”的完成体助词。如李云兵曾提到,苗语中有一个从位移动词lɛ24(相当于“去”)演化而来的动态助词lɛ24,可以位于句中也可以位于句末,表示“动作行为或事物变化发展成为事实的状态”。[24]这个lɛ24与车田苗族汉话的“咧”[le44]不仅语音相似,其语法意义也相当于句中的完整体标记,与车田点的“咧”基本一致。此外,还有一个旁证,即:车田苗族汉话中,“咧”除了用作完整体标记外,还有一种表示将完成的事态助词用法与“去”完全平行,主要用于祈使句:
(54)你担伊食完咧/去。你把它吃完。
(55)□o²¹³□dui³³有□dai²¹³蛇,你担伊捶死咧/去。那边有条蛇,你去把它打死。
这种“咧”与“去”完全平行的用法,西南官话的“了”是没有的。我们认为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去”显然是汉语方言的,属语法借用;而“咧”则可能是苗语“去”义位移动词lɛ24在苗族汉话中保留下来的结果,二者正处在竞争当中。同一语法功能,既有转用汉语的表达形式,也有原语言底层的遗留,这也正体现了苗族汉话作为“民汉语”的特点。湘桂边青衣苗语的本来面目已经无从得知,但基于上述推断,我们认为车田苗族汉话的“咧”亦可能是类似lɛ24的苗族底层助词的遗留。
四、结语
胡萍曾通过综合考察使用功能和语言本体两方面的情况认为,湘桂边苗族汉话“完全可以归入到濒危方言之列,其发展趋势不容乐观,记录、整理、研究苗瑶平话应该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工作。”[2]本文通过深度田野调查,基于比较和接触视域,对湘桂边四个苗族汉话点的核心完整体标记“呱”“哇”“咧”进行了专题研究。研究表明,苗族汉话动词后虚化成分“呱”“哇”“咧”在性质上存在“结果补语—动相补语—体助词”的连续统。各苗族汉话点的完整体标记在语法化程度上内部一致性较强,从句法适配度、使用强制性和能否用于无界事件等角度看,苗族汉话的核心完整体标记“呱”“哇”“咧”的语法化程度明显高于湘语的“咖”,接近于普通话的词尾“了”。
从来源看,关峡、兰蓉点的核心完整体标记均用“呱”,是借用或转用老湘语体标记的结果。伟江点的“哇”与“呱”同源,是“呱”语音弱化、声母脱落的结果,可从语音演变及移民史两方面得到证实。从五团、马堤、伟江三个点的比较来看,苗族汉话核心完整体与句末已然体标记的共现模式呈以下演变趋势:V 呱O 呱>V 呱O哇>V 哇O 哇。车田点的核心完整体标记“咧”可能来自西南官话的“了”,亦可能来自苗语底层从位移动词演化为完成体助词的lɛ24。
注释:
① 湘桂边苗族汉话中“呱”“哇”“咧”等体标记所表示的体意义接近于词尾“了”,大部分情况下用于完成的行为事件,但也可用于已经发生但尚未完成的事件,且不必具有现时相关性。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完整体。
② 各苗族汉话点主要发音合作人如下:绥宁关峡黄彩菊,女,苗族,1964 年生,村干部;城步兰蓉雷学品,男,苗族,1972年生,教师;龙胜伟江石生武,男,苗族,1948 年生,教师;资源车田杨建国,男,苗族,1947 年生,教师。
③ 长沙话的发音人为杨玲,女,1963 年生,教师,长沙市人;沅江话的发音人为郭兆龙,男,1946 年生,教师,沅江市黄茅洲镇人;湘阴话的发音人为杨建凯,女,1964 年生,工人,湘阴县城关镇人。全文同。
④ 宁乡话例句参考了夏俐萍论文,并经发音合作人核实。发音合作人为王淑兰,女,1962 年生,农民,宁乡市回龙铺镇人。
⑤ 关于“咖”“呱”等体标记的来源,也有学者认为源自“解”,但源自“过”的说法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