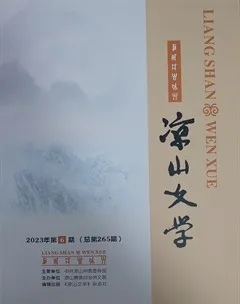珍珠米、荞麦及其它
吉好你布
1
人们一提到普格的地势,总喜欢用三山夹两沟来形容,螺髻山、中梁子、乌科梁子平行相向,中间是由北而南的则木河和西洛河,两条河最终在洛乌沟相会,变身为黑水河,最后流经宁南,汇入金沙江。
凡有河流的地方便有生机,则木河和西洛河用自身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沿河的普格儿女。同时也塑造着两地不同的地域环境,则木河两岸植被茂盛,风光旖旎,虽然没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秀丽,也大有杏花春雨江南的一丝风骨;西洛河两岸则风格迥异,崇山峻岭中夹杂着几多沧桑,这里植被稀疏,裸露的岩石和褐红色的大地肌肤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刺眼,走进这里便能感受到北方的粗犷,铁马金戈塞北的感受便油然而生。
滚滚西洛河源自昭觉县的洒拉地坡河,洒拉地坡河在洒拉地坡平坝上蜿蜒而平缓地流动着,不紧不慢、悄无声息,不激起一朵浪花,静如处子。如果不是岁月见证了它永不停息的决心,人们毫无察觉这里还有一条河流,在这里,我们相信是大地的汁液汇聚成了河流,而不是这条温顺的河流造就了这片平坝。
洒拉地坡河一出昭觉,便收起了温顺本分的好脾气,顺着地势的骤降而快马加鞭,一路欢快奔腾,当来到拉箐大峡谷时,便造就了名震大凉山的大瀑布——拉箐瀑布。流水在峡谷中腾空而降,腾起的烟雾遮天蔽日,两岸茂林修竹无法掩盖雪白的河流飞挂千米绝壁的雄姿,河流经过这一洗礼,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浴火重生,名字也变成了西洛河,彝语名叫色洛河。
从远古至今,西洛河总是在群山之间咆哮向南,冲刷和造就了一块块小型平坝和台地,人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这里辛勤耕作,河流两岸后来也就慢慢变成了一片片沃土和粮仓。茫茫群山间,一片片充满生机的梯田便雨后春笋般冒出,它们像一幅幅明亮的调色板,在四季的轮回中用多彩的色调装饰着单调的大山,也敞开自己温暖的怀抱熨帖着纯朴的山民。
宁喝阿尼新米汤,不吃好谷大米饭。这是一句流传于广大彝区的名言,瓦洛日呷、阿尼拉恩觉、瓦达洛、火洛格则、莫尔非铁这些赫赫有名的彝族古地名都是因为盛产珍珠米而声名远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被称为“澈米拉弓色坡”,“澈米拉弓色坡”为彝语,意思为“种植稻米的人”,翻译成汉语有点平淡,但在彝语中具有非常受人尊重的韵味,种植稻米的人,自然是以稻米为主食的人,也是离汉区最近、能够最先接触先进文化和先进思想的人,在族群生存竞争非常激烈的时代这里具有先天生存优势。
从阿尼瓦洛到夹铁尔库,再到洛乌营盘,星罗棋布的层层梯田用自己的产出滋养着这里的山民。褐色的群山、褐色的梯田、充足的光热、还有西洛河甘甜的河水,各种要素在大自然的奇妙组合下成为了绝佳的搭档。在大凉山,盛产稻米的地方很多,但西洛河流域的稻米非常独特,这一带由于光照强、温差大,加上至今保留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的绿色生态种植方式,出产的稻米米粒饱满、色泽洁白、晶莹剔透,形似珍珠,人们习惯性地将这里出产的大米亲切地称为“珍珠米”,自古以来就驰名于山里山外。
珍珠米核心产区夹铁镇在明清时期就叫“夹铁尔库”,汉名叫“小兴场”,是当时宁远府的一个驿站,也是凉山四大土司之一阿都土司的主要粮仓,和西昌的“大兴场”遥相呼应。“大兴场”就是今天的西昌市大兴镇,自古就是繁华富庶之地,能够和大兴场齐名,足见当年珍珠米产地的底气有多足,底蕴有多深厚。
2
夹铁镇的3000亩水稻田,莫尔非铁村就占了五分之一,据说这里的水稻种植历史已有几百年,甚至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期。
在这里,人们无法考究是谁挥下开垦层层梯田的第一锄,也无法探究是哪一个如玉的少女弯下美丽的弧线插下第一丛秧苗。包括第一次的秧苗返青,第一次稻田抽穗,第一次金黄的稻浪,第一口带着土地芳香的珍珠米饭是谁在尝鲜,都无从无探。
当一直迁徙的莫尔菲铁村的先祖的眼睛省略过高山、河流、峡谷、台地,最后时光让他们的脚步在这片美丽的土地停驻,他们的眼睛被眼前这一汪泛着逆光的水田所吸引。于是,迁徙的脚步被停止,漂泊的思绪被收缚,为何屋后有山不放牧,为何房前有田不种稻?
其实,在所有作物的种植过程中,水稻的种植是一个繁琐而很费力气的过程,各个程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种植水稻首先要开渠引水,完备的沟渠,固定而充沛的水源是关键,将平地开垦成可以关水的水田,形成诗情画意的梯田。大凉山山高坡陡,黄牛主要用来耕作山地,犁田耙田得养有水牛,还得有犁耙工具,所以水田和水牛也相依相存。在青青的秧苗栽种前,水田须犁耙三四遍,并将田埂糊好,阡陌纵横中明镜般的水田在静静等待一场积蓄力量后的倾力奉献。
当二月的寒意还未退去,稻农们便开始了一年中的忙碌,将精心挑选的稻种晒干,然后开始用木水桶将稻种泡水,泡上幾天,把水滤净,然后是各种器皿开始登场,再用稻草盖上,没过几天,稻种开始发芽,金黄而鲜嫩的胚芽在阳光下金光闪闪,这时候择一个良辰吉日,将长出了胚芽的稻种均匀撒下早已平整好的秧田,撒下稻种的同时也撒下了希望,也撒下辛勤的汗水。
金秋的田野充满丰收的喜悦。蓝天、白云、金黄的水稻,一派丰收的景象让人沉醉,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泥土和稻香的气息,这种清香是如此的诱人。农人们开始准备各种秋收的工具,大件如木伴桶、篾遮等,小件如口袋、镰刀,更为重要的是人力,农村打谷是一个需要多人合作的劳力活,这就需要几家互助协作,打完一家再打一家,直到颗粒归仓,最后一家的最后一粒收回家,整个秋收才算完。
从记事起,木拌桶就是打谷子的最为重要工具,这个家家都需要的东西呈四方大木斗型,四边角上各有一块木把手,这是打谷前进后退转场时的拉手,打谷时候围上一张篾遮便可以开始打谷了。虽说造型简单,但在那个困难的年月里并不是每家都有自己的木拌桶。一个木拌桶既要轻便、结实,还得耐磨损、耐水浸,不是专业木匠做不出来的。
在打谷的好日子,农人便早早吃过早饭,一群人就开始忙活起来。妇女们手勤,负责割稻谷,三四窝一把平放田里。剩下的人将木拌桶放到田里,用一张篾遮插入拌桶围起来,这样蹦跳起的谷粒就会落回桶里。
两个壮劳力各自握着一把稻谷,在露出的木拌桶边沿上用力地摔打,不断转动角度轻抖,两个人心领神会交替进行,“嘭叭嘭叭”的声音此起彼伏。重复上三四次后,一把稻谷就基本上从秸秆上全脱离下来了。打谷子是个体力活,一般需要四个年轻力壮的劳力两人一组轮流上场。没上场的人就一边休息一边将脱完粒的稻草捆起来,然后是用麻袋将谷子装好压实拴紧,堆放到田坎间干燥的地方。
我们小时候,各种运输工具没有现在那么发达,打下来装好的水稻只能是人背马驮,非常费力,但不管是人是马都是那么充满精神,在丰收的田野上来回穿梭,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如今,一群人用木拌桶打谷子的情景已经很难再看到了,有可以直接开到田里的打谷机,当然更多的是微型的谷物脱粒机,两三个人就能轻松操作。但我们还是怀念着以前用木拌桶打谷子的日子,怀念那此起彼伏的“嘭叭嘭叭”声,怀念那种在一起欢歌笑语劳动的场面,怀念那种极具仪式感的丰收场景。
收获过后的层层梯田退去了金黄的外衣,露出了暗红色的肌肤。稻草被勤勉的农人堆积在一起,洒落在田地里,远远望去,无数的稻草垛想一座座古代的圆形草房,在夕阳的余晖中熠熠生辉,到了冬天,稻草可以作为牛羊的饲料,也可以作为燃料,凡是梯田里的产出对农人来说都是宝贝。
秋天的天空是如此的高远,几朵悠闲的白云在天空上相互追逐。近处,牛、羊、马在收获过后的梯田吃草,秋收过后最为惬意的莫不过于它们了。这个时节,所有的田地都是它们觅食的地盘,不必畏手畏脚,也不必缩衣节食,敞开肚皮吃就是。那些马儿吃饱了一圈一圈的跑;那些调皮的公牛,吃饱了可以练一练自己的角力,随便找准一个土包,一截田埂,伸直尾巴,用力刨抵,等到筋疲力尽时才在牧人的吆喝下伴着夕阳的余晖慢慢归去。
放水、耙田、施肥、插秧、薅草、打谷、晾晒、碾米,一道道工序和先辈们相伴。只不过现在一些较为省力的工具代替了原先的器物罢了,不变的依然是对这片土地的一往情深。在极具仪式感的傍晚,夕阳金色的余晖早已消失在群山之巅,新米的芳香开始弥漫在每一间温暖的屋内,四季的轮回终于带来了收获后的品尝,岁月在充满希望的日历中不断翻新,珍珠米用自己晶莹剔透的洁白身躯熨帖着每一个稻农的梦想。
生活在大凉山的彝人在饮食上崇尚简单、纯正,在食物的烹饪上也追求原汁原味,犹如他们开门就能撞见的大山一样简单明了。
米饭配猪肉、包谷饭配牛肉、面团饭配羊肉、青稞饭配鸡肉,在这个不善对美食进行深入研究的山地民族眼中,也有一些美食与美食的最佳组合,它们的神奇相遇让本不挑剔的味蕾迸发出巧妙的盛宴情愫,莫尔菲铁村的珍珠米配当地土猪肉是我们魂牵梦绕的美食,这种味蕾的诱惑将永远积淀于灵魂深处无法忘却。
3
大凉山沟壑纵横,气候立体差异巨大,人们总爱用“十里不同天,一山有四季”来形容。独特的地形地貌和多变的差异气候,再加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彝族是一个习惯游走于山林间的民族,人们很难将他们和稻米的种植联系在一起,但恰恰相反,彝族很早前就与稻米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彝人的世界里,每一种与我们休戚相关的物种都有它们的起源史。彝族经典《物种源流》详细记载了水稻的起源史,从中证明了彝族先民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种植水稻。
远古的时候,天空孜紫鸟,孜紫尖嘴鸟,尖嘴阿者鸟,从蓝天降落,落到灰天上;从灰天降落,落到黄云上;从黄云降落,落到乌云上;从乌云降落,落到白云上;从白云降落,落到雾雨间,随着雾雨降,落到“滇帕舒诺”湖海外……洋人神仙得到后,拿到山顶种,种下未长苗;拿到山腰种,有苗不结籽;拿到山脚下,旱地中种植,有苗不结籽;拿到水中种,秧苗绿油油,稻穗弯如捕鸟架,水域满白米。
从充满传奇色彩和神秘主义的文字描述中可以看出,水稻的起源是如此浪漫,从起源史的开篇,我们可以看出,水稻并非是大凉山的土生土长的物种,属于凉山以外传入。水稻的诞生是如此神秘,水稻又是如何来到我们先民的中间的呢?《物种源流》同样作了精彩的叙述:
“滇帕舒诺”湖海内的人,想去寻稻种。“母猪阿支”派,“公狗达一”随,一同“滇帕舒诺”湖海去,寻找稻谷种。九日跑到夜,九夜跑到昼。来到“滇帕舒诺”湖海外,种植稻谷地,母猪裹泥浆,钻进稻谷地,公狗淋湿身,进稻中翻滚,稻粒口中衔,返回过江河。“母猪阿支”啊,泥浆裹稻粒,时而浮水面,时而沉水底,粒随泥浆被水冲进底,母猪空手归。“公狗达一”啊,尾巴带回来稻种,口中衔回来稻粒,回到了家中,拿到水中去种植,长势懒洋洋,秧苗也不高,开花白闪闪,稻穗弯如捕鸟架,稻粒也饱满。
“公狗达一”是一条狗的雅名,成为了我们先民取回稻种的英雄,当然我们也要永远记住母猪阿支的有勇无谋似的豪举。其实在彝族另外一部经典《创世经》中也作了详细的叙述,在人类最先的起源过程中,动物朋友们是我们人类的好帮手,它们和我们人类休戚与共、相互依存又各怀绝招,无论是蜜蜂,还是蛤蟆、毒蛇、乌鸦等在人類的创业过程中都立下过汗马功劳。当然,文学作品毕竟是文学作品,但从中也看出我们先民与万物和谐相处的旷达心理,也体现出他们世间万物都有灵性的生命哲学。
我们先民认为,狗、马、猫等都是通人性的,它们不光是人类忠实的伙伴,更是和人类一样是有灵性的动物,在生命的自然法则中,大家彼此依存,不能相互蚕食。所以,从古至今彝人不食狗肉、马肉的习俗由此而来。
在大凉山的广大彝区,每年水稻丰收后,都要举行“尝新节”,煮上香喷喷的新米,宰上一只金黄色的仔母鸡以示对丰收的庆祝,但无论谁家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新米饭的第一口要让自家的狗来尝,这也是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生生世世铭记狗的功劳,表达对狗的谢意。
曾经,猎狗、骏马、耕牛是彝族男人的标配。在远古,狗是狩猎的最重要工具,矫健的身躯,灵敏的嗅觉,它们穿山越岭、腾云驾雾、追赶猎物,成为人类最为重要的帮手。
如今,狗的职责变成了单纯的看家护院,它们总是一身肥肉蜷缩在院门,睡眼朦胧地盯着路人,高兴时悄无声息和陌生人相安无事;不高兴时便狗声大作,它们也深谙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略战术,总是用狗的方式、狗的思维和人周旋,凶狠的目光、锋利的牙齿、愤怒的表情,总是让路人避之不及。它们用自己的行动发出了狗的声音,表明了狗的态度。无论岁月如何交替,时光如何延展,狗在彝人的心目中还是具有极高的地位。
……适合种稻区,逐步蔓延开,拿到“阿洪你日”河边种,“阿洪你日”从此产稻米。拿到“乌托尔库”去种植,“乌托尔库”从此产稻米。拿到“甘尔莫波”去种植,“甘尔莫波”从此产稻米。拿到“利木竹核”去种植,“利木竹核”从此产水稻。拿到“色洛拉达”去种植,“色洛拉达”从此产水稻。
……孝敬白发老人的稻米,接待尊贵客人的稻米,走亲访友的稻米,喂养婴儿的稻米。水中沸腾的白米,长也长水中,煮也水中煮,米饭白如雪,米饭配猪肉,猪儿放牧沼泽中,稻米生长水田中,彝人喜欢种稻谷,汉人喜欢种稻谷。
“滇帕舒诺”是彝族古代典籍中经常出现的地名,多数专家认为就是今天的滇池,彝族古代英雄支格阿尔骑着神马经常飞越但最后落水而亡的地方也在这里,神话和传说就是人类早期童年时期的历史,我们相信,那里曾经留下过我们祖先奔波的身影。
而后面的一系列古地名全都在大凉山,并且至今还在沿用。“阿洪你日”就是今天安宁河谷的统称,“乌托尔库”就是越西坝,“甘尔莫波”就是雷波,“利木竹核”就是昭觉竹核坝子,“色洛拉达”就是今天的西洛河流域,特指盛产珍珠米的夹铁、瓦洛地区。从这里我们也看出,迁徙到大凉山以前,我们祖先就已经种植水稻,随着迁徙的步伐,水稻也一同迁徙到了大凉山的大小平坝上。
4
如果要用一些现代的词汇来形容我们这个永远在迁徙路上的民族的特性,那么尊贵、典雅、内敛、朴实、坚韧、沉默、奔放、得体等这些词语一点都不为过,为了适应脚下的这片土地,为了能在头顶的这片蓝天下繁衍生息,他们永不疲惫的身影总是在连绵不绝的群山间出没,日月星辰的交相辉映,山川河流的四时更替,已经融进了这个民族的血液,成为他们的精神图腾。
风在山岗上呼啸而过,阳光奢侈地洒满大地,带着希望的羊群在溪流和草甸间奔腾,土地上挥鞭耕耘的少年和那条温顺的牛……更多时候,我们这个族群是沉默的。
每当层林尽染、雁过晴空、牛羊满圈、仓廪充实、族群重逢、新娘进屋、逝者远去时,他们又是奔放的。酸甜苦辣的人生百态,风霜雨雪的季节磨炼,让他们在坚韧中保持着奔放,有时他们的奔放是在一场场生命的高歌时喉头发出的颤音,也是在一处处人生充满绝望的时空中蹦出的希望。
大凉山彝族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迁徙史,从传说中的祖地“兹兹蒲武”出发,翻过天险金沙江,进入大凉山,一路艰辛一路跋涉,族群的力量成为了抚慰心灵、医治创伤的的良药。于是,充满艰辛的迁徙之路成为了一次豪迈的探索之旅,一场壮丽的诀别之旅,悲伤与绝望也被铺天盖地的浪漫主义所淹没,《创世经》记载了当时迁徙的盛况:
西方住的伙,来到西方时;上游从吕黎渡口过,成百上千阉牛领头来,偶蹄家禽数不清;成千上万神马领头来,圆蹄家禽数不清。中游从尔基渡口过,金银跟着渡江来,财帛用不尽。下游从俄措渡口来,三百男丁领头来,三百姑娘领头来,人丁兴旺数不清……
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为的是一方丰美的水草,一片能够种出庄稼的土地。为了能丰衣足食,他们在不断追求自己理想中的居住地,在《创世经》中借对祖地“兹兹蒲武”的描写表达出了对理想居住地的要求:
兹兹蒲武这地方,屋后有山能放羊,屋前有田能栽秧,中间人畜有住处,坝上有坪能赛马,沼泽地带能放猪,寨内既有青年玩耍处,院内又有妇女闲谈处……兹兹蒲武这地方,屋后砍柴柴带松脂来,屋前背水水带鱼儿来……兹兹蒲武这地方,小马到一岁,肚带断九根;小牛到一岁,犁头断九架;小羊到一岁,羊油有九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凉山独特的地理地形让我们这个民族的耕牧文化有别于一望无垠的草原文明,也区别于沃野千里的稻作文明,人丁兴旺、牛羊滿圈、五谷满仓成为这个迁徙民族的那个时候的最高理想,并在此理念的促成下形成了独特的耕牧文化,《训世经》记载道:
居木之后代,种植五谷者,五谷堆成山;饲养牛羊者,牛羊满山坡;喂养骏马者,出门骑骏马……子孙想幸福,勤种五谷是出路,后代要安康,饲养牛羊是途经。
民族的迁徙实际是一部血泪史,离开自己熟悉的故土和精神家园,去寻找一片新的生存之地,寻求一种新的生存方式,构建一片全新的心灵故土,谈何容易。战争、瘟疫、饥饿等迁徙路上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成为族群挥之不去的梦魇;远去的故土,陌生的坏境,脆弱的心灵,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层面都需要抚慰,都需要重构。
“出门在外骑骏马,休闲在家能推磨”是彝族对优秀男人的标准要求,作为社会主体的男人,身上肩负着一个家庭丰衣足食和兴旺发达的双重任务。生活对男人的要求也很高,骑马射箭、上山狩猎、下河摸鱼、扛枪御敌样样都要精通;逢山就能开路,遇河还能架桥,生活和生存的重压也让男人们沉默持重、稳健端庄。
山下有田能种稻,屋后有山要放牧。种植水稻,白花花的大米饭能填饱肚皮,能够为我们提供生生不息的能源;养殖牛羊,能够为我们提供肉类,羊毛能够织成抵御寒冷的衣物,彝人特有的擦尔瓦、披毡等都是独具特色的衣物;牛羊的肥料能够滋养贫瘠的土地……这样的良性循环也让人与自然生态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
人生有时候也很简单。曾经,一个健壮如牛的老婆,一群茁壮成长的孩子,一个在黄昏时能让炊烟袅袅升起的木板房,还有一盆正冒着香味热气的珍珠米粥,一条在夕阳下被拉长了身影的竹篱笆下躺着的大黄狗,这些都是这个山地民族男人的人生追求。
在长期的水稻种植中,我们的祖先也开始积累了一些关于水稻的知识文化,长期的水稻种植经历也让他们在心理深处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文化情愫,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影响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心态气质。“谷草捆谷穗,不会有声响;赶猪进猪群,不会有叫声”“稻田喜水,旱地喜肥”“有米的舂米,有荞的磨荞”“借米的还米,借荞的还荞”“五谷不会因为热而生病,牛羊不会因为冷而生病”“五谷依靠水”“五谷的粮食是肥料,牛羊的粮食是绿草”,这些朴实但充满哲理的谚语无不透露出先辈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考和获得的经验。
5
拉箐河水的欢唱至今还在延续千年前的回响,阿尼山下的梯田层层叠叠,在季节的轮回中奉献着年复一年的丰收。
这里也是珍珠米的产区,更是彝族经典《妈妈的女儿》的诞生地,和晶莹剔透的珍珠米一样,无数深沉哀婉的妈妈的女儿从这里走向他乡,演绎一段段或喜或悲的人间真情。
清晨第一缕阳光总是透过乌科山上的群峰准时到达这里,金色的阳光在梯田如镜的水面上熠熠生辉。傍晚,夕阳的余晖又从阿尼山上倾斜而下,为梯田、山地抹上一层金色的霞光,这片多情的土地孕育着多情的妈妈的女儿们。
一座山,一片地,一条河,一个聚族而居的村落。山与山相连,沟与沟相通,沟壑交错中隐藏着一个个别具一格的村庄……这就是我的族群生存的天然环境。
很羡慕温润的江南,更羡慕江南一个个青梅竹马的绝美爱情故事。可惜我们这里山太高、沟太深,更何况这是一个以聚族而居为荣的山地民族,曾几何时,严格执行家族外婚的亘古不变的规矩。女孩们睁眼看见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姊妹,姑爷叔侄,那种“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的美好爱情与这片土地相去甚远。
高大挺拔的大树长在阿尼山上,树叶随风飘异地;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自阿尼山,浪花向东不回头;温柔漂亮的姑娘生在阿尼山下,长大就要嫁他乡。妈妈的女儿们在珍珠米的孕育下,随着岁月年轮一个个长得身姿卓绝,风雅绝伦。
通过媒妁之言,父母恩准,一个个妈妈的女儿沿着拉箐河畔的小路,沿着阿尼山上的盘曲山路走向了他乡。父亲的猎狗还在院内静躺,兄长耕地的犁头还挂在屋檐下。某一个清晨,当黎明褪去了黑暗的外衣时,妈妈的女儿已经穿上了嫁衣,枣红色的骏马在门外打着响鼻,兄长叔侄们个个精神抖擞,组成了送亲的队伍,倔强而高傲的父亲坐在火塘边上,沉默地抽着兰花烟,晶莹的泪珠已经在眼眶打转。
在这离别的时刻,还是母亲们老到:“自古他乡姑娘进我家,我家姑娘嫁他乡,来年大雁回阿尼山时,你们就背着美酒、冻肉拜年来了,我们会煮着珍珠新米饭配着过年肉等着你们。”转哭为笑的新娘们就这样铭记着珍珠米的芳香走向了他乡,去迎接属于自己的人生。
彝人们总是说,征战沙场的士兵出征前的笑是笑中带泪,尚武的彝人不愿意含泪奔赴疆场,只能是面带微笑慷慨前行;出嫁姑娘的哭是泪中有笑,哪怕对婚姻有多向往,也不能笑着离开自己的父母,离开自己的兄弟姊妹和生自己养自己的这片土地,心中有笑也只能用离别的眼泪来掩藏。
走进他乡的新娘中有位走得最远,在亲人的护送下从阿尼山下出发,沿着拉箐河畔,走过撒呷拉达,翻越嘛姑火普,穿越德普洛莫,最后到达能纸洛莫(汉源县境内)的夫家,沿途经历了风霜雨雪、虎豹豺狼……诸多能够想象的困难都已经遭遇,那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浪漫之行,而是一场西天取经般的磨难之旅。
新娘是位大家闺秀,饱读诗书,通晓古今,惊魂未定的她来不及好好体验新婚的快乐便开始了创作,用自己的亲生经历书写妈妈的女儿从呱呱坠地到出嫁的精彩人生。优美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刻的哲理,感动无数的新娘,感动无数的母亲,也感动无数的父亲,最后所有人都参与进来,进来了集体创作,《妈妈的女儿》便成为了不朽的彝族经典。
从层层梯田走出的新娘有的走进了异乡的梯田,但更多的是走进了他乡的燕麦地、荞麦地、土豆地。从此以后,那一湾湾明镜般的梯田便成为了魂牵梦绕的牵挂,珍珠米的饭香成为妈妈的女儿们永恒的记忆。
七月,一个如火的季节,山坡上的荞花已经开满大地,梯田里的水稻在抽穗扬花,一场丰收就在眼前,彝家火把节便悄然登场。
蓝天为顶,白云为盖,青草为毯,流动的黄伞,天籁般的少女的声音,这种民间少女集体大合唱最能表达出来自灵魂深处的咏叹。人们总是这样评价道,要说火把场上什么最能扣人心弦,让人怦然心动,使人潸然泪下,那便是彝家“朵洛嗬”。
妈妈的女儿哟,走了一程又一程,走到高山顶,高山寒流滚,女儿浑身冷冰冰;走到深谷中,深谷静悄悄,女儿心境更寂寥;走到森林里,风吹叶打颤,女儿心跳神不安……妈妈的女儿哟,走了一程又一程,最后走到布谷山南婆家门,诸多父亲正襟坐,我的爸爸却不在;各位阿姨笑盈盈,我的妈妈却不在,满屋宾客黑压压,我的好友却不在;他爸纵然千般好,我对我爸才是真心爱,他妈纵然千般好,我对我妈才是真心爱,他友纵然千般好,我对我友才是真心爱……
当彝族经典长篇叙事诗《妈妈的女儿》那深沉哀怨的基调和“朵洛嗬”相遇时,火把节最为美丽动人的歌调便诞生了。后来,《妈妈的女儿》中的歌词成为了“朵洛嗬”歌唱的主要内容,述说着新婚姑娘对亲人的思恋,哭述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以及崇山峻岭阻断下的撕心裂肺般对远方亲人的思念。
当天空的雁阵在阿尼山上徘徊时,群山上的层林开始金黄,彝历新年已经到来。无论距离有多远,远嫁他乡的姑娘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回娘家来拜年,美酒、冻肉、猪膀子、煮熟的鸡蛋、炒面、荞粉,凡是他乡的特产都要备齐,人背马驮,向离别已久的故乡归来。家人们则站在高高的山岗上极目远眺,望眼欲穿地等待亲人的身影从远方渐行渐近。
煮熟的鸡蛋和炒面祭祖先,美酒敬父亲,冻肉献阿妈。珍珠米的饭香已经飘满全屋,所有的思念和喜悦都浓缩在故乡特有的美食间,让亲情在岁月与山水间永远依旧。
相聚的时光稍纵即逝,珍珠米又一次被排上用场,让来时装东西的口袋都装上珍珠米吧,还是像来时一样在回家的路上也是人背马驮。在彝人的眼中必须礼尚往来,别人装东西的口袋和盆碗是不能空着拿回去的,哪怕他们是你的子女是前来孝敬你的,慷慨的父母还会让女儿一家赶着一头小母牛或者一群羊回去。
此刻,珍珠米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物象,又一次成为了族群相连、亲情相依的纽带。
6
大凉山并非一马平川,而是山水相间,山河相依。这里其实大部分地区适宜种植荞麦,并以荞麦为主食,形成了平坝以稻米为主食、高山以荞麦為主食的局面,犹如我国北方以小麦为主食,南方以稻米为主食一样。水稻、荞麦这两种喜好各异、迥然不同的作物成为这个高山民族的两大主食。
作为凉山地区彝人最早栽种的粮食作物之一,荞麦伴随着彝人的生存与延续,给彝人带来了人丁的兴旺。
同样是彝族经典《物种源流》,详细记载了荞麦的起源史。
远古之时,北方未闻有苦荞,南方未闻有苦荞;东方不种荞,西方还是不种荞,世上没有苦荞种……丁古兹洛哟,去寻荞来栽,兹阿乐尼山上寻,一天寻在山顶上,找是找着了,却见颗粒小如雪,结果不像果;又有一天来寻荞,寻到山脚下,荞茎粗又壮,荞秆长得茂盛又好看,有荞必开花,开花就结果,有果就有粉,此荞才是世间栽种谋生荞。
……丁古兹洛种荞来食用,红桦做犁弯,用铁铸铧口,杜鹃树做枷担,嫩竹作牵绳,金竹作赶鞭,赶着金黄牛,在阿甘乃拖来耕作,会犁地者来犁地,犁土一片片,种荞一片又一片,从此人间便有荞。
除了经典中记载的关于荞麦起源以外,在彝族美丽的神话中也有荞麦的一席之地。
相传远古时期,由于洪荒降临,彝人祖先阿普居木在忍饥挨饿、坚强抵抗着灾难和不幸,突然有天一只掠过惊涛骇浪、闯过狂风暴雨的金丝雀从遥远的北方,给阿普居木送来了一颗荞粒,并把它放在阿普居木的手心,金丝雀由于极度疲劳,吐尽最后一滴鲜血和胆汁后,倒在了阿普居木的手心里,阿普居木痛惜地捧着金丝雀,热泪洒在金丝雀的身上,于是金丝雀化作了美丽的女人——兹俄尼拖。
洪水退去后,阿普居木和兹俄尼拖将粘满金丝雀鲜血和胆汁的荞粒植入土中。不久,山坡上开满了粉红的荞花,结出的荞麦,苦味中散发着清香。美丽的兹俄尼拖把这种荞麦称为“苦荞”,从此,彝人在荞花满坡的大凉山上繁衍生息……
数千年以来,大凉山荞麦种植区总是流传着家喻户晓的苦荞歌,这些歌词用娓娓道来的方式述说着对食用苦荞时那种说不完、道不尽的好处。
撒下苦荞种,幼苗绿油油,嫩叶似斗笠,花开如白雪,结籽沉甸甸,荞麦堆成山。老人吃了还了童,少年吃了红润润,姑娘吃了双眼明如镜,乌发放光泽,十指嫩如笋,腰细如柳枝,容貌好似油菜花,迷醉多少男人心;马驹吃了乐津津,牛儿喂了胀鼓鼓,猪仔喂了肥胖胖,小鸡吃了鸣彻彻,瘦羊吃了蹦又跳……”
苦荞的产量和营养价值都高于甜荞,所以彝族地区普遍栽种苦荞。由于苦荞生长期短,存活率高,使其经常以备荒作物的面目出现,一旦有天灾人祸,苦荞便成为我们族群的救命稻草,即使到了三伏天气,仍能种苦荞麦以补救空地的荒废,到了晚秋,依然能有沉甸甸的收获。
每年六月,行走于大凉山时,总能遇见满目的绿色,那是正在茁壮成长的荞麦,接下来的七月便是一望无垠的粉红,八月九月便是满山遍野的收获景象,荞麦从生长到收获的过程中始终都是朴实无华、低调内敛,在与世无争中沉淀自己的芳华。
打荞的场景简单但是迷人,秋高气爽的日子,在一块早已成型的土坝上,或者就地取材在荞地边平整一块空地出来,放上一张竹篾,现在多半用彩色塑料篷布代替,女人们从四面背来已收割晒干的荞禾,那女人的汗味和荞香在空气中交融弥漫,男人们则抡起木枷打荞,看着荞粒慢慢地堆积起来,丰收的喜悦时常挂在他们的脸上。收割过的荞地里,早已是牛羊遍地,蓝天、白云、褐红色的荞杆、枣红色的骏马,还有黑白对半的牛羊,色彩斑斓的场面总是在我的梦中萦绕。
彝族有谚语:人在社会上,母亲位至尊;庄稼千万种,荞麦位至上。苦荞是大凉山彝人主食之一,它始终贯穿了彝人的农耕仪式、祭祀仪式、生育繁衍等过程,苦荞文化渗透在大凉山彝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苦荞”也已经超越了食物的含义,成为了彝人的精神寄托,也成为民族文化的载体。
水稻和蕎麦犹如两座山峰,在充实了我们的胃肠之余,高昂起了这个山地民族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