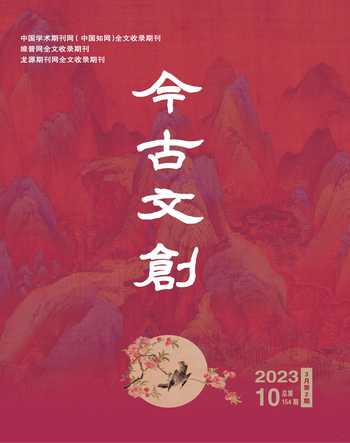《第四病室》中杨木华医生诞生因由考
祁瑞 孙洁
【摘要】 巴金在第三病室里遭受了医生对病人心理上的漠视,导致巴金本人产生了不适。所以巴金塑造了《第四病室》中的杨木华医生,并融合了他一贯的人道主义思想。相较于巴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杨木华更具人性的真实性,她的反抗性和斗争性并不强。杨木华这一形象的诞生及发展伴随着巴金心态的变化,其形塑及其结局变化具有必然性,对巴金后期的创作影响深远。
【关键词】《第四病室》;杨木华;患病体验;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0-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0.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抗战时期巴金的大轰炸书写研究”(202110637019)的阶段性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生死离别已经成了一种常态。伴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一些文人理想中的精神家园破灭。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很多文人生病住院。面对客观现实的层层矩阵,文人们会使自己的个体的生命体验在文学中得以呈现。他们往往通过塑造人物来承载自己的寄托,疗愈心灵,并以此进行自我疏导。巴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第三病室里医生对病人心理的漠视使得作为病人的巴金产生了极大的不适感,《第四病室》中的杨木华医生这一形象得以诞生。杨木华不仅承载了巴金作为病人的愿望,还融合了巴金本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故探究杨木华的诞生及发展对了解巴金的生命体验及创作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杨木华诞生:巴金的患病体验
抗日战争时期,巴金曾患病住院。医院里人和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段经历给他的身心带来了极大创伤。这种创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巴金手术后的个人体验,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医院里的现实困境。
巴金的个人体验主要指手术后身体上的痛苦以及心灵上的孤独。虽然他并不在意医院外部条件的恶劣,但也会因手术后的痛苦而感到煎熬。“手术完毕,麻醉药性已过,我感到极不舒服……在疼痛难熬的时候,在心烦不能睡眠的时候,我会单纯的像一个少年。”[1]感官在手术后被无限放大,巴金也变得愈发敏感。他希望能够得到医护人员的鼓舞和安慰。然而,现实往往与人的期待是悖离的:“可是医生们并不注意病人的心灵,他们倒习惯于把病人当成机器,认为只有用科学医治百病,甚至于吝啬一个好意的微笑或者一声亲切的招呼。”[2]医生对病人心灵的漠视,打破了巴金的幻想,让他认清了现实。他在医院里更多看到的是“医生粗暴地批評病人”[1]以及“医生跟病人吵架”[1]这类情形。这些经历让巴金明白了,他的鼓舞是一种奢望。清醒的认知使他的内心愈发孤独。
现实困境来自医院环境的恶劣,这种环境的恶劣不仅表现在外在条件上还体现在医院内部制度里。从外部环境上来看,“那间真实的外科男病房一共有三十四张床位,因此也显得更拥挤,更嘈杂,更不干净。在那里的生活可能也更不舒适。”[1]巴金纵然有着极强的意志力,却也无法长久适应。从内部制度来看,整个医院都被金钱支配着,充斥着阴暗和冷漠。“在这个病房里病人得用现款买药,自己不买纱布就不能换药,没有钱买药就只有不停地给打盐水针。”[1]医院里的人对病人生命的漠视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对此,巴金也曾发出质问:“你虽然害着可治之症,你没有钱买药,医生们也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去。”[2]医生的职责在于生病救人,但一些人早已成为金钱驱动的奴隶。眼前的情景无疑打破了他对医护人员的固有认知。 “我至今还不曾忘记他那充满痛苦的号叫。他在断气之前不知道叫了多少声,却始终没有人为他做任何事情。只见工友来把他那只鲜血淋淋的胳膊绑在板凳腿上。”[1]巴金亲眼见证了工友的冷漠无情,这也让他的内心的惊惧和悲哀愈来愈深。他常常在病床上反问自己:“这种种不合理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1]愤慨眼前的种种不公的同时,他也会因自己对现实束手无策而感到痛苦。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幻想的动力是未得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感到不能满足的现实有关联。”[3]在身心俱创后,巴金将希望寄托在具有现实支撑的幻想上:医院虽有冷漠无情的人,却也不乏善良的医生。“我也听见他们(他和她,我特别提出‘她的字,我觉得那些十七八岁的护士小姐都是很纯洁的、很善良的)不止一次地发过牢骚。”[1]经历了绝望和痛苦后的巴金看到为病人打抱不平的医生时,熄灭的热情再次重燃。这些十七八岁的女医生的单纯与善良给了巴金希望。因此,巴金在《第四病室》中塑造了杨木华医生这样一个人物。他的希望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满足,这让他将幻想和情感寄托在了杨木华医生身上。正如巴金所说:“受到疾病折磨的人的心灵仿佛干枯的禾苗,多么需要甘霖。”[1]巴金在这种愿望的支配下,“一天一夜、一点一滴地创造了杨大夫的心灵。”[1]巴金在遭受种种痛苦之后,塑造了《第四病室》中的杨木华这一理想人格,因此,在她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巴金的影子。
二、杨木华形象:病室中的一丝亮光
现实里的第三病室的外部环境恶劣,内部制度腐朽;书中的第四病室亦脏乱拥挤,到处都是床和人。医院里金钱支配着一切。没有钱的病人受到医生和看护们的漠视,无法得到合理的治疗。病室里哀号声不断,病人之间也会相互嘲笑,对此医护们习以为常。医院里人性凉薄,充斥着黑暗、麻木与罪恶。杨木华的出现无疑“给这阴沉、冷酷的地狱送来一丝亮光,温暖着人的心”[4],也为身处黑暗的病人带来了一丝生存的希望。
杨木华年轻善良且富有热情。作为医生,她不仅关注病人的生理健康,也关注病人的心理。一方面,她注重病人的生理健康。她会关注二号床病人的饮食以及日常生活,也会关注陆怀民的情况。“杨大夫在第二床旁边停留片刻,就走到我的床前来。‘你这样睡着觉得闷罢,她说着,大方地一笑……她的笑使我感到愉快。”[5]她的微笑和鼓舞是陆怀民急需的,也是巴金所渴求的。正如巴金在《谈〈第四病室〉》中所说:“我感到极不舒服时我多么希望有人对我讲两句安慰和鼓舞的话。”[2]杨木华的性格和行为里融合了病中的巴金对医生的憧憬。另一方面,她深入病人的心理,注重对病人在精神上的安抚。巴金在创作回忆录中提道:“她不过是这样一位年轻的医生:她不是把病人看做机器或模型,她知道她们都是有灵魂、有感情的人。”[2]杨木华她关注病人的情绪,希望病人能够从书中获得忍受痛苦和困难的勇气,她真诚地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够“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2]杨木华时刻都在努力为病人们减轻痛苦,给予他们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我是这样想:只要你在场,我一定不害怕,我率直地答道。‘那么我一定在场,她似乎感动地说。”[5]杨木华对陆怀民给出了职责之外的承诺,可贵且真切,这也正是陆怀民所渴求的。
在人性凉薄的第四病室里,杨木华的出现无疑是黑暗深处的一线亮光。然而,她只是在大环境下挣扎的小人物,仅凭个人的力量始终无法与时代对抗。她的改变并不彻底,且受制于现实。正如巴金所说:“是的,杨大夫一定会接受改造的。过去她不是革命者,也不是一位进步的民主人士。”[2]相较于医院里其他医生,杨木华会关注病人的心理,也希望能够改变医院的现状。但阴暗的第四病室里真正有觉悟的人太少,仅靠她个人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她只能选择适应,甚至逃避。当陆怀民质疑头等病房的病人拿掉胆囊是因为他有钱时,“她受窘似地红了脸”[5]她的反映暗示了真相正如陆怀民所预料到的:如果没有金钱,即使是可治之症也得不到治疗。杨木华的窘迫背后饱含了种种痛苦、挣扎与无奈,在她离开前,她选择了直面这一切。“我倒有责任……就是我学医学到了天大的本领,也不见得便能够救人。我敌不过金钱。没有钱的人得不到我的好处……这样敷衍地对付过去,我等于在杀人。”[5]杨木华深知自己之前的行为是违背本愿,“但是在那个环境里她能够做什么呢……她也只好让那些本来可以不死的贫苦病人一个跟一个呻吟、哀号地死亡。”[6]因此,在现实境遇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唯有离开,到前线医院,这是她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唯一选择。第四病室的阴暗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医院的腐败象征了一个时代的堕落。在黑暗腐朽的大环境下,杨木华始终是个小人物。
三、杨木华的发展及其意义挖掘
杨木华的出现不是偶然,她的诞生具有必然性。杨木华是巴金人道主义这一惯有思想下的产物。相比于巴金前期作品中的人物,杨木华这一形象的塑造没有强烈的革命性,甚至还存有一定的局限。这局限背后正是巴金创作心态的反映。巴金追求光明的创作心态影响了杨木华这一人物的结局。
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他一直怀有一颗鞭挞黑暗追求光明的心。早期的激流三部曲揭示了封建礼教对人的残害,宣扬五四时期的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精神。其中觉民和琴为了自己理想以及婚姻而同封建礼教进行反抗,虽受制于现实,却也起到了一定警示作用。《憩园》中的万昭华渴望追寻自由,却被困于憩园这一方小小的天地。只能通过阅读小说来实现自己对自由的追寻。《寒夜》中的曾树生渴望打破传统的观念,实现自我的价值,却悖离了那个时代的顽固思想。觉民、琴、万昭华、曾树生以及杨木华都是在大环境下苦苦挣扎的小人物,她们或为自己的婚姻而反抗,或为理想和自由而斗争。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虽无法改变那个时代,却也能激荡起浪花,给人以警示。从早期的《激流三部曲》到后来的《人间三部曲》,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始终贯穿其中。
巴金笔下的杨木华等人是在大环境下苦苦挣扎的小人物的代表,他们融合了巴金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激流三部曲》取材于巴金真实的经历。巴金亲眼看着亲人们相继沦为了礼教下的牺牲品,却束手无策。这让巴金极度痛恨封建制度。因此,他在觉慧等人身上融合了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憩园》也是巴金在目睹故居颓败之后生起了奇异的情感,万昭华、黎先生对姚、杨两家的帮助,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第四病室》中杨木华善良热情,她对病人生理和精神上的关怀也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巴金面对的医生更多是注重对病人身体上的治疗,而忽略了病人的心理上的安抚。杨木华医生是巴金的内心所憧憬的医者形象的投射,融合了他接触的医生形象和行为,也承載了他的寄托。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杨木华并不是真人, 真实的只有他的外形。我作为一个病人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位医生, 我编造的是自己的愿望, 也是一般病人的愿望。”[4]在潜意识里,巴金渴望能有一位医生用温言暖语鼓舞他,给予他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所以他在《第四病室》中虚构了杨木华,并在她身上放置了自己理想的人格。因此,杨木华的产生是巴金个体生命体验中的惯有思维的产物,她的诞生具有必然性。
但相较于以上人物,杨木华是特殊的:杨木华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她对时代的反抗并不明显。为了更契合杨木华的这一形象,巴金将《第四病室》中杨木华送给陆怀民的书由倡导自由平等的《在甘地先生左右》改为提倡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与觉慧等人不同的是,杨木华没有完全实现自我思想的转变,更没有想过要改变大环境。在那个时代下,杨木华的诞生是必然的,她这并不完全的自我觉醒也终将使她走向死亡。
杨木华医生虽承载了巴金的理想,却也抵不过现实。巴金在《谈〈第四病室〉》中提到过:“在小说的《小引》里我终于写出了杨大夫死亡的消息……我很想明确地说像杨木华大夫那样善良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里活不下去,她一定会得到悲惨的结局。”[1]相比于其他人,她与巴金的个人体验相关,对巴金的影响更久,甚至让一向追求真实的巴金改变了她的结局。最初,巴金十分肯定杨木华的死亡,他在书中写道:“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且热心地帮忙着抢救受难的人……她自己也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5]但后来他认为,“我自己也受不了那种等于空虚的渺茫的希望……我愿意让这样一个人长久地、健康地活下去。”[1]经历了抗战时期的磨难后的巴金,心灵一片枯寂,对光明和希望的渴求愈发强烈。因此,巴金在成都校改这部小说时,改变了杨木华的结局。他在《小引》上加了一段,暗示杨木华在四川改名再生,额上还留着一块小伤疤。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巴金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愈发强烈。他曾说:“我要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伟大的人民,歌颂伟大的领袖。”[9]于是他怀着火一样的热情和希望继续踏上创作之路。这一时期他接连出版了《华沙城的节日》《保卫和平的人们》《友谊集》《倾吐不尽的感情》等一系列散文。巴金在这些散文之中传达了对新中国的美好愿景。“文革”后巴金重读《第四病室》时,心中依旧怀有热情。正如他所说:“重读它我更加热爱生活……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经很有限、很有限了,我还是在想:‘怎样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2]杨木华这一形象诞生及发展见证了巴金心态的变化,对巴金后期的创作亦影响深远。由此可见,杨木华这一形象塑造及其结局变化都具有必然性。
四、结语
第三病室里的种种经历给巴金留下了深刻印象。医生对病人的漠视引发了巴金本人的不适。身心煎熬下的巴金将未得满足的幻想寄托在杨木华这一人物身上。杨木华身上承载了理想,却也关联着现实。在阴暗的第四病室里,她空有仁爱之心,却不会反抗,始终只是一个小人物。杨木华这一形象的塑造及其结局变化具有必然性。从巴金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来看,杨木华是巴金一贯人道主义下的产物,但她相较于巴金同时期及之前作品中的人物更具人性的真实性,她的身上没有强烈的斗争性和反抗性,这也是这一人物的独特之处。杨木华的诞生及发展与巴金的心态密切相关,巴金心态的变化带来了杨木华结局的变化,他将杨木华这一理想人格放置在阴暗现实中,却又因悲悯之心改变了她的结局,没有将赤裸人性和阴暗现实贯彻到底,透过这样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巴金在当时思想上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文集第十四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422-427.
[2]巴金.巴金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492-595.
[3]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M].包华富,陈昭全等编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38.
[4]彭小花.巴金的知与真[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07-224.
[5]巴金.第四病室[M].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1946:4-300.
[6]巴金.巴金文集第十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426.
[7]巴金.巴金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巴金.巴金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229.
[9]巴金.巴金近作[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
[10]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祁瑞,重庆开州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级本科生。
孙洁,重庆奉节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级本科生。
——评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