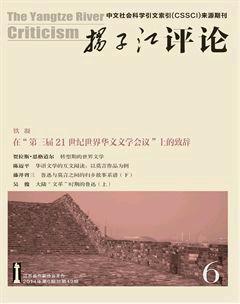当代文学研究之人道主义维度的建构努力
——评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
王春林
当代文学研究之人道主义维度的建构努力
——评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
王春林
如果从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算起,中国当代文学存在发展的时间就已经差不多有65个年头了。正如同中国当代文学本身成绩的突出一样,这么多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不可小觑的可观成绩。然而,在看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得必须承认,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其中,不容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人道主义角度研究的明显匮乏。假若我的记忆无误,早在1986年,在纪念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先生所作的主题报告《论新时期文学主潮》一文的基本主旨,就是力图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而对于新时期文学有所概括。但或许因为人道主义在中国当代曾经长期遭到排斥打压的缘故,此后尽管也不乏有研究文章坚持从人道主义角度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潮流派与作家作品有所探讨,但迄今为止,我们却一直都没有一部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进行整体性深入剖析的研究著作。假若承认我们以上观察的合理性,那么,王达敏的这部《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2月版),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做是国内第一部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于长达将近65年历史的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系统梳理分析的学术专著。这部研究专著的问世,标志着王达敏教授在确立中国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研究维度方面所作出的扎扎实实努力。如果说人道主义思想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文学之魂的话,那么,王达敏的研究显然就是在为中国当代文学招魂。对于如此一种具有突出的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建构努力,我们理应表示充分的敬意。
在业已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学研究生涯中,王达敏一贯以严谨认真而称道于学界。轻易不做结论,一旦做出某种学术结论,则肯定会言必有据,可以说是王达敏文学研究一个突出的特点所在。这一特点,在这部《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中同样有着极其鲜明的体现。体现之一,就是一种严谨周全的理论建构。要想完成一部理想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首要的问题,就须得弄明白究竟何为人道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王达敏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简单地给出一个定义就了事。细读此书,即可以发现,围绕人道主义定义的提出,王达敏最起码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在一个宏阔的视野内对于人道主义的历史演进状况及其不同的表现形态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深入考察。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道主义起始,中经中世纪基督教人道主义、文艺复兴至近现代人道主义、俄罗斯“新精神哲学”人道主义,一直到包容了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哲学的反人道主义、世俗人道主义以及生命伦理人道主义等几种不同样式在内的20世纪多元化的人道主义,作者以言简意赅的方式,对于人道主义思想在西方的演进流播情形做了精准的概括与扫描。其二,以否证和排除的形式逐一对比说明人道主义不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工作,王达敏自己在书中有着很好的说明:“关于人道主义是什么,前者用的是加法,即在追问何谓人道主义与辨析人道主义历史及其形态中,确定人道主义质的规定性及在历史演进中累积的特定内涵。后者用的是减法,即用否证法和排除法减去混存于人道主义中的‘杂质’和‘他物’,最终留下来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人道主义的‘沉淀物’。”在这一部分,王达敏引经据典,在充分比较的基础上,澄清了经常会混淆在一起的人道主义与“人性”、“道德”之间的异同关系。其三,简洁地引述介绍了若干有代表性的关于人道主义的定义。正如同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人们对于人道主义的理解也可以说是言人人殊各不相同。由于定义众多,所以王达敏只能够择其要者区分为三个层面加以展示。一个层面是诸如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哲学百科全书》以及中国《辞海》等相关词典与百科全书中的说法,一个层面是世界一流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解释,另一个层面则是当下时代中国三位学者给出的定义。正是在以上三方面充分准备的前提下,王达敏结合前人的思考成果,根据自己的体会,明确地给出了自己对于人道主义的定义:“为了使我的这个课题能够顺利展开并对人道主义的解释有所推进,我必须给出一个我所认定的人道主义定义。这个定义既要符合人道主义质的规定性,又要体现出人道主义对于现实建构的目的性。我的定义是:人道主义是一种从人性、人道的立场出发,以善和爱为核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存、权利、尊严、价值,以人的自由、幸福和发展为最高目标,具有人类性、普世性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和平、宽容、同情等)的伦理思想或思想体系。当它演进成势时,便形成了思潮或运动。”这一定义的明确提出,对于这部《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的写作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人道主义概念的提出固然重要,但对于一部具有鲜明文学史性质的著作来说,更重要的理论建构,恐怕却应该体现在相关文学史概念的处理上。与人道主义概念的给出相比较,王达敏更具原创性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首先是从启蒙人道主义到世俗人道主义这样一种发展过程的提出。在王达敏看来,人道主义在已经长达将近65个年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可以被切割为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的起止时间是1949年到1966年。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时代文化语境强力打压的缘故,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阶段有过良好表现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处于特别式微凋零的状态之中:“受战争思维和政治阶级论主导的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被动地接受了这一悲剧性的现实,并在现实政治的规约下,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强行纳入到阶级论的构架之中,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理论’、‘修正主义意识形态’。”既然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之类的语词搭配在一起,那么,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被无情放逐,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基本事实。惟其如此,人道主义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也就只能是:“具体到文艺界,一边是作为文学之本性、之血脉魂魄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或自然而然地流露,或有节制地机智闪现,或借机破冰而出,形成一股时大时小、时断时续、时隐时现的潮流;一边是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意识形态调动比这不知要大多少倍的力量对其进行压制和批判。”正因为人道主义在政治的高压之下只能够偶一现身,所以这个时期人道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便乏善可陈。而王达敏的学术原创性,也只有到面对另外两个时期的文学时方才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第二个时期的起止时间是从1978年到1989年,这一时期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1980年代。在具体关注王达敏关于这一时期启蒙人道主义的定位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他一种具有相当洞察力的宏观描述。在把百年来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划分为三个三十年的前提下,针对最后一个三十年,王达敏写到:“第三个三十年,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潮在新一轮‘现代性叙事’中再次崛起,并形成了丰富而深入的逻辑演进的态势,即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启蒙人道主义演变成90年代以来的世俗人道主义。我注意到,学术界对其的关注,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在新时期初期的启蒙人道主义上作低空盘旋,未能发现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人道主义思潮——世俗人道主义思潮。”一方面是关于启蒙人道主义的研究尚且很不到位,另一方面是世俗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阙如。这就为王达敏的相关研究预留了极大的空间。先来看作者关于1980年代启蒙人道主义见解。“从1980年开始,……举凡一切优秀之作,尤其是那些产生了轰动效应又引起广泛争鸣之作,不是因为思想尖锐深刻,就是因为表现了丰富敏感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更多作品是二者的融合。文学史显示,从70年代末出发的人道主义思潮,到80年代初中期就汇成了一股以思想启蒙为特征的人道主义思潮,即启蒙人道主义思潮。”应该注意到,王达敏之给出“启蒙人道主义”的命名,明显地受到过欧洲18世纪的启蒙人道主义的影响。而且,王达敏是在一种广义启蒙的意义上使用启蒙概念的。所谓广义的启蒙,“则是指一切唯客观真理是求的理性活动,是指人类思想史上与当前现实中一切反封闭、反黑暗、反僵化、反蒙蔽、反愚昧。总之一句话就是反精神奴役的思想运动与文化精神。”
然而,与1980年代的启蒙人道主义相比较,王达敏的理论能力更显示在关于世俗人道主义的概括提炼与理解定位上。在王达敏的这部著作中,所谓世俗人道主义,就是指出现于1990到2010年之间的一种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尽管说世俗人道主义的命名很显然受到过美国哲学教授库尔茨所提出的世俗人道主义相关论述的影响,但因为迄今为止只有王达敏一位学者率先用世俗人道主义来指称1990到2010年之间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所以其学术原创性的存在,当然毋庸置疑。在王达敏的理解中,世俗人道主义思潮主要由人性本位人道主义、生存伦理人道主义、生命伦理人道主义以及理想∕审美人道主义四种不同的样态组成。但较之于这样的四种分类,最能够见出王达敏理论构建力的,还是他给出的关于世俗人道主义的命名阐释:“新时期世俗人道主义是中国语境中产生的一种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与西方的启蒙—人本人道主义、美国的世俗人道主义、新时期的启蒙人道主义比较:启蒙—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世俗性’是相对于中世纪的神本主义而言的,‘世俗’是先被人文主义继而被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当作启蒙的现实依据,新时期世俗人道主义则是从‘启蒙’中抽身而出,专注于世俗伦理和人性本位的人道主义;美国的世俗人道主义是民主的、无神论名义下实施的无边的人道主义,新时期世俗人道主义则是自我定位的、伦理和人性本位的人道主义;新时期启蒙人道主义是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明显的人道主义,意在用人道主义实现启蒙之目的,世俗人道主义疏远甚至脱离政治、意识形态、阶级论等权力的控制而回到人道主义自身,以人性来表述的具有世俗伦理取向的人道主义。总之,世俗人道主义是自我定义的、伦理和人性本位的人道主义,它从人性、人道的立场出发,以善和爱为核心,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生存、生命、自由、尊严、权利和价值,其世俗的伦理观念直接与人道主义的人类性和普世性观念相通。”就这样,通过与西方启蒙—人本人道主义、美国世俗人道主义以及新时期启蒙人道主义之间堪称纵横交错的参照比较,王达敏最终给出了自己对于新时期世俗人道主义主要内涵的一种基本理解。
其次,是王达敏关于中国当代同情人道主义的理论辨析。之所以在全面梳理了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状况之后,要专门单独辟出一章来专门讨论同情人道主义文学的问题,就足可见出这一问题在王达敏论述框架中的重要性。在这一部分,王达敏论述到:“文学中的同情是一种高贵的感情,它既与心理学意义上的同情有别,也与伦理学意义上的同情不尽相同。它属于伦理范畴,但它的本源性和普遍性又决定它具有超越性,能够在更大范围被人道主义涵括,使之成为人道主义思想中最本原、最普遍、最直接、最强烈的情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叙写始于同情,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在‘五四’新文学、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中,同情常常代人道主义发言,成为人道主义代言人。基于同情的人道主义,我称之为‘同情人道主义’,是镶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乃至新世纪文学上的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显在标志。”在承认王达敏论述所具合理性的同时,稍微感觉有点遗憾的是,既然作者强调他所命名的“同情人道主义”有着突出的民族特色,那么,由此而必然导引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其他国家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思潮,人道主义肯定是人类文学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照理说,要想得出“同情人道主义”具有民族特色这一结论,就必须与其他国家的人道主义文学进行相应的比较。只有在充分比较的前提下,才能够断言“同情人道主义”是“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显在标志”。遗憾处在于,我一直没有在本书中找到进行此种论述的痕迹。正因为缺少了这样一个环节,所以论述的说服力也就多多少少受到了一点影响。但在这一点缺憾之外,王达敏这一章的总体论述,却具有着充分的逻辑说服力。作者首先介绍了对于“同情现象学”有着深入研究的哲学家舍勒发现的“同情”的四种形式,即“情感共有”、“情感参与”、“情感传染”以及“情感一体”。然后,又大量引用中西方学者的观点,论证说明“同情”既是一切美德之本源,也是人道主义生成的原点。在此理论基础上,王达敏的落脚点最终回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抽象概括地描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同情人道主义文学的发展演进过程。在充分肯定中国当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同情人道主义文学取得成就的同时,作者也不无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同情人道主义文学所存在的不足:“但是,即使是这些优秀之作,也还有待超越生命存在意义而进入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如果拿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与19世纪以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为代表的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相比,其差距立见高下;就是与20世纪西方全力反思历史和战争,已经进入深刻反思人性和人类的《钢琴家》、《奥斯维辛的爱情》、《美丽人生》、《辛德勒的名单》、《拯救瑞恩大兵》、《命运无常》、《朗读者》等作品相比,也缺乏这些作品超常的深刻性和巨大的震撼力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的未来之路,需要在这两个方面作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建构。”
如果说严谨周全的理论构建是这部《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第一个突出的特征所在,那么,这部著作另外一个突出特征,自然而然也就体现为王达敏对于若干重要的作家作品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切入进行了非常富有学术新意的解读与阐释。举凡张贤亮、鲁彦周、贾平凹、苏童、戴厚英、余华、严歌苓等重要的人道主义作家,都在王达敏这里得到了一种充分个性化的人道主义分析。人都说,窥一斑而知全豹。这里且以方方的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为例,说明一下王达敏人道主义解析的个性特色。王达敏是把方方的这部作品作为一部“忏悔—赎罪型”的人道主义作品加以理解的。或许是因为中国人普遍缺失宗教信仰的缘故,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鲜有纯正地道的“忏悔—赎罪型”人道主义作品。在作者看来,一直到“2008年,随着方方长篇小说《水在时间之下》的发表出版,‘忏悔—赎罪型’人道主义终于‘春暖花开’,结出硕果。”在关于小说主人公水上灯之“复仇”、“人性搏斗”以及“忏悔赎罪”三阶段的论述中,尤以以下这段对比性的话语值得注意:“水上灯苦难、复仇、赎罪的一生,在人性演变和人道主义建构上,与《德伯家的苔丝》、《巴黎圣母院》、《复活》、《罪与罚》等‘忏悔—赎罪型’人道主义之作有着一致性。所不同者,《复活》等作品人物的忏悔赎罪经过宗教伦理的引渡而进入人性升华、灵魂复活的崇高境界,而水上灯的忏悔赎罪则由世俗伦理的引导而走向既基于民间又超越其上的自在人性,其‘忏悔—赎罪’的人道主义则体现出中国化特色。”
与对于一系列作家作品的精到人道主义阐释相比较,我以为,王达敏此著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业已被文学史冷落了很多年的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发现。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刘克。对我而言,尽管此前也隐隐约约还记着曾经有过刘克这么一位作家,但除了那部名叫《飞天》的小说之外,他到底写过一些什么作品,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品质究竟如何,我其实都一无所知。只有在读过这部《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之后,我才发现,其实刘克真的是一位被文学史长期遗忘了的优秀人道主义作家。比如,刘克的《古碉堡》,就绝对应该被看作是一部优秀的人道主义小说。小说所集中展示的,是一个名叫曲珍的藏族女性的命运悲剧。而曲珍的悲剧成因,却与她那种特殊的活佛小老婆的身份密切相关。故事开始于西藏民主改革时期,活佛外逃,曲珍被迫留在国内,住在山上的古碉堡里。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如何对待曲珍,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立场。一种是以薏西卓玛为首的大多数古热村村民。或许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这些民间伦理的体现者,是曲珍坚定的保护者。一种是阿望和洛布顿珠。前者是卑鄙小人,尽管曾经与曲珍有过爱情,但极端自私的他,却在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后者则是“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思维极端化的产物,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他坚持要严惩曲珍。另外一种,则是身兼叙述者角色的“我”,古热村工作组的组长。“我”的立场带有鲜明的两难特征:“从革命的和阶级的立场出发,‘我’厌恶活佛小老婆,当‘我’看到凄伤的曲珍怀抱着孩子孤立无助时,无意间,‘我’感到‘这是一个可怜的女人!’”经过一番两难心境中尖锐激烈的内心冲突,最终还是一种发自人性深处的同情与悲悯心理占了上风,“我”决定不惜自毁,也要想方设法为曲珍平反。小说最后的悲剧性结果是,“为了彻底断绝‘我’为她平反的念头,曲珍在雨夜追赶到‘我’回拉萨途中住宿的古驿站,站在门外向‘我’告别,合掌为我祝福,然后跳崖自尽。”
能够在1980年代初期就注意到身份问题的重要,刘克的《古碉堡》在这一点上可谓占尽了风气之先。惟其如此,我才特别认同王达敏对于小说及其作者刘克给出的最终文学史定位:“同情受苦受难受迫害的不幸者,是人道主义最基本的命题,这篇反思中国当代历史的小说,正是对人道主义这一命题所作的新的演绎。在人道主义长期被防范、被监控,直至新时期文学初期仍然没有完全被解禁的情况下,刘克于1981年写出了这样一篇思想尖锐,并且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实在令人敬佩。《古碉堡》已经成为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滥觞之作,文学史应该记住《古碉堡》和《康巴阿公》等小说,以及它们的作者刘克。”
任何一部优秀的著作,也都难免会存在一些缺憾。尽管存在着一些缺憾,但从总体上说,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研究还十分匮乏的情形下,如同王达敏这样一部《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的出现,也还是非常及时的。其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意义,非常显豁。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计,对于王达敏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人道主义维度的建构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肯定。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