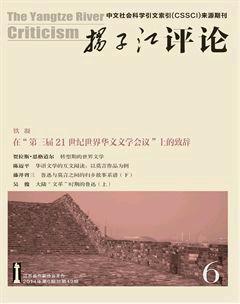徐晓鹤:绝望中的笑声
杨小滨
徐晓鹤:绝望中的笑声
杨小滨
徐晓鹤小说的深刻重要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彻底发掘。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琐碎和荒谬的行为给快乐的误喻提供了途径,主流话语并没有受到严肃的抵制,却在把握特定的社会或群体中悲惨痛苦而又毫无意义的处境时遭到毁形。对徐晓鹤来说,无能为力的表现意味着,惟一的表现途径就是让人陷入现有话语的陷阱,这个陷阱始终诱使现实误入表现彻底失败的荒谬处境。
徐晓鹤在1983年转入小说写作,在此之前他曾经是偶尔被归为“朦胧诗”的诗人。他最初发表的短篇小说《残局》,从标题看就暗含了与著有剧本《终局》的贝克特(SamuelBeckett)之间的某种血缘关系:贝克特对现代社会中语言和交流的怀疑同样指明了徐晓鹤小说的某种倾向。尽管这篇小说还不像他后来的小说那么具有美学的颠覆性,但《残局》出色地展示了叙事的“空白”。故事中最紧要的悬念,即“老汉”守了一辈子的残局让“后生”破了之后赢去的铁盒里的奖品究竟是什么(贵重到了“后生”觉得“受不得”而到处打听老汉的去处以便归还),到小说结束时仍然是个谜。这样的技巧在1985年以后的先锋作家,如马原和格非等人那里获得了普遍的运用。
徐晓鹤小说唐突滑稽的风格介于马原、格非与残雪、余华之间。他对文革话语似是而非的附着是显而易见的。他与残雪和马原的区别在于他对群众从个人与集体对波澜壮阔和颠倒是非的历史事件的体验中演绎而来的不仅是反讽的而且是疯狂闹剧般的呈现。
叙事的非理性与主流话语
徐晓鹤的“疯子”系列始于1985年的中篇小说《院长和他的疯子们》。他后来大部分作品中的背景和人物都是从这里发展而来的。像其它“疯子”系列中的作品一样,小说没有什么中心情节,而是展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境遇,其中正常与失常似乎无法区分。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院长追逐“越狱”的疯子的景象,而村民们则比鲁迅笔下的看客生动许多,“跟着一并去甚嚣尘上”。这个开始预示着徐晓鹤的一种对荒谬的兴趣,因为看起来村民们并不比疯子们更正常,疯子反倒由于负担着“逃亡的使命,复又跑得张牙舞爪”。重要的是,这种荒谬是在一种颇为普通或正常的形式中展现出来的。村民们从疯人院的墙外看见的疯子们的集合是这样的:“有几个排成队笔直地走路,碰了墙就拐一百八十度的弯打转。有的唱歌,越唱声音越大。有的做演讲,将手指戳到另一个的脑门上,另一个只好抱头鼠窜。有个女疯子摘了一大把夹竹桃,喊着欢迎、欢迎。”①
如果我们不能觉察到一种近乎寓言的内涵,一种对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透视,这里的荒谬性就不会令人震惊。无疑,对过去的记忆痕迹悄悄地潜入了叙事过程之中:诸如“军训”、“批斗会”、“欢迎会”这样高度政治化的仪式一并以缺乏理性和目的的方式扭曲地再现了。在另一个段落里,一个逃亡的疯子好像主流文艺中的地下工作者或伤员(比如在样板戏《沙家浜》里)一样受到了群众的掩护和款待,却由于忍不住“咯咯地笑”而暴露了身份,被捉回疯人院。这些可能成为经典场景的叙事片段在疯人院的现实背景下被漫画化了,主流文学的那些“原型”——英雄、同情者和敌人——的关系遭到了戏仿。
对于院长来说,疯人院是一件宏伟的事业,他甚至劝说并不疯的人也搬进疯人院来住。这里,徐晓鹤专注于一种叙事语调,以强化院长这项事业的反讽功能。当院长“亲切地”②邀请后来证明并不疯的苏神经到疯人院去的时候,苏神经给了他一个耳光,使得院长“雄赳赳的脸上,写五根鲜红的手指印”③。首长式的“亲切”,英雄式的“雄赳赳”和同烈士或理想有关的“鲜红”被带入了荒唐的境遇,使在这些担负有强烈意识形态使命的语词背后的主流话语遭到了瓦解。在小说接近尾声时,疯人院改建成了一所学校。院长却仍旧不甘心退休,又下乡动员办一个更大的疯人院,却在示范拖一个疯子到水塘洗澡的时候失足落水,使其宏伟的“事业”示范出了颇为荒诞的意蕴。最后,院长在疯人院周围挖土沟,不知是不是“干部参加劳动”④,也“不知那沟里,春天会不会游出扭尾巴的蝌蚪来”⑤。就这样,主流话语,包括展望未来的象征性话语,被一种无关痛痒的、难以确定的叙事所消解。
徐晓鹤1986年的短篇小说《人或红毛野人》同样以寓言的方式探讨了中国特定文化状态下的话语和真实:一项虚幻的“伟业”被揭示为仅仅建立在某种话语之上,并且,话语的统治从不实现它对真实或真理的允诺。小说通过把空谈中的“野人”设立为中心,戏仿了追求原始价值或本质的“寻根文学”。整篇小说不分段,一气呵成地记述了一群声称为红毛野人目击者的集会。虽然红毛野人作为话语的核心令人振奋,但人们对证明红毛野人的努力却只能抵达徒劳的结局。这里,对政治运动中的群众集会的记忆再度浮现了,但占据主要地位的却不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蛊惑,而是盲目的大众狂热。集会中的人都不知姓甚名谁(像鲁迅的那篇迄今被忽视的杰作《示众》里的看客一样),因为没有人具有个体的确定身份。不管“红毛”的“红”是否有意暗示了特定的色彩,“毛”是否有所特指,“红毛野人”在这里的确成为具有神话般召唤力的口号。
集会上有人声称曾与红毛野人握过手,但他出示的红毛在传阅了一圈之后已经不那么红了。红色的褪色指明了这个辉煌的象征色彩不稳定、无法持久,这使集会者开始怀疑关于“红毛野人”的神秘话语。但无论如何,叙事者的声音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中。众人在听到这个人曾与红毛野人握过手时,“大家立刻把那只手如同一面旗帜一样围起来”⑥。“旗帜”一词(以及在其周围围拢)的意识形态庄严感嫁接到了同野人相关的一只手上,显得滑稽而突兀。这时,另一群人“推出”了一位年轻后生,说是红毛野人的后代,尽管后生再三表明自己无非是来证实见过红毛野人的而已。一个老汉便开始讲述起关于这个被指定为红毛野人后代的后生的冗长故事,却在紧要关头一命呜呼。
此后,遭到误用的主流话语鬼影幢幢地穿插在叙事中,一种指导历史理性的语言基质成为无理性的起源。当众人指责年轻后生“还配作红毛野人的后代!”⑦时,此人却说他已经不是先前那个,那人已经跑了。但红毛野人不能“后继无人”⑧,此人便只好补缺,听到众人责备说“这样子对得起谁”⑨,便只能“羞愧”地在众人的协助和提词之下,继续讲述老汉起头的那个设想自己来历的故事,最后得出了娘被红毛野人从虎口救出“才有你的今天”的结论。⑩既然是话语决定现实,后生必须以爬树来配合关于他是红毛野人后代的说法。在他摔下来崴了脚之后,他还必须思考,如果“真正的红毛野人也许正应该脚朝一边歪”,他应该如何“无愧于朝一边歪”。可以看出,生活的逻辑完全被诸如“(革命)后代”、“(共产主义事业)后继无人”、“对得起(先烈)”、“(党救出劳苦大众)才有今天”或者“无愧于(党的培育)”这类主义家谱学的话语元素所打乱和恶化,而与此同时,这些话语元素却由于这样的误用而暴露出极度的武断与荒谬。这个貌似随意流动的故事又经过更多的有关男女红毛野人关于谁为“正宗”的争执,最后的结尾是,那个藏有一根毛的人声称藏的只是一片树叶罢了,拿出来果然是树叶。这样似是而非的叙事在许多徐晓鹤的小说中出现,使叙事的可靠性降至极小值。这也是对主流话语的绝对性的一种反动。
从崇高到荒诞
通过各类话语“误用”,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美学在徐晓鹤那里等同于荒诞美学。作为《院长和他的疯子们》的续篇,他1986年发表于《收获》的中篇小说《疯子和他们的院长》把这种荒诞美学推向极致,“反讽是无法缓和的眩晕,抵达了疯狂的顶点”⑪。在故事层面上,小说描写了疯子们在院长领导下的所谓“东征”。这不仅令人想起“北伐”、红军的“北上抗日”或者主流文学中的《南征北战》,或者还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全国串联有某种联系。在上篇《院长和他的疯子们》里,院长就企图要建一个“集各村疯子之大成”⑫的疯人院,而这篇小说可以算是对这种愿望的一次满足,是一场死之舞,或否定意义上的巴赫金式的狂欢节。整篇小说描写了院长组织的(或不如说是搅乱的)疯子们所谓的“东征”(多么辉煌的名称!)。
实际上,小说却并未提供任何可以复述的中心情节,只有疯子们种种可笑但却颇为认真的表演。比如,疯子们在“东征”的具体路途中——跨过“铁桶、钢锭、木箱、四轮推车、馊水缸、汽车轮胎、鼓风机、扫把、蜘蛛网、青苔、万用电表”,过一会儿阵脚大乱又回头跨过这些“表电用万、苔青、网蛛蜘、把扫、机风鼓、胎轮车汽、缸水馊、车推轮四、箱木、锭钢、桶铁”⑬。读过文化大革命中“样板戏”剧本的人可能会记得,这样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戏仿了对现代京剧舞台上“革命群众”的英雄式表演的描绘。⑭在另一处,徐晓鹤戏仿了主流文学中对领导者的描写:“他套上湿糟糟的裤衩,重又打开灯铺一张白纸继续描画疯子院的前景。很多年过去了,那前景越来越五彩缤纷。农民们撑着锄头饶有兴致地听他讲演,关于疯子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⑮“一张白纸”明显挪用了“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而强烈地召唤了农民阶级的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宏大历史却换上了疯人院的背景。而疯子们乱敲钢材奏出的“交响乐”中竟然还混有《东方红》的歌词“呼儿嘿哟!呼儿嘿哟!”
更关键的是,徐晓鹤大量“误用”了崇高的叙事语式,使话语的理性再度同行为的无理性产生巨大的张力。在话语的层面上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意义受到虚妄的行为的强烈质疑。比如,张金娥的娘是这样加入“东征”的:
不小心门板拍在她肚子上,只觉得腹中荡漾了一下,裆里立刻湿了大片。这反而坚定了她的决心,弯下身把门口又压了一块冰凉的麻石,朝茅屋望了最后一眼,扭头加入了疯子的队伍。⑯
熟悉主流话语的读者不难分辨出英雄主义与琐碎卑微、无关紧要的话语之间的反讽裂隙。诸如此类的段落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比比皆是:
男女疯子在桥上会师,纷纷地只是握手。⑰
疯子们兴高采烈要唱很多歌。院长夫人义正词严不准他们唱,他们只好不唱装作没一点事的样子嗯嗯呀呀,其实心里充满了激情。⑱
疯子们从悲怆忧愤中昂起不屈的头颅,鬼一样慌乱,时刻准备着屁滚尿流。⑲
第一段可以被看作是对正统风格的“会师”的历史场面的戏仿,第二段和最后一段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详尽分析。显而易见,对诸如“兴高采烈”、“充满了激情”、“悲怆忧愤”和“昂起不屈的头颅”⑳这类饱含意识形态意味的习语具有高度的反讽性,按理说,这些习语应该被用来塑造意志坚定或者体魄强悍的英雄人物。混淆悲剧(这些习语)与滑稽(疯子的行为)使我们失去了对主流话语庄严性的依赖,将我们从宏伟堂皇的陈词滥调的抽象本质中解放出来。叙事的声音就这样从主流话语的限定中解放出来,但并不是达到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所设想的语言乌托邦,而是朝向了对语言悖论的认知。这段引文的下一个句子立即指出的这种失魂落魄(“鬼一样”)破坏了先前描写的合理性。对英勇的革命党人(比如《海港》里“时刻准备着”的方海珍)和对怯懦的敌人(比如“屁滚尿流”的钱守维)的规范表现混为一体,叙事的声音强制性地扭曲了话语的原有秩序,强化了不平衡或者游离。
类似的反讽裂隙也出现在徐晓鹤另外的作品中。比如在《浴室》(1986)中的洗澡和《标本》(1986)中探究打狗与创建工厂之间的有机联系成为同时是话语的赏趣和心理的恐惧,既然惟一的真实是主流话语的不可质疑的真实性,不管这种叙事的对象如何荒谬。所有这些作品用夸大陈述(overstatement)的方式,强化了高调的意识形态与卑微的历史现实之间的不谐和。对话语原型的戏仿是对那种权力中心的游离,但又没有彻底遗忘那种权力的压迫:压迫以扭曲的方式浮现出来。因此,徐晓鹤作品中的疯狂确切地体现了福柯意义上的对霸权体系的瓦解:
通过疯狂,一件似乎淹没于世界的,揭示其无意义的,以及把自身转化为病理学形态的作品,实际上在自身中占用了世界的时间,把握它,引领它;通过疯狂,一件艺术作品开启了一种虚空,一个寂静的瞬间,一次没有回答的提问,在世界被迫质疑自身之处引发了无法弥合的罅隙。㉑
无论如何,徐晓鹤的小说不是讽刺,因为不仅是叙述的客体受到嘲弄,而是叙事主体自身蕴涵了一种“无法弥合的罅隙”,这是某种威权统治的历史及其话语之下的创伤主体。徐晓鹤的叙事主体不再具有总体化的或全知的力量,而是以破碎的叙事游戏把宏大的线性历史打乱,用异质的和杂质的微量细节颠覆一元的主流话语。因此,真正的无理性不仅存在于疯子们的行为逻辑中,而更存在于主体的叙事逻辑中。以下所引的一段中,叙事过程中的那些连接词就可以看成是主体疯狂的明显征候,因为正是这些连接词所提供的混乱的叙事逻辑,而不仅是叙事中的疯子本身,表达了无理性的状态:
我们第一次看见他是一个下着浓雾的早晨,他湿淋淋地沿着黑河一脚高一脚低地唱歌。张金额的娘挑桶浇菜,三次差点滑倒。小白狗只对他叫了两下就得了感冒,将喷嚏打得死去活来。院长闻声赶来,他还在白茫茫一片中赤足而歌。一会儿凄恻,一会儿悠扬,万般情态。院长装作要过桥,笑笑笑笑,突然伴上去把他捉住。言午许正要狡辩,张金额的娘用粪瓢子从下游舀起一只完整的凉鞋。这才低头无语,住进了疯人院。㉒
在很大程度上,《院长和他的疯子们》展示出宏大叙事无法以正当的方式呈现的一种混乱而无聊的人类景观。这篇小说由此涵盖了中国先锋小说的多种特征:时间错乱、重复、语词游戏、自我否定以及拼贴等等,每一项都是对主流话语统治下的历史的癫狂的揭示,对历史创伤的主体意识的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对疯狂的展现,也是对疯狂的拒斥。正如费蔓(ShoshanaFelman)指出的:“对疯狂的谈论总是对它的否认。……呈现疯狂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表露出对自身疯狂的否认的场景”㉓。和王朔小说中的耍贫嘴不同,徐晓鹤小说中的荒诞是不可言说的,或者说是言说错乱的结果。这也是费蔓所说的“无法总体化的运作,无法控制的语言游戏,其中意义失效,文本的陈述从表演中疏离出来”㉔。也就是说,这种不断否定的游戏以绝望的辩证法揭除了现存的伪善面具。
如果说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代表了五四文学的范例,徐晓鹤的《院长和他的疯子们》则可以被看作是先锋文学的范例。两者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就是两个时代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文学规范的缩影,他们都面临着从旧的、灾难深重的社会文化模式向新的、不可预知的社会文化模式过渡的关键历史转折,尽管他们展望的未来可能完全不同。总而言之,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揭露在意识形态上被现存的话语体系当作理性接受的那种社会非理性。
鲁迅的狂人和徐晓鹤的疯子之间的差异与他们的类同一样显见。鲁迅的狂人是反抗历史压迫的代言人,他把“正常的”和“文明的”社会颠倒成一个反常的和野蛮的社会,而徐晓鹤的疯子们却只能在他们之间引起不断的吃吃窃笑。徐晓鹤的小说呈现了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裂隙或者主体表现的疑惑,疯狂不能魔术般地变为理性,却只能体现疯狂或混乱的真相,这样的真相引爆了利用“理性”力量操纵社会意识的主流话语的总体性。徐晓鹤与前辈的差异在于他否定历史的任何绝对正面意义。如果说鲁迅的狂人的疯狂逻辑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徐晓鹤的疯子则仅仅显示了无序错乱的举止。徐晓鹤揭开了鲁迅狂人的无意识秘密,他的反叙事旨在通过误喻或言语误用展现还原历史“理性”意义的不可能性。他们的区别还在于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鲁迅的狂人背后是一种沉湎于尽管前途渺茫的未来的绝望英雄精神。然而,在徐晓鹤看来,却只有看不到历史进步的悲喜交加的现在,那是一个饱受精神创伤,仍然备受势力强大却又不确定的主流话语折磨的社会心理现在。
鲁迅肯定不是惟一描写疯狂的主要现代作家。徐晓鹤与鲁迅的疯狂概念既相似又相异,这种异同也存在于徐晓鹤与其他作家,比如茅盾和沈从文的疯狂概念之间。茅盾的短篇小说《疯子》(1934)就把疯狂当作对现实中压迫和非人道话语的不可避免的反应。茅盾笔下的疯子阿四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疯子”,而不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狂人”(如鲁迅笔下的);茅盾通过使人变疯的事件来表达他对现实的谴责。在这个故事中,疯子叫嚷道“杀胚!”㉕然而,那只不过是对真正的危险的一种骚乱反应:
只在走近了时,才看得出他的眼光不定,而且他像避猫的老鼠似的在时人们身边偷偷地走过,怀疑地偷相着别人的面孔,似说一切人都会害他。
不是他想杀人,倒是他的被人家谋害罢?我常常这样想。㉖
显而易见,茅盾的讲述模式的叙事试图通过把疯子定义为社会的受害者来认同鲁迅笔下的狂人,尽管他笔下的疯子怀有攻击别人的个人动机。茅盾的《疯子》的出色之处在于小说隐约地意识到现实中话语的构成性力量。小说中的阿绣好几次被描写为一个饶舌的(咭咭刮刮的)告密者㉗。她显然是一个传递传统压抑话语的人物,她的老处女身份象征着弘扬没有性欲和抑制欲望的中国文化。叙事者的结论意味深长:老处女阿绣“这样咭咭刮刮的,所以不会疯吧?”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健全”的基础就是传统话语:那是“健全”的体系通过饶舌,通过把话语禁忌强加给人类心灵而产生的疯狂。茅盾与鲁迅的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也用疯狂谴责“健全”的社会。
在沈从文的作品里,疯子与社会之间的鲜明对照消失了。疯狂被当作一种心境,它以某种方式与社会历史现实保持距离。在《阿黑小史》(1933)中,五明发疯同样也是对爱情悲剧的心理反应,就像茅盾《疯子》里的阿四。作为精神分裂的疯狂在这里被描写成破灭的梦,那是一个暗地里通过追忆在想象中寻求重新整合的梦。另一方面,《山鬼》(1928)讲述的是一个完全脱离社会的疯子的故事。这个非世俗的人物不仅使我们联想起屈原创作的神话原型,而且还蕴涵了承载着人类审美品质的浪漫角色。毫无疑问,这个人物的“少同人说话”(脱离社会话语),“天真”和“任性”的个性㉙概括了沈从文的人文理想观念:“笑不以时候,哭也很随便。他凡事很大胆,不怕鬼,不怕猛兽。爱也爱得很奇怪,他爱花,爱月,爱唱歌,爱孤独向天”㉚。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笔下的疯狂既不是“狂”也不是“疯”,而是“癫”,“癫”这个字指的是固执或者迷醉。疯子的暂时脱离社会必须被看作追求更高的生存方式的一种失败的努力。沈从文的疯子身上具有“一种去拥有被现实或现实主义写作所否定否决的不可能的欲望,一种去整合已经被这些能指所切割了的世界的欲望”㉛。沈从文的“癫”意味着让破碎的现实“破镜重圆”或总体化的深刻“愿望”,那是中国现代作家普遍向往而又无法实现,却又遭到先锋派作家质疑的一个愿望。
戏仿的宏大蓝图
总而言之,沈从文试图在他的叙事中提供的那种模式旨在使本真的存在,与混乱的社会现实相对立的理想本质化,尽管这样的主体努力具有自身的障碍和问题。对徐晓鹤来说,对叙事者,也就是对主体自身的整体性和自足性的质疑才是对现代性话语的真正挑战。他的小说《水灵的日子》(1988)里那些似是而非的、梦境般的场面与其说是对写实主义写作的背离,不如说是对那种表现式写作的主体限度的探索,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主体的质疑。显而易见,徐晓鹤的叙事不再展示叙事者完整的、全能的声音,相反,叙事成为可疑的、不确定的、自我否定的过程。在这种自我否定的过程中,徐晓鹤质问了主流集体话语的个人主体基础。《水灵的日子》中对那条大鱼的最初发觉始于叙事者听见“一个辨不出性别的人在遥远的地方含混不清地唱歌。以为是言午许”,过了几段之后,“忽然我记起那个唱歌的所谓遥远的人其实就是歪角牛”㉜。然而还不是。在下一段里,我们才发现也不是歪角牛:这个“看上去有些疲倦,还不时拿腔拿调地叫那么一两声”的东西“这时听起来一点也不象歪角牛而象一艘即将远航的巨轮”,“而且是远航得乘风破浪的巨轮”㉝。这却是一条蹦起来时“以为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㉞的大鱼。
不仅是叙事的飘忽不定暴露了主体的缺憾,任何熟悉当代主流话语的读者都不会轻易放过“乘风破浪的巨轮”或者“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类习语(cliché)的误用。这种误用,严格说来,正是徐晓鹤小说中寓言性的起源。不是人民公社,也不是改革开放,而是一条半死不活的大鱼,大得出奇、大得绝无真实性的鱼,在这里被比作“不仅仅是远航的巨轮,而且是远航得乘风破浪的巨轮”。徐晓鹤的小说似乎并没有政治寓言的意图,然而我们又无法否认这篇小说的寓言性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关联着我们生存的历史境遇。镇长娇婆蓝(这个形像当然和《疯子和他们的院长》中的院长是相应的,这个院长的角色在本篇中也略有提及),一个“计划一下子把路修到这里,一下子修到那里”㉟的领袖或总设计师,“全替我们考虑好了”㊱(业已规定了总体化的、目的论的未来),并且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所有的人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㊲。但对这个可怜的叙事者来说,“我们搞不清所有的人是不是也包括我们,同时还没认识到的是哪一点,雾就起来了”㊳。我们看到的不是对于现代性的灾难的控诉,而是对于现代性远大规划的茫然和疑惑,对那种话语的所指的瓦解。
同时,徐晓鹤没有简单地注定了那个现代性规划的破产,相反,在临近结尾的倒数第二段里,我们看到了“娇婆蓝终于将我们带到那条他修成的路上”㊴。那个“沿途不断地有人跟他打招呼,娇婆蓝向他们频频点头,我们也只好跟着点头”㊵的场面也的确是领导和群众会面的典范场景。不过,对徐晓鹤来说,“无聊”成为灾难的核心部分,这种无聊正是我们在贝克特众多剧作里看到的那种荒凉的末日景象。一种对主流话语的戏仿再度出现:“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起码在天黑以前要走完它还需付出相当大的努力”㊶。但“天黑以前”的插入使话语的意蕴产生了一点滑稽的效果,我们不但不知道这条路的真正功用是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非要在“天黑以前”“走完”那条原本是现代性象征的金光大道,而不是像正统的话语规范那样沿着它走向曙光或黎明。
无论如何,对于娇婆蓝来说,“这是长期从事一项事业的结果”㊷。并且,事业的完成似乎是唯一的、绝对的目的,这个目的中内容的匮乏是决定性的:“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发生。人们把嘴巴喔成鱼的样子,赫赫地笑两声就算完事。或者干脆连鱼的样子也没有”㊸。这样,娇婆蓝的宏伟事业同人们的无聊行为就荒诞地接合在一起,成为现代性规划的一个注脚。“但是”——这个“但是”是徐晓鹤提示我们的——只有从“从很近的地方”——微观的,而不是从宏观的历史全景——我们才“看到了娇婆蓝后脑壳上的那块疤”㊹,这激发了叙事者的难以复原的记忆,有关这篇小说主要段落中宰杀大鱼的那个事件:“那是被大鱼甩开的梯子砸中的。尽管如此,我仍然充满了疑惑。事情毕竟已很久远了,甚至很可能根本就不曾发生过。记忆往往错了,往往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我的病便是从中而来”㊺。根据随后提到的疯人“院长”来看,这里所说的病指的无疑是疯病。也就是说,叙事者的确是处在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中。不过,这种非理性正是由某种貌似理性的事件引发的精神创伤所带来的,这使得遥远的真实事件变成记忆中错置的事件甚至变成幻觉,正如整篇小说的叙事风格提供给我们的那样。强烈的精神创伤,从心理分析学的角度来看,致使了完整的主体性的分裂,剥夺了对创伤起源事件的理性陈述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整篇小说闪烁不定的叙事永远无法清晰地穷尽对那个宰杀大鱼事件的陈述。
小说的主要部分所涉及的这个宰鱼事件当然更是一个足够荒唐的事件。根据娇婆蓝的指示,镇民们纷纷走进被剖开的大鱼(一条大得失真的鱼)的肚子,从中挖取可当即食用的内脏和肉,这就是整篇小说的中心情节。不过,正如我已经提到的,小说的关键在于叙事者的似是而非的叙事,使这个客观事件的荒诞性首先建立在主体的荒诞性之上。这里似乎有必要再次提及我在本文开始时的一个关键论点:徐晓鹤小说叙事的不确定性在对事件过程的描述中愈演愈烈,不断的误述,不断的游离,可以说是先锋小说中最激进的对叙事整体的解构。这种解构颠覆了传统写作中的总体性话语规范:没有不可逆转的话语,没有任何能够豁免了怀疑的陈述。比如,“一些人变化太大,致使邵大伯看起来不象邵大伯,而象娇婆蓝。很久以后才搞清楚,他果然就是娇婆蓝”㊻。而那个“朝狗脸噗地喷了一口酒”的才“是真正的邵大伯。因为眼珠子发红。不过后来发现娇婆蓝的眼珠子更红,那我就不管了”㊼。似乎每一个后继的陈述单元都可能是对既有陈述的偏离或背离,这使叙事的稳定性降低到最低点。类似的然而更不负责任的叙事出现在“我”和双木林的一次幽会中:
我知道我不会错,但我还是错了。她一笑,石片从肩胛上掉下来。原来是一块螃蟹壳。那就怪不得了。我问她认不认得院长。她说当然。是哪个院长。我也搞不清是哪个院长。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问起好几年以后我才认识的院长。所以疑心一切只是一场梦。双木林不认为是梦。因为不可能很多人都做同一个梦。虽然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㊽
如果说这样的不断游离已经使人极度难堪,在经过了很长一段关于“我”和双木林的描述之后的该章结尾就更加令人眩晕:
我看看双木林,她却并不是双木林。她是胖姑。“早就是这样了”,她说。㊾
正是这样的叙事模式,而并非单单是所叙事的事件本身,应当看做是整篇小说的核心。这种梦境般的场景是叙事迷宫的起点,而不是终结。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穿越这样的迷宫才能领略到令人眩晕的事件,而不可能在迷宫之外谈论事件的眩晕性。这是徐晓鹤小说中最不妥协的话语政治,不但是对总体化的政治话语模式的消解,也是对总体化的主体话语的自我消解,因为徐晓鹤所面对的已不再是一个易于匡正的对象,而是必须永远探究的自身的绝境。当然,这种自身的绝境是同外在事件对主体的打击交织在一起的,不然小说中就不会一再提及疯病的发生同宰鱼事件的关系,不但叙事者“的病便是从中而来”,而且,另外的人物也在相同情形下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
大鱼动了一下,悠悠吐出一口气。
“还没死!它还没死!”
艾宝一怔,手舞足蹈地跑开。言午许和古月胡从鱼腹里伸出脑袋来看了看,抹一把脸上的血,旋又缩进去翻搅。艾宝从那时起变得神经错乱了。一听到风吹草动就手舞足蹈。㊿
的确,没有什么比我们对血腥历史的参与更具有精神上的毁灭性了,但也正因为我们自身的参与,历史就不仅仅是悲剧,而成为荒诞剧,它意味着历史所规定的主体话语同历史事件永远无法吻合,或者说,真实的历史将我们置于话语的尴尬之中。这种尴尬性一直是徐晓鹤小说的精髓所在,在《水灵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宰鱼事件的壮观场景和事件的血腥效果及人们的卑琐意向之间的内在冲突。在某些情形下,徐晓鹤甚至将那种无聊和恶浊误置于诗意的场景中,显示出叙事主体在一种无法理喻的境遇中的表达的错乱:
共田八和言午许共同挽着一大挂肠子从鱼肚子里爬了出来。……他还没恢复到非跟我们讲话的地步就捧着它们一径走到娇婆蓝即将修成的路上。我想只要没人劝他他一定会这样走下去,于是并不去劝他。他却停下回过头,朝言午许脸色血红地看看。言午许也脸色血红。两个人捧着同一挂肠子,相对无言。(51)
显然,“相对无言”的抒情或诗意的内涵被转换成对空虚无聊的暗示,一种面对意义匮乏而产生的失语状态。对于他自己的参与宰鱼事件的开始,叙事者是这样描述的:“贵爹要我到鱼肚子里做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他给了我一把刀,我猜出是娇婆蓝指使他要我这样干的”(52)。同样,像“开拓性的工作”这样的词语所暗含的话语性在事件本身的血污和荒谬的衬托下反而标志着总体化历史的无效。
相对于《疯子和他们的院长》中的可笑的精神“东征”,《水灵的日子》里的宰鱼事件以及那些大嚼鱼肉的场面降至一个更为低俗的行为系统中,这似乎也是文革时代转换为后文革时代的一个恰当注脚。在这个“开拓性的工作”中,“我”在大鱼的肚子里遭到了墨鱼的缠绕,这样的缠绕却又误述在一种主流的集体性话语中:
黑暗中它软塌塌的触须搭在我的肩膀上,好像我就是它的亲密战友。我从血浆里抽出自己的手,拂开触须,假装是挪动一个位置。战友毫不介意,软塌塌地挽住我,要与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53)
然而,这就是“我身上那些被墨鱼的吸盘灼伤然后又生过蛆的地方,如今已经都平复了”(54)的来源。直到最后,叙事者“误入了大鱼的肠道……只听得一声臭烘烘的巨响,我被它的肛门忿然排泄出来”(55),对一场貌似伟大的事业的叙事结束于一个极为污秽的场景,一个既可怜又可笑的窘境之中。徐晓鹤在整篇小说中就是把这种对秽物学(scat o l o g y)的癖好同末世学(esc h at o l o g y)的倾向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作品的基本面貌。这种秽物学在整个叙事中把事业抽象的美学降至细节的污浊中,而这种末世学则展示出生命的耗尽和无聊。这两点使我们再次想到贝克特的《终局》,那些从垃圾箱里发出的无意义的对话标志了欧洲二次大战后的存在绝境。
同贝克特一样,徐晓鹤的小说绝不是虚无主义的对存在的弃绝。相反,正是一种自我审判的叙事揭示出对历史中存在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甚至不是能够确知的,或者说,它的强度是它无法被理性把握的原因。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主体被推向了一个荒诞的境遇,一个被剥夺了自足性的境遇:“要是再清晰一些,或许我会看到事情的真相。一切的回忆都不会有错。要不就都是错了”(56)。这种自我怀疑,这种叙事的自嘲,似乎成为面对绝境的唯一出路。但是“清晰”的“真相”在不断地受到质疑、扭曲,这正是一次没有终结的否定性探索,是自我意识的痛苦而荒谬的挣扎。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⑫徐晓鹤:《院长和他的疯子们》,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版,第147、153、153、155、155、116、117、117、118页。
⑩“才有……今天”这个短语也被广泛用来感谢中华民族的解放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小说里想象中的救星居然是一个红毛野人。
⑪De M an,Paul.Blindness and Insight.M 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 innesota Press,1983.
⑬此处文字据《收获》最初发表的版本修改(《收获》1986年第6期)。
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戏仿在这里指对话语的微妙而又决定性的歪曲,我们可以从《海港》中看到十分类似的场面,但是表演者不是疯子,而是那些所谓的正面英雄人物:“三工人上,腾空越过缆绳,作拉缆舞:翻身,前弓后箭,探海,跨腿,转身,骗腿,亮相;转身挂缆绳于缆桩上。”(上海京剧团海港剧组:《海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
⑮⑯⑰⑱⑲㉒㉕㉖㉘徐晓鹤:《院长和他的疯子们》,台北远景出版社1989年版,第128、106、131、93、112、97、107、107、108页。
⑳诸如此类的语句在主流文艺中比比皆是。例如,“昂起不屈的头颅”就是《海港》中“昂首阔步”的翻版。
㉑Foucault,M ichel.M adness and Civilization: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Trans.Richard How ard.New York:Pantheon Books,1965.
㉓㉔Felm an,Shoshana.W riting and M adness.Trans.M artha Noel Evans and Shoshana Felm an.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㉗徐晓鹤:《院长和他的疯子们》,台北远景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107、108页。
㉙㉚沈从文:《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卷第151页。
㉛W ang,David Der-w ai.Fictional Realism in the Tw entieth-Century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
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51)(52)(53)(54)(55)(56),徐晓鹤:《水灵的日子》,《湖南文学》,1988年第12期。
※耶鲁大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