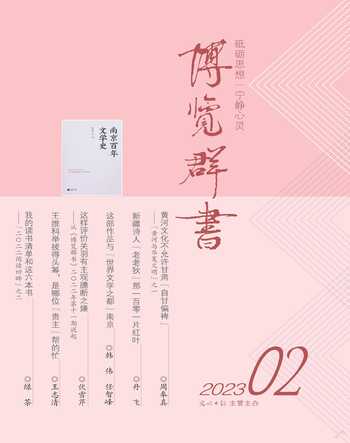东亚释奠走笔
刘慧琳
释奠是儒家最具有代表性的祭祀仪式。《礼记·文王世子》载:“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释奠”是先秦时就有的古礼,其后逐渐演变为专门在学校设酒食以奠祭先圣先师的一种典礼。汉儒郑玄等认为“先圣”与“先师”分别指周公与孔子,因此汉魏以来盛行周孔合祭。这一时段在主祭、每年祭祀频率问题上莫衷一是,至唐太宗以孔子为先圣,定释奠时间于仲春仲秋。由此,“释奠”成为“祭孔”礼之代称。
孔子身为文明的先驱,教化万民,带给人类无限福祉。祭孔的释奠之礼,维系的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稳定的秩序,是我们漫长历史过程中民族精神流动的血液,也对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力。重儒重礼,最终成为了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底色。
壹
《古事记》有这样一则记载:公元三世纪的应神天皇时期,一位名叫王仁的五经博士由百济到达日本,献《论语》与《千字文》,后又成为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这段记载虽多遭史学界诟病——如《千字文》的成书时间与应神天皇在位时间都与史实有所出入,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来自中国的儒学很早就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更在几个世纪后的大化改新中为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提供了政治理念与管理模式上的启发。
从现有文献来看,日本至少自大宝元年(701)起就在官吏培养教育机构“大学寮”中,于每年农历二月、八月的上丁日定期举行释奠。15世纪70年代,应仁之乱的大火把大半个京都化为焦土,京都朝廷的释奠亦被迫中止。17世纪江户幕府成立后,武士阶层开始尊崇儒学,尤其是世代担任幕府儒官的林家学派,一力促成了释奠的复兴。江户幕府第一代大学头,幕府官学的开创者林罗山曾发出“时盥漱 ,登圣堂肃拜周旋,远忆太学寮事载《延喜式》而不在于今也。告朔礼废,羊亦亡矣,可以长吁”的感叹,体现其了对中华文化及古代日本宫廷文化的尊崇及战乱后礼崩乐坏的惋惜。罗山第四子读耕斋亦在《释菜说》中称:
余尝见《延喜式》,每岁春秋,修释奠于大学寮,致祭于先圣夫子,以先师颜子及九哲配焉。祭器完备,祭用丰足,有司不乏,祭仪可观。加之诸国各有释菜,呜呼盛哉。儒风之浩然,文物之勃起,可谓能继中朝之美矣。
江户初期的儒者眼见周边国家祭孔之古礼犹存,儒风浩然,而日本的祭孔则只能回首年代久远的《延喜式》等歷史文献,因而强烈呼唤恢复祭孔礼制。罗山第三子鹅峰曾赋予孔子以家业守护神的形象,称“镇座安稳以长以久,而家运亦受保佑之护也”(林鹅峰《圣殿复座告文》)。如果说鹅峰对孔子神化的作用尚且集中于“家”这一单位,那么幕府第三代大学头,鹅峰之子凤冈则更进一步,赋予孔子国业守护的神格,是为“仰冀圣神,来格于兹,镇护国家,补助救治,百禄多益,万寿无疆,长固太平之基,久行二仲之奠”(林凤冈《释菜告文贞享四年丁卯二月》)。
随着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释奠礼结合日本本土特色,被儒者赋予独特内涵。日本释奠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其祭品中对血牲的避讳。自汉高祖刘邦以太牢 (牛、羊、豕)亲祭孔子后,太牢就成为文庙最重要的祭品,中国、朝鲜、越南、琉球均用太牢,唯不见于日本江户。近世日本释奠时多用鱼,虽也有使用鸡、鸭、雁、兔的情况,但无“毛血豆”的使用。这一现象可追溯至《延喜式》中“避讳三牲,代之以鱼”的记载,究其原因,其一便是日本民族触秽观念的影响。秽即不洁,顾名思义,“触秽”便是沾染不洁。学者山本幸夫氏研究认为,在古代日本人的观念中秽即为秩序的对立面,社会成员对其持有强烈的不安和恐惧,并竭力试图规避。《延喜式》中规定的秽恶事多与死亡、血污相关,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释奠所用牺牲避讳兽类,尤其是带毛血的动物。除触秽观念外,另一影响因素或与佛教倡导不杀生密切相关,如《百炼抄》记载了一则大治二年(1127)八月的释奠,称“八月十日,释奠依杀生禁断,不供荤腥之类”。
在多种文化合力下,释奠在日本逐渐发展出不同于东亚其他国家的特色。当代日本民间的“孔子祭”,便是在删减古礼的基础上,结合神道元素,增添了不少和风礼节。日本释奠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彰显东亚文明包容性与开放性的交流史。
贰
1976年在久米村建成的至圣庙,被视为“日本最南端的孔庙”,就其历史脉络而言,探究其崇儒祭孔、重视中国文化的底色还要追溯至琉球王国时期儒学的传入。
察琉球王国时期重要岁时记录《年中仪令》,便会发现其二月、八月篇均有“上丁日祭孔子庙”的记载,这与明清以来崇儒重道风气的传入密切相关。琉球国自明洪武年间与中国建立藩属关系以来,积极学习中国文化,并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排遣官生入国子监学习。儒家思想文化传入琉球后,其对孔子与祭孔的重视程度亦与日俱增。据史料记载,第一座进入琉球的孔子圣像是明万历年间由紫金大夫蔡坚从山东曲阜请来,祀于家中。孔子像被请入后,琉球人视若珍宝,纷纷请求请入家中祭拜。清康熙年间准予立庙后,加之当时的统治者尚贞王好学重礼,琉球遂掀起了一股尊孔重礼的风潮。在此背景下,圣庙于久米村建成,并在当年即举办了释奠礼。
《中山传信录》载:
圣庙,在久米村泉崎桥北门,南向。进大门,庭方广十余亩。上设拜台。正堂三间,夫子像前又设木生,四配各手一经,正中梁上,亦摹御书“万世师表”四大字榜首;前使汪、林各有记书木牌上,立左右。
汪、林二人指入琉册封使汪楫与林麟焻,康熙二十一年(1682)册封琉球国王,翰林检讨汪楫为正使,麟焻为副使,二人对琉球礼制完备、庙学系统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汪楫曾指出至圣庙规制的问题所在:“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座左右,颜曾思孟为配享,未有设十哲诸贤之主,且其学校之制又未备也。”按汪楫所言,至圣庙配祀人物除主像孔子外,仅设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配,未设其余孔门十哲陪祀,认为不够完善。
琉球国至圣庙虽在规制上并不十分完备,但在祭品方面基本与中国完全相同,除严格遵循太牢祭孔外,其他祭品,如稻、粱、黍、稷、枣、栗、榛、菱、鹿脯、饼、韭菹、芹菹、笋菹、兔醢、鹿醢等,分盛于簠、簋、笾、豆之内;此外,神位前还需供奉帛、羹、香烛等物品。
论及琉球的释奠,就不得不提及被尊为“琉球圣人”的程顺则。他是尚氏王朝时期著名的儒学者,先后四次赴闽学习。主持释奠时,程顺则严格遵循中国礼制,以诚敬之心祭祀圣人。他曾有言:
夫以圣人而君天下,不如以圣人而师天下也。君天下者,泽及于一时,师天下者,凡古今来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舟车所至,日月所照之处,靡不被教化焉。
在程顺则心中,教化万民之师才是民心之所向,大道之所指,这种影响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甚至在人君之上。或许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何直至今天至圣庙的释奠仪式仍在继续,隶属于久米崇圣会的民众们依然愿意在孔子及四配神位前行繁复的跪拜礼,以此表达这份尊师重道之情了。
叁
20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学界对位于越南河内的一处名为东山村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发掘,发现了著名的东山遗址(公元前3—1世纪)。根据考古报告,在东山遗址的上层曾发现少量明显属于中国的器物,其中包括中国形制的钟、磬等礼乐器,与《越史略》中士燮“出入鸣钟磬,备威仪”的记载相吻合。士氏家族曾是汉末三国实力雄厚的地方势力,士燮威望极高,甚至不在南越王赵佗之下。此二重证据的作用下,以瑞典考古学家高本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提出越南东山文化源于中国或深受中国影响说。诚然,这一假说是否成立尚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自汉文化传入交趾以来,来自中国的礼乐文化就一直影响着越南。打开越南典籍《历朝宪章志》,《礼仪志》开篇即言“国之道,莫大于礼者”。
越南的第一座文庙建于后李朝圣宗时期,李公蕴自幼饱读诗书,尊崇孔孟之道。公元1070年河内文庙建成以祀孔子、教化臣民。《大越史记全书》載:
庚戌年,李朝圣宗皇帝神武二年八月秋建文庙,立孔子、周公及四配塑像,画七十二贤肖像,四季供祭。
从史实角度而言,有学者认为该记述明显为误载。如前文所述,四配增订时间为南宋咸淳三年,即1267年,因而《大越史记全书》里四配的记载或为后世史家追记。以上配祀人物均为来自中国的大儒,不过与中国稍有不同的点在于河内文庙还会供奉本国著名儒者、思想家,例如朱文安、张汉超等人。
《清朝文献通考·安南》载“交州有国学、文庙,各郡县皆建学,祭祀、配享俱如中国。”众多的历史文献告诉我们,越南释奠礼与中国具有极高的相同度。以后黎朝为例,黎太祖时已有“祀孔子以太牢”的记录。黎圣宗在位期间,曾对释奠礼做出规定,是为“每年各府春秋二仲,上丁行礼”。18世纪以后,统治者对“礼器”愈发重视,黎裕宗曾于1732年“谒国子监,拜谒先圣,以新制礼器为之”,且这类新礼器“皆用金锡雕绘”,规模不凡。此观念在其后的阮朝亦得到传承,阮明命帝曾于1822年春祭亲自行礼,并交代礼部“凡祭品祭器并要精洁,分献陪祀百官各敬谨其事,永承朕尊师重道之意。”明朝是古代中越关系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阶段,明太祖朱元璋试图恢复中国传统的邦交理念,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主导,有等级秩序的、和谐的理想世界秩序,即以传统儒家观念“礼”为基础的理想化的天下秩序。随着历史的演变,释奠文化融入当地成为其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几年前越南《青年报》曾报道过一篇社会新闻关于永富省投资2710亿越南盾兴建供奉孔子的大型文庙。该项目的历史顾问解释称,正如河内文庙奉祀人物中就有本国儒者,文庙除供奉孔子外还会供奉其他本国名人,而在越南民众心目中,河内文庙代表的绝非狭义的中国文化,而早已成为其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强烈自觉,作为“外来者”的孔子在祭典中的权重虽有所下降,但释奠这一“礼”之精神并未消退,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存在于当代越南社会。
肆
《周礼》有言:“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朝鲜太祖七年(1398)设立的成均馆得名于此。成均馆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大成殿内供奉孔子及其弟子15位先贤位牌和以朱子为首的6位性理学大家先贤的位牌,另外还供奉18位韩国性理学先贤,总共为39位。这里是现存各国孔庙中唯一完整地保存祭孔典礼原貌的文庙,每年举行春秋两季大型释奠祭祀活动,在韩国被称为“释奠祭”。
释奠自中国宋代传入,曾因政治、战乱等原因中断,后在朝鲜世宗大王时得以复原后,一直延续至今。《韩国增补文献备考·学校考·文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东国自丽初立庙于国子监,三国史虽不言立庙,而新罗圣德王时,奉安孔子像于大学,则亦必有享礼矣。唐开元二十七年尊为王,谥文宣,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谥玄圣,五年以“玄”字犯讳,改称至圣,元武宗加谥大成,我国亦遵用焉。
如文字所述,朝鲜历朝不断沿用中国赋予孔子的谥号,在祭礼方面亦几乎完全遵从中国。据国内学者考证,成均馆文庙也是中祀的规格,与《儒教大事典》“释奠陈设图”笾豆数目相同,此完全按照中国释奠规格。
古代成均馆释奠一般由国王遣官以王的名义举行,举行时间按每年春秋二仲月的上丁日。据《朝鲜志》记载,李朝时期国王释奠极为重视,“时时亲行释奠,或不时幸学,与师儒讲论,或横经问难,或行大射礼,或亲策儒生”。谚文的创造者,被誉为“海东尧舜”的世宗曾于1429 年秋“率王世子幸学谒圣,世子行亚献礼”,第九代君主成宗亦多次“幸成均馆,释奠于文宣王”。《成宗实录》记载了成宗二十三年(1491年)成均馆释奠的盛况:
八月己巳,上幸成均馆,亲享文宣王,御下辇台,大飨百官,儒生皆插赐花,互歌新乐章以侑之,命都承旨郑敬祖语儒生曰:今日之事,非为宴乐也,乃所以崇儒重道也,其各醉饮。与宴儒生总三千余人,观听之人填溢桥门。
朝鲜成均馆释奠礼就其完整性、连续性而言,是东亚诸国中最接近古礼原貌的。朝鲜半岛地理位置紧邻中国,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存在慕华思想。在朝鲜王朝,慕华思想尤其得以发扬光大。李成桂立国之初便请求朱元璋赐国号“朝鲜”,制度、文化上均向明朝学习,双边关系发展成为典型的朝贡关系。明亡后更以“小中华”自任,不认同清朝为中华正统,认为自己是中华世界唯一的中华余脉,乃至儒学大家崔益铉公然宣称“至于本朝则得复小中华,而崇祯以后则天下欲寻中国文物者,舍吾东无可往”(崔益铉《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这种文化力量转化到成均馆释奠礼之上,就成为了朝鲜释奠长期认真维护程序和细节完整性的巨大动力。
释奠作为仪式政治的重要手段,在王朝时代结束之后丧失了其原有的政治与社会功能,随之演变为一种文化遗产。当代韩国依然极力践行宫廷雅乐、推广古典释奠礼仪,努力追求着传承的连续性。朝鲜成均馆释奠礼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纵观释奠礼的传播过程,其由中国传至朝鲜半岛,又在当代由韩国“回流”,这一耐人寻味的循环充分显示出东亚文化交流内部蕴藏的巨大潜力。立足于当代,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释奠礼结合当地文化融入日本、越南民俗,虽存在较大程度的改动,仍不失为一种文化传播、交流的典范。相较之下,韩国“释奠祭”可谓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古文化的承续性。其在国家的直接支持下,由原为国子监的成均馆大学和聚集在这里的一批对于古典儒学、雅乐和佾舞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负责传承祀典礼仪,树立了释奠礼保存的优秀典范。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东亚诸国尽管由于地理、历史和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也各具特色,但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受到中国儒家礼乐文化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合作的不断加强,人们逐渐重视历史文化留下的宝贵积淀。作为一个传承千年的祭祀仪式,释奠在东亚持久的存在和影响,反映了东亚民众对礼乐之道的价值认同,这种广泛的文化认同绝不局限于近代民族国家界限而及于更深广的范围。行文于此,不禁感叹曾经春秋时代奔波于中原大地,执着地想要传播自己思想的孔子,如果知道自己的主张可穿越山海,为整个东亚整体奠定了一个“礼”的世界,该何等笑慰于心。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巍山文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