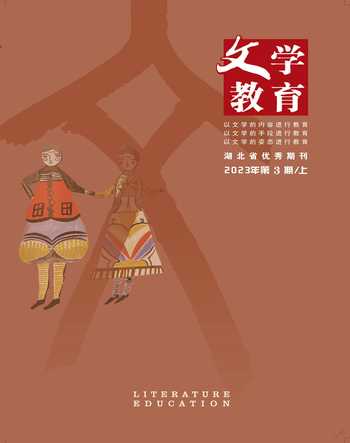于纷扰中寻求生命的暖色
内容摘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与山海经》创作的时间、创作主题、创作风格颇为相似,由于这种内容上的互文性,在教学时,亦可以着眼于其一致性和连贯性。鲁迅在这两篇散文中采用了儿童与成人的双重叙事视角,将童年的花蕾与中年的藤蔓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明暗交织的生命体验图。在讲授这两篇课文时,教师应该注重将文本解读与学生的生命体验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感悟人生况味,从而学会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懂得珍惜成长所必经的每个人生阶段。
关键词:统编教材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阿长与山海经》 生命体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与<山海经>》都创作于1926年,是鲁迅回忆童年生活的怀旧之作,收录到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由于《朝花夕拾》是鲁迅笔下最为温暖的一抹亮色,因此被认为适合低年级的中学生阅读。在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安排在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单元目标”指出“了解多姿多彩的学习生活,感受他人的学习智慧,获得人生启示”。《阿长与山海经》安排在七年级下册,单元目标指出“结合文体特点和作者的叙事风格,展开多种形式的诵读,加深对作者情感态度的理解和对文本意蕴的体悟。”由此可见,两篇课文的教学重点都是通过文本阅读和分析,进入对作者思想情感的体悟,获得一定的人生启发。两篇文章创作的时间、创作主题、创作风格颇为相似,由于这种内容上的互文性,在教学时,亦可以着眼于其一致性和连贯性,挖掘鲁迅的生命体验。两篇文章中“我”的年纪与初中生相仿,因此在讲授这两篇课文时,尤其应该注重将文本解读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感悟人生况味。
一.一颗童心最珍贵
打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个色彩鲜明、充满生命力的“乐园”便呈现在我们面前。“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1]这时,人届中年的鲁迅拨开岁月的尘雾,把自己完全沉浸在孩童的世界中,沿着儿童的眼光兴致勃勃地介绍着百草园。只有在孩子的眼中,石井栏才是“光滑”的,因为孩子会动手去摸,皂荚树是“高大”的,因为“我”是矮小的。只有孩子才会注意到草里鸣叫的蝉,菜花上伏着的黄蜂,从草里窜上天的云雀。也只有孩子,会翻开砖石探究底下会有什么稀奇的东西,会用手指去按斑蝥的脊梁,看它的后窍喷出的烟雾,如此反复,不亦乐乎。孩子会听到传说后心心念念,执着地寻找人形的何首乌,不惜弄坏泥墙。孩子会不怕刺,摘小球状的覆盆子,品尝它酸酸甜甜的味道。正因为鲁迅以孩童的感受力和想象力看世界,百草园之“乐”才得以灵动得再现。
当然,百草园作为“我”童年的乐园,不仅仅有趣味十足的自然事物,还有温暖的人情味。长妈妈给“我”讲了园子中赤练蛇的传说,作为孩子的“我”对世界的认识是浅显的,对这个传说深信不疑,这成了“我”童年的一大心事,以至于夜晚不敢去看那墙。中国的长辈为了管教孩子,阻止儿童去危险僻远之地,就会编出一些故事来起威慑作用。长大后的鲁迅明白这不过是长妈妈杜撰的,但丝毫不怪罪她,反而感到这样的故事为童年增加了趣味,增加了对神秘世界的神往,过后回想,也觉得饶有兴味。除了长辈的厚爱,百草园里还有同龄伙伴的友情。文中提到“我”与闰土冬天捕鸟的趣事,后来这一情节也出现在《故乡》里,可见鲁迅对此印象之深。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提到的长妈妈便是《阿长与山海经》中的主角。此文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前半部分写“我”对阿长的“憎恶”。这部分的语言幽默俏皮,谐趣十足,因此即使鲁迅特意强调“抑”,但我们读到的却并非“憎恶”,虽有微讽,但不冷峻,可谓“抑中有扬”。比如鲁迅描绘了阿长“切切察察”的神态,但她切切察察的后果却有点“可笑”,那就是“我”若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被她说成过于顽皮,向“我”的母亲告状。鲁迅又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阿长举止粗俗,睡姿很不讲究,而“受害者”又是“我”——推不动,叫不闻,还要承受她一条臂膊压在颈子上。阿长还教“我”许多规矩,这也令“我”颇感不耐烦,但又没有反抗之力。不过阿长终于在讲“长毛”的时候收获了“我”的敬意。起初这个故事并没有骇住“我”,阿长见状更加“添油加醋”地渲染长毛如何凶残,直到她讲了自己會被掳去脱下裤子做人肉城墙,这才令“我”刮目相看。鲁迅用了“伟大的神力”,“特别的敬意”这样崇高的词汇来形容“我”对阿长的敬意,“大词小用”的手法含有夸张和调侃的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妙趣,既传神地绘出了阿长的神采飞扬,也将“我”的童真稚气展现得活灵活现。不过在“我”知道阿长谋害了隐鼠后,这种敬意完全消息,“我”“极严重地诘问”,“当面叫她阿长”,这种“郑重其事”的画面也令人忍俊不禁。
“隐鼠事件”之后,文本进入了“扬”的部分。“我”对《山海经》十分渴望,或许因为《山海经》并非正统科举书籍,大人们都不肯真实地回答“我”怎样得到它。只有阿长这个不识字的、“我”最不寄希望的人,将一个孩子的心愿放在心上,竟然买到了带图画的《山海经》。尽管长大后“我”发现这是部刻印、纸张都十分粗糙的本子,但在当时,那是“我”最初得到的,最为心爱的宝书,此后回想起来依然满怀感动。除了阿长,远方叔祖周玉田也给鲁迅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是一位胖胖的,和蔼的老人,喜欢种花木,也许是为了打发时光,也许他本身喜欢孩子,他乐于与孩子们来往,称“我”为“小友”。“我”有机会接触他的藏书,正是通过他知道了神秘的《山海经》,打开了读书的天地,孩子的想象力得到发展。有了这些长辈的关爱,鲁迅度过了既拘束又不无美好的少儿时光。
通常在解读《阿长与<山海经>》时,教师都将重心放在阿长身上,剖析这一人物形象的特质:她作为一个典型的底层农村妇女,具有搬口弄舌、行为粗俗、迷信无知的弱点,也有淳朴、真诚、善良的优点。事实上,“我”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人物。童年的鲁迅时常对阿长有抵触情绪,是因为阿长总是管束他,而从成年人的角度来看,长辈管束孩子是很自然的道理,并非什么“深仇大恨”。这时的鲁迅再回忆阿长,目的并非批判阿长,而是带着更复杂的情绪,回味自己童年时的精神心理。鲁迅从“我”的视角写阿长,对阿长的态度上附着了浓厚的主观色彩,在描写阿长的同时,也在描写着“我”,一个童年的小鲁迅的形象便活脱脱地勾勒出来。这个“我”活泼好动,向往自由,心地单纯,爱护动物,喜欢绘画,富有想象,爱与憎的情感简单、分明。“我”过着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当然生活中也有烦恼,这烦恼无非是长辈禁止自己淘气或不小心踩死了“我”的宠物,但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打击。“我”的快乐也很简单,一本渴慕许久的画书便足以让“我”忘记曾经的不愉快,感受到天大的惊喜,萌生强烈的感恩之心。成年以后的鲁迅回眸童年的自己,既羞愧于当初的幼稚,也欣赏那份珍贵的纯真,揶揄中难掩洋洋自得之意,故而采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实则将对童年生活的深挚怀恋渗透在字里行间。
两篇文章都以童趣见长,字里行间渗透着鲁迅对童年的眷眷深情。在成年人眼中,百草园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菜园,比如周作人晚年时回忆道:“百草园的名称虽雅,实在只是一个普通的菜园”[2]。阿长与童年鲁迅之间的故事,也不过是极为普遍的长辈与孩子的日常。但是鲁迅尊重和珍惜孩子活泼好奇的天性,懂得孩子眼中的世界和大人看到的不同,将视若平常的童年生活还原出活色生香的本色。世界著名童话《小王子》的作者埃克苏佩里说过:“每个大人都曾是小孩,只是只有少数人记得。”鲁迅自己也说过:“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3]鲁迅就是少数记得自己曾是孩子的成年人。他借助笔端与另一个自己相遇,小心翼翼地捧起那颗潜藏许久的童心,痛痛快快地又做了一回天真烂漫的孩子。
二.挥别童年,接受成长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前半部分写了“百草园”,后半部分写了“三味书屋”。两部分之间有个过渡段。“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4]可见,鲁迅在回顾自己的成长轨迹时,将入三味书屋划作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入私塾意味着他从童年自由自在的形态,进入了正规的受教育阶段,开启了被社会化、被规训的人生历程。纵然,鲁迅与自己的“乐园”告别时透露出淡淡的惆怅,但“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之间并非简单的褒贬关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配合对我国应试教育的反思,学界将“百草园”与“三味书屋”的关系解读为对比或衬托关系,认为鲁迅通过前后自由快乐生活和枯燥迂腐生活的比照,表现前者适合儿童的天性,后者阻碍儿童的身心发展,以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对儿童的束缚和损害。近年来,研究者摒弃了先行的理念,综合文本分析和鲁迅的生平经历,提出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首先,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于寿镜吾先生的描写是正向的,笔触间不乏宽容和温情。鲁迅称先生“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给予先生很高的评价。他主持的三味书屋传说是全城最严厉的一家,虽然有着传统私塾惯有的戒尺和罚跪的规则,但都不常用,最多是瞪几眼令大家读书,可以想见此“严厉”不是来自严苛,而来自先生的敬业和躬身示范。当然,鲁迅也描绘了他身上迂腐的儒生气:一是庄重严肃地引大家拜孔子、拜先生,二是在“我”询问“怪哉”这虫时,面有怒色地说“不知道”。这表明他受时代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封建私塾先生的传统性。但鲁迅并不是进行辛辣的嘲讽,而是以诙谐的方式,进行善意、点到为止的展现,所以先生给人的感受整体上依然是亲切的,这种亲切之感也是当时作为孩子的“我”切切实实的感受。
其次,“我”在三味书屋也很快找到了乐趣。三味书屋也有一个小小的园子,可谓“百草园”的延续,孩子们可以在学习之余去折腊梅,寻蝉壳,最有兴趣的是捉了苍蝇喂蚂蚁。先生并不禁止孩子入园玩耍,只要适可而止便可,但若逗留太久也不责罚,只一句“人都到那里去了”将学生们唤回来。可见,先生给孩子们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未泯的童心得到了一定的绽放。更重要的是,在先生的严格要求和以身作则之下,三味书屋培养了“我”对知识的兴趣,养成了勤奋务实的治学态度,为将来从事文化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寿镜吾先生最初对“我”很严厉,后来便好了,因为小鲁迅聪明过人、品格高尚,先生对他格外器重,给他读的书比其他同学多,这也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先生读书时全身心地投入,这让“我”疑心这是极好的文章,潜移默化中也启发了“我”对读书的兴趣。在读书的间隙,“我”迷上了画画,书读得越多,绘画成绩也越来越好。考察鲁迅传记可以知道,在“三味書屋”接受的启蒙教育是鲁迅一生的宝贵财富,他离开三味书屋去南京、日本求学后,每次回绍兴都要去拜访寿镜吾,师生之间形成了深厚的情感。
总之,进入三味书屋后,“我”并没有产生抵触心理,而是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渐渐长大,进入了更加成熟的人生阶段。这也是题目的意味所在,题目采用“从……到”,而不是“百草园与三味书屋”,就是为了强调“百草园”与“三味书屋”之间的承续关系,寓意着人生成长的动态过程。鲁迅入三味书屋时是12岁,这篇课文安排在七年级,学生们正好也在12岁左右。七年级是学生学习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告别了小学时代,进入了课程门类增多、学科内容趋向抽象化的中学阶段,学习的强度和难度都有所增加。这就需要学生形成新的素质,无论心态、学习态度、学习能力都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学习生活。这篇课文选在此时可谓恰合时宜。教师可以结合鲁迅的成长过程,引导学生接受成长,在目前的学校生活中找到乐趣,让学生认识到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自有其美好,中学阶段虽然告别了无拘无束的童年,但也可以体会知识的美好,感受友谊的快乐。为了让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入,可以让他们动手写写自己进入中学生活后的所见、所思、所想,与鲁迅的写作进行对比,从而反思当代中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学习智慧。
三.“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
两篇文章在轻松、温暖的基调之外,也时时流露出一丝沉重,这使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儿童文学,而具有更丰富、更多层次的意蕴。这是因为鲁迅在儿童视角之外,还采用了成人视角,他将童年的花蕾与中年的藤蔓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明暗交织的生命体验图。谈及《朝花夕拾》的创作因由,鲁迅说道“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5]鲁迅于1926年3月10日创作了《阿长与<山海经>》,此时的他刚刚经历了“女师大风潮”,又逢政治环境恶劣,心境并不明朗。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不久,北京的政治环境进一步恶化,鲁迅离开生活了十年的北京南下厦门,但在厦门遭遇了与北京同样污浊的政治空气、人际关系危机等等,在这样的状态下写就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朝花夕拾》是鲁迅在纷扰和孤独中的心灵之作,温暖的回忆纵使暂时抚平了心灵的焦虑,但当下巨大而广漠的悲哀又怎能不时时涌出。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在回忆过去的时候,现在的他也会时时站出来发出议论和抒情,为文章蒙上一层忧郁深沉的色彩。他提到百草园早已连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时,言语间充满了惋惜与留恋;他回忆起自己画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的一大本绣像,后来为了要钱用卖给了一个同窗,淡然的语气中满是落寞和惆怅。文章就以“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收尾,看似平淡实则一语双关、余味深远,既陈述了文化物品更新换代的事实,更是感叹一去不返的还有自己的少年时光。当鲁迅沉浸在过去的甜蜜回忆时,也会流露出现在时的焦虑感。比如,提到美女蛇的故事时,鲁迅插入议论,“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6],显然这是有了丰富的战斗经历、背腹受敌后,鲁迅对人事艰险的体验。鲁迅通过儿童视角尽显自然之美、童年之乐,又以成人的全知视角道出了百草园后来的归属,客观上抒发了成人怀念童年和故土的感怀,快乐中包含着惆怅。两种视角之间没有断裂感,而是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升华了作品的精神高度,增加了作品的情感浓度。
《阿长与<山海经>》于轻松中也附着着沉重。比如鲁迅一直在强调阿长“无名”。文章一开头,鲁迅就先讲明阿长不姓长,“长”也不是形容词,只因前一任女工名叫阿长,鲁家的长辈们叫惯了口,于是她就默默地继承了这个名字。在文章的结尾,成年后的鲁迅怀念起长妈妈,深愧于始终不知道她真正的名字、经历,仅知道她过继过一个儿子,猜想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阿长就这样籍籍无名地在雇主家劳动了十多年,她自己的姓名如同本人的命运一样,沦为一片不被关注的黑暗的土地。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彰显着身份建构和身份认同。封建社会的妇女都处于“无名”的处境,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独立的身份和主体,在权力秩序中居于客体地位。“阿长”被命名,意味着她的存在价值首先在于作为劳动力的价值,而她自己的主体世界则无人问津。当然,这其中的沉重是儿时的鲁迅无法意识到的,所以他会稚气地在“憎恶”她时直接唤“阿长”。成年后的鲁迅成为一名人道主义者,经历家庭变故、生计艰辛等一系列曲折后,对劳动人民的生存处境产生深刻的认识,理解和亲近底层劳动人民。文章全篇都未直接展现阿长的人生挣扎,但不动声色地展示了这位底层妇女寥落的一生,倾注着鲁迅深挚的同情和悲悯。
鲁迅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无限感怀,将深沉的情感都寄托到了文章的最后一句:“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吧。我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7]鲁迅在这里采用了为数不多的直抒胸臆式表达,虽保持着一贯的节制风格,但字字句句都凝结着无限深情。鲁迅是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战士,肩负着破除蒙昧、开启民智的使命,他对魂灵的有无一直持怀疑态度。不过鲁迅愿意为了所爱之人“说假话”,他在杂文《我要骗人》中说过:“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8]鲁迅虽不信鬼神,但他领悟了长妈妈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他愿意俯就她的思维,祝愿她的魂灵安息,或许这是唯一能做的对她的补偿和报答。总之,鲁迅以儿时的心态回忆阿长,同时以成人的眼光去反观阿长的命运,但是第二层的意味含蓄而隐忍,渗透在文本的深处。通过儿童和成人的两种视角,“我”与阿长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阿长伟大的母性为“我”的成长保驾护航,既带来成长的“烦恼”,更带来热爱生活的温情。与阿长相处的经历构成了“我”日后亲近底层大众的情感基础,随着成年后具备了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我”进一步理解了阿长的命运,文本中便增添了理性的思索和沉重的怀念。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阿长与<山海经>》以儿童和成人的双重视角叙述往事,儿童的稚气语言和成年人的老到旁白相交织,揭示了一段重要的心路历程。“儿童视角”为传达鲁迅“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内容,找到了一个最佳角度,使所述记忆取得了真实感和生动感。儿童的视野是一种“有限视野”,儿童的理解力也有限,留下了许多没有说满、说透的空白。于是,鲁迅又设置了一个全知客观的成人叙述者,隔着岁月的沉淀审视过去的“我”,以深沉、严肃、忧伤的语调,在自我对话中生发出深邃的思考。通过这两篇课文的学习,学生可以跟随鲁迅的文章寻找其经历过的生命痕迹,感受成长的苦乐百味中蕴含的温馨,从而学会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懂得珍惜成长所必经的每个人生阶段。
参考文献
[1]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87页。
[2]周作人:《鲁迅的故家》,《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902页。
[3]鲁迅:《看图识字》,《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4]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89页。
[5]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
[6]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88页。
[7]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5页。
[8]鲁迅:《我要骗人》,《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05页。
基金:泰山学院2021年度教师教育研究专项课题“课程思政背景下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性别教育”(JY-01-202110);泰安市教育科学规划专项研究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域下中小学性别教育研究”(TJK202106ZX013)。
(作者介紹:房存,文学博士,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