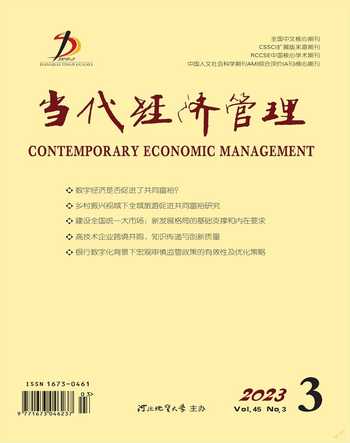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鸿沟的现状、影响与应对策略
周慧珺 邹文博
[摘要]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重要特征。然而,数字鸿沟等副产品也初现苗头,威胁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总结来看,我国接入型数字鸿沟正在快速缩小,使用型数字鸿沟持续存在但影响可控,知识型数字鸿沟的负面效果逐渐凸显,值得进一步关注。如果数字鸿沟继续扩大,将可能拉大收入和财富差距,强化市场垄断,降低企业创新动力,加剧社会阶层分化,拖累社会进步。结合我国的现实经济背景,弥合数字鸿沟需要继续推进宽带普及政策,提高整体供给数量和质量,并对老年群体、未成年群体重点关注,尽可能缩小弱势群体鸿沟。此外,还应当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励机制,加强区域间协调合作,合力打造包容和谐的数字社会。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互联网;数字鸿沟;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F4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0461(2023)03-0060-08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规模迅速扩大。尤其是疫情暴发以来,线下行业发展受挫,数字企业抓住机遇,成功将“人口红利”转化为“流量红利”,成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也为疫后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2020年底,我国大型数字平台总价值31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达到248%,已经和美国并列为全球数字经济“双引擎”。可以说,数字经济俨然成为目前市场上最具活力和创新力,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大重要特征。
然而,与此同时,“互联网+”的新模式、新业态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部分技术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农村居民等由于缺乏信息的可及性和使用能力难以从数字经济中获利,与信息技术富有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形成了明显的“数字鸿沟”。这种数字鸿沟如同一道栅栏,将一部分人排除在数字经济带来的红利之外,给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还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数字中国,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增长引擎①。這也就意味着,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已经不可抵挡,那么此时,如何规避或者减少数字鸿沟这样的“副作用”就成为更加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更进一步地,想要给出弥合数字鸿沟、减少其负面效应的有效策略,就必须先了解数字鸿沟带来的实际问题及数字鸿沟产生的主要原因,本文也希望从这两个角度入手,深入剖析数字鸿沟的现状、影响及应对策略,为下一阶段消弭数字鸿沟、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在以往的文献中,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互联网、数字金融的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问题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影响。例如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发现它能够使得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1],李金昌和任志远(2022)则利用微观数据分析发现,数字鸿沟将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不平等[2]。杜勇等(2022)将重心放在企业数字鸿沟上,探讨了平台化在企业跨越转型升级数字鸿沟中的重要性[3]。其他关于数字鸿沟影响带来收入差距的国内文献还包括胡鞍钢和周绍杰(2002)、汪明峰(2005)、邱泽奇等(2016)、苏岚岚和孔荣(2020)、王修华和赵亚雄(2020)、粟勤和韩庆媛(2021)等[4-9],国外文献还包括FORMAN等(2012)、DAHLBERG(2015)、BAUER(2018)、GONZALES(2016)等[10-13]。总结来说,以往的学术文献中,对于我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鸿沟带来负面影响的系统性梳理和总结还相对较少[14]。因此,本文也希望从这一角度出发,详细阐述我国数字鸿沟可能带来的问题及内在成因,深入探讨数字鸿沟未来的可能走势及其理论依据,给出弥合数字鸿沟的合理政策建议。
二、目前我国数字鸿沟的现状及主要特征
(一)数字鸿沟的基本内涵和现状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一词最早被定义为信息技术的持有者和缺乏者之间的差异[15]。自此之后,研究者们对于其内涵与特征进行了更详细和具体的刻画[4-16]。早期研究认为,信息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等维度的差异可能带来收入或财富的差异。根据差异形成原因的不同,数字鸿沟可以分为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前者代指信息技术的可及性差异,又被称为第一类数字鸿沟,后者代指技术的使用差异,又被称为第二类数字鸿沟。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们逐渐发现,即使在互联网可及性相同的情况下,由于不同人群通过使用互联网获取到的知识也有所不同,他们将这一鸿沟称为知识鸿沟,即第三类数字鸿沟[17-18]。
在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数字鸿沟出现在年龄、城乡、地区等多个层面上。从年龄层面上来看: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约27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达到189%。如果人口总和生育率继续维持当前水平,那么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还将不断扩大,老龄化不断加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老年群体在智能化技术学习和应用上的严重弱势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结果显示,截至2021年底,60岁及以上网民占总人群的比重为115%,远低于人口实际占比,互联网普及率仅为432%,远低于同期总人群平均值。尤其在疫情发生之后,老年人由于不会使用电子支付、电子证件等,在就医、出行上面临极大的困扰。与之相对应的,未成年人的网络使用频率却在稳步提升,网民“低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数据显示②,我国未成年网民数量超过18亿,337%的未成年人在进入小学之前就接触了互联网。疫情之后,线上课程的普及更加加深了未成年人的网络依赖程度,829%的未成年人拥有手机、平板电脑等上网设备。长此以往,代际矛盾和隔阂还可能进一步加深。不仅如此,数字鸿沟还体现在城乡、地区等层面上。2021年底,我国农村网民数量达到28亿,占比276%,较2020年同期下降37个百分点。从互联网普及率上来看,城镇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为813%,较2020年提高15个百分点,而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76%,较2020年提高17个百分点,城乡差距高达25%,部分农村偏远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很完善,当地居民能够有效利用的互联网资源非常有限。同样的问题也表现在地区之间。腾讯研究院数据表明,我国数字化基尼系数为059,数字化发展水平还很不均衡,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的“互联网+”指数摇摇领先,一线城市指数明显高于二、三线城市。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也显示,不同城市的数字红利指数具有显著差异,一、二线城市家庭的指数明显高于三、四、五线城市。
(二)目前我国数字鸿沟的三大特征
总体而言,我国目前的数字鸿沟表现出几大特点:
一是接入鸿沟正在快速持续缩小。接入鸿沟由互联网相关技术的普及程度差异引发[15],又可以细分为物质接入鸿沟和心理接入鸿沟[16],前者主要形容互联网的可及性差异,后者则主要形容对网络技术的兴趣差异。2017—2021年,我国网民规模由772亿上升至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由558%上升至730%,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城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由2020年同期的239%下降至237%,缩小02个百分点(见图1)。近五年来,两者差距呈持续下降趋势,说明城乡之间的接入鸿沟正在逐渐缩小。与此同时,我国非网民规模较2020年同期下降超过3 000万,在目前不上网人群中,仅有175%的人不上网的原因为没有电脑等上网设备,这也就是说,截止到目前,我国的物质接入鸿沟已经明显缩小,互联网可及性差的问题得到大幅缓解,剩余不接触网络原因大多为心理接入鸿沟,如年龄、兴趣等③。我国能在短期内实现互联网普及率的大幅上升和接入鸿沟的快速缩小,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国数字技术整体发展水平快速提高,市场覆盖面快速扩大。近年来,我国数字技术和平台经济发展速度有目共睹,人工智能、云数据等技术创新独立性增强,远程办公、互联网就医等新模式不断涌现,技术应用场景日益广阔。2020年底,我国大型数字平台总价值31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达到248%,已经和美国并列为全球平台经济“双引擎”。2021年,我国信息网络技术迈上新台阶,5G技术发展进一步加速,互联网供给能力不断增强,5G移动用户数量超过35亿户,5G基站数量超过140万个,为互联网普惠效应的体现和接入鸿沟的缩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政府充分发挥能动性,在偏远贫困地区积极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有效抑制数字鸿沟扩大。长期以来,我国在农村地区、贫困偏远地区实施了一系列通网通宽带举措,早在2013年,我国就已经提出了“宽带中国”理念,要求提高宽带覆盖率和接入能力。在扶贫行动开展之后,网络扶贫更加成为重要的帮扶方式,截至2021年11月,我国行政村都已实现“村村通宽带”,截至2021年底,我国农村地区的宽带用户总量已经达到158亿户,较去年同期上升11%,全国乡镇镇区5G覆盖率超过80%,农村地区通信困难问题得到明显缓解。互联网甚至开始成为不少农村居民打开农产品销路,促进跨地区贸易流动的有效手段。从地区差异来看,2021年底,我国东中西及东北地区百兆以上固定互联网接入用户数量在926%~941%之间,极差仅15个百分点,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接入鸿沟,尤其是物质接入鸿沟的逐渐缩小。
二是使用鸿沟成为目前数字鸿沟的突出表现形式。随着互联网普及程度的上升,信息使用的程度、技能等方面的差异成为当前数字鸿沟的突出表现形式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VAN(2002)指出,网络的使用渠道具有多樣性[16],一部分人能够有效利用网络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另一部分人则仅用网络进行基础通信或娱乐活动。数据显示④,906%的老年人能够使用网络进行即时通信,848%的老人能够使用网络视频,但使用网络支付的老年网民占全体老年网民的比例仅为706%,有约1/3的老年人能独立完成订票、挂号问诊或使用网银。人民网和腾讯联合调查报告也显示,中老年人最常用的上网功能集中于聊天社交、浏览新闻和网络视频。这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老年网民而言,网络还未能完全达到提供便捷服务和有效信息的目标。
不仅如此,在不使用互联网的人群中,有484%选择的不上网理由是不懂电脑或网络,还有257%选择的理由是不懂拼音等文化程度限制,这两者也是非网民不接入网络的最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也可以看成是数字使用鸿沟的另一表现形式:正是由于使用技能上的差异,他们自我感觉无法驾驭智能设备和相关应用方法,才被迫选择了不接触互联网。
在青年群体,尤其是未成年人群体内部,使用鸿沟同样非常明显。这类人群对于新知识的接受能力更强,上网功能的可选范围也更广,基本上不存在知识水平限制智能设备使用的情况,然而,在使用功能的自主选择上,不同人群的决策则可能差异巨大。数据显示,我国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经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在网络使用方面,农村未成年人明显更偏向于使用短视频、动画等功能,而城镇未成年人则更常使用新闻、搜索引擎等。休闲娱乐功能的长期使用不但无法带来效率提高、工作机遇增加等正面效果,还可能形成网瘾,耽误正常工作或学习,造成负面影响。
针对老年群体使用鸿沟问题,平台企业积极改进,极力简化操作流程、降低使用门槛,打造老年友好型操作界面,不少平台还推出了老年关怀版软件,帮助老年群体跨越使用鸿沟,共享数字红利。但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群体内部使用鸿沟问题仍较为突出。从理论角度分析,更高的使用率甚至成瘾行为是平台企业盈利的重要基础,因此,平台通常没有实质性动力改善这一问题。
三是知识鸿沟的负面效果逐渐凸显,值得进一步关注。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老年群体、农村群体等开始接入互联网,不少老年人甚至将越来越多时间投入手机使用,成为“网瘾老人”,然而,这也滋生了更新且更严重的数字鸿沟问题,即知识鸿沟。事实上,知识鸿沟也可以看成是接入鸿沟和使用鸿沟带来的深层影响,正是由于互联网使用技能和程度上的显著差异,才使得不同人群通过互联网获取的信息和知识不同。数据显示⑤,有662%的中老年网民遭遇网络谣言,527%遭遇虚假广告,还有超过1/3的中老年网民曾被网络诈骗,诈骗渠道包括保健品、红包、彩票等。不仅如此,年龄越大的网民,较容易受到网络谣言和诈骗的侵害,尤其在保健品诈骗中,71~80岁的老年网民遭遇保健品诈骗的概率达到362%,较50~60岁网民高出161个百分点。这也足以说明,即使能够接入互联网,使用频率高,各年龄段之间的知识鸿沟也难以被完全消除。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低文化程度的上网人群中,由于对网络信息真实性的鉴别能力较低,他们往往更容易落入虚假广告、网络传销等诈骗陷阱,造成财产损失。
值得提出的是,知识鸿沟的出现在中老年网民的意料之内。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老年群体担心自己遭受网络诈骗、谣言和虚假广告,多数中老年人有意识地关注可能的安全事件,提高自己上网的安全性,但即使如此,类似的事件发生率仍然居高不下。更糟糕的是,中老年人受网络诈骗的社会舆论对这一年龄阶段的潜在网络用户造成了很强的负面效应,又进一步地降低了他们对于数字技术的信任程度,强化了抵触心理,形成了更大的数字鸿沟。
三、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可能带来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如果数字鸿沟继续扩大,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具体来说,首先,在个体层面上,数字鸿沟加大了弱势群体的可能损失,提高了优势群体的当期和未来收入,拉大贫富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次,如果数字鸿沟继续延展到企业层面,使得企业异质性增強,行业垄断程度提高,底层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则可能进一步影响国家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最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数字鸿沟可能会扩大人群间的社会资本差异,加剧社会层级的分化,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
(一)拉大收入和财富差距,影响共同富裕进程
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鸿沟使得一部分群体被边缘化,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收入或财富的上升速度较其他群体而言更加缓慢。例如汪明峰(2005)研究表明,互联网接入的空间差异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5],且一般而言,互联网更加“偏好”大城市,也因此能为大城市带来更多可能收益。FORMAN等(2012)通过美国数据研究发现,互联网对于收入和就业的促进作用只体现在极少部分地区,因此互联网的持续发展和普及未能缩小数字鸿沟,反而使得地区间的不平等加剧[10]。邱泽奇等(2016)则通过企业数据统计发现,东部发达地区往往能从互联网红利中受益更多[6]。具体而言,数字鸿沟可能通过以下三个渠道影响收入和财富差距:
首先,短期来看,数字鸿沟提高了低文化水平、老年等群体的可能损失。这些人对于信息真实性的识别能力更差,也更容易遭受损失财产。近年来,老年群体、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在线上购物、知识付费中受骗的案件屡见不鲜,不乏有犯罪团队针对弱势群体的心理特征定制诈骗技术和相关产品。王修华和赵亚雄(2020)从数字金融的角度入手,发现非贫困户在利用数字金融手段防范风险、平滑消费上都具有明显优势,因此能够有效提高家庭收入,而贫困户缺乏必要的金融素养,数字金融对其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两者的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8]。这也是数字鸿沟对财富不平等最直接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这些弱势群体越多接触互联网,使用互联网,就更有可能遇到网络骗局,蒙受经济损失,和其他群体的财富差距随之拉大。
其次,中期来看,数字平台为使用者提供了更优质和广阔的创业、招聘等信息资源,促进部分人群的收入提高。一方面,对于求职者来说,网络平台无疑提供了更完备的招聘就业信息,有利于使用者获取更有益的资源,进而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从搜寻-匹配机制的角度出发,这相当于将处于数字鸿沟两端的人群分割为两个市场,能够有效使用互联网的人群对应的劳动力市场匹配摩擦下降,匹配效率降低,工资收入提高,而无法有效使用网络信息的群体对应的劳动力市场则依然保持原状,收入差距由此产生。另一方面,对于创业者来说,互联网的使用让他们获知了更多有效信息,提高了创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例如苏岚岚和孔荣(2020)通过对山西、宁夏和山东的创业农户调查研究发现,互联网采购、销售能够明显提高农户收益[7]。粟勤和韩庆媛(2021)研究则表明,接入鸿沟能够通过提高信息优势家庭的创业和金融投资的渠道扩大财富不平等,使用鸿沟则能够通过影响家庭融资拉大群体经济差距[9]。
最后,长期来看,数字鸿沟加大教育不平等,提高预期收入分化程度。网络往往能为求学阶段的使用者提供有益的教育资源,提高学习效率和受教育水平,进而提升其未来收入。目前,互联网使用者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尤其在疫情背景下,互联网更加成为大部分中小学正常教学的重要工具。大城市学龄人群积极利用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捷地获取学习资源,但部分农村、山区的学生仍然不得不到处借用网络上课,课后复习、资源查询等活动的便捷程度明显低于大城市,教育资源不平等程度明显上升。大量教育经济学相关研究表明,教育的不平等是长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重要和主要来源,学历、知识水平和工资收入、财富水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9-22]。因此,从长期看,随着数字鸿沟继续加深,其带来的教育不平等及未来收入分化问题都可能会逐渐显现。
(二)强化市场垄断,降低企业创新动力
目前,数字鸿沟大多停留在个体层面,即不同人群的数字技术使用效率有所差异,区域、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本质上也都是个体数字鸿沟的具体表现形式。但与此同时,也有文献认为,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个体之间,也体现在企业之间[23-24]。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进程不断加深,不同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开始出现明显差异。不仅如此,在行业内部,不同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同样存在异质性,小部分企业抓住互联网红利时机,快速抢占市场,掌握话语权,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形成行业巨头,市场格局日趋两极分化[25]。
在这一情形下,行业的垄断程度提高,小部分巨头企业和绝大多数小微企业并存,市场整体的创新动力也随之下降。以整体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平台企业为例,目前,我国平台企业的基础研究、底层技术创新实际上相对薄弱,具体表现为研发投入占比较低,与美国同量级企业相去甚远。2021年,我国头部平台企业阿里巴巴后三季度研发支出总计44521亿元,仅占营业总支出(570948亿元)的780%。另一头部电商企业京东2021年研发支出更低,仅为16332亿元,占营业总支出的172%。新晋电商平台拼多多全年研发费用不足100亿元,占总营业支出的1033%,而销售和营销费用(包括促销和广告活动)却达到44802亿元,相当于研发费用的4倍多。腾讯公司近年来更加强调对科技和研发投入的高度重视,2021年研发投入同比增长33%,研发人员增长41%,新增研发项目超6 000个,但即便如此,其研发费用和营业总支出之比也仅为1165%。相比之下,美国头部平台更加注重核心技术的创新引领,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信息等多个领域保持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2021年,谷歌公司研发支出201229亿元,占营业总支出(1140756亿元)的1764%。Facebook研发支出157192亿元,和营业总支出(453795亿元)之比更是高达3466%,相当于阿里巴巴的4倍,京东的20倍。
企业数字鸿沟形成的行业垄断为什么会导致创新力下降?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一是数字鸿沟带来的垄断大多依赖于并仅依赖于营销模式的创新。先发企业利用数字化、平台化为用户提供便利,快速吸引大量用户,形成用户使用惯性,占据垄断地位。这一垄断不是来自于高精尖的技术支持,而是来源于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或是侥幸的把握和大量的商业宣传。因此,为了在短期内稳住市场地位,避免利润损失,这些企业只会更加急功近利,加强广告力度和商业模式创新,对投入大、短期成效低的技术攻关不屑一顾。更进一步地,这样的商业模式创新又引发一系列连锁问题,如反垄断指南细化条例准确解读等。这些事务继续大幅挤占这些巨头企业的时间和资源,导致企业研究底层技术,创新突破瓶颈的精力过少。二是创新激勵和垄断地位本身矛盾。一方面,创新研发是典型的高初期投入、高风险项目,且回报周期往往较长。经济学理论表明,要企业积极开展自主创新,加强研发投入的关键前提是足够的垄断利润。如果无法长期占领市场,利用技术获得垄断收益,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始终不足。另一方面,正如此前所述,对于依赖数字鸿沟发展起来的垄断企业而言,目前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基本足够吸引用户。因此,企业没有底层技术方面的“近忧”,进一步创新的动机只能来自于“远虑”,如果企业长期获利的不确定性加大,经营短视性增强,底层技术创新的“性价比”和动力则更加下降。
这样一来,巨头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精力和动力都有所不足,而其他小微企业更是面临生存压力,不具备进行技术研发的财力物力。而商业模式的驱动力和数字化带来的“流量红利”总是存在饱和水平,长此以往,一旦饱和水平临近,企业仍然要面临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窘境,核心技术创新力的匮乏必将影响我国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加剧社会分化,不利于社会进步
数字鸿沟的长期存在还可能导致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增长的落后。目前,数字化转型的快速推进无疑拉动了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经济的增长本身只需要经济总量的扩大,至于智能产品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行业垄断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数字鸿沟等副产品则会被其正面效应所掩盖,无法从经济增速中看出。相比之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则要求一个更加文明和和谐的状态。“十四五”规划中指出,“十四五”时期,社会文明程度要取得新进步,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质应当有明显的提高,民生福祉应当达到新的高度。想要达到这一目标,就不能允许一边是摩天大楼,一边是贫民窟的场景出现,不能因为数字鸿沟而产生社会排斥和公共风险,助长两极分化的社会形态。从理论上分析,数字鸿沟对社会形态的可能影响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数字鸿沟可能扩大社会资本差异,加剧社会分化。社会学理论认为,人在社会中的空间位置取决于其持有的经济、社会等方面资本,其中社会资本则决定于其所在社会网络中的成员数量、关系、信任程度等等[2]。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会资本可能会通过个人的成长和继承等渠道发生转移,形成社会流动。一般来说,我们更期待看到个体通过个人才能、努力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26],促进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然而,数字鸿沟的出现却往往与社会资本的固化及阶层的固化联系在一起。在我国数字化的进程中,位于城镇地区、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地位更高的个体往往能够更容易地接触并合理使用数字技术。换句话说,互联网让本来就持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更多地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优势,而本来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非但没有受益,反而可能因为过度娱乐、沉迷网络等原因身陷困境。这样一来,数字化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可能会逐渐演变成不可愈合的社会差异,社会阶层也可能会进一步固化。
另一方面,数字鸿沟可能会形成群体间的社会排斥,不利于社会稳定。数字鸿沟像一道栅栏,拦在不同年龄、不同区域的人群之间。中老年人对数字化相关产品的掌握程度普遍较低,使用功能较单一,难以和青年人群产生共鸣,代际交流障碍进一步加深。更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化使得不同类型的使用群体也产生了交流障碍甚至社会排斥,人们更愿意与使用类似数字产品功能,关注类似话题的人群交流,而对那些偏好异于自己的群体抱排斥态度。那些沉迷网络游戏、渴望不劳而获的群体也同样会形成集聚,使得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快速增加,违法犯罪概率提高,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四、弥合数字鸿沟的相关政策建议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字化转型蔚然成风的大背景下,数字鸿沟的问题也引起了党和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早在2002年,习总书记就曾指出,要缩小山区与沿海地区获取信息的差异⑥。21世纪以来,我国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中央政治局多次集体学习中都强调,要严密关注数字鸿沟问题,避免信息弱势群体由于跟不上数字化高速发展的节奏而脱离主流社会。2021年,“十四五”规划将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推动数字化应用作为重要的战略规划,可见对数字鸿沟问题的重视程度之高。那么,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到底如何有效弥合数字鸿沟,促进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接下来,将先从数字鸿沟的成因等方面分析弥合数字鸿沟的思路和策略,而后给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一)弥合数字鸿沟的思路和策略分析
关于数字鸿沟的未来走势,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个观点是:随着数字技术的继续进步和发展,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数字鸿沟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就像很多新事物出现时,总会有一部分人先动起来,获得超额利益,此时两类人群之间的差距必然会越来越大,但随着市场的不断完善和新企业的不断进入,市场的进入门槛越来越低,更多的人得以以更低的成本进入市场,“鸿沟”也就随之消失[27-28]。与这一观点相对应的,有研究表明,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我国平台经济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逐渐从阻力变为动力,收入不平等会先上升后下降[1]。这也就意味着,数字鸿沟不会成为长期隐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就将能够平等地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高效和便利。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则报以悲观态度,认为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数字鸿沟缩小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不再变化,这也就意味着,总是有一批人跟不上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节奏,成为技术变迁进程中的牺牲品。
这一思想的理论依据与数字鸿沟的产生原因息息相关。结合上文的分析,数字鸿沟形成的可能原因包括以下三点:一是互联网接入程度的差异。由于城乡、地域、家庭收入等方面的原因,总有一部分人无法接触到数字技术及其带来的好处,因此和其他人的差距慢慢拉大。二是应用新技术的能力不同。目前,大部分人群都能够接触到智能手机、电脑等数字化产品,但受前期受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的影响,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有效利用网络,从中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却难以有效利用甚至深受其害。三是市场设置的正反馈调节。从供给侧的角度出发,数字鸿沟来源于市场供给对需求的正反馈调节:第一,青年、城镇居民等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往往具有更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因此,在最大化利润的目标驱动下,大多数企业趋向于迎合优势群体的需要,而并不愿意考虑老年人等非目标受众。这又将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数字化产品使用的门槛,降低使用体验,形成两级分化的正反馈调节。第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人群对于网络游戏等娱乐活动的沉迷正是相关行业所喜闻乐见的,甚至为了进一步增加营收,这些行业还将想方设法让这些人群在游戏上停留更多时间,花费更多金钱,离有效利用网络资源的道路越来越远。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更新和政府“村村通”工程的不断推进,接入程度的差异必将逐渐缩小,并有望在短期内消失。但与此同时,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现状尚且堪忧,人群的前期受教育程度、家庭环境的强异质性在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数字技术应用有效性差异的弥合也是一個长期工程。更值得一提的是供给侧的问题,市场对于特定人群的选择性供给造成了很强的正反馈调节机制,趋向于让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越来越大。从这一角度出发,如果政府不加干预,任市场自由发挥裁量,那么数字鸿沟能否彻底弥合的确存疑,这也是部分人认为数字鸿沟最终难以弥合的主要原因。
(二)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结合我国的现实经济背景,本文认为数字鸿沟问题的解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继续推进宽带普及政策,提高供给数量和质量,彻底解决接入鸿沟问题。得益于前期普惠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接入鸿沟已经逐渐缩小,但城乡、地区间差距仍然存在。下一阶段,应当继续加强宽带网络建设,加强智慧乡村建设,着力提高农村地区、偏远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在此基础上,应当提升宽带接入质量,推动基础网络服务提速,鼓励互联网企业积极投入研发,降低使用成本,保障弱势群体能够支付得起基础网络服务费用,彻底解决接入鸿沟问题。
二是建设老年友好型智慧城市,减少弱势群体使用鸿沟问题。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由于购买力弱、消费意愿低等特点无法成为数字企业的目标受众,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越来越大。这一问题的解决亟需合理运用政府+市场的手段,进一步强调数字社会的包容性,加强对这些群体数字技能的公益培训,鼓励家庭内晚辈积极分享和传播数字化产品使用技能。不仅如此,还应当在医院、信用社等老年人比例较高的场所保留人工窗口,设置设备操作引导人员,保障弱势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
三是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使用规范,避免过度沉迷带来的鸿沟问题。未成年人在接触数字产品时自控能力较弱,容易因沉迷游戏、小说等不可自拔,与其他群体的差距越拉越大,形成另一种类的数字鸿沟。因此,应当加强政府干预,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使用,合理约束未成年人软件使用行为,降低未成年人内部使用数字鸿沟对于长期收入和财富分化的影响。
四是严格信息保护,加强网络宣传,缓解知识鸿沟问题。目前,我国数字市场的个人信息和财产保护措施尚有待提高,弱势群体上网时容易落入诈骗陷阱。数据也显示,677%的老年网民希望政府能加强网络治理,在安全上网方面提供有效帮助。下一阶段应完善网络安全立法,明确网络服务主体责任,提高互联网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规范性,切实保障消费者利益。
五是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励机制,改善企业数字鸿沟现象。一方面,由于资金不足等问题,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程度往往较低,与大企业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可以将数字化相关创新活动作为政策支持力度的重要参考指标,设立数字化科创专项贷款,重点扶持、优待数字化创新型中小企业。另一方面,由于动机不足,收益较低等问题,大企业利用数字化获得垄断地位后,硬科技创新往往较少。因此,应当综合市场份额、技术含金量等因素合理设定创新专利保护期限,允许那些开展核心技术创新的大企业通过专利变现、技术产业化等手段获得合理垄断利润,鼓励大企业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先行军、主力军,避免因企业数字鸿沟带来的行业创新力下降问题。
六是因地制宜,加强区域间协调合作,打造包容和谐的数字社会。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面临的数字鸿沟类型也有所不同,有的省份城乡数字化差距大,农村地区网络覆盖率和数字产品使用率低,有的省份则更多的表现为年龄鸿沟或企业数字鸿沟。因此,应当因地制宜,鼓励地方政府发挥主观能动性,及时了解当地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形式,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此外,应当加强区域间协调配合,加强网络制度规范的全国一致性,共同打造包容、平等、和谐的数字社会。
[注释]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② 数据来源:《2020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
③ 还有部分人群不使用互联网的原因为不懂电脑或网络,不懂拼音等,这可以归结为使用鸿沟带来的前置问题,我们将在使用鸿沟部分进行详细描述。
④ 2022年第49次《中國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⑤ 2018年《中老年人上网状况及风险网络调查报告》。
⑥ 节选自习近平《缩小数字鸿沟,服务经济建设》,《福建日报》,2002年5月17日。
[参考文献]
[1]程名望,张家平.互联网普及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与实证[J].中国农村经济,2019(2):19-41.
[2]李金昌,任志远.互联网使用是否会加重社会阶层分化[J].经济学家,2022(7):98-108.
[3]杜勇,曹磊,谭畅.平台化如何助力制造企业跨越转型升级的数字鸿沟?——基于宗申集团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2,38(6):117-139.
[4]胡鞍钢,周绍杰.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J].中国社会科学,2002(3):34-48.
[5]汪明峰.互联网使用与中国城市化——“数字鸿沟”的空间层面[J].社会学研究,2005(6):112-135,244.
[6]邱泽奇,张樹沁,刘世定,等.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6(10):93-115,203-204.
[7]苏岚岚,孔荣.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户创业增益了吗?——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0(2):62-80.
[8]王修华,赵亚雄.数字金融发展是否存在马太效应?——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经验比较[J].金融研究,2020(7):114-133.
[9]粟勤,韩庆媛.数字鸿沟与家庭财富差距——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9):80-96.
[10]FORMAN C, GOLDFARB A, GREENSTEIN S. The internet and local wages: a puzzl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2(1):556-575.
[11]DAHLBERG L. Expanding digital divides research: a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media [J]. Communication review,2015,18(4):271-293.
[12]BAUER J M. The internet and income inequality: 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in a hyperconnected society [J].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018,42(4):333-343.
[13]GONZALES A. The contemporary us digital divide: from initial access to technology maintenance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6,19(2):234-248.
[14]王春英,李金培,黄亦炫.数字鸿沟的分类、影响及应对[J].财政科学,2022(4):75-81.
[15]ATTEWELL P. The first and second digital divides [J]. Sociology of education,2001(3):252-259.
[16]VAN D J. A framework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 [J].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2(12):1-2.
[17]韦路,张明新.第三道数字鸿沟:互联网上的知识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4):43-53,95.
[18]李雪莲,刘德寰.知沟谬误:社交网络中知识获取的结构性悖论[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12):5-20,126.
[19]GALOR O, ZEIRA J.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macroeconomic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3,60:35-52.
[20]BECKER G S, CHISWICK B R. Edu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56:358-369.
[21]呂炜,杨沫,王岩.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政府教育投入[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3):20-33.
[22]杨娟,赖德胜,邱牧远.如何通过教育缓解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2015(9):86-99.
[23]GALLIANO D, ROUX P. Organisational motives and spatial effects in internet adoption and intensity of use: evidence from French industrial firms [J].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08,42(2):425-448.
[24]MIDDLETON K L, BYUS K.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use in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the influence of hispanic ethnicity [J]. Management research review,2011,34(1):98-110.
[25]BARNETT G A, RUIZ J B, XU W W, et al. The world is not flat: evaluating the inequality in global information gatekeeping through website comentions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2017(4):38-45.
[26]FISCHER C S, HOUT M, JANKOWSKI M S, et al. Inequality by design: cracking the bell curve myth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27]GREENWOOD J, JOVANOVIC B. Financial development,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1):1076-1107.
[28]ABEL A B. The effects of investing social security funds in the stock market when fixed costs prevent some households from holding stock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1,98(1):128-148.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fluen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Digital Divi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Zhou Huijun1, Zou Wenbo2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836, China;
2.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Beijing 100045,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s boom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some byproducts such as digital divide are also emerging, threaten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The paper finds that now the digital divide in access in China is narrowing, the digital gap in usage remains but with controllable impact,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the digital divide in knowledge are gradually prominent, which deserves further attention. If the digital divide continues to expand, it will likely widen the income and wealth gap, strengthen market monopoly, reduce the motivation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tensify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trata, and drag down social progress. Combining with Chinas real economic background, to 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needs to promote the broadband popularization policy, improv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upply, and focus on the elderly and underage groups to reduce the gap of vulnerable groups as much as possible. In addition, we should also strengthen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enterpris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trengthen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n inclusive and harmonious digital society.
Key words: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ternet; digital divide; common prosperity
(責任编辑:张丽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