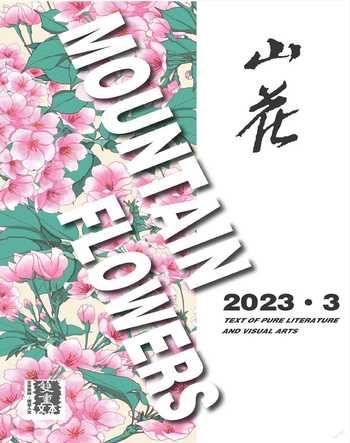海甸岛 (向斯蒂凡·马拉美致敬)
蒋浩
1、说
他说。用一种海甸岛的语言。逗号的石头渗进了海水,石脉是淡蓝色的。一本流水线装的页岩。他说。手指触摸橡皮树的结节。暗绿色的树皮汲着亲爱的汁液。有一棵死于台风,根须像章鱼干枯的触手。他摸到胸前的一颗纽扣:小小的吸盘,收集心之激流。有一棵椰树倒了——大肚的酒瓶椰,倒出迷醉的语言。粗眉状的叶子边缘稍稍灰白卷起。语言遇到了热情。他的身体同样如此。早晨的海水也暖暖的,泡在里面,皮肤感到了咆哮。夜里的一只青蛙还滞留喉间舞蹈。光洁之躯像一台发动机,海为之沸騰。灰白沙滩边缘发卷舌音:“是”或“不”。他确信裁浪为刀可以切下远处的天空一角装在玻璃缸里,在壁上绘出永恒的彩色热带鱼:每一条都是“是”或“不”。鱼说水的语言,人说岛语。但在水里它们却像一把钥匙。当它游动起来,整座大海变轻了。它迅速穿过深色海藻,到一片黑暗的海底峡谷。冰冷海水在那里有一个绕口令式的回旋。它吐白气泡,给这片海底标点句读。它最先停留在他的手边,模仿他张开但五指紧并的手掌。鱼鳞闪闪发光,来自海底的黑暗。握住它,像握住一片镜子。又软又滑的时间之镜,穿过发灰的黑发,进入石纹的脑海。他试着用一根根光线去垂钓刚才欲擒故纵的时间之鱼。在记忆里,光线因波动而纠结成无数个阿尔法直到阿尔法又引来其它的线形字母。他的阿尔法。透过其间的空洞向外看:像一个哈叭狗的项圈,优美的。交叉处穿上闪光的金属链。那链子是音乐。仿佛一抖动,每一个精致的小小金属环都是回声。即使是一阵雨濡湿表面的金属光泽,那声音仍然清脆如雨滴。有一滴从水龙头冒出来。一个个孤单的单词,在触到地板的瞬间,开花,紧接着是花开的声音。地板吸收了它的重力,表面湿湿的。一张可涂改的脸,如果他把脸俯贴下去,水流回溯初始,在脸上犁开沟壑,一双干涸的眼睛可怕地汲进了光线。他用手吃光线,满嘴海腥味。他说。用一种鱼骨的语言。淡蓝色的鱼骨像剃去树叶的小小木麻黄树,富有弹性的枝柯,每一处弯曲都蓄满音乐。他说。从一块黑色火山石里慢慢抽出这棵树。裸树。他用海水清洗上面火焰之遗迹。他触摸其中的瘤节:一颗颗牛角扣子。解开。裸树内部的几何图形像墨迹。一些淡淡远山或有烟雾的橄榄林。它显示出来。通过他的语言,他消失在他的背后。一艘船驶离了港口,留下一片泡沫和垃圾。海甸岛因无船出入而陷入自闭。他说完了,给自己在镜子前画下一句话的形象。他看着这句话从这首诗里滑逸出来,像一条蛇,曲过细脖去咬自己的尾巴。
2、听
他把蚕豆大小听诊器般的海甸岛放在海水镂刻的鼓腹上倾听。树林在海面震荡,深奥的信写在表面。词语的海市蜃楼,一束光在清扫。他随手翻开一本书。黑白方块字像一座座坟墓或一艘艘船。有时候,他看到汉字的牙齿,有的字因此听起来格外咯咯作响。手碰到了指南针。风挂在窗子上像块玻璃,蓝色窗帘分泌出蓝色染着可视天空。一群灰鹆像撒落的一瓶药片落到笼子里。他相信秩序。秩序的声音就是节奏清晰之变化。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声音。比如楼梯的声音暗示着分手。关于他与她的故事,简直就是两个回声之间的一片小海域。两个岛间的浅海。比如海浪的声音意味着思想有一个弧度。他关于波浪的解读配得上沉默。比如月亮的声音推演着潮汐之涨落。他用月光来改变自己的体温和肤色。纺锤形的耳朵,熟睡在脑袋两侧,听事物如摸象。鹦鹉螺般的耳朵,收集到海底的求爱声。一头盲目的鲸鱼在向船体缓缓靠近。海怪的背脊有时会变出波浪状的山脊。鲸鱼吞下了他的一座图书馆,一张床,一盏台灯,一个笔记本电脑,也许还有一张她的照片。它在腹腔里安放,新位置对应于旧航空港。他用盐水去洗头顶的腹壁,里面隐匿了星象图。星辰是发光的脑袋,从一个胃袋里脱颖而出。一个个标点。标点没有声音,当它们掉进一行诗句中,种子般在贫乏的园子里溅开了蓝色涟漪。鲸鱼有一只耳朵,从往昔美人或今世浪荡女那里倾听到叹息。环绕在一艘巨大沉船内部。海盗船或者太空船?一个欲望推动它的心脏。海贝里是一个蠕动的柔软思想。这里没有冬天。鸟儿的叫声织出洁白的网。鱼的倾听,裁剪着它的方格。这些声音从骨骼里发出来。如果我们用钻凿出空洞或小穴,放在嘴边向里面吹气,能听到来自骨头的声音。陶器和石头或竹管都是骨性物。声音反射在一个圆形废墟的黑眼窝里。用橡皮树叶或枇杷叶盖住。产生的阴影对声音是足够的吗?声音顺着渐枯的叶脉流向树干是可能的吗?重新被一只鸟听到,在巢里孕育,像一颗露珠那样露骨。他把这颗露珠般大小的海甸岛放在海水镂刻的一枚桑叶上倾听。声音像银蚕在偷吃月光。桑叶在手掌上,五个指头是白色之蚕。手掌像枚桑叶。他期待着一个个美妙轻盈的词能从丝蛹里孵化出来。岛上到处画满了彩蝶。热带彩蝶。蝴蝶没有牙齿,它们吸食空气以保持轻盈。像乐器依赖空气发出优美的声音。蝴蝶在岛上的白日里演奏,没有一棵树,一片草,一朵花,一排浪,不被它的香气所感染。岛事实上是一个迷醉的涡旋,当它清醒过来时,形成了此刻所见的清晰形体:一个压扁的葱绿卵蛋,在这片巨大的叶子上微微滚动。它的声音,像是小学老师用彩笔不断在天空的蓝色板上画圆圈时的沙沙声。灰一点点落下来,堆积成此刻的……海甸岛。
3、写
我写。是一个反复。好好结束,写作。我使用的这个动词并不救出“安静”。夏日是一只蜜蜂,它给我的肉体搬运蜂蜜,像溶化的碎玻璃涂抹我们的身体和嘴唇。我唱出甜蜜的诗句。伤心也是。来自海上的歌谣,也被酿成忧伤之蜜。掺杂了凌乱的光线。夏天的气味如一只水蜜桃,在你的身上滚动,分散我们专注的视线。我想到了岁月,还有衰老和青春。仿佛是罩在你身体上的一件白色T恤衫。风俗吹动着它,我们住在这座岛上。海水帮助我们恢复一些毁坏的沙滩。岛与水之间因此显得不那么突然的孤独。生活是一种节奏。任何日子都像星辰试图来嵌入或打破我们的默契和寂静,都显得那么无聊。我写作,把一些词语弃在火山石上,看它在夜里更黑或更亮。也把另一些词涂在折断的枝柯裂口处,让它们恢复对风暴的回忆。但有一些词像夏日永恒的落霞,盘旋在海面上。那片海域,我曾游向它,但现在我只在岸边。在海的这一边。我想起她就在此刻推拉这扇白昼之窗时,心绪如落日不经意望了这岛屿一眼。岛屿,所有的岛屿在黄昏都像坟墓。我写。从这坟墓里拖出一截朽木,雕刻贝壳或鳗鱼。一条海豚又吐出了它。溅满的泡沫像污点。它极可能来自于一艘沉船。我从未去想过那艘船的年龄和建造者。也许我坐过。当然,我坐过船。每个漂浮在水中的肉体都有船性。它沉没的原因不可知。每一块船板原本都是循环自足的再生物。当船上住下一群海妖,迷乱的歌声引诱了那些船板之间的默契。如果舱里渗进了蜂蜜,海水也会燃烧。大海摇晃着它们,像要把朝霞或晚餐都通过回流、涡漩等汇聚到一个桌上的盘子中心。但海妖们困倦的时候只吃木头以汲取其中的疏松。她们梳长发,涂血红的樱唇。在乳房上抹珍珠粉,用墨鱼汁画眉,通过抚摸波浪来恢复同性恋。笨拙的木船压在沉重的波浪上,像一把钝刀背压在舌头上,词语被挤压出来。我写:沉船,海妖。也许一个朴素的名词救出了其中的一块朽木。但形容词被华丽的海水洗尽了。用于粘连的冠词、介词、连词、副词都跑到哪里去了?事情的真相是一粒盐,透露出严肃的盐性。它溶解,一切都变味了。我写。啊,我写。这是一个反复。像翘起舌头那么简单?但愿这个虚幻的动词是个可触摸的名词,诞生于自然,又模仿了自然。诗歌是这样,如此的自然而然。如果用空气去挤压它,弧形的诗行也是一截朽木。海水是羞耻的,因为它在试图朗诵而不是书写。看啊,它在落日下变红了。
4、歌
“引文是一只蝉”。在秋天,也是蟋蟀,也是一排浪。任何事物都倾向光。倾向无理数。抽水马桶在防波堤下响起,一条狡猾的鲱鱼,两只红色眼睛像警报器。引文也是一枚水果,比如外表丑陋的菠萝蜜,在这棵像石榴树的庞大建筑中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反讽。芒果有大有小,金色坚韧的纤维磨砺着牙齿,坚硬果核像一个不好的习惯。她在厨房里煎双黄蛋,淡蓝烟雾来自远处起伏的山脊。她掺进海水在锃亮的油锅里,火烧得很旺,围裙边缘泛起了波澜,通过它触摸到窗外的海。物质有时也表现出疯狂,随手插下一根紫荊,开花了。一只蚯蚓在岩石里碰到了鸟粪里的种子。她打开远方的门,从这里来到客厅,有一棵水仙在等她。她的裙裾挂在一棵树上。她用仙人掌汁抹手臂,碎芦荟来洗脸。她的肌肤像一段小夜曲那样光滑优雅,催人无欲而眠。我看不到我自己的肮脏,如果在水龙头下使劲揉搓皮肤,也会出现黑色细灰合成的条状小颗粒,在海水里却没有。海水很脏,但不长蚂蟥。海蜇裹着白色水晶体的乳嫩胶质皮肤,她执意要过来搂抱。有时沙滩上几乎无人,他坐在那里喘口气,甚至抽烟喝矿泉水,斜躺着看夕阳,用手指在沙滩上画一个少女,那是一个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的少女。大海是一篇引文,沙滩是注释。一只海鸥斜斜飞过,在它下面划些着重点或竖线。鸣叫,像一串钥匙或铜钱掺在一起。当一阵雨点从那边追随过来,我首先看见的是一团褐云,沉船般随海底的暖流缓慢移动并改变着可见外形。云腐蚀着可见天空局部的秩序。心灵即使在沙滩上,也能创造出无限和有限。诗是描述它的泉水,在一个云状的陶罐里。谁能证明它出自我们能弹钢琴的手指和忧郁之火呢?它被搁在书架上,知识酝酿在周围,黑白文字的书籍每个字都像牧师。我记得小时候用针尖去阅读,像捣蚁窝,惊慌蚁群沸腾四散。我丧失了。我的善良抹上了格言。我现在用舌头去阅读,但石头对我说话,桉树和棕榈汲取着火山土中的毒素,阳光把鲸鱼晒出了一副优美竖琴般亲切的骨架。岛啊,海甸岛在漂流:一枚脱离了纬线的铜币。沙滩是一段长长引文,在岛之边缘播放了大海的某些祈祷。我们触了电,头脑中灌进了美及迷醉。我们脚下的海甸岛是海中的一个电器巨大的插座,我们的双脚正穿进漆黑插孔。大海在百米外涌动着,有时是在手边。水跃上掌心,一个词一个词地从床跳到地板上。刷白的医院卧在岛中的蓊郁山凹处,像头奶牛。我们去那里,你腹中的孩子将献给大海一声歌唱:她是你生活中的一段引文。
5、思
“大思者必将大错”(马丁·海德格尔语)。错误藏在一片眉毛般的小榕叶下。我们惺忪的腐朽睡眠染上浅浅的黄绿色,超过身高的蒿草肃穆、锋利的长叶比划着为海风裁制晚礼服。那被衰草裹住的,有着体温样恒静的一枚从脸颊掉下的白色卵石,它的皮肤印上了草叶之香,浮现,伤心的样子引来一只鹈鹕黑色的单翅。我们从望远镜里看见它们在海岸线发毛的边缘,像一个带着唾沫的复句。我从我的瞭望中救语法的错误,在大海的腋窝里掏出一点呕吐物,直到暴雨来改变事物的含水量。先是一朵云,收集着天空中光线形成的圆圈,在渐暗的毛玻璃上反复擦拭着单词拼写的错误。我们的目光连接着遥远的海平面,用一颗眼泪。每次它的影子都不同。海是其中一次,透过玻璃镜片的放大或缩小,它的影子改变了自身。我们看见的,也可以是我们想象的。但我们曾经的切肤之感,如果有,也可以是事物在成为灰烬之前的那个欲望。哦,古老的,他给琴装上一根海平线,演奏意味着漫游。请给睡眠加一点糖。他的木石居建在一排浪旁,一只狗,忠贞地,给他带来大自然的信息和讨论。他可以在红木桌边饮茶,盹思,一只微微颤抖的手靠在朴素的水果边。白日梦是反光造成的。夜晚造出他的水瓶座,白羊座,大熊座。波浪撤下一些晚宴,会把照了月光的诗句端上防波堤。如果失眠,思想像渔网,如果没有足够重的铅坠,它将无法展开。诗歌是其中的一个网眼,每一条鱼都在试图避开它,而避开的方式却是穿过。这是真正的错中错,当我从网里捡起这些闪光的鱼们,我沉思那空空如无的网眼的意义。是的,每个网眼,都洁白地看着我们劳作的双手,谁曾想起就在刚才,那里曾是一片海水呢?是的是的,鱼医治着那些空洞的虚无,网多少只是一个诱惑。当它呼啦一声撒入蓝色海水,我们感到轻松,因为相信。从那些鱼身滴下的水珠,带着它们的低体温,要来理解这岛上世界渴望的热烈。它们离开它,首先是死亡了。干涸了。鱼的眼睛,像一滴水。世界的无奈和绝望反映在那里。在烹煮之后,是完整的凝奶般的乳白色,意味着反复和单调无趣。鱼眼保存着我们的视力与想象。这是构成思的建筑,而思的边界不可以简单视为诗的边界。我们用一尾任何鱼把海洋联系起来,仿佛大海只是一个玻璃缸,我们甚至可以在它的底部烧出火焰让它沸腾,产生潮汐。我们把玻璃缸放在阳台,里面的水拉下天空的云朵,或者是旁边的一绺风。当它整个重量在减轻时,阳台像一个敞开的母腹或子宫。一颗眼泪掉进缸里,变成一尾鱼,在游动。网消失了。消失的过程很迷人。从你脸颊掉下的一粒白色卵石,激起浪花的同时也打碎了这个玻璃缸,缺失的部分是一个半月,三两点星辰,连接到一个受孕之夜。
6、问
“云的尾巴像无政府主义者肮脏的长衫?”我很慢。匍匐的岗岭在严肃空气里硬邦邦地把峭壁巉岩延伸出来,它像一条长裤,两只硕大裤腿像空洞的搅拌机,在接近沙滩的开阔地上来回徘徊、交错领先地自语。滚边的裤脚里照例系了根灰白的海岸线。这是问题的关键?但愿只是两只雌雄同体的漏斗在吮吸同一道重力:漏下来的雨点像清洗过的沙粒。海敞开她的无边的唯物主义来接受空中那个渐渐成型的胚胎。船无声地咬着对讲机,鱼在周围画线。假如这是事实的边界,加入到以“我”为中心的,寻找相似性的遗忘之旅中,每一道隆起的排浪埋葬目不识丁的信天翁,都像是牧人在剪羊毛。寻找啊,水编织一个个问号似的巢穴,瞬息之间,殖民般,在礁石上繁殖有机建筑:这是你的卧室,写意的水草铺的床垫上可以眺望大海,装配360°环形落地的禅学玻璃窗;这是你的客厅,水母打磨的哲学茶几,鲸鱼骨椅子,章鱼眼睛做的烟灰缸……你的厨房的抽油烟机像珊瑚烟斗,顶端连接着扇贝样的逻辑的马桶。你不必抱怨你比这涌现的海水生活得更咸涩,你像她一样曾经只是一个平躺在地上的动词?呵,海如果站起来,清澈的玻璃,散开的发辫,你愿意你是她的柔软的舌头,舔到来世:是一截舌根,被埋在深深的话语的遗嘱里。波浪学会了人的语言,挤在船下,接受规训,签写非平等条约:这浴缸里边裂开边愈合的反物质是否应该取代银河系中反刍的金牛座前的瑶池。但愤怒的皮肤鼓胀着,把年龄修饰成崭新的,星星的遗址。你取代了你的思想,突然出现在岬角。长堤延伸到水里,像一个带长柄勺的问号?你省略了你的眉眼,放大手掌,“看”和“借取”都使用同一副担架,同一种纤维提炼的游戏。那里也竖起一架梯子,侧面更像一把梳子。一个长颈玻璃瓶在攀爬,收集了经过折射的声音——它们在里面挤啊挤,越来越锋利,像小小的鱼片,和面包屑。爬到顶端,再顺着弧形脊背溜下来,像一盏灯,亮了,又熄灭。上下之间,两点之间,是我们最容易获得的判断力和视觉。云,为我们准备的一场雨,有时更像是一次精致的说谎。你相信了,你解脱了,你曾经受困于事物的侧面捶打出的锋利的睫毛切开的光学曲线,而现在,显然是一朵云在替你搬动泡沫填充的高枕,轻盈如蓝,没有回忆,没有悔意。海匍匐在你脚边,温顺地治疗着她自己的冲动性格,从一而终,波浪到来时的样子就像个浪子?你宁愿相信一个人的耐心才是雄心。和我们看见的风景相比,每个人都虚弱得像其中的空空山谷,不是被花花草草乱七八糟地修饰着,就是被飞鸟鱼虫吵吵闹闹地拆迁着。海水来了,就盖蜃楼;潮退了,就倒卖搁浅的契约。那团双方刚刚签名的云,像验钞机,钞票都裹着纱布,验货时,失真于环岛而生的烟火气。
7、读
“疑义相与析。”(陶渊明《移居二首》)读出声!读出声!!读出无声!!!赤条条的波浪捎来书页和节奏,霓虹灯般旋转、迷离,像数只搅料玻璃花瓶上红、蓝、白三色相间的斜纹扭打在一起,慢慢地消失在圆润长颈松弛的敞口处。海的凹凸表面,也是塌陷的玛格利特帽子的表面,堆沙的结果就是迷失于沙堡相互吞噬的苟延残喘中。沙滩是个巨大的呕吐物,也是排泄物,还在排泄沙。潮汐正抄袭着水珠膨胀的声音,一些细微的滋滋声,像瓷器在缓慢开裂的裂纹里分泌出来的露水:海在一丝不挂地,一丝不苟地,一言难尽地,排卵。多么迷乱而无助,屈从于引力,也受制于潮汐亢奋的集体之舞,在浪尖上啸叫,在浪花里失眠,在问题的核心里推动着问题的轱辘碾压着一切有迹可循。去吧,去吧,这些精致的无核之卵诞生出这个时代最出色的脑袋,相互挤压在一枚枚潮汐磨圆的小卵石上,风与水之轮番演经与讲经难道不是一场借助于天地不仁的轮盘赌?读啊!读啊!受制于心灵成长的筚路蓝缕,一股来自北冰洋的暖流像引线,从脚心向上燃烧着,世界最后悬停在一个点上,是“轰”的一声而不是轻轻一嘘,从你手中瘪掉了。读吧,我们在爱人中培养了一个敌人,那敌人是黄昏的偶像,在书本中树立了风度和颓废,告诉你:一生长于一个生日,一瞬只不过一个瞬间。我们在两撇波浪的夹缝里,窥见了白龟过隙,白鲸过海,卷起的闪电勾住海之一角,对岸的塔楼倾斜过来,城市倒挂在展开的风衣里。每一滴滴下的水在滴滴答答地,读。读不再是一个动词,而是一个灌了酒的主动词:生动地,一目十行,一日千里。水面在镜面静止时,读……读出了一个个绵延而松开的旧圈套,一个个释然无解的反程序。你相信的生殖只不过是一种无性的繁衍,任其自然,大海是我们关于天性的伟大衍生品,每一次阅读,都是误入,都在丧失天真。但哪里是关于乐趣的本体论?我们拿着星空图,找到明朝那位航海的死者。他的头骨里藏了只蓝环章鱼。沉香熏过的宋朝山水册页,喂养了她的孤独。但章鱼不是鱼。因为它能两足行走,崇尚那些复杂问题的概念思维,却学不会无思想。它和你拥有不同的情感质地,堪比人猿之别。你们身上唯一相似的是:大眼睛。显然,它遗传自长袍使者的公主。它的三颗心:对应于现实、过去和未来。而你的心只属于你没有到过的地方,像一座小岛,在海岸线上跳跃,读着穿梭于头顶的飞机。只有在下雨时,它才尽力为你展开柔软的身体,看上去像是一把撑开在水中的雨伞。雨,从伞缘读出了海的味道:我们对无知的兴趣,远远大于知识本身。
8、看
“看见的事物其实是似乎被看见。”(华莱士·斯蒂文斯《徐缓篇》)当你改变看的习惯,静下心来,观察一种思想:“观察就是思想,观察者也是,但这样的思想没有一个源头,也没有凝聚成一个恒温的结构。她的对立面是造成散点透视的可见光。”你因此加入到看,你看被看的事物,如同想象你在看你的眼睛。你有权利赞美你的看,但你用权利赞美时,你的手在看着你。你的看集中于一个携带振幅的中心,视野限制了阅读探究到的模糊边界,风景“违反了山谷、草原、树木的形象”(斯蒂凡·马拉美语),在新的有机体的凝视下,词如流星,获得了逆天之流,飞向他们自己的原音之巢。在这里,在一棵菠萝蜜树上,看就是构造。一种泥土中提炼出来的粗颗粒。从看开始,那个有着复杂蜂巢般外壳的巨果,悬在树杈间,像一口教堂之钟。钟舌裹着磁性之蜜。声音牺牲了。声音克隆了声音中的一点原始寂静,被蜜像光线一样弯曲地粘在表面。声音在声音造就的空间寸步难行,看却可以透过看不见而获得一种悠远的共鸣。那棵树是一个教堂。但那片树林是海。每一片树叶都是一尾游鱼,她在文学上酬谢了大海铺张的赋的缺陷,成为修辞那美妙又恒定的友谊和补充。看和看见中间隔着一圈求解似的波纹,看见和看不见中间隔着俳句般的细浪,看不见和看中间隔着一口深井般彼此映现的钟。声音是对看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回答,而看被压缩进无视,液体状的,裹在一个黝黑自闭的句号里。那不是结束。看没有终点。每一次目光所及都像是四壁在繁衍八方,而在熟悉的,比如,空气的表面,是看与看在交叠。我们看不见看,如果失去了物象作为视力的唯一之源,并借助他表面的温度来感知光线的演奏,心灵就只是一个关于心的摆设,还占据了一朵花的假想蕊。那里,恰恰是最神秘的腐朽。看和看之间的引力把花蕊拥抱成一朵古典之花,那些对称的花瓣反而多余得像云的鳞甲,而这朵花只是关于云的注释,吸引我们释放海岛般古老的激情。看是因为单纯的吸引,而看与看之看却仅仅是出于一种无声音乐的相似性,既是天籁的,也是物理的。我们存在在看中,我们是那个被看的存在者,相互之间并不相同的原因是:看通过看获得了无处不在的自我发展的视力。而我们葆有了来自星球深处的有机体构成的云图切片。但看加进来,她们叠加的视觉和渊深的绝句一样,总是从一个受限制的此在之点上,联通了几乎所有的代词,而唯一缺席的却是:我们。我们还在被我们控制中,帮我们打破我们的也许是:看。那束来自你的目光,更像是我们的反光。如果她产生的折射能够切割这些钻石般的日子,从生活的余屑组装的书籍坟墓中,死者会让我们被自己听到我们正在看。所以也因此变成了因此。
9、致
“有一天我要泄露你们隐秘的起源”(让·尼古拉·阿尔蒂尔·兰波《元音》)。海在这里。海的秘密对于海来说,就是她无比轻盈的起源。凝结的,反射海之微光的,挂在眼角的泪水,和挂在衣角的露水,是同一种泄露。不同于你我之间易朽的结晶和约定,泄露首先是一种薤露。泄也是一种露。泄也必然是一种出路。展示了事物成型前最完美的啟蒙变体。你在棋盘般的海面安放的每一枚船舶,循着既定的轨迹,出现与消失,如这露之盈亏,只是把滚圆的无声传递给我们起伏的峰谷了。回声折叠的未知旅程,扩散到波浪折叠的书卷里。脸上的印痕,被声音吻过。“大海是地球的一滴露”,“地球是宇宙的一滴露”,但在你我的异代之构中,悲欣交集也不过是一滴露。一滴,显而易见的不露。寥若晨星,但又寂寂无闻的结局像观察到的一件幻象之衣,上面满是结痂的树液。海甸岛是这如电如露之核心,锥子般钉住这无尽展开的波浪之绸,潮汐的每一次回溯,都在吞噬自己吐出的沙与沫。大海分娩了一个昼夜那么漫长的海岸线,串起的贝壳,和住在贝壳里的日子,像蚕在织蛹,更像是蚕在坐禅,所有听到的风声都是关于风如何把塑造的排浪保留在涌动中。在海看来,这句号般徒具空壳的小岛,像一颗在巨大荷叶中心滚动的露珠,是波浪借口于面对风波之恶的一个微小的普罗透斯式的掩体,对称于那些沙聚的螺塔。我要把这万千之水的任意一勺寄给你,顺着螺壳的盘旋之形幻化出无数歧路,一条条通到你的无数化身之酶中。当你陷入迷宫般的跌宕起伏中,凭一根箴言的绳子来引路,你的身影就是你的闪动的谎言。而你的谎言证实了你走过的路,也可能是,只是一根绳。大海为我们制造了那么多争论和误会,每枚礁石都挺出水面来解释他们的底部是如何崇山峻岭地构成了一个大陆共同体。但大海始终是平的,正如世界是平的。海的重量不是海水的重量,约等于空气在真空中的重量。但秘密是轻的,也许是最轻的灵魂。假如天使也有灵魂,那就是天使的秘密。当她飞起来,尤其是在夜空里,她的秘密就是夜的秘密:像一根饱满的弧线,不断向各个方向运动,变幻出无数彼此交叉、分割、重叠的弧线。夜何其大!秘密的关键始终在于:飞。但夜不是鸟。鸟在夜里的睡眠像大海安静的水面。海永远也不会飞,这是她诚实而痛苦的根源。“春鱼如鸟飞(汕头民谚)。”海的翅膀是鱼的刀鳍。她雕刻波浪,划伤那些雕刻波浪的波浪之手。当她低低地垂下来,收拢在身体两侧,像你在你的名字旁收起了呼和吸的偏旁。海睡眠时,是个婴儿,光光的脑门像一片用于亲吻的沙滩。不一定有鸥鸟降临,她为这片海提供片刻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