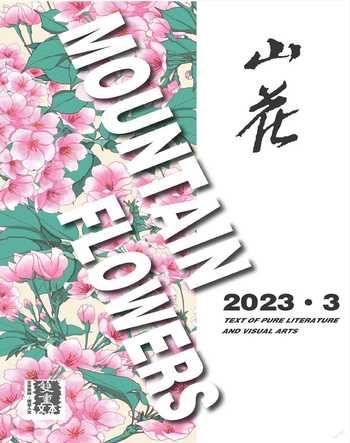我辈复登临
张执浩
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新旧两党之争已臻白热化。在长江中游洞庭湖畔,一座颓败的木楼在被谪郡守滕子京的主持下,即将修葺一新。这座始建于三国时期的木楼,原名为“阅军楼”,乃东吴大将鲁肃检阅水师的场所,其功能与古代许多亭台楼阁一样,主要用于军事瞭望。直到公元759年,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回返江陵、岳阳,登临赋诗《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之后,才被更名为“岳阳楼”:“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此时,李白的醉影尚在浩渺的烟波之中晃荡摇曳,这座焕然一新的木楼已经又涌来了新一波骚客。
新楼落成之际,身在邓州知府任上的范仲淹,突然收到同科好友滕子京的书信,以及一幅《洞庭晚秋图》。看着这幅图,想象着从未去过的洞庭湖和岳阳楼,范仲淹禁不住浮想联翩。作为庆历革新运动的领导者,范仲淹一直秉持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政治救国理念,极力倡导新政,开启了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然而,在积弊日深的大宋朝堂,他的主张屡遭挫败。联想到自己的遭遇,范仲淹难掩其为民请命的博大胸襟,宕笔写出了千古传诵的名赋《岳阳楼记》。这种缺席审美的创作手法,开创了“身不能至而心至之”的文学典范。当后世惊叹于作者奇诡卓绝的笔力和想象力,摇头晃脑地吟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滕子京是这样解释该楼功用的:足可以让人“凭阑大恸数场。”
在江南三大名楼(另两座是黄鹤楼、滕王阁)里,岳阳楼是最低的一座,楼高不足二十米,仅三层,但它采用了非常独特的盔顶结构,远观像一顶旧时的军盔扣在楼顶上,引人遐思。滕子京之恸,让我们想到了古代文人尤其是诗人们常有的凭阑思幽之情,站在高处,目力所及无非是苍茫的大地、浩渺的山川、圆满而孤单的落日,以及袅袅升起的炊烟……每一种物象都会引人反观自省,兴味无穷。而“凭阑大恸”之说,看似滕子京有牢骚苦闷之意,实则体现了那个时代每一个心怀理想的文人,对社会现实的一腔隐忍苦情。
“不歌而咏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汉书·艺文志》)在中国古代,登高不仅仅是肉身的拉抻或自我精神的超拔,这种寻常的人类行为,很早就被赋予了更为深刻丰厚的文化内核。登高而赋,既是检阅士大夫心性的思想标尺,也是评判个人才华的重要手段。汉代韩婴写过一部内容庞杂的传记《韩诗外传》,以儒家思想为本,阐发《诗经》的内容。在“卷七”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在孔子看来,登高具有启发人心智的功用,甚至你无需发愿,这一行为本身就会替你传达出某种精神意愿。也就是说,山顶、楼台、庙宇或碣石,托举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更是我们腾空达观的心灵世界。对此,刘勰说得更为明白:“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興,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对于古代的文人来讲,登高既可以明义理,巧辞令,还能够通古今,这的确是一件具有相当诱惑力的事情,不仅风雅,而且可以大大提升拓展自我的胸襟,平添壮志豪情。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九歌·河伯》)在屈原发出了“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招魂》)的浩叹之后,宋玉随后又发出了悲秋之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九辩》)送春迎秋,望川见月,总在高处,正是通过历代诗人前赴后继的精神接力,登高这一身体行为,最终成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被反复书写的醒目主题之一。
公元205年(东汉建安九年)秋,才华卓异却被荆州牧刘表弃用的王粲,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之气,登上了麦城(湖北当阳)附近的一座城楼,写下了《登楼赋》。这篇赋不仅为后世提供了一种经典的登高姿势:“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而且,将登高文学的基调清晰地定位在了“忧”字上,忧国、忧世、忧民、忧乡、忧己。此后,举凡登高者不仅形成了一种形象可感的固定的登高姿势,而且总有类似的情感喷薄而出。王粲的忧情并非没有依托,作为一介大夫,他无疑读过《大学》里的这段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高处是一个人的行止之地,当我们再也无力向上、向前时,内心就会腾涌出一缕缕空蒙苍茫的情绪,恰如朱熹所言:“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止,定,静,安,虑,而后得,这个过程囊括了一个人在高处所有的情感行为线路,而“登高必自卑”与“止于至善”“知止后有定”,因果循环,环环相扣,形成了一种整体的情感模式,构成了中国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实现路径。
到了初唐诗人陈子昂的手里,这种恣意的情感,一下子被推向了高峰和极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登幽州台歌》)
短短四句话,二十二个字,瞬间道出了几乎所有文人的命运和心声。
《登幽州台歌》所引发的情感共鸣,千百年来之所以反响这么强烈,是因为它触及到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士普遍的悲剧性命运,具有深刻的自省意识和反讽意味。据史料记载,燕昭王姬职当年筑台招贤,取名为幽州台,又称黄金台,本意是为了用这种醒目的方式招贤纳士,吸引各方人才,“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走燕”(刘向《新序·杂事第三》),终使燕国跻身七雄之列。但事实上,历朝历代被朝廷招来却弃置不用,甚至时遭贬谪的文人,比比皆是。陈子昂本来是以随军参谋的身份,跟随武攸宜前往幽州的,在唐军兵败契丹后,他的谏言不仅被武攸宜断然否决,他本人还因此被怒斥,降职。于是,百般无奈的诗人在极度郁闷、彷徨无助之下,来到了这座具有象征意味的求贤台,登台赋诗。这首诗中没有一字情景描摹,它采用的是直抒胸襟、大开大合的语言策略,其苍茫遒劲的笔力,直逼屈原的《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这种天地苍茫、满目空蒙的忧伤感和悲怆感,深刻的孤独体验,以及生之有涯又无限的宏大宇宙观,正是这首诗歌越拧越紧、越吟越响遏行云的内核。
历代文人无不热衷于登高赋诗,而且这类题材的名篇佳作不断,登高的主题也在争相书写的过程中被不断地拓展开来。从早期的游子思乡、思妇怀人、怀才不遇、嗟贫叹厄,到后来的家国破碎、壮士悲歌、矢志不渝,诸如此类的心灵密码,被登高者一一破译出来,化成了他们一啸愁怀的重要传导介质。而除此之外,抒怀励志,咏唱亲情,展现自由美好的心性,赞美大好山河风物,也是登高者不可或缺的主题内容。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这是一首充满了感伤之情的七律,作者柳宗元当时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至柳州,站在城上高楼,目力所及之处尽是萧瑟肃杀之气。诗人想起与自己同时落难又天各一方的朋友韩泰、韩晔、陈谏、刘禹锡等人,不禁愁绪漫涌,思念之情一时难以遏制,却又因身处僻乡而滞涩难遣。柳宗元的“愁思”,不在于他登得不够高、看得不够远,而在于他纵有“千里目”,也无法看清楚自己人生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辛弃疾索性将文人们热衷于登高的心理原因和盘托出,“强说”虽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书写现象,但也不排除,有人的确将个人之愁升华成了时代的审美所需,在移步换景的过程中,实现了对时空和生命气象的精准把握。唐人李峤作《楚望赋》,在序中分析了登高给人带来的心理反应:“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远而远必伤。千里开年,且悲春目。一叶早落,足动秋襟。坦荡忘情,临大川而永息,忧喜在色,陟崇冈以累叹。故惜逝慜时,思深之怨也;摇情荡虑,望远之伤也。伤则感遥而悼近,怨则恋始而悲终。”在历代文人的心目中,登高其实已经不是肉身的简单位移了,它演变成了一种具有强烈象征性和连续性的精神活动。当这种身体行为与诗人的心境相熨相贴时,某种极具感染力的声音就会脱口而出,由自我述怀变成一个时代的情感共同表达。
公元725年前后,黄鹤楼迎来了它建址以来最重要的一位访客:崔颢。此时,这位年轻的诗人并非我们现在想象中的那样神采飞扬,相反,他的眉宇间深藏着一丝丝愁怨。据史料记载,年少成名的崔颢因作《王家少妇》一诗,“增饰古典,语近佻闼”,而“名陷轻薄”,被时人视为有才无行之人,曾遭时为户部郎中的李邕斥责。进士及第之后,崔颢一直仕途坎坷,郁郁寡欢。为了平复内心的孤愤,他一气之下,索性远离长安这个是非之地,四处漫游。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有一天,崔颢转悠到了自己的“政敌”李邕的故里江夏,“登黄鹤楼,感慨赋诗”。
历史总是以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为后世提供各种茶余饭后的谈资,让我们在感叹造化弄人的同时,不免想窥探命运的玄机。而彼时的黄鹤楼,也远非我们现在想象中的峻拔和宏阔,它还只是一座临江负险、作军事瞭望指挥之用的岗楼,这种局面还要等将近一百年之后才会得以改观(直到唐敬宗宝历年间,权臣牛僧孺建江夏城,才首次将黄鹤楼与城垣分离,使之成为一座独立的观景楼)。事实上,在崔颢之前,已有南朝陈代诗人张正见和南朝宋代诗人鲍照等人,先后为黄鹤楼赋诗,写下了“飞栋临黄鹤,高窗度白云”(张正见《临高台》)、“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鲍照《登黄鹄矶》)等诗句,但他们留下的诗篇,终究没有能扛过岁月的淘洗,最终湮没在了时光的淤泥中。唯有后来者崔颢的这首《黄鹤楼》,突破江险,灿烂于夜空,成就了这样一座巍然于华夏文明之巅的“诗楼”,被后代誉为“唐人七言律诗之首”。“楼真千尺回,地以一诗传”,清人赵瓯北因此而感叹不已,而在他感喟之余,崔颢早已从后来者变成了先临者,永久性地占据了黄鹤楼最为显赫的位置,全方位地俯瞰着随后蜂拥而至的登临者,一劳永逸地拥有了对黄鹤楼的永久的署名权。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著名的景点,无论是云台寺庙,还是河流山川,大到云山雾水,小到树木花草,一切自然、人文景观,既是物质的,同时也是精神的。一个简单的、无一例外的事实是:凡是没有被文学之光探照过,尤其是没有被诗歌照亮过的地方,无论它多么优美丰饶,都不过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偏僻之乡。
诗歌的“照见”功能,在“诗教”浓郁、重视自然书写的古典中国,一直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使用价值。无用之诗只有在穿越了时光隧道之后,才会显示出它对岁月、对时光本身的强大吸附力,而真正优秀的诗文,其实就是这样一束光,先是照亮,然后才是唤醒和复活人类的心灵世界。崔颢的到来,以及他的提笔赋诗的行为,就完成了这样一个由幽微到璀璨的转换过程,奠定了黄鹤楼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位置,超越了一座楼在建筑学上的地位,赋予了这座建筑物独特的精神坐标气质。反过来讲,黄鹤楼的存在也成就了崔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名与物之间的相互成全关系,构成了人类文明的内在基石,即,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照见”,既可探幽去蔽,又能够拨云见日,唯有被语言之光探照过的地方,才能在人类的文明的长河里熠熠生辉。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在崔颢吟罢搁笔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有文人骚客前来登临黄鹤楼,一个个摩拳擦掌,一试笔锋,但随即就陷入了“吾生晚矣”的困扰之中,而在这群跃跃欲试的骚客里,就包括素来以“大鹏”自居的天才诗人李白。
我們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李白第一眼看到崔颢那首题诗时的情形,无法知道他究竟是在怎样的心境和环境里,阅读这首壁上之诗的。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位自视甚高的大诗人,在面对这首崔诗时,一定有过恍若电击般的震惊体验。优秀的读者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往往是在冥冥之中,上苍馈赠给优秀作品的额外奖赏。对于崔颢的《黄鹤楼》而言,李白就是被命运之手推送到它跟前的。如果没有李白这位杰出的读者,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位夸张而真诚的读者,那么,崔颢的《黄鹤楼》就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世人的关注。李白一生曾多次路过和登临黄鹤楼,前前后后写过数首关于黄鹤楼的诗篇,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黄鹤楼》《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江夏送友人》等,也写出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等名震江湖的诗句,然而,无论怎样写,他始终觉得,自己的这些诗篇都不足以与崔颢的《黄鹤楼》相媲美;而且,关于黄鹤楼的诗,他写得越多,沮丧感和挫败感就越是强烈。这无疑是一桩让他难以接受的事情。
在“崔白之争”这段文坛公案里,我们看到了强力诗人之间的角逐,明显带有“精神赤子”的意味。也就是说,作为后来者或晚生者的李白,他耿耿于怀的其实已经不是对黄鹤楼的“署名权”,而是面对先临者崔颢时,自己该如何全面而彻底地激发出内心的“斗志”,使自己的书写也能与这首崔诗一样,精确地抵达名与物之间相互照见、相互成全的效果。
强力诗人之间的角逐,往往会超出普罗大众的想象和期待,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好诗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等待后来者去发现,去超越;而且,这世上绝无无可超越的好诗,只有不一样的好诗。何处最高与哪首诗最好,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黄鹤楼这里,被绝妙地并置在了一起,成为古往今来历代文人检视自我精神度量的标尺。这或许才是登高的本义,就像南宋词人韩元吉所言,“登临自古骚人事”,文人墨客们在登高的过程中,将历史和文化积淀下来的复杂情感,与个人的现实处境相映照,从中生发出独具气象、富有个人语言魅力的诗句,并由此形成了某种生命的呼应感。如果说,“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诗经·豳风·东山》),是这种情感模式的前文本之一,那么,后来者则需要创造出超越它们的“后文本”来,如此,他们才能真正摆脱被前人遮蔽的命运。而这样的命运,在黄鹤楼这里,在所谓的“崔白之争”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李白怀着执念,在不停地强攻,甚或佯攻,却久攻不下的过程中,完成了某种心境转换,也完成了某种对自我的精神超越。公元748年前后,李白第二次来金陵游历,突然灵机一动,决定另起灶炉,写一首关于凤凰台的诗,而且他暗自要求这首诗,一定要能足以与崔颢的《黄鹤楼》旗鼓相当。从《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的结构和意境营造来看,李白无疑是以某种雄心来完成这首杰作的,他借助了前者的经验,同时也超越了自我的局限。正是这首同为杰作的《登金陵凤凰台》,体面地挽回了这位天才的颜面。作为一位强力诗人,李白的不甘不屈之心,的确显得天真可爱,甚至多少还带有一点孩子气,但恰恰是这种同行之间纯粹的诗艺竞技行为,成就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诗坛佳话,也为中国文学带来了后浪推前浪、前浪堆后浪的活水之源。
“诗的影响不是一种分离的力量,而是一种摧残的力量——对欲望的摧残。”“诗没有来源,没有一首诗仅仅是对另一首诗的应和。诗是由人而写就的,而不是无名无姓的‘光辉。越是强者的人,他的怨恨就越强……”。我在青年时期,就读到过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随着后来我在诗学中浸淫越深,越感觉类似的“焦虑感”,其实也是一种命运的必然。在这部影响巨大的专著中,布鲁姆坚持认为,欧美十八世纪以后的大诗人其实都生活在弥尔顿的阴影之下,而当代的英美诗人,则活在那些与弥尔顿作过殊死搏斗之后,最终幸存下来的诗人的阴影里。他甚至断言,历史上所有的强力诗人,都无法摆脱迟到者身份的焦虑。我们看到,这一论断不仅在李白身上,哪怕是在更晚者杜甫身上,都得到过确实的印证。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是同为唐代优秀诗人的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生发出来的感叹。诗人以一种释然的姿态和心境面对着命运的无常,勉力书写着自己命理中的文字。每一位诗写者在登临复登临的过程中,如何完成自己对眼前江山物象的命名,真是一桩“哀莫大于心死”的事情,但怎样去克服和战胜这样的哀怨和心魔,重新激活自己的内心世界,却是考察一个诗人心智和才华的标尺。孟浩然的这首诗,之所以后来有无数的读者拥趸,就在于它以一种完全开放的态度,参与到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不卑不亢地承受着命运,并心怀蒙恩者的复杂情感。
公元769年,已经在无可挽回的命运之途中行至人生暮年的杜甫,拖着病体残躯来到了岳麓山的道林寺,望着眼前那一块块覆满藤蔓和苔藓的石壁,以及前辈诗人宋之问题写在石壁间的诗行,他写下了《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在这首诗的末联,诗人写道:
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流待老夫。
好一个“分”字和“待”字,充分体现出了诗人对造物主公允之情的信赖,也体现出了杜甫对自我才华的信任,就像他先前在《后游》一诗中所言,“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待”在这里体现为,诗人与造物主的双重耐心和相互期许。而唯其如此,后来者才有望获得命运的厚待。
杜甫在道林寺承认了自己处于迟到者的不利位置,但面对无可逃避的命运,他没有任何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信”,信任造物主,也相信自己,因为江山和花柳的情谊我们不能辜负。这显然与李白执拗的行事风格不同,也与孟浩然看淡世事的态度不一样,因为杜甫始终相信,无论多么逼仄的人世间,仍有可以题写的空间在等待着他,甚至是,专门为他的到来而静静等候在那里。尽管这种局面略显尴尬,留给后来者的可题写之处,很有可能只是前人余下的“物色”,但即便是边角废料,又有何妨?这样的坚执与自信,让我们在文学史上看到了一个与李白全然不同的大诗人形象,而这种形象,也完全与我们心目中的那位吟哦着“诗是吾家事”的诗人情貌相吻合。杜甫在道林寺这里,以一种近乎自谑的轻松方式,消解了前人施加给他的压力,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完成了對人间“物色”的再次分配和拥有,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道林寺的永久占据者,以至于晚唐诗人崔珏再来道林寺时,根本就不再提及先前题过诗的宋之问了:“我吟杜诗清入骨,灌顶何必须醍醐。”以示弱之势行霸气之实,杜甫反宾为主的做法,不得不令人叹服,难怪后来者嗟叹:“壁间杜甫真少恩”(唐扶《使南海道长沙题道林岳麓寺》)。不留余地,倾尽才华,这才是杜甫作为晚来的大师,在面对晚来者的命运这一重大的人生命题时,所葆有的诗人本色。
“愿意工作的人将生下他自己的父亲。”这是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中的论断。尼采在此基础上补充道:“当一个人缺少好的父亲时,就必须创造出一个来。”与其在焦虑面前缩手缩脚,倒不如放手一搏。问题是,如若已经有了一位好“父亲”,或好“祖父”,作为后辈晚生究竟有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弑父”?如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我们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死去的前者,会依附于正在书写的后来者身上,复活过来,而每一次复活,都是一次新生,一次无怨无悔、愿赌服输的登临。
这是一个先来者与后到者相互唤醒、相互成全和相互致敬的过程。李白与杜甫采取的路径全然不同,但是他们都各自完成了对前人的超越,至少后来者与先临者打成了平手。无论是黄鹤楼、凤凰台,还是道林寺,都经由他们之手完成了自足的文学构造,诗人也因此参与到了对江山、自然、社稷的反复重建过程中,并由此获得了不死不朽的豁免权。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在这首《夜宿山寺》里向世人传递出了一种普遍的情感体验,即,对高处的渴望同样伴随着对高处的惊惶。这样的体验,已不似当年王之涣在《登鹳雀楼》里所产生的那种欣喜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如果说,王之涣是怀着更大的期待登临鹳雀楼的,那么,李白则是在体验到了身在最高处的惶恐感后,提醒我们,高处虽美,但不可造次。如今,我们已经很难查证李白这首诗里的“山寺”究竟在哪里了,有人说它在湖北黄梅,有人说在诗人老家绵阳,但无论它在哪里,都不妨碍我们对这种情感的真实体验。“摘星辰”的美妙与“惊天人”的惶恐,相互交织,这种心理上的悖论,其实与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所生发出来的感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差别仅仅在于,李白的情感是纵向的,一飞冲天的,而陈子昂是横向的,亘古亘今的。它们共同编织出了一张纵横交错的情感时空大网,时刻捕捉着从我们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情感信息。而正是这种信息电波的强弱,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寻找的艰难,以及相互慰藉之必要,即所谓: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公元675年,时为洪州牧的阎伯屿,在新近落成的滕王阁上宴请同僚,也想借此机会向众人推荐其婿吴子章的文才。而此时,恰逢年轻的诗人王勃正打算前往交趾探望父亲,路过此地,听闻盛会,他“无路请缨”,用自己的惊世才华為中国古代的登高文学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唐书》本传里说,王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从这段关于诗人写作的情景描述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想出,王勃登上滕王阁时的盛况:在众目睽睽之中,这位天才诗人旁若无人地研墨、畅饮、酣睡,而后忽然一跃而起,奋笔疾书。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如游龙惊凤一般,落于纸上时,满堂喝彩震耳欲聋。“阁中帝子今安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这掌声是世人送给王勃的,更是王勃送给落霞、孤鹜、秋水和长天的,是所有登临高处的诗人对生命纵情的礼赞。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若干年后,苏轼在《水调歌头》里再一次发出了类似于李白的浩叹,“高处不胜寒”从来不是孤寒,但也只有像他们这样,真正登临过孤绝的人世之境的诗人,才能真正感受和体味到人生的薄凉与苍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