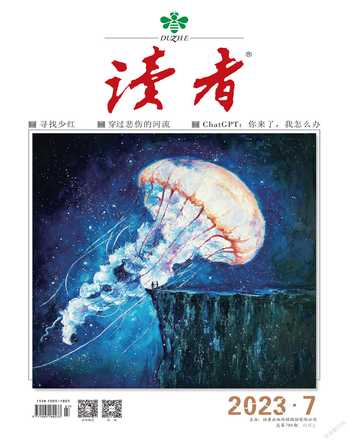烟火人间
张佳玮

“烟火气”这个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李安导演的影片《饮食男女》里,归亚蕾扮演的梁伯母,在美国女婿家住不惯,回家一口湖南腔跟人抱怨:“吃饭咧,除了洋葱就是汉堡,我炒个蛋炒饭,他的报警器都会响咧!我在那里真是生不如死!”的确,吃惯汉堡、家里又有烟雾报警器的人,很难理解蛋炒饭的流程与意义。厨灶间烟火飞舞,哪怕一碗蛋炒饭,都让人感到生机蓬勃。
十二年前,上海遵义路天山路那一带,夜间会停一辆大三轮车,放下炉灶、煤气罐、锅铲和各类小菜。推车的大叔把火一生,大妈把车上的折叠桌椅拆开放好。
你去吃,叫一瓶啤酒。问大叔:“有什么?”大叔年纪已长,头发黑里带白,如墨里藏针,但钢筋铁骨,中气充沛,就在锅铲飞动声里,吼一声:“宫保鸡丁!蛋炒饭!炒河粉!韭黄鸡蛋!椒盐排条!”
“那来个宫保鸡丁!”
“好!”
他家菜的种类不算多样。如果有人提过分要求,比如:“老板,韭黄炒鸡丁!”老板就皱起眉来,粗声大嗓地说:“那样炒没法吃!”
但这几样菜,千锤百炼,油重分量足,炒得又地道,能吃辣的,喊一声“老板加辣椒”,老板就撒一把辣子下去,炒得轰轰烈烈。冬天,坐得离大叔近些,边吃边看他巨锅大勺地炒,人都能吃出汗。有鼻塞的能吃到吸溜鼻涕,在阵阵烟火与辣椒味中,边打喷嚏边抹鼻涕:“这辣!”
这便是烟火气,扑面而来让人看不清楚,但又感到无比快乐。
比如,冬天早起,摸黑去早点摊、包子铺,笼屉高高叠起,大家排队递钱。“两个素包子。”“一个素包子,一个霉干菜肉包子,一个肉包子。”“豆浆有没有不甜的?”
卖包子的开笼屉盖,呼一下白气扑面,对面不见人。老板摸到烫手的包子,滑进小塑料袋里,扎好,给食客递过去;买包子的捧着烫包子,左手交右手,右手交左手,“谢谢啦!”有的食客,比如我,一面往回走,一面又忍不住地用手掏一个包子出来,还冒热气呢,咬一口去了一小半。
往身旁瞥一眼:生煎正在起锅,哗啦一片白气撞人,排队的、卖生煎的都迷了。只听卖生煎的问:“你要几个?”买的人比画着手指报数——那片嘈杂混乱,看不清听不清净划拉的感觉,就是烟火气。
又比如叫花鸡上桌,撬开荷叶泥封,哗啦一缕白气冒出。这时趁热吃,就觉得丰厚润泽、锣鼓齐鸣、欢腾喜乐;搁凉了吃,油凝皮干,残垣断壁。
往回几年,重庆夏天,南滨路附近,还吃得到柴火鸡与火盆烧烤。
大夏天,围炉而坐,烟火喧腾。鸡是烤熟了,人也被烟熏火燎,汗如雨下。大家都开玩笑:也不晓得烤的是鸡还是人!苏轼有所谓“燎毛燔肉不暇割,饮啖直欲追羲娲”,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那时对烧烤不太懂,只听同吃的人啧啧感叹“好柴,熏得香”,还不知所以。后来去了贵州的几个小城,吃了夜市烧烤,明白了:好炭与不好的炭、好柴与不好的柴,烤出的味道完全是两回事。
真让人投身其间、恨不得将头埋进去的,大概是东北的开江鱼。
听人说过,吃开江鱼讲个兴高采烈、热热闹闹。敲冰捞鱼,炖一大锅,咕嘟咕嘟。吆喝着,开心着。我自己去吉林时,真见到了,氛围惊人:大块肥鱼、五花肉片、老豆腐、粉条在锅里慢熬着,吃着吃着,热得指尖脸庞都慢慢融化了,连酸带疼到舒服,出汗。到要吃粉条时,已经进入鲁智深所谓“吃得口滑,哪里肯住”的阶段。
我跟一个陕西朋友聊,他说他们老家,吃臊子面,讲究碗得大过脑袋;冬天,臊子、酸汤,一大碗,捧着、扶着,老人家摘了眼镜叠好,脸凑着碗口吃,吃到脑袋几乎要钻进碗里。
大概吃东西有两种状态:一是冷静的、克制的、细致的、条理分明的,二则是狂热的、囫囵的、按捺不住的、热情澎湃的、一头埋进烟火气里的。
前者回想起来清晰明白,我还见过探店的美食家边吃边给餐酒搭配打分做记录的。后者则剩下一片单纯的快乐,一份忘我又安泰的、想起来可以原谅一切小瑕疵的快乐。
(明 赫摘自《新华日报》2023年1月11日,陈岱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