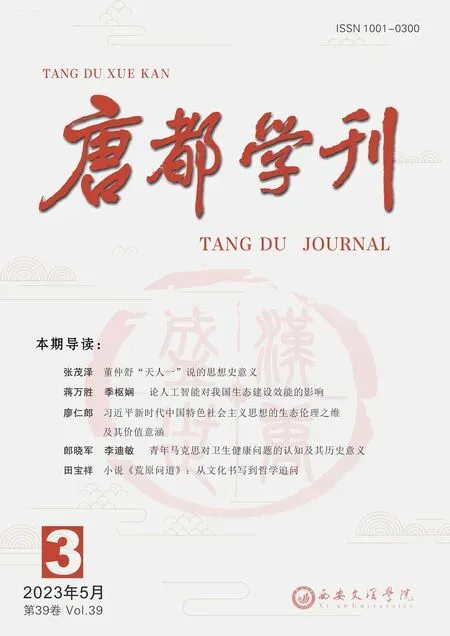中古嘉礼研究之一
——礼书所见嘉礼内容的变迁与意义
吴凌杰,叶 锋
(1.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2.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研究所,浙江 温州 325002)
中古时期是礼制发展的重要阶段,自西晋诞生的五礼制度为礼制分类奠定了基础,这已成学界共识。而后各朝礼典修撰连绵不绝,受到了广泛关注。张文昌先生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礼典的形成与礼官职能的演变,指出随着专业的礼官制度形成,促成了这一时期礼典的兴盛;梁满仓先生详细考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及其内容;汤勤福先生采取长时段的视角,梳理了秦晋之间五礼制度的诞生及与政治的关系(1)参见张文昌《中国礼典传统形成与礼官职能演变之关系——以魏晋南北朝为探索中心》,载于《兴大人文学报》,2008年第40期;汤勤福《秦晋之间:五礼制度的诞生研究》,载于《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以上诸位先生的探讨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已有研究似乎多将五礼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对五礼制度的内在变动分析稍显不足。五礼是什么?五礼的次序是否经历过变动?由此引发的深入思考是五礼在漫长的中古时期,它所涵盖的内容是否有过异化与整合?我们相信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无疑会加深学界对五礼本身的理解,故本文以五礼之一的“嘉礼”为切入点,梳理中古礼书所记载“嘉礼”的内容,从文本演变着手揭示其中意涵,论述不当之处,祈望方家斧正。(2)相关研究可参见拙作《中古五礼次序的变迁与礼学思想的转型》,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23年第1期。
行文之始,特需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的“礼书”一词,并非狭义的专指私人修撰的礼书,而是涵盖了当时的礼典与正史《礼仪志》,理由有三:一是无论是《汉书·艺文志》还是《隋书·经籍志》,礼典、私修礼书、正史都属于同一门类,在前者同属于“六艺略”[1]1709,在后者同属于“史部”[2]1086-1100,这至少反映出在汉唐之际正史修撰者看来,它们具有某些相同的特质;二是它们的修撰者不仅拥有着相同的知识谱系与思想世界,而且很多情况下就是同一批人,如魏收、长孙无忌、许敬宗等人,既领修正史,又参与礼典的修撰;三是它们的文本经常互通,修撰者们据此修彼的情况较为普遍,如沈约修撰《宋书·礼志》时采据《晋礼》、令狐德棻等人修撰《隋书·礼仪志》时也多采据北齐礼典等。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因它们的体裁不同,就认为它们是毫无关联、独立的文本体系。
一、中古礼书所见嘉礼内容
《周礼·大宗伯》将嘉礼分为“饮食、婚冠、宾射、飨燕、脤膰、贺庆”六项,“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迎来了新的演变:“饮食”从天子招待宗亲之宴,随着秦汉以后分封制的瓦解而日益湮没;“飨燕”从天子招待臣属之宴,逐渐与元会大典交织成为后者附庸性程序;“宾射”从主客欢愉的嘉礼转为严肃整齐的军礼,自身娱乐性不断消失;“脤膰”从皇帝赐宗庙祭肉与群臣,融入吉礼中作为祭祀的附庸仪式,其礼仪归属逐渐从嘉礼转为吉礼,故后世以“赐胙”代称之;“庆贺”的命运与“饮食”一样,原本为天子庆祝异姓国,随着分封制瓦解天下一统,逐渐作为仪式融入其他礼制当中成为附庸性程序;唯有“婚冠”作为成人与男女之礼一直存在,但后世对它的划分仍然有过变化(详见后文)。由此可知,随着时代的发展,嘉礼的含义与内容也发生着转变,那么中古礼书对于嘉礼的内容有如何变化呢?现以礼书的性质分别论述。
首先是正史《礼仪志》中的嘉礼内容。现今所见汉唐之际的正史虽有15部之多,但仅有八部修《志》(《史记》《汉书》《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隋书》《晋书》),而以五礼制度为体例的《礼仪志》只有《隋书》和《晋书》。
《隋书·志》又名《五代史志》,乃是太宗于贞观十五年(641)为弥补官修五史无志的缺憾,下诏于志宁、李延寿等人而作,共10志、30卷,其中嘉礼的内容集中在卷四到卷七,内容大体有:禅让、册皇太后(册皇后)、册皇太子、册诸王(三公、尚书令、公主、太妃等)、皇帝加元服、皇太子冠、皇帝纳皇后、皇太子纳妃、聘礼、讲学(释奠)、元会、正至日劳州郡国使、皇太子监国、皇帝受贺、皇太子受贺、读时令、策秀孝、宴宗室、养老、舆服之制等。然后是《晋书》,它是贞观二十年(646)太宗为排除诸家《晋书》,御赐定于一尊所作,它的体例并非承自前朝《晋书》,而是唐人的制作。于志宁等人在开头序文便说道:“五礼之别,其五曰嘉,宴飨冠婚之道于是乎备。”[3]662(嘉包括冠、婚、养老、乡饮、释奠、祓禊、射)从此可以看出,虽然《五代史志》与《晋书·礼志》的创作时间相去不远,但对嘉礼的定义具有较大的不同,《隋书》的内容远较《晋书》丰富,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冠婚养老等必备仪式,而且加入了禅让、册礼、元会、劳国使、皇太子监国、受贺、读时令、策秀等诸多内容。(3)有关汉唐正史《礼仪志》的具体分析,可参见拙作《走向五礼:汉唐之际正史“礼”类典志的变迁与意义》,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待刊)。
然后是《大唐开元礼》(以下简称《开元礼》)中的嘉礼内容。成书于开元二十年(732)的《开元礼》,传为玄宗制作的、用于象征盛世大唐的礼仪巨作,不仅著名于当时,也影响于后世,是中古时期官修礼书的集大成者,它对嘉礼内容的记载,不仅代表了当时礼官的思想,也体现出唐代官方对礼制认识的权威。它对唐代嘉礼内容的记载如下:
皇帝加元服,纳后,皇帝元正冬至受皇太子朝贺,皇后元正冬至受皇太子朝贺,皇帝元正冬至受皇太子妃朝贺,皇后元正冬至受皇太子妃朝贺,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皇帝千秋节御楼受群臣朝贺,皇后正至受群臣朝贺,皇后正至受外命妇朝贺,皇帝于明堂读孟春令,皇帝于明堂读仲春令,皇帝于明堂读季春令,皇帝于明堂读孟夏令,皇帝于明堂读仲夏令,皇帝于明堂读季夏令,皇帝于明堂读孟秋令,皇帝于明堂读仲秋令,皇帝于明堂读季秋令,皇帝于明堂读孟冬令,皇帝于明堂读仲冬令,皇帝于明堂读季冬令,皇帝于明堂及太极殿读五时令,皇帝养老于太学,临轩册命皇后,临轩册命皇太子,内册皇太子,临轩册命诸王大臣,朝堂册命诸臣,册内命妇二品以上,遣使册受官爵,朔日受朝,朝集使朝见,皇太子加元服,皇太子纳妃,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群臣贺,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宫臣朝贺,皇太子与师傅保相见,皇太子受朝集使参辞,亲王冠,亲王纳妃,公主降嫁,三品以上嫡子冠,三品以上庶子冠,四品五品嫡子冠,四品五品庶子冠,六品以下嫡子冠,六品以下庶子冠,三品以上婚,四品五品婚,六品以下婚,朝集使于尚书省礼见,任官初上相见,京兆河南牧初上,万年长安令初上,乡饮酒,正齿位,宣赦书,群臣诣阙上表,群臣奉参起居,皇帝遣使诣蕃宣劳,皇帝遣使宣抚诸州,皇帝遣使诣诸州宣诏书劳会,皇帝遣使诣诸州宣赦书,诸州上表。[4]27-39
我们可将上述记载归为“冠、婚、册封、读令、朝贺、朝集使、宣赦诸州、敬师养老、上任起事、上表起居”十类,这也代表了官方对嘉礼划分的基本看法。
最后是《通典·礼典》中的嘉礼内容。成书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的《通典》,实则是一部贯通古今的政书,并非专门记载礼仪制度,但全书煌煌200卷,其中就有100卷专涉礼制,每当国家面对礼仪活动时,也往往将它拿出作为必备的参考书,故不容忽视(4)参见葛兆光《杜佑与中唐史学》,载于《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通典·礼典》之价值,在于体现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的唐廷,对于礼制认识有何种转变,以嘉礼为例,大体有冠、笄、婚、养老、乡饮、册封、追封、读时令、元会朝贺、上表朝见、舆服首饰、宗族亲属、尊父敬师、收养子嗣、监国任官等内容。可知,相比于其他礼书而言,《通典·礼典》嘉礼内容最为繁复,也最为不同。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对中古礼书所见嘉礼内容的梳理,我们便可明显发现三个特点:一是不同性质礼书对于嘉礼的定义不尽相同;二是相同性质礼书对嘉礼的定义也有所不同;三是相同性质、且修撰年代较近的礼书,对嘉礼的定义亦各不同。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区别?我们将于下节展开论述。为清晰表现出礼书所见嘉礼内容的区别,现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如下。

表1 中古礼书所见嘉礼内容
二、中古礼书所见嘉礼内容演变的原因
从上节我们对中古礼书所见嘉礼内容的梳理可知,唐人对嘉礼的认知有相对固定的部分,如“冠、婚嫁、养老、乡饮”等,这些内容基本延续着《周礼》的安排,但亦有认知不同的部分,如“读时令、册封、元会朝贺”等,这些内容超出了《周礼》的记载,于是不同礼书对这些内容的接受有所不同,这便值得我们探讨,现以《开元礼》记载的嘉礼为定本,对其他礼书所载的不同与原因论述如下:
一是《通典·礼典》。从上可知,杜佑在承袭《开元礼》所述的嘉礼之外,还将收养子嗣等内容纳入嘉礼,此种行为当与《通典》的成书性质有关。据《旧唐书·杜佑传》云“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5]3982可知《通典·礼典》的内容,是杜佑编撰自“开元礼、乐”,而非承袭于刘秩的《政典》。据此,冯茜先生曾指出杜佑认为三礼都是对过往制度的真实记载,在他的笔下,汉代以后“两分”的礼经学与礼制学都融汇在一起。后世划分的“吉凶军宾嘉”五礼,在他眼中成为三代的实际存在,因此他按照五礼为行文纲要,从三代写起,不考虑三礼内部的文本背景与特殊意义,反而打碎重组,并与后来的仪注学一起构成了书的内容主体(5)参见冯茜《唐宋之际礼学思想的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4-88页。。
笔者大体认同冯茜先生的看法,《礼典》的内容分为两种:一类是单独礼目,如“天子加元服,皇太子冠”等,杜佑从历代经典中采择下来,将其作为礼经从三代开始追溯,并以朝代为序分门别类的排布;二是带“议”的礼目,如“大功小功末冠议”等,与前者不同的是,它们多来自于史书的礼论与文集,属于后世对礼仪问题的争议,对于它们,杜佑亦以朝代为序进行排列。但与冯茜先生的看法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杜佑并非将礼经学与礼制学融汇不分,而是有着自在的逻辑,现检索《礼典》可知,一般单独的礼目,它们作为礼经,是整部《礼典》的主体内容,从始至终贯穿着全书,而带“议”的礼目作为礼制与仪注则是对前者的补充,它们是对礼经的特殊问题的解释,杜佑修撰后者为的是让后人更好地理解前者。
让我们的视野重新回到嘉礼,现今可见《通典》之嘉礼,不见于《开元礼》者,大体有“天子诸侯大夫士养子仪(君薨后嗣子生附),天子诸侯大夫士之子事亲仪(妇事舅姑附),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诸侯崇所生母议,支庶立为天子追尊本生议”等内容,这些带“议”的礼目与“册封”与“养老”条互动,是后者的补充。也就是说,在杜佑看来,天子除了要立皇太子外,亦需立其他子嗣为王,诸侯大夫与其同理,于是天子诸侯大夫生前收养、册封子嗣,收养的子嗣为他们养老送终,这些内容整体化成为杜佑对“养老”等礼经的解释,这集中表现了杜佑对中古时期嘉礼实用化、现实化的改造。
换言之,官方修撰的《开元礼》等礼典所规定的乃是“一般性”礼经原则,而修撰者萧嵩等人,也不太考虑礼仪与现实如何融洽的问题,但杜佑却不同,多年的行政经验,促使他在修撰《通典·礼典》时具有“沿革性”与“实用性”的精神,这一点也为往日学者所揭示(6)参见葛兆光《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状况》,载于《唐研究》,1999年第1-34页;张轲风《〈通典〉与〈政典〉渊源考辨》,载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有关杜佑的礼学思想,日本学者岛一曾做过专题研究,参见岛一《唐代思想史论集》,中国艺文研究会,京都,2013年。此文得益于西北大学王璐博士的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因此在修撰《礼典》嘉礼部分时,杜佑不仅概述嘉礼的一般性原则,而且往往通过以“某某议”的形式,将围绕在嘉礼背后的诸多礼制与仪注性问题进行集中论述,这样就使得整个《礼典》的嘉礼部分内容庞杂到远超《开元礼》之记载。这种将礼经与现实结合的修撰手法,也恰好成为《礼典》权威性之所在,从史书的诸多记载可知,每当朝廷遇见礼文与现实抵牾之处时,《礼典》成为他们辩驳与行用的基础。
二是《隋志》与《晋志》。如前所述,《隋志》《晋志》二者修撰时间相去不远,修撰者的组成亦高度重合,故在此合并论述。从上述表格可见,《隋志》将“禅让、释奠”归于嘉礼,将“诸王朝见”归于吉礼;而《晋志》将“释奠、读时令”归于吉礼,将“册封诸王、追封太后、元会朝贺、藩王朝见”归于宾礼(7)朱溢先生指出:“随着五礼制度的逐渐成熟,这些在性质上与宾礼不同的礼仪逐渐被剥离,不再出现于宾礼中。”参见朱溢《中古中国宾礼的构造及其演进》,载于《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对此史书并未给出相应的解释,但杨英先生在论述《宋书·礼》与《晋礼》之关系时指出:“承《新礼》(《晋礼》)而来的《宋书·礼》在体例上属于早期五礼体例……《宋书·礼》将冠礼、昏礼、元会朝觐、巡守归入吉礼,唐人编的《晋书·礼》则将巡守、朝觐归入宾礼,冠礼归入嘉礼,反映了晋唐对五礼认识毕竟不一样。”(8)参见杨英《中古礼典、律典分流与西晋〈新礼〉的撰作》,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8期。
诚如杨英先生所言,在魏晋“五礼”诞生以前,当时的史书多以“礼事”记载礼制,故《史记》《后汉书》中的“礼制”基本上以具体的“礼事”(如封禅、释奠等)存在,但西晋以后五礼初建,人们开始根据自己对“礼事”的认识将不同的礼制归入五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对五礼次序认识不一,而且对具体礼制归属于何种五礼亦有不同看法。这便有了杨英先生列举的《宋志》将“冠礼、昏礼、元会朝觐、巡守归入吉礼”的现象。梁满仓先生亦举出魏晋时期婚礼归入吉嘉二礼未定之案例:
除了魏晋隋唐的事例外,实际上倘若我们稍将目光延至宋代,便可发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亦与《开元礼》在五礼内容上表现出极大的不同,如它将册命诸王移入军礼、在冠礼上取消皇帝与亲王冠、将朝贺归为宾礼、删除乡饮礼等(10)参见张志云《宋代嘉礼内容演变探析》,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由此可知,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礼制的归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当然我们对杨英、梁满仓等先生的观点亦有存疑,尤其是《隋志》与《晋志》修撰年代相去不远,二者的修撰者实则多有重复(如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等人),很难相信在如此相近的年代、且修撰者大体相同的情况下,《隋志》《晋志》会在嘉礼部分产生如此明显的不同。
囿于现存史料的缺乏,对于这个问题想必很难找到答案,不过,我们推测这或许与史书修撰时面临的现状息息相关,《隋志》(《五代史志》)的出现晚于五代史,且前后修撰时间持续了15年之久,当时的修撰者在面对广博的魏晋南北朝文献时,可以从容不迫地加以采择;《晋书》却不同,在经历了废太子之争的太宗,意图借助修撰《晋书》推行教化,加之前朝18家私修《晋书》的存世,因此官修《晋书》的编纂者只需要在前代的基础上,稍作调整便可告成,这也是《晋书》修成之速的原因。两书在修撰时面临的实际情况不同,故在《礼志》上,虽然二者都采取了五礼书写体例,但是对嘉礼的记载也不同。这反映到《晋志》《隋志》上便是大量内容无法与《开元礼》《礼典》相贴合。
总之,通过对中古史书所载嘉礼内容的梳理,可发现不同文献对于嘉礼记载有所不同,对此,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与史书的编撰体例与思想有关,如杜佑在编撰《通典·礼典》时就秉持“沿革性”“实用性”的思想,全书以具体礼目为纲,掺杂了大量现实性、议论性礼文,这使得它不仅内容庞杂,且远超《开元礼》之记载,但这种编修方式也恰好成为《礼典》权威性之所在,由于其他礼典并不考虑礼仪现实行用问题,故每当朝廷遇见礼文与现实抵牾时,常引据《通典》为论述基础(11)参见张轲风《〈通典〉与〈政典〉渊源考辨》,载于《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也与五礼制度本身有关。现今我们所谓的“三礼”,乃是经由郑玄、王肃等人的阐述,演变为经学的概念,但“五礼”则不同,它是史学的概念,仅代表着礼制划分的方式,自然可以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而除“五礼”外,当时还有“四礼”“九礼”等不同的礼制划分,那么人们根据自己对礼事的认识,将同一礼事归入不同的五礼亦不足为奇。
三、中古嘉礼渊源——以《开元礼》为中心
有关中古礼制之渊源,陈寅恪先生有过精彩的论断:“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故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既后世用之不能大过,是唐礼不亡即隋礼尤存,其所从出之三源者,亦俱托唐礼而长存也。”现今学者们在陈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亦对中古礼制渊源展开了精彩的分析,其中以吴丽娱先生的成果最为丰富,她从《唐会要·五礼篇目》引《贞观礼》所增29条出发,对魏晋隋唐礼制沿革展开详细论述,涉及嘉礼的内容为“读令、养老、乡饮、纳后”,她指出:“从纳后、皇太子入学等礼制可以看出唐代礼典对南朝制度的吸收,从读令、养老、乡饮则可看到唐代礼典中对古礼的遗存与贵族社会的保留。”(12)参见吴丽娱《关于〈贞观礼〉的一些问题——以所增“二十九条”为中心》,载于《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在此我们举《开元礼·嘉礼》两例以和之:
一是“皇帝加元服”。“元服”即“首服”,常作为冠礼的替代词,现今史料所见有关皇帝冠礼记载较多,但以“加元服”为名之例则始见于西汉昭帝“(元凤)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见于高庙。赐诸侯王、丞相……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勿收。”[1]229虽然昭帝加元服的细节不详,但可知此名号当为《开元礼》“皇帝加元服”之滥觞。而后东汉“和、顺、桓、献”四帝加元服时,皆“改年号、赐群臣百姓”;曹魏承汉制,齐王曹芳于正始四年加元服时“赐群臣各有差”[6]120;西晋无皇帝加元服之记载,衣冠南渡而来的东晋,早期典章之制缺乏,《晋书·华恒传》云:“及(成)帝加元服,又将纳后。寇难之后,典籍靡遗,婚冠之礼,无所依据。恒推寻旧典,撰定礼仪,并郊庙辟雍朝廷轨则,事并施用。”[3]1263由此可见,成帝加元服时“大赦,改元,大酺五日,赐鳏寡孤独增米文武位一等,人二斛,京师百里内复一年。”[3]196-170即延承汉制而来。总体观之,汉魏南朝加元服较为简略与灵活,它不仅简化了加元服的若干步骤,而且插入了古礼未有的“改元”等环节,这表明南朝礼制对古礼的扬弃。但北朝则更为繁复呆板,据《隋书·礼仪志》云:
后齐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圆丘方泽,以币告庙,择日临轩。中严,群官位定,皇帝着空顶介帻以出。太尉盥讫,升,脱空顶帻,以黑介帻奉加讫,太尉进太保之右,北面读祝讫,太保加冕,侍中系玄纮,脱绛纱袍,加衮服。事毕,太保上寿,群官三称万岁。皇帝入温室,移御坐,会而不上寿。后日,文武群官朝服,上礼酒十二钟米,十二囊,牛十二头。又择日,亲拜圆丘方泽,谒庙。[2]176
可知与魏晋南朝相比,北齐皇帝加元服除告庙、赐群臣外,还引入了古礼的“告圆丘方泽、三加、变服、上礼”之制,删去了汉魏南朝新增的“改元”等仪式,总而观之,北朝之礼不仅繁杂而且更趋复古之势,使得整个仪式显得呆板又刻意。从现今《开元礼·皇帝加元服》的记载看,它的仪式步骤不仅完全贴合北齐之制,甚至在礼目顺序上也完全一致,或可完全将前者视为后者的扩写本,那么二者关系当极为密切。
二是临轩册命诸王大臣。临轩是唐代册命仪式中的最高级别,皇帝前往正殿(一般为太极殿)举行仪式。所谓“诸王大臣”则是“诸王”与“大臣”两类不同的群体,唐代“诸王”皆无封地,仅有虚号,在唐人眼中可等同视之。汉代则不然,我们需分开论述。首先是“临轩册命诸王”,相关记载可追溯到西汉高祖立诸子为王,李俊芳先生曾对两汉以来诸朝册命亲王进行过仔细探讨,他指出汉代册命诸王大臣步骤由授予茅土、读册、授玺印等步骤组成,其意义在于训诫诸王大臣对中央保持臣服,继而以盟约的形式要求被册立者效忠于中央(13)参见李俊芳《汉代册命诸侯王礼仪研究》,载于《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再者是“临轩册命大臣”,据《汉书》等史书记载可见,当时朝廷将“大臣”的范围限定在三公,并非如唐代的“诸王及职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一品,并临轩册授”[7]359。由此观之,汉唐虽共有此仪式,但二者无论是仪式步骤还是礼制精神都完全不同。
随着分封制的瓦解,诸王成为虚衔,于是册命诸王与册命大臣在礼文上走向一致,并随着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开始逐渐与官品门阀相联系。据《南齐书·王俭传》云:“(晋)中朝以来,三公王侯,则优策并设,官品第二,策而不优。优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书职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书令品虽第三,拜必有策。录尚书品秩不见,而总任弥重,前代多与本官同拜,故不别有策。”[8]429由此可知,此时的临轩册命之制与官品爵位联动,三公与王侯并为臣子,以其品阶为册命依据。与《开元礼》重亲属之精神相去甚远。正因为自晋朝以来册命诸王与品爵等职官制度挂钩,册命的诸王与大臣再次进京朝贺时,皇帝以宾客之礼相待,所以《晋志》才会将其册命诸王归入宾礼而非嘉礼。北朝则与之不同,从《隋志》可见,北齐册命对象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到诸王、三公、公主等井然有序,体现出偏重血缘亲属的精神。现检视《开元礼》“临轩册命诸王大臣”条,后者不仅在书写体例上与其保持一致,而且相关条目亦是相同,由此我们认为南朝册命制度深受官品门阀的影响,而北朝的册命制度则受宗室亲属影响较深,继而延续至《开元礼》。
当然南朝因子对于唐代嘉礼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在隋开皇初年,太常卿牛弘云:
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诏曰:“可”。[2]156
在牛弘看来,南朝礼制“多违古法”,且与北朝礼制“风牛本隔,殊不寻究”,北周北齐由于“宾嘉之礼,尽未详定”而效仿南朝,在他眼中是“童牛角马”“不伦不类”的行为。由此透露出的信息,表明至少在“嘉礼”方面,由于北朝相关礼仪残缺,故在实行时多采择南朝嘉礼仪式。以“皇帝婚礼”为例,吴丽娱先生就从《开元礼·纳后》的“皇帝嘉命,访婚陋族……某官封臣姓名稽首顿首,再拜承制诏”“凡六礼,皆以版长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答版亦如之”等记载出发,指出所谓“六礼版文”乃是采择自东晋南朝之礼仪,此礼由南朝传自隋进入唐代。(14)参见吴丽娱《关于〈贞观礼〉的一些问题——以所增“二十九条”为中心》,载于《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当然,我们认为南朝的影响随着隋代的建立而逐渐衰弱,从牛弘等人对南朝礼制的猛烈批评来看,我们不难想到之后由他主持修撰的《开皇礼》会采北朝而舍南朝,而《贞观礼》接续《开皇礼》自然也会“重北抑南”,使得整个北朝礼制占据主流,这一点往日也为吴丽娱先生所论证。(15)参见吴丽娱《对〈贞观礼〉渊源问题的再分析——以贞观凶礼和〈国恤〉为中心》,载于《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由此可见,南北因子对于中古嘉礼都有影响,不过根据以上种种表现,笔者认为北朝因子重于南朝。
总之,中古嘉礼来源较为复杂。通过对相关内容的考察,大体符合陈寅恪先生所言“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认为唐人制礼虽常自称“师法汉代”,但实际上汉代的礼制对其影响“名大于实”,故中古嘉礼多承袭自北朝,当然吴丽娱先生的研究提醒我们古礼与南朝贵族文化对唐人的影响亦不可忽视,由此可见层层叠累之下的中古嘉礼成为多种文化杂糅的产物,并且似乎北朝因子大于南朝,但并非定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四、结语
通过我们对中古时期礼书所见嘉礼内容的梳理与研究,大体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一是中古各类礼书对嘉礼的记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我们认为这与书籍本身的编撰思想与方式有关,不同史书在记载嘉礼时,作者具有不同的考量,如《通典》在编撰时,杜佑更加考虑现实的行用性,而萧嵩等人在编撰《开元礼》则更偏向“垂范后世”的“经典性”,这使得他们对于嘉礼的定义不尽相同。
二是五礼制度仅作为礼制的一种划分原则,本身就具有时代赓续性,中古五礼制度处于草创时期,人们对何种礼制当归入何种五礼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历代修撰者在根据自己对五礼认识的基础上又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这便成为礼书所见嘉礼内容不同的根本原因。
三是通过对《开元礼》所载嘉礼的内容分析,我们认为唐代嘉礼多源自北朝,并夹杂对古礼的模仿,呈现出“虽师汉代,实承北朝、远肇周礼”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