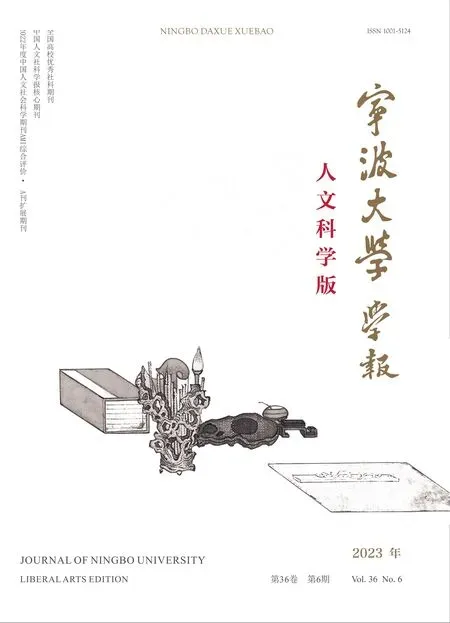契嵩“心”本体的建立与诠释
刘 祎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契嵩是佛教史上倡导儒佛一贯的代表人物。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在理论内涵、思维方式、思想旨归等方面和儒家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两种不同的文化如何实现会通、融合,始终吸引着我国古代思想家的重视和关注。契嵩认为,“心”是本源,是儒释道三教所立的根本:“心也者,谓佛与众生本觉之灵源也,具一切诸法,备一切功德,即为三教圣人所立道与义之根本也。”[1]34儒释二家可以在“心”的问题上找到共通之处。契嵩出入于儒释之间,汲取其思想精华,以本体之“心”作为融合儒释二家的理论基础,从内部打通了儒学与佛教的理论隔阂,从外部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互融互鉴。
一、形而上的本体之“心”
“心”在契嵩的理论体系中居于本体地位。在《广原教》中,契嵩对“心”的本体属性做了归纳:“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凡一切众生,皆从此一心之所出也。”[2]61本体之心就是真如:“心必至,至必变。变者,识也;至者,如也。如者,妙万物者也;识者,纷万物异万物者也。变也者,动之几也;至也者,妙之本也。天下无不本,天下无不动。”[2]26变是心动的开始,至是万物之妙的根本。在这里,“至”相当于“极”,意为最高本体,这一本体就是“如”,而“如”在佛教中又作如如、真如,即一切万物真实不变之本性。
“心”在佛教教义中有多种分类,如华严五祖宗密所言四种心,分别是肉团心、缘虑心、集起心、真心[3]401下。受宗密的影响,契嵩也将“心”分为肉团心、缘虑心、集起心、坚实心四种,其《坛经赞》云:“曰肉团心者,曰缘虑心者,曰集起心者,曰坚实心者,若心所之,心益多也,是所谓名同而实异者也。”[2]60钱穆先生就曾评价契嵩“兼治华严,大有宗密之风”[4]42。第四种坚实心即“真心”是契嵩最根本、最重要的范畴,此“心”并非生理之心,亦非认识之心,而是形而上的本体之心。
“心”之所以能作为万物之本源、众生之本体,首先是因其先在的、不可分的且高度抽象的外部情状,具体来说是横竖周遍、绝言离相、非空非有、不可思议。
第一,横竖周遍。契嵩称“心”即是“佛祖所传之妙心”,并称赞其“大哉心乎”。契嵩将“大”解释为“谓其体无边际、绝诸份量、竖通三世、横该十方,故云大哉心乎”[1]138。“竖”指纵向的时间,“横”指横向的空间,这是从时间和空间的两个维度来分析心的特点。在时间维度上,心“竖通三世”,存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时间;在空间维度上,心“横该十方”,“十方”为四方、四维、上下之总称,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因此,作为本体的“心”超越有限的存在,横竖周遍,无有穷极,无所不至,无处不在。
第二,绝言离相。从性相的角度来看,本体之“心”绝言离相,超越了相对和绝对。《广原教》中言:“心乎大者至也矣。幽过乎鬼神,明过乎日月。博大包乎天地,精微贯乎邻虚。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绝大;微而不微,故至微。”[2]27世间万物皆是真心所出,真心作为诸法之本体、万物之本原,它至幽、至明、至高、至大、至微,幽冥超过鬼神,光明超过日月,广博宏大包含天地,精粹微细贯通微尘。“心”如此玄妙之极,所以契嵩称它“是可以言语状及乎,不可以绝待玄解谕”,即“心”之奥妙,体离言象,言诠所不及。
第三,非空非有。“心”非空非有,超越了空和有而存在。《夹注辅教编·广原教》言:“此之心法,相似乎有,相似乎无,相似乎非有非无,相似乎非非有,相似乎非非无。”[1]62意心既似有,又似无,既似非有非无,又似非非有、似非非无。此处有、无、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互立互破,以中道般若观破万法而显真空之理,论万法之缘起而显妙有之义。
第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即不可思虑言说之境界,主要用以形容诸佛菩萨觉悟之境地,以及智慧、神通力之奥妙,契嵩则用“不可思议”来形容真心。《坛经赞》有云:“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灵,若寂若惺……此谓可思议也,及其不可思也,不可议也,天下谓之玄解,谓之神会,谓之绝待,谓之默体,谓之冥通。”[2]61“心”似明似暗,空虚又灵知,寂静又智慧。真心的神奇深妙,不可以思之,不可以言议之。
在描述了“心”外部情状的基础上,契嵩进一步强调了其灵觉、寂净、圆融的内在特征,凸显了形上之心的超越性。
契嵩把真实心称作是“灵觉”,《夹注辅教编·广原教》云:“此真实心,即一切众生清净本觉,亦名佛性,亦云灵觉,亦是一真法界。”[1]53此外,契嵩还把“心”看作是“佛与众生本觉之灵源”,不仅指出作为佛与众生的心之本源,更强调了本心具有灵觉的本质,认为灵是心的重要体现,万物都有的灵性叫作心,“万法同其觉灵,乃谓之心也”[1]61。
契嵩讲“灵觉”,重点在于“觉”。“灵”是相,是“心”的外在表现,“觉”是体,是本质。《夹注辅教编·坛经赞》云:“方《坛经》之所谓心者,亦义之觉义,心之实心者也。”[1]61“心”有本觉的性质,《坛经》所讲的“心”,正是此义。契嵩对“觉”的理解,无异于中国佛教宗派对“觉”的释义。吕澂先生曾指出,印度佛学主张心性本净,中国佛学则主张心性本觉[5]4。“本觉”是《大乘起信论》中的重要思想,与“始觉”相对,指本有之觉性,先天本有而不受烦恼污染等迷相所影响,其心体本性乃本来清净之觉体。契嵩《坛经赞》云:“夫妙心者,非修所成也,非证所明也,本成也,本明也。”[2]64所谓本成,即自然而成,生来就具有的;本明就是本觉,在佛教中因本觉之体清净而有大智慧光明,故称本明。本成和本明,强调了“心”无须通过修行,也不须外求,它是“心”本来就具有的内在特质。
契嵩讲“心”的觉性,是为了论证“心”的清净。他在《夹注辅教编·劝书》中言:“佛乃觉义也,今所谓释迦文佛是也。此佛预证得乎一切众生一心觉源清净之理。清净,即真正之种智也。”[1]34所谓种智,即佛之一切种智,离烦恼之垢染,即是一切种智。在《夹注辅教编·广原教》中,契嵩又云:“佛谓妙觉圣人,此妙觉圣人已正乎清净之一心源也。然此非筭数之一,谓如理虚融,平等不二,故称一也。”[1]76佛与人有着同一心源,这个“一”指的不是数字一,而是说佛与人之心都具有觉性且清净。契嵩常言“寂静”,寂静即寂灭、清净,且时常把这两个词等同起来使用,“夫清净谓其性之妙湛。寂谓至静,灭谓灭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顽寂死灭之谓也”[2]297。清净寂灭是指无漏无染,度脱生死,有情无累,而非死寂虚无。其《传法正宗记》也有云:“然心本清净,无生灭无造作,无报应无胜负,寂寂然灵灵然。”[6]730下 清净之心,不生不灭,如如不动,空灵常寂。契嵩认为修行清净寂灭之心可以成就佛道,他在《原教》中说:“夫妙道也者,清净寂灭之谓也,谓其灭尽众累,纯其清净本然者也,非谓死其生、取乎空荒灭绝之谓也,以此至之,则成乎圣神以超出其世。”[2]8所谓妙道,就是清净寂灭。世人如果能修此清净寂灭,那么所蕴藏的佛性就会成熟显现,进而成就佛道。
“心”若离念清净、纯真一如,便可广大圆融,契嵩称此曰“玄妙圆极”。其《夹注辅教编·广原教》言:“心即圆极之理,乃上乘之至也……‘至者,如也’者,谓此三种之至,都是真如圆极之一心也。”[1]60《夹注辅教编·孝论》曰:“天下凡所谓玄妙之事法者,无有玄妙过于一法界圆极之道理也。”[1]117一法界指唯一无二,绝对平等之真如理体,即华严宗所说之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圆融周遍,表示世界万有最终的圆融,也就是圆极。宗密把华严宗称为圆极,把真心称为“一真法界”之体,云:“华严是圆极一乘,亦以此心为一真法界之体。故彼疏说,统四法界为一真法界。谓寂寥虚旷,冲深包博。总该万有,即是一心。体绝有无,相非生灭。乃至云,诸佛证此妙觉圆明。”[7]676中 契嵩的“玄妙圆极之一心”正是来源于此。
契嵩继承了华严与禅宗思想,通过“心”这一概念的抽象化、超越化、普遍化,建构起“心”的形而上基础。
二、以“性情”为前理解
在契嵩的理论体系中,高度抽象的本体之“心”是以“性”与“情”作为认识的中介即前理解而展开。
关于“心”与“性”、“情”三者关系,契嵩受《大乘起信论》中“一心开二门”思维图式的启发,提出“心统性情”的命题,他在《夹注辅教编·广原教》中直接提出:“性能生也,情所生也,即‘心真如’而变为‘心生灭’也。”[1]63契嵩认为“性”与“情”来自“心”的两个方面,即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性”能生发,是“心真如”,“情”是被产生的,即“心生灭”。在“心统性情”的基础之上,契嵩对“性”与“情”做了诸多规定。
“性”的特性和“心”基本相同,契嵩对二者的区分并不严格。“性”是真实无妄、真如不变的。《逍遥篇》云:“其分定而其性不可移。”[2]142性者,不改之义也,通因果而不改自体是云性[8]1164。《夹注辅教编·广原教》云:“夫性之德者,乃为真而无妄,为如而无变,为圆极无有不偏,为真正而无邪,为清净而无染,为寂静而无生无灭。”[1]64性是清净寂灭、无漏无染的,他说:“夫清净谓其性之妙湛,寂谓至静,灭谓灭其情感之累,非取其顽寂死灭之谓也。”[2]297“性”同真心一样也具有灵的特性,故其《中庸解》第三云:“天命则天地之数也,性则性灵也。盖谓人以天地之数而生,合之则性灵者也。”[2]75
与“性”的真实性不同,契嵩认为,情的本质为伪、为识,“夫情也,为伪,为识。得之则为爱、为惠,为亲亲、为疏疏、为或善、为或恶;失之则为欺、为狡、为凶、为不逊、为贪、为溺嗜欲、为丧心、为灭性。夫性也,为真、为如、为至、为无邪、为清、为静”[2]28。总的来说,“情”可以抽象概括所有具体情感的表现形式,得之则为爱好、为恩惠、为亲其亲、为疏其疏、为或善、为或恶,失之则为欺诳、为奸狡、为凶暴、为不顺从争议、为贪婪、为沉迷爱欲、为丧失其真实心、为灭没其正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情”可以看作是佛教对世俗世界特征的总结。
关于“性”与“情”是如何发生的,契嵩认为性是生来就具有的,“情”是“性”的显发。《中庸解第三》云:“性乃素有之理也,情感而有之也。圣人以人之性皆有乎恩爱、感激、知别、思虑、徇从之情也,故以其教因而充之。恩爱可以成人也,感激可以成义也,知别可以成礼也,思虑可以成智也,徇从可以成信也。孰有因感而得其性耶?夫物之未形也,则性之与生俱无有也,孰为能感乎?人之既生也,何待感神物而有其性乎?彼金木水火土,其为物也无知,孰能谆谆而命其然乎?”[2]75“性”是人生而具有的,是由天命赋予的一种本来属性;“情”是人与外界接触,有感于外物而生起的精神反映。契嵩还强调,金木水火土与其他物一样,都是自然之物,且是无知的,无法把“五常”之性赋予人,进而否定了郑玄“感神物而有性”的主张。
作为一对能够反映“心”属性的相对概念,契嵩认为,“性”与“情”又具有如下分别:
其一,性静情动。“性”是无生无灭、真如不变的,概括来说就是“静”。契嵩对“性静”做了诸多论述,如“性者寂静不动”“性贵乎静”等等。而“情”作为外物的感应,相较于“性”来说,是动的状态,“天下之动生于情”。“静”与“动”描述的是性与情的状态,在“心”未开始思虑之时,人的真心、本性具有“静”的属性;自性动而起的就是情的范畴,故《夹注辅教编·原教》云:“凡一切心识,自真如性而起动者,皆属情也。其情所染习者,或善或恶。”[1]6
性寂静不动,故而“性”是“本觉”,情感而遂动,故而“情”是“不觉”。《夹注辅教编·原教》:“性者寂静不动,人之资质者也,亦其本觉者也;情者感而遂动,人之欲者也,亦其不觉者也……性亦本觉之真性也,情亦不觉之妄情也。”[1]4寂静资质者都是万物之体,本觉真性亦都是万法所依之体。人的欲望是“七情”的异名,不觉一念动者,亦都是“七情”之异名。
其二,性净情染。契嵩在强调性静情动的同时又对善恶的产生进行了分析,由性情的状态继而推导出性情的善恶属性。在性情的善恶问题上,契嵩主张“情有善恶,性无善恶”,其《中庸解》第四云:“善恶,情也,非性也。情有善恶而性无善恶者,何也?性静也,情动也,善恶之形见于动者也。”[2]76因为“性”为静,“情为”动,“性”是静止的,所以没有善恶,情动才会表现出善恶,故而“性无善恶,情有善恶”。也就是说,善恶的表现是“情动”的结果。
契嵩强调,“性”无善恶之别,由后天所感而形成的善恶以及“五常”“七情”,这些都属于“情”的范畴,而非“性”的体现。《中庸解》第四言:“苟以性有上下而不移也,则饮食男女之性,唯在于智者,而愚者不得有之。如皆有之,则不可谓其性定于上下也。韩子之言,其取乎仲尼所谓‘不移’者也,不能远详其义而辄以善恶定其上下者,岂诚然耶?”[2]76他在《非韩·中》也提到,“如此则韩子之谓五谓七、谓善谓恶者,岂不皆情耶?”[2]305在契嵩看来,韩愈所说的“五常”和“七情”都是围绕情而论,并没有真正地触及到“性”。契嵩以情的“寂然不动”状态作为人性的解释,表达了佛教对人性的基本看法。对此,有学者认为韩愈用善恶的标准来谈人性,结果将“性”与“情”的关系弄得有些支离,逻辑上的确有些混乱,而契嵩超越了善恶的标准来谈人性,发现了韩愈人性论中的某些弊端,确实有过人的地方[9]112。
“情”的善恶则与受到的熏习有关,契嵩在《广原教》中曾言:“夫心动有逆顺,故善恶之情生焉;善恶之情已发,故祸福之应至焉。”[2]29由于人“心”与外物相接,“情”才有了善恶。心动就称为业,心与业会合就称为感,由心动产生不同的善恶之情。他在《原教》也说:“情也者,发于性皆情也。苟情习有善恶,方其化也,则冥然与其类相感而成其所成。”[2]1即由“性”生发出来的“情”,或受到善的染习,或受到恶的染习,等到人死之后,其魂魄就会与其生前或善或恶之情互相感应,各自成就其不同的果报。
因“心”统摄“性”“情”,加之“性静情染”之故,契嵩认为“心”之广大能包容一切,其间善、恶、迷、悟圆融无碍,“善恶皆生、迷悟同体,故皆谓之心也”[1]53。而心有善恶之分,故表现为染净相混。他说:“心有善者焉,有恶者焉。”[2]27“心,谓如来藏心也,此之藏心染净相混,具凡圣所到之二至也。”[1]60因此,须辨别其中的真心和妄心,以区别精神作用里的正直之心。“其此之心,虽有真实之心,有妄想之心,是皆欲别辨其心所之中之真正心也。”[1]139契嵩对“性”与“情”所做的规定,解释说明了“心”的基本特征和本质特性,即“性”指向了“心”的真如不变,而“情”的存在则解释了“心”的圆融义。
三、以法界观作为方法论
为了进一步解释清净无漏的心本体与世间生灭法的关系,契嵩以华严法界观作为方法论,解决“心”的归依问题,从而构建起一个融合的理论体系。
华严法界观以理事范畴为核心,从理论的辩证分析入手,通过理与事、事与事之间的回互融通,层层递进,最终达至事事无碍的终极圆融境界。法界观相传为华严宗初祖杜顺所立,有三重之别,第一重真空观,第二重理事无碍观,第三重周遍含容观。澄观将华严先祖所述三观,加上三观所依之事法界观归纳为四法界,真空观相当于四法界中之理法界,理事无碍观相当于理事无碍法界,周遍含容观相当于事事无碍法界。
法界之种类固然繁多,然一切终归于一真法界,即诸佛众生本源之清净心。“心”远离一切迷情所见之相,超越了“有、无”之相对,呈现的是一种真空的状态。真空并不是虚无的空,它不是事物的现象,但被万物所依,无相的真空是包罗万象的。对此,契嵩《坛经赞》云:“心乎,若明若冥,若空若灵,若寂若惺。有物乎?无物乎?谓之一物,固弥于万物;谓之万物,固统于一物。一物犹万物也,万物犹一物也。”[2]61即“心”是真空,但不能说它有物,也不能说它是无物。在《夹注辅教编·坛经赞》中,他又补充道:“此心之所谓无有定相,或似乎光明,又似乎冥昧;或似乎空虚,又似乎灵知不绝;或似乎寂灭,又似乎惺惺。若言之为一法,则其体平等,故弥遍于万法;若言之为万法,则其体故通是一体。一法即万法,万法即一法,是盖无碍法界一多相摄之义也。”[1]141真空是万物的所依,所以真空中就有一切事物。在事物显现时,观察事物全体如观真空,观察真空时,全体真空即是事物,所以见事物即见真空,见真空即见事物。万法唯心所造,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心”即万法,万法即“心”,圆融无碍。
契嵩借鉴华严学中一真法界的生成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旨归,从真心的生成角度论证其本体特色。宗密认为,一真法界不仅是本体范畴,还具有生成论意义,它是现世和出世间一切法的本体,没有一法不是自心所现,没有一法不是真界缘起。“万法资假,真界而得初始生起也”[10]222中,从宇宙论的生成角度看,没有一法是在真界之前。对此,契嵩在《广原教》中说道:“有形出无形,无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寻,不可以无测,不可以动失,不可以静得。圣人之道空乎?则生生奚来?圣人之道不空乎?则生孰不泯?善体乎空不空,于圣人之道其庶几乎。夫验空莫若审有形,审有形莫若知无形。知无形则可以窥神明,窥神明始可以语道也。”[2]41有形之物,必定以无形之物作为本质;无形之物,可以生出有形之物。对于最为神妙的道理,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有形还是无形,而要善于体悟佛圣人之道的空与不空。验证佛道的空,最好的办法就是考察有形之物从何而来;考察有形之物,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有形之物出自无形之物这一道理。因为有形之物出于无形之物,所以真心才可成为万物的本体。
相较华严先祖,契嵩对一真法界和法界的运用范围更加灵活。他认为,所谓法即是一种自然的规则,是本来存在的一种法则,它不因人们的尊重而有所增,亦不因人们的不信而有所减。“法界常住,不增不减。及佛氏所论法界者,谓其广大灵明而包裹十方者也。”[1]158故而,契嵩以法界来论证心的广大。其《夹注辅教编·广原教》云:“一心之理包圆十方,故云无外一心之道;法界无边,故云无不中也。是故十方法界,无一事物而不厕预于道之中也。”[1]53按“法界无边”出自《大方广佛华严经》“众生无边、世界无边、法界无边、三世无边、一切诸佛自在无边,觉如是等,无有障碍”[11]599下。此处契嵩是以“法界无边”论证心之外无他道,道法无边。接着契嵩提出,心是十方世界的至极之道,他说:“广大乃道之广博宏大,横竖周遍,无有穷极;灵明亦法理冥灵寂照,未尝泯昧。而具此二者,举十方世界,无有至极者过乎此道也。神而自得,德无不备,妙以应用,用而无穷,具此二者,举十方世界,无有至极者过乎此心也。”[1]54
根据理事关系,契嵩提出“道同教异”的儒佛关系命题。契嵩为了推行他的三教会通思想,作出了具有类似本体意义的论证,论证的主要方式是“理迹本末”说,即首先设立三教“同于为善”的理体(本),然后又肯定三教各自表达的行迹(末)[12]121。契嵩所讲的“理”是三教共同的道,即共通的“心”本体,与“道”相对的就是教迹。其《广原教》云:“夫圣人之教,善而已矣;夫圣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2]34他认为佛圣人之教,其根本在于善,佛圣人之道,其根本在于正。对于世俗之人来说,重要的是所行之道正、所行之事善,而不是一定要分清楚这个人是僧还是儒,是属于彼还是属于此。或僧、或儒,不过是传道所采取的具体形式罢了,无法决定其道的正与不正,其事的善与不善。佛圣人垂示教迹,其目的在于保存道这一根本,也就是“存本而不滞迹”。因此,世人须关注根本之道,而不拘泥于圣人教迹。
将“心”作为支点,以“事事无碍”的观法看待社会上儒佛不同的现象,契嵩提出了“儒佛百家,心一迹异”的观点。他在《广原教》说道:“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2]46“心一”即是儒、佛都有道德之心,向善之德,在教人为善的本质方面存在一致性;“迹异”即是各家教化的方式不同,有浅有深,有近有远。而“心”这一绝对主体为“事事无碍”的主客合一提供可能。对此,荒木见悟认为,“将此穷理尽性、彻果该因、汪洋冲融、广大悉备、随兴无碍的绝对主体称之为‘一心’的话,事事无碍的论理不单只是解析其存在的客观论理,也不是主观意识当中探求客观事物的唯心论理,而是主客合一、一真法界的论理”[13]43。依荒木见悟所言,若要真正实现儒佛之间的会通,应当从本体而不是从教迹上去看待问题。儒释两家为教虽不同,但最终的价值取向是相同的,正如契嵩云,“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2]149,儒、佛不同的教化手段是表象,其本质都是为了劝善去恶,服务于王道。
纵观契嵩整个逻辑进路,是从关注一心开始,到超越儒、佛不同的教迹,最后回归本体,得出儒佛一贯的结论,其“心”本体论的最终精神指向是“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2]34。契嵩开演华严之奥秘,达于圆融之妙,在佛教内部融合佛教诸宗,在佛教外部沟通儒道,这是一种极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和境界,为儒佛会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化解对抗与冲突的根本之道对现代思想文化的建构有积极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