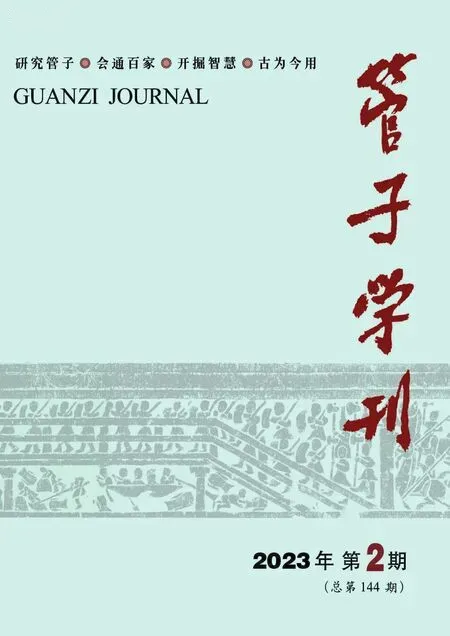“比”:从生活世界通向道德世界的桥梁
——再论简帛文献的先秦儒学诗学传统
王 欣
(河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自公布以来,受到了学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连篇累牍。《孔子诗论》涉及的竹简共二十九支,诗文五十四篇,一千余字,基本上是对“诗”各个构成部分“风”“雅”“颂”主旨,或某篇诗文篇旨的概述。从诗文篇名到结论,大多是用一句话、几个字,甚至一个字来概述,行文风格简洁明快,诗文的生活世界与孔门儒学的道德世界直接相通。但也正因其简洁明快,缺乏如传世文献中间较为详尽的推导过程,从诗文到结论这种直接相通的方式显得比较突兀、生硬,导致一些研究成果只是按照文本顺序,就文本而释读文本义理,仅仅做一些解释性工作,而不能对《孔子诗论》思想作整体性的释读。
笔者认为,化解这种困境的有效方式,是从《孔子诗论》文本中挖掘“比”的阐释方法,并以此为理论支点,从逻辑上展开《孔子诗论》文本结构所缺乏的中间推导过程,架构从诗文的生活世界通向孔门儒学道德世界的桥梁。另外,帛书《五行》列举的“目而知之”“譬而知之”“喻而知之”等阐释方法,为我们准确理解孔门儒学简帛文献的思想内容,合理判定简帛文献对先秦儒学诗学思想传统的贡献,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参照。本文依此具体展开。
一、《孔子诗论》“比”之显性方式
诗文中鸟兽草木众多,“比”的方式俯拾皆是。孔子要求弟子们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郑玄等:《十三经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023页。。“识”,原为识别、认知之义,王应麟《困学纪闻》中谈诗云:“格物之学,莫近于《诗》。……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有多识之益也。”(2)王应麟:《困学纪闻》,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所谓“引伸”“触类”,亦即“比”的方式。由此推断,《论语》中孔子除明确使用“兴”的阐释方法之外,似乎亦隐隐推出“比”的阐释方法。例如:“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3)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1977页。“暴虎冯河”是对诗文“不敢暴虎,不敢冯河”(4)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256页。的化用,孔子以此喻示子路不可鲁莽好勇。孔子与子贡论诗,子贡引诗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5)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1954页。,喻指“富而好礼”即德业升进的工夫,孔子赞誉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6)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1954页。这种赞誉应包括子贡能够突破悟解“诗”的困难,“这困难显然是由于诗的表现方式造成的,因而可以想见诗的含蓄的、隐喻的或象征的艺术特性,无疑是被肯定的”(7)张亨:《思文之际论集:儒道思想的现代诠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在孔门诗学视域中,“比”这种阐释方法,即借用诗文中的生活世界,譬喻、类比、类推孔门儒学的道德世界。通观《孔子诗论》文本,没有明确使用“比”,不过,却出现了“譬”“拟”“喻”“犹”等术语,这些都可以归之于“比”的显性方式。下面我们逐次展开释读。
第四章:
《十月》善譬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耻之。(8)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此文提到了三篇诗文,《十月》(毛诗作《十月之交》)、《雨无正》、《节南山》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上之衰”。分别来看,《十月之交》以日食、月微为征候,喻指天下纷乱,如“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9)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69页。。《雨无正》以雨水纷多喻指政令繁重,如“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如何昊天,辟言不信。”(10)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第273页。《节南山》喻指为政不均,多乖戾之事,如“昊天不傭,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11)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第263页。。不过,这三首诗采取“言”的方式是“譬言”。“譬”是先秦诸子使用较多的言语方式,墨子专门谈到这种言语方式的特点:“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12)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43页。孔子云:“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3)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1976页。老子云:“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14)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页。这种譬喻的方式,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情感的类推。显然,《孔子诗论》亦传承了这种言语方式。“王公耻之”,“耻”是一种道德情感,即以此为“耻”。《孔子诗论》中类似的说法很多,这种道德情感是指情感的存在本身就含有道德取向。王博先生认为,“耻”是“‘诗可以兴’的具体表现,王公读到此类诗,当会兴起‘耻’的感觉”(15)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7页。。这种释读是契合文本义涵的。
第一章:
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16)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8页。
《关雎》诗文以“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象征君子求好淑德的喜悦,而《孔子诗论》作者则表达了“好色之愿”,即对于美色的喜悦。孔子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17)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1987页。孔子以“好色”比喻“好德”,并非因为人们重于“好色”而薄于“好德”,而是引导人们如同“好色”一样“好德”。谢良佐曰:“好好色,恶恶臭,诚也。好德如好色,斯诚好德矣。”(1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8页。其中“诚”尤为关键。“诚”即真诚,是指内心情感的真切、诚挚。这两句话的不同点在于,前者是通过诗文“琴瑟”“钟鼓”这些器物形态表达,后者则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好色”。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前者通过“寤寐求之”“寤寐思服”表达,后者是一种“愿”的表达,都是发自内心的。通过“拟”这种方式,《孔子诗论》作者已经把《关雎》中的情感进行了一种儒学意义的转换。
第四章:
《小旻》多疑矣!(19)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9页。
第一章:
《关雎》以色喻于礼。(22)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8页。
“喻”是孔门儒学经常使用的方式,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3)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1966页。。“色”即上文“好色”,这是人的一种自然情感,在《孔子诗论》作者看来,应以“礼”安顿这种自然情感,使之在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范围内发生。郭店简《性自命出》曰:“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24)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始”即情之显发,“终”即义之依据,所以,孔门儒学不是要断绝这种自然情感,也不是放纵这种自然情感,而是以“礼”去调适、引导之。以诗文之“喻”这种比拟方式,使这种情感的调适、引导即“喻于礼”的方式,带有一种柔性的更易于让人接受的倾向,而不同于后儒那种以礼制、礼法进行刚性的约束、节制。
第五章:
《湛露》之贝益也,其犹车它与?(25)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9页。
“车>它”,读为“驰”,犹驰驱也。《湛露》(26)《湛露》诗文:“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沾沾露斯,在彼丰草。厌厌夜饮,在宗载考。沾沾露斯,在彼杞棘。显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岂弟君子,莫不令仪。”见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第231-232页。诗文共4章,末句分别为“不醉无归”“在宗载考”“莫不令德”“莫不令仪”,始于宴飨夜饮,进而祭祀宗庙,最终美令德、令仪。“驰”比喻进德之速,为赞誉之辞。“贝益”即“益”,厚遇,指天子燕诸侯之礼。刘信芳先生认为:“就思想层面之意义而言,《湛露》之‘益’,是天子之礼也;‘驰’,是诸侯之报也。是知《诗论》之评《湛露》,用意深矣。”(27)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第十章曰:“诗其犹平门与?”(28)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60页。“平”,训为宽广,“平门”犹四门洞开,指学诗可以通达人情事理。《孔子诗论》第八章曰:“《邦风》其内物也博,观人俗焉,大敛材焉。”(29)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60页。此章虽专门对“风”而言,其中“纳物也博”“观人俗”“大敛材”与“平门”近义。《论语》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30)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2003-2004页。“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31)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2023页。指学诗不仅可“达政”“使于四方”,而且可以涵盖人生的全部意义。
二、《孔子诗论》“比”之隐性方式
《孔子诗论》中也有部分文本并非明确标识“譬”“拟”“喻”“犹”等,但也在运用“比”之阐释方法,相对而言,可以称之为隐性方式。明人郝敬在《读诗》中,就毛诗中“比”的具体方式,作出了清晰的分类:“比者,寓托之义,非独两物切譬为比也。但不直斥此事,而托言于彼,皆是比。”有“亲切譬喻者也”“类比之取义者也”“类比之为隐语者也”“类比之切响者也”“类比之会意者也”(32)郝敬:《毛诗原解 毛诗序说》,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4页。。这对于我们解读《孔子诗论》中“比”的隐性阐释方式,提供了一种理论参照。我们先看相对集中的第六章:

《宛丘》是《陈风》首篇,诗文曰:“洵有情兮,而无望兮。”“洵”,信也;“望”读为“忘”(34)林义光:《诗经通解》,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45页。。诗文大意是说,相信有情而勿相忘。郭店简《五行》曰:“善,人道也。”(35)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五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以“善”评判,意谓这种情义乃人间正道。《猗嗟》是《齐风》其中一篇,诗文“四矢反兮,以御乱兮”,“反”,复也;每射皆能中的,如是反复四次。郑笺:“射必四矢者,象其能御四方之乱也。”(36)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第138页。对此镇抚四方的能力,以“喜”判定。第三章曰:“《杕杜》则情,喜其至也。”(37)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9页。《杕杜》表征宗族兄弟之情,《孔子诗论》以“喜其至”判之,“喜”即发自内心的赞赏。《鸤鸠》是《曹风》其中一篇,诗文“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是从鸤鸠养子专一,引申到对待人和事要专心。“结”即坚固、执一之义,可以引申为“信”,即心志坚定之义,与孔子主张“主忠信”(38)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2000页。一致。
可以看出,第六章“诗文名称+吾…之”的文本结构,不是一种描述,而是一种判断,这些判断的命题采取了“亲切譬喻”“类比取义”等“比”的方式。诗篇及其诗文的选取,源于《孔子诗论》作者深厚的诗学修养底蕴。通过对这些诗文的突出和强调,并抉发诗文中的自然情感和文武之德,得出了这些判断用语。姜广辉先生认为:“‘《宛丘》吾善之’,是‘善’其情真;‘《猗嗟》吾喜之’,是‘喜’其艺精;‘《鸤鸠》吾信之’,是‘信’其意诚;《文王》吾美之,是‘美’其德高;‘《清庙》吾敬之’,是‘敬’其有典型;‘《烈文》吾悦之’是‘悦’其不忘本。”(46)姜广辉:《关于古〈诗序〉的编连、释读与定位诸问题的研究》,姜广辉主编:《经学今诠三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这些判断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孔门儒学的道德命题,另一个是发自内心之“性”,显示出《孔子诗论》以德正心(志)(对诗而言,为“志”;对人而言,为“心”)的思想主旨。
有的学者认为:“《孔子诗论》论诗中之情,多数都很难区分是自然人情,还是道德情感。”(47)刘宁:《论毛诗诗教观与思孟学派的思想联系》,杜维明主编:《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页。其实《孔子诗论》对“爱”“孝”“怨”等的释读,都带有鲜明的道德色彩。我们看第一章关于“爱”的文本记载:“甘棠之爱,以召公……情爱也。”(48)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8页。第五章曰:“《扬之水》其爱妇烈。《采葛》之爱妇□。”(49)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9页。《甘棠》是《召南》其中一篇,诗文是由对甘棠之爱转换为对召公之敬。《孔子家语》亦云:“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50)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2页。在《孔子诗论》作者看来,对召公之敬是“情爱”的一种体现。《扬之水》选自《唐风》,诗文三章首句为“白石凿凿”“白石皓皓”“白石粼粼”(51)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第150页。,“凿凿”,鲜明义,“皓皓”,洁白义,“粼粼”,清澈义,均喻为情感外显,故《孔子诗论》以“爱妇烈”判之。
《采葛》是《王风》其中一篇,以诗文“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岁兮”(52)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第103页。,比拟相思情感之浓,以“爱妇深”断之,合乎诗义。这种“爱”源于人与人相悦的自然情感,或对召公的尊敬情感,这不是抽象义理,而是凸显了“爱”的生命实存意义。不过,在《孔子诗论》中,这种“爱”已转化为孔门儒学的一种道德情感。这种“爱”即孔子所谓“爱人”之“仁”,郭店简《性自命出》曰:“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53)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性自命出》,第70页。所以,《孔子诗论》所谓“爱”之“情”、之“烈”、之“深”,其本质即孔子“爱人”之“仁”。
另外,比较鲜明的还有“孝”“怨”等道德情感,也采用了“比”的方式。第五章“《蓼峩》有孝志”(54)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9页。,《蓼峩》描述的是“哀哀父母”之艰辛,“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55)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第294-295页。,充满了对父母的感念。因此,《孔子诗论》以“孝志”诠释篇旨,“孝”是孔门儒学的核心观念,“志”是沿顺“诗言志”的理路,强调“孝”发自内心。“怨”相对集中于第三章,其曰:“既曰‘天也’,犹有怨言;《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因《木瓜》之报,以抒其悁者也。”(56)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9页。所谓“藏愿”,即内心的美好愿望,从《木瓜》诗文来看,“木瓜”与“琼琚”、“木桃”与“琼瑶”、“木李”与“琼玖”对应,末句为“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种愿望是一种情感表达,诗文并不注重礼物是否厚薄,礼物之间是否对等,末句“永以为好也”才是重心。所以,诗文之“怨”并非怨天尤人之“怨”,而是“闺怨”。但《孔子诗论》作者并非仅仅停留于这种“闺怨”,而是喻示为孔门儒学的道德情感。“怨”是孔门诗学的重要概念,《论语》中孔子论诗,“可以怨”(57)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1954页。,“怨”指一种普遍意义的情感。
孟子与其弟子论诗,高叟以《小弁》为“小人之诗”,缘由即在于“怨”。孟子却回答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58)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2142页。按照高叟的说诗逻辑,《小弁》多次谈到“心之忧矣”,是对亲人的怨怼,故谓“小人之诗”。孟子并非似高叟只沉浸于原义之中,而是在生活世界中具体理解诗义,在亲人之间的血缘情感中细微体会。这种亲人之“怨”,充满了亲情与爱意,这与孔门儒学之“仁”最为切近,故谓“亲亲,仁也”。所以,“既曰‘天也’,犹有怨言”。学界对于对应诗篇一直未有定论(59)主要是关于《鄘风·柏舟》《鄘风·君子偕老》《邶风·北门》等篇,学界一直未有定论。参见刘信芳:《孔子诗论述学》,第208-209页。,恐怕根源不在于对何种诗篇的诠释,而在于对“怨”的理解。《小弁》诗文“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毛传:“舜之怨慕,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60)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第281页。即可参证此句义理的诠释。
三、帛书《五行》“比”之具体方式
与《孔子诗论》类似,马王堆帛书《五行》也是孔门弟子比较典型的诗学文献(61)美国的王安国(Jeffery Rigiel)教授讨论过《五行》对《诗经》的解释。参见王博:《中国儒学史·先秦卷》,第475页。。帛书《五行》与郭店简《五行》不同,它既有“经”文,也有“说”文,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阐释。在帛书《五行》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中(62)帛书《五行》原文顺序及释文,主要参照魏启鹏:《简帛文献〈五行〉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分别提出了“目而知之”“譬而知之”“喻而知之”,是这部诗学文献对“比”之具体方式的阐释。
先看第二十三章“目而知之”的“说”文:

“目”,视也,“比”,比类。“说”文三次提到“目之也者”“目之已”“目也”,意谓这种比类方法贯彻始终。“进之”,“说”文亦三次以“进耳”阐释,说明阐释这种升进路径亦是贯彻始终的。以下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进耳”亦是此义,不再单独解释。

再看第二十四章“譬而知之”的“说”文:
譬而知之,谓之进之。弗譬也,譬则知之矣,知之则进耳。譬丘之与山也,丘之所以不名山者,不积也。舜有仁,我亦有仁而不如舜之仁,不积也。舜有义,而□□□□□□□□义,不积也。譬比之而知吾所以不如舜,进耳。(64)魏启鹏:《简帛文献〈五行〉笺证》,第117页。
“譬”即比喻,不过,从此章文本来看,“譬”为类推、类比方式更为贴切。“进之”亦指升进路径,其关键词是“积”。丘不如山更高,在于其积累不够;普通人(我)与大舜相比,“仁”“义”的层次不如大舜,亦在于积累不够。这就是说,虽然我与圣人都好仁义,但层次与“积”的工夫相关,这是以“辟”的方式对德业升进工夫的强调,“积”与“不积”,成为普通人与圣人的根本差异。孟子在承认“圣人与我同类”的同时,也看到了“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65)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2136页。《孟子·告子上》记载:孟子曰:“圣人与我同类者。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合观帛书《五行》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更可以看出二者之间思想的一致性。。就此而言,孟子传承了帛书《五行》的思想。
再看第二十五章“喻而知之”的“说”文:
喻而知之谓之□□。弗喻也,喻则知之□,知之则进耳。喻之也者自所小好喻乎所大好。“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求之弗得,寤寐思伏”,言其急也。“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言其甚□□□如此其甚也。交诸父母之侧,为诸?则有死弗为之矣。交诸兄弟之侧,亦弗为也。□□邦人之侧,亦弗为也。□□父兄,其杀畏人,礼也。由色喻于礼,进耳。(66)魏启鹏:《简帛文献〈五行〉笺证》,第117页。
“喻”亦是“比”的方式,从此章“经”文和“说”文来看,“喻”为比拟、喻示,而且是“自所小好喻乎所大好”,即以小喻大。“好”,即“爱好”之“好”。“说”文虽未明确引诗,但整体结构都是以《关雎》诗文为引子。何谓“小好”?对于美色之“好”,“说”文连续用诗文比拟,以“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比拟“思色”,以“求之弗得,寤寐思伏”比拟“其急”,以“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比拟“甚急”。以诗文比拟的这种方式在《孔子诗论》中也出现过,如第一章曰:“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好。”(67)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8页。虽然对于美色之“好”如此之急迫,但是仍有“弗为”的要求,在“父母之侧”“兄弟之侧”“邦人之侧”是不可为的,其中在“父母之侧”的要求最是严厉,“死弗为之”;其次是“畏父兄,其杀畏人”。由此引出了“大好”,“大好”即“礼”。所以,“以色喻于礼”即由“小好”喻示“大好”,也是一种升进路径。
“喻”在文本中除以诗文比拟“小好”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作用,即把这种对于美色之“好”,置于孔门儒学的道德世界中,置于现实的伦理处境中,这与由“小好”喻示“大好”,“以色喻于礼”是一致的。在此,“好礼”成为“好色”的语境和前提,尤其是最后连续使用“死弗为之”“其杀畏人”这种语气,“小好”陡然进入了庄重、严肃的氛围之中,由此便会产生以“好礼”对“好色”的约束和节制。《孔子诗论》中也出现了“以色喻于礼”。虽然二者都是以“礼”去安顿对美色之“好”,从诗文的生活世界通向孔门儒学的道德世界,相对而言,帛书《五行》更倾向于通过刚性的节制和约束,使人们产生“好色”的敬畏之心;《孔子诗论》则主张通过柔性的引导和调适,把人们的“思色”之情纳入礼制轨道。这种细微的不同,恐怕与二者在先秦儒学思想史中的前后地位相关。
结语
诚如本文开始所提出的,《孔子诗论》这种出土文献与诗学文献,其文本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思维的跳跃性,很多句式结构大多是用一句话、几个字,甚至一个字来概述。如果没有深厚的诗学修养,没有孔门儒学的思想底蕴,很难领会这种思维跳跃所隐含义理的致思进路。对此,陈来先生指出:“在竹简古文献中这种跳跃很为常见,古人的文字亦不注重逻辑,我们必须把其中的跳跃弥补出来,而不是无视它所预设的中间过程、简单地利用其结论。在解释实践上,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一个概念出现的具体上下文环境中来认识其意义,而后考虑如何在整体上加以贯通。”(68)陈来:《帛书〈五行〉篇说部思想研究》,杜维明主编:《思想·文献·历史——思孟学派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挖掘《孔子诗论》中“兴”“比”等阐释方法,有其非常重要的思想价值。
作为先秦时期孔门儒学的出土文献和诗学文献,《孔子诗论》非常具有典型性。这种典型性不仅在于普遍地论诗,还在于或隐或显地使用了“兴”和“比”两种阐释方法。就二者的相同之处而言,“兴”带有一种价值属性,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兴发、萌动,而是“向善”的冲动与创造。“比”同样带有一种价值属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以此物“比”彼物,而是一种“向善”的譬喻、类推、喻示。“比”以诗文中的鸟兽草木、山川湖海、圣王功德等为象征,或是以同类相推的方式,或是以递次升进的方式,或是以以小喻大的方式,从诗文的生活世界推论出孔门儒学的道德世界,包括道德情感、道德命题,道德评判等。这意味着在诗文的生活世界与孔门儒学的道德世界之间,“比”这种“桥梁”不仅起到了一种平行的相通作用,而且还有一种向上的提升作用。“比”这种具体方式“充分表明孔子《诗》学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话语的深刻影响”(69)魏启鹏:《简帛文献〈五行〉笺证》,第179页。。“兴”和“比”共同的“向善”属性,既是先秦时期孔门儒学的论诗方式,也使这种论诗方式带有孔门儒学的价值取向。这是孔门儒学诗学文献与其他诗学文献不同之处。
《孔子诗论》中“兴”与“比”的阐释方法,使这种诗学文献的思想世界不是停留于抽象概念,而是富有先秦儒学活泼的生命气息,富有先秦儒学的诗性智慧,由此“正见中国人心智中蕴此妙趣,有其甚深之根柢。故凡周情孔思,见为深切之至而又自然之至者;凡其所陈,亦可谓皆从观物比兴来。故比兴之义之在《诗》,抑不仅在《诗》,实当十分重视”(70)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52页。。
在孔门诗学视域中,“兴”与“比”相对而言,具有以下区别:第一,“兴”发源于“心”的感性萌动,“比”的推论带有一种理性色彩,《孔子诗论》和帛书《五行》对“比”之方法的自觉使用和具体阐释,说明随着先秦时期孔门诗学的发展演变,其阐释方法的理性色彩愈加浓厚。第二,“兴”是双向或多向的共同感应,是师生之间相互启发的群体性活动;“比”是一种单线的思维进程,是从诗文出发通向道德世界的个体性活动。第三,“兴”面向人的“心”“性”,与心性之学在孔门儒学本体地位相一致;“比”面向生活世界,是孔门儒学道德世界的具体展开(71)许春华:《“兴”:“诗”与“仁”的对接——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哲学研究》2022年第6期,第77页。。“兴”与“比”都是孔门诗学不可或缺的阐释方法,共同构成了先秦儒学诗学的经典阐释传统。仅仅依据《毛诗序》“六义”说,便推断汉儒贡献了儒家诗学传统中“兴”“比”的阐释方法(72)箫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是缘于对先秦简帛文献的儒家诗学传统缺乏“同情之了解”。
应该说明的是,“兴”与“比”作为孔门诗学的阐释方法,是通过引诗、论诗来引发、推论孔门儒学道德世界的方式。不过,在汉唐儒学诗学视野中,却经常混淆孔门诗学“兴”与“比”的关系。在注疏孔子“诗,可以兴”时,孔安国释曰:“引譬连类。”邢昺疏:“诗可以令人能引譬连类,以为比兴也。”(7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486页。《周礼·春官》载“大司乐”职责:“以乐语教国子,曰: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兴者,以善物喻善事。”(74)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476页。另一处载“大师”的职责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郑玄注:“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75)郑玄等:《十三经古注》,第483页。不论是孔安国、邢昺“引譬连类”,还是郑玄“以善物喻善事”“取善事以喻劝”,其注疏方式均是以“比”释“兴”。这种注疏方式不仅导致“兴”的表象化、物象化,更为严重的是使“兴”丧失了本体地位,“比”也相应失落了“体”之源。
与之相关联的另一种影响,是把“赋”“比”“兴”作为并列的三种表现手法,这一点始作俑于《周礼·春官》和《毛诗序》。《毛诗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76)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第1页。“六义”说与《周礼·春官》所谓“六诗”顺序完全一致。作为先秦时期孔门诗学最为重要的两种阐释方法,却被《周礼》所谓“六诗”、《毛诗序》所谓“六义”排列到第三位和第四位,以“兴”与“比”为主的孔门诗学经典阐释传统,转变为汉儒诗学的创作手法和表现手法,进而转换为汉唐儒学诗学以传、笺、注、疏、义解等为主要方式的阐释传统,孔门诗学的道德生命也随之异化为训诂、章句的文献考据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