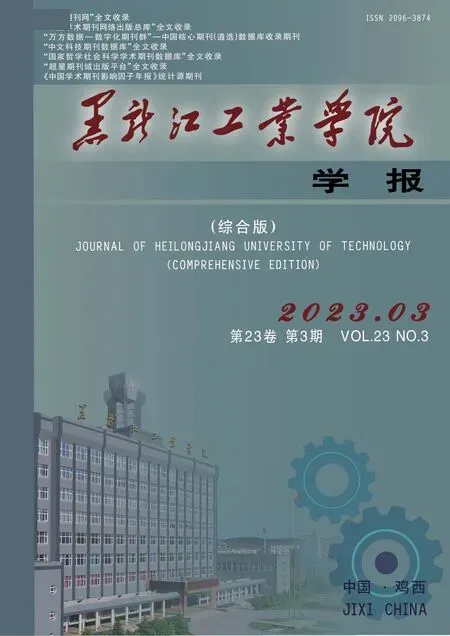诺木洪农场生计方式变迁研究
韩非儿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0)
生计是人们维持生活的计谋或办法,与自然资源相关;而生计方式是指人们相对稳定、持续地维持生活的计谋或办法,即通常所说的生计模式或生活习惯。由于生计模式与自然环境、人口及劳动工具、种植作物密不可分,当其中有因素发生变化,生计方式也就发生变化,这就被称为生计变迁[1]。没有一种“纯粹的生计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到物质及其生产方式的制约。诺木洪农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适应高原荒漠地区的生计方式,但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诺木洪人的生计方式也在不断变迁。了解诺木洪农场生计方式变迁的过程,是认知诺木洪农场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对当前高原地区开发建设实施情况的认识缩影。
一、诺木洪农场概况
青海诺木洪农场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南缘,海西州都兰县境内,农场南北宽5千米,东西长30千米,呈扁条状分布;农场属高原大陆性气候,空气干燥,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据《都兰县志》显示,1958年4月3日,诺木洪地区大风持续7个多小时,吹揭房顶9间、吹毁帐房10顶,3884亩小麦、303亩青稞、60亩豌豆幼苗在大风中被吹毁,部分庄稼被连根拔起;1960年3月19日,诺木洪地区风沙肆虐,有300亩土地的3~4厘米地表土层被席卷而去,400亩春小麦的种子随风飘零,100万公斤的有机肥被洗劫一空;1966年8月14日,诺木洪地区3.77万亩已近成熟的农作物在风灾中平均每亩落粒20公斤,共损失粮食18.5万公斤;1970年4月16日,诺木洪地区最大风速达35米每秒,已播种春小麦9937亩被大风摧毁[2]。农场属干旱区,降水少,风速大,蒸发量大。很多耕地因缺水未能很好垦殖,表1为诺木洪农场1971—1980年夏季农田苗期旱灾程度统计表[2]。

表1 诺木洪农场1971—1980年夏季农田苗期旱灾程度统计表
农场始建于1955年,农场位于西连甘肃、新疆,南接西藏西北地区的重要通道节点,地处青海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格尔木、德令哈等工业园的结合部,是青海省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重要绿洲农业区和藏、蒙、回、汉等多民族聚集区,在柴达木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中承东启西、南联北进,支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维护边疆与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地位突出。建场以来,几代诺农人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气候和环境条件,培育出了柴杞、苗木、猪肉、紫皮大蒜、白皮莴笋等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享有“沙漠绿洲”“翰海明珠”的美誉,成为戈壁绿洲农业的典范,被誉为绿洲农业的奇迹。
二、诺木洪农场传统生计方式
1.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计方式
据统计资料表明,诺木洪一带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是个沙丘遍地、风沙横行、猛兽出没、人烟稀少之地。仅有少数蒙古族牧民在这里以放牧为生,与农耕无缘。1955年10月青海诺木洪农场建场之初,一大批转业军人、干部和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柴达木腹地,通过艰苦卓越的奋斗,建成“田成方、林成带、路成网、渠成系”的高原特色农林产业区,创造出高原戈壁绿洲农业典范[3]。诺木洪农场的生产活动因受地形、地质、地貌和热量条件的制约,上世纪50年代农场农作物的种类较少,品种单一,主要以小麦、青棵、豌豆、马铃薯为主。其中,春小麦是农场的优势作物,农场是当时青海省春小麦高产地区,以及海西州的主要粮油生产基地。油料主要是小油菜,蔬菜多系耐寒品种,有雪里红、甜菜、紫皮大蒜、白皮莴笋、白菜、甘蓝、萝卜等。
可以看出,诺木洪农场保证了国家、青海省和本地区粮食供给,维持了农场的生存与运转,在物资极其困难的年代,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立足于通过农业生产来发展农场生计。在“以粮为纲”的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在农业科技不断进步与革新中,农场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农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成为青海省重要的商品粮油基地,促进了青海的经济建设,保证了粮油供给,繁荣了地方经济,带动了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
2.以畜牧业为辅的生计方式
为解决职工、家属的肉食供应和开荒造田役畜需要,畜牧业从自养、自给、自用发展起来。1960年后,本着农牧并举的方针,扩大开荒面积,增加役用牲畜,畜牧业得到较快发展。1991年养猪实现保温猪舍半机械化生产,养鸡实现机械化,成为格尔木市场主要肉食品供应地;1995年基本形成以养猪为主体的畜牧业,实行“二级三化”繁育,即种猪场实行一级繁育,培育优良杂交一代种猪,各商品猪场进行二级繁育,育肥出栏。1998年以工副业大队为主体的畜禽公司成立,畜牧队从各大队分离出来成为畜禽公司的直属单位,工副业大队养猪场为畜禽公司种猪场。因气候寒冷、设施差、饲料不足,种猪繁殖率低、生猪育肥周期长、出栏率低、饲养成本高,造成养猪多赔钱多。2001年采取家庭承包、个人承包的形式,压缩自繁自育猪群规模,逐步向外引和分散育肥为主。2005年,生猪基本无产出,只有少量家用畜禽养殖[4]。
综合来看,诺木洪农场的畜牧业发展在整个农场生产中所占比重较低,农场的重心在种植作物上,对畜牧养殖关注较少,受客观因素制约,畜牧业在农场的生产中起辅助作用,畜牧养殖在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为青海海西地区的开发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农副产品,为保障农场及周边地区生产、生活需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变迁后诺木洪农场生计方式
1.以枸杞种植为主的生计方式
农场所在区域有中国最古老、面积最大、最集中的原生态野生枸杞资源群落。农场利用这些资源,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进行野生枸杞人工驯化种植。枸杞是一种耐干旱、耐贫瘠、耐盐碱的多年生灌木经济作物,喜冷凉气候,耐寒力很强。当气温稳定在7℃左右时,种子即可萌发,幼苗可抵抗-3℃低温在-25℃越冬无冻害;春季气温在6℃以上时,春芽开始萌动。同时枸杞根系发达,抗旱能力强,在干旱荒漠地区仍能生长。光照充足时,枸杞枝条生长健壮,花果多,果粒大,产量高,品质好。枸杞多生长在碱性土和砂质壤土,最适合在土层深厚、肥沃的壤土上栽培,由于耐干旱,可生长在沙地[5]。
1990年开始,诺木洪农场种植业养殖业效益逐渐降低,在市场竞争中慢慢失去优势,农场转型迫在眉睫。随国家退耕还林项目建设的实施,农场在此机遇下邀国内农业专家进行相关专业测定,发现诺木洪地区小环境较为适宜种植枸杞。农场随即决定调整产业结构,大规模种植枸杞。从此,诺木洪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人员构成、生活习惯开始随枸杞在诺木洪的种植而接连发生变迁。枸杞的种植技术比普通农作物的种植更为复杂,需要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和累积工作经验,不然很难适应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方式,起初大家对枸杞的种植热情不高,农场不断地引进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农业科技的普及,以及前期种植获得的良好经济效益,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一定的种植规模,枸杞慢慢变成了诺木洪农场种植规模最大的作物,改变了以粮食作物为主种植的种植态势,种植结构变得更为多元,在全国枸杞产业中声名远播,影响巨大,市场知名度、信誉度远在同行业之上,已居青海枸杞产业的龙头地位,枸杞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许多高效益、创新型的新兴产业,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生活水平,也使得生计方式得到了新的扩展与创新。
2.衍生出以采摘业为辅的生计方式
随着枸杞业的发展,得益于枸杞广阔的市场需要,农场采摘业兴起,技术简单,对文化程度要求不高,虽然工作比较辛苦劳累,需要忍受高温晒以及长时间的户外劳作,但由于采摘偏向于季节性劳作,一般集中在枸杞丰收的7到9月,吸引了大批劳动者。
四、生计方式变迁的原因
生计变迁一般考虑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即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共同形成一种外部推动力量。人们要不断调整可以维持和延续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生计方式。人力、自然、经济资本和社区等资源的各个维度都会影响生计变迁的过程,尤其是各种资源在具体生产生活中的分配和使用,其不平衡性导致人们对于其生计选择的决定是充满波动的,这些外力的作用是客观产生的不可抗力因素。而内部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个人为主的自身进步与发展,个人试图去寻求更好的生存状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体通过对生计方式的调整从而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可以说生计方式变迁本身就是多元的,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
1.自然环境因素
生态人类学认为,人类的任何生计自然特征不纯粹是一种自然选择方式,而是一种文化选择。人类传统生计方式的维持离不开自然要素本身的这种系统性观念[1]。诺木洪地区严重的风沙灾害常常吹毁帐房、刮散羊群、导致牲畜体内热量散失和疫病流行,在农业上也会造成埋没农田,吹倒苗根的后果。
综上,可以看出大风及干旱天气对当地生计方式均造成了负面影响。自然灾害的发生本身是一种不可抗力,对生产生活的破坏巨大。选择更适合在旱地种植的品种,可以减小因为旱灾造成的作物减产失收,天然的环境制约了传统农业的发展,合理选择作物品种有效地避免了作物低产失收现象发生,进一步达到减少经济损失的作用。生计方式的适当调整,维持了正常的生活状态,削弱了灾害带来的损害。
2.社会环境因素
影响生计变迁的社会因素有政府政策、市场需求等。政府出台的政策会促使生计方式的改变,市场的需求也会导致生计方式上的调整。生计与所处社会环境是无法剥离的,生计方式要不断地适应社会环境。
农场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抢抓国家西部大开发、退耕还林工程建设的机遇。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四个发展”的战略目标,调整种植结构,着力培育发展枸杞特色产业,加快诺木洪枸杞产业园区规划建设。农场要不断调整自身的生计方式,才足以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社会进步具有必然性,生计方式的变迁顺应了时代的选择,与时代共同前进。农场进入市场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自身便对生产环境具有客观的调控作用,符合当时需求的产品才具有经济价值。在“以粮为纲”的计划经济时代大面积种植小麦,在枸杞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的情况下选择大规模种植枸杞,无疑是市场导向作用的显现。
总之,由政策和市场所构成的社会环境因素,致使诺木洪农场不断去调整自身定位,使自身性质与其相适应。可以看出在这种客观的环境条件下,生计方式的改变并不受某一个单一因素的制约,而是受不同时间段、不同社会体制以及不同市场结构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最终导致生计方式的改变。
3.诺木洪农场人自身因素
自身因素作为升级方式转变的内部因素,是由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决定的。客观来看,个人大多为了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才会改变自身的生计方式,即可能由于当前的生计方式无法满足自身生活需求,从而试图改变生计方式获取更好的生活状态。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再局限于满足自身衣食住行的需要,逐渐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生计方式不仅仅作为满足日常生活的方式。而逐渐演变为追求更高生活品质,实现自身追求的一种路径。除去客观性的一面,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在不断加强。追求自身发展作为由个人所主导的内部因素,对生计方式的改变有巨大的影响。就诺木洪农场本身而言,农场自身外部环境的转变促使了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农场人为实现自身发展而改变生计方式去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生计方式的转变与选择导致了整体生计方式的变迁。
五、生计方式变迁的启示
生计方式变迁是由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合力影响造成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外部因素即外部环境对生计方式选择的影响,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内部因素即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善自身环境的时候,生计方式也随之改变。诺木洪农场从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生计方式转变为以枸杞种植为主采摘业为辅的生计方式。生计方式的成功转变,是在其面对发展困境的时候,直面问题并有效解决,这也是农场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随着时代的发展,农场也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
1.因地制宜是农场发展的前提
发展要立足自身实际,突出特色、创新,而不能一味地模仿照搬他人。农场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宜普通农作物的生长,农场以枸杞种植为突破口寻找诺木洪的致富之路,是在当地政府与相关部门的指导与帮助下,从农场的现实条件出发而量身定制的产业发展之路。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发展模式,要利用独特的地方资源优势发展相关产业,与建设农业生态区或示范区结合起来,整合土地资源、林业资源,改善当地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以助力当地的发展建设。
2.关注民生是重心
民生问题主要是如何“富口袋”的问题。要以生活富裕为根本,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不断增强农场人的获得感。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升人口整体素质水平,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和人民增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善人居环境,要加快推广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中的运用,打造科技农业、智慧农业,全面激发农村市场活力,让更多人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