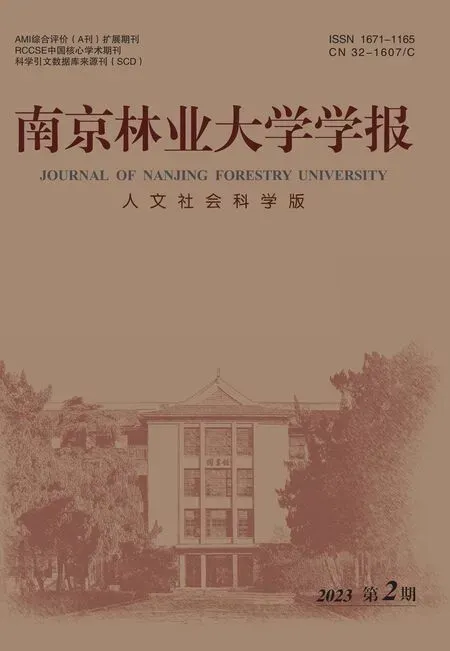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论软约束与全球风险*
卢卡斯·麦尔,马西罗·阿劳杰 著,杨通进 译
(1.格拉茨大学;2.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3.广西大学)
本文将考察用于应对2020 年新冠疫情的措施,把它作为评估气候控制目标之可行性的模型。评估这种可行性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考察人类在以往面临类似挑战时是如何采取那些取得不同程度之成功的有效应对措施的。正如杰瓦尔和契尔普指出的那样:“判断政治可行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诉诸历史案例。”①Jewell,Jessica,and Aleh Cherp.2019.“On the 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Pathways: Is it Too Late to Keep Warming Below 1.5°C?”WIREs Clim Change 11:e621.(doi:10.1002/wcc.621),p8.这种进路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人类从未遭遇过像危险的气候变化这样的事件。但是,近来人类的处境发生了显著变化。2020年,人类见证了一项独特的事件——新冠疫情,对该事件的独特应对方式使得它成为评估气候政策目标之可行性的重要模型。
新冠病毒的出现带来了一种严重的全球危机,因为所有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公民社团都不得不采取某些极端的措施来限制新冠病毒的扩散。这些措施在过去几十年是前所未有的,它们非常类似于人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的措施。例如,2020年3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我们处于战时状态。”①Emmanuel Macron:“Nous sommes en guerre”.Paris,16 March 2020.在3月22日的一次媒体会议上,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处于真正意义上的战争状态。”②The White House.2020.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Vice President Pence,and Members of th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in Press Briefing.Washington,22 March 2020.在随后的几个月,把抗击新冠类比为一场世界大战的说法充斥于各大媒体。
为了抑制疫情,各国不得不对某些非常敏感和十分重要、涉及人们自由和权利的社会生活加以干预,例如,迁徙和集会的自由,隐私权和教育权,以及人们开展业务和服务消费者的权利(比如,要求消费者提供个人信息以便追踪疫情,实施隔离措施,或强制佩戴口罩)。疫情期间,国家还引入特殊的法规来约束人们对食物、药品、健康保健等稀缺资源的获取。国家采取类似措施禁止航空公司的长途航班,而这又间接导致了——即使是暂时的——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降低。③Le Quéré,C.,R.B.Jackson,M.W.Jones,et al.2020.“Temporary Reduction in Daily Global CO2 Emissions During the COVID-19 Forced Confinement.”Nat.Clim.Chang.10:647-653.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严峻的气候变化将在未来几十年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影响,而这些影响确实可能比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更加有害,但是各国政府和公民社团没有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而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悖论呢?
有人可能会说,与抑制新冠疫情的传播相比,人类(比如在2020年)还有更多的时间来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适应未来的气候变化。然而,正如我们想在本文表明的那样,这种假设是误导人的。鉴于每一种威胁都存在着相应的时间约束因素,采取紧急措施是必要的,不管是为了抑制流行病还是为了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人们可能还会认为,流行病带来的后果比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更为明显,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可以基于每天的数据而得到准确的统计(参见Worldmeter的世界实时统计数据)。但是,气候变化导致的致命后果也已经变得相当明显。例如,2003年欧洲发生的热浪夺去了7万多人的生命。④Robine,Jean-Marie et al.2008.“Death Toll Exceeded 70,000 in Europe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3.”C. R. Biologies 331:171-178.根据2019年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在未来几十年中,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预计会更高。⑤WMO(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2020.Statement on the State of the Global Climate in 2019.Geneva:WMO.即便据估计气候变化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会远远高于目前新冠疫情导致的死亡人数⑥Watts,Nick.2019.“The 2019 report of The Lancet Countdown on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Ensuring That the Health of a Child Born Today is Not Defined by a Changing Climate.”Lancet 394:1836-78.,人们对气候变化也没有采取应对2020年瘟疫的类似措施。因此,上述悖论依旧存在。
为了化解这一悖论,我们试图对“硬约束”(hard constraints)与“软约束”(soft constraints)作一下区分,而这种区分在关于政治可行性的哲学争论中很常见。⑦Gilabert,Pablo and Holly Lawford-Smith.2012.“Political Feasibility: A Conceptual Exploration.”Political Studies 60:809-825.(doi: 10.1111/j.1467-9248.2011.00936.x).Lawford-Smith,Holly.2013.“Understanding Political Feasibility.”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1(3):243-259.Brennan,Geoffrey,and Geoffrey Sayre-McCord.2016.“Do Normative Facts Matter…to What is Feasible?”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33(1/2):434-456.我们认为,为了能够同时成功应对流行病(不仅仅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和危险的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人类需要采取减缓与适应并重的措施。我们将首先区分两种非常难以克服的软约束——我们称之为“结构性约束”(structural constraints)(或“缔约政治约束”)和“亲密关系约束”(proximity constraints),然后指出,那些妨碍气候变化控制目标之实现的软约束(一方面)与那些妨碍疫情防控医疗政策之成功实施的软约束(另一方面)具有不同的弹性(malleability)。我们的分析表明,防范气候危机所面临的障碍更加难以克服。人类如果想把一个安全而舒适的地球留给子孙后代,那么,目前面临的关键问题可能是如何克服跨国层面和代际层面的结构性约束与亲密关系约束。不过,我们只能把克服这些软约束的希望寄托给年轻的一代,即在后疫情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
一、硬约束与软约束
在解释了硬约束与软约束之间的差别后,我们将讨论和分析“结构性约束”与“亲密关系约束”,并说明这些约束因素如何阻碍了应对瘟疫和气候变化危机之减缓措施与适应措施的实施。在下一节,我们将说明为什么这些约束因素在疫情防控中具有更大的弹性。
硬约束和软约束具有不同的性质。如果一个或者多个行为者以G为目标,那么可能会存在两类阻碍他们去实现目标G的障碍。其中一些障碍不能通过社会政策、制度设计或人类决策来克服,因为这些障碍或是根植于逻辑原则和自然法则之中,或是依赖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例如,人类可以通过制定社会政策来促进碳汇的发展(目标G),但是,决定光合作用或海洋盐度这类现象的化学定律,是通过制定政策也改变不了的。因此,这些化学定律就构成了影响目标G之实现可行性的“硬约束”。如果至少有一个硬约束阻碍了G,那么追问实现G有多困难就没有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G根本无法实现。就硬约束而言,实现G要么可行,要么不可行。因此,硬约束给G的可行性施加的是二进制值(而非标量值)的限制。
但是,即使没有硬约束的阻碍,软约束也可能成为G实现的障碍。尽管硬约束隐含在诸如自然法则和逻辑定律等因素中,但是,软约束却来源于社会的和人类心理的某些因素。不同于硬约束,软约束具有弹性:行动者能否成功实现G,或取决于他们克服社会文化、经济、法律、地缘政治等制约因素的能力,或取决于他们改变那些妨碍G实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软约束给G的可行性施加了一个标量值。因此,在不存在硬约束的情况下,某些目标会比其他目标更具可行性。
当我们把一种约束称为“软约束”时,这并不是说它很容易被克服,而只是说它具有弹性。当我们说钢具有弹性时,这并不意味着它很容易被扭曲,而只是说,当其暴露在适当的热量和压力下时,它就可以被锻造成人类用来(以多种方式)改造其环境的仪器和工具。软约束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有时也相当难以改变。它们塑造了国内的和跨国的政治生活。它使得行动者只能采取某些将会妨碍其他人追求目标的措施,或使行动者倾向于选择某些在危机时期将会伤害其他人的公共政策。对全球关注的那些问题——诸如气候控制目标(简称CG)和流行病控制目标(简称PG)——的成功解决(或失败,正如目前的形势所表明的那样)来说,这些软约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2020年,我们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有效控制新冠疫情的健康政策在未来3到4年内不会遇到可行性方面的硬约束;用于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这一目标的气候政策在未来30年内也不会遇到可行性方面的硬约束。因此,这样的问题就出现了,即哪些软约束阻碍了这两组目标(CG 和PG)的实现,这些软约束的弹性如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了解经常出现在气候争论中的一种区分,而目前在关于新冠疫情的争论中,这种区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即适应措施和减缓措施之间的区分。因此,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两组目标(PG和CG)和四个子目标,如表1所示。

表1 两级目标(PG和CG)和4个子目标
四个子目标描述如下:
子目标1:流行病控制目标中的适应目标(P-A);
子目标2:流行病控制目标中的减缓目标(P-M);
子目标3:气候控制目标中的适应目标(C-A);
子目标4:气候控制目标中的减缓目标(C-M)。
一些软约束可出现在多个子目标甚至全部子目标中。以2020 年的新冠疫情为例,政府就必须克服来自法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软约束。这些都属于P-A子目标的软约束,因为在2020年,政府的主要目标不是降低某种新的或未来的流行病的发生率,而是适应已经存在的新冠疫情。为了遏制新冠疫情的蔓延,各国政府不得不实施许多临时限制措施,比如限制航空旅行和迁徙自由。在出现健康危机的这段时期,各国政府还不得不调整财政预算,以保护无法开工的企业和员工。目前,为了有效实现气候控制目标(子目标C-A 和C-M),政府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克服类似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约束;这些措施不像追求子目标P-A那样是暂时性的,而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甚至可能是无限期——都会实施的。正如我们稍后将更详细予以说明的那样,国际社会为应对由流行病暴发所造成的未来健康风险(子目标P-A)而准备采取的那些措施,也会迫使各国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采取各种措施来克服类似的法律、政治和经济软约束。但另一方面,某些软约束只会出现在某个特定的子目标中。子目标C-M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子目标C-M的可行性取决于跨国层面和代际层面的合作。这就要求相关的行为者具备一种克服所谓“基于时间的亲密关系约束”(time-related proximity constraints)的能力,这种“基于时间的亲密关系约束”并不妨碍子目标P-A、P-M 或C-A 的实现。
虽然一些软约束可能同时出现在多个子目标中,但在不同的子目标中,它们的弹性通常是不同的。例如,某个软约束可能更具弹性,因为相关行为者认为他们必须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克服这些约束因素,如果超出了这个时间范围,社会将会退回到以前的危机状态,而软约束的弹性程度也恢复到过去。我们将使用“弹性”一词来指软约束的这样一种属性:根据它们在子目标中出现的频率,相关行为者经过努力能够克服它们,无论是在短时间内还是无限期内。我们想在本文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确认出现在每一个子目标中的主要的软约束。就本文的目标而言,我们并不断言已经确认了所有相关的软约束(存在着数十种软约束);我们仅仅是指出了对气候控制目标与疫情控制目标之实现来说最重要的那些软约束。我们将关注两种最重要的软约束:“结构性约束”(或地缘政治约束)与我们所说的“亲密关系约束”。我们区分了两类亲密关系约束:“基于空间的亲密关系约束”(space-related proximity constraints)和“基于时间的亲密关系约束”。我们想在本文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某个软约束对某个子目标(P-A)的实现具有更大的弹性,而对其他子目标(P-M、C-A以及C-M)的实现具有较小的弹性。相关的行动者不想承受长时期的牺牲,这并不是使得某个约束变得具有更大弹性的唯一相关因素。我们认为,结构性约束与基于时间的亲密关系约束是最难以改变的(它们的弹性不高)。
二、减缓与适应的目标
瘟疫不同于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像气候变化一样,瘟疫的出现有人为的原因。例如,众所周知,非法的农贸市场会导致病毒的扩散,从而导致瘟疫的暴发。野生动物贸易以及通过毁林(或森林的碎片化)而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侵蚀也会把病原体从野生动物扩散到人类,从而引发瘟疫。亲民的航空旅行价格以及跨境人员流动的增加,也十分有利于新病毒的快速扩散。①Dobson,Andrew P.,Stuart L.Pimm,Lee Hannah,et al.2020.“Ecology and Economics for Pandemic Prevention:Investments to Prevent Tropical Deforestation and to Limit Wildlife Trade Will Protect Against Future Zoonosis Outbreaks.”Science 369(6502): 379-381(10.1126/science.abc3189).Tollefson,Jeff.2020.“Why Deforestation and Extinctions Make Pandemics More Likely.”Nature 584(7820): 175-76.Lindahl,Johanna F,and Grace,Delia.2015.“The Consequences of Human Actions on Risks for Infectious Diseases:A Review.”Infection Ecology and Epidemiology,5.奥斯特霍姆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曾认为,当代世界尚未准备好如何应对瘟疫——尽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瘟疫发生的频率将越来越频繁。②Osterholm,Michael T.2005.“Preparing for the Next Pandemic.”Foreign Affairs 84(4):24-37.自那时以来,科学共同体与国际协调机构已经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新的瘟疫日益增加的可能性,强调采取合作行动以便在全球层面实现目标P-A和目标P-M的重要性。③Pike,Jamison,Tiffany Bogich,Sarah Elwood,et al.2014.“Economic Optimization of a Global Strategy to Address the Pandemic Threat.”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52): 18519-23.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18. Annual review of diseases prioritized unde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lueprint Informal Consultation.Meeting Report.Geneva: WHO.Coats,Daniel R.(ed.).2019.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January 29.目标P-M致力于防止新的流行病的暴发。即使流行病暴发了,有效的P-M政策也能降低该流行病演化成瘟疫的概率。从这个角度看,应对新冠瘟疫的措施所追求的目标很明显是P-A,而非P-M。这些措施致力于降低已经出现且已在全球扩散的疾病的影响。
实现目标P-A的大多数措施都是地方性的。各州(省)和各个城市有权在其边界内实施追求该目标的政策。目标P-A的实现并不要求紧密的国际合作。例如,实现目标P-A的措施包括紧急状态法的实施、野外医院的建立、追踪社交轨迹、大规模检测、设立隔离区,以及保持社交距离。这些措施一般都是临时性的。接种疫苗也是一种适应措施,因为它的目的主要是调节人的免疫系统以适应新的环境。目前研发疫苗而投入的物力和人力最终在未来可能会间接地有助于目标P-M的实现。当瘟疫最终结束后,要求人们继续接种疫苗的政策也可被理解为一种减缓措施:它防止了未来的瘟疫。因此,政府和公民都有很强的意愿通过克服法律和伦理方面的某些软约束(例如,迁徙的自由,对隐私权被侵犯的关切)或暂时改变其生活方式(如佩戴口罩、避免握手)来追求目标P-A。但是,吊诡的是,当涉及目标P-M时,这些相同的行为体却把类似的软约束视为具有较少的弹性,即使某些研究成果(新冠疫情暴发前已经发表)已经表明,目标P-M的实现比目标P-A的实现所付出的代价更小。①Pike et al 2014.Madhav,Nita,Ben Oppenheim,Mark Gallivan,et.Al.2018.“Pandemics: Risks,Impacts,and Mitigation.”In Disease Control Priorities: Improving Health and Reducing Poverty,edited by Dean T.Jamison,Hellen Gelband,Susan Horton,et al.,315-345.Washington,DC: The World Bank.UN EP.2020. Preventing the next Pandemic: Zoonotic Diseases and How to Break the Chain of Transmission.Nairobi: UNEP(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p7.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看,追求目标P-A的代价本身(与追求目标P-M的代价相比)就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青睐目标P-M,而非目标P-A。从伦理的角度也很容易认识到,目标P-M 应当优先于目标P-A,像2020年新冠疫情这样的巨大流行病所造成的生命损失是很难用成本-收益的计算来衡量或予以补偿的。
气候控制目标的实现也需要采取减缓与适应的措施。目标C-M主要致力于到2030年大幅度降低CO2的排放,到2050年实现全球碳中和。②IPCC.2018. Global Warming of 1.5°C. An IPCC Special Report on the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 of 1.5°C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and related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pathways,in the context of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response to the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efforts to eradicate poverty,edited by V.Masson-Delmotte,P.Zhai,H.-O.Pörtner,D.Roberts et al.In Press.Available at: https://www.ipcc.ch/sr15/.Steininger,Karl W.,Lukas H.Meyer,Stefan Schleicher,Keywan Riahi,Keith Williges,and Florian Maczek.2020.“Effort Sharing Among EU Member States: Green Deal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for 2030.”Wegener Center Research Briefs 2-2020.Wegener Center Verlag,University of Graz,Austria,September 2020.Meyer,Lukas H.2020.“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ummer 2020 Edition),edited by Edward N.Zalta.Available at: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20/entries/justice-intergenerational.目标C-M(与目标P-M一样)的实现也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目标C-M的收益(像P-M的收益那样)主要是全球性的。但是,目标C-M的积极影响要经过几十年才会体现出来。③Samset,B.H.,J.S.Fuglestvedt,M.T.Lund.2020.“Delayed Emergence of a Global Temperature Response After Emission Mitigation.”Nature Communications(11):3261(doi:10.1038/s41467-020-17001-1).当下的一代人,特别是那些40岁或更老的人,不可能指望在其有生之年能够从他们对目标C-M的追求中获得多大好处。因此,目标C-M的有效实现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以及紧密的跨代或代际合作。同时,像目标P-A 一样,目标C-A能够在地方层面并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有效实现。目标C-A致力于,例如,重建城市的基础设施,以便它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极端气候;用混凝土而非木材来建造房屋,以使它们不易受到丛林大火的威胁。目标C-A不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但是,目标C-A的长远效果最终取决于目标C-M 的成功。没有C-M 的C-A 最终将以失败告终。如果到2070 年海平面平均升高1 m,或到21世纪末上升超过2 m,那么,那些生活在海岸地区的许多国家人民很可能缺乏实施有效适应措施的经济实力。①Bamber,Jonathan L.,Michael Oppenheimer,Robert E.Kopp,Willy P.Aspinall,and Roger M.Cooke.2019.“Ice Sheet Contributions to Future Sea-Level Rise from Structured Expert Judgment.”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23):11195-11200.在这些国家,人们的唯一出路是选择撤离海岸地区。
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许多软约束——它们同样妨碍气候目标的实现——得到了有效克服,间接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大量减少。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相比于目标P-M、C-A和P-M遇到的软约束,目标P-A遇到的软约束具有更大的弹性。理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理论假设是,一个目标的实现越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与代际合作,那么,该目标的实现所遇到软约束的弹性就越小(表2)。

表2 理论假设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目标C-A的实现既不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也不需要紧密的代际合作,但是其长远效果的实现需要以目标C-M的实现为前提,而目标C-M的实现又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与紧密的代际合作。人们可能会争辩说,目标P-A的有效实现也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即使它不需要紧密的代际合作。毕竟,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国家都能在没有其他国家之帮助的情况下研发出新冠疫苗。然而,我们至少能够设想三种情形,在其中,一个国家无须借助于紧密的国际合作而能够有效地实现目标P-A。
情形1:一个国家(或一个规模较小的国家联盟)在研发有效疫苗方面确实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且只有在其国家的所有人都接种该疫苗(且在其领土内储存了数百万剂疫苗以备未来之需)后才同意与其他国家分享其疫苗。
情形2:一个国家(或一个规模较小的国家联盟)未能成功地研发出有效疫苗,但是,它是如此的富有,以至于在那些疫苗被分配给贫穷国家之前,它能够与医药公司进行谈判从而可以排他性地获得那些疫苗。
情形1与情形2是人们广为熟知的“疫苗民族主义”的例证。②Kupferschmidt,Kai.2020.“`Vaccine nationalism'Threatens Global Plan to Distribute COVID-19 Shots Fairly.”Science,28 July.Brown,Gordon,and Daniel Susskind.2020.“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36(Supplement 1): S64-76.Callaway,Ewen.2020.“The Unequal Scramble for Coronavirus Vaccines -By the Numbers.Wealthy Countries Have Already Pre-Ordered More Than Two Billion Doses.”Nature 584(7822):506-7.
情形3:一个国家既无力研发出自己所需的疫苗,也没有足够的金融资源与医药公司进行谈判从而排他性地获得疫苗的供应。于是,这个国家封闭其边界,强制实施行程追踪与封闭隔离等措施。在实施这些措施的过程中,数千公民因缺乏疫苗和治疗而死亡,但是,剩余的人口最终对病毒形成免疫,或者不再遭受病毒的侵袭,因为该国的边界永久性地关闭了(作为预防在未来再次出现健康危机的一项措施)。
在情形3中,一个国家可能会面临经济停滞的局面,失去与其他国家进行紧密科研合作或成为文化伙伴的机会。当然,目前,通过紧密的国际合作,目标P-A在全球层面将能够更有效地得到实现,但是,这并不需要紧密的代际合作。另一方面,任何国家都不能通过封闭其边界来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或通过实现目标C-A来完全避免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为了应对危险的气候变化,人类同时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与紧密的代际合作。
那么,对实现紧密的国际合作与紧密的代际合作而言,什么是最明显的软约束?我们认为,对气候控制目标与流行病控制目标的实现来说,最难以克服的软约束是结构性(或地缘政治)软约束与亲密关系软约束。正如我们想证明的那样,亲密关系约束是比结构性约束更难以克服的。
三、结构性软约束与国家体系
国家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一种结构,在其中,各民族国家在全球层面不能够依赖存在于典型的民族国家内部的那类执法和司法机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政府的缺失必然会妨碍国家与国际机构之间在一系列领域中的相互合作。民族国家与国际机构会通过外交、贸易、国际规制、学术合作、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其他合作项目实现互利。例如,可以回想一下20世纪70年代消灭天花病的国际努力。该努力见证了人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该事例中是10年)实现跨国合作的能力。同样,小儿麻痹症的消灭也常常被当作“国际合作与预防医学的一个胜利”来加以称道①Henderson,D.A.1980.“A Victory for All Mankind.”The World Health(The Magazine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May:3-5,p.5.,也被当作“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伟大的国际合作”②Barrett,Scott.2016.“Coordination vs.Voluntarism and Enforcement in Sustain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PNA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13(51):14515-14522,p.14519.加以称赞。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些学者认为,对这些努力的成功而言,诸如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这些有时被称为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之支持者的学者看来,民族国家并不是国际领域中唯一的相关行为体,世界政府的缺失所导致的结构性软约束并未排除国际合作的可能性。③Keohane,Robert.1984.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Weiss,Thomas G.2013.Global Governance:Why?What?Whither?.Cambridge:Polity Press.
自由制度主义的支持者能够解释消灭小儿麻痹症这类工程的成功以及外交与人道主义援助这类机制的持续存在。但是,现有的国际制度尚不能阻止新冠演变成一种重要的流行病,迄今也没有国际制度能够阻止过去几十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支持者会倾向于认为,制度约束的弹性比自由制度主义支持者所主张的要低得多。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主要的(即使不是唯一的)相关行为体。就某些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言,一个国家要想确保其内部的安全,就只能依赖自助,而非国际制度。现实主义的著名支持者瓦尔茨对这一问题作了如下的著名表述:“国家体系不是一个自助体系,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①Waltz,Kenneth.1979.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104.被理解为主权政治实体的每一个国家最终都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一名现实主义者对缺乏紧密的国际合作来追求目标P-M 和(特别是)目标C-M的解释是,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的安全,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在短期内的经济发展看得比(从长远的角度看)预防流行病与气候变暖更重要。证明这一观点的一个理由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减缓气候变化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而有效实现目标C-M的代价却是众所周知的奇高——高到阻止经济增长,破坏国内的稳定。②Nordgren,Anders.2016.“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lf-Interest.”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Ethics 29:1043-1055,p.1045.Symons,Jonathan.2018.“Realist Climate Ethics:Promoting Climate Ambition Within the Classical Realist Tradi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5(1):141-60,p.5.Mearsheimer,John.2001.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p.371.这一问题因博弈论的这一洞见而变得更为复杂:今天,对于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国家来说——从它们自身的角度来单独考虑——如果它能够享受(由其他国家的努力所实现的)紧密的国际合作的好处,而它自己又无需承担追求目标C-M的代价,那么,这对它来说是最好的。③Nordgren,Anders.2016,p.1047.
当然,自由制度主义的倡导者也不否认,国家行为常常反映的是利己主义的自保的逻辑与国家福利的最大化逻辑(无论怎么理解自保与国家福利的含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学派——现实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都承认,结构性约束可以解释国际舞台中的国家行为。但是,自由制度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由于国家不是国际舞台唯一的相关行为体,因而,结构性约束常常能够被外交措施、国际制度与非政府行为体等因素所克服。然而,在现实主义的支持者看来,结构性约束的解释力比自由制度主义的支持者所愿意承认的要更为有力。现实主义者认为,结构性约束解释了国家在过去是如何行动的,例如,国家为什么把经济增长看得比实现目前的气候控制目标更为重要;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人们会期待国家在未来采取哪些行动。现实主义的某些支持者还提出了更为激进的看法,认为现实主义不仅能够解释国家的行为,而且还能够告诉国家,在一个缺乏全球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在为生存而斗争时应采取哪些行动。米尔斯海默把这类现实主义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
进攻性现实主义解释了,大国在过去是如何行动的,它们在将来可能会采取哪些行动。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是一种规范理论。国家应当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指令而行动,因为它指出了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的最佳生存之路。④Mearsheimer,John.2001,p.11.
结构性约束看似合理地解释了国家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的行为。大多数国家能迅速采取极端措施来控制新冠病毒传播(目标P-A),却迟迟不采取行动实现目标P-M 的原因在于,它们主要关心的是新冠流行在其国界内所带来的影响。面对重大的危机,国家必须要依靠自助(而非国际制度)来维护国内的稳定。在关键时刻,国家是唯一拥有合法权利来实施这类措施的行为体:例如,禁止飞机长途航运、强制封城并隔离其民众、实施临时措施限制迁徙自由与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国际机构可以提供有益的建议,但是,它们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合法性在民族国家层面实施并协调有效实现目标P-A的措施。出于论证的需要,让我们暂时假定,这是对国家在重大健康危机期间所采取的行动之理由的合理描述。那么,我们能否据此得出如下结论:在面临未来的全球危机时,国家也应当在我们所描述的结构性约束的范围内采取行动?
从国家在过去已经采取了某些行为模式这一事实,我们肯定不能推导出这一结论:国家在未来应当固守这些行为模式。现实主义的支持者把国内的稳定看得比紧密的国际合作更重要,因为他们把为了权力的斗争视为在一个缺乏全球中央政府的世界中的唯一生存之道。正如米尔斯海默在对现实主义的较有影响的辩护中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表述那样:“……我提出的理论认为,大国主要关心的是,在一个没有任何机构为其提供保护的世界中如何生存;这些大国很快意识到,权力是它们能够生存的关键筹码。”①Mearsheimer,John.2001,p.20.在这种情形——在其中,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是其他国家的存在——下,这种解释看起来是可信的。但是,在面对流行病出现的频率日益增加与危险的气候变化日益明显这类威胁时,这种解释还有吸引力吗?米尔斯海默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捍卫基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这一假设,但是,由气候变化与未来流行病带来的那类威胁是不能通过采取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措施来加以解决的,因为,这类威胁的性质决定了,没有紧密的国际合作,它们就无法得到解决。尽管在2020年全球健康危机暴发初期,各国首领都使用了战时动员的口号,但是,很明显,气候变化与流行病——仅仅指出两个明显的全球威胁——代表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敌人。在20 世纪60 年代早期,摩根索等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者似乎已经认识到,国家体系完全无法应对那些带来全球风险的威胁,这类威胁只能通过采取紧密的国际合作措施——这类措施需要几乎所有的国家尤其是最强大的国家的参与——才能予以解决。在出现第一次热核炸弹试验时,他就写道:
现代技术使民族国家变得过时。因为民族国家已不能发挥它作为一个政治机构的基本功能,即保护其成员的生命与生活方式。……在前-原子武器时代的技术条件下,比较强大的国家还能够建立起(如果它愿意)保护之墙,在这个保护墙内,其公民能够生活在安全之中,比较弱小的国家只能通过大国权力的平衡才能得到保护,这进一步增加了强国控制弱国的机会。
交通、通讯与战争的现代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毁灭一切的原子弹战争的可能性,完全摧毁了民族国家的这种保护功能。面对毁灭一切的原子弹的攻击,没有哪个民族国家能够保护自己的公民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它的安全只能依赖于防止这类灾难的发生。②Morgenthau,H.1966.“Introduction.”In A Working Peace System,edited by D.Mitrany,7-11.Chicago: Quadrangle Books,p.9.
摩根索所担心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比我们面临的气候变化困境更为乐观,因为国家并未处于通过有效禁用核武器来避免核战争发生的时间约束压力之下。在相互威胁信条的引导下,核大国至少在原则上能够无限期地拥有其核武库,并承诺只有在对核攻击实施报复时才使用它们。因此,在这里,相关的时间约束并不是如何避免一场核战争,而是如何对核攻击作出回应。如果一个核大国有理由相信,它正处于被核武器攻击的边缘,那它就得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做出是否实施核报复的决定。因此,重大的核冲突只有在出现非常紧迫的时间约束和糟糕的报复证据的情况下才会发生。①Cirincione,Joseph.2008.“The Continuing Threat of Nuclear War.”In 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edited by Nick Bostrom and Milan M.Cirkovic,381-40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83-384.另一方面,应对当前的气候控制目标的时间约束也相当紧迫。但是,迅速采取行动以避免危险气候变化的理由并不是基于糟糕的证据。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拖延实施有效实现目标C-M的措施,只能急剧增加应对危险气候变化的成本,包括人力成本。②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2014. Climate Change 2014: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Cambridge,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2.因此,我们不能指望通过简单地遵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教条去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
当然,结构性约束,尤其是现实主义的支持者所设想的那类结构性约束,仍是有效实施气候应对政策的最严重的障碍之一。不过,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结构性约束并不是硬约束,正如自由制度主义的支持者在过去的几十年所强调的那样。结构性约束因条件的改变而变化。正如后文将指出的那样,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在后疫情时代,结构性约束将比目前变得更具弹性。
四、亲密关系约束与后代人的权益
对气候与疫情控制目标的有效实现而言,还存在其他一些因素导致了难以克服的软约束的出现。一些人对自己国家毫无条件地支持(甚至在自己国家的行动损害了其他国家之公民的利益的情况下)很容易阻碍紧密的国际合作的出现。另一方面,人们有时倾向于青睐他们自己这一代人(不管他们是否是自己本国的同胞)的利益,而忽视下一代人的利益。有时,人们更青睐其他人的利益,不是因为那些人是其本国同胞或同辈,而是因为那些人与他们共享同一宗教或同一种世界观,或仅仅因为那些人是他们的朋友或家庭成员。这些不同的关系(我们这里只列举了少数几个)派生出了忠诚的纽带,这些纽带(从许多方面看)也许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它们促进了相互的支持,培养了一种团结的情感。但是,这些纽带也常常妨碍紧密的国际合作与紧密的代际合作。我们称这些关系为“亲密关系约束”。
亲密关系约束使得行为者偏袒那些他们与其关系较近的人的福利。亲密关系约束影响着处于不同时空中的行为者的行为。这种约束的空间维度是相对较为明显的:我们倾向于关心那些在空间上离我们较近的人的利益。但是,为了避免导致混乱,有必要更为详细地弄清亲密关系约束的空间维度。人们可能觉得某人或某些人与他们较为亲近,但是,这并不是严格的空间距离上的相近。例如,朋友与家庭成员或许相信他们对彼此负有特殊的义务,即使他们相隔数千英里。亲密关系约束常常起源于物理空间意义上的相近。但是,它们所生发出的义务感与忠诚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分离、祖辈的移民或历史上的大迁徙后仍能保持不变。我们这里所说的基于空间的亲密关系约束指的是想象中的亲密关系或亲密感,而非实际的或空间上的相近。
基于空间的亲密关系约束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民族主义。亨利·苏把这种特定类型的软约束称为“同胞优先原则”①Shue,H.1980. Basic Rights: Subsistence,Affluence,and U.S. Foreign Polic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131-132.。近来,这种态度也被称为“吾国优先”进路。②Brown and Susskind 2020,S68.Contractor,Farok J.2017.“Global Leadership in an Era of Growing Nationalism,Protectionism,and Anti-Globalization.”Rutgers Business Review 2(2):163-85.在重大的健康危机期间,一个国家能够通过采取一些强制措施,例如禁止那些优先保护其家人和朋友的公民囤积生活必需品,在国内层面克服某些基于空间的亲密关系约束。但是,要阻止各个国家保护其人民的利益(哪怕这种保护会损害其他国家的人民)却要困难得多。在2020年疫情期间,各个国家都没有克服民族主义,因为这种特定的基于空间的亲密关系约束有利于各国的P-A目标的实现。民族主义使某些国家在疫情期间(为了确保国内的安全)采取的禁止食品与医疗设施出口的政策具有了合理性。例如,美国政府就被指责非法拦截了提供给欧洲的(护理人员使用的)一些防护设备——借口是为了保护其自己的人民。早在新冠疫苗未被证明为有效与安全之间,某些分析家就已经警告说,疫苗民族主义会延缓世界人口的免疫进程,因为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可能会试图囤积疫苗,或为了优先使其人民获益而控制疫苗原料的供应,哪怕是以其他国家之人民不能获得疫苗为代价。③Bollyky,Thomas J.,and Chad P.Bown.2020.“The Tragedy of Vaccine Nationalism.Only Cooperation Can End the Pandemic.”Foreign Affairs,July 27.Kupferschmidt,Kai.2020.Brown and Susskind 2020.民族主义这类亲密关系约束不仅没有阻碍,反而促进了目标P-A(可能还有目标C-A)的实现。但是,从长远来看,针对流行病和气候危机所采取的适应措施将是无益的,甚至是代价高昂的——如果不同时对流行病和气候危机分别采取减缓措施的话。但是,针对流行病实施的减缓措施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而针对气候危机采取的减缓措施却同时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与代际合作。这要求我们审视亲密关系约束的时间维度。
亲密关系约束的时间维度可能没有空间维度那么显而易见。但是,在评估气候控制目标的可行性时,它却更为紧迫:与那些在时间上距离我们较为遥远的后代人的利益相比,我们倾向于看重那些在时间上距离我们较近的人的利益;与我们未来的更为重要的利益相比,我们有时甚至倾向于看重我们的短期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非-相互性”的性质决定了当代人能够影响后代人的生活条件,但是,后代人却无法影响当代人的福利。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这种力量的不平等导致了加丁纳所恰当地称呼的“当代人的暴政”④Gardiner,Stephen.2011.A Perfect Moral Stor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43-184.。
然而,就当今的一代人而言,这种暴政仅仅是表面的,而且把这种不平等关系称为暴政是相当误导人的,因为后代人的出现本身就取决于逝去的上一代人所实施的那些行动。斯切华茨和帕菲特是较早注意到这类悖论的哲学家。①Parfit,D.,1976.“On Doing the Best for Our Children.”In Ethics and Population,edited by M.D.Bayles,100-115.Cambridge,Mass.: 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Parfit,D.,1984. Reasons and Persons.Oxford: Clarendon Press,p.351-390.Schwartz,Thomas.1978.“Obligations to Posterity.”In Obligations to Future Generations,edited by R.I.Siroka and Brian Barry,3-13.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代际关系是一种悖论,理由在于,后代人或许想责备上一代人(目前的一代),因为后者采取的一些行动损害了后代人,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没有上一代人的那些行动,那么,未来的一代人就不会以他们所表现的特定身份出现。上一代人所采取的不同的行动将会导致另一批不同的后代人的出现,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特定的行动,后者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可能就永远不会遇到对方,这些特定的后代人就可能不会出现。斯切华茨称这种悖论为“受益人-合并谬误”(fallacy of beneficiary-conflation)②Schwartz 1978,p.7.。不过,该悖论目前更为流行的名称是“非同一性问题”③Parfit 1984,p.359.。关于非同一性问题的哲学文献相当丰富,而关于伤害的阈值概念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成功的回应。④Shiffrin,Sheana.1999,“Wrongful Life,Procreative Responsibility,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arm.”Legal Theory 5(2):117-48.Meyer,Lukas H.2003,“Past and Future.The Case for a Threshold Conception of Harm.”In Rights,Culture,and the Law. Themes from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oseph Raz,edited by Lukas H.Meyer,Stanley L.Paulson,Thomas W.Pogge(eds.),143-59.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Meyer 2020.另外,基于权利的利益论⑤Raz,Joseph.1994.“Rights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In Ethics in the Public Domain: Essays in the Morality of Law and Politics,Oxford: Clarendon Press,p.45-51.Kramer,Matthew H.1998.“Rights Without Trimmings.”In A Debate over Rights,edited by Matthew H.Kramer,Nigel E.Simmonds,and Hillel Steiner,7-111.Oxford: Clarendon Press,p.60-101.,后代人可以拥有针对当代人的权利。能够行使自己的权利(要求或放弃某种权利的强制实施),既不是一个人能够成为权利拥有者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其必要条件。⑥Meyer 2020.例如,我们能够把权利赋予那些无法要求其利益和需要得到满足的人,诸如婴儿、智障人士,甚至非人类动物。我们把权利赋予他们是基于这一理由:他们能够感受痛苦,他们拥有利益、基本需求或某些能力;我们正是基于这些理由而把类似的权利赋予目前活着的人。目前,在规范理论家与决策者之间的一个广泛共识是,怀疑后代人针对当代人之要求权的道德合理性是站不住脚的。2014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评估报告也承认,这些理论问题已经得到妥善解决。⑦Working Group III 2014,p.215-218
就此而言,有人可能会同意未来的人拥有针对当代人的道德要求权的观点。但是,也有人可能会认为,由于存在时间上的距离,我们对后代人的关心不如我们对当代活着的人的关心那么重要。⑧Nordgren 2016,p.1047.还有人会补充说,未来世代在时间上距离我们越遥远,其针对我们的道德要求力量就越弱。然而,这些论点合理吗?道德要求权的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弱吗?正如拉姆西(Frank Ramsey)在近百年前指出的那样,对后代人利益的麻木不仁“在伦理上是站不住脚的,来源于想象力的贫乏”①Ramsey,Frank.1928.“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s.”The Economic Journal 38(152):543-559,p.543.。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令人信服地指出:
从普遍的观点看,一个人存在的时间位置并不会影响到他幸福的价值;而一个功利主义者必须要像关心其同代人的利益那样关心后代人的利益,除非当代人的行为对后代人的影响(甚至对后代人之出现的影响)是非常不确定的。②Sidgwick,Henry.1981[1907].The Methods of Ethics,7th ed.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p.414.
如西季威克那样,一个人并非要接受功利主义才能认识到,对后代人福祉的道德关怀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的那样,“某件事情发生得或迟或早这种仅仅存在于时间位置上的差别,自身并不构成对它应给予或多或少的重视的合理依据”③Rawls,John.1971.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293.【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修订本),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p.23。译注】。认为后代人的利益与需求因时间距离的遥远而变得不太重要的观点,与那种认为(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或者自己国家内的)穷人的利益因为地理位置的遥远而变得不太重要的观点一样都是武断的。事实上,当代人应关心后代人福祉的理由,与当代人应关心其同代人福祉的理由同样具有说服力。
另一方面,布罗姆、波斯纳与森斯坦等理论家已经指出,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危险的气候变化并不一定是当代人的纯粹负担。④Broome,John.2018.“Efficiency and Future Generations.”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34(2):221-241.Posner,Eric A.,and Cass R.Sunstein.2008.“Climate Change Justice.”Georgetown Law Journal 96(5):1565-1612他们认为,目标C-M能够以一种普世帕累托最优的方式来实现,以至于当代人能够把实现目标C-M的成本转移给后代人,而每个人的处境会因此变得更好。然而,正如一些理论家指出的那样,这种建议从规范⑤Brennan,Geoffrey,and Geoffrey Sayre-McCord.2016.“Do Normative Facts Matter… to What is Feasible?”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33(1/2):434-456,p.440-441.、理论⑥Kelleher,J.Paul.2015.“Is There a Sacrifice-Free Solution to Climate Change?”Ethics,Policy &Environment 18(1):68-78,p.75-77.与实践⑦Caney,Simon.2014.“Two Kinds of Climate Justice: Avoiding Harm and Sharing Burdens.”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22(2):125-149,p.133-134.的角度看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气候控制目标的可行性取决于我们解决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上的亲密关系软约束的能力。尽管从目前看来,这些软约束非常难以克服。
五、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风险
有些软约束可能非常难以克服,但它们的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软约束是“时间-敏感”的。正如吉拉伯特和劳福德史密斯对这一问题的表述那样:“改变或消解这些软约束是可能的,以至于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它们不再是约束。”⑧Gilabert,Pablo and Holly Lawford-Smith.2012.“Political Feasibility: A Conceptual Exploration.”Political Studies 60:809-825.(doi:10.1111/j.1467-9248.2011.00936.x),p.814.鉴于2020年的流行病所带来的空前的人力与经济成本,以及流行病在未来再次暴发的可能性,难道我们不期待这些结构性的与亲密关系的约束(它们是我们实现气候与流行病控制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后疫情时代能够被消解或至少变得不那么难以解决吗?关于全球风险的未来展望,我们这里仅提出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尽管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约束与基于空间的亲密关系约束,目标P-M在未来几年仍将是国际事务的优先事项。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与公民将越来越倾向于克服那些阻碍目标P-M 有效实现的结构性约束与基于空间的亲密关系约束。国际法的历史表明,作为对灾难事故的直接回应,国际社会已经创造了某些重要的立法框架。例如,切尔诺贝利(1986)与福岛(2011)这类核事故已促使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和某些国家修改了安全使用核能的国内立法与国际协议。①IAEA(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2006. International Nuclear Law in the Post-Chernobyl Period(A Joint Report by the OECD Nuclear Energy Agency and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Paris: OECD,p.76.Stephens,Tim.2016.“Disasters,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the Anthropocene.”In Research Handbook on Disasters and International Law,edited by Susan C.Breau,and Katja L.H.Samuel,153-76.Cheltenham:Edward Elgar Publishing,p.167.Gioia,Andrea.2012.“Nuclear Accidents and International Law.”In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Law,edited by A.de Guttry,M.Gestri,and Venturini,85-102.The Hague(The Netherlands): Springer,p.100.Tromans,Stephen.2010. Nuclear Law: The Law Applying to Nuclear Installations and Radioactive Substances in its Historic Context.London:Bloomsbury Publishing,p.253.第二个假设是,为预防其他流行病而日益增加的国际合作可能会导致国际社会采取越来越多的国际措施,以应对由危险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我们将更为详细地对这些假设作出说明,并就一些针对上述假设的反对意见作出回应。
那些生活在假想国A且距离国家B相当遥远的人民,可能愿意为国家B的公民提供一笔费用,以帮助后者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病毒在国家B扩散甚至演变成流行病的可能性。这笔费用将由第三方来管理,事实上诸如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第三方机构已经存在。国家A的公民必须采取行动帮助国家B 的理由很清楚:他们或许不关心国家B 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并未感觉到自己与国家B是近邻,但是会非常关心自己国家发生了什么。因此,即使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现实主义者可能也会支持紧密的国际合作,并承认,就预防未来的流行病而言,国家边界(虽然对于阻挡敌人很重要)似乎帮助不大。国家边界并没有阻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一个明确接受现实主义教义、狂热认可“吾国优先”理论的总统的领导下)成为新冠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事实上,该国死于新冠流行病的人数比1945 年遭受原子弹袭击的广岛与长崎死亡的人数还多。在美国,仅2020年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比在海湾战争(1990—1991)、阿富汗战争(2001—2021)和伊拉克战争(2003—2011)中死亡的美军士兵的总数还多。只要有一个被感染的同胞将病毒携带回国,那么,一种新的疾病就会在整个国家蔓延。如果健康机构能够快速查明问题,关闭边界可能会减缓新冠感染人数的增加,但很难在第一时间阻止该病毒传入该国。早在2016年美国国家医学院(美国的一个非政府机构)发表的一份报告就对这一问题做了总结:“流行病不知道边界,因此,国际合作非常关键。全球健康安全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需要采取共同行动来提供。”①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2016. The Neglected Dimension of Global Security: A Framework to Counter Infectious Disease Crises.Washington,DC: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p.4.
对2020 年疫情的亲身感受,可能会使公民与决策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基于空间的亲密关系约束与结构性约束的力量,尤其是,如果公众能够更为深切地意识到,科学家、研究机构与国际组织多年来就一直在警告一场重大流行病将会降临。例如,在2016年,美国的情报系统(它负责就全球安全问题向美国参议院提供建议)提供的一份报告就作出如下结论:“国际社会仍未准备好采取集体协调行动,以应对疾病的威胁。”②Clapper,James.2016. 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9 February,p.13-14.2019年初,就在中国报告第一例新冠病毒案例数月前,美国的情报机构就发表了一份关于全球威胁的报告,再次指出国际社会仍然未做好应对新流行病暴发的准备。该机构在这次报告中还强调,气候变化可能会增加新流行病暴发的可能性:
我们估计,美国和世界将难以应对下一场流感或感染性较强的疾病的大规模扩散,这些疾病将导致较高的死亡率与残疾,严重影响世界的经济,消耗国际资源,增加对美国的依赖。虽然国际社会已经做出巨大努力来改善全球健康安全,但是这些努力可能难以成功应对我们预计将会更为频繁出现的传染病的挑战——这些更为频繁地暴发的传染病的出现乃是源于快速而盲目的城市化,久拖不决的人道主义危机,人类对以往不适合居住的自然区域的入侵,国际旅行与国际贸易的增加以及区域气候变化。③Coats,Daniel R.(ed.).2019.Statement for the Record Worldwide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January 29,p.21.
此外,在2019年,全球备灾检测委员会(一个独立的监测与咨询机构)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存在着由传播快、死亡率高的呼吸道流行病构成的非常真实的威胁,该流行病将杀死5 000~8 000万人,消耗世界经济的5%。如此大规模的全球流行病将是灾难性的,会造成大范围的破坏、混乱与不安全。”④Global Preparedness Monitoring Board.2019. A World at Risk: Annual Report on Global Preparedness for Health Emergencies.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p.6.正如布洛伯格指出的那样,2020年的全球健康危机暴发之前几年里出版的大量报告与学术成果,就已经呼吁人们关注迫在眉睫的流行病风险,关注国际社会缺乏应对全球健康问题准备的事实。⑤Broberg,Morten.2020.“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2005)in Times of Pandemic: It is Time for Revision.”European Journal of Risk Regulation 11(2): 202-9,p.204.see also Maxmen,Amy,and Jeff Tollefson.2020.“Two Decades of Pandemic War Games Failed to Account for Donald Trump.”Nature 584(7819):26-29(doi:10.1038/d41586-020-02277-6).因此,让我们假定(如我们建议的那样),对过去警告的公共觉醒可能会使公民社会与决策者深刻体认到,2020年的疫情不是一个一次性事件,而要实现目标P-A和P-M则需要紧密的国际合作。那么,这里的讨论对气候控制目标的实现又意味着什么呢?
早在2005年就有大量证据表明,像2020年这样的流行病迟早会暴发。同样,现在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不受控制的气候变化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而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采取适应与减缓措施。随着2020年流行病的影响在次年(或十几年后)的减弱,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这次健康危机暴发时他们甚至尚无选举资格)可能会认识到,恢复现状可能并非他们唯一或最佳的选择。例如,近期在14个国家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年轻一代越来越意识到了与严峻的气候变化有关的危险,并认为气候变化甚至比未来可能暴发的流行病更具威胁性。①Poushter,Jacob,and Christine Huang.2020. Despite Pandemic,Many Europeans Still See Climate Change as Greatest Threat to Their Countries.Washington:Pew Research Center,9 Sept.2020.我们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传统态度本身可能也将被理解为对生存的一种真实威胁。新一代立法者与行政官员也可能会成为决策部门的重要官员。②Schreus,Miranda,Elim Papadakis 2020.“Introduction.”I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Green Movement,edited by Miranda Schreurs and Elim Papadakis,1-33.Lanham et al.:Rowman&Littlefield,p.16-24.基于这些理由,下一代人可能会愿意做出牺牲,对其生活方式至少做出某些改变,以便应对未来的全球风险,而他们的政治代表可能也会认真实施相关政策。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而某些人会认为它太过天真乐观而宁愿将其抛弃。有人可能想提醒我们,目标P-M 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目标C-M 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与后者不同,前者不需要依赖于紧密的代际合作。这意味着每一代人可能都会愿意支持有助于目标P-M实现的措施,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从这些措施中受益,尤其是如果他们经历过像2020年流行病这样的事件。但是,就目标C-M而言,每一代人都可能会更加愿意把减缓与应对措施的成本转嫁给后代。因此,即使下一代人更愿意克服妨碍紧密国际合作(紧密的国际合作对于实现目标P-M是必要的)的结构性约束,他们仍然需要克服妨碍紧密代际合作(紧密的代际合作对于阻止危险的气候变化是必要的)的以时间为基础的紧密关系约束。
因此,甚至连政治现实主义的支持者也愿意承认,从自利的角度考虑,国家应当把流行病视为对其国内安全的真正威胁,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才可能愿意接受甚至强制实施跨越边界的立法制度与国际规制,以便预防可能会演变为流行病的新疾病的暴发。确实有一些理由相信,2020年的流行病已经削弱了结构性约束对实现目标P-M的影响力。2020年,三位坚定的“吾国优先”信条的支持者——英国首相约翰逊、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曾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他们各自的随从人员中也有被感染者。正如《纽约客》杂志所报道的那样,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成员——陆军、海军、空军、海上自卫队以及其他部门的最高官员——都被隔离两周”。据该杂志报道,一些资深的美国战略家担心,一些竞争国家在看到美国的这一短肋后,可能会利用这一时机并试图威胁美国的海外利益。该杂志提出如下建议,“从多个角度(包括特朗普总统也是联席会议领导人这一事实)来看,新冠病毒才是现在对美国国家安全真正的威胁”③Wright,Robin.2020.“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Now a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The New Yorker,8 October 2020.。因此,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可能会承认,从“开明自利”①Attfield,Robin.2014.Environmental Ethics:An Overview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Polity Press,p.183.Symons,Jonathan.2018.“Realist Climate Ethics: Promoting Climate Ambition Within the Classical Realist Tradition.”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45(1):141-60,p.142.的角度看,每一个国家都有充分的理由既要在国内层面追求目标P-A,还要在国际层面追求目标P-M。不过,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可能还会认为,目标P-M的实现不仅需要相互监督,还需要对那些威胁不合作的国家施加压力。然而,当代人与后代人关系的性质表明,后代人既不能监督当代人的行动,也无法向当代人施压。基于这一理由,现实主义的支持者可能仍然会找不到理由来支持实现目标C-M 所需的紧密的代际合作。尽管如此,我们最后还是想补充两个论点来支持我们的乐观假设。如前所述,该假设反映了如下考量: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许多人(即使不是所有的)都认为,为控制新冠疫情而采取的那些经济代价高昂且严重限制自由的措施是合理的。他们把这些措施视为成功控制新冠病毒所必须采取的措施。这种共同担责并共享成功努力的经历可能会增强他们接受类似负担与代价以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其他全球危机的意愿。相应地,他们也会支持那些致力于克服这类约束——它们是预防气候灾难的障碍——的相关政治行为体。
我们最后提出两个论点来支持这一乐观假设。第一个论点是,气候变化具有地缘政治的意涵,即它具有诱发国际冲突的巨大可能。这可能会使相关行为体采取某些措施来克服那些妨碍目标C-M实现的结构性约束,以免打破目前的权力平衡。2014年,美国国防部在发布的一份文件中,把气候变化的影响称为“威胁的放大器”:
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剧水资源短缺,并导致粮食价格的飞涨。气候变化带来的压力将会影响资源竞争,并给世界各地的经济、社会与政府机构带来额外负担。这些都是威胁的放大器,它们将恶化海外的压力源,诸如贫困、环境退化、政治动乱以及社会紧张——这些因素能够引发恐怖主义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②Hagel,Chuck(Secretary of Defense).2014. Th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QDR).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p.8.Available at:https://history.defense.gov/Historical-Sources/Quadrennial-Defense-Review/.
这些当然是支持目标C-M 所需之长期合作的地缘政治理由。但是,预防国际冲突并不是支持目标C-M 唯一的、甚至不是最紧迫的理由。地缘政治理由并不能帮助我们克服基于时间的亲密关系约束。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这种约束仍然是实现目标C-M 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之一。这把我们引向了第二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是,我们并不认为,总的来看,与相信气候控制目标不可行相比,我们拥有更多的理由相信,人类会采取措施有效地实现目标C-M 以便及时防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我们提供的理由是为了培育彼得沃斯所谓的“坚强的乐观主义心态”③Beardsworth,Richard.2020.“Climate Science,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and Futures of I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4(3):374-90,p.386.。我们假设,预防未来新流行病暴发而采取的较强的国际应对措施,能够引导国际社会采取类似的措施以应对危险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能够引导人们更加关心后代人的要求权;在提出这种假设时,我们并不是在宣称,这是基于最可靠证据而作出的对未来事态发展趋势的最可信的预测,我们毋宁是想指出,当代人能够避免过去的错误,并以负责的态度应对气候危机。但是,有人可能会问,在对气候控制目标的可行性进行哲学讨论时,这是一个可信的推论吗?当然可信,至少,只要我们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并不是力图简单地描绘一幅关于未来的乐观图景,而是首先致力于提供一些理由来告诉人们如何防止灾难性未来的出现。对政治现实主义提出的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是,它起初是一种关于国家行为的描述性理论,但它很快演变成一种关于各个国家在一个缺乏中央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应当如何行动的规范性理论。而政治领导人与决策者会假定该理论正确,并根据该理论的预测来调整他们的行为。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的那样,现实主义从其自我应验的预测中获得支持。①Wendt,Alexander.1992.“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2):391-425,p.410.尽管有人最终可能还会反对说,我们的乐观主义假设与政治现实主义一样都是从自我应验的预测中获得希望,但是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
凯恩斯在1931年出版的《劝说集》序言中断言,“如果我们始终不懈地在乐观的假设下前进,假设就不难转化为事实;否则,如果在悲观的假设下采取行动,那我们就将永远陷入困乏的沼泽中无法自拔”②Keynes,John Maynard.1931. Essays in Persuasion.Available at: https://www.economicsnetwork.ac.uk/archive/keynes_persuasion/。如果是这样,我们愿意接受对我们的乐观主义假设的上述批评;我们的乐观主义假设有助于一个更少动乱、更多友善的未来世界(我们的后代将会生活在其中)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