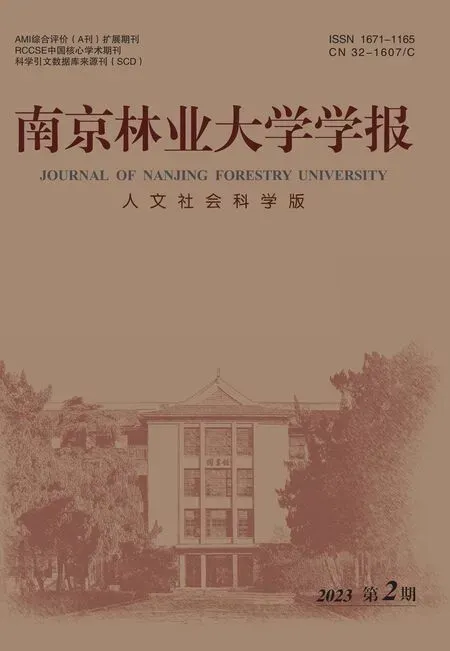生态批评维度下新时代国产电影的地方想象*
孙祖欣
(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生态电影是生态批评在文艺学乃至影视学中的延伸。2004年,美国学者斯格特·麦克唐纳在《建构生态电影》一文中提出了“生态电影”(eco-cinema)的概念,尽管麦氏的生态电影概念抛开了主流商业片,关注视野较为狭窄,但标志着生态思潮和电影研究、影像生产之间关系的正式确立。①孙绍谊.“发现和重建对世界的信仰”:当代西方生态电影思潮评析[J].文艺理论研究,2014,34(6):60-70.“随着‘生态电影’概念的日益成熟,学者们把‘生态电影’的疆域扩展到了商业剧情片和动画电影,避免了生态电影一味强调实验影像的单一性。”②张志庆,门晓璇.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电影的发展[J].当代电影,2021(2):153-158.从广义角度来看,国产生态电影有着丰富的创作实践。学者鲁晓鹏将中国的生态电影总结为六大主题:普通人的生活被环境破坏所影响,城市规划、拆迁与城市移民命运,残障人的生活与奋斗,人与动物的关系,乡村生活模式的投射和描写,商业社会中宗教的整体性思想的重建。③鲁晓鹏,唐宏峰.中国生态电影批评之可能[J].文艺研究,2010(7):92-98.在其后的学术会议中,鲁晓鹏又指出了生态电影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强调生态电影的公民属性和市民属性,他认为:“生态电影,尤其是生态纪录片所达到的目的和效果,是促使人们介入社会,促使人们思考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建立新兴空间。”④鲁晓鹏,陈旭光,陈阳.“华语生态电影”:概念、美学、实践[J].创作与评论,2016(24):107-115.
中国内地电影市场2010年总票房突破100亿元,2012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⑤丁亚平.中国电影:如何走向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J].艺术评论,2018(10):59-66.巨大的市场为纷繁多样的电影创作提供了空间。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引入“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①赵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政治与立法实践[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3):137-142.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2012年以来新时代的国产生态电影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中,新时代国产生态电影并非特指一种电影类型,而是一类在叙事和美学中展现了生态批评理念的作品。严格地说,国内还缺少一大批以生态批评为创作主旨的电影作品,也尚未形成以生态主张为追求的创作思潮,电影中的生态内涵还主要是文艺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但大量跟生态有关的创作实践依然为生态批评在电影领域的理论延伸提供了土壤,也为有待形成的生态电影创作浪潮提供了蓄力。本文以生态批评中的“地方”概念为导入点,研究电影传递出的人与地方的关系。呈现美好故乡(乡村)的电影勾勒出一幅幅和谐美好的生态画面,画面中人被自然环绕又紧紧依附于自然;讲述传统乡村与现代城市交互的电影则展现了文化的断裂和人的不安。关于城市的电影对城市特色文化符号的描画,让城市从意义匮乏的空间,逐渐彰显出地方感,而城市电影对于资源的探讨,又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环境公民意识,最终将城市改造为新的“地方”。
一、想象的故乡:地方感的建立
地方(place)是承载生态批评具象化的重要舞台。与抽象思维中的空间(space)相比,地方是实在的情感依附的场所,在布伊尔的总结中,“地方是‘可感价值的中心’,‘是个别而又灵活的地区,社会关系结构的设置位于其中,而且得到人们的认同’”②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0.。地方是一个囊括了前现代生存哲学的概念,是包含了地理、社会和精神领域的故乡。在布伊尔的地方依附(place-attachment)的现象学理论中,地方依附包含了五重维度,其中第一个维度便是被个体情感认同的同心圆生活圈。③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0.它往往指传统乡村等不借助太多外力便可以轻松触及的场所,是许多人所经历的传统故乡。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将故乡归纳为一个蕴含了天空、大地、动植物、时光、岁月的自然环境,是一支包含宗族、血亲聚集的种群,是生命的源头、人生的起点,同时又是已经不在场、被想象的心灵境遇。④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97.
电影呈现的故乡成为现代社会中原子人的情感依附之地,承担着流浪者心灵寄托和疗愈的功能,帮助人们建立起人与社会(自然)情感上的关联。《一点就到家》(2020)将舞台设置在远离城市的遥远的茶乡,在那里,乡亲们对自然、土地有着浓浓的眷恋;而主人公魏晋北,经历了大城市数次创业失败而来到茶乡疗愈,友情的羁绊和自然生态的美景治愈了他的失眠,让他终于体会到久违的安宁,他也终于意识到他所要回到的地方不是冰冷的大城市,而是亲情浓郁的乡间。《我和我的家乡》(2020)中的每个故事都表达着人与当地的情感联系:其中,《回乡之路》里讲述的是受到关照的孤儿成年后回乡植树造林、造福一方;《最后一课》展现的是乡村教师与贫穷学生在艰苦条件下建立的师生情谊;《神笔马亮》记录的是放弃留学的美术家回乡,一边脱贫致富,一边建设美丽家园的故事。电影对于传统故乡的想象,展现了在充满地方感的空间里人的自由和天性,是现代人心向往之的精神状态。
如果上述电影对于故乡的地方想象是一副静态的情绪充盈的风景画,那么公路电影则明确地展现出逃离空间回归地方(故乡)的动作或者意图。从生态批评角度来看,地方是“抵抗政治”的前提①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3.,其抵抗的对象是那种打破了地方与社会有机融合的在现代化进程中生造出来的意义匮乏的空间,它可以是千篇一律的钢筋混凝土城市,可以是背井离乡让人无所依傍、倍感孤独的旅居地,也可以是讲述职场精英的文艺作品中符号化的“办公室、公寓、地铁、飞机、出租车、饭店、宾馆、网络工作站”②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1.等。公路电影往往以逃离为始,其逃离之地常常是情感稀薄、让人压抑的城市空间,而远方是被赋予社会感、自然感和浪漫感的地方。《心花路放》(2014)中的主角为了走出情伤而远离都市,并在大理找回了离婚以后的平静。《送你一朵小红花》(2020)讲述了两个身患癌症的少年渴望游历青海的梦想,梦想里如镜的青海湖和雪白的羊群是他们病痛生命的反面,是向死而生的寄托。《囧妈》(2020)展现的是一场从混乱走向秩序之旅,正在经历婚姻失败、事业混乱的男主角意外陪伴母亲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列车,一路上的挫折和磨难缓和了母子关系,消除了摩登都市带来的失序,最终抵达了怀旧与和谐的目的地。公路电影往往都是背离城市的归乡之旅,意指从现代文明的生态失衡中解脱出来,回归人之初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心灵的和谐境界。
尽管当代社会依然有许多居民生活在传统的故乡和家园,但现代化、电子化和全球化带来的人的物理和信息迁移不断地剥蚀着人与故乡的关联,因此,关于故乡的电影才能获得观众的情感共鸣。这种共鸣是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想象有着强大的能量,因为“尽管想象者并未到过,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到达此处,却很难削弱这种传说中或想象中的地方引发的向往和忠诚”③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1.。想象让现代人的地方依附有了落脚点。
对于现代人来说,故乡终归是一个不在场的心灵境界,电影通过将内心的需求外在化和视觉化,为现代人无所依附的地方感提供了落脚点,但对于故乡想象本身该如何落地,却超出了电影能力的范围。在想象之外,部分电影发现了传统故乡的失落以及乡村与城市的断层,展现了地方感摇摇欲坠的现实危机。
二、地方的断层:乡村与城市之间
断层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指岩石中发生过运动的破裂处或断裂处,它处在板块或者岩石的边缘地带,当运动在断层处发生时,便会引发地震等地质危害。④阿瑟·格蒂斯,朱迪丝·格蒂斯,杰尔姆·D.费尔.地理学与生活:全彩插图第11版[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62-68.本文中地方的断层,指的是那些在乡村(故乡)和城市(空间)的衔接处同样不断发生运动的地带。乡村和城市是社会发展至现代过程中人类主要的生存环境,围绕两个文明板块的环境特征和文化符号而进行的文学艺术创作,诞生了城市文学、乡土文学、都市影视剧、农村题材影视剧等类型,但是针对二者的接壤地带,尚未形成创作趋势。这种接壤并非地理上的城市郊区、小镇或城乡结合部,而是一种文化上的断层,一种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跨越进行时。在城市与地方的相互作用中,反而蕴含着巨大的冲突、摩擦和断裂。了解这种生态批评意义上的城乡断层,是立足现代文明现实,实现从正视地方依附在传统故乡中的退化,到寻找在城市再栖居可能性的必由之路。
《雄狮少年》(2021)是一部将留守儿童作为关注重心的励志电影,但在成长故事之外,电影还在城乡的文化断层处刻画了一幅残破的生态图景——传统文化失序(舞狮文化的没落、宗教信仰的失守)、新文化苍白(钢筋水泥里的城市人如机械一般运行),人在此间流离失所。阿娟是一个留守少年,父母在广州打工,彼此皆过着艰苦的生活。电影刻画了浓郁的粤文化风情——对佛祖的信奉、对舞狮传统的怀念,等等,但是这些关于地方(故乡)的精神实质却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风化、销蚀——舞狮被视为玩物丧志,佛祖石像在杂草丛中无人祭拜。电影里,在参加舞狮大会的主线下,埋藏着大城与小镇的紧张关系:父母被迫离开阿娟去城市打工,阿娟每年期盼父母回家过年陪伴;当父亲在工地受伤后回家康复,阿娟却进城打工,迈入无望的下一个轮回。在这个城市与故乡的关系里,亲情之间的陪伴被取消,责任成了唯一的纽带,从断层张望两端,城市是吞噬一切的猛兽,故乡是难以为继的虚弱内核。
在描绘城乡断层方面,《雄狮少年》是写实的,这种写实暴露了断层两端的生态危机,但是失去地方精神的城市空间,在建构自己的精神内核时,又往往将目光投射到故乡。《相爱相亲》(2017)围绕为父亲迁坟而引发的冲突展开。主人公岳惠英代表着典型的城市精神,理性、秩序、严谨、低调,她在争取为父亲迁坟权利的时候,利用的是资料、档案、证件等,这些千篇一律、适应当代社会管理和高效统治的规则,恰恰是“地方剥夺”(place-deprivation)的符号性存在;而乡下的父亲原配虽然也曾咨询律师,但她始终坚信的是传统、宗族、情感和承诺,她与丈夫的婚约是地方宗族见证下的,是被周围环境认可的。在生态批评的视角下,与其说电影描述了岳惠英和父亲原配关于迁坟权利的冲撞,不如说是展现了城市文明和地方传统的断层。在城市一端,不论是岳惠英,还是她的女儿薇薇以及薇薇的男友阿达,都在经历着文明社会的精神危机,当他们愿意跨过断层,扎根到土壤肥沃的另一端,便会获得一种解脱。岳惠英通过放弃对规则的崇拜而倾听父亲原配久远的故事,达到了内心的平静以及与家庭的和解,薇薇通过在乡下跟老人的相处,从感情的泥潭里走了出来,阿达则在老人的棺材里想通了自己未来的音乐之路。在这些情节中可以看出,尽管乡村正在经历自身的衰败,但它依然是城市空间空洞内核的给养源泉。
这些电影在地方的断层地带上演了文化碰撞、摩擦、拉锯的故事,通过对这些戏剧动作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故乡实体的传统乡村已然衰落,但是以故乡为基础生发的地方感依然在人的内心中绵延留存,成为在意义匮乏的空间(城市)中生存的人的心灵解药。然而“生活在此地心灵在别处”的模式并非长久之计,也无益于人与在地的地方感的维系。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大多数人的生存归宿,在生态批评的视阈下如何展现城市的栖居和城市的地方化,是电影明确其生态属性、传递生态意涵的重要标志。
三、城市的地方化:情感、知识和行动
由于城市是大多数人最终的居住场所,生态批评不应简单将城市排除在外。布伊尔坚持使用“环境批评”这一术语,在于“‘环境’拥有更加全面的含义,表明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不是简单的‘自然’空间,而是一个由生物地理与人工建筑共同构成的混合体”①岳友熙,劳伦斯·布伊尔.美国生态想像理论、方法及实践运用——访劳伦斯·布伊尔教授[J].甘肃社会科学,2012(5):52-55.。它不是“传统的‘自然环境’,而是‘自然’与‘人工’的统一,其中包含着城市生态空间”②郭茂全.“重新入住城市”: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中的城市想象[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4(2):97-101,107.。然而布伊尔通过文学研究发现,“关于‘城市生物区域’想象的文学仍然相当缺乏”,偶尔出现的城市绿洲描写往往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生态批评将城市认可为地方,却是非常必要的进步。③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5-97.一般现代人理解的城市,尤其近年来发展出的城市新区,只能认定为方便管理、经营和生产而创造出的空间,并非蕴含生命意义的地方,将这些空间进行地方化改造,即城市的地方化,是生态中的人必须抵达的目标。
城市的地方化是一种再栖居(reinhabitation)的过程。相较于传统故乡中的原住民,当今城市的主体为移民,移民者(settler)从故乡迁移至新的场所,建立与场所相互依赖的关系,当他认识到“这个”城市是“我的”城市后,他便开始对城市主动担责,完成再栖居,最终获得新的环境公民身份(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④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7.,而城市也在这个过程中从空间转变为地方。在这里,可以从情感、知识、行动三重递进关系来研究都市电影中的生态意蕴,发现移民者再栖居和城市地方化的影像表达策略。
第一,生态电影展现了人与城市的情感纽带。地方感的重要指标是人与地方的情感关联,部分都市电影对城市特色的着重刻画,使得画面里展现的城市个性十足而鲜明,有别于其他符号化的城市空间,成为与个体生命经验产生重叠的“这座”城市。自2012年以来,许多电影在创作中加强了地域属性,在方言、地标建筑、市井生活的描摹中,强调城市的地方性,产生观众与属地的情感共鸣。例如,自《疯狂的石头》(2006)上映以来,重庆便成为一个时常入镜的城市,其丰富的地理特征和文化特色为故事的上演尤其情感的抒发,提供了意味浓郁的天然场地。随后十几年,有《火锅英雄》(2016)、《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016)、《少年的你》(2019)、《刺杀小说家》(2021)等作品把事件的中心都放在了这座城市。在这些电影里,清晰可辨的重庆方言、山城风景、过街天桥、江流河堤、火锅小吃、市井文化等,不仅给当地居民带来亲切感,也让其他观众向往。其中,虽然《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在塑造成人的爱情童话中脱离写实、走向浮夸,但电影巧妙地运用城市广播串联起人物关系。城市广播极具地方意义,在传播的向度里,它诉说的都是本地的见闻和人事,是人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声音伴侣。广播尤其能够增强地方感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双向的交互平台,当地市民不仅聆听广播、获取资讯,还通过热线电话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分享给更多的听众,这一过程实现广泛的在地连接。电影中,主角陈末是电台DJ,他在自己的频道里倾吐爱情中的落魄,幺鸡是陈末的追随者,她在电台连线中寻找生命的慰藉。城市广播是市民故事的见证者,一个人的故事在经过广播的放大,成为一个城市集体的故事,正如布伊尔在分析散文作品《记忆地方》时所指出的,在共享中,“我的记忆地方”变成“我们的记忆地方”,因为有了宝贵的生命经验,地图中的空间变成了地方。①劳伦斯·布伊尔.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4.
第二,生态电影让观众获得了“城市是生态系统中的城市”知识或印象。相较于传统乡村里农耕、畜牧、交易、纺织等简单知识,城市是知识急剧扩增和综合的复杂体,包含了工业生产、商业贸易、能源资源、交通运输、垃圾处理、城市文化等不同的知识群落,即便是最富经验的城市管理者,也不可能获得关于城市的全部信息。这种复杂掩盖了关于城市的一个重要知识,即城市并非一个独立的自我循环体。市民在如此复杂的城市里生活,只经验到可接触范围内的城市表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于是产生一种城市能够全能和自足的错觉。期待电影传达城市运行的知识是徒劳的,但生态电影的价值在于,它可以通过影像和叙事让观众获得城市位置的知识和观念:城市仅仅是生态中的一环,它的存在依赖的是城市以外的资源、能源等,于是,对个体生活方式的保存一方面需要珍视城市现有的资源,另一方面也要保护生态全链条上各个环节。
电影《奇迹·笨小孩》(2022)再现了深圳“科技之都”这一形象,航拍镜头下的密集楼群景象像是高集成度的芯片,暗合了电影中芯片回收的叙事,象征了深圳的高科技引领发展的城市精神。电影以青春奋斗为故事主线,在主线之下,隐含了“设备回收再利用”这一生态主张。主角景浩为了筹钱给妹妹治病,尝试做手机零件回收的生意,然而由于技术限制,回收的良品率一直无法与国外竞争。在景浩的破釜沉舟和一众朋友的合力之下,他们终于克服困难使回收良品率达标。在电影中,这一成功既为主角的生活打开了出路,创造了经济价值,又暗示了城市文明(电子产品)实现部分自我循环的可能性,表达了“珍视城市资源”这一生态立场。
在展现城市的有限性这一知识和观念方面,《新神榜:哪吒重生》(2021)、《罗小黑战记》(2019)、《美人鱼》(2016)等作品有着生动的表达。《罗小黑战记》将视角关注到土地,展现了城市画卷边框之外的空间。“现代城市的土地经济利益……令城市与自然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加深。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与城市人口增长,城市土地和居住空间不足的问题也愈加凸显。”②马特.从缺席到在场:生态批评的城市维度[J].外国文学研究,2017,39(4):54-62.对问题的粗暴解决意味着对城市周边自然空间的挤压,电影以精灵的口吻控诉了这种扩张对自然的破坏。抑制城市对周边挤压首先要获得“城市须与周边共生”这一知识,因为“任何人居环境(包括城市)的人类活动都是全球生态的一份,存在着人类活动的生态极限”③黄肇义,杨东援.国内外生态城市理论研究综述[J].城市规划,2001(1):59-66.。电影最后展示了一种难得的平衡状态,在没有外力施压的情况下,人类实现了一种自我约束,建立了一种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美人鱼》在展现城市边界与扩张方面则更为直接。故事中,资本家为攫取更大利益,在生态海湾填海造田,用声呐驱赶海湾里的海豚和美人鱼,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害。电影以非常鲜明的环保立场批判了城市的野蛮扩张,展示了城市与自然的边界。城市并非自足的,这意味着城市要对资源进行循环利用,纪录片《城市梦》(2019)用一个拆迁的故事传递了城市土地资源规划循环的理念。纪录片中,在武汉经营报摊和水果摊的一家人,在城市规划进程中一方面最大化地争取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又迁入新店面,展开新生活。它显示了城市变迁可以不似草木那般野蛮生长,提出了一种自我调节和理性规划的可能。《新神榜:哪吒重生》正视了城市与资源的关系,展示了资源匮乏下城市的脆弱。电影以瑰丽的混搭美学风格,再造了一个水资源被垄断的城市贫民窟景象。在那里,人们排队接取饮用水,涓滴的水流成了宝贵的资源,每天寻找水源也成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一切使得对于淡水的渴望溢出银幕。电影以一种寓言的形式传递了“城市无法自足反而严重依赖外部”这一知识。这些电影并不展示城市运作的技术细节,但以一种整体观的面貌告诉观众,城市是生态中的城市,它吸取外部资源并产生废料,对城市发展的节制是减少外部消耗的有效方法。
第三,生态电影促使人们产生行动,成为行动中的环境公民。电影并非宣教片,不要求观众成为环保主义者,但当观众对生态中的城市产生情感,获取城市在生态系统中位置的知识后,便会萌发行动的种子。这种行动不一定是直接参与环保活动,它可以是一种公共空间的建立,也可以是一种特定舆论的参与。《穹顶之下》(2015)是一部产生广泛影响的生态纪录片。该片通过专家访谈、现场采访、实地调查等手段,绘制出空气污染的清晰脉络,给观众带来震撼。它的价值在于促进了城市工薪阶层在网络公共空间对该议题的持续讨论,提升了普通市民对于空气污染来源和治理的关注,从民间的角度促进了近年来国内空气质量的大幅改善。然而,这种直接激发环境行动的电影并非国产生态电影的主流,不似西方社会持续创作《永不妥协》(2000)、《难以忽视的真相》(2006)、《黑水》(2019)等一系列直指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作品。这与不同地域的电影创作环境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已经将关注的焦点从阶级转向环保、移民等议题,而我国的生态建设则走向一条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特色之路。要求生态电影一定要具备行动属性是艰难的,城市的再栖居也不要求每个市民参与生态建设的专业分工。对于城市移民者,再栖居实际上是建立一种城市里诗意栖居的观念,“是……针对(信仰失落、审美贫乏、人类沉湎于消费主义和感官刺激)此一情形而提倡的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也是人类关照、修筑自身内心精神家园的一种生活态度”①施旭升.城市意象与诗意栖居[J].文化艺术研究,2010,3(5):8-15.。
情感、知识和行动是观众可以从城市生态电影中获取的信息和价值。首先,电影通过将城市特色杂糅在叙事中,以东方特有的抒情手法建立城市的地方感。其次,通过客观地陈述城市在生态系统中的依赖位置,电影又传达了城市的依赖性这一知识和观念。两者的交互作用可以唤起观众的环境公民意识,完成在城市的再栖居,而推动观众从知道到行动,实现学者鲁晓鹏所言的“介入社会”,则是对生态电影的更高要求。
四、结语
自2010年大陆电影总票房突破百亿以来,国产电影市场不断扩大,不同主题、形式、内容的电影获得了巨大的创作空间。在这种背景下,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检视国产电影,能够发现其中生动的生态表达。新时代国产电影恢复了对传统故乡(乡村)的影像重建,通过对美丽乡村的想象为背井离乡的现代人建立久违的地方感;但这种地方感的获得几乎全部依托想象,在关注城乡互动的电影中,可以看到传统故乡精神的失落以及城市空间的苍白。由于城市是大部分现代人的最终归宿,移民者需要完成在城市的再栖居,而关于城市的电影恰好提供了一条从情感共鸣、获取知识到产生环境行动的再栖居路径,最终完成城市的地方化改造。
生态电影并非一种新兴的电影类型,在生态公共空间尚且稀缺的环境下,国产生态电影的创作尚未汇聚成一种现象和思潮,即便如此,依然可以在浩瀚的电影文本中寻找到生态属性和特征,其中地方感的塑造和表达,成为生态批评视角下进入电影的一个切入点。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当电影中的地方想象和生态表达不再是一个叙事的背景和副产品,而成为电影诉求的核心时,国产生态电影将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生态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