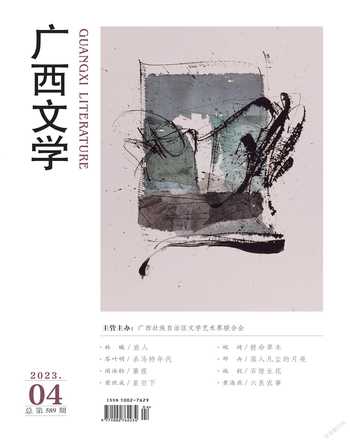落入凡尘的月亮
邓妹在五岁前没有正式的大名。她出生于高考恢复那年,从她呱呱坠地到上户口,当高中教师的爸妈每天起早贪黑,又上课又照顾邓妹和两个哥哥,忙得团团转,完全来不及给她想名字,就在户口簿上匆匆地登记了“邓妹”二字。等邓妹快上小学时,阿爸才发现这名字似乎有失正式,深感内疚,于是翻字典,郑重地给这个小女儿起了大名。但家里还是习惯唤她“邓妹”,左邻右舍提起她也常说:“哦,就是邓老师家的那个细妹啊。”
邓妹在十二岁跟父母迁回家乡贵港前,对云垌村一无所知。
一个姓氏和一个遥远的小村庄,意味着什么,在外地出生、纯属放养长大的邓妹对此毫无概念。
直到多年后,当一本族谱和一本村志交到邓妹手上时,她才醒悟,冥冥中早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注定要落在自己肩上。
明月不常满
月亮对着池塘照镜子。天空有一弯月牙,水面也有一弯月牙。
池塘也是月牙形的,如嵌在大地上的半月。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云垌的客家围屋群就在郁江之南离城区约四十公里的眉眼盈盈处。
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客家人善于以五行造物,其中以土为尊,以水为财。
围屋是古代客家人制造的最大的生存器物。择山水,看地形,测风向,慎重定下方位,以铁锹在地上挖出一个半圆形大坑,起出的黄泥加糯米、红糖、蛋清等夯实,建成方形土屋,凿出的大坑则变成屋前的一泓月牙池。此布局从阴阳两仪太极图化成,暗合“天圆地方”。
客家民居多有天井,下设铜钱状排水口,通往屋前月池。下雨时,雨顺着四方滴水檐落下,由铜钱口流入月池,月池下另有渠道引向稻田,可用于灌溉。
村庄里每多一栋房屋,地面就多一弯月池。一屋一池,一方一圆,造化无穷。
大海有真能容之度,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月盈则亏,客家人的池塘总是半圆形的,如一枚上弦月。土地不断地趋向饱和,当一个村庄的土地无法喂养更多人口时,客家人就该迁徙了。
云垌村,在农耕时代收容了很多个村庄迁来的客家人,得以成为一个新的村庄。
两百多年前,地处木梓和木格之间的云垌,荆棘满目,人烟稀少,时见匪贼出没。只有迁移的客家人在这无主之地寻找生机。
一天,一户何姓客家人来到此间,夯土为房,开荒为田。此后陆续有客家人迁入。荒野默默收容了他们,使他们的躯体和灵魂都不必再漂泊。这常年被白云和群山环绕的荒野也因此有了人气,有了名字,唤为云垌。
把目光穿越回1765年的云垌,一处叫洛麻坑的荒地。
烈日下,一个男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甩开膀子开荒。他衣衫褴褛,皮肤黝黑,目光坚毅,身板结实。一把粗糙的铁镢高高举过头顶,然后猛然落下,扎进杂草丛生的土地,再用力一拔,一个土疙瘩被翻了起来。
这朴实无华的一起一落、一镢一翻、一步一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荒地里上演。土块中的草根、石块、虫子需仔细清理,荒土才能变成熟田,才能供养稻子、玉米、红薯,让一家老小吃饱肚子。
男人的身影渐渐伛偻了。他旁边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那是他的儿子。年轻人眼里露出同样坚定的目光,双臂抡起沉重的铁镢,夹着山风的呼号,劈开坚硬的黄土地。
他们是第一户迁入此处的何姓客家人。
身上到处是伤,手掌满是水泡和血痂,磨破了,长茧了,一层层叠在手心。几十年后,整片洛麻坑都被翻了个遍,瘠土化为活壤。荒野在开垦的疼痛中分娩出稻田、土屋、池塘。那是一个村庄的雏形,它像一个初生的婴儿,成长于天地。
多年后,一位面容清瘦的老人与村委退休老支书沿着洛麻地来回丈量,老人眼露惊奇,在随身手稿上记下一行字:“清乾隆三十年至嘉庆末年,何氏父子徒手开荒水田九十四点三亩。”
小鸡与老虎
“妹妹,幫打一份稿子。”
看着手稿上密密麻麻凌乱潦草的小字,刚加班回家的邓妹顿时欲哭无泪:“阿爸!你隔三岔五整那么多文稿,我也顶不住呀。能不能找个文印室来处理?”
“嘿嘿,写得乱了点,还得反复改,编委会没啥经费,文印室不愿接这活。你就帮帮阿爸吧,我要写我们村第一本村志。”
“什么村志?”
“就是记录乡村历史的书。云垌围屋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专家说我们村历史特辉煌,值得出一本村志。”
邓妹想起自己第一次跟父母回村时,乡路弯弯绕绕,走得脚都磨破了,疼得她直掉眼泪。村子里到处是斑驳的老房子,阿爸说那些全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邓妹则狐疑地看着眼前疑似风化的土墙,残缺的青砖乌瓦,檐下的蛛网和从墙角探头探脑的老鼠……
“什么陈年烂芝麻的辉煌村史,该作古了。”邓妹嘀咕。
阿爸生气了:“冇识就冇乱讲!云垌村的历史,是一部客家人迁移后的开发史,客家人用不到一百年时间就把这片荒郊变成贵县(今贵港市)‘小香港,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好好好,我马上整理稿件还不行吗?”邓妹头痛欲裂。她从小喜爱文学,唯独对历史地理绝缘,读书时永远背不出“公元某年某地某人某事……”之类的概念,索性弃文学理,结果发现自己学理科更菜,没法子硬着头皮磕磕碰碰完成学业出来工作。然而,某一天,阿爸无意中翻到邓妹的文学摘抄本,大喜过望,认定邓妹是三兄妹中唯一继承了他文脉真传的孩子,于是乎,为阿爸整理文档的苦差就落在邓妹的身上了。邓妹心里那个愁啊,就像电脑前的手稿文字一样剪不断理还乱。
十多年来,阿爸与几个退休老乡一起组成村志编委会,收集大量乡村资料。老人不会电脑,邓妹一边帮忙打字和校稿,一边听老人聊往事。
邓妹的先人,是众多迁入云垌村客家人中的一户。
两百多年前,邓氏“龙凤朝阳”(文龙、文凤、文朝、文阳)四兄弟千里迢迢,风尘仆仆,从广东龙川县登云镇石福村迁入广西贵县(今贵港市)怀北二里上垌村。
乘一叶扁舟,逆流而上,寻觅新的生存家园。只是天地茫茫,何处可容此身?族中长老吩咐,随船携带一只抱窝的老母鸡,孵着一窝鸡蛋,当第一只小鸡出生之时,便是上岸之时。
小船渐行渐远,乡愁渐浓,出走的客家人扶栏远眺,目光翻山越岭,想竭力看清,又总是看不清,命运究竟要将自己指派到何方。
某天,一声叮响,一只湿漉漉的小鸡破壳而出,睁大乌黑的眼睛好奇地张望着外界。
船上众人惊喜交集,赶紧移舟靠岸,查看地形,一番寻觅后到了云垌。此处依山傍水,藏风聚气,虽少见人烟,但有可开垦的荒地。天性乐观的客家先人放下行囊,搭建窝棚做饭。
远处山上,一只猛虎正在巡视领地,它闻到风中捎来一缕陌生的气息,发出一声威严的低吼。
那时老虎还是山间的王者。
一百多年后,老虎在云垌村四周的山峦间彻底绝迹。
“什么?从前我们这个小地方居然有老虎?”邓妹听着父亲的讲述,发出一声惊呼。
“这有啥好奇怪的,《贵县志》有记载,从前许多山头都有老虎。”
到目前为止,在人类与任何物种之间的地盘争夺赛中,人类都是稳稳胜出的一方。只是,如果在时间长河里走得再远一些,胜者未必永远胜利,不知祸福之所倚。如今人们只能抚书想象山间那一只孤独的老虎,以及它所统治的一方山林,众多的狐狸、野猪、兔子等。
有所围有所不围
人类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对弈。
前世冇修简让穷,扑壁无尘四面空;篾柏织门冇挡水,芋叶遮窗冇挡风。屋亚公来广西,过山过水走千里;百年风车带落屋,肩头脱开两重皮。旧时老虎好凶恶,半夜拖人跳过崖;南蛇大过饭桶仔,步狗狐狸专担鸡。围屋菜园四四方,东种香葱西种姜;北边龙眼南边荔,菜蔬豆子种中央。鸡鸭成群牛儿肥,做砖做瓦烧石灰;半夜起身做豆腐,又勤又俭福自来。讲做先理唔怕难,北海担盐日日肩……
村里一位独居的许姓老人收藏着客家人迁移后编的山歌,热心地提供给村志编委会。
邓妹一边打字一边纳闷:“什么是‘先理?”
阿爸说:“客家话,‘先理就是‘生意。都怪阿爸,从前没教你学客家话。”
“歌词里说,去北海担盐?”
“从前,农闲时,我们村很多人靠两只篾笼、一条扁担,跋山涉水,到北海和周边县城,收些海味、食盐回来贩卖。还有走得更远的,用手推车把土产运到贵州、四川,换药材运回来。”
“啊?那也太辛苦了吧?”
“客家人的字典里没有‘苦这个字。”
风餐露宿,筚路蓝缕,少数有头脑的客家人,竟能渐渐富足,先理越做越大,慢慢完成了从农夫到小商贩、又从小商贩变成大老板的进程。
盗贼时时觊觎着村庄。
附贡生邓逢元在上垌中段建筑了第一座客家围屋——段心围。这脱胎于古代中原庭院府第式的围屋,以厅为中心,东西两侧各有横屋,与四角四楼组成方城。房屋设灰塑博古脊,脊身饰各种浮雕。围屋外墙融合了三合土、河卵石、青砖,墙上四口炮眼,一字摆开,墙面布满枪眼,防御异常严密。
一座大围屋可容纳几十或上百人,祭祀、上灯、设宴……屋内有着自成一格的规矩,俨然一个独立小社会。继段心围后,桅杆城、云龙围、隆记城……一大批围屋像雨后春笋般崛起。
围屋设私塾、书馆,请先生教娃娃读书。段心围是清兰小学堂的旧址,招收附近村民的子弟入学,办学经费由邓家蒸尝支付。
“唔同人家赛过年,要同人家赛耕田。”“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教书先生除了教传统国学,还教些通俗的客家谚语。淘气的娃娃却笑嘻嘻地编了顺口溜:“先生教(方言:我)人之初,教先生打野猪,野狼飙过河,先生冇(方言:无)奈何……”
先生取过板子作势要打手心,娃娃们顿时噤声。
晴耕雨读,客家人晴天在土里刨食,雨天在圍屋里读书,一来二去就念出一丝诗与远方的感觉。
从清朝开始云垌就有学生娃走出村庄,漂洋过海去留学。每一次出走,都带回新的视野,围屋里的课程除国文算术外,增加了英语、物理、体育、图音等课程。学生们在课间打起了乒乓球、篮球。
围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动静同出一源。围屋,曾经可以围拢一个家,护佑着生而脆弱的生命。
在这脆弱的生命中,却生出了有趣的灵魂,突围而出。诗与远方一旦苏醒就反客为主、化守为攻,蓬勃地生长起来。
隔代的呼唤
为了修村志,编委会查阅了村里黎、叶、曾、黄、邓……各个姓氏的族谱。阿爸兴冲冲地搬出一大箱邓氏族谱,指挥邓妹帮忙摆好。
“怎么这么多?”
“我们祖上已经经历过多次搬迁,几经周折才把各地族谱时间脉络连接上。邓氏族谱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其中云垌邓氏是从乾隆时期记起。”
邓妹头脑一阵眩晕:“三千年这么长,是怎么记录下来的?”
“这就靠一代代人的接力啦!有了它,你才能在千百年后,依然知道自己从哪来。”
邓家祠大门两旁的堂联是“南阳世泽,东汉家声”, 邓氏堂号为“高密第”。阿爸时时眉飞色舞地对邓妹讲,世居河南南阳的邓姓在东汉时扬名天下,四十七世祖、“东汉开国第一人”邓禹被封为高密侯,故有此堂联和堂号。
当年迁入云垌的邓氏四兄弟,已化作无数分枝,出过留学生、大地主、县长、金融家、工程师,有富甲一方的大户人家,当然大部分还是朴素的小户人家。邓妹家就是这朴素的小户人家之一,爷爷奶奶一辈子务农,当教师的阿爸已算是家中的秀才了。村里读书人多,但执笔写史的不多,于是阿爸被推做族谱和村志主编。每当阿爸喝了点小酒,慷慨列数祖上荣光时,邓妹和阿妈就会窃笑,笑他天生的儒生意气,阿爸不以为忤,下次喝点小酒还继续讲。
渐渐地,阿爸讲的故事断层了,时间接不上,有些人物与事件模糊不清。
云垌电影院只有一张青砖建筑物的旧照片,图片说明无从写起。云龙长城有个解放军俱乐部,搞不懂何年成立,只余下墙上几个残缺的大字。村里的人口数与庄稼收成漏记了好些年,翻箱倒柜掘地三尺也找不到档案……
有人打电话给邓妹:“你阿爸叫我帮忙整村志,我不是不支持,但实在太难,我放弃了。你也劝劝你阿爸,别太累了。”
邓妹还没想好要不要劝阿爸,阿爸就住院了,他在病床上叮嘱邓妹“别告诉你伯父”。
邓妹还没想好要不要把阿爸生病这事告诉伯父,堂哥就捎来消息,“四伯摔跤住院了,他说别告诉你爸。”
纸究竟包不住火。阿爸一声叹息,拖着病体去探四伯,老哥俩絮絮叨叨地聊了许久。邓妹陪在一旁,心中怔忡不定,细细的话语不时传进她耳里:“村志和族谱就交给细妹吧,别让大伙的心血付诸东流……”
那一场交谈后,阿爸和四伯相继离开人世,像一棵大树上的两片绿叶,曾经平平淡淡又蓬勃茁壮地生长过,最后悄然随风而逝。
邓妹开始频繁地回村了。
邓妹去寻找阿爸未讲完的故事。
村庄还是老模样,但在邓妹的眼中,一切又都不一样了。村里的一草一木、一屋一池,都变得有生命、有脉搏,会呼吸、会疼痛。
因为不会说客家话,邓妹回村有些拘束,但邓妹又依恋着这村庄,像一种隔代亲。人们都说爷爷奶奶和孙辈是隔代亲,而邓妹既没有见过爷爷奶奶,也没有在云垌村生活过。
在经历失去之后,邓妹才真正听到了来自村庄的呼唤,隔代的呼唤。
月牙池镜像
邓妹珍藏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一个憨厚的布衣少年立于池塘前,笑容与水边的小树一样青嫩。这是阿爸留下的唯一的一张少年时期的全身照。
如果月池是一部有记忆的录像机,那么后人就能从池中看到云垌过去两百多年的镜像。这半月形的图腾里,不断反复浮现着日月星辰、飞鸟游鱼、牛羊、稻穗、白玉蔗……还有荷锄来去的村民。
邓妹凝视祖屋前的池塘,透过氤氲的水面,她看到正当壮年的爷爷在扛玉米、晒谷子,奶奶安静地织草席。童年时的阿爸在放牛,穿着旧布衣,裤管挽起一半,他仰头看着爷爷:“阿爸,我想上学。”“乖,等小牛养大了,换学费给你上学。”他们都有着相似的单眼皮、方脸颊和憨厚的笑容。多年后,阿爸成为乡镇教师,奔波往返于学校与家。一个清秀的女孩背着书包走过池塘,对着水面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发梢,神情腼腆。那是邓妹的阿妈,读师范放暑假回来,到阿爸家帮忙干农活……突然,几个戴着红袖章的人把阿爸带走了,给他扣了顶子虚乌有的帽子,关进了牛棚。爷爷奶奶急得去找村委反映,曾经当过红小兵的母亲写信给革命委员会,诉说阿爸的清白无辜。大半年后阿爸回来了,一家人喜极而泣……
鄧妹睁大眼睛,想看到更多的画面,但一阵风吹来,把这氤氲的画面吹散了。
每个月牙池的镜像记忆都是不同的。
大户人家门前的池塘,见惯大世面。比如桅杆城的池塘,照映着两条高高的桅杆,顶端用上等白玉雕成毛笔尖状。那是在清宣统元年黎赓扬考取拔贡后官府立的桅杆,但凡路过此地的官吏,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表示敬意。
隆记城的池塘,目睹过许多盛大宴席。当年村中首富给母亲过寿,宾客满堂,宴席从屋里一直摆到了屋外。爷爷带着当时年幼的阿爸去帮工,干完活,阿爸第一次痛快地吃到了大块的鲜美扣肉,对穷人来说,那滋味真是香啊!
段心围的池塘跟土匪打过照面。一群恶匪进村打劫,村民们跌跌撞撞地奔入段心围,关上大门。森严的炮楼、幽深的月牙池与匪徒冷冷对峙。突然,围屋咆哮着喷出猛烈的炮弹,土匪仓皇逃窜。围屋主人邓逢元奉宪谕督围中练丁助剿,士兵在晒谷场上日夜操练,震慑着村外的匪贼。
一群学童蹦蹦跳跳地从塘边走过。围屋中响起琅琅读书声:“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
声音渐渐淡去。
传统农耕时代落下帷幕,客家人不再聚族而居,围屋和月牙池日益消瘦。
村里人走进了城里,走进了各种大大小小规规矩矩像格子一样的房子。城市的高楼大厦结实漂亮,总是一副公式化的精英面孔,气质跟村庄截然不同。
其实所有在城市出生和长大的孩子,都是村庄隔代的孩子,包括城市本身也是村庄的孩子。
白玉蔗
邓妹对着村志手稿犯愁,围屋手绘图得返工。邓妹去找奇哥,村志编委会的一位成员,阿爸曾叮嘱过,有困难可找奇哥。
奇哥做事利索,为人爽朗,眼神处处透着老江湖的狡黠。他打量着邓妹,操着一口正宗客家话问:“你就系邓老师的细妹?你冇识(方言:不懂)讲客家话?忘本哟!”邓妹额头冒汗,小声说:“我小时不在村里,不会说,但能听懂。”
奇哥咄咄逼人继续诘问:“他们说邓老师把村志和族谱都交给你,让你代表他全权负责?你确定你能代表你阿爸?俗话说,女子不入谱,我从没见过女子修村志。”
邓妹原本低着头,一听这话,心头冒出一团火,她猛然抬起头来,盯着奇哥一字一句地说:“阿爸把事情交给我,自然是相信我,难道你不相信我阿爸眼光?谁讲女子不能修志?古代就有班昭续汉书的例子!”奇哥哈哈大笑:“好!你阿爸没看错人,我帮你。”
奇哥与邓妹在村中来回转,重新标注围屋群手绘图。邓妹方向感差,常常绕到东边就忘了西边,带路的奇哥一脸无奈与嫌弃。
稻田对面小山坡上有座古朴的围屋叫火砖城,大门紧闭。奇哥给邓妹推了个微信:“这是围屋主人的女儿阿玉,在香港做大生意,你联系她找老照片。”
微信是个英文名,主人头像看来是位四五十岁的富家太太。邓妹犹豫一下,问奇哥:“我应该怎么称呼她?邓总?”
奇哥说:“太生分了,直接叫名字就行,她还要叫你姑姑呢!”邓妹在族中辈分颇高,有些同龄或年长的族人,见了她还要唤一声姑姑甚至姑婆,令她周身不自在。
微信加上了。阿玉在语聊中用客家话热情地喊邓妹“姑姑”,邓妹期期艾艾答不上一句话。阿玉有些急性子:“你冇识讲底话?敢样冇得,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底(方言:的)在香港的阿焦仔,就算冇在村里,但客家话讲得好正的。”
“我、我会慢慢学的。”邓妹像个小学生般讷讷地说。
邓妹跟着奇哥走在田埂小路上。金黄的稻海间有一棵树,树枝飘逸出尘,红色小果如红霞朵朵。邓妹好奇地问那是什么树,奇哥说那是熊胆树。树下另有一小片低矮的绿色植物生长在水田里,枝条呈绿色长细杆状,造型奇特。邓妹诧异:“这又是什么?”
奇哥闻言又笑得岔气:“城里人五谷不分,连马蹄(茡荠)都冇识!”说完拔起一根绿色细杆,果然其下连着一个黑色的马蹄(茡荠)。
邓妹觉到很没面子,于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去买几扎白玉蔗。”
云垌的白玉蔗是扎束种植的,以老蔗叶将多根玉蔗绑成一束,使其整整齐齐地长大,远看像椰子树,有些成熟早的已开始收割了。
邓妹拿起一截刚砍的白玉蔗,正想去洗洗,转头看见奇哥蹲在田头,拎起蔗条随手拍去泥尘,撕开表皮就啃。邓妹也跟着蹲在田头啃起蔗来。撕蔗皮并不费力,白玉般的蔗肉嫩得不像话,轻轻一咬就迸发出一股清甜蔗汁,在舌尖上化开。看来白玉蔗被誉为“果中珍品”不是随便一说。
啃着蔗,邓妹就忘了奇哥刚才的嘲笑,又习惯性地提问:“白玉蔗会开花吗?”
“会。开花耗营养,蔗汁品质就差了。在开花前就得收割。”
大部分水果都是花朵的产物,只有白玉蔗必须放弃花朵,才能成“果”。
村里有好多人就像白玉蔗,沒有花哨的架子,讲话做事却耐人寻味。
邓妹在家里做饭,用不伦不类的发音反复哼唱一支歌:“哦嗨……故乡介山歌青山间流,故乡介山歌从春唱到秋……”
孩子问邓妹唱什么,邓妹认真地说我在学客家话。
太阳雨
出版社催邓妹交村志定稿。一连几个周末,邓妹让孩子跟爸爸回乡下,自己专心对稿。将志稿中的大事记与各篇章细节内容逐一比对,检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各要素,纠正有偏差的细节,找编委会讨论……要做的事情太多,邓妹从早到晚吃饭睡觉都抱着书,梦里都是文字和图片飞来飞去。周末和晚上不够用,就把公休假全部安排上,邓妹瘦了一圈。孩子爸爸从乡下回来看到邓妹黑眼圈蓬头垢面的样子吓了一大跳,说这真是修志走火入魔了。
白玉蔗丰收的季节,云垌村志正式出版了。
一辆货车满载着印刷好的村志新书,开到了邓妹面前。那一瞬间她有点恍惚,等待这一刻,已经等了太久。
邓妹招呼开车师傅帮忙把志书一箱箱卸下,推进储物房清点。两千五百本新书,整整齐齐地码在邓妹的面前,这可是凝结了阿爸和众多父老乡亲几代人心血的智慧结晶啊!
那天本来是个大晴天。可是当邓妹清点完志书时,门前突然掠过一阵风,原本强烈的阳光变柔和了,雨点纷纷从天而降。
邓妹疯了似的跑出去站在雨中,仰望苍穹,泪如雨下。
阿爸,是你吗?你看到村志了吗?
邓妹跟着编委会回村,开村志发布会,她代表阿爸向乡亲们深深地一鞠躬。编委会把村志赠送给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收到了热烈的反响,好多人都争着想多要几本书,分发给外地老乡。
赠书活动结束后,邓妹整理会场,发现有个座位上遗落着一本村志,连塑料封装都没有撕开。
会场外,一个染着黄头发的小年轻正跟同伴商量去某个网红打卡点。邓妹走过去沉下脸说:“小风,你的书忘拿了。”
小风否认:“不是我的书。”
邓妹把书塞进他怀里。他躲闪着说:“我一看书就瞌睡,这书送其他人吧,别浪费了。哎哟,打我干吗?”邓妹撵着他一顿敲打:“我就是要打醒你,你阿爸年纪大了不便回来,你不把书交给他,我饶不了你!”
“我带,我带!这书有什么好看的,矫情。”
“不懂就好好学,云垌的历史,是一部客家人迁移的历史……”
“姑姑,我发现你说话越来越像八叔公了。”八叔公指邓妹的阿爸,他在族里同辈排第八。
系客家妹
村委的电脑坏了,邓妹的哥哥跟几个老乡买了新电脑送到村委办公楼。村里组织“社科大讲坛”,一群穿着红马甲的文化志愿者涌进云垌村,邓妹也走在队伍中。途中经过祠堂,看到正厅新挂了一盏花灯,灯下一个小婴儿正熟睡在母亲怀里。客家人的风俗,凡有添丁,都举行上灯仪式。
邓妹停下来出神地看着那灯,心里涌起一种仪式感,族谱里又该添一个新名字了。
这时大路边传来一个刺耳的声音:“你们修的路都不经过我们屯,凭什么要我捐钱?”邓妹循声望去,原来是小风直着脖子正跟村支书争吵。
另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莫吵!条条大路通罗马,莫管在哪个屯,对底村有利,就捐。支书,收那份。”是奇哥,他一边用微信转账,一边踹了小风一脚,小风不服,但没吭声。
邓妹走过去问怎么回事,村支书和奇哥说村委正挨家挨户动员捐资修路,让同村兄弟们一起出力拓宽村里的路,捐资无论多少都是心意。
“捐钱修路算我一份。”邓妹对支书说。
“好咧,欢迎外嫁女回村支持家乡!”
邓妹豪气地说:“莫叫外嫁女,敢见外,系客家妹!”
略带生硬的发音把村支书和老乡们逗笑了。
“笑麻介(方言:什么),莫讲女子不入谱,族谱和村志里,有底客家妹介(方言:这)名字!”邓妹一本正经地说。
八岁的小侄女菲菲问:“姑姑,我也是客家妹,那我的名字也在族谱里吗?”
“当然,从前女子记姓不记名。现在不同了,无论生男生女都记名。你的名字是你爷爷帮记上的,你是云垌村邓氏第八代传人,好好记住了。”
一个中年汉子热情地对邓妹说:“姑姑,上次我看见你在日报社直播间介绍村志,为咱村代言了!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尽管交代我们!”这是在广东创业的阿兴,恋土情结颇深。
邓妹看了看比自己大了将近十岁的阿兴,再看看八岁的菲菲,又想起香港的阿玉,他们都喊自己“姑姑”,他们的名字都在同一本族谱里。族谱里有很多很多名字,每个名字代表一段人生,有的人生已经画上句号,有的才刚开始。如果没有族谱和村志,也許就不会有他们此刻的交集。邓妹对阿兴说:“叫我名字就行,不用论那么多。”
“不行,辈分不可乱。那边屋介大堂哥的大儿子,快七十岁了,还要叫你姑婆呢!”
邓妹终于落荒而逃。
新的开荒
年轻的村支书坐在村委,低头看着云垌的规划图纸,眉头紧锁。这是一个当过兵、下过海的年轻人,他的祖上从广东迁来,他的父母又回到广东创业,他的童年一半在云垌村度过,一半在广东度过。冥冥中似乎有种声音在召唤他,促使他回到童年的村庄。
邓妹看着他,想起了多年前退休的老支书。老支书就是两百多年前第一个迁入云垌村的客家汉子的后代,这村里的每一块地,都是客家先人在两百多年前一镢一镢开荒得来的。
乡贤会上,来自各个行业的同乡都一致提出,保护好围屋,老祖宗留下的宝贝毕竟不多了。
年轻的村支书的眉头蹙得更紧了。村里有块闲置地,大部分村民都同意用作围屋周边道路和停车场。偏偏有一个性格倔的村民不同意,事情就被耽搁了。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村里的事情从来就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直接简单明了。同一个老祖宗的子孙后代们,虽然不再住在同一座围屋,但依然有着相同的倔脾气。
村支书和奇哥准备约几位熟悉村里事务的乡贤,找那位村民出来聊聊。
令人头疼的那块地,就像两百多年前被挖出的第一个土疙瘩,在其静默的内部,是盘成一团的草根和石砾,需耐心捋顺清理。
村庄也是由一个巨大的土疙瘩变出来的婴儿,慢慢长大,又慢慢成为一个老者。
但这么说好像也不全然对。
还是换个说法吧。当人们看到陈旧的围屋时,村庄像一位老者。当看到新起的红砖房和小别墅时,村庄像一个青壮年。当人们试图把网红墙、奶茶店、微花园、公交车的概念引进村庄时,它又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了。
因此,现在的村庄,既是老人,也是青年,也是孩子,它一边老去一边重新长大。父辈沉甸甸的铁镢交到了年轻人的手里。新的荒野出现了,年轻人一步一镢,延续着开荒的历程。
邓妹拎着一把从池塘边采来的瓜蒌叶,牵着菲菲,去堂哥家做豆腐酿。
偶遇阿爸从前的学生,热情地和她叙旧:“以前你爸妈都回过村呼吁修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就是第一条能让小汽车开到村宅边的路。”
脚下之路一直在蜕变。
当先祖背着单薄的行囊第一次走过时,这儿还没有路。
爷爷挑着稻谷走过,这儿形成了一条泥路。
阿爸骑着二十八寸自行车经过,这儿变成了石碴路。
哥哥开着小汽车经过,这儿变成了平整的水泥路。
现在,村里想修一条能让大巴车通行的大路,一条能够连接起公路和围屋的大路。
有人修路,有人修志,所修的都是道,此道连接起过去、现在、未来。在拓荒者的脚步声中,沉睡的乡村正在苏醒。
月亮对着池塘照镜子。天上的月亮落入凡尘,化作一叶扁舟,在时空里浮沉。
皎洁的月光下,一只老虎缓缓而行,一只小鸡破壳而出,它们彼此对视,又在彼此的眼眸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邓卉,贵港市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广西作家协会会员、贵港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贵港市诗词学会副会长,曾担任贵港市首部传统客家村志《云垌村志》编委。热爱自然万物,专注于有知识性、思想性和哲理性的文字,作品散见于《广西文学》等。】
责任编辑 韦 露
——江苏省张家港市较大规模推进村志编纂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