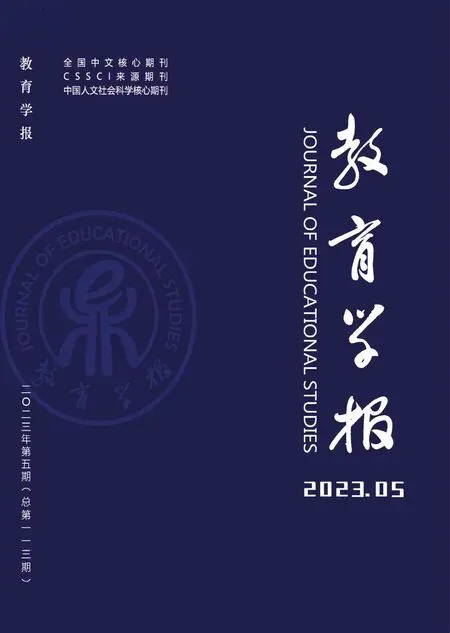回归核心知识:美国赫希课程思想及其启示
张旭亚 殷世东
(福建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福州 350007)
20世纪20年代,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为先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以教育思想“革新”为显著特征,对美国教师教育和基础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50年代,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形式主义、技能主义、反智主义、反课程等思想,开始在美国教师教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60年代,受进步主义思想熏陶的教师占据美国公立学校教师的大多数。1983年,美国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布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A Nation at Risk)显示,美国基础教育质量严重下滑,社会不公问题也进一步加剧。艾瑞克·唐纳德·赫希(E.D.Hirsch,JR.)是美国教育学家、语言学家。他认为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美国主流教育思想过于偏狭,导致基础教育出现了严重的“轻视知识”现象。为此,赫希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起了一场以“捍卫核心知识”为宗旨的课程改革运动,进而成为美国“学校重建运动”(school restructuring movement)的典范。
一、观念偏狭:赫希对主流教育思想的批判
赫希在对美国教育现实困境的研究过程中发现,造成基础教育课程“知识匮乏”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教育理论中的六种主流思想出现了问题。
(一)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导致课程知识虚化
自然主义(naturalism)认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自然人,自然的事物和自然的发展都是好的,因此教育也应遵循自然,让儿童按照天性发展。[1]赫希认为,这种自然主义观点具有“天赋个人主义”(providential individualism)的意味,并因看似具有极强的“人情味”和“关怀性”,而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2]11事实上,自然主义关爱儿童、尊重儿童的立场本身并没有问题,但其预设儿童会自然而然拥有各种知识和能力的观点缺乏科学根据,是必须对其进行反思的关键所在。在这种思想的预设下,相应的课程内容往往缺乏实质化、系统化的知识,容易出现过于单薄、零散、虚幻的问题。同时,在课程实施中教师也会因持有一种“顺其自然”的心理,导致整个过程失去应有的程序性和进阶性,这样的课程无法有效、高效地传授知识和技能,教学质量与学习质量自然也就低下。另外,自然主义认为,教育是一个具有自身本来形式和节律的自然过程,这种形式和节律因人而异,而且当它与自然的现实目标和生活情境相结合时,效果最佳。具体到课程方面,就表现为课程目标的空泛和不明确。实际上,诸如母语、行走等初级学习能力在自然状况下确实能够得到良好掌握,但类似读写等次级学习能力则无法在自然状况下发展至较高的水平。也就是说,课程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实施途径,应设置从初级到次级的连贯、明确的目标,才能实现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渐进性、进阶性掌握。
浪漫主义(romanticism)教育思想中充满了“人性本善”“圣洁”“乐观主义”“友善”“阳光”“美德”“神圣”等美好的词汇。在反对和批判传统教育思想的话语中,则往往会使用“死板”“堕落”“不健康”“不自然”“有害”“腐败”等词汇。按照浪漫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学生的发展:每个学生的能力都是不同的,有着自己先天注定的发展速度,不能用外力去强迫他学习,使其达到与其他人相同的水平,否则有可能会伤害到学生心理或生理的健康。在这种浪漫主义思想影响下,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对教幼儿识字、拼读、算数等持有较为消极的态度,不仅在课程设置中过于规避事实性知识(factual knowledge),在课程实施中也出现了一种重视活动而轻视知识的现象。如若坚持这种片面的浪漫主义儿童发展观和课程观,就是给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合理化学生间差距的理由,而这种合理化会让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孩子更积极努力地学习,而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孩子则可能就此屈服于自身弱势的现状。与此同时,在课程目标制定和课程评价等过程中,教师也理所当然地对不同孩子提出差异性的学习要求,鼓励学生按照自己的速度学习和发展,即所谓的“自速学习”(self-paced learning)和“适当发展”(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这看似是在倡导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目标,实际上很可能导致学生间差距的再次扩大。正如赫希所说,“人类活动几乎没有是在顺其自然的情况下圆满成功的”,而“文明的目的要想实现,教育的结果要想达成,都不能完全顺随人的天性,而是要尽量引导其走向人道的和有价值的目标”[3]77。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善意的干预,“如果没有干预,就等于不存在教育的意志,也就等于不存在教育,那教育者也就不成其为教育者了”[4]。因此,教师在课程实施中不应该盲目地遵循所谓“自然”和“浪漫”,而是应该恰当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和引领作用,促进学生更有效、更科学地学习和成长。
(二)形式主义与技能主义导致课程知识低质
形式主义(formalism)认为,“过程实际上是内容的最高形式”[5]。在课程知识方面,形式主义认为“在学校里学到的特定知识(智力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远没有获得正式的学习方法那么重要,因为这些方法有助于学习未来的知识。”[3]219并且,当前知识的更新和发展速度极快,知识的未来需求难以把握,届时可以通过各种参考书、技术工具等轻松获取,因而不需要教授事实性知识。[6]这种形式主义观念对美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目标和知识结构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课程目标层面上,表现为倡导培养一种能够将外在模式或策略应用于新问题的能力。在课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对传统课程的排挤,以及对注重所谓形式的实践型课程的鼓励。尤其明显的是,1926年美国小学的3R(读书、写作、算术)传统课程的占比,相较1856年下降了20%以上,而图画、体育、音乐、活动、手工等经验性课程比例则大幅度上升,课程结构的整体比例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7]
技能主义(skill-centrism)倡导要培养以批判性思维为代表的通用技能(general skills),以及获取信息所需要的认知技能(accessing skills)。这种通用技能和认知技能被认为具有迁移性,能够有效运用到不同的主题和领域当中,并达到较高的水平和效果。在课程设置中,事实性知识遭到了技能主义者的反对,被看做是占据学生宝贵时间的“无用之功”,导致了课程中事实性知识地位的低下。事实上,虽然批判性思维能力(critical-thinking skill)、高阶思维(higher-order skills)等技能本身确实存在,但那种寄希望于某个领域内的一种思维技能可以无条件、可靠地转移到其他领域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赫希指出,任何领域思维技能的培养和提升,诸如阅读、写作、分析、学习等实际能力,都无法离开“某个领域的特定知识”独立存在,都需要以广泛的、完整的与该主题相关的背景知识为基础,并不存在所谓的跨领域、跨学科、跨主题的通用技能。在国际层面,有研究在进行比较后发现,那些采用高质量、系统化课程知识的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虽然没有美国这么重视所谓思维和技能的训练,但是在实际测评中的成绩表现却远远超过了美国。[8]总之,具体课程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于一个个清晰的学科主题上,并以全面、系统、高质量的主题知识作为课程内容,才能够真正有效培养和提升学生基于特定领域的思维技能。
(三)反智主义与反课程运动导致课程知识空洞
在形式主义和技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误以为学校能够培养学生独立于具体事实和相关知识的“高阶思维”“批判性思维”等能力,导致对事实性知识、公共知识的批判声也愈演愈烈,这种态度和立场被称为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9]赫希认为,这种反智主义的课程思想正是造成美国教育失败的重要原因。反智主义理论秉承着诸如“知识容易过时”“事实不如理解”“教儿童而不是教学科”的主张,对于“纯粹事实”(mere facts)的学习持有反对和厌恶的态度,形成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反知识观”。反智主义认为,在当今这个“新技术世界”“知识爆炸”的时代,许多“今天的事实”对于未来没有价值。因此,在课程编制的过程中他们极力排斥诸如“七大洲的名称与形状”这类事实性的知识,认为这是无价值、无意义的内容,认为在学校教育中传授这种“与学生个性兴趣和现实生活经验相距甚远的知识”,会“造成支离破碎、枯燥乏味和不人道的学习后果”[3]54。
这些具有反智主义思想的教育工作者,对事实性知识所怀有的轻视、排斥,甚至是厌恶的态度在实践中不断扩大和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一场反课程运动(anti-curriculum movement)。反课程运动倡导者认为,所谓“真正的知识”应该是把握“事物的相互关系”,并且应当是在实践中获得的。然而他们却无法解释,现实中的美国学生为何未能在实践中获得所谓“真正的知识”。他们打着“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教孩子而不是教学科”等口号为自己辩护,称自己并不是在反对知识本身,而是反对“不连贯”的事实性知识。在反课程主义者看来,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要依据儿童自身的发展规律开展教育,认为理想的学习状态应当是能够解放儿童的天性,并能够让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10]44赫希认为,20世纪50年代是反智主义、反课程思想影响美国教师教育领域的重要时间点。到了60年代,这批受反智主义、反课程思想熏陶的教师逐步进入公立学校,并将相关思想付诸于课程与教学的实践当中,对学生的课程知识学习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发布的1965—2005年SAT的数据显示,学生语文和数学成绩从6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急速下滑的现象。
在赫希看来,以上这六种思想之所以能够对美国基础教育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究其根本是它们与“美国文化中自然生成优于人工制造的浪漫主义偏好”相符合[3]257,虽然倡导者的出发点是正义和高尚的,但与美国学校教育中的现实情况相矛盾,导致课程轻视知识问题的出现。
二、轻视知识:赫希对课程问题的揭示
赫希指出,美国基础教育阶段出现了严重的“知识匮乏”现象,学生学习质量严重下降,社会不公问题也进一步加剧。
(一)学生学习质量下降
“知识匮乏”的课程导致美国学生知识基础的不牢靠,各种形式的考试也遭受到了抱怨与规避。
1.学生知识基础不牢
在国际层面上,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于1988年发布的工作报告中指出,通过比较1970年和80年代开展的两次跨国的科学成就研究数据表明,在参与调查的17个国家中,1970年排名第七位的美国在80年代却跌落至第十五位。IEA认为,这种显著性的下滑应当引起美国教育界的特别关注。[11]另外,就美国本土范围内来看,1983年由美国教育部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发布的《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显示,17岁的青年中近13%是半文盲,少数民族青年的半文盲比例高达40%,成年人中更是约有2300万人为半文盲。由此可见,美国的教育质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该报告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育报告,在美国产生了极大的轰动,再次证明美国教育亟需变革。实际上,无论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标准化运动,2002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law,NCLB),还是2010年的《各州共同核心标准》,美国政府和教育工作者都在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方法改变这种成绩持续下滑的局面。但据《国家教育进步评价》(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NAEP)报告显示,此类行动和法案所取得的效果微乎其微。赫希研究发现,这是由于此类改革仅仅停留在结构性调整的层面,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即课程内容本身存在的“知识匮乏”现象。[12]
2.考试受到抱怨和规避
一直以来,美国社会都对考试有着各种抱怨,甚至在教育实践中,也出现了排斥考试、规避考试的现象。对考试的抱怨主要有两种。其一是认为考试的命题方式出现了问题,导致教师未能针对学科教学的主题及课程内容开展教学活动,只是盲目地围绕着考试项目进行机械化、重复性的技能训练,从而使课堂教学丧失了应有的知识传授价值,造成学生的学习枯燥且乏味。其二是认为美国的中小学将开展考试作为教育改革的主要手段,过于依赖那些现成的考试,从而出现了滥用考试的现象。教育政策制定者们为了不因考试目标和策略的问题左右为难,鲜少对考试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调整。不仅如此,教师的教学重点也被局限在将要评测的特定题目上,这种片面化、浅层化的测试无法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无法反映出学生的真实水平,无法发挥考试反哺课堂教学的应有价值。
(二)课程变化导致社会不公问题加剧
伴随着20世纪初公立学校的衰退,一股倡导个性与技能,反对传统教育的思潮成了美国教育思想的主流。在这种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基础教育课程缩减和忽视具体的知识内容,这种课程变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社会不公。
1.优势与弱势家庭学生之间的差距扩大
因家庭之间存在差异,学生所具备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也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优势家庭的学生来说,学校往往只是教育活动的场所之一,同时他们所享有的良好家庭教育和校外教育,能够创造丰富的语言环境和浓厚的学习氛围。因此,优势家庭的学生已经在学校以外的地方积累了一定的公共知识和文化基础,即使课程中缺乏系统化的事实性知识,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但对于弱势家庭的学生来说,由于缺少获取知识的其他渠道,他们的学习几乎完全依赖于学校的课程学习。这就意味着,学校课程公共知识的缺乏,会对弱势家庭的学生造成更大的损害,进而导致与优势家庭学生间差距的再次扩大。[10]163这种优势家庭和弱势家庭学生间的差异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具体表现为:文化背景的差异、知识基础的差异、学习速度的差异、学习质量的差异等。如果后续的课程实施未能对这些差异进行有效弥补,则会导致优、弱势家庭学生间的差距随着年级的增长持续扩大。
2.高人口流动率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高人口流动率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现象。美国审计总署(The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调查统计发现,美国每年搬家的人口比例高达五分之一。对于学校教育来说,高人口流动率意味着会有较大数量的学生面临一次或多次转学的情况,而转学就必然会对学生的学习造成影响。事实上,大部分美国学生在随家庭迁移到新学校后,在知识学习方面都难以较好地适应和衔接。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缺少清晰明确的课程标准和统一连贯的课程。不同州,甚至同一州的不同学校,所教授的课程知识都存在很大差异。学生接受的知识内容往往是片段式的,无法将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不同主题下的知识连贯化和系统化。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进入新学校时难以具备新学校课程学习所需要的背景知识(background knowledge),从而也就无法实现知识的有效衔接,学习的质量自然也就无法得到保障。赫希认为,虽然这种因流动而对学生学习产生的不利影响是无法避免的,但通过提升学校课程内容的公共性和基础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13]
三、核心知识:赫希对学校课程思想的重建
赫希课程思想体系的成熟,以1987年《文化素养》一书出版为标志。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又相继出版了《我们需要怎样的学校》(1996)、《知识匮乏》(2006)、《造就美国人》(2009)、《为什么知识很重要》(2016)、《如何培养公民》(2020)、《美国的种族》(2022)六本教育学专著。赫希认为,学校要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设置与实施核心知识课程,让学生能够掌握共同的基础知识,获得成为公民必备的文化素养。
(一)基于质量与公平的课程目标观
赫希认为,要构建基于质量与公平的课程目标观,让学生能够做好学习的准备,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优势与弱势学生之间的差距,实现教育的补偿性均衡。
1.做好学习准备
美国的中小学有着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宗教的学生,学生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赫希指出,“对于每所学校来说,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确保本校的所有孩子都能够具备在下一学年学习所需要的知识。”[3]33据2012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Th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研究发现,诸如日本、芬兰、韩国等小学办学质量较好的国家都拥有清晰的课程标准与具体的课程内容。[2]93-94由此可见,清晰的课程标准和课程内容是学生获得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技能、做好学习准备的重要前提条件。
为了真正将“做好学习准备”这一目标落实到美国的教育实践当中,赫希及其核心知识基金会编辑出版了具有一致性、连贯性、综合性特征的核心知识系列教材。在实施核心知识课程的学校中,教师能够为同一年级的儿童提供相对明确的知识内容,让学生得到系统、连贯的知识教学。当所有的学生都具有学习所需要的背景知识时,教师就能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复习和补漏上转移到新知识的教学上,教和学的效率和效果都会得到质的提升。同时,优势学生和弱势学生都能获得更多的新知识,并为接下来的课程学习做好学习准备。[14]
2.缩小学生差距
赫希指出,学生家庭之间存在的“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差距,正是导致美国教育不公平的重要原因。知识具有累积性,同样,差距也具有累积性。学习是在已有累积知识上进行的,先前的学习缺损如果未能得到及时修复,则会随着年级的升高进一步扩大。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补偿性的服务,培养学习所必备的知识与技能,通过核心知识课程弥补缺损,让同一年级的学生在学期结束的时候能够达到相对一致的水平。虽然核心知识课程的实施无法完全弥补优势与弱势学生间的差距,但是通过弥补学生的知识缺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和缩小这种差距。
以语言学习为例,核心知识课程能够有效缩小学生之间语言成绩的差距。[2]92学生词汇和语言学习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年级课程内容的包容度和广度。同时如果教师在实际的课程实施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教授丰富、扎实的知识内容,就能够让基础较差的学生获得比基础较好学生更多的词汇和语言知识。研究显示,法国的小学通过采用系统的教学内容标准,在学习至六年级的时候,不同群体学生间的成绩差距在全国层面上得到了大幅度缩小。也就是说,系统的课程内容和教学内容能够在提升优势学生成绩的同时,更大程度地提升弱势学生的成绩,从而减小优势学生与弱势学生之间的差距。
(二)基于语言与文化的课程内容观
虽然美国的每个州和地区都有自己的“课程指南”,但实际上其中并未清晰指明每个年级学生所应学习的具体内容。这种缺乏精确性的课程指南实际上正是导致学生学业表现差的重要原因。为此,赫希认为要构建基于语言与文化的课程内容观,倡导制定明确、系统的课程指南,培养能够掌握标准语言(standard language)和标准知识(standard knowledge)的美国公民。
1.传授标准语言
在美国,标准语言被部分人士称为“上流社会的特定阶层语言”,因而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和反对,甚至还有人强烈指责公共学校,称教授标准语言的学校教育是一种文化强权主义的现实体现。由于担心陷入各种争议,教师、学校管理人员、教材编写人员,甚至政策制定人员的行动都谨慎起来了。事实上,标准语言并不是某个特定阶层的语言,它所蕴含的也不是某个特定群体的文化。标准语言是一个国家的报纸、广播等媒体所使用的语言,它的产生与确定,往往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其中蕴含着一个国家历史与文化发展的隐形财富。
赫希认为,掌握标准语言是参与公共社会生活的前提,学校教育必须承担起教授学生标准书面用语和口头用语的责任。[15]40-41他特别指出,对于部分学生来说,标准语言与他们在家庭中习得的母语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学校教育的压力较小,发挥的是补充和完善语言能力的作用。而对于另一部分母语与标准语言不一致的弱势学生来说,若学校不教授标准语言,他们就无法学习和掌握标准语言,也就不具备有效理解社会公共文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反对教授标准语言的行为才是对弱势群体、少数群体真正的排挤和压迫。另外,语言的统一化和公共化是美国公民之间得以交流、各州得以团结的前提性条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普及化的教育和标准化的语言,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将难以进行。
2.提高文化素养
赫希指出,文化素养是学生建构完全公民身份的唯一门票。对于学生来说,仅仅掌握标准语言还不够,无论是书面语言的理解还是口头语言的沟通,都要以相应的背景知识为基础,以一定文化素养为支撑,才能有效进行。[16]然而,由于受美国主流教育思想的影响,在形式技能得到大力倡导的同时,标准知识与公共文化却遭到了排斥。令人深思的是,《文化素养》的出版,使赫希被称为是一个“试图阻碍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文化反动分子”,有关“文化素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被看做是一场“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 hegemonism)下的文化攻势。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教育领域中公共知识的确立与传播,是提升公民文化素养的必要前提。[17]主流文化和公共知识虽然不是一个人学习能力发展以及经济收入提高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只有掌握主流文化和公共知识,才具备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基础,才能够有效把握语言文字背后的含义,才能够学习和掌握其他社会生存所必需的能力。[10]152一个在其他领域能力突出的人,如果缺乏某个主题的背景知识,也难以通过词语文字本身来判断其所表达的涵义。也就是说,诸如交流、阅读这类理解性、解释性的活动,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比所谓技能和技巧的影响要大得多。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Florida)有一所大型混合公立小学,名为三橡树学校(Three Oaks School)。在校长康斯坦斯·琼斯(Constance Jones)的带领下,该校成为全美第一所按照《文化素养》中相关课程与教学原理办学的学校,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受该学校的影响,校长杰弗里·利特(Jiffrey Litt)也将相关思想引介至自己所在的67号莫希根学校(No.67,The Mohegan School)。这两所学校因在学业成绩方面的显著表现,不仅得到了《生活》(Life)、《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等杂志和报纸的关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也带动了一些其他学校对核心知识课程以及相关课程理念的尝试。
(三)基于考试与知识的课程评价观
如何运用考试和传授知识是课程实施的关键所在。赫希认为,只有有效运用考试,才能够准确把握学生的课程学习状况;只有构建基于共同基础的核心知识课程,才能为学生打下牢固的文化基础。
1.有效运用考试
考试是课程评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如何更科学、更有效地设计和运用考试,是需要不断反思和完善的问题。传统的标准化考试之所以无法有效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主要是因为它未能针对课程内容进行考察,而是试图去评估所谓的思维能力和通用技能。这种与具体学科知识内容脱节的考试方式,不利于教师有效评估和判断学生对不同主题、不同学科中课程知识的掌握水平和欠缺情况,同时,教师也无法根据考试结果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进而导致考试实际功能的低下。[18]
赫希认为,有效运用考试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确保考试的不可预测性,让教师和学生无法有针对性地为考试做准备,即无法局限性地学习某些主题内容,或者机械化地训练所谓的解题和应试技巧。因为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的不确定性,学生会通过阅读大量不同主题、不同类型的知识材料为考试做准备,在阅读过程中实现知识的积累与拓展,真正有效地提升阅读能力。[15]102-106另一方面,确保以学校课程中的具体知识为核心内容,精心设计考试,以科学评估学生的学习水平,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19]
2.构建核心知识课程
随着有关课程思想的成熟,赫希于1986年募资创办了基金会,命名为“文化素养基金会”(Cultural Literacy Foundation),后因其中“文化”(Cultural)一词容易引发歧义,更名为“核心知识基金会”(Core Knowledge Foundation)。核心知识基金会致力于为基础教育研制课程与教学的内容体系,让更多的学校使用系统、扎实的核心知识课程,从而推动美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回归核心知识”的课程改革。核心知识基金会在建立之后,历经四年的研究和探索,研制出了从幼儿园至八年级的核心知识系列教材,并以此为载体构建了核心知识课程。核心知识课程的目标是让所有的美国学生都能成为“受过优质教育的学生”,促进美国教育的“优异与公平”(excellence and fairness)。该课程明确规定了不同年级学生所要学习的主题,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方面都提出了更加细致的要求,与此前美国基础教育阶段所使用的课程和教材存在显著性区别。[20]从课程知识构成上来看,核心知识课程的内容遵循共享性、稳固性、序列性和具体性四项原则。首先,课程知识具有共享性。这种共享的知识(shared knowledge)受基础文化知识(literacy)、社会的流动(social transience)和社会的内聚(social cohesion)三方面因素的要求,是由被美国社会所认可的、沟通交流所需要的知识构成。[21]其次,课程知识具有稳固性。这种稳固的知识(solid knowledge)能够经受住时代发展和历史传承的考验。再次,课程知识具有序列性。这种序列的知识(sequenced knowledge)体现在不同年级之间课程内容的衔接性、连贯性,能够避免知识内容出现断裂和重复的情况。[22]最后,课程知识具有具体性。这种具体的知识(specific knowledge)意味着课程内容的清晰化,能够让教师和学生都明确不同主题、不同学科、不同年级课程的详细内容。
然而,核心知识课程因其具有“共性”“统一性”等特征,被认为是一种与富有多元性的美国相背离的事物,被贴上了“反美国精神”的标签,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实际上,美国社会之所以会如此强烈抵制核心知识课程,是源于对“统一”的深刻恐惧和误入歧途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些民众甚至将20世纪早期秉承传统办学模式的学校称作“工厂型学校”(factory-model schools)。相关抵制者指出,瑞士与美国相似,也无国家级的核心课程,但其教育却表现较好。实际上,这是因为瑞士的每个行政区都有区级的核心课程,其中包含了系统且详细的课程知识。如果美国也采用这样的核心课程,同样也能够让学生做好学习准备,即使学生跟随家庭流动后,仍然能较好地适应新的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在部分核心知识学校的实践影响和教育媒体的持续报道下,使用核心知识课程的学校越来越多。据2023版《核心知识序列》显示,截至目前,美国已有大约1万所学校正在使用核心知识课程(1)参见:Core Knowledge Foundation.Core Knowledge Sequence:Content and Skill Guidelines for Grades K-8[S].Charlottesville:Core Knowledge Foundation,2023:vii.,遍布近50个州。核心知识课程和核心知识运动的影响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对英国、加拿大、挪威、葡萄牙、韩国等国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启 示
赫希的课程思想不仅对美国基础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和学校课程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警惕教育理论的极端化
赫希认为,美国的师范院校在美国的教育界传播着一套看似可靠、实际无效,且缺乏科学依据的理论话语。这套话语体系在师资培养的过程中得到了不断复制和传播,在极大程度上维持了教育界绝大多数人,包括教育研究者、教育从业者等群体思想的统一性和较强的专业共识。赫希指出,这实际上是美国教育理论界维护自身话语方式和教育主张权威性的重要手段。诸如“整体教学”“成绩评定”“标准化考试”等术语和理念遭到坚决反对,而“实践性学习”“发现式学习”“自主学习”“合作学习”“非标准化评估”等观点却受到大力推崇。由于传播这些观点的人是师范院校具有一定地位的教授和学者,从而赋予了这套话语体系极强的说服力和权威性,使一批进步主义教育的拥护者站到了与传统教育思想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去。
这种教育术语对立(educational terminological polarization)的现象长期存在于各国教育理论研究中。然而,这种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价值立场容易将不同理论的思想观点简单对立起来,造成理论研究的片面化和极端化,这是作为教育理论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当警惕和避免的行为。实际上,教育理论研究者“为了儿童”的基本出发点都是一致的,之所以在理论观点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主要是因为看待教育的立场、视角和维度有所不同。因此,教育理论工作者应自觉秉持客观、谨慎、辩证的学术态度看待不同的理论观点,有机汲取其中合理、科学的部分,竭力避免教育理论研究的极端化现象。就我国21世纪以来的课程改革而言,在本质上并不是要对传统教育思想进行全盘否定,而是要借鉴国内外课程与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现行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以《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版)》为例,尽管它特别强调核心素养、学科实践,但并不等同于否定核心知识、课堂教学的基础性、前提性作用。因而,无论是教育实践工作者还是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运用辩证的眼光予以解读和践行,警惕为了突出所谓的“新”和“改”而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之中。
(二)谨慎运用主流研究成果
当前,教育研究领域存在着一种“盲信主流研究”的现象。将西方的“新理论”“新思想”视为“科学”和“权威”的标志,部分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甚至盲目推崇某些主流或新生的研究发现,对所谓的观点和成果不加以考证和深究就予以使用。然而,这些所谓“先进”的理论是否科学、是否合理、是否全面,均有待进一步考证。同时,当前教育领域还存在着一种“研究的选择性利用”现象。有些研究者只截取部分与自身观点相一致的研究结果,为其披上“权威外衣”的同时,故意忽视其他不一致的部分。这种刻意的选择性利用是一种对学术和科学的不尊重和不负责任,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
赫希指出,作为教育研究工作者,在分析和使用各种教育理论和研究成果时,应当时刻提醒自己做一名“清醒的怀疑论者”[3]16-17,要能够从客观的立场出发,避免受到自身研究偏好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盲目地信从某一种理论或思想。教育理论只有具备真实性和完备性才能够有效指导实践,否则就失去了生命力和解释力。正如在教育学和心理学领域,有关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受到众多学者的引用和推崇,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然而,大多数的研究仅停留于对皮亚杰早期观点的认识,熟不知皮亚杰在后期的研究过程中早已对自身的理论和观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23]事实上,这种对主流研究把握的局限性和片面化并不少见,而这往往会导致部分学者“断章取义”地引用和分析,并得出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的研究结果与结论。总之,教育研究者要持以谨慎和质疑的眼光看待各种研究成果,以科学严谨的学术态度进行判断和分析,同时,要结合我国教育的现实情况,科学合理地予以使用。
(三)提升课程的衔接性和系统性
美国基础教育阶段不连贯、不统一的课程体系,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产生了许多的负面影响。对于那些在基础词汇与背景知识方面相对薄弱的学生来说,对学校课程的依赖性远远高于那些来自优势家庭的学生。然而,学校的课程由于缺乏连贯一致的内容,根本无法在课堂教学中有效地传授基础知识,弱势学生的学习需要也就无法得到满足。[24]对于美国来说,想要提升基础教育质量,首先就必须设定明确、详细的课程方案,在此基础上为学生设计具有系统性、衔接性的课程内容,落实向学生传授一致性和系统性的核心知识的课程目标。
反观我国基础教育,如何提升课程内容的衔接性和系统性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就衔接性而言,基础教育课程由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三个阶段课程构成,不同年级、不同学段之间课程的衔接都至关重要。这种衔接性应当是一种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多个维度共同实现的结构性衔接。[25]知识的学习正如树木的生长,旧枝干滋养着新枝干,旧知识也支撑着新知识。旧枝干越茂盛,树木生长越快,旧知识越扎实,新知识学习也就越快。[26]《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版)》更是对学段衔接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特征,注重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之间的衔接,体现不同学段目标要求的层次性。”[27]4就系统性而言,在课程建设过程中要“加强一体化设置,促进学段衔接,提升课程科学性和系统性”[27]2,在内容方面要“加强课程内容的内在联系,突出课程内容结构化”[27]11,在教材编写方面要“关注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强化教材学段衔接”。因此,通过课程衔接性和系统性的提升,能够更好地确保不同学段、不同年级、不同学期之间知识内容得以连续化、层次化、进阶化,从而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四)确保课程的公共性与文化性
由于受到进步主义的主流教育思想的影响,美国在历史、地理、文学、科学等学科的知识基础和文化基础的传授方面有所忽视。[28]赫希指出,如若一个国家的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失去了公共性,公民所知道的知识也将失去公共性,这将成为导致国家凝聚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29]实际上,如果要成为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年轻人就需要被灌输一些普遍认同的知识”[30]。因此,学校应从核心知识课程建设的层面入手,确保学校课程的公共性与文化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培养公民的社会功能。具体来看,学校应教授具有普世性、普适性、多样性、综合性的公共文化和共享知识。学生只有良好地掌握本国的标准语言,以及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才能够成为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现代公民。
实际上,赫希对课程公共性和文化性的强调,与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所倡导的核心理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就公共性而言,新课程改革一直强调面向全体学生,高度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31]8《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版)》明确要求,应“以国家课程为主体,奠定共同基础”,同时,以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为补充,兼顾不同学生间的差异。[27]4就文化性而言,新课程改革强调“高质量课程建设的内核是中国文化,失去了中国文化特征的课程建设是无意义的”[32]。另外,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建设必须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内容。[31]4总而言之,基础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和学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应精选课程内容,建设具有衔接性、系统性、公共性和文化性的课程体系,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