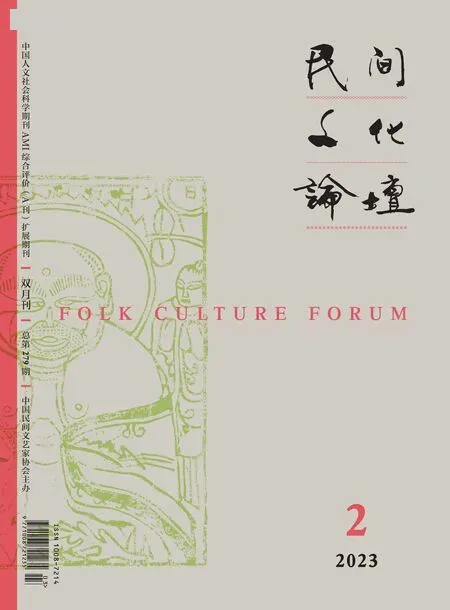斗草阆苑:仇英笔下女性游乐形象的图像定格
张玉芝
明中叶,仕女画已成为当时绘画形式的重要类型之一。以仇英为代表的仕女画作者为适应当时市民文化的审美趣味,创作了反映女性园庭生活的系列类型化作品。笔者发现图像学研究方法可用于解析画面中人物、场景、活动等内容,探究作品所表现的母题,特别是画作中展现的东方女性特有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趣味。如此,可使今人深入理解明代画家看待女性生活的视角、情趣和格调。笔者试通过对画作进行形态分析,辅以相关文献资料论证,以阐释中国古代女性园庭游乐生活的文化含义,以及画家创作此类绘画作品的背景和意图。
一、仕女图解读可适当借用图像学分析理论
图像学理论是由20 世纪美国艺术史学者潘诺夫斯基提出的作为美术史研究的系统方法论。他认为对艺术作品的解释应分为三个层次进行:第一层,为前肖像学描述阶段。解释图像的基本的或自然的题材,又分为事实性或表现性题材,构成艺术母题的世界;第二层,为肖像学分析阶段。解释从属性或约定俗成的题材,构成了形象和寓言的世界;第三层,为圣像学分析阶段。解释图像内在的含义或内容,构成“符号性”价值的世界。①[美]E·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傅志强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 页。这三个层次的范畴表示的是对同一视觉形象解读的几个侧面。按照这个研究方法,实现揭示作品所反映出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目的。显然,图像学理论架构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最后要解读构成“符号性”价值的世界。那么,将此研究方法应用于仕女画的解读是否可行,也是当下需要探讨的问题。
作为中国画画科之重要构成类型的仕女画在唐宋开始增多,其艺术风格多工致妍丽。所谓“仕女”,实则涵盖对特殊女性身份的限定,主体多系宫妃或贵族妇女,在图像表现中她们或独坐沉思,或对镜自怜,或游憩庭园,或含情育幼,或琴棋书画。在以女性活动为题材的二维空间里,画家们总是依据仕女们的生活环境和日常活动习惯,将建筑、器物、花草、动物等配景元素置入画面,以此增加女性活动的意趣。但这些美人图式中的人物姿态及配景元素并非随意安排,画家往往采用符号性语言加强对某一主题的表达,充满象征与隐喻,如美人执扇往往代表伤感,以手托腮是寄托忧思等,画中人物动作的一招一式、一颦一笑逐渐形成绘画创作的一种范式。再如凤、牡丹是富贵吉祥的象征;芭蕉在中国文化中的寓意为孤独、忧愁;松鹤、兰、梅等分别代表长寿、高洁、坚贞情操等精神品格。长期以来这些文化符号已内化于国人的文化认同结构中。这些配景元素连同画中人物活动本身一起构成了女性活动图景,使观者在欣赏画作时不仅能欣赏她们的庭院、房间和衣饰,而且品味她们的表情、姿态及了解其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学者巫鸿指出:“观者在这个‘美人空间’里看到的是一系列并无焦点的能指,以它们的集合构成再现的目的和内容。”①巫鸿:《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 362 页。诸多象征某种文化寓意的符号性表达正符合图像学理论中的第三个层次,即解释对象的内在含义或内容,构成“符号性”价值的世界。使人们在观赏作品时不但接受画家传达的表面信息,更能深入了解艺术创作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内容,挖掘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从这一层面上看,借助图像学理论方法来诠释仕女画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二、仇英《斗草图》的画面描述
图像学理论基本原理的第一层含义是解释基本的或自然的题材,关注作品传达的基本信息。在这幅《斗草图》(图1)中,画家仇英给观者展示的是一群芳龄女子园中斗草游戏的场景。人物刻画细致入神,游戏气氛活跃。带给观者轻松自然的感受,亦不免令人对画家所选题材和活动内容产生探求的愿望。

图1 仇英(款)《斗草图》,嘉德2006 第4 期四季拍1419 号
仇英(约1498-1552,字实父)生活的年代在明代中期,江南经济蓬勃发展,世风日渐侈靡,导致大众视觉消费需求的提升,这时仕女画中的女性身份便被隐藏,更加强调女性美貌的视觉吸引力。极具视觉吸引力的“美人画”被大量生产,融入当时的流行文化。这些被称为美人画的画作常常在家庭内部按照节令展示,如在一年初始、七夕乞巧、十一月深秋和年底腊月等时间节点悬挂不同的内容,变成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成为通俗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显示出了画作的公众性质。这类绘画涉猎题材广泛,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岁时节令时的游艺活动,如穿针、乞巧、拜月、斗草等;日常生活从事的雅事,包括梳妆、赏花、煎茶、焚香、扑蝶等活动;妇女雅会时的对弈、赏画、博古等行为;还有反映女性技艺的内容,如弹琴、围棋、吟诗、作画、秋千、蹴鞠、刺绣等,林林总总的绘画主题皆反映出女性日常生活的丰富性。美人图像的基本模式为单独的美女形象或女性多人活动的呈现。因当时造园之风勃兴,园林风格逐渐精致化,画家在形式布局上也常常截取园林一角,创造出一处优雅的理想环境,拉近观者与画中人物的距离。当时涌现出大量创作此类绘画题材的画家,其中最著名的有杜堇、吴伟、唐寅、仇英、陈洪绶等,他们长于将女性活动进行多角度刻画。这类绘画并不追求现实真实,仅仅将园林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或人物内心世界的反映,以求达到情景交融的效果。
仇英一生作品数量繁多,涉及题材广泛。更擅人物画,尤工仕女,是一位高产画家。技法上以工笔、水墨和白描技巧相结合,设色精美华丽。仅以仕女群体性园中游乐为题材的经典作品就有《春庭行乐图》《汉宫春晓图》《仕女游园图》等多幅,内容涉及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幅传为仇英所绘的《斗草图》(图1),画面刻画的是春日里一群芳龄仕女在园林中踏青斗草游戏的场景,属于女性活动集合呈现的图像模式。画作中没有题跋,只在其左下角有“仇英实父制”的落款。此画设色古朴,在设色方面主要涉及桃红、青、绿、褐等几种色彩。人物造型准确,形象秀美,线条流畅,刻画细腻,形神俱佳。主要是对一群年轻女子席地围坐于树荫之下,春日踏青斗草的场景刻画。这是仇英以女性园林游乐为题材的仕女画中的一幅,画中活动属于岁时节令游艺活动的一种。
《斗草图》采用常见的三段式构图,即分为中景、近景、远景三个部分。近景处,鲜丽繁茂的花草枝叶伴其左右,或盛于篮中,或置于身侧。七位女子神态各异,有的伸手向同伴索要花草,有的手持花草向同伴展示,有的正独自拈花细赏。画中女子头梳发髻,身着长衣裙衫。其中,位居中间身着红衣的女子最为引人注目,她体态安然,双手抱胸,神情恬淡,抿嘴略带笑意,表情神秘作倾听状,两侧的女子正三三两两手拈花草作交谈状。周边有假山和小溪环绕,将人物与景物隔离开来,形成一处闭环空间,围坐一起的女子们处于画面的独立空间位置,在整幅画面中显得较为醒目,形成视觉中心。一般构图的视觉中心应是画面的中间部分,但仇英的这幅画作却将最引人视线的七位女子围在一起席地而坐的场景安排在画面最下方,采用近景手法细致描绘,显然其用意是引领观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以拉近观者与画中人物的心理距离,增强代入感。环绕于周边的假山和小溪,将女子们与其他景物隔离开来,处于画面空间的独立位置,有突显人物主题活动的意图。中景处一纤巧女子手捧一束刚刚觅到的花草,正兴致冲冲地途经小桥走向不远处正在折花的仕女,她俩目光相视,形成互动关系。折花女子被一棵棵茂盛树木围绕,其身侧设有傍池栏杆,栏杆的另一侧是开阔的河面,远处蜿蜒而来的河道之水正向此处汇集。这两位仕女周围有枝叶繁茂的绿树环绕,将其与远处的山水和前景处七位围坐的女子隔离开来,同样形成一处独立空间。这部分处于画面的第二个层级。但因人物较少,景色为多,所以观者依旧会将视线聚焦在前景处的女子们身上。而两处独立空间人物的多寡在视觉上形成疏密对比,更加凸显出前面七位围坐女子的热闹氛围。远景处伫立的山石和蜿蜒的河流相映成趣,既有开阔之感,又充满野趣,令人遐想。这部分作为背景出现,属于画面的第三个层级。
画面远景处伫立的山石和蜿蜒的河流均衡了画面构图,使画面布局匀称合理。这种巧妙的构图手法,既细致真实地描绘了各女子相聚在一起活动的情形,又充分展示了户外高远开阔的景色,衬托出悠然闲适,意趣盎然的氛围。在这个山环水绕的空灵之境里,众多美貌女子活动其中,使人顿生悠然惬意之感。
三、《斗草图》中的女性及活动分析
图像学的第二层含义是解释从属性或约定俗成的题材,构成了形象、故事和寓言的世界。斗草之戏为春日游艺中颇受大众喜爱的一种游戏,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和特定内容,通过画作表面形式透露出的信息解读其背后的文化渊源,是图像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仇英款的这幅《斗草图》中,假山、草木、小溪、石栏、小桥等诸多造景元素齐备,皆向观者暗示这是一处园林环境。从远处的自然山水和开阔的视野进行判断,是郊外一公共园林,而非私家园林。作者绘制此画时,不仅对画中女子手拈的花草进行细致描绘,刻画其洁白粉淡之色,还对枝繁茂叶的树木采用翠绿色进行绘制,不仅衬托了女性的柔美,还凸显了园林的景色,暗示了活动的时节。女子手中所持、篮中所置的鲜花嫩草,枝繁叶茂的环境,身着的单衣长裙及潺潺流水的小溪等诸多方面都向观者提示这是一处春季园林景色。
《斗草图》中人物绘画写实,从发式、着装款式和服饰色彩方面均可看出作品所描绘时代的流行元素,进而可辨别画中人物的身份以及所处时代。从发式看,明初女子发髻基本还保留宋代式样,嘉靖以后变化丰富。明代发髻式样繁多,有桃心髻、鹅胆心髻、高髻、包髻、牡丹头、堕马髻、盘龙髻、牡丹头等多种形式(图2)。仇英生活的年代在正德、嘉靖年间,观察画面可知《斗草图》中所绘女子发式和明代的式样相符。图中画面中最显眼的红衣女子和紧挨她右侧的女子,左下方露出部分红色上衣的女子,中景处站立折花的女子等四人均为高髻发式。红衣女子对面身着青衣的女子髻上加包巾,为典型的包髻装扮(图3)。按照《明史》中“凡婢使,高顶髻,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双髻、长袖、短衣、长裙。”②张廷玉总纂:《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珍藏本。的说法,图3 中红衣女子左侧花篮旁边的娇小女子及图4 中小桥上走来的女子梳双髻,应是小婢身份。

图2 明代女子发式与发饰图①李芽:《中国历代妆饰》中插图,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年,第148 页。

图3 仇英 《斗草图》(局部一)

图4 仇英 《斗草图》(局部二)
从服饰方面分析,图5、图6 为梳髻、交领衣、长裙女乐伎,是明代中期妇女装束。③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32 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62—463 页。图3、图4 中女子穿戴和图5、图6 极为相似,应是明代中期女性服饰。其他文献记述中对明代妇女服饰也多有提及,如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引《太康县志》曰:

图5 梳髻、交领衣、长裙女乐伎(一)

图6 梳髻、交领衣、长裙女乐伎(二)②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32 卷中插图,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62—463 页。
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缎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襕。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少……。①顾炎武:《日知录》,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1年,第160 页。
图3、图4 中女子“髻高寸余”,也有“衣衫大至膝”的装扮,以此证明画中人物着装为典型的明代中期女性服式,这和仇英生活的年代相符。
从色彩方面看,画面中主要涉及桃红、青、绿、褐等几种色彩。衣物颜色淡雅,仅有个别呈桃红或青色,这其中同样蕴含着人物身份的象征含义。明代有着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如《明史》中就有“皇后冠服:蔽膝随衣色,以緅为领缘,用翟为章三等……皇妃冠服:蔽膝随裳色,加文绣重雉,为章二等……皇太子妃冠服: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二等……”③张廷玉总纂:《明史》卷六十六,志第四十二,舆服二。的记录。明代对民间妇女的约束也是有章可循,《明史》中记述“民间妇人礼服惟紫絁,不用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④张廷玉总纂:《明史》卷六十七,志第四十三,舆服三。。坐于中间的女子身着桃红上衣,而非大红,其他女子大多都是浅淡颜色,和仇英的另一幅作品《汉宫春晓图》(图7)中宫中女子们的艳丽服饰相比,加之这些女子们发髻上几乎都朴素异常的现象综合考量,基本可以断定这些女性非宫人或贵妇。小婢的出现,则暗示她们来自民间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家庭。

图7 仇英 汉宫春晓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整体来看,画面构图是按自下而上的叙事手法将人物置于一处固定环境进行描绘,以凸显绘画主题。在人物造型的设计上,作者对画中的女子形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人物体型纤细匀称,充满女性的阴柔之美。众女子神态各异,或相对交谈,或折花自赏,一颦一笑无不展现出中国女性的独特风韵。在仇英的《汉宫春晓图》和陈洪绶的《斗草图》(图8)画作中也有相近的描绘。皆为三五女子围坐一起,手持花草嬉笑交谈,可见这种情形是一固定且具有某种范式的表达,是体现特定文化背景的主题活动。

图8 陈洪绶 《斗草图》,辽宁博物馆藏
其实,“斗草”不仅是画作中的一个创作主题,诸多经史子集中也多有记述,成为普及性话题。斗草也称“斗百草”,学界普遍认为最早的文献记述是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有“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①宗懔著,熊澜校:《荆楚岁时记》,民国景明宝颜堂秘笈本。之说。斗草开始时作为民俗存在,是端午习俗中的一种,这与五月湿毒的节气有关。五月间,毒虫泛滥,容易引发疾病,百姓也因此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燕京岁时记》中就有关于五月端午避毒虫的记述,“初五日,为五月单五。临节送礼,粽子、樱桃、黑白桑椹、五毒玫瑰饼饵之类。……自初一,以雄黄合酒晒之,至节涂于小儿耳鼻及额,以避毒虫。”②王碧滢、张勃标点:《燕京岁时记 外六种》,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第224 页。同样,“斗百草”为的是寻药草,治百病,其目的和避毒虫是一致的。唐代韩鄂在《岁华纪丽》中指出:“端午,结庐蓄药,斗百草。”③韩鄂:《岁华纪丽》卷二,明万历秘册汇函本。明代谢肇淛在《五杂组》中也曾记述:
古人岁时之事,行于今者独端午为多,竞渡也,作粽也,系五色丝也,饮菖蒲也,悬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兰汤也,斗草也,采药也,书仪方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辟蛇、虫诸毒,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沸而浴之。④谢肇淛撰:《五杂组》卷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24 页。
又有《岁时记》“五日,士人踏百草,作斗草之戏,以拯屈三闾之溺”⑤高濂著,赵立勋等校注:《遵生八笺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第140 页。后随着人们兴致的提高,慢慢演变成为一种休闲游戏,称为“斗草之戏”。因此,“斗草之戏”成为历代民俗活动的主题。
从文献记载看斗草的缘起是因寻药草,治百病,在端午节进行。后出于人们对斗草之戏的迷恋和喜好,在时间上逐渐灵活起来。明代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中写道:春日,妇女喜为斗草之戏。黄子常《绮罗香》词云:“绡帕藏春,罗裙点露,相约莺花丛里。翠袖拈芳,香沁笋芽纤指。”⑥田汝成著,陈志明校:《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369 页。就连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在《西游记》第八十二回(姹女求阳 元神护道)中也曾这样描写:若到三春闲斗草,园中只少玉琼花。⑦吴承恩:《西游记》,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第907 页。通过以上信息可知,斗草之戏在春日、三春等各时间点都可进行。可以说斗草活动发展至明代,时间已不仅限于端午节,而是外出踏青之时任一时间。因此,仇英这幅《斗草图》中的游戏时间不一定是端阳节,而是某一踏青时间。
这些妙龄女子围坐在一起,围绕花草交流谈笑,沉浸其中。那么,到底是何原因使闺秀们如此兴致。翻阅历代文献记述、诗词歌赋、文学作品,其中多少会透露相关信息。唐代孙棨在《题妓王福娘墙》诗中写道:移壁回窗费几朝,指镮偷解博红椒。无端斗草输邻女,更被拈将玉步摇。①本社编:《全唐诗》第5 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903 页。又有柳永词《夜半乐》中:“竟斗草、金钗笑争赌。”②柳永:《柳永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0 页。南宋《苕溪渔隐丛话》中:“君莫羡花开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③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后集,卷十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95 页。以上三篇文献词赋记述中皆出现“输”“赌”“赢”等字眼,可见斗草的乐趣重在一个“赌”字,赌得金钗、赢得珠玑等这些女儿家喜爱之物,才能激发斗草兴致。诚然,这也意味着斗草之戏开始时要费些心力,争取寻得奇花异草,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历史上为此投入大量心思的例子莫过于唐代韦绚在《刘宾客嘉话录》中所提到关于乐安公主的斗草举动了:
晋谢灵运须美,临刑,因施为南海祗洹寺维摩诘像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乐安公主五日斗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骑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无。④韦绚:《刘宾客嘉话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 页。
乐安公主为赌赢一场斗草不惜令人千里之行弄到谢灵运之须,凸显出斗草之戏中的别出心裁,可见其重视程度。另外,明人在《隋炀帝演义》中写道:
……杳娘道:“这样春天,百花开放,我们去斗草,何如?”妥娘道:“斗草左右是这些花,大家都有的,不好耍子,倒不如去打秋千,还有些笑声。”⑤齐东野人编著,王汝梅校点:《隋炀帝演义》,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53 页。
这也变相说明无新奇花草的游戏注定毫无乐趣。所以,斗草之戏追求的就是别出心裁、出其不意的效果。由此可以想见《斗草图》中小桥上抱花挎篮走来的女子,是不是为了赌赢这场斗草之戏,独自一人跑到远处寻了些奇花异草正兴致而归呢?
无可否认斗草之戏需要大量奇花异草,但仅仅具备这个条件未必能赌赢,还需通过考察斗草类型、方式、规则等问题才能解决。斗草内容主要分为武斗和文斗两种类型,所谓武斗,顾名思义,就是有些许武力成分,即在找寻花草过程中,各自寻找韧性较强的草茎,然后将两种花草之茎相互交叉套住,用力拉扯,先断者输,未断者赢。这类比试方式因不需太多文化知识,且易于找寻花草草茎,比较适合儿童和乡间没有文化的女子。清代画家金廷标在《群婴斗草图》(图9)中表现的就是俩儿童正在进行武斗的场景。文斗与武斗相比难度较大,需要大量文化和药理知识,非普通人可以掌握。从明人吴兆在《秦淮女儿斗草篇》中描述的斗草词中可窥见一斑:

图9 金廷标 《 群婴斗草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君有麻与枲,妾有葛与藟。君有萧与艾,妾有蘅与芷。君有合欢枝,妾有相思子。君有拔心生,妾有断肠死。”⑥夏晨中,宙浩等编注:《金陵诗词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第151 页。
这种斗法是要对花草种类有足够地了解,并知其名。同时互报的花草名还应像对联一样用对仗手法将其对上,追求的就是一个 “妙”字。清代曹雪芹《红楼梦》第六十二回章节中也有文斗的详细描写:
……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畔的牡丹叶。”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荳官便说:“我有姊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①曹雪芹著,脂砚斋批评:《脂砚斋批评本红楼梦》(下),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年,第544 页。
这段描写详细展示了“文斗”场景。虽是清代人所述,不能完全证明是明代斗法,但从中依旧能感受到此种斗草方式不仅需要广博的学识,还需才思敏捷、反映灵活,深受知识女性的喜爱。结合上述内容进行分析,仇英《斗草图》中描绘的斗草内容应是“文斗”斗法。包括他的另一幅画作《汉宫春晓图》和陈洪绶的《斗草图》中的斗草方式都属于这类性质的游戏。因为画面中展示的是女子们拿起花草进行比试,而非用力拉扯。再看女子们动作文雅,有的将花草藏于袖中,有的两两交谈,亦有相互伸出花草两两比试……。衣着装扮形象显示皆为一群具有文静气质之人,也只有她们才具备这种智力游戏的条件。结合社会背景可知,明代妇女好文风气盛行,书香门第的闺秀们闲来无事喜欢吟咏,市井人家的女子也受到影响,跟风学习。这种背景下,进行文斗游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由此可见,绘画内容和文献描述基本一致,是一典型文斗斗草之戏活动场景的再现。
外出踏青是闺中女性热衷和流行的活动。女性天然和花草有着不解之缘,当她们来到山环水绕的园林中,三五成群一同拾翠踏青,坐享春和景明,“斗草”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女性寻求闺趣的一部分内容。文献资料记述的斗草之戏给今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字材料,而画家则用画笔向世人展示了更为生动的视觉形象,印证了文献所述内容。
四、女性、花草、自然的审美精神
图像学的第三层含义是解释作品内在的含义或内容,构成“符号性”价值的世界。在《斗草图》画作中仇英将斗草地点置于某一自然园林中,将女性和花草紧密联系,首先应从花之于女性的关系方面考量。花与女性相关的文化极为丰富,如十二个月花神皆为女性;《诗经·周南·桃夭》中写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②王昶编著:《古典诗词曲名句鉴赏》,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年,第2 页。以桃花喻美人的新婚祝福;朱熹笔下留有“便赋新诗留野客,更倾芳酒祭花神”③国馆:《图说二十四节气》,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41 页。的优美诗句;更有“出水芙蓉”“花容月貌”“蕙心兰质”等诸多比喻女性美貌的成语等等,这些都离不开对花的比附、赞美与崇敬。此处的花草俨然已成为女性美貌、品格与精神专属的象征符号,在画作、诗词歌赋等艺术形式中成为永恒的美学主题。如何从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解读,樊美筠在其《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一书中曾这样分析:“在中国古代美学中,凡是被赞为自然的,其基本的意象都是青春少女的形象,就是取其纯洁之意,如出水芙蓉……。而女性与自然常常互为象征出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所以,中国传统美学历来崇尚自然,这实际上就是对女性的一种崇尚。”④樊美筠:《中国传统美学的当代阐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26—127 页。从这一观点来看也就不难解释女性、花草与园林的关系,以及画家对女性和自然的崇尚之情。
其次,画作中女子们轻松自由的游戏场景,象征着普通女性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热爱。仇英生活年代为明中叶,原籍江苏太仓人,后移居苏州。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接触的阶层也多为平民阶层,所绘人物应是平常人家的女性形象,这从散落在地的花草所显露出的世俗生活气息便可看出。通过上文的服饰分析,确定所画人物皆为明中期女子,正是他所处的生活年代和阶层的人物形象。而非像他的另一幅画作《汉宫春晓图》所描绘汉代宫中女性生活那样,假托前朝之事进行的意象抒发。明中叶社会经济发达,江南造园之风兴盛,时值江南女子游风盛行之时,就连普通人家的女子也常常参与进来。这和嘉靖以前的女性生活大为不同。明代顾起元撰写的笔记小说《客座赘语》中记述明正德、嘉靖(1506—1566)以前社会风气较为淳朴,他描述南京的妇女生活状况是“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①顾起元撰,孔一校点:《客座赘语》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 页。也就是说这时的女性依然以家庭为主,沿袭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由于“学而优则仕”的入世准则与女性无缘,因此她们的生活重心仍是家庭,所有的活动紧紧围绕孝敬父母、相夫教子的内容展开。但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女性拥有了闲暇时间,嘉靖以后江南妇女游风兴起。仇英生活年代正值“吴中女郎类嬉游”②徐献忠辑:《吴兴掌故集》卷十二《风土》,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第763 页。时期,她们游山、游湖、游河、游园,不一而足,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妇女广泛参与游览已成为事实,这标志着女性由家门逐渐走入更为广阔的外部空间。对女性郊游的情形,明人张瀚曾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这样一种生动场景,令人心向往之:
杭俗春秋展墓,以两山逼近城中,且有西湖之胜,故清明、霜降二候必拜奠墓下。……然暮春桃柳芳菲,苏堤六桥之间一望如锦,深秋芙蓉夹岸,湖光掩映,秀丽争妍。且二时和煦清肃,独可人意,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游人笑傲于春风秋月中乐而忘返。四顾青山,徘徊烟水,真如移入画图,信极乐世界也。③张瀚撰,萧国亮点校:《松窗梦语》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0 页。
文中所描绘的如诗如画、春光无限的场面令人艳羡不已,可见当时郊游之风的兴盛。虽然明代社会礼教更为强化,曾遭到部分维护封建礼教人士的反对,甚至一些地方官为整顿民风,还下了禁止女性出游的禁令,但结果是因女子们外出郊游的愿望异常强烈,禁令未能长久施行,最终以失败告终。同时也反映出女性追求精神解放的强烈愿望,更为画家提供了表达女性追逐自由生活的题材。
最后,从“天人合一”的自然宇宙观看,园中踏青游戏实际上是女性内心追逐自然山水需求的表达。园林之于女性和男性同等重要,园林本身的“曲、藏、遮、隐”等特征都具有女性特点,和女性心理极为相符。同时,园林的开阔空间又能使女性被封建伦理所抑制的情感在广阔的外部空间得以释放。因此将女性活动置于园林既是自然花草和女子品格相比赋的和谐,又是心理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相统一的结合。曹林娣在她的著作《中国园林文化》中也曾作出分析,“深沉的自然山水意识渗透到生活领域。清谈、静坐、吟诗、绘画、读书、诵经、调素琴、弈棋、啜茗、饮酒、垂钓、采药、炼丹、游山泛舟等成为魏晋南北朝文人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后世文人园林中的主要活动。”④曹林娣:《中国园林文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54 页。这种游乐方式对于内心渴望自由的女子们来说,无疑更具吸引力。
再看画作,色调恬静,环境春意盎然,女子们轻松愉快的交谈、游戏之姿,都给观者留下恬淡、闲适和心灵奔放的印象,向世人传递出明代世俗女子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此看来,画家将女子们置于园林美景进行描绘,有花、有草、有欢乐,是一情景交融的场景刻画,是对他所处时代的女性生活的真实反映,更是构成女性、花草、自然三者之间的符号性价值世界的表达。
结 论
仇英的《斗草图》以斗草为主题,栩栩如生地向人们展示了明代闺阁女性春季踏青斗草的生动场景,使今人对这一游戏有了更加真实的认识和理解。从艺术美学的角度看,《斗草图》已经达到了相当高妙的艺术创作水准和审美高度。通过对此绘画作品进行图像学分析,挖掘斗草活动背后的文化渊源和审美趣味,对了解明代女性社会角色和文化心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绘画图像的表现形态与要表现的人物、事件、习俗等密切结合,浸润在内敛、柔美、谐趣的审美意味中,洋溢着独特的东方世俗文化格调。女子园林闺阁生活绘画图像的形态构成同国人的生物本性和文化潜意识相触碰,反映出中国妇女特有的闺阁心理和艺术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