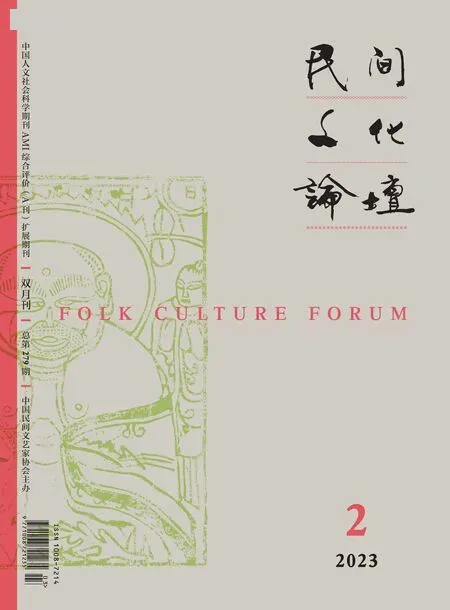转危为机:紧急情况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活用
—— 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行动的循证研究
程 瑶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激增。注意到这种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教科文组织”)在官网上设立了“危难时刻,公众需要文化”专题页面。教科文组织助理干事奥内托(Ernesto Ottone)提到:“在这个数十亿人在空间上彼此分离的时期,文化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在这个令人焦虑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文化提供了慰藉、鼓舞和希望。”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危难时刻,公众需要文化”专题页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官方网站,https://zh.unesco.org/news/wei-nan-shi-ke-gong-zhong-xu-yao-wen-hua,发布日期:2020年3 月29 日,浏览日期:2022年11 月1 日。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传承在面临危机的同时,也给人们以心灵的慰藉,借助互联网连接起孤立在家的个人。这正是紧急情况下非遗的双重属性的一个缩影——自然灾害、武装冲突和疫情给非遗保护带来了严峻的危机,同时也是非遗为地方社区提供复原力来源的时机。注意到紧急情况给非遗带来的“双机”,教科文组织经过多年努力,在2020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八届会议上审议通过了《紧急情况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作原则和模式》(以下简称“《原则和模式》”),为缔约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框架下进行紧急情况时非遗保护和活用确立了原则,奠定了各行动方设计更具体模式的基础。这也意味着国际层面对非遗与紧急情况的关系认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原则和模式》的出发点是在各种紧急情况下确保非遗得到最有效的活用和保护,以此为开展实际行动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其出台也可以视为一个知证决策的案例。本文即以教科文组织对紧急情况下的非遗保护的关注历程为循证线索,所选取的档案材料主要来自咨询机构的调查报告和案头研究,同时以教科文组织新冠肺炎疫情与活态遗产平台中各缔约国提供的实践案例作为参证,集中探讨紧急情况下非遗保护的行动逻辑。虽然复杂的紧急情况类型使得非遗的活用和保护难上加难,并且不同领域的非遗项目的传承和存续力也有不同,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保护方法和原则能够为中国的保护实践提供重要的参考。
一、教科文组织对紧急情况下的非遗保护的关注历程
《公约》在制定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紧急情况下保护非遗的需要。在国家层面,缔约国在申请将遗产项目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简称“急需保护名录”)时,“委员会在极其紧急的情况(其具体标准由大会根据委员会的建议加以批准),可与有关缔约国协商将有关的遗产列入第一款所提之名录”(第17 条)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 版)》,内部资料,2020年,第12 页。这里的“委员会”指的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后文皆同。,在国际合作和援助层面,“如遇紧急情况,委员会应对有关援助申请优先审议”(第22 条第2 款)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 版)》,第13 页。。《公约》出台后,政府间委员会和缔约国大会在不同的场合讨论了与紧急情况相关的问题,并在《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以下简称《伦理原则》)中完善了相关的标准框架。
早在2010年委员会第五届常会上,委员会就审议了“紧急情况”的定义,并讨论了符合《公约》中紧急受理急需保护名录申报和申请优先国际援助的条件。在2014年缔约国大会第五届会议上,缔约国大会核准了对《操作指南》的修改,将“紧急情况”的界定加入了“国际援助”的部分中。“当发生灾难、自然灾害、武装冲突、严重疫情或者任何其他给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作为该遗产持有者的社区、群体或有关个人产生严重后果的自然或人为事件,缔约国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克服上述任何境况时,应认为存在紧急情况。”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操作指南》第50 段,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 版)》,第31 页。另外,《操作指南》还指出了紧急情况下委员会受理急需保护名录申报的方式。
2015年委员会第十届常会上,《操作指南》增加了第六章“在国家层面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可持续发展”,其中涉及“紧急情况”的部分包括“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和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节的相关内容肯定了社区的非遗中有关地球科学,尤其是气候相关的知识和实践是其抵御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能力体现。因此,鼓励缔约国“将持有此类知识的社区、群体和个人充分纳入减少灾害风险、灾后恢复、气候适应和缓解气候变化的体系和项目中。”④同上,第191 段,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 版)》,第58 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和平”一节中,认可了非遗对于社会凝聚力和公平、预防和解决争端、恢复和平与安全、实现持久公平的贡献,并鼓励缔约国充分活用非遗的这些作用。这一点在同届会议上核准通过的《伦理原则》中也有体现:“应确保社区、群体和个人有权使用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器具、实物、手工艺品、文化和自然空间,以及纪念地,包括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巴莫曲布嫫、张玲译,《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3 期,第6 页。
教科文组织在《公约》体系之外也推进了对紧急情况时文化保护的关注。为了减少冲突前、冲突时和冲突后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的脆弱性,2015年教科文组织第三十八届大会通过了《加强教科文组织在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和促进文化多元化的行动》(以下简称“《行动》”)(第38C/48 号决议)。这份《行动》战略是建立在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领域的总体任务,以及保护文化遗产和多样性、促进文化多元化的相关公约和建议的基础上的。作为一个协调机制,它能够促进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和利益攸关方对紧急情况下影响文化的威胁和损害做出全面反应。在2016年缔约国大会第六届会议上,希腊发表声明,请秘书处“促进进一步审议和阐述非遗的价值及其在武装冲突中的保护和在和解中的作用”(ITH/16/11.COM/15)。①本文引述的相关工作文件可按括注夹注内提供的文件代码从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documents.un.org)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图书馆(unesdoc.unesco.org)查阅和获取,后文不再赘述。
与此同时,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也认识到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根据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人权理事会最近在一项关于文化权利和保护文化遗产的决议中承认,“对任何民族的文化遗产,包括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损害,均构成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害”,并呼吁“查明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防止侵犯和践踏文化权利以及预防和减轻对文化遗产,包括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造成损害的创新办法和最佳做法”(A/HRC/33/L21)。为了在文化领域的其他规范性文书下推动该主题的发展,2016年9 月,文化公约委员会主席联席会议举办了论坛,以供各公约国之间就这一主题信息的分享。
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2015年日本仙台第三次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世界会议通过的《仙台宣言》以及《2015—2030年框架》是一个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达成共识,即作为对研究性知识的补充,传统知识和传承人的实践在制订和执行减少灾害风险计划和机制、灾害预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灾后阶段对非遗的关注也在进行。自2014年起,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灾后需求评估机制(Post Disaster Needs Assessments, PDNA)专门将文化(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12 个可能的干预部分之一,并把具体措施落实在教育、基础设施和卫生等领域。
国际上对紧急情况和文化的关注,构成了2016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上首次审议紧急情况下的非遗的背景。会议在相关讨论中就紧急情况下非遗的双重属性达成了共识——非遗既受到威胁,又是复原和复原力的强大工具。然而,国际层面积累的紧急情况下的非遗保护经验仍然十分有限,如截至本次会议委员会只批准了三项符合《公约》第22 条第2 款的紧急援助。鉴于此,委员会鼓励秘书处开展更多与该主题相关的活动,以探究非遗在紧急情况中的潜力和如何根据《公约》采取干预措施。秘书处随后围绕紧急情况下《公约》的实施情况展开了调查,如在教科文组织遗产紧急基金(UNESCO’s Heritage Emergency Fund)的资助下,包括叙利亚难民的非遗调查、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流离失所者的非遗保护需求确认和太平洋诸岛的降低灾害风险战略等。2017年的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审议了这些活动的成果,并把基于社区的需求确认作为未来行动的重点,促进非遗与灾害风险管理之间的联系。根据决议,秘书处采取了三方面的行动:确保以社区为基础的非遗保护干预纳入基于项目的紧急措施;为了提升能力和认识,将灾害风险管理纳入非遗清单编制的指导说明和相关能力建设培训材料中;加强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和人道主义利益攸关方的合作。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委员会在其2018年第十三届会议上认为制定紧急情况下保护非遗的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秘书处于2019年5月在教科文组织总部组织了一次有关“紧急情况下的非遗”的专家会议,希望将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形成理论,并转化为对缔约国或其他任何相关国家或国际利益攸关方的方法指导。
除了上述主题的讨论,专家会议还指出,任何在紧急情况下非遗保护的行动都应符合国际上的相关框架、文书和标准。首先在人权方面,《公约》指出,“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 版)》,第8 页。,即要求缔约国将其保护工作与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书保持一致。因此,作为第一项专门关注文化遗产及其在维护和平与安全中的作用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第2347(2017)号决议在此被予以特别关注。虽然该决议没有具体涉及非遗,但它关注的各社区赋予其遗产的一套价值观与非遗有重要的联系。
接着是与紧急情况下保护有形文化遗产相关的国际文书。以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及其两项《决定书》为例,国际法往往只注重保护有形遗产,但在紧急情况下,有形和非物质遗产往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公约》在对非遗的定义中认为“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构成了非遗的表达和实践。基于此,教科文组织力求在执行文化相关的公约时建立协同合作机制。而紧急情况下的非遗保护运作原则和模式也要通过促进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与协作,以加强对各种形式文化遗产的保护。
专家会议的成果连同《原则和模式》一起被提交至2019年第十四届会议并获得通过,而后被提交至2020年的缔约国大会第八届会议审议,最终被批准通过。这份《原则和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广泛适用性和灵活性。一方面这里的“紧急情况”包括自然灾害和人为冲突,两者差异巨大;另一方面制定者根据以往经验,又希望寻求普遍意义上的非遗保护原则和方法,以便尽可能地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紧急情况。因此,制定《原则和模式》的目的不是确定一份详尽的行动列表,而是提供在紧急情况下保护非遗的一般原则和措施,在此基础上能够使不同的社区、群体和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更具体的行动模式。
在委员会的倡导下,教科文组织二级中心也在积极进行对紧急情况下的非遗保护的探索。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研究中心(IRCI,日本)于2016年开展了一系列关于非遗和自然灾害的活动,迄今已出版了两份出版物。该中心近来关注的重点是灾后的非遗情况。拉丁美洲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区中心(CRESPIAL,秘鲁)则于2018年底启动了非遗与突发事件之间关系的研究计划。同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和加勒比档案协会与圣马丁岛政府合作举办了一次关于“灾后恢复和遗产保护的区域方法”会议,并建立了包括非遗保护在内的加勒比遗产保护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危机,教科文组织迅速响应并做出一系列行动,包括利用其全球网络建档记录活态遗产受到的影响,并在不同社区之间交换经验。2020年4 月,教科文组织发布线上调查,邀请大量利益攸关方尤其是与《公约》相关的社区分享活态遗产经验。截至2022年11 月,教科文组织在官方的“活态遗产经验与新冠疫情”平台展示了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253 份案例。这些回应一方面反映出新冠疫情给非遗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保持距离和封锁隔离期间,非遗在保持社会连通性和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台挑选出来的经验案例来自全球范围,包括:非洲13 例,阿拉伯国12 例,亚太地区46 例,欧洲和北美地区101 例,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81 例。来自中国的案例有9 个。②详见教科文组织“新冠疫情与活态遗产”平台页面,https://ich.unesco.org/en/living-heritage-experiences-and-the-covid-19-pandemic-01123,浏览日期:2022年11 月1 日。
二、紧急情况下的非遗:存续力危机
借助教科文组织《公约》工具包中的《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提供的以复数的“人”和“过程”为基点的非遗概念解读路径,我们可以充分理解非遗潜在的脆弱性和紧急情况下这种脆弱性造成的存续力危机。
首先,正如《公约》定义所强调的“世代相传”和“不断地再创造”,非遗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文化表现形态本身,而在于知识和技能的财富能代代相传”。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巴莫曲布嫫译,《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1 期。《公约》对非遗的定义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 版)》,第7—8 页。也就是说,复数的“人”,即社区、群体和个人世代传承或传播非遗的过程才是非遗保护的重点,而不是作为结果的文化“产物”。然而在这种不断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中,非遗也具有潜在的脆弱性,“非遗的许多表现形式和表现形态都受到威胁(threats),既面临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的危险,也面临缺乏支持、欣赏和理解的危险。倘若得不到培育,非遗就会有永远消失的风险(risks),或当作一种仅属于过去的实践而被冻结。”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巴莫曲布嫫译,《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1 期。如果没有社区内部和代际之间的对非遗的不断实践和习得,也就意味着“知识、技能和意义传承的过程”中止,社区自身拥有的传承体系也就此崩溃。紧急情况或突发事件往往可能会给非遗带来“灭顶之灾”。自然灾害、冲突和疫情改变了社区生活的常态,也使得人们实践和习得非遗的条件发生改变。当人们无法再进行必要的表达和传承,非遗的生命力也消耗殆尽。
以新冠肺炎疫情对非遗的影响为例。根据《活态遗产和新冠疫情——教科文组织线上调查简报》统计数据,94%的受访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活态遗产。秘书处在各缔约国提交的案例中选出了与新冠肺炎疫情对非遗的影响有关的词汇,并对其频率进行了统计③UNESCO. Snapshot of the UNESCO online survey, https://ich.unesco.org/doc/src/8GA-snapshot_on_survey_living_heritage_pandemia-EN.pdf.发布日期:2020年8 月,浏览日期:2022年11 月1 日。:

表1 新冠肺炎疫情对非遗影响的类型统计④表一由笔者译自《活态遗产和新冠疫情——教科文组织线上调查简报》(Snapshot of the UNESCO online Survey),第9 页。
从上图的统计可以看出,除了少数的案例外,新冠肺炎疫情更多地给非遗传承和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有效遏制病毒的传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保持社交距离和封锁隔离的措施,导致许多节庆活动和仪式被迫取消和推迟。与此同时,活态遗产实践必需的空间、场所、物品和材料的获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随着封锁隔离而来的各行各业的停摆也导致了在非正规部门经营的传承人和实践者失去收入来源,无法维持生计。
相比在空间上影响范围较大的疫情,局部发生的武装冲突虽然涉及的地理范围较小,但却可能对相关社区造成更大的物质、社会和经济灾难。2017年,受秘书处委托完成的调查报告《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的非遗》①GeraldineChatelard, Survey Repor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Displaced Syrians, UNESCO, https://ich.unesco.org/doc/src/38275-EN.pdf,发布日期:2017年11 月,浏览日期:2022年11 月1 日。通过访谈来自叙利亚社区的流离失所者,展示了武装冲突如何给非遗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就“传统手工艺”而言,持续的冲突使得传统手工制品的生产和销售都难以为继。许多匠人们在冲突中死去,背井离乡幸存下来的匠人们则发现自己很难获取生产原料。艰难维持生计的人们也无法承担起手工艺品的消费,而交通不便让原本惨淡的经营状况雪上加霜。在这样充斥着死亡和恐怖气息的氛围中,人们也不再进行节庆活动和表演艺术。战争的破坏甚至改变了叙利亚人惯常的饮食制备和待客习俗的实践。叙利亚人尤其是妇女从她们独有的食谱中获得认同感的来源,然而战争造成的粮食短缺使得她们无法继续制作和分享传统食物,待客之道也大大从简。年轻一辈因此失去了本该从亲身参与和观察中学习待客礼仪的机会。被迫简化的还有丧葬仪式。面对冲突带来的大量流亡,人们却被剥夺了举办相关哀悼仪式的权利,这样无疑加剧了失去亲人的人们的心理创伤。
《原则和模式》中紧急情况下保护非遗的运作模式与应急管理周期中准备、响应和恢复三个主要阶段相对应。每个阶段都涉及对非遗项目的评估,如“响应”阶段要求“每当进行灾后或冲突后需求评估时,尤其是在多方国际危机应对机制的框架下,都要确保将非遗纳入评估”(LHE/20/8.GA/9)。了解灾害对非遗直接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灾后需求评估(Post Disaster Needs Assessments,PDNA)。灾后需求评估是“在灾难发生后的几周内进行的调查,以记录文化部门内不同领域的损害和损失(建筑遗产与文化遗址,文化创意产业,非遗和传统知识、动产,文化治理与遗产机构,记忆库)”。②Meredith Wilsonand Chris Ballard, Safeguarding and Mobilis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ontext of Natural and Humaninduced Hazards, https://ich.unesco.org/doc/src/38266-EN.pdf, 发布日期:2017年9 月,浏览日期:2022年1 月10 日。与非遗相关的评估内容涉及建筑物、演出场所,与非遗生产和时间提供空间或物质手段的资源和物件,以及社区和非遗传承人的物质活动和迁移。虽然短期的灾后需求评估为识别非遗受到的影响提供了权宜之计,但这类灾害风险管理方式很难把非遗存续力受到的影响量化。
例如,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三次灾后需求评估(2012年萨摩亚、2015年瓦努阿图和2016年斐济)均用文化的有形方面来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和损失。③同上。在瓦努阿图,评估考虑了瓦努阿图文化中心及其岛屿前哨、社区集会屋(nakamal)、世界文化遗产马塔王酋长领地(Chief Roi Mata’s Domain)以及手工艺品和艺术中心。对于瓦努阿图社区来说,社区集会屋是社区进行知识传承的地方,马塔王酋长领地则靠文化旅游来进一步传播马塔王酋长的故事。然而,评估却没有具体说明飓风对这些地方相关的非遗表达和传承的影响。同样,在2012年埃文飓风之后的萨摩亚,政府评估了传统萨摩亚集会屋(fale)的损坏情况,并将这些结构从文化景观中迅速消失与建筑大师(tufunga)的去世联系在一起。然而,评估报告没有考虑飓风造成的损害与建筑大师数量的下降以及其他历史因素加在一起,是否会影响萨摩亚群岛非遗的总体生存能力。2016年,斐济飓风灾难后评估的重点是与非遗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原材料的损失情况,却没有考虑非遗传承人或其他非物质文化项目受到了多大程度的影响。
三、复原力之源:灾害风险管理与非遗的活用
自然灾难、冲突和疫情往往给人们带来了物质和精神文化上的双重损失。物质上的损失能够通过量化评估来恢复和重现,但精神创伤和文化损失却难以在短期内体现出来,因此各种灾后管理和干预措施都缺乏相应的重视和详尽的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人们认同感和持续感来源的非遗,可以成为社区复原力的重要来源。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UNISDR)将灾害风险管理(Disaster Risk Management)定义为“使用行政指令、组织、操作技能和能力来实施战略政策和提高应对能力的系统过程,以减少灾害的不利影响和灾害发生的可能性”①Meredith Wilsonand Chris Ballard, Safeguarding and Mobilis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ontext of Natural and Humaninduced Hazards.。对于灾害管理周期来说,非遗是直接提高抗灾能力和降低脆弱性的减灾战略中的一个关键工具。大量例子证明非遗的实践可以在准备、响应和恢复的三个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不仅如此,非遗蕴含的备灾经验可以在有类似情况的社区之间共享。
首先,“准备”(preparedness)被定义为“社区和个人拥有的能够有效地预测、应对和恢复可能发生的、即将发生的或当前灾害影响的知识和能力”②同上。。在准备阶段,非遗蕴含的代代相传的经验使得社区能够有效地预测和应对可能发生的灾害的影响。然而这种经验的代际传承依赖于历史、记忆和故事等文化传递机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艾塔佩港海啸从反面说明了非遗的存续力凋零给地方社区备灾带来的影响。1998年,一场海啸吞没了艾塔佩港沿岸的村庄,灾后的科学研究发现这类规模的海啸灾难曾在1907年发生过,然而与备灾有关的记忆和故事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对于没有灾难经验的新移民社区来说,备灾战略往往尚未牢固地扎根于社区内。这类间隔时间较长的灾难需要建立更牢固的传承机制以传承备灾相关的非遗。重视对相关非遗项目的清单编制也是准备阶段的重要工作,如2018年被列入代表作名录的联合申报(瑞士—奥地利)项目“雪崩风险管理”展示了阿尔卑斯山原住民防范和管理雪崩风险的地方性知识。几个世纪以来,为了防范雪崩灾害,该社区形成了相关的文化习俗,发展了风险规避战略。相关知识也从口头传承走向了经验和实践结合的动态发展过程。测量仪器和风险地图之类的现代工具出现,补充了原来由传承人实地积累和调整的传统知识,形成了从科学转向实践、再由实地转向研究的过程。
其次,“响应”(response)的定义为“在灾害发生之前、期间或之后立即采取行动,以拯救生命、减少对健康的影响、确保公共安全和满足受灾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③同上。。在响应阶段,非遗是重要的复原力资源。它既能给人们精神和情感上的慰藉,又能带来替代性的收入和物质援助。新冠肺炎疫情与活态遗产平台中的大量案例展示了非遗在疫情中的作用。例如,口头传统、音乐和舞蹈作为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方式,还可以用来表达对战役前线医护人员的支持。在西班牙,唐布拉达鼓手演奏仪式(the tamboradas drum-playing rituals)是天主教圣周庆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今年没有在街头举行。相反,位于卡斯蒂利亚—拉曼恰(Castile-La Mancha)的海伦圣周鼓手俱乐部协会提出了“待在家”的口号,并邀请鼓手在城市的窗户、阳台和露台尽可能多地进行演奏。圣周五受难日下午5 点,整座城市同时响起密集的鼓声,全家老小一起出现在阳台上,让人们获得了领集体圣餐的感觉。这些例子说明非遗对很多人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并能够为身处困境的人们提供归属感和慰藉。另外,人们还用吟诗、歌唱和故事讲述等不同形式的活态遗产来交流关于新冠的信息,促进公共行为改变并倡导公共卫生建议。柬埔寨的急需保护项目长臂琴(Chapei Dang Veng)就起到了传递重要的公共健康信息的作用。长臂琴在柬埔寨社会的传统功能之一就是向社区传达重要的讯息。如今孔奈大师(Master Kong Nay)遵循这一传统,但其内容演唱的是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和其他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安全提示,同时通过社交媒体扩大其影响力。
另外,不少与传统手工艺相关的非遗项目贡献了抗疫所需的物资和传统医疗知识,如不少国家的织造手工艺人都纷纷发挥自己的特长,就地取材制作口罩。在我国的“中国传统和香制作技艺”案例中,非遗项目“盛京满绣”防疫香囊(满族荷包)也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传承人创造性地将满族香囊制作与传统中医相结合,把含有抗菌消炎成分的药粉装入绣有传统图案的满足香包中,在投入市场后立刻接到了大量订单,实现了传承人创收和社区防疫的双赢。
最后是“恢复”(recovery)阶段。“恢复”被定义为“恢复或改善受灾社区或社会的生计和健康,以及经济、物质、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资产、系统和活动,以符合可持续发展和‘重建得更好’的原则,以避免或减少未来的灾害风险”①Meredith Wilson, Chris Ballard. Safeguarding and Mobilis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ontext of Natural and Humaninduced Hazards.。如果响应阶段包含灾害发生后立即稳定局势的短期措施,那么恢复阶段就是一个将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恢复到接近“正常”状态的长期过程。一个社区的恢复速度与灾难的性质和规模有关,也取决于社区的准备和应对能力,以及更广泛的国家或社会的援助能力。在1997—1998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接连发生干旱、饥荒与海啸,家庭和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自身的恢复。当地在灾前做好了住房和粮食供应方面的准备,因此灾害的直接伤害被降到最低的同时,灾后恢复所需的时间和资源也大大减少。有些社区将储备食物以应对饥荒的知识世代相传,因此也具有很强的灾后恢复能力。除了这些与物质资源恢复相关的非遗知识和实践,地方社区的文化信仰和传统价值观也对精神上的恢复至关重要。2009年,萨摩亚海啸发生后,萨摩亚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被确定为灾后恢复的核心,以便当地社区充分利用由热情好客与家族团结的观念构筑的强大的社会和家庭网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共享资源进行灾后恢复。
因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也活用非遗进行灾后的恢复和重建。在实践非遗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得到了心理和精神上的慰藉,也获得了适应新环境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一些工匠和手艺人的手工技艺成为了他们的收入来源。此外,非遗还充当了一种维持人们的认同感和持续感的媒介,不仅能够增强叙利亚人之间的互助和凝聚力,还可以帮助叙利亚人缓和与东道国社区之间的紧张局势。例如非遗的某些形式可以调解流离失所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新社会关系,改善东道国社会对叙利亚人的看法。在不同社区之间、不同文化传统之间所展开的对话有助于建立彼此之间的友谊和互相尊重,有助于实现更长久的和平与发展。
四、基于社区:能力建设和多元行动方的联合
非遗为人们提供了持续感和认同感,在紧急情况下保护非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需要多元行动方共同提高认识,在实践中增加对非遗的理解和保护经验的积累。另外,紧急情况对非遗保护工作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而基于社区的需求确认是所有保护行动的核心原则。《公约》的出台,使得原本附属于物质遗产之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独立进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作为文化主体的“社区、群体和个人”也被赋予了认定其非遗价值的权力。从赋权社区的基调出发,可以认为“社区、群体和个人”是《公约》的基石。没有社区对其非遗的表达和传承,也就没有保护的对象可言。非遗的“活态性”决定其保护必须要关注到整体的传承系统,这也意味着保护行动的主体指向了“创造、传承和延续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和个人”。只有在社区最大限度的参与下,被视为他们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非遗”才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得到过程性的活用和保护。
《公约》对“保护”的定义为:“确保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和振兴。”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8 版)》,内部资料,2020年,第8 页。“立档”(documentation)应表述为“建档”,“保存”(preservation)应表述为“维护”,“宣传”(promotion)应表述为“促进”,为避免混淆,本文在后续讨论时仍采用中文官方文件中的表述。以上九个保护环节构成了非遗保护的动态性过程。在《公约》提供的保护工作框架内,加入对紧急情况的考虑,要先从确认、立档和研究方面入手,加强社区能力建设,并在实践中与其他保护环节联动。
一项对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名录中非遗项目申报材料的分析表明,很少有缔约国关注自然灾害对非遗的影响。对于那些最容易受到自然危害的缔约国来说,这种限制更为严重。2016年,世界风险指数通过将一个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程度与脆弱性进行指数化来计算风险,结果显示在自然灾害风险最大的20 个国家中,有6 个国家没有任何名录项目,8 个国家只有一个名录项目。日本和越南拥有的遗产项目数量排在所有缔约国的前列。然而在他们的30 个遗产项目中②此项目数量为2016年的数据,截至2023年2 月,日本和越南拥有的《公约》名录项目数量为37 个。,却没有提及与自然灾害有关的威胁或保障措施。与这一事实对应的是,急需保护项目申报表的第2 节中,要求缔约国确定和描述“对项目持续传承的威胁”,在代表作项目申报表的第3 节中,要求缔约国概述“保护措施”。然而,这两份表格以及相关的说明材料都没有特别要求或提示考虑自然灾害的过去、现在或潜在影响。
在今后的清单编制工作中增加对此类项目的关注,可以提高灾害应对相关非遗项目的可见度,提高社区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同时也能让此类非遗项目在紧急情况下成为地方复原力的来源。
社区在进行清单编制时,就应着手对非遗项目在紧急情况中的风险和存续力的相关数据进行建档。对于单个非遗项目来说,可以通过一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灾难传记”(ICH-disaster biography)来记录它的存续力风险和可活用方式。这类传记需要类似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对项目展开长期的跟踪记录,并结合相关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进程。这种建档方式的前提是认识到非遗的活态性,并把社区世代传承和传播非遗涉及的过程视为保护的重点。如此才能为紧急情况下的非遗保护和活用提供更多详实的历史资料。
目前,缔约国、社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业人员缺乏明确和实际的指导,以使他们能在灾害语境下采取预测、记录、跟踪和保护非遗所需的措施。虽然《原则和模式》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总体上的行动方向,但是我们仍缺乏具体操作的经验。2010年发布的《世界遗产灾害风险管理资源手册》(以下简称《世界遗产手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作模型。按照“知识共享的伙伴立场”,缔约国可以制定一本“非遗手册”,以共享紧急情况中保护和活用非遗的经验。在以《世界遗产手册》为范本的同时,这本“非遗手册”需要体现遗产的有形和无形部分的差别,例如非遗的活态性和过程性保护,以及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复杂背景下非遗的脆弱性,以便让保护行动更有针对性。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通过循证研究的方式梳理了教科文组织在紧急情况下是如何开展非遗保护的国际行动,以及形成了哪些政策性成果。从对非遗双重属性的认识,到确定基于社区的需求确认,再到《原则和模式》的制定,无不可以看出这一点。“活态遗产经验与新冠疫情”平台的案例让我们再次认识到紧急情况下非遗保护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非遗保护在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文化政策推进,最终都要以社区、群体和个人的日常实践为基石。社区的能力建设功在日常,需要多元行动方的共同参与,其中也自然少不了学术界的参与。有些民俗学者已经身体力行地展示了,有必要在非遗保护研究中寻找学理和文化实践的对话与有机结合①详见朱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以越南富寿省唱春项目的名录转入为个案》,《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6 期。,“以自觉的方式履行学科公共职能”②康丽:《公共危机时刻的学科实践与学者自觉——疫情中的民俗学思考》,《京师文化评论》,2020年秋季号(总第7 期),第188 页。。对于紧急情况下的非遗保护来说,灾害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和口头传统等相关的研究都可以、也都有必要转化为社区能力建设的强大资源。对于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来说,只有居安思危,才能转危为机,本文所做的探索只是一个小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