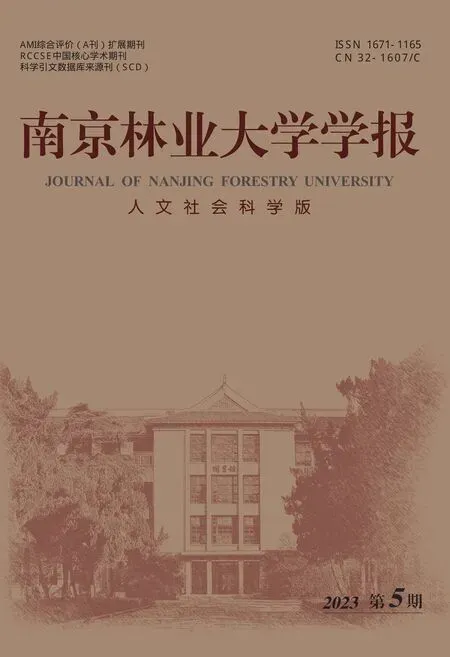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的生态重估
李思捷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文化研究领域的开创者。虽然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及其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在中国学界的热度、熟悉度与普及度较高,但是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其中存有的生态思想却仍属于一片广阔而又陌生的“处女地”,缺乏相应的关注与重视。
在1995年弗雷德·英格利斯(Fred Inglis)为雷蒙·威廉斯出版的传记中,曾记录下威廉斯女儿对其父亲晚期事业评价的一份“绿色声明”:“为了绿色政治,为了生态;为了盖亚。”①INGLIS F.Raymond William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14.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起,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已经出现了“生态转向”的兆势,并在日后将生态文化研究(ecocultural studies)发展成为其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②西方学者罗德·吉布莱特(Rod Giblett)用“ecocultural studies”概括威廉斯用文化研究的生态维度及其生态贡献。参见:GIBLETT R.Nature is ordinary too:Raymond Williams as the founder of ecocultural studies[J].Cultural studies,2012,26(6):922-933.在该文中,吉布莱特指出,威廉斯既是生态文化研究的创始人,也是生态批评的创始人,尽管“生态文化研究”一词并未直接出现在威廉斯的作品中。细读威廉斯的理论作品,结合当下西方生态人文学界对威廉斯文化研究所开展的部分分析,可以看出威廉斯的生态文化研究主要体现为三个维度:对自然的概念分析、对文学作品的生态批评以及对社会发展的生态批判。对于探讨三个维度的发展脉络、内在关联、具体内容以及当代价值而言,需要我们采取一种“生态重估”的方法与态度,即要求我们从一种生态视角,对威廉斯的文化研究进行重新的勘探,重新的认识与发现,以及重新的评价。通过这样的“生态重估”,不仅将为我们还原出一个“绿色威廉斯”的形象,也将为我们进一步挖掘威廉斯文化理论遗产提供“绿色的指向与索引”。
一、作为“关键词”的“自然”
“自然”始终是生态领域关注的首要对象,对“自然”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我们人类的生态理念,尤其是对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等关系的相关认识。对“什么是自然”这一问题的回答,一直是当下生态人文学者持续参与的辩论话题,而威廉斯的自然观则是他们时常回溯的理论焦点,这可以从环境历史学家凯特·索珀(Kate Soper)同名书籍中一窥而知。①SOPER K.What is nature? :culture,politics and the non-human[M].Oxford :Blackwell,1995.对于威廉斯而言,他的自然观主要是通过“关键词”的方式进行阐发。可以说,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所开创的“关键词”传统,至今仍是对特定概念分析的强大而有效的方法。就“关键词”这一概念分析方法而言,“自然”并不仅仅是学术文本中的“关键词”,更重要的是“文化与社会”中的“关键词”。
在《自然的观念》(“Ideas of Nature”,1971)一文中,“自然”无疑成为了全文的关键词。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于J.本索尔(J.Benthall)主编的《生态:塑造调查》(Ecology: The Shaping Enquiry)。该文对“自然是否包括人类”这一问题进行了重点探讨。威廉斯的核心观点在于“自然包括了人类大量的历史”②WILLIAMS R.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selected essays[M].London :Verso,1980:70.。在他看来,自然的观念其实就是人的观念,进一步来说,是人在社会中的观念,表明了人对社会的各种看法。例如,“自然”在宗教者眼中往往被拟人化为各种神灵,代表一种神圣的秩序;在进化论者眼中则意味着食物链、凶猛动物以及生存竞争,代表着一种世界的物理危机。就此而言,“自然”在启蒙时代哲学家、政治家以及浪漫主义作家眼中,同样具有不同的含义与形态,成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建构的产物。
在威廉斯看来,人与自然的分离的确是历史上发生的某些思想倾向,但人与自然的分离,同样来自人类活动。这一过程并不仅仅是现代工业和城市主义的产物,甚至从早期农村劳动出现便已开始。威廉斯反对把“自然”概念抽象为单一概念的文化倾向,尤其是将“荒野”作为“自然”的全部形式。对于“荒野”这种“无人自然”的概念来说,它同样是人类观念的一种投射。这将带来一种人与自然完全分离的错觉,遮蔽了我们在当下时代与物质世界多样化的真实关系。威廉斯认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人类劳动与地球的紧密结合,并以一种整体的方式重新思考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对此,威廉斯指出:
垃圾堆是像煤一样真实的产品,就如同因污水和洗涤剂而恶臭的河流像水库一样是我们的产品。封闭肥沃的土地是我们的产品,但是清除了贫穷的种植者的荒原同样如此,这留下了可以被视为空虚的自然。此外,我们自己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产品:工业社会的污染不仅可以在水和空气中,也可以在贫民窟、交通堵塞中发现,同样不仅在这些实物,也可以在身处其中的我们自身及与它们的关系中发现。③WILLIAMS R.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selected essays[M].London:Verso,1980:83.
在此基础上,威廉斯反对经济学和生态学知识间的分离。正如“经济学”(economics)和“生态学”(ecology)两个单词拥有共同的前缀“eco”,现实生活中经济与生态问题是复杂交织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人类自身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作为“风景”存在的“自然”或是“荒野”,是消费者眼中所追求的原生态“产品”,但是欣赏过程中被排除的具有破坏自然和污染环境性质的“副产品”,则被简单划归给了自身之外的生产者。威廉斯借此想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及其意识形态力量,正是借助这样的分离化操作,从而完成了对“自然”概念的形塑。
在《关键词》(1976)中,“nature”被威廉斯称作“也许是语言里最复杂的词”①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26.,也是在这本书中,威廉斯正式确认了“关键词”的研究方法。从文本篇幅看,“nature”的确是所有“关键词”中书写页数最多的。这一词条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自然的观念》,具有诸多相近的内容。不同之处在于,词条的书写模式更侧重于历史语义的梳理,在概念归纳上更加清晰化、条理化,并从词源上作出进一步考察。威廉斯认为,“nature”主要有三种可以区别的含义:(1)某个事物的基本性质与特性;(2)支配世界或人类的内在力量;(3)物质世界本身,可包括或不包括人类。②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26.威廉斯对这三种基本词义的态度,事实上表明了他既承认自然的物质存在,也承认自然的心灵力量。可以看出,威廉斯并不像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两者视作互斥方面,这体现出了他生态思想中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该词条的文末,威廉斯还特别列举了与“自然”相关的词汇,如“乡村”、“文化”、“生态”、“进化”等,这种“相互参照”的做法是威廉斯书写“关键词”时的有意设计,他正是希望借此“提醒读者注意词汇重要的关联”。③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
这里,我们也有必要对威廉斯的文化观进行一定的考察。这不仅是因为“文化”常常被视为“自然”的对立面,更在于“文化”之于威廉斯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在《关键词》中特别区别了“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文明”带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往往代表“文化”的负面影响,构成与“自然”的对立冲突。而“文化”的涵义则在浪漫主义的层面上,对“文明”提出了一定的纠偏和批判。事实上,“文化”同样是英语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其含义远比浪漫主义的理解更加丰富。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认为:“在过去,文化指心灵的状态或习惯,或者说一些智性和道德活动,现在则包括了整个生活方式。”④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M].高晓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22.从威廉斯后来在《漫长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进一步发展出的文化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文化既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基础的反映,也不只是一种决定性的意识形态结构,而是整个物质社会过程构成和被构成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对于整体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的强调,正类同于生态学的相关内涵与观点。基于此,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威廉斯对文化的定义与生态学很接近。⑤EAGLETON T.The idea of culture[M].Oxford:Blackwell,2000:127.由此,无论从“自然”来看,还是从“文化”来看,它们都是“整体的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进而消解了长期以来的自然/文化概念上的二元对立模式。
从上文可以看出,作为“关键词”的“自然”,首先关注的是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自然”概念的多元文化层次及其社会背景,它将自然和文化的转变同时置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观察与对照;其次,以一种简洁而不简化的方式最大化地挖掘出“自然”概念的潜在价值,这种潜在价值说明,“自然”并不是文化变革的反面,而是社会批判和替代价值的重要来源。其三,“关键词”本身构成了一种词汇的生态网络,既具有一定的辞书性,也具有一定的反辞书性。“自然”的概念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文化争论”中,由单数化的形式走向复数化的形式。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追寻“自然”在威廉斯文化研究中作为“关键词”的生成历程。由此来说,对于任何一种特定的“自然”的概念,都有其合法性存在的历史基础。威廉斯借此提醒我们,比起追问“自然”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关注“自然”背后存在的人类历史。从事实来看,这也正是生态问题的症结,而相似的历史意识,作为一种“元方法论”,也同样贯穿于威廉斯对文学作品生态批评和对社会发展生态批判中。
二、环境写作的生态批评
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威廉斯《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1973)这部批评著作,我们会发现,它所涉及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属于“环境书写”(environmental writing)或具有“环境书写”的成分以及类似性质,而其中部分文学作品更是可以直接归类于“自然书写”(nature writing)。由于这部著作以一种潜在的生态视角,对英国大量的乡村文学和城市文学作品作出了出色的分析与深刻的批评,因此后来也被赞誉为“生态批评的先锋杰作”①HEAD D.Raymond Williams and ecocriticism[J].Green letters,2000,1(1):7.。
在《政治与文学》这部采访录中,威廉斯曾明确表示,他写作《乡村与城市》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评估针对田园诗提出的文学批评问题”②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M].樊柯,王卫芬,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309.。从当时的主流批评环境来看,英国学者对田园诗的探讨往往只关注其中的“文学性”,而忽视了其中显而易见的“社会-政治前提”。但是,在威廉斯看来,文学并不只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对历史的表现。因此,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辨识出田园诗中存在的虚假表现,而这与利益、特权、阶级立场息息相关。在这一点上,以本·琼森(Ben Jonson)的《致潘舍斯特》(To Penshurst)和托马斯·卡鲁(Thomas Carew)的《致萨克斯海姆》(To Saxham)为代表的“乡村宅邸诗”,受到了威廉斯的尖锐批判。这些诗人通过“赞美自然”的方式服务于特权阶层的需求,在“田园诗”中呈现出自然富足的简单面貌,遮蔽了“劳作乡村”中农民、劳工的实际生活条件和其中的政治景观。对此,威廉斯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模式引入了田园诗的批评中,指出这些诗人和乡村宅邸方面的资助关系及其采取的美化视角,进而打破了田园怀旧的神话。威廉斯对田园诗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田园诗的研究传统。生态批评家杰拉德(Greg Garrard)就曾指出:“《乡村与城市》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对田园诗的解读,以及后来对田园诗定性或反驳的生态批评回应。”①GARRARD G.Ecocriticism[M].New York:Routledge,2004:37.
在“乡村宅邸诗”之后,威廉斯进一步调查了英国其他文学作品对乡村和城市的想象。其中涉及英国诸多代表性作家,包括反田园诗人克雷布,浪漫主义田园诗人华兹华斯、克莱尔;小说家科贝特、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狄更斯、托马斯·哈代、劳伦斯;以及其他都市小说、新乡土小说作家等等。这些作家至今都是生态批评项目清单中的重点对象,为生态批评提供了广泛的文学素材。尤其是威廉斯对英国小说的分析,使得《乡村与城市》的生态批评价值远远超过了田园诗的批评层面,也超过了他对自己作品的预期。在对众多文学作品的历史考察中,尽管一些作品突破了固定的视角,表现了城乡之间的内在流动性,但是威廉斯发现,在一个整体的文学传统中,乡村和城市似乎经常处于相互对立中,例如“乡村被视为同自然的合作,城市和工业被视为是对自然的凌驾和改变”、“关于乡村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关于城市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②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97,402.。从一个更加原型化的视角来看,“乡村”即代表“自然”,“城市”即代表“文化”。
对此,威廉斯认为这样的抽象化分离其实都来自社会利益和控制模式的决定,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优先特权的强加。事实上,乡村与城市的发展一直处于联系之中,并且二者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中间形式以及新的社会、自然组织。正如马丁·莱尔(Martin Ryle)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必要的联系感是威廉斯坚持的基础,即生态问题不是把自然从世界中分开和我们如何保护和享受偏远和野生的地方的问题,而是整个生产模式对人类与地球关系的构建与决定。③RYLE M.Raymond Williams:materialism and ecocriticism[M]// GOODBODY A,RIGBY K.Ecocritical theory:new European approaches.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1:46.作为一个整体的环境,威廉斯拒绝对乡村与城市进行简单划分。他认为,我们应该从“单一传统中的乡村和城市”走向“多样的乡村”与“多样的城市”。这体现了他在生态视野上对城乡二元对立模式的一种超越性的前瞻意识。与此同时,威廉斯立足于文化唯物主义中复杂性的考虑,也对城乡发展采取了一种辩证的视野:
一方面,威廉斯对城市发展问题抱以乐观态度。他指出:“如果我们摆脱有关城市的观点,我们会在异常压力下发现许多充满爱心的、高明的工作,它们可以让城市变得更干净、更优美,让城市显露出其最好的资质并构筑这些资质。”④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07.威廉斯在对威尔斯(H.G.Wells)的“城市未来小说”进行评论时,特别提到了他的“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按照威尔斯的观点,这是一种兼具科学性与社会性的新的集体意识,通过对环境进行总体掌控,可以由新科学指引朝着人类成就的方向发展,进而改变无计划的、无知的和攻击性的发展对人与动物、乡村与城市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同于其他评论家,尽管威廉斯对其中包含的“城市进步主义”保持了一定的警惕,但他并没有把“城市未来小说”完全当作一种“乌托邦”幻想,而是适度肯定了其在面对大都市与工业文明危机背景下所具有的积极的反应价值。
另一方面,威廉斯同样认为我们在当下城市化进程中,一定程度上无法回避资本主义发展所带给我们的处于“怀旧”与“进步”、“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分裂状态。这里,威廉斯所指出的分裂状态正属于我们现今所说的“精神生态”问题。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威廉斯又肯定了以克莱尔(John Clare)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绿色语言”(green language)。对于克莱尔的“绿色语言”,威廉斯指出,“正是为了作为能够思考和感觉到人生存下去,他才需要新的自然的绿色语言”①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00.。在这种“绿色语言”中,诗人可以通过自然的感觉重新创造世界与人类。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想象的诗学,从文化治愈的层面寻求对自然的回归。这种绿色的文化诉求,在威廉斯对劳伦斯小说的评论中得到更明确的彰显。威廉斯总结道:“土地的歌,乡村劳动的歌,还有对生命各种形式——我们同它们一起分享这个物质世界——感到快乐的欢愉之歌,它们是那么重要、那么动人,我们不能乖乖地放弃它们,把它们出卖给与真正的、重要的独立和复兴为敌的狂妄之徒。”②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73.由此来看,威廉斯将情感视为当代人类和自然世界之间重新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进而将浪漫主义的生态维度有机融合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维度之中。可以说,在对自然生态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威廉斯以一种互补的态度实现了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诉求的辩证统一。
作为威廉斯的标识性概念与重要批评方法,“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在《乡村与城市》中起到了联结自然与文化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说,上述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情感结构”,无论是乡村怀旧主义的情感结构,还是城市进步主义的情感结构,它们既包含于某种内在的文学与艺术传统中,也对照着自然、乡村、城市的变化与人类社会的实践发展。除了这些“情感结构”类型本身值得我们注意外,威廉斯对这些“情感结构”背后的“社会结构”的挖掘更加值得我们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社会结构”同样是一种生态真相,从而预示了威廉斯“生态政治”(ecopolitics)的理论向度。
三、生态政治与“生计”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在威廉斯的文化研究中,“生态”一词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多。作为一个明显的标志,“生态”在1984年第二版《关键词》中,和其他20个词汇一同被威廉斯拣选增添了进去。这与威廉斯的政治参与和新的政治形势发展有密切的关联。生态运动、英国政党当中的绿党成立和左翼当中的绿色思潮,都助推了威廉斯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在《希望的资源》(Resources of Hope,1989)所收录的文章和《走向2000年》(Towards2000,1984)这部专著中,威廉斯将生态问题与政治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进一步阐释与发展了前期作品中潜在的生态思想。
《社会主义与生态》(“Socialism and Ecology”)是威廉斯在英国社会主义环境与资源协会(SERA)的演讲,当时威廉斯正受邀担任该协会的副主席。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迈克尔·洛维(Michael Löwy)曾指出,这篇文章是欧洲最早将“生态”和“社会主义”两个术语联系起来的文章之一。①LÖWY M,SAYRE R.Raymond Williams,romanticism and nature[J].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18,29(2):86.在这篇文章中,威廉斯主要对社会主义者中存在的两个错误的生态论调进行了分析。②WILLIAMS R.Resources of hope:culture,democracy,socialism[M].London:Verso,1989:210-226.其一是“从工业社会倒退到对环境没有破坏的前工业化社会”的论调,该论调简单地把环境与资源问题归结为工业革命的出现。威廉斯用新石器时期就存在的过度耕作放牧、植被破坏、荒漠化、气候变化的例子尖锐地反驳了这一论调。他认为,这一论调对自然状况进行了错误的对照,并且忽视了我们当下的经济状况。其二是“增加生产是解决贫困的有力的而且是唯一的办法”的论调。威廉斯指出,近半个世纪生产的高速发展虽然整体上改善了我们的状况,但没有消除贫困,甚至还造成了新的贫困。症结的根源不在于生产问题,而在于分配问题。显然,如果仍然简单地坚持这种“增产”观念,不但不利于我们当前生态状况的缓解,反而会进一步造成生态恶化。那么,如何在正视当下经济状况与兼顾未来生态状况的前提下,妥善处理我们的社会发展所必须面对的生产问题,成为威廉斯寻求绿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思考方向。
在《走向2000 年》一书中,威廉斯将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等新的政治因素,视为建立一个新社会秩序的“希望的资源”。这本书也更集中地展现了他的生态政治目标。威廉斯认为,资本主义深深嵌入了一种将世界作为原材料的方式之中,它将所有其他东西服从于生产及其优先事项,使更广泛的人类和社会问题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置于次要地位。此时,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变化通常被视为生产的“副产品”(by-product),而“副产品”的词语含义则会使我们轻视它们潜在的危害。然而,对于威廉斯而言,真正的生态危机并不只是环保主义者所重视的工业和化学污染、自然栖息地和物种的破坏等显在的问题,它同样来自对人类本身生活的观照,并不能用简单的“去工业化”的思路和方式来解决。这构成了威廉斯绿色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生态论点”(ecological argument):
真正的问题是,地球的生命形式是可提取和可消费的财富这种说法。我们看到的不是许多生命形式的来源和资源,而是一切,包括人,作为可用的原材料,被挪用和改造。与此相反,生态论点表明,在一个又一个案例中,作为一种看待整体的不同方式,即一个复杂的物理的及其侵入性和相互作用的生物过程,不能长期以这样的方式处理,忽视严重的和不可预见的损害。③WILLIAMS R.Towards 2000[M].London:Chatto&Windus,The Hogarth Press,1985:214-215.
从“生态论点”出发,我们对生态危害的预测,既要考虑到非人类的存在,也要考虑到人类自身。值得敬畏的是,威廉斯亲自参与并支持了南威尔士矿工的抗议游行活动。这些矿工希望能够保留这份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的极端危险的工作,而不是被政府的环保举措所直接取缔。对于这些工人来讲,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而这就是他们的“生计”(livelihood)。在一个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从这一例子可以看出,威廉斯反对肤浅的、形式的、激进的环保主义(environmentalism),因为它和普通群众,尤其是劳工阶层的一般利益缺乏联系。作为解决办法,威廉斯认为对这样事件的处理应该通过协商的方式,并且稳步推进。在《乡村与城市之间》(“Between Country and City”)一文中,威廉斯呼吁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性生态(a new kind of political ecology):“它能把生产过程追溯到经济与社会结构上,其发展、巩固与前两者紧密相关,并且能够合理地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经济和社会体制。”①WILLIAMS R.Resources of hope:culture,democracy,socialism[M].London :Verso,1989:233.在这样的平衡取向下,威廉斯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章和著作中启用并发展了“生计”这一概念语。
“生计”是威廉斯更深层次的概念。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威廉斯的文化研究中,“生计”和“生产”是一组对照概念。“生产”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往往在利益驱动下并不考虑生产的内容、质量和其他人和事的影响。相反,“生计”则需要从人类真正的需求(非消费社会“物欲”下的操控需求)开始,并考虑所有相关生物的利益。其次,“生计”概念作为一个中间术语,将避免“自然”和“生产”之间的简单对比,同时改变地球及其生命形式作为普遍生产的原材料的主导概念,进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物理世界和所有真正必要的物理过程。此外,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威廉斯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中的“生计”问题,并把此视为生态和劳动力之间关系的核心困境,这也构成了其原创性思考当中最具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的部分。
然而,威廉斯并未对“生计”一词进行过明确的定义,但是从它的使用上来看,它一方面意味对更广泛的人类群体福祉的考量;另一方面,基于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人类作为社会系统中重要的主体,需要兼顾处理好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关系,即人类通过自主管理,要承担好整个系统发展的责任与义务。事实上,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已经推翻了这种“生计”的观念,并把广义的生产和利润置于此之上,进而形成了城乡之间,乃至国际体系之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主导秩序。因此,对于一种绿色的社会主义来说,威廉斯认为无论从观念上还是实践上,便需要从“生产”转向“生计”。正如罗德·吉布莱特(Rod Giblett)所指出的,“‘生计'暗含着一个人的工作和他的物理环境,他们的环境支持和影响,以及类似于美国生物区域的概念”②GIBLETT R.Nature is ordinary too:Raymond Williams as the founder of ecocultural studies[J].Cultural studies,2012,26(6):928.,也正是由此“生计”概念在生态层面解构了自然与文化、城市与乡村、生活与工作的二元划分,成为威廉斯生态文化研究后期成熟阶段的最重要的思想结晶。
威廉斯始终认为,我们关心环境问题,要与广泛的政治因素联系起来。在《未来阶段的种种问题》(“Problems of the Coming Period”)、《走向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Towards Many Socialisms”)、《面对社会主义的种种犹豫》(“Hesitations before Socialism”)等文章中,威廉斯也都表达了对相似问题的同样思考。③这三篇文章也都收录于WILLIAMS R.Resources of hope:culture,democracy,socialism[M].London:Verso,1989.威廉斯始终坚持文化研究的政治批判与社会批判维度,追求“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的社会理想,而现代生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阶级利益的存在,构成了对这一理想事业的冲突,这进一步激发了威廉斯在文化研究中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最终发展出了其“生态政治”的理论向度。
事实上,威廉斯富有洞察力的言论,已经揭示了21世纪生态辩论中提到的大多数紧迫问题,甚至包括了气候变化、核武器战争等。基于一种共同的生态利益,威廉斯认为,我们需要在政治上扩大原有的共同体或寻求建立新的共同体。对此,我们只有坚持“真正经验共享、深信人类平等的立场”,通过协商的方式,统筹考虑生态学和经济学,才可以走向公平、共享的新型政治,实现绿色的社会主义。
四、威廉斯文化研究的生态转向及其当代价值
尽管上述内容并不能完全展示出威廉斯在生态文化研究方面的全部内容与思想潜力,但是足以揭示出威廉斯文化研究生态维度的存有,及其在威廉斯整个文化研究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与发展脉络。概以观之,在20世纪70年代的作品中,威廉斯对自然的关注度显著提高,开始探究自然与文化、乡村与城市的内在关系,生态意识以一种隐性状态存在于概念分析层面、文学批评层面;在80年代的作品中,威廉斯直接介入社会生态问题的探讨,发展出生态政治这一重要理论向度,贯通连接了先前隐性存有的生态意识,并以显性状态直接应用于社会批判层面。如此可以看出,从70年代起,威廉斯的文化研究发生了“生态转向”并且这一转向变得日趋明显。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威廉斯的文化研究没有可以发掘的生态内容,只是说明在70年代之前,无论从其相关的作品数量,还是从其关注与重视的程度来看,生态议题都还未进入到廉斯文化研究的中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威廉斯的文化研究融合了他的学术事业、政治事业与社会事业。可以说,对于威廉斯而言,文化研究是贯穿其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威廉斯在文化研究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直到今天,他的文化研究仍然在引领着当下文化研究的前行,拓展着文化研究的相应领域。威廉斯文化研究的生态转向,不仅推动了自身文化研究体系的一种生态转向,更是推动了整个西方文化研究体系的生态转向。其中包含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值得我们探究与肯定。这主要体现为三点:
一是开创了一种带有生态导向的文化唯物主义自然观。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中,“自然”既具有“物质实体”属性,也具有“社会实体”属性。对于后者,威廉斯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西方对“自然”讨论的“建构主义”路径,接连了后现代主义对传统“自然”范畴的怀疑与批判。相较于单独将“自然”解读为一种“物质实体”,威廉斯发掘与审视了“自然”概念背后的文化意义,把自然看作是一个展开和流动的动态过程,质疑了各种自然表现背后的意识形态论述,丰富了我们与自然世界的联系的生态认知。基于“整体的生活方式”,威廉斯将我们对于自然的理解融于普通人的社会关系、经济活动、生存需要和日常经验中,打破了自然与文化、乡村与城市、社会与生态之间的二元对立,提供了一种具有一个整合、参与和非二元论生态自然观。
二是促进了生态思维范式由深层生态学向社会生态学的转变。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突出了自然的自在价值和非人类物种的天然权利,在当代环保运动兴起初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推动作用。例如,在《深层生态学》中,比尔·德沃尔(Bill Devall)和乔治·塞申斯(George Sessions)将该运动的“终极规范”描述为“自我实现和以生物为中心的平等”①DEVALL B,SESSIONS G.Deep ecology:living as if earth really attered[M].Salt Lake City,Utah:G.M.Smith,1985:205.。但是深层生态学在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判时,往往容易走到生态中心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它对“未被破坏的自然”与“荒野”地区的强调,造成了人类和自然之间分离的观念倾向,缺乏对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与环境之间互动的关注,更忽视了我们当下的城市生活本身。相比之下,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关注人类创造和使用的自然世界,将生态问题置于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复杂交叉点,抵制简单地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相反尝试,对深层生态学进行了补充性的反思。社会生态学的创始人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认为,“我们的基本生态问题源于社会问题”②BOOKCHIN M.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ecology:essays on dialectical naturalism[M].Montreal:Black Rose Books,1995:35.,这与威廉斯对“生态政治”的理论向度具有诸多重合之处。在当下环境正义、城市自然、劳工运动等社会生态学议题中,威廉斯的生态文化研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社会生态学重要的理论支点。
三是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批评的产生与发展。在西方生态批评各种简介的书写中,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往往都被视为早期重要的开创性作品。以《剑桥文学与环境导论》为例,该书便指出,生态批评作为一个可定义的知识运动,是以1992 年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的成立为标志,但是公认的生态实践形式可能更古老,比如雷蒙·威廉斯的《乡村和城市》。③CLARK T.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3-4.对此,迈克尔·马莱(Michael Malay)也曾通过横向对比研究,表明“尽管威廉斯在‘生态批评’成为一个流行的词之前就去世了,但他的许多观点都与生态批评的目标和原则密切相关”④MALAY M.Raymond Williams and ecocriticism[J].Key words:a journal of cultural materialism,2014,12:12.。而从西方生态批评纵向发展历史来看,威廉斯生态文化研究中的浪漫主义生态维度主要被英国生态批评所继承,这孕育了英国第一本正式意义上的生态批评著作——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的《浪漫生态学》(Romantic Ecology),并影响了后来英国浪漫主义生态批评的走向与发展形态。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威廉斯生态文化研究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第一波和第二波生态批评浪潮的迭代上。根据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划分,第一波生态批评聚焦于自然写作、自然诗歌和荒野小说,第二波生态批评倾向于环境正义问题和社会性生态批评。两者相较来看,作为对第一波生态批评浪潮的修正,第二波生态批评浪潮更加关注城市中的自然遗迹,或对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态非正义罪行等问题。⑤布伊尔.生态批评的未来[M].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这也正是受到了生态思维范式由深层生态学向社会生态学转变的影响。在第二波生态批评浪潮中,威廉斯越来越多的作品受到生态批评家们的关注与引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批评相关项目的深入融合。正如纽曼(Lance Newman)所指出的,“开始展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批评项目的相关性的一个好方法是,简要回顾英国社会主义者雷蒙·威廉斯的文化工作”①NEWMAN L.Our common dwelling:Henry Thoreau,transcendentalism,and the class politics of nature[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127.。可以说,威廉斯的生态文化研究将社会分析、文本批评和政治倡导密切结合,为生态批评提供了一种典型范式。当下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已从文学作品扩展到整个文化制度及其实践,成为当代生态人文学科知识的集大成者,并反向对社会生态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时至今日,威廉斯的生态文化研究仍有很多可供生态批评挖掘与吸收的理论资源,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索。
五、结语
徐德林在《威廉斯研究在中国:遗产与债务》一文中指出:“在我们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新文化现实的当下,再次寻找‘希望的资源’是一种必须。”②徐德林.威廉斯研究在中国:遗产与债务[J].文艺理论与批评,2022,218(6):33.事实上,威廉斯的生态文化研究正是他所留给我们的“希望的资源”,也是我们中国学界目前对威廉斯研究的一项未完成的债务。
总体来说,《自然的观念》《乡村与城市》《关键词》《走向2000年》和《希望的资源》等多部作品构成了威廉斯生态文化研究的基本文献,展现出了威廉斯对生态、文化和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深刻思考与把握。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立场下的“自然观”,他在生态批评中对浪漫主义生态维度与马克思主义生态维度的融合与发展,以及他在“生态政治”理论向度中所提出的“生态论点”、“生计”问题、“产品”和“副产品”新论断,对我们当下的生态问题的学术介入,都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反思价值。另外,通过威廉斯的生态文化研究,我们也可以发现“关键词”、“情感结构”以及“共同文化”等“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在生态与文化结合地带所具有重要的理论效应。也就是说,除了关注威廉斯本身对于生态内容的论述,其在分析自然与生态问题时所使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分析同样值得我们借鉴。还有,威廉斯文化研究的生态重估应该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例如,在近年来的研究中,理查德·麦克韦尔(Richard Maxwell)和托比·米勒(Toby Miller)结合威廉斯的生态思考与其媒介研究对劳工运动进行的探讨③MAXWELL R,MILLER T.Cultural materialism,media and the environment[J].Key words:a journal of cultural materialism,2013,11:90-106.,便预示了一种生态批评与媒介批评融汇的可能潜力。这启示我们,可以从多维度、跨学科的角度进一步发掘威廉斯生态文化研究中潜在的理论资源。
基于此,对威廉斯文化研究进行“生态重估”,不仅有利于我们从生态维度发现与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威廉斯,寻找出威廉斯理论研究新的生长点,也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与发掘威廉斯的理论遗产,进一步推动当下文化研究的生态延展与人类社会的生态发展。尤其是在“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背景下,威廉斯的生态文化研究将显示出更强大的适切性与指导价值,也将在未来持续不断的生态重估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