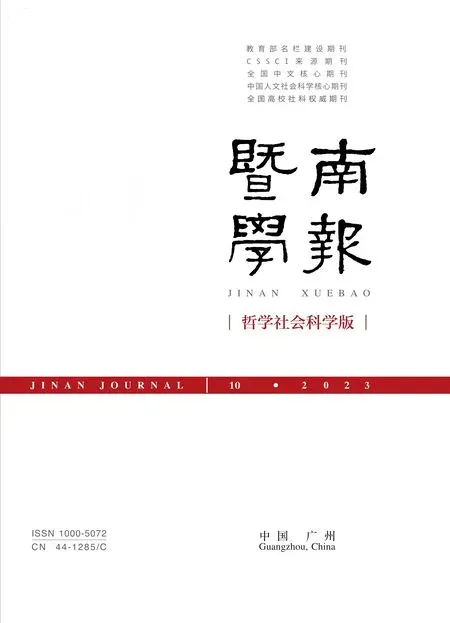“数字遗迹”治理困境与转型路径
——基于对逝者数据交互治理的考察
单 凌
一、作为新治理难题的“数字遗迹”
随着数字媒介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网民在频繁发布、记录、编辑、点赞、链接、转发等过程中,有意无意间留下了大量的数字痕迹。根据权威机构IDC(Internet Data Center)的预测,到2025年,平均每个网民每天将进行超过4 900次数据交互——约18秒进行1次,全球数据量将升至163ZB(1ZB等于1万亿GB)。(1)IDC,“Data Age 2025”,https:∥www.import.io/wp-content/uploads/2017/04/Seagate-WP-DataAge2025-March-2017.pdf,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在与日俱增的数据流动性背后,数据违规收集、数据使用争端、隐私泄露等风险也在同步增加。这些风险在用户去世后继续升级,毕竟逝者不再能管理个人数据。根据牛津网络研究院的推测,2050年Facebook已逝用户的账号数量会超过活跃用户。(2)Carl Öhman,David Watson,“Are the Dead Taking over Facebook?A Big Data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Death Online”,Big Data and Society,Vol.6,2019,p.1.当越来越多的数字痕迹成为“数字遗迹”(digital remains)时,(3)Jessa Lingel,“The Digital Remains:Social Media and Practices of Online Grief”,The Information Society,Vol.29,2013,p.191.如何管理海量的“逝者数据”(postmortem data),使人类在死后仍能维护“声誉、尊严、完整性、秘密和记忆的权利”(4)Lilian Edwards &Edina Harbinja,“Protecting Post-Mortem Privacy:Reconsidering the Privacy Interests of the Deceased in a Digital World”,Cardozo Arts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Vol.32,2013,p.101.,成为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技术的复杂难题。
学者们尝试从不同学科视角探讨“数字遗迹”的保护、继承和管理实践。这个概念所涉及的范围略有不同,比如有研究将逝者遗留的数码硬件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也纳入“数字遗迹”的范畴中。(5)Ylva Hard af Segerstad,Jo Bell &Daphna Yeshua-Katz,“A Sort of Permanence:Digital Remains and Posthuman Encounters with Death”,Conjunctions,Vol.9,2022,pp.2-3.不过,更多的研究指向社交网络平台及其他在线服务平台的用户去世后储存在网络空间里的数字信息内容。(6)Margaret Gibson,“Digital Objects of the Dead:Negotiating Electronic Remains”,in Brussel &Carpentier,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ath,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p.221-238.社会学者关注“数字悼念”(digital mourning)实践,探讨用户如何通过纪念账户、纪念页面与之保持“持续的联结”。(7)Jed Brubaker,Gillian Hayes &Paul Dourish,“Beyond the Grave:Facebook as a Site for the Expansion of Death and Mourning”,The Information Society,Vol.29,2013,p.153.档案学侧重强调“数字档案”(digital archive)的文化传承价值,呼吁建构记忆数字资源库,以丰富档案数字资源。(8)庞亮、易茜:《永不消失的“记忆”:数字时代档案建构的功能与危机》,《现代出版》2023年第2期;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档案学通讯》2012年第3期。法学则聚焦于“数字遗产”(digital legacy)或“数字资产”(digital assets)等概念,强调个人数字信息是一种可被继承的遗产,(9)Carl Öhman,David Watson,“Are the Dead Taking over Facebook?A Big Data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Death Online”,Big Data and Society,Vol.6,2019,p.3.讨论数字遗产的法律属性、分类标准与继承方式,以及可能产生的隐私冲突。(10)陈奇伟、刘伊纳:《数字遗产分类定性与继承研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牛彬彬:《数字遗产之继承:概念、比较法及制度建构》,《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杨勤法、季洁:《数字遗产的法秩序反思——以通信、社交账户的继承为视角》,《科技与法律》2019年第2期。
由上可见,这一议题的妥善解决需要交叉学科共同进行探讨与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数字遗迹”是更具包容性的集合概念,包罗规模巨大的个人信息,既能兼顾其情感、文化和财产的不同属性与价值,也不像数字悼念、数字档案、数字遗产等概念预设了对记忆和保存的不懈追求。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数字遗迹”也可以是“陈旧过时”(obsolescence)、“短暂的”(ephemeral),支撑它们的数字技术在不断的迭代中会被淘汰。(11)Tony Walter,“Communication Media and the Dead:From the Stone Age to Facebook”,Mortality,Vol.20,2015,p.215.因此,“数字遗迹”理应有一定的存续时限,这就为遗忘权、删除权或拒绝权的讨论留下了空间。
其次,以往的研究为“数字遗迹”的治理结构给出了不同的思路和建设性架构,但很少着眼于治理的过程性和互动性视角,然而在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由于互动机制缺位、权益关系不平等导致的治理失灵问题。尽管最新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填补了现有立法中对逝者信息权益保护的空白,承认用户生前对数据拥有一定的处置权,近亲属享有相应的继承权,并将用户的意愿优先于继承人的意愿,然而,“数字遗迹”问题之所以难解,其关键一方面在于用户对个人数据根本没有“事实上的管领力”,(12)牛彬彬:《数字遗产之继承:概念、比较法及制度建构》,《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另一方面,公法规则也难以约束互联网平台的内部规则。互联网平台凭借合同条款和技术上的优势,居于“数据垄断”地位,(13)许多奇:《论网络平台数据治理的私权逻辑与公权干预》,《学术前沿》2021年第21期。已成为网络数据的实际控制者。《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等规定内容过于笼统,缺少对平台的责任要求及其需要遵循的法治要件。超级平台常常只追求形式上的合规运营,规避法律的要旨与精神,未能履行与其专业能力和影响范围等相适应的义务。(14)卢家银:《无奈的选择:数字时代隐私让渡的表现、原因与权衡》,《新闻与写作》2022年第1期。对待“数字遗迹”,各类平台缺乏行业共识,无视用户需求的变化,常见的处理方式为直接舍弃或二次利用,无论是哪一种,基本都是“一刀切”的刚性手段。
当下平台在“数字遗迹”的治理问题上存在着显著的缺陷,难以回应利益攸关方的多元诉求。为了更妥善地保障各方利益,亟须注入新的平台治理精神。本文首先通过本·莱特等人所提出的“漫游方法”(walkthrough method)收集经验材料,(15)Ben Light,Jean Burgess,Stefanie Duguay,“The Walkthrough Method: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pps”,New Media &Society,Vol.20,2018,p.882.该方法是一种新兴的数字体验方法,通过对国内外各大平台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熟悉平台的界面设计、技术配置、数据管理工具和用户互动关系,以批判性态度反思当前主流平台对数字遗迹的治理模式。接着引入“交互治理”(又译“互动式治理”)的治理理念,重构“数字遗迹”的治理路径。“交互治理”注重多方行动者之间的动态交流和反馈,致力于让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在公共治理中发挥协同作用。(16)顾昕:《走向互动式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中“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变革》,《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基于此,本文进一步对“数字遗迹”治理网络的构成、运行机制、数据权利关系重新展开论述。最后,通过分析和反思Facebook的遗产联系人机制,对“数字遗迹”的可能治理模型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平台“单边主义”造成的治理失灵问题
网络平台数据是指“用户使用网络服务产生的被网络平台收集、存储、传输、处理和使用的各种电子数据”(17)陈荣昌:《网络平台数据治理的正当性、困境及路径》,《宁夏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从表面上看,作为数据供给方的用户理应拥有一定的数据所有权,但在实际使用中,用户为了享受平台服务的“便利”往往接受(或无视)网络服务协议的不利条款,放弃了己方的数据权益,结果就是平台基于数据管理的投入和网络服务协议,将“数据资源归网络平台所有”(18)张玉洁:《国家所有:数据资源权属的中国方案与制度展开》,《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各大平台在其营造的生态系统内已经建构了担任自身的监管者的秩序,(19)[美]亚历克斯·莫塞德、尼古拉斯L.约翰逊著,杨菲译:《平台垄断》,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145—146页。对逝者用户数据的技术安排,主要是按照网络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方式实现,即便一些平台开发了专属的逝后账户管理工具,也不过是对其服务协议进行的扩充。目前逝后数据的处置方案大致可以分为删除、纪念、继承三种,平台多采取其中一种方案或两种方案的混合。
(一)彻底删除账号及数据
一些平台将已故用户视为久不活跃的账号来处置,规定用户账号如果“长期没有登录或使用”就会被强制注销。例如,微信平台的服务协议显示:如果用户停止使用软件及服务,腾讯可以从服务器上永久地删除该用户数据,腾讯也没有义务返还任何数据。同为腾讯旗下的另一大平台QQ则在账号申请协议中明确指出“QQ账号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人,禁止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售卖”,拒绝授予第三方访问权限的可能。国外平台Google也表示一旦账号超过两年未被使用或登录,可能会删除该账号及其内容。(20)腾讯微信软件许可与服务协议:https:∥jiazhang.qq.com/zk/smallWeixin_agreement.html?lang=zh_CN,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QQ软件许可与服务协议:https:∥rule.tencent.com/rule/preview/46a15f24-e42c-4cb6-a308-2347139b1201,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Inactive Google Account Policy:https:∥support.google.com/accounts/answer/12418290?hl=en,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5月31日。
这些平台操作往往打着保护个人数据的旗号,实质是将用户数据私有,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由于数据存储需要调整、管理格式,更新软件和硬件以维护其价值,为了节省成本,删号也不足为奇。如此粗暴的管理方式纵容了“盗号”“贩卖数据”等灰色产业链的存在。有时逝者账号会“炸号”,有时被盗用后会突然“复活”,想要向平台申诉恢复账号也非常困难。
另一种情况是平台允许账户持有者删除账户以维护隐私。Facebook、B站等都已经为用户提供了删除账户的选择,由系统自动执行。相较前一种情况,平台优先考虑了用户需求,充分尊重“被遗忘”的意愿,用户也被赋予了更大的权限以维护其隐私。不过,这一方案欠缺灵活性,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或突发的意外需求,尤其对逝者近亲属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维护追思权益的纪念模式
一些平台意识到直接删除账号可能会加剧平台与用户之间的矛盾,已着手开始修正。Facebook进行了最为持久的探索,2009年开始将逝者账号设置为“悼念账号”,此后又增设了“委托联系人”来管理个人和集体的哀悼需求。(21)Facebook 选择委托代理人:https:∥www.facebook.com/help/991335594313139/选择委托联系人/?helpref=hc_fnav,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相比之下,国内平台直到2020年才做出回应,新浪微博、B站、豆瓣、快手、抖音相继调整了平台架构,将逝者账号从临时档案转变为永久保存的纪念账号。(22)新浪微博:关于保护“逝者账号”的公告,https:∥share.api.weibo.cn/share/227162453.html?weibo_id=4550080792898990,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哔哩哔哩社区小管家:公告,https:∥t.bilibili.com/471903763512561872?tab=2,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抖音:抖音上线逝者纪念功能 为账户设置保护状态,https:∥wap.xinmin.cn/content/32000242.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快手大事件:最后一条视频,https:∥v.kuaishou.com/9GYQYA,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
纪念账号的创设提供了一个保存全部数字遗迹的可能。由于账号并未关闭社交圈,用户通过发表评论,添加关注,使用标签符号、超链接、提及符号@等,可以使逝者成为“被激活的节点”,(23)Terrro Karppi,“Death Proof:On the Biopolitics and Neopolitics of Memorializing Dead Facebook Users”,Culture Machine,Vol.14,2013.pp.1-20.继续活跃在好友圈和社交网络中。为了更好地满足第三方对逝者的追思权益,B站、豆瓣和抖音还推出更为细致的情感化设计,包括点蜡烛、献花等“拟社会互动”,让生者与逝者保持“持续的联结”,以抚慰伤痛。
但是,满足生者对数字遗迹追悼需求的同时很可能违背了用户本人的隐私期待。大多数平台要求提供死亡证明或由近亲属确认用户身故。例如,快手指定“哀悼账号”由逝者直系亲属确认并成为账号委托人,将信息自决的权力交由亲属。然而,有些用户希望直接销毁账号及其数据,纪念账号的设置可能会违背这些用户自身对数字遗迹合理的隐私期待。
由于逝者纪念账号的公开性和可见性,悼念网络的构成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同到访者因悼念动机和印象不同而发生冲突,其行为最终可能会损害逝者声誉。例如,那些刷屏式的点赞留言,更多地为了自我表演,更为极端的是一些“网络喷子”,他们可能发表煽动性或诋毁性言论。平台虽有举报机制,但需要其他用户申请介入并等待平台审核,有一定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地对逝者的名誉利益造成伤害。
(三)账户数据的继承方案
纪念账号一般严格限制委托人(近亲属等)的登录权限,仅允许浏览其公开数据,不能修改也不能储存。那么,社交账户是否能够作为数字遗产完全遗留给继承人?问题在于不少社交账户运营商已经在服务协议中排除了继承权的可能。例如,腾讯明确要求第三方不可继承微信、QQ账户,新浪微博也在协议中指出“未经运营方同意,用户不得擅自买卖、转让、出租任何微博账号或微博昵称”。
然而,从继承人的期待利益来看,层出不穷的案例表明总有继承人期待数据的继承。(24)王旭:《数据法定继承规则的情境化构建》,《时代法学》2022年第1期。为了调和社交账户继承引发的矛盾,已有平台做出调整,将账户进入权限(账户的密码或登录信息)与账户中的数据信息区分开来,允许继承者转移账户中部分或全部数据,但不涉及账户控制权。谷歌提供了“非活跃账户管理器”(Inactive Account Manager)的服务,用户可以为账户设置“超时期限”,在死后或账户长期停用的情况下,与可信赖的人选择性地共享数据,包括Gmail邮箱、云端、相册、Youtube等。苹果公司也于2021年开启了遗产联系人的服务,用户生前指定信任的人在其去世后凭借访问密钥和死亡证明,访问并下载账户中的照片、视频、备忘录、文稿等。
账户数据的继承方案既满足了继承人对逝者数据的渴望,也并未与运营商的服务政策相左,还为用户数据处理自治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但是,这类数据的继承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矛盾。例如,多个继承人对账户数据的继承需求不同,这些差异势必要求在具体权利内容的继承上有所区别,而用户协议的菜单式选项过于粗放,难以满足更为细致的要求。其次,账户数据承载着被继承人生前及第三方主体的隐私利益,继承人可以私下拷贝、删除、更改数据,但是否可以在公开场合再利用和传播这些数据,目前并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来监管数据二次传播中造成的损害。
综上所述,目前主流平台处理“数字身后事”的三种方案都各有缺陷。对此,可以从用户和平台两个层面来解读。拥有网络账户的用户对数字遗迹的偏好各不相同,有人希望保留对其所有数字遗迹的访问权限;也有持完全相反观点的用户希望彻底删除数字遗迹,拒绝任何人的访问;还有用户希望严格控制,只允许访问或继承某些特定的数据信息。换言之,无论是电子邮件、社交网络还是云服务平台,用户可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评估不同类型数据的隐私敏感性,并选择是否、如何以及与谁共享个人数据。平台提供的极为有限的选择无法适应用户偏好的多样性。令问题变得更困难的是,即使个人对他们的数字遗迹有偏好,他们也很可能不知道有所作为或不作为带来的后果,并倾向于淡化负面情境,这也阻碍了用户提前对数字遗迹做出合适的安排。
面对逝后隐私权益的多重冲突,平台方显得应对不力。有的运营商依然默认平台有权删除死者数据,不少平台只是更新了网络服务协议,然而网络服务协议本就是由平台单向拟定的,在“缔约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的局面下,(25)李雅男:《民法典视野下社交网络账号的继承》,《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平台以维护逝者权益为由随意改动条款,与用户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无法感知可能造成的隐私伤害,也无法周全地顾及各方对死者数字遗迹的利益和需求。用户仅有被告知的权利,甚至从实际情况来看,就连告知权也未落到实处。一些平台上线了管理个人逝后数据的工具,却未能充分地履行告知义务。笔者在对国内外各大平台提供的这类线上工具进行调研时发现,很少有用户知道这些服务,不少用户干脆绕开了平台的控制,通过在应用程序上保持登录状态或将账号密码交付给可靠的亲友来实现“非正式”的继承。这一现状同样折射出平台与用户之间沟通不畅、权利失衡的问题。
三、走向“交互”:“数字遗迹”的治理路径转型
由于数字遗迹是一个新兴议题,平台在这方面的治理能力已明显滞后于法律规定与实践需求。在缺乏外部惩戒性监管措施的前提下,平台独占海量的逝者数据资源,对数据的舍弃(删除)或二次利用(纪念或继承)缺乏规范,常常只是平台单向推出“一揽子”计划,用户对逝后数据的保护意识普遍较为薄弱,要么一无所知,要么被动接受。这些因素的叠加进一步增强了对数字遗迹进行治理的正当性。
“交互治理”(interactive governance)是一种有别于单边主义的新治理范式。托芬等学者将其定义为“具有多元利益的多个社会和政治行动者相互作用,通过动员、交换和部署一系列思想、规则和资源来制定、促进和实现共同目标的复杂过程”(26)Jacob Torfing,B.Guy Peters,Jon Pierre,et al.,Interactive Governance:Advancing the Paradig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2-3.。该治理范式注重多方行动者之间的动态交流和反馈,致力于让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在公共治理中发挥协同作用,目前已经在环境污染、扶贫、住房、社区参与等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27)顾昕:《走向互动式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中“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变革》,《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针对平台治理的具体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平台内部的治理,而是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定位平台的社会功能,推动治理路径的重构。
(一)“数字遗迹”治理网络的构成
交互本是平台治理应有之义,因为平台就是“基于外部供应商和顾客之间的价值创造互动的商业模式,为这些互动赋予开放的参与式架构,并为它们设定治理规则”(28)[美]杰奥夫雷·G.帕克、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桑基特·保罗·邱达利著,志鹏译:《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但在实践中,对私利性的追逐驱使平台排斥竞争对手,独占数据资源。(29)王磊:《走出平台治理迷思:管制与反垄断的良性互动》,《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交互治理要求平台从狭隘自利转向更为开放的姿态,“动员和协调与某一特定问题或一系列问题有利害关系的行动者”(30)Jacob Torfing,B.Guy Peters,Jon Pierre,et al.,Interactive Governance:Advancing the Paradig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87.。
由于数字遗迹是一个宽泛的术语,涉及形形色色的“数码物”(digital objects),包括且不限于电子邮件、社交网络账户、照片、音乐文件和游戏皮肤。数码物构成的网络同时也是一种关系网。(31)许煜著,李婉楠译:《论数码物的存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30页。以每一类数码物为核心构成了不同的人与人、物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网络。例如,一位摄影师生前拍摄的专业照片可能牵涉版权、合同等要素,而业余爱好者发表的照片未必蕴含财产价值,却可能会唤醒亲友缅怀和修复创伤的渴望,同时还可能牵扯相关联的第三方主体的隐私。因此,理解数字遗迹的情境依赖性和社会复杂性是建设其治理网络的大前提。
依循这个逻辑,“数字遗迹”的治理网络将扩展为政府监管者、平台及关联企业(数据控制者、数据服务商)、用户(数据生产者、数据继承者、涉他隐私主体等)。治理网络还需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挑战。
治理系统的变化必然要求重新分配和协调治理权力。由于交互治理的核心在于打造更为扁平化的治理关系网络,随着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界限变得模糊,各治理主体在治理网络中的角色也需要被重新界定。以政府监管者为例,如果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平台所有者可能会滥用权力,以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目标。(32)Liang Chen,Tony Tong,Nianchen Han,“Governance and Design of Digital Platforms: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on a Meta-Organiza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Vol.1,2022,pp.147-184.但这并不是要奉行自下而上的控制,而是在不打击平台创新力与积极性的前提下,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平台责任的底线,为平台的创新治理行为提供法律支持和财政鼓励,推动这一复杂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个体用户过去总是作为被治理的对象而存在,极少参与到治理系统之中,但在交互治理模式下,广大用户跃升为治理主体,通过群策群力、广开民智,找到满足多元利益诉求的治理方案。最后,平台企业将从奉行单边主义的垄断者身份,转变为交互治理的召集者、催化者与协调者,积极维系动态网络的建设,组织多边主体顺畅沟通信息、制定平台规则。
(二)“数字遗迹”治理网络的运行机制
交互治理的具体实践包括横向治理、纵向治理和“对角线治理”(diagonal governance)或“蜿蜒治理”(zigzagging governance)三种方式。(33)Jacob Torfing,B.Guy Peters,Jon Pierre,et al.,Interactive Governance:Advancing the Paradig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31.平台治理既有赖于纵向等级的正式规则体系,即国际条约—国家立法—行业规范—用户协议/平台公约,(34)周学峰、李平著:《网络平台治理与法律责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41—43页。又有着横向的网络特征,各种非正式的治理手段对议程设置、制度扩散、政策执行的影响无处不在。(35)吕鹏、周旅军、范晓光:《平台治理场域与社会学参与》,《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3期。在实践中,纵向和横向治理各有其弊端,纵向治理往往过于依赖法治和行政手段,缺少对日常隐患的排查和反思,往往滞后于用户实践。横向治理则由于缺乏制度的约束,参与者容易产生倦怠、避责心理。过去,针对此类现象,不少平台也曾推出过五花八门的参与式机制,鼓励公众介入平台治理。例如滴滴的公众评议会、滴滴版吐槽大会、淘宝的大众评审团等,但在实际操作中平台缺乏公正性和公开性,而且用户数量庞大且分散,协商合议成本过高,参与动力不足,结果都收效甚微。(36)吴叶乾:《超大型平台自治规则的备案审查制度研究》,《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3年第1期。
“对角线治理”或“蜿蜒治理”融合了横向和纵向两种治理模式及过程,作为一种多维度的治理向度,强调“政府—平台—用户”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发生跨层级的动态互动。“对角线治理”或“蜿蜒治理”的实现需要“跨界者”(boundary spanner)的积极作用。(37)彭云、韩鑫、顾昕:《社会扶贫中多方协作的互动式治理——一个乡村创客项目的案例研究》,《河北学刊》2019年第3期。“跨界者”的概念最初来源于企业管理学,指的是能带入新领域或引入新思维、新模式、新技术、新流程,从而对原有行业产生巨大变革的个人或企业。(38)章长城、任浩:《企业跨界创新:概念、特征与关键成功因素》,《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年第21期。在公共治理体系中,学界、公益性组织常被视为跨界协调者。(39)彭云、韩鑫、顾昕:《社会扶贫中多方协作的互动式治理——一个乡村创客项目的案例研究》,《河北学刊》2019年第3期。在平台治理的语境下,跨界协调者不仅可以是个人、组织,还可以是人机协同智能。
在“数字遗迹”的治理决策与制度设计方面,算法作为“跨界协调者”可以发挥全过程、全环节、实时且闭环的作用。平台企业在算法评估方面本就具有无可匹敌的资源优势,可以全平台收集用户对“数字遗迹”的个人需求和决策偏好,对矛盾和争议点进行分类管理和聚类分析,形成治理需求收集和效果评估界面,输送用户反馈,促使政府、平台企业动态修正治理过程,优化治理模型,实现完整闭环的打造。在数据权利的执行程序和执行标准方面,算法可以发挥其动态敏捷的调节效应和技术加持。例如评估网络虚拟遗产的财产价值和使用期限,以网络游戏为例,由于每款游戏的代币和人民币都有不同的换算标准,若交由人工完成,不但耗时耗力还可能出差错,算法可以根据官方定价、市场价格等将现实货币与游戏内财产进行置换,确定虚拟遗产的价值;在继承人选择方面,算法可以识别“与该数据具备最密切情感联系之人”(40)王旭:《数据法定继承规则的情境化构建》,《时代法学》2022年第1期。。因为对一些用户而言,未必“越亲密,越放松隐私警惕”,有些信息屏蔽的行动,恰恰是针对亲密的家庭成员,不想被熟人知晓隐私信息,(41)王昕、邓国基:《互联网中的日常“隐私”实践——基于青年群体的质性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2期。由此可以优化继承法对法定继承人的顺位规则;在隐私识别和计算方面,算法可以对数据进行脱敏(隐藏个人身份信息)和匿名处理,在数据的流通过程中较好地保护数据主体的隐私,算法还可以识别个人数据中关涉的第三方隐私,尤其是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此类数据可以设置特别权限予以控制,如只将访问权和继承权开放给所关涉的第三方,这样就可以避免继承人在使用数据时有意无意间侵犯他人隐私。
通过融入算法技术,在政府、平台、用户三大主体之间生成了兼具人文精神和技术理性的跨层级协作行动机制。不过,为了避免算法滥用,在交互治理过程中应建立由政府、专业媒体人士和技术专家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对算法运用的全过程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以规避算法歧视等消极影响。
(三)“数字遗迹”治理中的数据权利体系构建
经过前期对治理网络的动态建设与维护,治理主体之间的多向互动沟通、交互治理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一定的制度保障,从而达成行动共识,展开稳定合作,实现各主体的权益优化。为了在网络平台构建良好秩序、实现社会正义,我们希望尊重逝者的不同意愿,也承认其家人和朋友有表达悲痛和纪念的需要,同时还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维护商业平台合法的商业利益。因此,数字遗迹治理问题需要构建一个体系性的数据权利结构,划定个人数据权利的保护范围,兼顾多元治理主体的利益。
数据权利体系的构造不可能是单一、静态的,需要在动态、多元的角度上根据不同主体的数据利益加以明确。首先,单一的数据权利往往无法满足不同用户的利益诉求,平台理应赋予用户“保存/删除、纪念/遗忘、继承/放弃继承”的基本数据权利,法律层面关于数字遗迹的保护方式也应从相对零散的论述整合成相对统一的理论体系。其次,数据权利的配置应该具有动态调整性,一方面,数据的访问权、更正权、可携带权作为新兴的数据权利正在生成中,另一方面,主要利益攸关方的核心诉求之间可能发生转移,需要在互动中协调,找到价值中间点。最后,个人数据权利的保护不能以牺牲国家的数据安全、平台的合理数据权益为代价。例如数据携带权保障了数据在不同平台之间的可迁移性,但对个人数据保护过度也可能伤害数据产业的发展。又比如平台将逝者账号设置为纪念账号加以保存,但数据存储应设置一定的期限,否则也会对平台造成过重的负担。
四、“遗产联系人机制”:Facebook对交互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反思
交互治理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交互治理是空泛的存在。相较于其他主流平台,Facebook对“数字遗迹”的治理模式做出了最为持久的探索,“遗产联系人”(legacy contact)是其最主要的一项发明,由创建于2011年的“同情研究团队”(Compassion Research Team)一手推动促成。通过对Facebook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进行追踪,可以发现其具有鲜明的交互治理特色。
首先,Facebook的治理网络趋向扁平化,“同情研究团队”主动邀约不同行业、不同层级的专家来解决棘手的平台治理问题,其团队流动性较强,包括且不限于平台决策者、算法工程师、界面设计师、法律专家、脑神经科学家等。2014年该团队的杰德·布鲁贝克(Jed Brubaker)博士和瓦妮莎·卡里森-伯奇(Vanessa Callison-Burch)开始推动数字遗迹的治理方案,在加入团队之前,杰德正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攻读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研究方向与社交网络上的数字遗迹有关,为此他付出了五年时间潜心调研用户和非用户的“痛点”,他的研究成果吸引了Facebook的重视,邀请他以专家的身份加入同情研究团队。(42)[英]伊莱恩·卡斯凯特著,张淼译:《网上遗产:被数字时代重新定义的死亡、记忆与爱》,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86—194页。杰德博士的跨学科背景,身为学者的中立身份,对该议题关涉的利益方能感同身受地倾听用户诉求并建立信任,使他成为建立跨层级交互的中心节点。与Facebook产品经理瓦妮莎、平台内外的法律专家等在协同合作中开启了“遗产联系人”服务。(43)Jed R.Brubaker,Vanessa Callison-Burch,“Legacy Contact Desiging and Implementing Stewardship at Facebook”,https:∥research.facebook.com/publications/legacy-contact-designing-and-implementing-stewardship-at-facebook/,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8月1日。
其次,作为治理工具的“遗产联系人”维护了用户对遗忘或纪念的不同数据诉求。首先,用户有权利决定死后注销账号,拒绝账号继承;其次,用户也可以指定一位Facebook好友作为“遗产联系人”,安排该“遗产联系人”管理和照看自己的页面,尽管无法以用户原先的身份登录账户,无法做出删除相册、发布新状态信息等行为。(44)Facebook,“Legacy Contact”,https:∥www.facebook.com/help/1568013990080948,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2月1日。“遗产联系人”的设置突破了传统继承法律的思维方式和治理理念。对于数字遗迹,近亲不再自动拥有决策权,用户可以选择那些没有血缘关系,但在网络平台上互动频繁的用户访问甚至控制数字遗迹,更好地适应了平台时代的新问题和新需求。正如杰德所期望的那样,当用户新增需求的速度远超过法律变革的速度时,与其等待法律明确后再行动,不如让超级平台真正起到带头作用,率先塑造未来的法律。
最后,通过“跨界者”(跨界组织)激发法律、平台、用户之间不同层级的互动,产生交叉效应,这正是交互治理所倡导的“对角线”或“蜿蜒”的治理形式,相较于纵向或横向的治理模式更具创造力。不过,Facebook的做法仍有不足之处。“遗产联系人”推出后收获了不少好评和质疑,但“同情研究团队”的工作重心已发生转移,Facebook也将遗产联系人视为完成状态,没有跟进后续开发,未能实现更优化的治理目标。
平台业态总是以“根茎式”的状态扩张,处于不断流动与变化中,由此产生的数字遗迹的规模和形态也不存在固定的模式。只有将平台治理真正转向交互治理,将治理系统视为一个演化和动态的过程,才有可能脱离封闭的状态而具有生成性、创造性,从而充分发挥技术自身的能动性,满足社会现实层面的情、理、法,增强平台治理的动态性和适应力。
以数字遗迹问题为例,未来总有一天用户中的逝者数量很有可能会超过生者数量,当到达那个临界点时,平台将再也无法逃避商业利益之外巨大的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与其仓促应对,不如提前规范和引导平台治理向可持续、可操作的方向发展。为了应对数字遗迹问题的主体多元性和复杂动态性,本文提出以交互治理的理念重构数字遗迹的治理网络和运行机制,搭建体系性的数据权利结构,并引入Facebook平台在交互治理模式方面的探索,以期为可能的治理模型提供参考。不过,未来要实现真正的交互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根据不同平台的账号数据特性、协议模式等,继续细化并完善治理网络的构成和运作程序。
-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伦理审视与优化
- 电子商务平台自律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