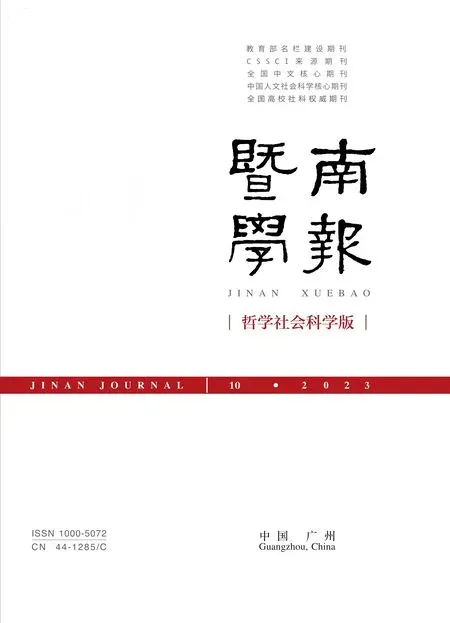电子商务平台自律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
武 腾
一、问题的提出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电子商务平台在促进信息技术进步和数字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下简称“平台经营者”)利用电子信息技术促使大量主体不断开展交易,无论是对购买者的不当行为,还是对销售者的不当行为,其都会采取技术手段进行检查,并采取相应管理措施,以维护平台内交易秩序。在司法实践中,平台经营者作为平台内交易秩序管理者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可。(1)比如,在“上海宇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诉浙江天猫技术有限公司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某公司的系统测试影响了平台内交易秩序,平台经营者判定该公司存在虚假交易行为,并给予其处罚,符合平台规则。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5491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件可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19)粤0192民初2472号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356号民事判决书。一方面,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交易秩序的有效管理成为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平台经营者在管理过程中可能采取不公平、不合理的行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乃至社会公共利益,有必要深入探讨其行为性质和法律效果。
平台经营者采取管理措施具有复杂的性质和效果。平台内管理活动可能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要求,也可能是基于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用户之间的合同;平台经营者实施自律管理既能够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又可能具有维护平台内公共利益的作用。所谓平台内公共利益,是指平台服务面向的不特定多数交易主体通过平台内互动所能获得的利益。平台服务种类越多,受众越广,其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往往越复杂、越重要。平台经营者自身的利益与平台内公共利益可能存在高度一致性,因为平台内的不诚信行为会导致平台内交易主体互动减少,不仅直接损害可能参与平台内互动的不特定多数主体的利益,也直接损害平台经营者自身的利益。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互联网典型案例“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诉许文强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2)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沪01民终13085号民事判决书。从违约责任的角度对该案进行的分析,参见刘力、何建:《电商平台打假的裁判规范及其法理逻辑——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诉许文强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法律适用》2019年第6期。中,人民法院认为许某某在淘宝网上出售假冒五粮液的行为不仅损害了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影响了消费者对淘宝网的信赖和社会公众对淘宝网的良好评价,故以平台经营者商誉受损为由支持其有关赔偿损失的主张。从该判决中可以发现,平台内经营者的违法行为不仅可能对知识产权权利人、消费者等不特定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还往往损害平台经营者的商誉;平台经营者以维护自身商誉为由追究售假者的法律责任,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不过,平台内交易主体类型众多,利益需求复杂,各类公共利益的内容和重要性并不相同,特别是平台内中小微企业的利益与平台内大企业的利益不尽一致,与平台内消费者的利益也不一致。不同利益之间,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3)例如,平台内“退款不退货”规则虽然有助于保护普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该规则一旦遭到滥用,平台内经营者便会承担明显超出违约责任范围的不利后果,故须谨慎适用此类规则。有关纠纷可参见叶丹:《拼多多频被“炸店”,“仅退款”惹的祸?》,《南方日报》,2023年4月7日,第B03版。在实践中,平台经营者可能以损害平台中部分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追求自身短期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平台经营者可能在追求快速扩张的时期疏于履行其注意义务、附随义务,放任部分侵权行为、违约行为的发生。又如,平台经营者可能在其市场地位稳固之后,对在一段时期内不活跃的平台内经营者采取暂停服务、终止服务的措施,从而显著增加平台内中小微企业劳动者的劳动强度。还如,如果平台内经营者漏发、迟发货物的行为并非基于严重过错,而平台经营者仍然采取严厉的处置措施,就会迫使平台内经营者负担更高的成本。在上述后两种情形中,平台经营者不断向平台内经营者施压,表面上看是为了尽可能满足消费者的所有需求,(4)See Jane K.Winn,“The Secession of the Successful:The Rise of Amazon as Private Global Consumer Protection Regulator”,Arizona Law Review,Vol.58,No.1,2016,p.193.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谋求自身相对于其他平台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故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害平台内不特定多数经营者的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围绕平台自律管理的依据、具体管理措施的合理性等产生纠纷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其管理依据、管理措施以及管理程序。
目前,针对平台经营者的自律管理行为已有不少研究。有学者从规制理论出发,探讨平台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之间的关系。(5)参见高秦伟:《分享经济的创新与政府规制的应对》,《法学家》2017年第4期。有学者以《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6)依据该条,平台经营者不得“对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等规定为着眼点,探讨如何对平台经营者进行竞争法规制。(7)相关探讨,可参见王晓晔:《论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现代法学》2020年第3期;袁波:《电子商务领域“二选一”行为竞争法规制的困境及出路》,《法学》2020年第8期。有学者对《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五条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进行解释论研究,尤其围绕如何妥当适用通知规则进行探讨。(8)参见杨立新:《电子商务交易领域的知识产权侵权责任规则》,《现代法学》2019年第2期;薛虹:《中国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深度剖析与国际比较》,《法学杂志》2020年第9期;杜颖:《〈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条款的适用与评价》,《电子知识产权》2021年第4期。还有学者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必要性、理论基础、实施方案等问题进行探讨。(9)相关研究可参见孙晋:《数字平台垄断与数字竞争规则的建构》,《法律科学》2021年第4期;张晨颖:《公共性视角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只不过,既有研究尚未对民商事审判中平台自律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进行充分的实证考察,(10)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已有一些实证研究。比如,孔祥俊、毕文轩:《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恶意投诉的规制困境及其化解——以2018—2020年已决案例为样本的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对于平台自律管理行为的性质、司法审查之法律依据的适用及其限度未能予以深入探讨,未充分揭示《民法典》中相关规定对矫正平台的不当管理行为、实现合理的平台自治所具有的意义。(11)平台治理存在强化公法规制而忽视私法机制的现象。参见金善明:《电商平台自治规制体系的反思与重构——基于〈电子商务法〉第35条规定的分析》,《法商研究》2021年第3期。有鉴于此,本文结合有关平台经营者管理活动纠纷的司法案例,先澄清平台经营者实施自律管理的动因和性质,再分别探讨如何依据现行法规定对平台自律管理依据、具体管理措施以及管理程序进行司法审查,以期弥补既有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为司法裁判提供助益。
二、平台自律管理的动因和定性
在探讨平台自律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之前,须先阐明的是,平台经营者是否都会对平台内交易秩序自发地实施管理活动;在现行法上,对于这些管理活动应如何定性。
(一)平台自律管理的动因
在市场经济中,能够长期存续的平台经营者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平台内交易秩序进行管理,尤其是对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人身权益、财产权益或者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管理。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平台经营者只有妥善处理一些外部性问题,保障平台内主体之间的互动有效开展,才能维持平台的存续和发展。其一,平台经营者需要解决行为外部性(behavioral externality)问题。(12)David S.Evans,Richard Schmalensee,Matchmakers:The New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6,pp.136-137.平台内经营者实施欺诈等行为时,会产生负的行为外部性。如果平台内经营者是不可信任的,那么消费者在平台内进行交易的风险便会升高;如果消费者难以获知平台内经营者是否会进行欺诈,那么信息的隐蔽性会产生“柠檬市场”效应,优质的用户会被逐出市场。(13)David S.Evans,Richard Schmalensee,Matchmakers:The New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6,p.138.负的行为外部性还会导致新的消费者不愿进入平台,消费者即使进入平台也不愿进行互动。(14)See David S.Evans,Richard Schmalensee,Matchmakers:The New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6,p.140.因此,平台经营者有很强的动力通过建立信用评价机制来解决信息隐蔽性问题,通过一系列措施来惩罚不诚信行为。(15)网络平台具有强大的自我监管动力和能力。参见王利明:《论互联网立法的重点问题》,《法律科学》2016年第5期。其二,平台经营者要应对多边平台中的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16)关于网络外部性的介绍,参见[法]让·梯若尔著,张维迎总译校:《产业组织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9—430页。问题。在多边平台内包含多组性质不同、需求不同的用户,平台必须确保各边都有足够多合适的用户,即其他边用户希望与之进行互动的用户,才能使平台存续下去。(17)See David S.Evans,Richard Schmalensee,Matchmakers:The New Economics of Multisided Platforms,Bost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16,pp.29-30.根据间接网络外部性理论,如果平台内消费者的数量减少到一定水平,那么平台对经营者的吸引力会随之下降,进而平台内经营者的数量减少;平台内经营者数量减少到一定水平,会进一步削弱平台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导致消费者数量进一步减少。因此,尽管平台内经营者的个别背信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往往十分有限,但背信行为的数量累积到一定程度,便可能引发严重的间接网络外部性问题,导致平台内各类交易主体迅速减少,平台经营者随即遭市场淘汰。
平台经营者解决上述外部性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在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中规定管理性规则(以下简称“平台规则”),并据此对实施侵权、违约等行为的平台内交易主体采取警告、降低信用等级、暂停服务、终止服务、扣除消费者权益保证金等措施。(18)即使平台经营者通过实施高度一体化方案转化为自营者,其同样需要解决雇员侵害客户合法权益的行为所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此时其解决方案便是制定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并据此对雇员采取惩戒措施。质言之,平台经营者实施管理活动主要是一种自发形成、自我约束的行为,该行为主要是“自律”的,而非“他律”的。即使法律未作规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平台经营者也会主动采取一系列维护平台内交易秩序的措施。
平台经营者实施管理措施也可能主要是为了配合行政机关实现其管理目标。比如,依据《电子商务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平台经营者应当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信息。又如,依据《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第九条第一款,平台经营者应当对平台内经营者提交的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信息至少每6个月进行一次核验更新;在发现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的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行政许可有效期已届满等情形时,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屏蔽、断开或删除链接、暂停或终止交易等措施。显然,平台经营者实施这类管理活动时不具有自发性,这类活动也并非管理性服务活动,而是属于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立法者之所以强化平台经营者的行政管理职责,是为了促使其“协助甚至替代监管部门完成整饬市场秩序的公共目标”(19)赵鹏:《私人审查的界限——论网络交易平台对用户内容的行政责任》,《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
上述两类管理措施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存在一定重叠之处。尽管多数平台经营者都会自发采取一些管理措施,立法者为了防范、应对平台内交易秩序混乱等现象,仍规定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平台内用户实施侵权行为时采取“必要措施”。这部分管理措施既与充分市场竞争条件下良好的商事实践相契合,又以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基础。本文所探讨的并非平台经营者纯粹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活动,而是平台经营者基于市场竞争会自发实施的管理行为(以下简称“平台自律管理行为”)。
(二)平台自律管理行为的定性
平台经营者实施自律管理时,其与平台内经营者围绕有关删除、屏蔽或断开链接、暂停或终止服务、扣除消费者权益保证金等活动产生纠纷的,人民法院应主要适用民商事法律规范予以处理。要研究人民法院如何对平台自律管理行为进行审查,须先探讨平台自律管理行为在民商法中的定性。
第一,从侵权责任的角度说,平台经营者负有预防、制止平台内侵权行为的义务,故其必须采取一些基本管理措施。《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平台经营者负有预防、制止侵权行为的义务;其违反该义务,造成民事主体损害的,原则上应承担帮助侵权责任。原《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将本来“只适用于利用特定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涉嫌侵害著作权的通知规则,创造性地上升为适用于利用网络侵害所有类型民事权益的情形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一项基本规则”(20)程啸:《侵权责任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497页。对于通知规则扩张适用的反思,参见周学峰:《“通知—移除”规则的应然定位与相关制度构造》,《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民法典》对其予以继承和完善,以两个条文规定网络侵权中的通知规则。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有关网络用户侵权的合格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否则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还规定了网络侵权中的知道规则,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对平台经营者违反交往安全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情形作出具体规定,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五条对平台经营者违反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侵权责任作出具体规定。概言之,平台经营者在平台内交易主体实施或者可能实施侵权行为时,其基于过错未采取必要措施,从而未能预防、制止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平台内经营者采取检查、警示、暂停服务、终止服务等基本管理措施,往往是平台经营者履行其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的具体方式。检查是为了及时发现侵权行为,警示主要是为了预防侵权行为的发生,暂停服务、终止服务主要是为了制止侵权行为、避免损失的扩大。总之,平台经营者采取基本管理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履行其在侵权责任法上的义务。(21)有学者指出,平台经营者尽管不负有一般意义上的监控义务,但负有一定的管理义务、合作义务。参见曹阳:《互联网平台提供商的民事侵权责任分析》,《东方法学》2017年第3期。
第二,从合同义务的角度说,作为新型中间商(22)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作为新型中间商的特殊性,参见武腾:《最小必要原则在平台处理个人信息实践中的适用》,《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的平台经营者负有广泛的附随义务,这包括实施相关管理活动的义务。比如,平台经营者应当对欺诈、违约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置。如果背离了消费者对平台的信赖,对平台内经营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放任不管,平台经营者便违反了诚信原则以及平台服务合同中的附随义务。(23)参见[日]松本恒雄、斋藤雅弘、町村泰贵主编,朴成姬译:《电子商务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60页。平台内各边交易主体与平台经营者之间基本上都存在合同关系,对平台内一边用户采取警示、暂停服务、终止服务等基本管理措施,正是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其他边用户履行附随义务的具体方式。
第三,从合同债权的角度说,平台经营者实施精准化管理措施通常是其行使合同债权的表现。一方面,平台经营者有很强的动力对平台内交易秩序进行更加高效的管理,因为只有实施高质量的自律管理,平台经营者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在“刘国光诉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24)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3613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刘国光诉京东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可了平台规则中“先行赔付”条款的效力。该条款向平台经营者赋予以下权利:在平台内经营者不履行其与消费者之间的买卖合同时,平台经营者可以扣除保证金,并向消费者赔偿损失。该措施具有预防违约行为发生的作用,实施该措施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定,而是基于意定的平台规则。实践中,平台经营者为增强或维护其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往往会通过平台规则强化其管理措施。另一方面,法定的注意义务、附随义务内容抽象,如果不制定具体规则,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交易主体之间的管理关系难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因此,在实践中平台经营者往往会通过平台规则细化其自律管理措施,对各种各样的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进行区分,并规定各项具体管理措施的实施条件。
综上,一方面,基于网络侵权责任、合同附随义务相关规定,平台经营者负有基本管理义务;另一方面,平台经营者往往会通过平台规则细化、强化其管理措施,此时的精准化管理行为主要是平台经营者行使合同债权的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平台经营者违反了基本管理义务或者滥用合同债权,人民法院应主要依据《电子商务法》中的特别规定和《民法典》中的一般规定,判断平台经营者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
三、平台自律管理依据的司法审查
(一)平台自律管理依据效力的司法审查
平台规则是平台经营者自律管理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采取管理措施的依据(参见《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六条)。学界的主流意见是,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格式条款相关规定审查平台规则的效力。(25)代表性论述参见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条文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06页;赵旭东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释义与原理》,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84—187页。相关具体研究,可参见宁红丽:《平台格式条款的强制披露规制完善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杨显滨:《网络平台个人信息处理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4期;胡安琪、李明发:《网络平台用户协议中格式条款司法规制之实证研究》,《北方法学》2019年第1期。有观点认为平台规则属于交易习惯,同时具有习惯法的性质。参见杨立新:《网络交易规则研究》,《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然而,平台规则是平台经营者事先拟定的,且被订入合同之中,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平台规则采取的一贯做法实际上是当事人在合同约束下实施的行为。因此,平台规则虽然可能源自交易习惯,只要被订入合同中,便不应被定性为交易习惯或者习惯法。有学者认为,格式条款相关规定具有相当强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因其体现出对交易关系中弱势一方的保护。(26)参见秦前红、周航:《〈民法典〉实施中的宪法问题》,《法学》2020年第11期。该观点值得赞同。平台经营者实施自律管理行为的,不仅牵涉具体平台服务合同中当事人的利益,还牵涉社会公共利益。在认定有关管理措施的格式条款的效力时,需要考虑该格式条款是否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
在认定平台规则效力或内容的司法裁判中,不乏法院依据格式条款相关规定作出公允的判决。比如,在“深圳海豚之梦贸易有限公司诉杭州贝仓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27)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8127号民事判决书。中,人民法院认为,平台规则中已经约定了扣除保证金等违约责任,故十倍商誉赔偿金条款属于不合理地加重对方责任的格式条款,应认定为无效。又如,在“之道出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案”(28)参见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926号民事判决书。中,人民法院认为平台规则中所谓“平台所赠积分不得用于私下买卖、馈赠、营利及恶意消费等情形”的条款内容不明确,依据格式条款解释相关规定作出不利于平台经营者的解释。尽管平台规则是平台经营者为海量相对人拟定的格式条款,但是其影响广泛,且颇具专业性,各级人民法院也应当依法适用格式条款相关规定作出判决,维护电子商务领域的公平竞争秩序以及格式条款接受方的合法权益。
为使格式条款规定适用的实际效果更显著,有必要讨论哪些典型情形是《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在域外法上,存在对不同的格式条款予以类型化的做法。有的格式条款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给相对人带来特别沉重的负担,法院不应再予以利益衡量,而应一概认定其为无效;有的格式条款包含不确定概念,需要基于广泛的利益衡量来判断其是否无效,所以法院有评价可能性。(29)参见[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著,沈小军、张金海译:《德国债法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页。《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第二项(30)该项规定的无效情形是,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包含了“不合理”这一不确定概念,赋予了司法机关较大的裁量权,而该条第三项(31)该项规定的无效情形是,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未包含这一不确定概念,显然限制了司法裁量空间。就平台规则效力的司法审查而言,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和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平台经营者负有转送通知、声明的义务,平台内经营者享有提交初步证据、陈述事实的权利,平台规则免除平台经营者转送通知、声明的义务,或者排除平台内经营者提交证据、陈述事实的权利的,人民法院不必进行利益衡量,而应当依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和《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认定其为无效格式条款。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提交初步证据的时间作出较短规定(如48小时内),或者对初步证据的形式、内容施加较多限制的,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利益衡量,判断其是否属于“不合理地”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
在适用格式条款相关规定时,须注重保护平台内经营者有关数据和算法的权利。为了增强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服务关系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欧盟2019年通过了《关于促进向商户提供的网上中介服务的公平性和透明性的条例》(32)“Regulation (EU)2019/115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0 June 2019 on Promoting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for Business Users of Online Intermediation Services”,Se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L 186/57.(以下简称欧盟《网上中介服务公平透明条例》),其中便包含平台内经营者关于数据和算法的重要权利。其一,平台经营者在提供媒介服务过程中会处理平台内经营者的数据,这些数据具有不同程度的商业价值。平台内经营者对平台经营者处理平台内经营者数据的活动享有一定知情权,在合同终止后有权获取自身所提供或产生的数据。(33)参见欧盟《网上中介服务公平透明条例》第八条和第九条。其二,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负有算法解释义务。尽管不必披露算法的细节,但是平台经营者仍应告知平台内经营者影响后者排名的主要参数(main parameters),尤其是后者所支付的报酬对排名产生的影响。(34)参见欧盟《网上中介服务公平透明条例》第五条。在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采用“差别待遇”(differentiated treatment)时,平台经营者应当披露相关商业因素、法律因素,不论该平台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在平台规则中,排除平台内经营者获取数据的权利或者排除平台经营者的算法解释义务的,显然会损害不特定多数平台内经营者的商业利益,构成排除平台内经营者的主要权利,应当认定为无效的格式条款。
在适用格式条款相关规定时,须尊重平台经营者的自治空间。有的人民法院指出:“当平台内经营者在平台上注册后,双方形成合同关系,这意味着平台内经营者接受平台的自治规则及依据该自治规则可能实施的处罚。在民法上,基于团体协议,团体组织享有一种自治性质的惩罚机制。据此,对于违反自治规则的用户或成员,平台可以采取信用评级降级、屏蔽、除名等惩罚措施。”(35)参见“上海美询实业有限公司诉苏州美伊娜多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美询公司诉淘宝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4923号民事判决书。类似判决,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终10925号民事判决书。应予澄清的是,平台规则并不属于组织法上的法律行为。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经营者是基于合同而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平台经营者不是基于平台内经营者的意志而产生,平台规则也不包含组织的权力机关、执行机关等内容,故平台本身不是法律上的组织,平台规则与公司章程、业主管理规约在法律上也没有实质类似性。不过,平台经营者实施的所谓惩罚行为主要是自律管理行为,平台规则与处于市场竞争环境中的证券交易所制定的自律管理规则颇为类似。(36)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证券交易所通过自律管理提供公平、透明且管理有效的市场,是其取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参见徐明、卢文道:《从市场竞争到法制基础: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司法机关在依据格式条款相关规定审查平台规则的合理性时,应当充分尊重平台经营者的自治空间。
依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一条,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与知识产权权利人加强合作,依法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是平台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拘束平台内经营者,而且对平台外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具有重要影响。(37)参见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条文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页。表面上看,知识产权权利人只要不是平台内经营者,就不会受到平台规则的拘束。实际上,只有平台经营者与知识产权权利人保持良好合作关系,才能有效处理平台内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面对不特定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平台经营者往往会通过格式化的合作协议,促使知识产权权利人接受平台规则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比如,在国内某大型平台经营者发布的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使用协议中,载有如下条款:“平台用户了解并同意,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会根据权利人的投诉材料和卖家的申诉材料综合进行判断,并根据该判断结果决定是否恢复或删除商品。”(38)参见《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使用协议》(更新于2019年8月8日),阿里巴巴网站,https:∥ipp.alibabagroup.com/agreement.htm?spm=a2145.7275745.0.0.W9p1CG,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5月25日。知识产权权利人只要与平台经营者签订该协议,就会受到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拘束。平台经营者应当基于公平原则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与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结合知识产权的特殊性制定相关平台规则,针对各类必要措施分别规定实施条件。人民法院在根据格式条款相关规定审查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效力时,应当着重审查平台规则是否不合理地加重平台内经营者或者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举证负担或者责任,或者不合理地限制其有关提交证据的主要权利。如果这些规则系基于公平原则制定,人民法院便应当认定其有效,从而发挥平台自律管理的灵活性优势。
(二)平台自律管理依据修改程序的司法审查
《民法典》中有关格式条款的规定既有其重要作用,又存在适用上的局限性。(39)参见薛军:《〈电子商务法〉平台责任的内涵及其适用模式》,《法律科学》2023年第1期。在审查平台自律管理依据的修改程序时,格式条款相关规定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因为这些规定对于修改程序基本未予涉及。
依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四条,平台经营者修改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的,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采取合理措施确保有关各方能够及时充分表达意见;修改内容应当至少在实施前7日予以公示;平台内经营者不接受修改内容的,可退出服务关系。该规定确立了平台规则修改时的“相对人参与原则”,旨在保护平台服务合同相对人的利益,特别是保护依赖平台生存的中小微企业的利益。伴随着中小微企业对大型平台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大型平台经营者更容易采取不公平的单方行为损害中小微企业的合法权益;这些单方行为常常严重偏离良好的商业标准,或者有违诚信原则、公平原则。(40)Se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L 186/57.在传统民商法上,存在对一方当事人的生存利益予以特别保护的中间商合同制度,即代理商合同。(41)在我国,由于代理商合同未有名化,委托合同相关规定不得不肩负规范代理商合同的任务。参见武腾:《委托合同任意解除与违约责任》,《现代法学》2020年第2期。在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经营者之间,立法者所构造的是与代理商合同中的法政策类似、保护对象不同的服务合同制度。所谓法政策类似,是指立法始终侧重保护那些依靠长期性合同谋生的当事人,以防其生存利益遭到相对人的损害;所谓保护对象不同,是指保护的对象不是中间商(媒介服务提供者),而是委托人(媒介服务接受者)。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平台经营者运用大数据技术处理信息的能力使其具有更大话语权,在经济上和法律上重构了中间商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
在实践中,平台经营者的类型多样,平台内经营者的生存利益保护需求也有所不同。应当综合考察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的经济地位差异、前者对后者经营活动的控制力、后者对前者的依附程度等因素,将平台经营者区分为有用人单位特征(尚不构成用人单位)的平台和不具有上述特征的平台。对于后者,应充分尊重此类平台经营者制定平台规则的自主性,在认定《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四条中有关平台规则修改的程序要求时应较为宽松;对于前者,应当对平台内经营者的生存利益予以更充分的保护。具体地说,对于有用人单位特征的平台,尽管平台内经营者在营业时间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工作强度乃至营业内容却能进行较强的干预或控制。此时,平台经营者修改平台规则与用人单位修改劳动规章有类似性,应充分保障平台内中小微企业有机会参与平台规则的修改。具体地说,平台经营者只有采取以下措施才可谓符合《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采取合理措施确保有关各方能够及时充分表达意见”的要求:在合理期限之前将拟修改的内容予以公示;为平台内经营者表达意见提供便利的渠道;公示所收到意见的总体情况;在反对性意见占大多数时采取合理的调整方案,或在采用原方案的情况下告知其所考虑的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具体因素。
平台经营者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相对人参与原则的,行政机关应依据《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给予行政处罚。尚不明确的是,在违反该原则的情况下,被修改的平台规则内容是否对平台内交易主体产生拘束力。对此,《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42)依据该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存在适用上的局限性,因为该款规定的是格式条款提供方的提示说明义务,而《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四条并不是有关提示说明义务的具体规定或者特别规定,而是旨在“削弱”平台规则的不可磋商性,即平台经营者在修改平台规则时,有义务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在实践中,平台经营者可能在修改平台规则前未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却在修改后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故无法适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相对人参与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对平台产生较强依赖性的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利益。平台规则的修改违反该原则的,平台内中小微企业便没有机会促使平台规则朝着有利于自身生存利益的方向修改,或者避免平台规则朝着不利于自身生存利益的方向修改。该程序瑕疵难以在事后予以弥补。为实现该原则的规范目的,在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中小微企业围绕平台规则修改后的效力发生争议时,对于违反相对人参与原则的平台规则修改,应当作出“不利内容不生效”的判决,即从理性人的角度观察,如果修改后的内容对平台内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利益产生显著不利影响,那么后者可以主张该修改对自身不产生拘束力。
四、平台自律管理措施的司法审查
围绕应否审查、如何审查平台自律管理措施,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在“蔡振文诉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43)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6民终3872号民事判决书。中,平台经营者针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不当行为采取管理措施,一审法院认为平台经营者未对平台内经营者进行合理提示,应终止管理措施,二审法院则未对管理措施是否过于严厉予以审查。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83号“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诉永康市金仕德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44)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知终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中,人民法院就平台经营者采取管理措施时所应考量的因素和所应遵循的原则予以阐述,指出平台经营者在接受投诉后“对被诉商品采取必要措施应当秉承审慎、合理原则,以免损害被投诉人的合法权益。”指导案例83号中的基本立场值得赞同。人民法院不应回避对平台经营者具体管理措施的审查,而应依据《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中的原则、规则进行审查。
(一)平台自律管理措施实体正当性的司法审查
平台经营者采取自律管理措施的,须具备实体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所谓具备实体正当性,是指管理措施足以达到预防、制止不当行为的目的,且手段与目的之间并非显著不合比例。在对实体正当性进行审查时,人民法院应主要依据《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中关于违约金、网络侵权责任的规定以及禁止权利滥用规定。
第一,在平台经营者基于合同债权进行精准化管理时,人民法院应主要依据贯彻公平原则的具体规定对管理措施内容进行审查,如依据违约金相关规定审查消费者权益保证金扣除措施与保证金担保目的之间是否符合比例。在“成都希言公司诉上海寻梦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45)参见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7)沪0105民初3792号民事判决书。中,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睫毛膏为假货,平台经营者依据平台规则中的“假一罚十”条款将平台内经营者的账户冻结,划扣部分保证金并将其全部用于赔偿消费者。人民法院依据格式条款效力规定认定“假一罚十”条款有效,并在考虑平台损失以及平台自治空间的基础上决定不予调整。该案中的所谓“罚款”属于惩罚性违约金的支付,因为该保证金的数额并非当事人预定的损害赔偿数额,该保证金以督促平台内经营者严格按照平台规则履行义务为主要目的。该违约金所担保的内容是,平台内经营者全面履行其与消费者之间的合同,并遵守平台规则,不实施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以及平台内公共利益的行为。(46)类似情形在证券交易所的管理活动中也存在。依据《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59条,会员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证券交易所可以按照章程、业务规则的规定采取收取惩罚性违约金等措施。对于该违约金,应按照担保目的与担保手段之间是否显著不合比例来确定是否应予调整。(47)参见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通则》,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15页。
须指出的是,人民法院不能仅仅因为“罚款”被全部转交给消费者,便当然认为“假一罚十”之类的管理措施合理。在这类案件中,人民法院应从以下四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判断管理措施是否具有实体正当性:(1)所谓的“假”是仅指故意制造、销售假冒商品,还是也包括因过失导致标签内容与商品不完全相符(但不影响商品质量)等情形。(2)“假一罚十”条款中的惩罚性违约金旨在担保何种利益免受损害,是仅包括受损害的消费者个人利益,还是包括平台中不同类型的公共利益。(3)为保障上述利益不受损害,违约金的数额与担保目的之间是否符合比例。(4)提供该条款的平台经营者是否具有用人单位的特征。在平台经营者具有用人单位的特征时,其拟定“假一罚十”条款就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采用“偷一罚十”的规章制度,可能过分加重后者的责任。在“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等服务合同纠纷案”(48)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2民终4491号民事判决书。中,平台规则中包含“售假处罚百万”的违约金条款,人民法院认为其系平台经营者行使自律管理权的表现,其目的不是单纯弥补守约方的损失,而是为了“平台自律管理、保护消费者权益、加大商家违法成本、维护良好经营秩序的需要”。人民法院在综合考虑售假情节、平台治理成本、平台商誉损失等因素之后,对平台经营者主张的违约金数额予以酌减。
第二,在平台经营者为履行法定的注意义务而采取基本管理措施时,人民法院应主要依据网络侵权责任相关规定以及禁止权利滥用规定进行审查。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报案例“衣念(上海)时装贸易有限公司诉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杜国发侵害商标权纠纷案”(49)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中,投诉人先后7次向淘宝公司发送侵权通知。淘宝公司认为,自己先后7次删除被投诉人发布的商品信息,已属采取必要措施。不过,人民法院指出:“删除信息后,如果网络用户仍然利用其提供的网络服务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则应当进一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制止继续侵权。哪些措施属于必要的措施,应当根据网络服务的类型、技术可行性、成本、侵权情节等因素确定。”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平台规则,淘宝公司还应对被投诉人采取限制发布商品信息、扣分、冻结账户等措施,但其未采取相应措施,故应承担帮助侵权责任。可见,平台经营者的管理措施必须是“充分”的,即不仅足以达到制止现行侵权行为的目的,还要足以预防未来侵权行为的发生。
平台经营者的管理措施也不应是“过分”的。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平台经营者按照有效的平台规则所采取的管理措施,人民法院通常不会认定其在实体内容上超出必要限度。在前述美询公司诉淘宝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平台经营者不仅删除了被投诉的商品信息,还额外删除了平台内经营者的其他商品信息,最终仅为平台内经营者保留5个商品信息。人民法院认为,上述措施是平台经营者依据其发布的《假货限制商品发布数量》公告,在两次投诉售假扣分满24分后采取的措施,不构成不必要的措施。不过,对这类情形尚可进一步分析。尽管平台经营者发布的《假货限制商品发布数量》公告可能属于有效的格式合同条款,平台经营者在依据相关规则行使自律管理权时,仍可能构成滥用民事权利。原因是,投诉既可能是正确的投诉,也可能是错误投诉甚至恶意投诉;售假行为既可能是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是情节轻微的,假设平台经营者对各类投诉或售假情形不加区分,一概采取严厉的限制商品发布措施,便可能出现明显不公平的结果,甚至可能构成滥用民事权利。
有学者指出,只有参照比例原则等公法原则,对平台经营者行使私权力的行为进行审查,才能实现实体正义。(50)参见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该观点具有一定启发性。不过,人民法院在对平台经营者的自律管理行为进行审查时,应当以《民法典》中的禁止权利滥用规定为法律依据,根据禁止权利滥用规定的要件和效果作出裁判。《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认定构成滥用民事权利时,应考虑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依据该条第二款,以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行使民事权利的,构成滥用民事权利。依据该条第三款,构成滥用民事权利的,该滥用行为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滥用民事权利造成损害的,依照有关侵权责任等方面的规定处理。可见,滥用民事权利的构成和效果已有明确的规范依据。(51)相关研究参见彭诚信:《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律适用》,《中国法学》2018年第3期。具体到电子商务领域,平台经营者针对不活跃或者有轻微不当行为的平台内经营者采取暂停服务、终止服务等措施的,必须有助于实现正当目的,并且手段与目的之间须符合比例,不会致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显著失衡。人民法院在审查管理措施是否构成滥用民事权利时应考虑以下因素:平台内经营者的不活跃现象或者轻微不当行为是否、如何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或者其他不特定平台内经营者的利益?平台经营者采取暂停服务、终止服务等措施主要是为了维护平台内公共利益,还是主要为了确保自身相对于其他平台经营者的优势地位?如果是后者,那么平台经营者是否符合诚信地照顾到平台内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利益?其能否通过其他措施(如降低排名)便能实现目的?如果平台经营者的行为不具有正当目的,或者所采取的措施与所维护的目的之间显著不合比例,造成不同利益之间显著失衡,便会构成滥用民事权利,人民法院应判决其停止相关措施、继续履行合同、赔偿损失。
在对平台经营者基于合同债权实施的精准化管理措施进行审查时,人民法院之所以应依据禁止权利滥用规定进行审查,而非适用比例原则,根本原因在于后者中的最小侵害原则不宜用于调整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商事关系。比例原则不仅包含狭义比例原则(手段与目的之间须符合一定比例),还包含妥当性原则和最小侵害原则,其主要功能在于防范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的滥用。(52)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2015年,第112—113页。在法治国家,行政权力在侵害人民权利时不仅必须有法律依据(法律保留原则之要求),还必须选择在侵害人民权利的最小范围内行使,且在行为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应符合一定的比例。最小侵害原则是比例原则中不可或缺的子原则,对于约束行政权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53)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2015年,第111页。然而,若将该原则用于指引电子商务活动,会过分限制商事主体的行动自由。质言之,将包含了最小侵害原则的比例原则应用于审查平台自律管理措施,必然会与尊重平台经营者的自治空间的理念相矛盾,因为按照最小侵害原则的要求,平台经营者只能采取对相对人损害最小的措施,无权通过意定的平台规则强化惩罚措施。然而,平台规则产生法律拘束力的根据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以及承认该合意具有拘束力的法律规定(参见《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九条),只要意思自治原则还在电子商务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平台经营者就有权通过平台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调整惩罚力度。平台经营者在依据有效的平台规则进行精准化管理时,即使给平台内经营者造成了所谓“超出最小范围”的损害,通常也是允许的;只要超出的部分不显著,人民法院便不应进行干预。更重要的是,平台经营者与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具有显著差异,多数平台经营者长期处于十分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平台内经营者可能具有“多栖性”(同时接受多个有竞争关系的平台经营者的服务),往往会比较不同平台经营者的管理性服务水平,并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抛弃那些滥用管理措施的平台。只有依据禁止权利滥用规定审查平台经营者的精准化管理措施,允许平台自律管理具有较大的弹性,才能为平台经济保留足够自由的发展空间。
(二)平台自律管理措施程序正当性的司法审查
平台自律管理措施的实施还须具备程序正当性。平台经营者有义务设置适当程序给予平台内各边用户陈述事实、提交证据的合理机会,并采用统一的证据审查标准和证明标准。这些程序性义务以网络侵权责任相关规定以及诚信原则为根据。
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和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规定,权利人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为由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对所提交的证据进行适当审查,并转送合格的通知、声明;这些义务属于其程序性义务。(54)关于转送义务的定性,参见张新宝:《中国民法典释评·侵权责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13页。其一,权利人在通知中声称网络用户的行为构成侵权并提交证据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该证据进行适当审查,从而判断其是否构成“初步证据”。其二,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转送义务,一方面,其应当向涉嫌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转送包含上述证据的通知,另一方面,在被投诉人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合格声明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将被投诉人的声明转送给主张权利的民事主体。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平台经营者采取必要措施时不能仅仅听取主张权利一方民事主体的意见,而必须采取适当程序调查相关事实。如果平台经营者在未给予被投诉人相应程序保障的情况下,便采取删除、屏蔽、暂停服务、终止服务等措施,只要存在投诉人错误通知或者恶意通知的情形,平台经营者便可能对被投诉人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55)关于网约车平台经营者未依规管理,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判决,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17870号民事判决书。
《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五条对平台经营者调查、处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作出专门规定。在《民法典》通过之后,为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进一步实现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更为具体的裁判规则。第一,以合理期限代替15日期限,并采用了中止计算的规则,从而缓解了15日固定期限的僵化问题。(56)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第三条,在依法转送的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到达知识产权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网络服务提供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因办理公证、认证手续等权利人无法控制的特殊情况导致的延迟,不计入上述期限,但该期限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第二,为专利权侵权场合的通知、声明的具体内容作出更明确的规定,并规定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暂缓实施必要措施。(57)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指导意见》)第五条第二款和第七条第二款,通知或者声明涉及专利权的,平台经营者可以要求知识产权权利人或者平台内经营者提交技术特征或者设计特征对比的说明等材料。按照该意见第十条第二款,平台内经营者有证据证明通知所涉专利权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无效的,平台经营者可以据此暂缓采取必要措施。第三,为遭到投诉的平台内经营者规定所谓反向行为保全的规则,(58)按照《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指导意见》第九条第二款,因情况紧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不立即恢复商品链接、通知人不立即撤回通知或者停止发送通知等行为将会使其合法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平台内经营者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为平台内经营者立即恢复正常经营提供渠道。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较细致的规定,面对复杂多样的网络侵权行为,平台经营者仍有必要制定、实施更为精细的程序性规则。平台经营者系为平台内交易主体提供精准媒介服务,(59)参见武腾:《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侵权责任》,《法商研究》2022年第2期。与仅提供自动接入、缓存等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本质区别。在判断平台经营者的间接侵权责任或帮助侵权责任时,应当考虑到其承担较高程度的注意义务。(60)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640页。从平台自律管理的角度来说,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应当承担实质审查职责,针对不同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分别判断初步证据是否满足要求,并在相关处置措施可能给平台内经营者的营业造成重大影响时,采取向知识产权权利人收取保证金或者事前接收平台内经营者的声明等程序措施。举例来说,商标权人以其商标权受侵犯为由要求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商品采取删除、屏蔽等措施的,相当于诉前保全行为。(61)参见周学峰:《“通知—移除”规则的应然定位与相关制度构造》,《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6期。尽管《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未规定交纳保证金是采取必要措施的前提条件,但是对初步证据内容单薄、可靠性难以判断的通知,仍有必要考虑引入保证金制度。进一步说,只有对不同的通知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才符合相关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规范目的。《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对于恶意通知规定了加倍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几个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第五条对于善意发出错误通知的行为人予以免责。可见,不同类型的错误通知产生明显不同的法律后果。(62)简言之,承担加倍赔偿责任的恶意投诉人系明知错误仍发出通知,可以免责的善意投诉人系不知错误且无过失,承担一般侵权责任的善意投诉人系不知错误且有过失。按照《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指导意见》第六条第一款和第八条,“恶意”主要是指“明知”错误而为,至于目的为何,在所不问。平台经营者不能为了规避自身的责任而对平台内经营者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也不能为了维持平台内的交易量而向知识产权权利人施加过重的举证负担,其应当同时防范和应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公平对待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平台内经营者,根据通知或声明的可靠性,决定是否要求补充提交证据、交纳保证金。
对于平台经营者采取的相关程序性措施,人民法院应当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审查。比如,鉴于实践中错误投诉、恶意投诉的情形逐渐增多且较为复杂,补充提交证据的期限、采纳证据的标准等问题有待澄清。在前述美询公司诉淘宝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电子商务法》第四十三条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的规范目的,平台经营者应“通过程序设置甄别出可能的错误通知并及时予以终止,以平等保护权利人和被投诉人的利益”。该裁判说理颇具启发性。平台经营者必须为平台内经营者陈述事实、提交证据以及补充证据指定合理期限,并提供合理的提交证据途径。其对于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适用统一的采纳标准和证明标准。(63)在美询公司诉淘宝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平台经营者未妥当处理错误投诉,人民法院认为其应承担侵权责任,平台经营者的过错包括:(1)一方面要求平台内经营者进一步提供证据,另一方面明显未给予其合理的准备时间;(2)在双方都提交证据的情况下,对不侵权声明中的证据和侵权通知中的证据,采用了不一致的审查标准。又如,平台经营者通过平台规则强化其管理措施时,有必要设置相关异议程序。在前述刘国光诉京东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人民法院认为平台经营者所作出的“先行赔付”决定仅是基于“中间、临时、形式的判断,而非对商家赔付义务的最终责任认定”,平台经营者应当基于符合其自身认知水平的审查标准审慎作出判断,同时通过设置异议程序赋予平台内经营者一定的申诉权利,尽量防止利用规则漏洞不诚信刷单恶意索赔情况的发生。在平台经营者实施这类管理措施时,如果不设置异议程序,在错误赔付的场合便可能产生严重不利于平台内经营者的结果,因为一旦赔付完成,平台内经营者只有付出很高的代价才能经由诉讼实现返还财产,一些中小微企业可能难以负担跨地区诉讼的成本。总之,人民法院应依据诚信原则对平台经营者自律管理的程序正当性进行审查,在平台经营者强化其管理措施时,人民法院应根据具体案情要求其设置相应的管理程序,以保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平。
还需指出的是,平台内经营者的不当行为可能不构成侵权行为,而仅仅违反其与平台内消费者之间的合同(如迟延发货)。无论是《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五条,还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至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条,都仅仅对平台经营者调查、处理平台内经营者的侵权行为作出规定,未涉及有关平台内经营者违约行为的调查、处理。然而,无论是对侵权行为的调查、处理,还是对违约行为的调查、处理,程序方面的要求并无实质不同,因为平台经营者始终应在程序上公平地维护平台内各边用户的利益。因此,上述程序性义务亦适用于平台经营者预防、制止平台内经营者实施违约行为的场合。
五、结 论
为应对外部性问题,平台经营者通常会对平台内交易秩序主动实施管理。不过,其在采取自律管理措施时可能为促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平台内各类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故有必要对平台经营者的自律管理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在现行法上,平台经营者的基本管理义务是其基于侵权责任法、合同法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平台经营者还往往通过平台规则细化、强化其管理措施,此时的精准化管理主要是平台经营者行使合同债权的表现。
对平台自律管理的依据——平台规则的效力进行审查时,人民法院应以《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等法律中的格式条款相关规定为法律依据。平台经营者采取扣除消费者权益保证金措施的,应依据惩罚性违约金相关规则审查。针对平台经营者依据有效平台规则采取的管理措施是否属于“必要措施”,不应依据比例原则进行审查,而应依据网络侵权责任规定以及禁止权利滥用规定作出判决,尊重平台经营者的自治空间。依据上述规定进行司法审查时,须注重考察平台内公共利益的维护。上述规定的主要局限在于,未为审查平台自律管理的程序提供足够明确的指引。对平台规则的修改程序进行审查时,应遵循相对人参与原则;违反该原则产生“不利内容不生效”的后果。在为保护知识产权而采取程序性措施时,平台经营者应当公平对待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平台内经营者。平台经营者负有的程序性义务包括:为平台内经营者陈述事实、提交证据指定合理期限,对平台内各边用户采用统一的证据采纳标准和证明标准,在采取难以消除相关后果的管理措施之前设置异议程序等。
-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重大传染病患者涉罪案件判罚的伦理审视与优化
- “数字遗迹”治理困境与转型路径
——基于对逝者数据交互治理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