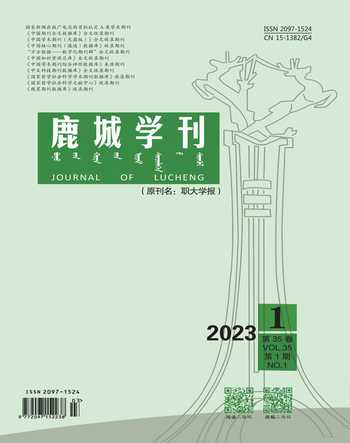敦煌写卷《渔父歌沧浪赋》探析
苏慧霜
摘 要:敦煌遗书主要是唐五代时期的写本和刻书,其中伯二四八八、伯二六二一、伯二七一二收录《渔父歌沧浪赋》(三卷)。同时,敦煌旧钞亦见存《楚辞音》残卷,敦煌遗书与残卷的发现,见证隋唐《楚辞》的流传。本文就敦煌遗书中的《渔父歌沧浪赋》写卷分析,从楚辞到唐赋,观察辞赋同源流变的轨迹,思考敦煌《楚辞》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楚辞渔父;渔父歌;沧浪赋;楚辞音;敦煌写卷;唐赋
An Analysi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Fishermans Song of the East Sea Ode”
Su HuiShu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Changhua City)
Abstract: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nsist mainly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 handwritten and engraved books. Among them,the manuscripts numbered 2488,2621,and 2712 include “Fisherman's Song of the East Sea Ode” (three volumes).In addition,remnants of “Chu Ci Yin” (the music of Chu poems) were also found in the Dunhuang old notes.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and remnants of “Chu Ci Yin” testifie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u Ci” (a poetic anthology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Fishermans Song of the East Sea Ode,”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poetic expressions from “Chu Ci” to Tang dynasty poetry,and considers new directions for the study of “Chu Ci” in Dunhuang.
Key words:Chu Ci;Fishermans Song;East Sea Ode;Chu Ci Yin;Dunhuang manuscript;Tang dynasty poetry
一、前言
自西汉刘向集楚辞、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以后,《楚辞》专书至宋而大兴,晁补之《重编楚辞》、洪兴祖《楚辞补注》、杨万里《天问天对解》、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钱杲之《离骚集传》、吴仁杰《离骚草木疏》、谢翱《楚辞芳草谱》专书继出[1],洪兴祖《楚辞补注》[2]、晁补之“楚辞三种”:《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3]、朱熹《楚辞集注》等更是重中之重的《楚辞》专著,还有熟谙楚赋的苏轼“手校《楚辞》十卷”[4]。相形之下,唐代《楚辞》专著不多,唐代《楚辞》研究一直是相对匮乏的。敦煌写卷的出现,大量唐代传抄的诗赋写本面世,弥补了唐代研究的缺憾。
敦煌写卷中以赋为体,原卷篇题标名为“赋”的二十八篇作品中,《渔父歌沧浪赋》(三卷)分别载于敦煌遗书伯二四八八、伯二六二一、伯二七一二。伯二四八八卷前题:“前进士何蠲撰”。何蠲为唐代进士,写卷赋云:“昔渔父兮泛彼中流,逢逐臣兮沧浪渡头。”借渔父之歌赋沧浪之情。赋中渔父自言:“愚本楚人,家于楚地”,显示与《楚辞·渔父》同为楚歌一系,《渔父歌沧浪赋》以骚句起兴,赋中有歌、衍为对问体赋,从楚辞到唐赋,一“辞”“一“赋”,文体的流变对研究敦煌《楚辞》提供了新的思考:敦煌写本中的诗词曲赋,有俗赋、唱词、变文等,写本中的曲子词出现很早,唐诗和曲子词一起被传唱与传播,许多俗文学也从佛教的讲唱文学中汲取营养,但可能还有更多杂在赋中的歌谣被忽略,《渔父歌沧浪赋》显示民间抄本中的楚歌或楚赋,或可能作为赋中的一个变体文学存在于各类杂抄中。
二、撰作与传抄
敦煌写本《渔父歌沧浪赋》分别三见:
伯二四八八卷前题:“前进士何蠲撰”。卷末题:“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书记之耳”。
伯二六二一卷末题:“长兴五年岁次癸丑八月五日敦煌郡净土寺学士郎名”。
伯二七一二卷末题:“贞明六年庚辰岁次二月十九日龙兴寺学郎张安人写记之耳”。
(一)撰作者
《渔父歌沧浪赋》作者,伯二四八八赋前署名:“前进士何蠲撰”。关于何蠲,一说为唐德宗、僖宗年间人,唐代康骈《剧谈录》提到唐大中、咸通(懿宗.僖宗年)间有何涓者善文章:
大中、咸通之时以文章称者有温庭筠、郑渎、何涓等。[5]
一说或即何涓,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载:
何涓,湘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6]
湘南人何涓,善辞赋,作《潇湘赋》传天下。何涓能诗赋,又见录于宋代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古今诗话》录有《潇湘赋》两句:“镜敛残色,霞披晓光。”[7]赵逵夫先生《历代赋评注》一书以为《渔父歌沧浪赋》作者何涓即何蠲,因“蠲”“涓”同音,二者为同一人,《历代赋评注》赋评曰:
何涓有诗云:雁影数行秋半逢,渔歌一声夜深发。皆曲尽其妙。所引何涓。诗与何蠲此赋的意境甚为相似,益可证何蠲即何涓。[8]
欧天发以为:“生卒年不详,后梁以前在世。前进士。”[9]关于“前进士”的身份,伏俊琏先生《俗赋研究》曾考论:“称其为前进士,则其已进士而尚未受官。《称谓录》卷24:“唐代有举人进士之名,特为不第者之通称。”[10]又“何蠲、何涓是否一人,不得而知。”[11]
由以上材料大致可推断《渔父歌沧浪赋》作者为唐代进士何蠲(或即何涓),湘南人,[12]德宗、僖宗大中、咸通(851-862年)间与温庭筠、郑渎等人以文章闻名,精通诗赋,作《潇湘赋》天下传写。
从作者进士身份看来,是以文人之笔,借渔父情事抒不遇之怀,不论是从赋文之耀艳丽词或作者身份,将此赋视为文人雅赋,都是可以成立的。[13]何蠲是湘南人,其《潇湘赋》写洞庭雁影:“镜敛残色,霞披晓光。”与《渔父歌沧浪赋》中“渡若洲边,称为渔者;往往潇湘水上,乱入鸥群。”之潇湘景语,与一般敦煌俗赋已然有别。
(二)手书题记
敦煌写本是由抄写者编辑整理而流传,写本的传抄有赖抄写者之力。现存敦煌写本多为残卷,抄写者多题署学郎、学士郎等,少数具名,如伯二四八八署名“吴狗奴”,潦草的抄写字迹,明确标明来源的写本极少见,格律诗与千字文、偈赞、古体诗、赋等民间唱曲抄录在一起的情况比比皆是。文书内容多代写契约、买卖地契、房舍、奴仆等法律或实用文书,写本出现学士、学士郎、孔目官、僧政等题记。在敦煌写本和藏经洞窟中,写本的抄手,学士郎不是唯一抄写者,有学士郎、孔目官、僧政等题写人,其身份或是敦煌寺学郎,或是官府抄书手,朱凤玉《敦煌学郎诗抄析论》一文以为:敦煌地区唐宋时期对各级学校的学生称谓,有自称为:“学士郎”“学郎”“学士”或“学生”。这些学生在抄写、持诵的书本卷末或卷背,每每信手涂鸦,抒怀感慨地留下一些诗歌作品,便是我们所谓的学郎诗抄。[14]
这些抄写者抄写文书、佛经、变文、蒙书、经典、诗赋等,卷末题记的保存,记载抄写时间、地点、身份、人名,因此题记的整合见证文学的传播,提醒千年文化传播的轨迹。
考《渔父歌沧浪赋》三卷的题记:
伯二四八八卷背题: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书记之耳。
伯二六二一卷背题:“长兴五年岁次癸巳八月五日敦煌郡净土寺学士郎员义”。
伯二七一二卷背题:“贞明六年庚辰岁次二月十九日龙兴寺学郎张安人写记之耳”。
唐“辛卯”年有三次: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然作者何蠲为唐德宗、僖宗大中、咸通年间人,因此作品传抄不可能早于此,所以伯二四八八所载“辛卯年正月八日”传抄时间最有可能是唐懿宗咸通十二年辛卯(871年),印证唐代康骈《剧谈录》: “大中、咸通之时以文章称者有温庭筠、郑渎、何涓等。”[15]以文章称名来看,传抄时间最是吻合。
伯二六二一载:“长兴五年岁次癸巳八月五日”,“长兴”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第二个年号,约公元930—934年之间,此纪癸巳年在公元933年。伯二七一二卷:“贞明六年庚辰岁次二月十九日”之“贞明”是后梁末帝朱友贞的第一个年号,约公元915—921之间,此庚辰年在公元920年。以上根据三卷写本题记显示:《渔父歌沧浪赋》之传抄流传在敦煌是在五代后梁至后唐之际,大约在公元871—933年间。
至于传抄地点,伯二六二一与二七一二分别记载“敦煌郡净土寺”与“龙兴寺”。根据郑阿财《敦煌佛教寺院功能之考察与研究——以敦煌文献与石窟为中心》研究指出:龙兴寺简称“龙”。(S.381《毗沙门天王灵验记)。《全唐文》卷332房管《龙兴寺碑序》及《唐会要》俱云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辟,命天下诸州各置中兴寺观,旋改名龙兴寺。敦煌之龙兴寺晚至唐宝应二载(763年)初见其名(S.2436),至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犹存(《天禧塔记》)。吐蕃占领时期辰年(788年)有僧众二十八人(S.2729),唐末增至五十人(S.2614V),后晋天福二年猛增至一百人(P.2250)。吐蕃戌年(818年)有寺户不下四十三户(S.542),收入来源于田园、羊群、马群、利贷、布施等多种项目。后梁时设有寺学(P.2712)兼授僧俗生徒。有藏经楼储藏佛经供寺僧诵读(S.476)。吐蕃时代“收得道门及诸家旧藏”储于此(S.5832)。龙兴寺为敦煌的官寺,在沙州城内。节度使曹元忠给予布施以结善缘(S.3565)。曹宗寿为此寺修像而向宋王朝乞请金箔(《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著名僧人日进、龙藏、明照、德胜、庆林、深善等皆出家于该寺。莫高窟第36、85、144等窟有该寺僧人供养像及题名。[16]
在沙洲城内的龙兴寺于后梁时期设有寺学(P.2712)兼授僧俗生徒,且有藏经楼储藏佛经以供寺僧诵读。吐蕃时期收得道门及诸家旧藏于此,此中“诸家旧藏”的具体书目犹未考知。龙兴寺晚至唐宝应二年(763年)初见其名,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犹存,符合伯二七一二卷:“贞明六年庚辰岁次二月十九日”所记载920年庚辰年传抄时间限。
至于敦煌净土寺,根据陈大为《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净土寺研究》:
净土寺简称“土”。吐蕃占领时期申年(840年)初见其名(P.3410)。下至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犹存(S.3156)。唐末有僧、沙弥二十三人(S.2614V),收入有田园、租税、油梁、硙课及利贷、布施等项来源(见P.2032、P.2040、P.2049、P.3234及S.6452)。P.2049V保存有净土寺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及长兴元年(930年)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晚唐至北宋开宝年设有寺学(P.2570及S.2894(5)),兼授僧俗生徒,设经库收藏佛经,供寺僧诵读。该寺在敦煌佛教、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著名僧人有法成(吴三藏)、崇恩、谈广、慈恩、绍宗、愿济、保护等。寺址在沙州城内(P.3234背、P.2032)。[17]
净土寺于晚唐至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年间设有寺学,兼授僧俗生徒,设经库收藏佛经供寺僧诵读,如陈大为所指:“寺院不是隐身山林的修道院,而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融入社会群众的宗教性开放空间,具有明显的人间性与世俗性。”[18]因此《渔父歌沧浪赋》在五代后梁至后唐之际,大约公元871-933年间,经敦煌郡净土寺学士郎员义与龙兴寺学郎张安人传抄流传。可见唐五代时期寺院在佛教、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作用之外,于文学经典的传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龙兴寺为敦煌的官寺,净土寺设置有寺学,因此有学士或学士郎抄手,但是伯二四八八写卷显示敦煌写本是自抄本,这一点可以从多则题记左证,如伯二四八八卷背题:“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书”,伯二七一八题记:“开宝三年(970)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书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伯三七八零题记“丙子年(976)五月十五日学士郎杨定千自手书记之也不乱人取”等。题记“自手书写”是自抄写本的例证。
根据李正宇先生统计,在敦煌写本卷所见的一百多则学郎题记,基本上都是抄写儒家经典《论语》《尚书》《毛诗笺》《孝经》和诗赋、蒙书、书仪、类书和变文故事等,[19]学士郎抄写的内容有学校学习教材的儒教经典、类书、书仪、蒙书,和通俗文书占卜、变文、诗赋。赋出现学郎题记的作品,目前所见有《秦妇吟》三卷、《王梵志诗》四卷、《苏武李陵往还书》五卷、《燕子赋》三卷、《捉季布传文》三卷、《茶酒论》二卷、《碎金诗》和《训女文》一卷等,[20]如今再加上《渔父歌沧浪赋》三卷,推想此外应该还有更多待发现的题记。敦煌写本经过学士郎抄写而流传,反映了唐五代诗歌典籍流传的途径,通过题记,可以探知《渔父歌沧浪赋》是辗转通过龙兴寺学士郎张安人与敦煌郡净土寺学郎题记之管道传抄于寺院之间,从唐到五代,寺院不但是唐人讲经、说话等讲唱文学娱乐活动的场所,也是唐典籍文学的传抄之地。寺学之外,更有像吴狗奴这样自手书的手抄本,如张利亚《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及其传播接受》所言:“写本生成来自于口述文献和文本文献,这些文献凝聚着民间和官方记载,是民间和官方两套文献”。[21]
此外,就《楚辞》相关作品而言,除《渔父歌沧浪赋》外,敦煌旧钞现存《楚辞音》残卷,相传为释道骞所撰,释道骞善楚声,《隋书·经籍志》记载:“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渔父歌沧浪赋》与《楚辞音》的发现,无疑补证了唐五代《楚辞》在敦煌的流布与事实,并且透过寺院管道学士郎题记与寺院寺学,理解为何僧人释道骞善《楚辞音》的原因了。
三、敦煌俗赋
赋渊源于《楚辞》,亦诗亦文的赋与《楚辞》关系密切。敦煌原卷篇题标名为“赋”的作品一共有28篇,《渔父歌沧浪赋》或名《渔父沧浪赋》,[22]伯二四八八卷前题“前进士何蠲撰”。以骚体兮字起兴:“昔渔父兮泛彼中流,逢逐臣兮沧浪渡头。”,对问体答问,敷衍《楚辞》渔父故事,赋中云“愚本楚人,家于楚地”,对应了《楚辞·渔父》莞尔鼓枻,濯足沧浪的人物情节,寓抒情传统以文化上的意义。
伏俊琏先生《敦煌俗赋之研究范畴及俗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一文指出敦煌俗赋有三种类型:“故事俗赋、对问体俗赋、歌谣体俗赋”。[23]《渔父歌沧浪赋》写卷保留骚体兮字句,并延续渔歌对问形式,赋中系歌,赋末乱辞,骈俪兼散行,从赋体形式到故事内容,兼具了“对问”“歌谣”两类特质,至于是否是“故事俗赋”,显然有更多讨论空间。
(一)对问体
《楚辞·渔父》收录在王逸《楚辞章句》,又见录于梁朝萧统《昭明文选》第三十三卷“骚下”,[24]为辞赋类古文,是散文化的辞赋。战国时期的《楚辞》体辞赋已具有散文化的特点,《渔父》《卜居》篇的对问,通篇自由,骈俪散行可视为散体赋的发端。《楚辞·渔父》如下: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25]
与《楚辞·渔父》同,《渔父歌沧浪赋》写渔父对话,并保留骚体兮字句式,赋中系歌,显示楚赋与唐赋“同源流变”的例证。
假设对问本是辞赋常见体式,屈原《渔父》有对问之实,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纪昀评:“《卜居》《渔父》已先是对问,但未标对问之名耳。”[26]屈原之后,宋玉赋沿袭对问体例,刘勰首先指出《文心雕龙·杂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27]所以《对楚王问》直接题名“对问”,《登徒子好色赋》虽为赋名,实则是宋玉与襄王答问,可见辞赋早已具备实质意义的对问赋体了。《渔父歌沧浪赋》通篇以问答:
渔父……于是停桡而问曰
……乃言曰:愚本楚人,家于楚地。……
渔父曰:振佩鸣珂,其生若何?……
赋云:“愚本楚人,家于楚地尝欲去奸党,涤浮媚,殊不知世以昏兮道不行,我独醒兮人皆醉。”家于楚地,印证楚歌的渊源。赋中渔父与逐臣之对问,韵散间出,多排偶句,正是一篇典型的对问体赋。
(二)歌谣体
刘熙载《艺概·诠赋》:“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虽赋之卒,往往系之以歌。”[28]“乱”本是乐曲卒章,赋末“乱辞”为曲终收尾,《论语·泰伯》云:“师挚之始,关雎之乱”,[29]“始”与“乱”相对,可见“乱辞”有乐终之意。屈原《楚辞》作品中的《离骚》《怀沙》《哀郢》《涉江》《抽思》《悲回风》《招魂》等篇末均有“乱辞”,东汉王逸于《抽思》篇:“少歌曰:与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无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辞而不听。”下注:“小吟讴谣,以乐志也。”[30]又注“歌曰”:“愤懑未尽,复陈辞也。”[31]可见“小歌曰”“歌曰”是以吟讴形式陈辞言志的歌谣。
《楚辞》之“乱辞”一般在赋末,或作:“乱曰”,如《离骚》末: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32]
乱辞或称“歌曰”,如《渔父》:
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33]
汉以后,乱辞或称“乱曰”“诗曰”“歌曰”“辞曰”“颂曰”“重曰”“和曰”“以矣哉”等,有时赋中还有系诗,魏晋赋如马融《长笛赋》、赵壹《刺世疾邪赋》、鲍照《芜城赋》、萧绎《采莲赋》等赋中有乱辞“歌曰”。敦煌赋《渔父歌沧浪赋》的“歌曰”系在赋中,两首歌共八句,是整齐的七言诗:
歌曰:微风动兮百花坞,扣舷归兮满江雨。挂云帆兮何足数,来濯缨兮沧浪浦。
又曰:泛蓬艇兮戏凫鹥,澄水镜兮照虹霓。指尘路兮何足迷,来濯缨兮沧浪溪。
伏俊琏先生《敦煌俗赋之研究范畴及俗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一文指出:“……就如同敦煌写本中的《渔父歌沧浪赋》。《高兴歌》是省称,省掉了后面的“酒赋”二字,就像伯二六二一号写卷《渔父歌沧浪赋》尾题“渔父”一样。我们虽然还不能找出乐府旧题中的《高兴歌》,但《乐府诗集》卷83《杂歌谣辞一》载有《渔夫歌》古辞,敦煌本《渔父歌沧浪赋》本意当是指以《渔夫歌》那样的调子讲诵《沧浪赋》,或者以《渔夫歌》的形式来表现《沧浪赋》。”[34]从敦煌写卷《渔父歌沧浪赋》中两首“歌曰”看来,敦煌本《渔父歌沧浪赋》正是“以《渔夫歌》的形式来表现《沧浪赋》”,因此,“以《渔夫歌》那样的调子讲诵《沧浪赋》”是完全可能的,虽云“讲诵”,但也或可能是“唱诵”。
根据《汉书·王褒传》:“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35]的文献记载,汉宣帝时九江被公犹能诵读《楚辞》,九江位于安徽寿县,曾是楚国春申君的封地,战国后期楚国迁都至此,命名为郢。与此同时,敦煌残卷见存释道骞《楚辞音》印证楚音之存在,《隋书·经籍志》叙录:“释道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36]可见汉至隋唐之际诵读楚声的人还是有的,而且还随着释道骞《楚辞音》和《渔父歌》调流传于西域。《渔父歌沧浪赋》与楚歌的渊源明确,证据还有二:一是作者何蠲,据《唐摭言》卷十:“何涓,湘南人也。”[37]湘南地属古楚地。二是敦煌本《渔父歌沧浪赋》中主人翁自言:“愚本楚人,家于楚地”。
不论是作者或作品主人翁,均爰属楚地,由此赋可见唐代楚赋流传之一斑。
四、对敦煌俗赋的商榷
1900年当敦煌遗书发现《燕子赋》《韩朋赋》《丑妇赋》等题名为赋的作品之后,通俗的语言,诙谐的趣味,通称为俗赋。“俗赋”一词见于清代刘熙载《艺概·赋概》:“古赋意密体疏,俗赋体密意疏。”[38]将“俗赋”与“古赋”对举。伏俊琏先生《俗赋研究》引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一文指出俗赋的四个主要特征[39]:一是基本上是叙事文学;二是大量运用对话;三是带有诙谐嘲戏的性质;四是大体上是散文,句式参差不齐,押韵不严。从上述四个特征看俗赋,伏俊琏先生《俗赋研究》一书将其分为“故事俗赋”“客主论辩俗赋”“咏物类俗赋”三类别,其“敦煌咏物俗赋”一章中收录《渔父歌沧浪赋》《驾幸温泉赋》《龙门赋》《酒赋》《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秦将赋》、《丑妇赋》《月赋》《子灵赋》等十篇咏物俗赋,[40]若是根据上述四特征论断,《渔父歌沧浪赋》具足俗赋的四个特征。
然而,相较于汉代以来的大赋与文人雅赋,俗赋是近代敦煌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战国宋玉、景差等以戏谑或讽谏为目的,创作所谓“曲终奏雅”的赋,[41]随着倡优将赋带入朝廷贵游文学之中,[42]文人、倡优辄利用俗赋幽默诙谐的主调创作赋,敦煌俗赋的面世,让我们关注到文人赋与民间俗赋之间,赋的“雅”“俗”之辨。然而,有趣的是:一向被视为敦煌俗赋的《渔父歌沧浪赋》,作者是唐代进士何蠲,赋中:“苹风夕起,层台艳艳之波。兰露晓浓,两岸绵绵之草。”铺采摛文的景语使人疑惑,不禁要问:“文人赋”与“俗赋”,“雅”与“俗”的界义何在?辨证俗赋与文人赋之际,《渔父歌沧浪赋》正是一篇极其有趣的观察。
敦煌写本的抄写者依据隋唐五代善本加以辑录,虽然在传抄过程中或可能舛误或脱漏,但像《渔父歌沧浪赋》这样的文本,不论文字或体式都是赋的能手,辞藻绝艳展现绝佳的文人赋情。
《渔父歌沧浪赋》中有散文,有韵文,骈偶交错,交互问答,延续骚体“极声貌以穷文”的写作特色,[43]兹引赋文分段如下:
昔渔父兮泛彼中流,逢逐臣兮沧浪渡头:我有垂纶之思,君含去国之愁。
纫佩江边,悄尔投荒之泪;鸣桹波上,飘然不系之舟。
于是停桡而问曰:人合娱情,子何丧志?况斯处也,水迭晴绿,山横晓翠,
曾无止足之心,似有关身之事。
乃言曰:愚本楚人,家于楚地。尝欲去奸党,涤浮媚,殊不知世以昏兮道不行,我独醒兮人皆醉。
渔父曰:振佩鸣珂,其生若何?胡不钓寒林,挂烟萝,笑迷津而指道,逐鼓浪以长歌?
歌曰:微风动兮百花坞,扣舷归兮满江雨。挂云帆兮何足数,来濯缨兮沧浪浦。
又曰:泛蓬艇兮戏凫鹥,澄水镜兮照虹霓。指尘路兮何足迷,来濯缨兮沧浪溪。
从赋的情节、人物对话到抒情写景,无论是结构、手法、行文等,都与《楚辞·渔父》并为双璧。根据“极声貌以穷文”看此赋的布局:
1.骈俪对句:
“昔渔父兮泛彼中流,逢逐臣兮沧浪渡头”
“挂云帆兮何足数,来濯缨兮沧浪浦”。
2.精炼语法:
“胡不钓寒林,挂烟萝,笑迷津而指道,逐鼓浪以长歌?”
“殊不知世以昏兮道不行,我独醒兮人皆醉”。
3.散行对问:
“于是停桡而问曰:人合娱情,子何丧志?……”
“乃言曰:愚本楚人,家于楚地”
“渔父曰:振佩鸣珂,其生若何?”
渔父逐臣、濯缨沧浪,垂纶鼓浪,如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夺胎换骨之功力,足证《渔父歌沧浪赋》作者是杰出的赋手,深厚的赋学学养,赋中极尽抒情写景之能:
已而渐回远汀,还依曲岛,鹤性多暇,龟年自保。
难知避世之由,但见无羁之抱。
苹风夕起,层台滟滟之波;兰露晓浓,两岸绵绵之草。
去影才分,余声尚闻,似落寒林之叶,不归暮岭之云。
渡若洲边,称为渔者;往往潇湘水上,乱入鸥群。
至今兹地长闲,斯流无极,前溪后溪之山影,千年万年之水色。
吾欲棹孤舟而钓沧浪,其奈名未成而来不得。 [44]
骈俪对偶之美,散行流畅之妙,诙谐论辩之外,兼擅华藻典嬗之美,相较于《楚辞·渔父》的质朴古拙,更推衍了汉赋“极靡丽之辞,闳辞巨衍”[45]的笔法,由此观之,可见《渔父歌沧浪赋》在敦煌俗赋《丑妇赋》《燕子赋》《韩朋赋》《晏子赋》等俗赋之外,别开唐赋抒情绝美一系。不能与一般“俗赋”等视。
五、从楚赋到唐赋
赋渊源于《楚辞》,继承了《楚辞》的特点及性质,刘熙载《诠赋》云:“叙物以言情谓之赋。”[46]唐代以“渔父”为赋题另有一篇宋言《渔父辞剑赋》(以“济人之急,取利诚非”为韵):
彼子胥兮亡命江湄,赖渔父兮停桡在兹。既横流而济矣,因解剑以酬之。
厚意殷勤,何惜千金之器;高情特达,竟陈三让之辞。
稽其去国无途,迷津独立。前临积水之阻,后有追兵之急。
踌蹰而鹤发相哀,顾盼而渔舟可入。……[47]
此赋载于《文苑英华》卷一○三及《全唐文》卷七六二,为一篇律赋。[48]同为唐代进士,何蠲和宋言均以“渔父”为题作赋,但《渔父歌沧浪赋》更向楚骚美学传统的复归,集骚辞、楚歌于赋一身。
(一)赋骚辞
“兮”字是骚体《楚辞》独特的声情表述,节奏变化,更适合吟咏歌唱。虽然萧统《文选》分立“骚”、“赋”为二,[49]然更多地将骚归于赋体,如明代吴讷《文章辨体》与徐师曾《文体明辨》在其“序说”中皆目“骚”为“楚赋”,清代陆葇《历朝赋格》称:“骚者,诗之变,赋之祖”,[50]钱陆灿《文苑英华·律赋选序》称:“《楚辞》皆谓之赋”,[51]无不归骚于赋。
《渔父歌沧浪赋》一开始即以骚句起兴:“昔渔父兮泛彼中流,逢逐臣兮沧浪渡头。”兮字吟咏,赋中间一段且援引两首骚体兮字七言之歌,“歌曰”:
“微风动兮百花坞,扣舷归兮满江雨。挂云帆兮何足数,来濯缨兮沧浪浦。
又曰:泛蓬艇兮戏凫鹥,澄水镜兮照虹霓。指尘路兮何足迷,来濯缨兮沧浪溪”
两首歌系诗八句,七言系歌,是《楚辞》一系的骚辞。融骚体与赋于一,因此为楚辞体流变的指标。
《渔父歌沧浪赋》逐臣曰:“我有垂纶之思,君含去国之愁。”去国愁思正是“忧幽穷蹙”的楚骚情韵。[52]此赋抒情写景迥异于汉大赋体物与讽喻的记事,更与唐赋的帝京气象不同。[53]六朝以后,论辩俗赋由荀子短赋辩理转向长篇叙事写志,倾向于扬雄所谓:“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的抒情言志,[54]“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清浊的哲学之思,相对也就淡化了“讽谕”的汉赋精神。高似孙《骚略》自序推尊《离骚》以为:“《离骚》不可学,可学者,章句也;不可学者,志也。[55]何蠲托渔父以寄情,不仅效可学的《离骚》章句,更师楚骚精神,恢廓楚赋,展现从辞到赋的创变精神。
(二)系楚歌
文学抒情传统的确立有两个精神上的原型,一是《诗经》,另一则是《楚辞》。屈原以清白濯缨的典范成为文士精神与抒情歌谣的指标,沧浪写情成为一种精神向往,何蠲的渔父,“昔渔父兮泛彼中流,逢逐臣兮沧浪渡头”至“难知避世之由,但见无羁之抱”,点染渔父行止的飘忽不定之美。赋中系歌,歌曰:“微风动兮百花坞,扣舷归兮满江雨。挂云帆兮何足数,来濯缨兮沧浪浦。又曰:泛蓬艇兮戏凫鹥,澄水镜兮照虹霓。指尘路兮何足迷,来濯缨兮沧浪溪。”句中用“兮”的整齐七言体,如同《楚辞·九歌·山鬼》的句中用兮句式:“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56]
何蠲是唐人,盛唐时内地与敦煌的交流非常频繁,敦煌文献寒山、拾得、李白、白居易、元稹、韩愈等唐人诗歌选集,其中多可见渔父之迹,唐诗多以渔父钓叟为题名,《全唐诗》所载渔父诗,保守估计至少有百首,渔父诗创作兴盛,盛唐诗以“渔父”题名的即有李颀《渔父歌》、岑參《渔父》、高适《渔父歌》和储光羲《渔父词》等诗,此外,不以“渔父”题名而实写渔父者,如韩愈《湘中》诗:“空闻渔父叩舷歌”。在唐代科举诗赋取士的制度下,赋与诗媲美,作为应试工具的同时,律赋的形成已然完备,所以宋言《渔父辞剑赋》以律赋写就,在此环境下,何蠲《渔父歌沧浪赋》独以楚赋系歌,因此突出楚赋在唐代赋作中的独特性。
六、结语
唐代《楚辞》学因为资料匮乏,对比于汉、宋,相关研究相对不足,如今随着敦煌写卷的发现,许多唐代文献的出土,对研究《楚辞》文学与文化的流传提供新的史料。
赋的源头在民间,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融合的成果,本文从敦煌写本《渔父歌沧浪赋》溯源《楚辞·渔父》,从楚赋到唐赋,看到文人抒情精神的歌谣化,赋体文学对于歌谣的转化,补证伏俊琏先生《敦煌俗赋之研究范畴及俗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所指出:“敦煌俗赋文人赋的区别,更多是反映了中国文学本源同流变的区别。”[57]从骚到赋,看到敦煌赋在唐赋研究中的价值与重要性。
与此同时,笔者关注到敦煌旧钞《楚辞音》残卷的出现,此卷虽未注明撰者姓名,但其中“骞案”云云,据考定为隋释道骞所撰。释道骞善楚声,《隋书·经籍志》载:“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58]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的敦煌旧钞《楚辞音》残卷,仅存84行,从“驷玉虬以乘鹥兮”至“杂瑶象以为车”,共释《离骚经》188字,注文96字,一共284字。此卷保存了自汉至隋的楚辞遗说,在《楚辞》辑佚上有相当的价值。
从释道骞《楚辞音》到《渔父歌沧浪赋》,见证了隋唐《楚辞》古音与楚辞本事在西域敦煌的流布,从敦煌写卷赋的题记整理中,考知唐赋流传之迹,特别是寺院里作为教材读本的传播渠道,对于研究西域《楚辞》学提供了新素材。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枢纽,亦是多元文化的交融之所,除了文学本身的历史发展之外,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楚文学的神秘在于幻想与神话,在《楚辞》的《离骚》《涉江》《远游》等章多有昆仑求仙之举,随着西域昆仑神话的脚步探知,《天问》“顾菟在腹”的于菟舞,可能从湖北楚地或楚人后裔巴人传到青海,青海祭仪巫觋文化传承至今,于菟傩舞是活化石,也是楚文化瑰宝。企盼从楚地巫觋到昆仑神话,从楚赋到唐赋,从楚辞到楚辞音,透过文学、神话、语言、文化等更多出土文献,可以看到《楚辞》在西域的发展,此研究成果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周建忠.五百种楚辞著作提要[M].施仲贞,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11-23.
[2]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晁补之.鸡肋集·离骚新序[M].四部丛刊影明本卷36[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4]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楚辞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34.
[5]康骈.剧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144.
[6]王定保.唐摭言卷十[M].台北:新兴书局,1977.
[7]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M].古今诗话[M].四部丛刊初编缩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25.
[8]赵逵夫.历代赋评注·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645-647.
[9]赵逵夫.历代赋评注·唐五代卷[M].录欧天发《渔父歌沧浪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645.
[10]伏俊琏.俗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407.
[11]伏俊琏.俗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407.
[12]伏俊琏.敦煌俗赋之研究范畴及俗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J].政大中文学报,2012(18):37.
[13]朱凤玉.敦煌学郎诗抄析论[J].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7(48):111-138.
[14]康骈.剧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1:144.
[15]郑阿财.敦煌佛教寺院功能之考察与研究——以敦煌文献与石窟为中心[M].台湾地区科学事务主管部门专题研究,2006年8月-2008年1月:12.
[16]陈大为.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净土寺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5.
[17]陈大为.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8]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J].敦煌学辑刊,1989(1):26-40.
[19]朱凤玉.敦煌学郎诗抄析论[J].东海大学文学院学报,2007,7(48):111-138.
[20]张利亚.唐五代敦煌诗歌写本及其传播接受[D].甘肃:兰州大学,2017.
[21]伏俊琏.敦煌俗赋之研究范畴及俗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J].政大中文学报,2012(18):35-36.
[22]萧统.昭明文选·骚下·渔父[M].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729.
[23]王逸.楚辞章句[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239.
[24]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5]刘勰.文心雕龙[M].台北:里仁书局,1984.
[26]刘熙载.艺概·赋概[M].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101.
[27]何晏,注.论语·泰伯[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8]王逸.楚辞章句[M].九章·抽思[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177.
[29]王逸.楚辞章句[M].九章·抽思[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177.
[30]王逸.楚辞章句[M].离骚.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68.
[31]王逸.楚辞章句[M].渔父.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241.
[32]伏俊琏.敦煌俗赋之研究范畴及俗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J]政大中文学报,2012(18):35-56.
[33]班固.汉书·王褒传[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
[34]魏征等.经籍四集部[M].隋书卷三五[M].台湾:中华书局,武英殿本校刊印行,1971:1.
[35]王定保.唐摭言卷十[M].台北:新兴书局,1977.
[36]刘熙载.艺概·赋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01.
[37]伏俊琏.俗赋研究[M].敦煌咏物俗赋考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8:2.
[38]伏俊琏.俗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407.
[39]司马迁.史记[M].台北:新象书店,1985:2999.
[40]简宗梧.魏晋六朝贵游文学活动与其赋之特色[G].第四届魏晋南北朝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政治大学,1998.
[41]刘勰.文心雕龙·诠赋[M].台北:里仁书局,1984:138.
[42]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一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3]班固,撰.汉书.扬雄传[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
[44]刘熙载.艺概·赋概[M].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5:89.
[45]董诰,等.钦定全唐文卷七百六十二[M].台北:汇文书局,1961. 李昉,等.文苑英华卷103[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6]宋言.新唐书·艺文志四.宋言赋一卷[M].
[47]萧统.昭明文选60卷[M].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
[48]陆葇.历朝赋格·凡例[M].清康熙25年刻本.
[49]钱陆灿.文苑英华·律赋选序[M].清康熙25年吹藜阁铜活字印刷.
[50]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M].台北:艺文印书馆,1983:413.
[51]吴仪凤.赋写帝国——唐赋创作的文化情境与书写意涵[M].台北:万卷楼图书出版,2012.
[52]扬雄.扬子法言[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53]高似孙.骚略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12.
[54]王逸.楚辞章句[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105.
[55]伏俊琏.敦煌俗赋之研究范畴及俗赋在文学史上的意义[J].政大中文学报,2012(18):35-56.
[56]魏征,等.隋书卷三五经籍四[M].台湾:中华书局,武英殿本校刊印行,1971:1.
(责任编辑 吴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