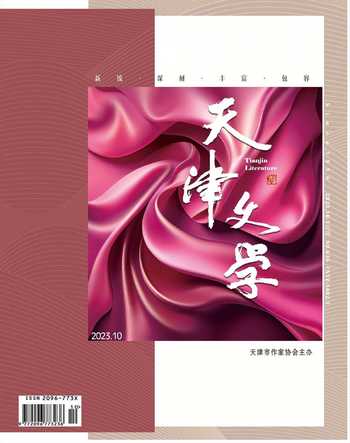过桥
桥就在离女孩几十米远的地方。女孩在路边的草地上、在毒日头下坐许久了,却依然不敢向它靠近,就别说踏上走过去了。
关键那是座什么桥呀!说它是桥,不过是块尺把来宽的厚木板。女孩四岁多时走亲戚,妈妈抱着大妹,后大背着女孩过这桥,走在上面,一步一颤的。女孩伸头朝下一看,黑洞洞的,吓得心惊胆战。现在,女孩怀里抱着小妹,又怎么敢过这桥呢?何况,小妹在她怀里一直哭闹踢腾个不停。
小妹一直哭闹踢腾个不停,是因为右手被烫成了“癞蛤蟆”。
自进入夏季抢收季节,妈妈就把小妹交给了女孩,不但让女孩在隔壁托儿所里帮着梁奶奶照看小妹,连女孩和小妹的饭,妈妈有时没顾上,女孩也得自己做。
这天早上就是这样。这天早上,女孩是在梁奶奶的喊叫声中惊醒过来的。
“看看都几点了,还赖在床上不醒?没听见你小妹饿得嗓子都哭哑了?”当梁奶奶怒斥般的叫喊伴着一片哭声传入女孩的耳膜,女孩感觉小妹那歇斯底里的哭声就像领唱者引吭高歌,惊得她顾不得揉眼穿鞋,就冲向灶台一把掀开锅盖。
锅里却是空的。
“你妈、你后大忙着把你大妹送到你奶家,走得太早,没顾上给你姊妹俩做饭。”女孩还没反应过来,梁奶奶的话就不耐烦地紧跟过来,“还不赶紧出门抱柴,烧火做饭。”
女孩一听,两脚匆忙地找到鞋,就赶紧出门抱柴,烧火做饭。
女孩会做的饭,也就是熬粥。即便熬粥,她也做不太好。后来,她勉勉强强熬好一锅粥,盛一碗,担惊受怕地抠着碗沿儿来到托儿所门前。小妹正坐在门边的凉席上,一边拍打席面,一边无助地哭嚎着,见她端着粥碗过来,便停止哭闹,一边饥渴地睁圆眼朝她张望着,一边兴奋地上下耸动着身子。女孩小心翼翼把粥碗放在离小妹稍远点儿的地方,一抬手却发现忘了拿喂小妹的勺子,眼睛不由就在托儿所里搜索起来。她看见梁奶奶家灶台上有把勺子,黑眸子便流溢着怯意看向梁奶奶。
梁奶奶正拍打着一个在她怀里哭闹的孩子,看见女孩投过来的眼光,便不耐烦地凶她:“赶紧回家拿去。”
女孩看看小妹,便赶紧扭头朝外跑。谁知,原本不会爬的小妹,这天大概是饿急了,竟然会爬了。女孩冲进家门,拿了勺子,刚走出来,隔壁就传来小妹炸雷似的一声惊嚎。女孩心里扑腾着赶紧冲过来,正好看见梁奶奶斜着身子,一手揽着那个正哭着的孩子,一手把小妹的右手从滚烫的粥碗里拔出来。
“咦,真是作孽呀!”梁奶奶叹息着,发泄着对女孩的不满与不屑,嫌棄地瞪女孩一眼,夺过她手中的勺子,就把没命大哭的小妹,塞进惊恐地呆立在那里的女孩怀里。
“去,赶紧抱你小妹去门外的水渠边,把她的手,摁到凉水里浸一会儿。”梁奶奶挥着手,就像赶苍蝇似的对女孩说。
女孩顾不得屈辱,便慌慌地抱着小妹往水渠边来。可水渠里的水落得很低,女孩很为难。她左看看,右看看,只得抱着小妹先蹲下坐到水渠边,用两个脚后跟,用力地在斜坡上蹬出两个深窝来,以防身体下滑,然后才笨拙地一手揽住小妹腰,一手握住小妹的右臂,俯身朝水渠下面伸过去。这种朝下匍匐的动作,原本就难度太大,维持不了太久。后来女孩双脚一下滑,就赶紧跐蹬着回到岸上来。小妹的手猛然离开凉凉的渠水,就又尖叫一声大哭起来。
梁奶奶听到哭声,便凶凶地喊:“抱过来我看看!”
女孩便抱起小妹,惶恐地来到梁奶奶跟前。
梁奶奶伸手拽过小妹的小胳膊,眯缝着眼一看,便惊叫起来:“就一碗粥,咋就烫成这样了呢?”
只见小妹大半个小手都红了,五个小手指头都虚起一层水泡。女孩伸头一看,怯怯的大眼里立即就溢出明亮的惊恐来。她当即就想起了后奶蛇一样的眼神和后大打她的大巴掌。
“这,这——”梁奶奶看着看着也惊慌起来。只见她为难地环视一眼满屋哭闹的孩子,犹豫一阵,就挥手指向房子西头那条通往诊所的土路,对女孩说:“快,快,快抱着你小妹去大队诊所,让医生看看!不然一旦感染化脓,发起烧来就没命啦!”
女孩一听,眼里的惊恐更明亮了。也就从她照看小妹开始,才摆脱了整天挨打、挨饿,被逼着离开妈妈的厄运。她需要妈妈。她不想离开妈妈。可如果小妹有个三长两短……女孩想起后奶蛇一样阴鸷的眼神,想起后大凶凶地把她扔出家门的情形,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她太紧张了,根本没顾得多想,就抱着小妹朝那条土路奔去。
其实,女孩家离大队诊所也就一里多路。踏上土路,向东北走一段,然后折向正北,穿过一大片开阔地,朝前再走几十米就是了。如果是个大人,十分钟也就到了。可女孩不过六七岁,她怀里的小妹已半岁多,最少也有十几斤重吧?平时她抱着小妹,最多也就从家里到托儿所,从托儿所到家里。哪儿走过这么远的路呢?
这天,女孩抱着小妹,顶着盛夏的毒日头,趔趔趄趄,慌慌张张,没走多远就大汗淋漓了。一路上,女孩紧张得,看到漂亮的蝴蝶,都没敢分心;看到鲜艳的花朵,也没敢驻足;看到可以编小花猫的狗尾巴草,更是连多看两眼都没有;甚至,她累得腿发软,都没舍得多歇半分钟。可是,她累得精疲力竭,衣服湿透,抱着小妹好不容易穿过那一大片开阔地,猛一抬头却看见前方横着一条壕沟,一条挡她去路的壕沟。她这才想起,到大队诊所,还要过一座桥。
想着那桥,女孩腿一软,便跌坐在路边草地上。跌坐在草地上,没有了行走的摇晃和风,又被盛夏毒日头燎烤着,女孩怀里的小妹就烦躁地踢蹬哭闹起来。
女孩只能一边摇晃拍打,一边朝四下里张望,期待能走过来个大人帮帮她。可她坐下去时,太阳照出的草影还斜斜的,现在斜影缩到草窠下,太阳照得路两边的荒草白光光的,也照得她两眼直冒金星,却依然不见有人走过来帮她。
正是夏季抢收季节,大人们天不亮就上工了,中午又不回家吃饭;就算有没上工的,也都病歪歪躺在床上,女孩又怎么可能等来大人帮她呢?别说大人了,就大点儿的孩子,大中午头的,太阳耀得人眼都睁不开,不是躲在家里,就是躲在哪里的阴凉地里,谁又会到这地方来呢?
女孩也曾想过找个阴凉处避避日头,可桥这边没有一棵树,只有桥对岸,诊所旁长着一棵楝树,她过不了桥,又怎么去避呢?
问题是,开始还能听见不知哪里传来的说话声,后来连说话声也没有了。四周静寂一片,连点儿风声都没有,冷清得让人心里发凉发怵。女孩心里一慌,就喊起来:“有人吗?帮帮我,帮我把小妹抱到桥那边儿去!”
“哇——哇——”从对面诊所旁那棵楝树上,却传来几声乌鸦叫。
女孩再喊,那乌鸦又叫了几声,阴森可怖。
女孩听了心里好瘆,好凄凉,突然就想起了妈妈。这时,小妹大概也是因为那乌鸦声,又“啊”一声大哭起来。
女孩赶紧用力摇晃,汗水不停地从她脸上淌下来,淌下来。女孩的太阳穴咚咚地跳着,头嗡嗡响着,就像有个知了在耳边鸣叫。要知道,一早起来她到现在还滴水未进呢!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小妹却哭闹踢腾得更厉害了。女孩就有些气恼,想给小妹一巴掌,一低头却看见,小妹热得小脸通红,双眼被太阳晒得眯着,头发都湿成了绺,几乎成了个水人。女孩又心疼起小妹来。她看向小妹的小手,每个手指头上都是明晃晃的水泡,鼻子一酸,就呜呜大哭起来。
女孩一哭,她怀里的小妹,就踢腾着哭得更起劲儿了。此时的女孩,又累,又热,又饿,又困乏,只能机械地摇晃着,任由小妹哭着,耳朵里一旦没有了小妹的哭声,人一松劲儿,也就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沉睡中的女孩,后来是被小妹的哭叫声吵醒的。小妹的哭叫声尖锐而沙哑。她努力睁开眼,只觉得头被刀子剜着一样痛,太阳虽没那么刺眼了,热却依然熥烤着她。迷迷糊糊中,她闻到热热的青草味,看到小妹滚在身边的草地上,一只绿头苍蝇正嘤嘤嗡嗡盘旋在她伤手四周。一定是这只绿头苍蝇擦碰到了小妹的伤手,小妹受惊右手一甩,又尖锐刺耳地哭叫起来。那时,女孩也滚在草地上,就赶紧挣扎着坐起来,却见小妹烫伤的五根手指头,肿得就像五个透明的鱼泡。而且有几处,皮已经碰破了,有明明亮亮的水,正从那里一滴一滴地坠下来。绿头苍蝇正围绕四周嗡嗡叫着寻找机会,似乎打算再叮上一口。女孩赶紧挥手赶苍蝇。
没有了绿头苍蝇的侵扰,小妹的哭声一下就微弱下来,弱得比新生猫儿喵叫声还小。女孩听着,心里一阵惊悸,就想起了梁奶奶的话:“一旦感染化脓,发起烧来就没命了。”她赶紧去亲小妹的额头,却碰在小妹的脸颊上。小妹的脸颊滚烫滚烫,她又小心去触碰烫伤的小手,烫伤的小手更是烫得吓人。
女孩一下就慌了神。
小妹的手不但化脓了,人还发烧成这个样子……想到这个问题,女孩抱起小妹,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那一刻,她身上一下就凝聚起一股巨大的力量。她看到,有一道白光直通向桥面,便一步迈上去。那一刻,她感觉妈妈附体在了她身上,抱着小妹,目光平视,迈着坚实又有力的步子,稳当又从容地走在桥上……
走在桥上?当女孩意识到这个问题,她怀里的小妹正惊恐万状地注视着桥下,拽着她的衣服,一动不动,静得连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一时,女孩惊悚得浑身僵硬,再也迈不动脚步。可这时,她已抱着小妹走到了桥中间,退回去已不大可能了。怎么办呢?女孩只得硬着头皮,把脚一点儿一点儿地横过来。而当她紧张得双眼紧盯脚下木板,一点儿一点儿朝前挪的时候,眼睛的余光却发现,壕沟并不像她记忆里那么宽,那么深不见底;桥也不像她记忆里那么可怕,那么窄——她脚横过来,脚两边还都余出一横脚宽呢!
女孩便慢慢、慢慢放松下来。
其实,女孩眼里的壕沟也不过两米来宽。当离对岸仅剩一步之遥的时候,她用力迈出一大步,脚就稳稳当当踏在了结实的地面上。
这时,她心有余悸地回头看了一眼,再次发现,壕沟确实不像她记忆里那么宽,那么深不见底;桥也确实不像她记忆里那么可怕,那么窄。接着,她抬头看见诊所的招牌,就赶紧双腿一软一软地朝那里奔去。
诊所在桥这边,马路对过稍微高一点的平地上。女孩抱着小妹来到诊所门前时,诊所里的女医生刚刚睡醒走出来。她显然认识女孩,一眼看到她抱着小妹来到门口,便惊讶道:“哎哟,门口这桥,你抱着小妹就过来了?”
女孩顾不得回答女医生。她慌乱地问:“阿姨,我小妹手感染化脓,烧得吓人,是不是会死啊?”
女医生这才注意到小妹那肿得像鱼泡一样的小手。她问女孩是什么时候烫的,观察了一下,摸了摸小妹的额头,才回答女孩:“丫头,你小妹这手,没有化脓,是虚水泡了;她也没有发烧……”
女孩听到“没有发烧”几个字,浑身一软,随即就朝地上倒去。
女孩醒过来时,小妹的手不仅涂抹了药水,还进行了包扎处理,小脸也洗得干干净净。据说,女医生不仅给她喂了不少水和人丹,也给小妹喂了不少水和人丹,还给小妹喂了一大碗面条。女孩看着,听着,双眼逐渐明亮。她看着女医生,无声地表达着感激。女医生问女孩:“你们是不是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呀?”
女孩羞怯地扑闪着大眼。她不知说什么好,迟疑了一会儿,才拘谨地点了点头。
女医生惊得“哟”一声,温和地抚摸女孩一把,转身走进另一间房,出来手里就拿着个白白的大馒头朝女孩递过来,一边柔和地说:“来,这馒头上午才蒸的,你先吃着,不够我再给你拿。”
女孩却有些不适应。从她来到妈妈新家这个陌生的地方,后大打她,奶奶用阴森的眼看她;孩子们骂她、羞涩她、用泥巴甩她;邻居们冷眼看她,避着她;连她在托儿所看小妹,梁奶奶也嫌她没用,笨,总是凶巴巴,冷冷的。从来就没人对她这么友善,这么好过。她不敢接,她一直退缩着,退缩着。
“别怕,是阿姨让你吃的。”
女医生一把把馒头塞进女孩手里,女孩这才犹犹豫豫抱着馒头吃起来。开始,她只用牙齿咬下一小点儿,见女医生忙别的去了,才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个大馒头,她似乎并没吃几下就全吃完了。吃完了,嘴里还意犹未尽地咀嚼着。
后来,女醫生转过来问女孩:“吃饱了吗?”
“吃饱了。”女孩一边回答,一边环视着诊所。那时,她和小妹已在诊所的地上玩了一会儿了,感觉有些不好意思,便抱起小妹走出来。
女医生就像明白女孩的心思,就跟出来对她说:“外面凉快,你姊妹俩就在楝树下玩吧!一会儿天晚了,就该有人来看病了,到时我让人家背着抱着你俩过到桥那边去。”
女孩便抱着小妹来到楝树下。那时,树下凉风习习,树上没有了乌鸦,却有小鸟在树上聚会似的,欢快地啁啾鸣唱着。女孩毕竟只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她听到鸟儿欢快地鸣唱,心情也就跟着欢快起来。她把小妹放在树荫下,小妹肚子吃饱了,手不痛了,顿时就“咿咿呀呀”拍打着地面玩起来。女孩便找来几颗石子,蹲在小妹身边抓起石子来。
“过到桥西,小鸟叽叽;过到桥东,太阳晒蒸。”
“过到桥西,凉风习习;过到桥东,脑壳咚咚。”
女孩一边抓石子,一边吟唱,很快就沉醉进抓石子的快乐中。她想着医生阿姨的友好和温暖,感觉习习的凉风,鸟儿的欢快鸣唱,楝树散发的浓浓苦涩与淡淡清芬,都让她浑身充满了轻松与愉悦。她并不知道,过桥和过桥后女医生对她的那点温暖,对,就那点温暖,已改变了她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并将在她成长过程中孕育出自信、自豪和光明的种子来。到那时,她绝不再会像现在这样胆小、怯弱、拘谨又内向了。
晴月,原名董凤,自2006年从事小说创作。出版长篇小说集《晴月殇》和长篇小说《相伴》各一部。在《天津文学》《延河》《海外文摘》《鸭绿江》《当代小说》《海燕》《火花》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万字。
责任编辑: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