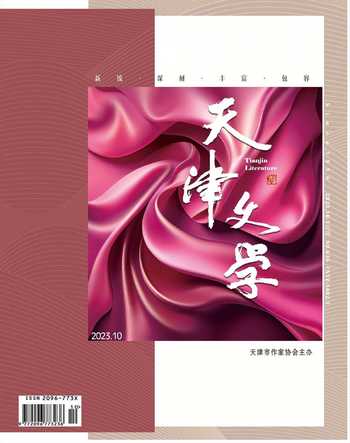短篇二题
村 口
我是在阿爸当兵半年后出生的。大约在我三四岁时,依稀记得阿妈牵着我的小手沿着机耕路走到村口等阿爸。这条坑坑洼洼的机耕路是云石村通向村外的唯一一条小路。村口有一座四方形的简陋的小庙,云石村的人习惯叫张飞庙,也有人干脆就叫路亭。庙里供着一块有些年月的石雕像,雕的是“桃园三结义”里的张飞,石像前断续有几炷香升腾着袅袅的细烟。紧挨小庙旁有一株上百岁的小叶榕树,如盖的枝叶像一把巨大的伞撑在张飞庙的上方。云石村张姓是大姓,我姓张,叫张小兵,阿爸给我取的名。阿妈告诉我,阿爸得知我降生后来信说就叫小兵吧,阿爸的大名叫大兵。那天在村口等阿爸的往事只留下些记忆碎片,记得阿爸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用他脸腮上坚硬的胡碴儿扎我的脸。还有大欣叔赶着马车出村口时巧遇阿爸,大欣叔跳下车擂了阿爸一拳,阿爸则叫大欣叔晩上来家喝酒。
阿爸探亲假虽然只有十多天,但自从阿爸归队后,我幼小的心灵似乎感觉到失去了某种支撑。我时常哭喊着扯住阿妈的衣襟催阿妈带我到村口,我盼望着在村口能再一次见到穿着绿军装的阿爸远远地朝村口走来……
在我六七岁大的时候已经能记事了,我时常伸长脖颈向村口张望,我多么想阿爸会突然出现在村口。
一天阿妈笑着跟我说:“娒,你阿爸信上说这个月底就到家了,你若想阿爸这两天下午就用心多朝村口瞄瞄,兴许会让你第一个看见阿爸呢。”
半年前我就听到阿妈跟爷爷和奶奶、姑姑说我阿爸信里说在队伍上升军官了,是个排长,换上四个兜的军服了,月月有五十几块的工资。爷爷很开心,叫了亲戚邻舍来家喝了不少的酒,爷爷还摸我的头说我孙子长大后一定比我儿子更有出息。
听了阿妈的吩咐后我每天下午就时不时地朝村口瞄上几眼,终于在几天后的傍晚,在视线可及的村口,在一片火烧云的背景里,我看见一抹绿色在不停地晃动,逐渐地变幻成完整的人影。我叫喊道:“阿爸,我看见阿爸了……”阿妈和爷爷奶奶还有姑姑听到我的叫喊声都跑到了屋外,奶奶把一只手掌在额头前搭了个棚朝路口凝视,说:“是大兵,是我娒大兵归家啦……”
我撒开双腿朝阿爸跑去,阿妈朝我喊:“小兵,慢点儿跑,别绊倒了……”
当我奔到阿爸的跟前时,却猛然刹住了脚步,我喘着粗气羞怯了起来。多少回啊,梦里的阿爸紧紧地搂着我,脸上坚硬的胡碴儿扎得我的脸蛋又痒又疼,我还没来得及挣脱开阿爸的怀抱,阿爸却突然把我放下,转过身大踏步地朝残云方向而去,我拼命地奔跑追赶着阿爸,不停地喊着阿爸,阿爸……在我的脑子里虽然还有上次阿爸归家时我每晚睡在他的怀抱里的记忆,但现在当我真真切切地站在阿爸跟前时,却对阿爸产生了陌生感。阿爸张开双臂喊道:“我娒儿长这么高啦,阿爸抱不动喽……”阿爸狠劲把我抱了起来,朗声笑道:“小子够沉的,快让阿爸扎扎小脸蛋儿……”
阿爸这次归家比上次风光多了,只要阿爸出现在田间村头就会有不少人簇拥在他身边说这问那的。大队张支书还亲自登门请阿爸喝酒。支书叮嘱我和阿妈一起陪阿爸去他家里吃顿晚饭。阿妈不愿去支书家,阿爸只好领着我去,支书眨巴着细眼朝我身后睃,问道:“阿秋怎么没一起来呀?”阿爸說;“我阿爸病了,她得在家做饭伺候,走不出来。”支书失望地说:“都说好的嘛。”
阿爸嘿嘿笑道:“张书记,要不把大欣喊来喝几杯吧,他能喝。”
支书习惯性地眨巴着双眼,半晌才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你俩打小就最好,可他那性子,简直一个猛张飞再世,是个犟牛烈马哩。我本想叫民兵连长也过来,可就在你归家的头天他被大欣用马鞭生生地在脸上给抽出了两道血印子。”
阿爸不解地问道:“为个啥?”
支书一撇嘴说:“还不就为村口张飞庙里的那块破石头嘛,人家为了破个四旧,带人去捣张飞石,可你说说看,他大欣顾自赶他的马车去呗,硬是狗咬老鼠多管闲事,立在庙口阻挡,这不就打斗起来了嘛。若不是我看在咱张姓面子上护着他,他早不知下场如何啦。”
阿爸冷笑一声说:“他反正单个人,身上还有点功夫,谁能绑得了他?”
支书垂着头寻思了一下,抬头说:“大兵,要不你去喊他一声吧,他若来了也好顺便敲敲他,你的话他能听。”
阿爸说:“还是算了吧,我晓得他的犟脾气。”
支书的老婆从灶间端来一盘炖整鸡蹾到桌面上,说:“大兵唉,你别看我这个老公当支书,他就是拿大欣没办法,心里怵他呢!”
支书老婆顶多一米五的个头,圆咕隆咚的身材好像稻桶。支书用厌烦的口气狠劲摆了下手说:“去去去,烂口舌的老娘客,管自烧菜去!”
“稻桶”斜了支书一眼,一声不吭地去灶间忙她的去了。
支书和阿爸对饮的时候,支书说:“大兵啊,你是咱这穷旮旯里第一个在队伍上提干的,你给云石大队的张家人长脸了。在队伍上好好表现,把脚跟儿站稳了,将来争取弄个营长、团长的干干,也算是光宗耀祖啰。”
阿爸嘿嘿笑道:“我当上排长也算是祖坟冒青烟了,以后归乡来给您当个民兵排长吧。”
支书端起酒杯“吱”的一声嘬了一口酒说:“你说啥呀,我还等着看你明年再升上个连长呢。”
队伍上体谅到阿爸已经两年没有享受假期了,特意给续了假,阿爸在家住了一个多月时间,我每晚睡觉时就钻进阿爸的被窝里听阿爸给我讲故事,阿爸从十大元帅朱德讲起,每晚一个人物,我听着听着便进入了甜美的梦乡。第二天我睁开眼睛时发现阿爸被窝里躺着阿妈。我问阿爸:“晚上我睡在阿爸的被窝里,早上怎么自己睡一条被子啦?”阿爸刮了我一鼻子呵呵笑道:“阿爸会变魔术哩。”
阿爸假期间好几次叫大欣叔来家喝酒。记得大欣叔第一次来喝酒时拎着一只自己打的山麂。阿爸拍了一下大欣叔的肩膀说:“行啊大欣兄弟,还真有两把刷子哩。”
阿爸和大欣叔还有爷爷坐下来喝酒时,阿爸敬了大欣叔一杯酒说:“大欣兄弟,我都听阿秋说了,我当兵这几年家里遇上些急事都多亏你相助。”
阿妈把一盘菜端上饭桌,插话说:“可不是吗,去年小兵半夜里发高烧多亏了大欣赶马车送公社卫生院呢。”
大欣叔把一口酒咽下,说:“说啥子哩,我住得近么不是,就隔一垄田。再说了,你我还有阿秋咱几个从小一块儿长大,你保家卫国去了,家里凑巧有点儿啥事,不就是喊一嗓嘛。快别说这些了,难为情。”
阿爸接着说道:“大欣啊,三年前当兵去的应该是你,接兵的多看好你呀,膀大腰粗的。”
大欣叔说:“当不当兵的没啥,反正我单个人,一人吃饱全家饱。”大欣叔说着敬了我爷爷一杯酒说:“打小也就你们一家老小拿我当人看,单凭这一点我也死认你们一家子哩。”
阿爸和大欣叔正在兴头上,大队张支书嘻嘻笑着进来了,阿爸和爷爷叫支书坐下来一起喝酒。可当支书刚把屁股粘到长条凳上时,大欣叔却一抬屁股要走,怎么拦也拦不住。
阿爸这次归队时我已经会耍赖了,在村口阿爸要坐上大欣叔的马车走,不让阿妈再送了。我哭喊着抱着阿爸的腿死活不肯放他上车。最后还是大欣叔调和,让我和阿妈一起把阿爸送到公社的车站后再坐马车归家。
一路上我依偎在阿爸的怀里,阿爸用他脸腮上的胡碴儿扎我的脸,我宁可让阿爸的胡碴儿扎疼脸也不舍得脱离阿爸的怀抱。
阿爸哄着我说:“小兵,再等不多久阿爸就可以接你和阿妈上部队随军了,那时你和阿爸还有阿妈就天天在一起不分开啦。”
我不解地问阿爸:“阿爸,啥叫随军啊?”阿爸“嗯”了一声说:“就是小兵和阿妈一起上队伍里帮阿爸保卫边疆。”
我又问道:“阿爸还要过多久才归家呀?我要到村口接阿爸。”
阿爸拍了拍我的脸颊说:“快着哩,阿爸明年就归家看小兵,明年你都八岁了,该上学堂了,上学了可不能给阿爸考个大鸭蛋噢。”
我上学堂了。我问阿妈:“阿爸都说好了的,等我上了学阿爸就归家啦。”阿妈说:“你阿爸信上说队伍上任务忙哩,等忙完了就归家陪你。”
村小离村口不远,我经常独自跑到村口,甚至爬到榕树枝上朝远方眺望,期盼着阿爸会突然出现在小路的尽头。
一天下午放学回家,陡然看见家里有两个穿绿軍装的人。我一时兴奋得几乎要脱口喊出“阿爸——”但我定睛一看,这两个人都不是我天天想念的阿爸。两位军人脸色黯淡,支书站在一旁吸着烟,两只细眼不停地眨巴。当时阿妈不在家,支书差人到田里喊回了阿妈。过了好一会儿,其中一位穿四个兜军装的军人才双手握着阿妈的手说:“嫂子,您可要顶住……张大兵同志他壮烈牺牲了……”
阿妈一时间懵着没啥反应,突然地,阿妈尖叫一声道:“同志,你说啥?大兵他,他……”阿妈一下子便瘫软在地上了。那军人解开带来的包袱,捧出阿爸的遗像,包袱里还有一套崭新的绿军装和别的一些遗物。阿妈发疯般地扑到桌面上抱起阿爸的遗像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起来。这时候的我,从疑惑到彻底地明白了阿爸死了,他再也归不来家了,我难过而又绝望地仰起脸放声大哭。
奶奶和爷爷没能承受住打击,卧床不起,没几年就相继离开了人世,奶奶和爷爷过世后阿妈一下子就瘫软了下来。一天傍晚,阿妈支撑不住躺倒在床上,呻吟着叫我快去叫大欣叔。大欣叔一跨进家门就焦急地问阿妈:“阿秋嫂子,你怎么啦?”阿妈说:“是腰,还有肚子一圈都灼灼痛,还全身烫。”大欣叔迟疑了一下,把手掌贴到阿妈的额头上,惊叫道:“喔哟,额头上滚烫,发高烧了。”大欣叔转过头问我:“你姑姑呢?”我结结巴巴地说:“姑姑送那个……那个‘相好的去了。”“相好”是我听阿妈说的,我问过阿妈“相好”就是姑父吗?阿妈笑着说:“现在还不是,以后兴许是。”
大欣叔接着问我:“出去多久了?”
我回答说:“出去好……好长时间啦。”
大欣叔说:“小兵,你沿路往村口方向找找,阿叔这就拉马车过来。”
我一路跑一路喊姑姑,一直跑到村口才看见姑姑和她的“相好”紧挨着站在大榕树下。我喊道:“姑姑,我阿妈肚痛下不了床了,大欣叔叫我喊你快归家。”姑姑“啊”了一声便往家跑。跑到家时,马车已经停在了家门口。大欣叔跟姑姑说:“得送你嫂子上医院。”姑姑说:“大欣哥靠你了。”大欣叔说:“我们快把你嫂子抱上车吧。”姑姑弯下腰试图抱起阿妈,但姑姑如何抱得动阿妈?姑姑的“相好”跟大欣叔说:“大欣哥,还是我俩一起抬嫂子上车吧?”阿妈呻吟说身子动一动更痛,要姑姑慢慢扶她下床。大欣叔想了一下说:“还是我直接抱上车吧,也好少些身子摆动。”大欣叔说着把一只宽阔的手掌伸进阿妈的背脊后,另一只手托起阿妈的双腿,小心地把阿妈抱了起来。大欣叔跟阿妈说:“把我头颈勾牢。”阿妈“哦”了一声,一只胳膊钩住了大欣叔的头颈。
看着大欣叔把阿妈抱上车的情景,我不禁联想起阿爸把灯下纺线的阿妈抱上床的一幕,阿爸抱阿妈的动作和大欣叔的动作一样,只不过那晚的阿妈没有勾住阿爸的头颈,而是在阿爸的怀里嬉笑着拍打阿爸的肩头,嘴里还说娒儿还没困着呢。我在被窝里想阿爸的力气可真大。
姑姑和她的“相好”坐上了车,我也要跟着上车,但姑姑不肯,叫我早点上床困觉,哪也不许去。
随着大欣叔“驾”的一声吆喝,马车便朝前方奔驰而去。我追赶着马车,一直追到村口,才喘着粗气看着马车消失在视线中。
第二天早上我跑到村口,盼望载着阿妈的马车出现在村口。从早上一直等到了中午,终于盼来了马车,我见车上没有阿妈和姑姑,就“哇”的一声哭了,叫道:“我阿妈呢?阿妈呢?”
大欣叔怜惜地搂着我说:“小兵真是个乖娒儿,你阿妈没大事了,是肾里长了块小石头,有你姑姑在县医院陪着,过几天就能归家了。”
我不解地问道:“肾是什么啊?”
大欣叔说:“就是腰呗。医师说是肾结石。”
两天后阿妈和姑姑果真乘大欣叔的马车归家了。第二天下午大欣叔拎来了一只山鸡跟阿妈说:“嫂子,刚打的,吃补。”
阿妈说:“大欣兄弟,这几天可累着你了。晚上留下来一起吃吧。”
大欣叔凝视了阿妈一眼,摆了一下手说:“不了,还有人等着坐车呢。”
大欣叔不肯留下来吃饭使我生出了失落感,我拽住大欣叔的衣襟不想让他走。大欣叔摸摸我的后脑勺说:“阿叔还有事体要做,去找你姑姑归家炖鸡。”
我痴痴地望着大欣叔离去,突然地我想起了阿爸……
姑姑要出嫁了。姑姑出嫁那天,我和一帮孩子跑到村口看迎亲队伍进村,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往村里开,车斗里坐了不少人,姑父穿了身崭新的衣服,胸前戴着大红花坐在拖拉机手的旁边。姑姑那天没坐拖拉机,是坐上大欣叔的马车走的。大欣叔用帆布把车斗包成拱屋,两侧外边贴上大大的红囍字,枣红马的脖颈上系了条红绸带,脖颈下还挂了个响铃铛。枣红马大概也感知到了喜庆,不时仰头“咴咴”叫唤。大欣叔打趣地说:“大妹子坐马轿出嫁喽。”
姑姑上车前把我搂入怀里,一串串泪珠滚落下来。
一天夜晚,黑魆魆的天幕挂着好多星星,我思念阿爸,独自坐到村口大榕树下的石板凳上,四周静谧得只听到蛐蛐的叫声和不远处田间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呱呱蛙叫声,我抬头数着星星,脸上不由自主地淌满了泪水,我哭了好久,直到迷迷糊糊地睡去。睡梦中我似乎听到阿妈和大欣叔在叫唤我,声音是那样遥远。我用力睁开双眼,眼前站着阿妈和大欣叔,大欣叔把我抱起来,然后又弯下腰把我背到了他宽厚的脊背上。大欣叔背着我走,阿妈紧跟在后头。大欣叔侧过脸来说:“小兵啊,阿叔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是个没人管的孤儿,常常半夜里独自哭到鸡叫。你要向你阿爸一样做个硬性人,快快长大也争取到队伍上去。”
那夜大欣叔的话植入了我的心头。
到家后我躺在床上心里很想大欣叔别走,晚上跟我一起睡,我还想从大欣叔的嘴里听到我阿爸从前的好多事。但大欣叔把我放到床上便转身和阿妈对视了一下就走了。
我依赖或者说佩服大欣叔还是从他手里的那根马鞭开始的。我最爱看他手里那根长长的神奇的马鞭在空中闪电般“噼啪”一声脆响,在我眨眼工夫,大欣叔已经“驾”的一声吆喝,那匹枣红色骏马的蹄下即刻尘土飞扬了。大欣叔用他的马鞭抽打过大队民兵连长,还狠狠地抽打过老是眨巴着细眼的大队张支书。支书挨鞭抽是因为他夜里酒后老爱敲我家的门。阿妈终是忍无可忍操起菜刀推门赶跑了他。那天晚上我心惊胆战地听阿妈在床上轻声地抽泣。过了几天,村里便传出支书被大欣叔给抽打的事。据说那天支书要上公社参加紧急会议。大欣叔破天荒地主动请支书乘他的马车去公社,同车的还有民兵连长。马车驾到村口,大欣叔突然勒住了马,一句话不说转身挥起鞭子就朝支书身上抽去。那是夏天,支书身上就穿了件白背心,背脊上顿时就显现出月牙般的红杠。支书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鞭子给抽蒙了,他“哎哟”一声,眼也不眨了,瞪着白多黑少的细眼吼道:“你癫啦?干吗打我?”
大欣叔瞪着一双铜铃眼喝道:“老子今天就是要打你!”大欣叔说着把鞭子朝空中“嗖”地旋了一个圈,照着支书的背脊身又是一鞭子,这回支书不只是“哎哟”了,连“亲娘”都喊出来了,他双手抱着头从马车上滚了下来,一个劲地朝呆若木鸡的民兵连长骂道:“你还是民兵连长吗?你看着老子挨打呀……”
民兵连长哪敢对付大欣叔啊,再说云石村的哪个不晓得大中午的支书作贼般地摸进他的家?而他却在道坦外朝一条摇着尾巴的土狗出气,狠狠地踢了土狗几脚,惊得土狗“汪汪”惨叫几声夹着尾巴跑了。这回他这个民兵连长兴许正在心里偷着乐呢。民兵连长拉了一把大欣叔,劝道:“大欣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别打了。”
大欣叔用胳膊肘撞了一下民兵连长,吼道:“滚一边去,你也不是什么好货,再管闲事老子连你一起打。”
民兵连长觉得自己劝过了就算是尽到责任了,待在一旁不声响了。
大欣叔手中的鞭子“噼噼啪啪”一下又一下地抽在支书的身上。支书在地上滚了几圈,撑起身子踉踉跄跄地跑了,他边跑边嘴硬地威胁大欣叔:“狗生的大欣你等着,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大欣叔叉着腰道:“好啊,老子等着你来收拾。你好生记牢,阿秋是张大兵烈士的老婆,以后再敢起邪念老子就拧下你的狗头当尿盆。”
大欣叔痛打大队支书的事在村里一夜之间传开了,同时也有传言大欣叔要娶我阿妈了,甚至有鼻子有眼地说大欣叔已经和阿妈住一起了。这些事还是多年后听姑姑跟我说的。
一天下午,大欣叔突然来我家和我阿妈说:“阿秋,我要离开云石去外地了,想必那条老狗再不敢欺骚你了。”
阿妈从水缸里舀了半瓢清水递给大欣叔说:“忒久不见你人影儿,这一见着就说要走,走哪去?非得走吗?走多久?”
大欣叔把半瓢水“咕噜”几下喝了,一抹嘴说:“我师父年老了,我去陪伴他。”阿妈“哦”了一声没再言语。
大欣叔又说:“我走以后若能赚点钱会寄点来,家里万一有个要紧事,特别是那条骚狗再敢欺侮你,你就照信上的地址给我写信,我马上回来。”
阿妈说:“不用寄钱,我和小兵能吃饱穿暖。”
大欣叔摸一下我的头说:“好好读书,听阿妈话,阿叔还会归来的。”大欣叔说完便转身走了。
我跟着阿妈走到道坦外,看着大欣叔上了马车,一甩鞭,“驾”的一声远去了。我回过身来,却见阿妈早已把身子背了过去。
一天晚上阿妈在床头上为我扇蒲扇,我问阿妈:“阿妈,大欣叔为什么要离开云石村呢?我听别人说他跟神仙一样神出鬼没的,他是神仙吗?”
阿妈说:“你大欣叔是个怪人哩,他十多岁时在村里突然不见人影了,谁也不知道他是去哪儿啦,还以为他死了呢。”
我问阿妈:“是大欣叔不想看见村里人吗?”
阿妈用蒲扇驱赶蚊虫,说:“你还小不懂,你阿爸兴许知道哩……”
我眨巴着眼睛问道:“等我长大以后就懂了吗?”
阿妈说:“等你长大后自己问吧。”过了一会儿阿妈接着说:“阿妈从前管你阿爸叫阿哥,你阿爸也是阿妹阿妹地叫着,一家人,亲兄妹一样的。”
阿妈说到这儿微微地笑了,又接着说:“阿妈和你阿爸还有大欣叔一起玩的时候你阿爸还叫大欣叔长大后当他妹夫呢。等到长大后阿妈和你阿爸正式定了亲,你大欣叔才赶着马车突然归回来了,他跟大师学了一身功夫,你阿爸说他学的是鞭拳。”
我好奇地问阿妈:“那大欣叔会飞檐走壁吗?他的鞭子会把天上飞的山雀抽下来吗?”
阿妈说:“大欣叔打鞭拳时不让人看,只有你阿爸看见过,村里的坏人都怵他的鞭子哩。”
我问阿妈:“支书是坏人吗?还有民兵连长也是坏人吗?”
阿妈没有声响。我接着问道:“阿妈你也是孤儿吗?”
阿妈问我:“听谁说的?”
我说:“听姑姑说的。”
阿妈叹口气说:“阿妈是外乡人,六七岁的时候跟着我阿妈,也就是你外婆一路讨饭到云石村,这儿的冬天寻常不下雪,可那天傍晚下了好大的雪,我和你外婆在雪地里又冷又饿直打哆嗦,你好心的爷爷奶奶让阿妈和你外婆进了屋。那天晚上你外婆刚吃了碗半饱的饭就咽气了。”
我“哦”了一声说:“阿妈从那天起就有了新的阿爸阿妈了吗?”
阿妈说:“是的呀,否则哪有现在的你哩。”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阿妈:“大欣叔没有老婆吗?他有娒儿吗?”
阿妈把蒲扇朝我额头上一拍说:“傻娒儿,大欣叔没老婆哪来的娒儿呀?”
我说:“阿妈,那我当他娒儿好吗?”
阿妈停歇了手里摇动的蒲扇,说:“夜迟了,早点困觉吧……”
我长到十六岁的时候没书读了,就一门心思想去当兵。我听说姑父跟公社武装部长是亲戚,便去找姑父帮忙。姑父把我领进武装部长办公室,部长把头摇成货郎鼓一样,冲着我说:“这我可做不了主,小兵你才十六岁不够条件,再说你当兵去了,留下你阿妈一人谁照应?听说你阿妈身体一直不大好。”
部长那儿说不通,回家后我不肯吃饭。阿妈叹息道:“你大欣叔这一走好几年了,要不写封信试试能不能联系上,他能有办法。”
我找出纸笔,阿妈口述道:“大欣兄弟,小兵想去当兵,你归来吧。”我写完信便一路小跑到公社把信封塞进了邮筒。
没过几天大欣叔像是天上掉下来一样地突然推门进家来了。大欣叔开口便问道:“小兵想去当兵吗?”
我浑身一下子来了劲,从床沿上倏地站起身说:“大欣叔,你以前跟我说过长大后到队伍上去,现在我不读书了,我想去当兵,我要接我阿爸的班,可是公社武装部不同意。”
大欣叔说:“走,上马车,阿叔这就带你去县武装部,我给他们赶过车,人头熟。”
县武装部负责征兵工作的王科长知道了我是张大兵烈士的儿子,很热情地叫我归家等通知,他们研究一下再说。
过了几天王科长亲自带着公社武装部长登门来了,是大欣叔给引进门的。王科长说主要是来看望烈士亲属,也想听听我阿妈对我当兵的想法和态度。
阿妈说:“小兵长大了,我支持他的志愿。”
王科长说:“小兵一走,家里就剩下你一人了,万一有个啥事……”
我不假思索地打断王科长的话说:“没有关系的,有大欣叔呢,他很热心常帮助我们家。”
大欣叔只是憨憨地笑着。
阿妈说:“村里的邻舍亲戚都热心着呢。再说我还不到四十岁,又没啥大毛病,你们就让小兵当兵去吧。”
王科长扫视了我们几个一眼,“嘿嘿”笑了几声说:“我有数了,小兵年龄的事我跟接兵部队商议一下,烈士的后代么,只要体检过关尽量特批吧。”
我如愿以偿当上了兵。离家的头天晚上姑姑和姑父带着五六岁大的宝贝囡儿妞妞来了,大欣叔也来了。
我从身后托起表妹妞妞旋着圈圈,妞妞欢快地笑着。我放下妞妞时脑子有点儿晕眩,妞妞稚嫩的脸蛋在我眼前晃悠,我忽然地就想起了阿爸的络腮胡子,心头酸了一下,我下意识地摸一把自己光滑的脸腮,朝妞妞说:“来,妞妞,让阿哥亲一口你的小脸蛋……”
大家吃过晚饭,我乘着酒兴叫大欣叔到道坦上给大家打一通鞭拳看看。大欣叔饭桌上喝了不少酒,甩了句“稍候”,便飞一般地离去了。不多时大欣叔就手捏马鞭站在道坦上喊:“小兵,都出来吧。”
待大家都出了屋,大欣叔扎下马步“嗨”了一声,便把手里的长鞭旋到了空中,随着“嗖嗖”的凛冽之声,便闻“啪”的一声脆响。大欣叔收回马鞭作了个揖说:“所谓鞭拳是误传,我打的是醉鞭,也叫‘双龙起舞。”
大欣叔说完便腾空而起,在空中飞旋了几个圈,双脚落地之际,他把马鞭抛向了空中,旋即将两只手掌往道坦上的一株大樟树的躯干上奋力一推,树上的枝叶一阵簌簌声。枝叶抖颠之间,马鞭已从空中坠落挂在了树枝上,大欣叔身轻如燕,跃身摘鞭。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连声叫好。
姑父惊异道:“这功夫就是传说中的‘鬼撞墙吗?这双掌要是打到土墙上墙都得半倒。”
我也跟着赞叹道:“太厉害了,功夫赛过了猛张飞。”
我叫喊的嘴巴还没闭上,马鞭已“嗖”地掠过了我的嘴唇,我吓了一跳,赶紧把头一歪。大欣叔哈哈一笑道:“抽不到你脸上,举起右手来。”
我乖乖地把右手举了起来。大欣叔惦脚旋转了几圈,待他停脚之时,我的右胳膊上已被细长的马鞭给裹住了。大欣叔喊了一句“挪脚”,我便被马鞭给拽到了阿妈怀里了。
看傻了眼的姑父“啧啧”了一阵后说:“小兵躲进阿妈的怀里了,这回有个照相机就好了。”
姑姑推了一下姑父说:“就门口这盏昏黄的电灯泡有照相机能有啥用?”
阿妈笑着说:“好啦好啦,屋外冷呢,都快进屋吧。”
大家正欲转身进屋时,大欣叔喊道:“这里看。”只见大欣叔从腰间抽出另一根细鞭,大声道:“且看‘双龙起舞。”
话音未落,大欣叔已旋风般地在地上翻起了筋斗,两条马鞭神奇地变幻出两个滚动的好似铁环的圆圈。大家正在“啧啧”惊叹时,却见两鞭已收圈升空,两鞭在空中弓弓直直,飘飘忽忽,缠缠绕绕又若隐若现。更为神奇的是,随着大欣叔一声:“听响”,捏在他左手的先前从腰间抽出的那根细鞭竟然在空中舒展团缩之间炸出了好似点燃的排子炮一般的“噼啪”连响,而且有炫目的火花闪烁。大家都好生惊讶,妞妞还用小手捂住了耳朵。我问大欣叔鞭子怎么会放鞭炮闪火星呢?阿妈笑着说道:“小兵啊,一定是你大欣叔事先在鞭子上涂上带响的火药了呗。”
大欣叔哈哈笑道:“还是阿秋嫂子厉害,一眼看穿了。”
晚上闹腾得迟了,送走姑姑一家后阿欣叔也要归自己的家去了,大欣叔离开前从裤兜里掏出十元钱塞我手里,说:“拿着。明一早阿叔就拉车过来。”阿妈站在一旁啥话没说,目送阿欣叔走了。
第二天清晨,有些甜味的雾霭笼罩着云石村,大欣叔早早地把马车歇在我家的道坦外,村前屋后的邻舍和亲戚都过来相送。我扶阿妈坐上马车。这时支书跑过来朝阿欣叔嚷道:“大欣,大队已经安排了锣鼓队和拖拉机,干吗坐你的马车呀?小兵,快扶你阿妈下来去大队部。”
我瞟了一眼大欣叔,大欣叔好像什么也没听见,看都不看支书一眼,管自一屁股坐到了驾座上。
阿妈坐在车上挽着我的胳膊一动不动。大欣叔回头喊了一声“坐稳啰——”,便把马鞭朝空中“嗖”地一甩,随即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我看见支书一双细眼狠劲地眨巴了一下,把脑袋往肩膀里一缩。
马车快奔到村口时,我见阿妈的眼圈泛红了,我挽着阿妈胳膊说:“阿妈,我一到队伍上就给您写信。”
阿妈抬起衣襟擦了下眼角,说:“那年你阿爸离家时阿妈正怀着你呢,阿妈送你阿爸到村口也是坐的大欣叔的马车,阿妈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驾辕的是一匹雪白的马。唉,你阿爸他怎么就归不来了呢……”阿妈说着突然叫大欣叔停车。大欣叔“吁”的一声勒住了马。
阿妈下了车,朝我摆了摆手说:“小兵长大了,自己到县上找队伍去吧,阿妈就送到村口了。”
大欣叔回过头说:“不碍事哩,送小兵去了县武装部你再坐马车归家嘛。”
阿妈说:“不用啦,你们走吧。”
马车“吱呀”一声缓慢地朝前方而去,此时太阳已经驱散了雾霭,我目不转睛地望着阿妈。我朝阿妈挥动着手,阿妈也挥动着手,我双眼模糊,看着阿妈单薄的身影越变越小……
我不晓得,阿妈为何只肯送我到村口。
在我当兵的第二年的一天,收到阿妈的一封来信,信里告诉我大欣叔在山崖上为阿妈采草药时摔死了。我心头猛地一沉,这怎么可能呢?大欣叔可是狩猎好手,一身的功夫啊,怎么会摔死呢?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我怀疑我是看花了眼,便睁大双眼把信又看了一遍,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滴滴答答掉落在信纸上……
无字信
孙女小ㄚ要去省城上大学了,临行前我和老伴弄了一桌菜,还包了三鲜馅的饺子,叫孙女和她爸妈一起来家吃顿饭。
在饭桌上孙女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突然问我:“爷爷,听我爸说奶奶从前是从很远的北方嫁过来的,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吧,爷爷您今天高兴,说点给小丫听听好吗?”
孙女长大成人了,考上了重点大学,我这个当爷爷的自然是乐不可支了。我呷了一口酒说:“小丫,你奶奶当年是回家呵。不过爷爷是有谋略的,你奶奶就乖乖地上钩了,哈哈……”
老伴一旁白了我一眼说:“小丫,你爷爷喝多了,别听他瞎掰……”
孙女摇着我的胳膊说:“爷爷快讲嘛,小丫爱听……”
“好,好,爷爷讲,爷爷这就讲给小丫听……”我对孙女讲述的“恋爱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当年,我在驻扎在北疆的铁道兵某工程连当通讯员。当通讯员远没有干体力活的战士辛苦,但责任挺大的,平时要服务好连长和指导员不说,每天得按时吹几次口哨是不能耽误的,比如起床、熄灯、出操、开饭、出工、收工、集合(包括紧急集合)等等都是靠我吹口哨通知的。连里有武器弹药,平常一般都分锁进两间屋子里,门钥匙由我保管。因此,在我的腰间上总是须臾不离地挂着钥匙串和一支口哨。
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日中午,我向连长请了假,与战友结伴到营区外寄信购物。边陲小镇上有一条两百来米长的水泥路,路上行人稀少,偶尔可见往返的马车或自行车。马路一侧有一家邮电所和一间小饭馆,距离小饭馆不远还有一家百货商店。我掀开门帘走进商店打算买两包香烟,就在我靠近柜台时,发现售货员是一个年轻白净的姑娘,我惊异在这北疆边陲居然会有这么个白皙的姑娘。姑娘穿一件白大褂,高挺的鼻梁,一双明净的大眼睛忽闪着羞态。我的双眼一愣又一亮,努力想象着眼前的姑娘像谁?像小常宝还是李铁梅呢?嗯,小常宝和李铁梅哪有眼前这位姑娘漂亮!后来看越剧《红楼梦》,我猛然觉得她像极了林黛玉。
正在我发呆的时候,姑娘微笑着问我:“解放军同志,想买啥?”
我“噢”了一声反应过来,说:“我想买……噢,我想买两包红梅牌香烟。”
买了香烟我像丢了魂似的随在几个战友的屁股后头离开了商店。一个战友回过头打趣说:“春阳,刚才看见那个女售货员两眼都发直了,现在连腿都迈不动了,不会是一见钟情吧?”
另一个战友则哈哈笑道:“一见钟情应该是双方的事吧,春阳这一出顶多算是单相思或者叫暗恋。”
我羞红了脸一拳头擂到战友的肩膀上。
打那以后我还真的常常问自己是不是患上了单相思啦?因为她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老也走不开。我只要有上街的机会,都会不由自主地拐进商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看看柜台里的货物,再尽量掏出点零钱买点儿什么。
有一回我陪战友去商店,那天我兜里没钱,但我很想借买点儿东西的机会能与姑娘说上几句话,哪怕就一两句也行。比如听到姑娘糯糯地问:“解放军同志,您买啥?”然后我正儿八经地回答说:“买一包烟。”接着我会听到她问:“要啥牌子的?”我就很自然地告诉她我要“红梅”或者“五一”。当我盯着她那纤细的手把香烟递到我手上时,我会礼貌地说一声“谢谢”。如此这般,我就会升腾起一股满足感。
那天我虽然兜里没钱,却跟战友要了两分钱,磨蹭到姑娘面前说:“我买一盒火柴。”
柜台内的姑娘看了我一眼说:“这回买火柴啦?”
我撇撇嘴说:“烟还没抽完呢。”
姑娘把一盒火柴递给我,说了一句:“烟抽多了不好。”
姑娘随口说的一句话,却让我有了一种暖暖的感觉,而且让我记住了一辈子。
有一个周日我和嘲笑我“单相思”的战友一起去商店,却没看见姑娘。我悄声问战友:“怎没看见她?她怎么会不在呢?”
战友“哧哧”笑道:“你真的单相思啦?暗恋的滋味可不好受哟,得,我替你问问看。”
战友问了柜台内的一位中年女售货员。她看一眼战友说:“哦,问春燕吗?她病啦。”
她叫春燕?她生病啦?什么病?要紧不要紧?在医院里还是在家里?所有这些疑问我都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但是,我怎么可以追问呢?凭什么?别人会怎么想呢?
大概战友怕我真的会傻傻地追问这位售货员,便扯住我的手臂离开了商店。
苦苦等到了下一个周日,一直到下午才请出假,我飞奔到商店。当我掀开门帘,便一眼望见了站在柜台内的春燕姑娘,压在我心头的一块石头一下子落了地。我走到柜台前贸然地问了一句:“听说你生病啦?”
春燕讶异地望着我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生病了?”
我支支吾吾地掩饰道:“是上次来店里买香烟无意间听另一个售货员说的。”
春燕微笑了一下,说:“哦,也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已经好了。”
春燕说完话还轻轻咳嗽了几声,我的心头也随之揪了一下。
自从听了春燕随口说的一句“烟抽多了不好”的话,我还真想下决心把烟戒了,但我转念又想,我若把烟戒了还有什么理由去商店呢?纸笔这些连部就有,水果罐头连里有分配。说到底,除了买几包香烟,这商店的其他物品还真没有我所需要的。最终我还是给自己找出了不彻底戒烟的理由,因为春燕说的是“烟抽多了不好”,那也就是说少抽点并非不好,于是我就由原来一周抽三四包烟减量为一周顶多抽两包烟了。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我还依旧有请假外出时可以拐进商店的“理由”。
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连长叫我去商店替他买一条香烟,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特殊”任务。这是我第一次在商店买一整条香烟。春燕觉得有点意外,半开玩笑地说:“这回买一整条哇,加津贴费啦?”
我摸一下后脑勺说:“这回是替连长买的。你说过的,烟抽多了不好,所以我现在只是偶尔抽一抽。”
春燕露出了她那特有的微笑,有些腼腆到底说:“哦,我不过随口说一下,你记性可真好。”
这一次我们还相互说了不少话,比之前每次来买香烟时的对话加起来还要多。
返回连部我把香烟交给连长,还得意地跟连长讨了一根烟抽。临近开晚饭的时候,我摸挂在腰间的哨子时才猛然发现腰间的钥匙串不见了。这真是非同小可了,房间里锁着的可是真枪实弹啊。我冒出了一身冷汗,胡乱地吹了几声开饭哨,连饭也顾不得吃,便朝商店跑,但愿钥匙是落在了商店里。
一口气跑到商店门口时,天色已经灰蒙蒙的了。雪花无声地飘落,寒风刮在脸上生痛生痛的。我在商店门口不由得“啊”了一声,商店的门已经挂上锁了。我只好对自己说,算了吧,回去再找找,找不到就明天再说吧。
“你来找钥匙的吧?”我的身后冷不丁传来了春燕的声音。
我转身惊喜道:“是呀,是呀,钥匙果真落你这儿啦?”
春燕把捏在手指间的钥匙串甩了一下,走到我跟前。她把钥匙串递到我伸出的手掌里,说:“钥匙是掉在柜台外的地上了,也怪我太粗心了。”
明明是我自己粗心大意,她倒自责了,我撇了撇嘴说:“春燕,该说粗心的是我,害得你大雪天里等我。”
春燕说:“这没啥,我估计会是你掉的,这儿的人一般不挂钥匙串。”
我把钥匙串挂到腰间的皮带上,笑着说了声“谢谢你”,但我又觉得单单说声谢谢还不够,便又正正规规地朝春燕敬了个军礼。春燕见我朝她敬礼,咯咯地笑出了声,说:“我家就在附近不远,要不先到我家烤烤火再走?”
我这时的心情可以用“激动”来形容。真想不到春燕会主动邀请我去她家烤火。我已经无数次地猜想过她家在哪里,她有几个兄弟姐妹,她爸妈是干什么的……今晚虽然意外地获得了被邀请的惊喜,但有军纪框着我,何况我是偷着跑出来的,我必须得迅速归队。我嚅嗫道:“我得赶紧回去,马上又要到吹哨时间了。”
春燕把垂下的两只手握在一起,略弯一下腰说:“哦,路上小心,再见。”
这次以后,便难得再遇到被邀请的理由和机会了。而且,我自己也丧失了再去商店见她的勇气。
就在这次被邀请之后不久,我擦枪时不小心走了火,一颗子弹在我的左脸颊上划过,淌了一地的血,挨了个处分不说,还在脸颊上留下了一道显眼的疤痕。我没有勇气再去商店让她看见我这张破了相的脸。苦闷得我也顾不上“烟抽多了不好”了,每月发的津贴费一多半都抽了“闷烟”了。过了好久,我叫嘲笑我“单相思”的战友外出时顺便给我带条香烟。战友回来后跟我说:“喂,你暗恋的那个梦中情人想你了。”
我瞪了战友一眼说:“你瞎扯啥呀,哪来的梦中情人。”
战友嘿嘿笑道:“真的呐,我买烟时她问起过你,说你为啥好久没来买烟了。表面上看好像是随口问问的样子,但我感觉她那是假装的,她心里肯定有你了,嗯……她这不是想念你了又是什么呢?哈哈……”
“去去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虽然嘴里骂战友,但我实在太想听到战友告诉我的这些事了。
当完三年兵我要退伍回乡了。越是临近退伍,我越是心神不定。我至少设想了一百种办法想试探她心里究竟有没有那个“意思”,哪怕只是一点点,不过,我的每一个设想都被我自己给否定了。毕竟我跟她只是一般的熟人关系,相互之间的情况也不了解,我回家后与她又是天南海北相距遥远,更何况我还是一个破了相的人。单相思或者说暗恋会使人不知所措但也往往会使人生发出胆量和勇气,胆量和勇气终于在我的心头占了上风,我不再纠结犹豫,打算在离队前去商店,借故买一条香烟,然后“顺手”给她留下一封信。说是一封信,其实是在信封里面装了一张空白的信纸,是一封“无字信”,说白了就是想试探一下她。那天我去商店穿的是已经摘了领章的绿军装,春燕看见我很意外,问我:“大半年没见你来买烟了,你,要退伍啦?”
我不自信地把左脸颊偏离她的视线,说:“是的,明天一早就要回家乡暖州了。”我这么说着却在心里头想,你大半年没看见我了,可我却看见过你好多次了呢。这大半年来我和战友来商店都是托战友进去替我买几包香烟,而我则站在门外透过门帘目不转睛地偷看你呢。
春燕“哦”了一声,自言自语道:“你是暖州人啊,江南暖州,小桥流水,鸟语花香……”
我问道:“你知道暖州?去过?”
春燕微微点了点头,说:“我们是老乡呢。”
一听春燕说是老乡,我陡然打起了精神,连声说道:“这太巧了,太巧了……”我紧接着就想问她家是在暖州什么地方?如果她愿意回答的话我还会一个劲地追问她为何会来到北疆这么偏远的地方?多大时来的?老家还有什么人?想不想吃老家的鱼丸和鱼饼?还有麦饼、灯盏糕……
但春燕显得很平静,还没等我问她,她突然注意到我左脸颊上的疤痕了,惊奇地问道:“你的脸……怎么了?”
我用无所谓的口气说:“没啥,被子弹划了一道沟沟‘留作纪念。”
“哎哟,人没事就好。”春燕仔细看了我左脸颊一眼,竟然微笑了一下说,“有点像电影里的蒙面大侠佐罗呢。”
我不由得摸了一下脸上的疤痕,跟着笑道:“是吗?你也看过佐罗电影?我们部队刚放过。”
春燕说:“前几天结伴去县城影院看的,外国拍的电影就是好看。”
我当着春燕的面划燃火柴给自己点了一支烟,其实就是给自己壮个胆,然后把裤兜里的信封掏出来放到了柜台上,说:“信封上写着我家的地址和我的姓名。如果你能给我回封信……”
春燕看了我一眼,似乎没啥反应,也没有马上把信封收起的意思。
我不好意思再往下说“如果”之后的话了,欲言又止地转身离开了商店。
退伍回家后我整日里猜想着春燕看到这封“无字信”后会是什么感觉,她会觉得莫名其妙吗?会生气吗?或者,会高兴吗?也许,也许她连看都不看一眼就把信封扔进了垃圾桶里了。万事皆有可能啊,当然,我跟自己说的最多的还是:树立信心别失望,春燕一定会来信的。
我每天掐着手指头算日子,终于,大约在一个半月之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北疆的信,是春燕寄来的。
我急切而又小心翼翼地拆开封口,信里只有三行秀丽的钢笔字,就写在我留给她的那张空白信纸上——
“春阳老乡:我就在你留给我的空白信纸上写上几个字吧。祝你心想事成,早日参加地方工作。希望有朝一日有缘在老家见到你。春雁。”
我感到好奇,女孩子的名字怎么会取个雁字呢?我还一直以为是燕子的燕呢。不过这对我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给我来信了,而且我因此也就有了给她回信的理由。
我立即动手给她写回信,但我寻思许久,还是就着这张信纸写了几行字:“春雁:我一直以为你叫春燕呢。你的来信让我兴奋得睡不着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缘在暖州相见的。盼来信。春阳。”
信寄出去未出半个月就收到春雁的回信了,这回写了一大段。她在信里告诉我她早前确实叫春燕,随父母到了北疆后改名叫春雁的。她还交代我有空可以去城西街N号看看她家的两间祖传老屋,政府已经落实政策归还老屋,并且她的父亲已摘帽平反,很快就要归乡了。
原来春雁还是正宗的暖州城里人呢,而我只是半个暖州人,父亲是随大军南下,在暖州娶了亲,然后有了我。
看完信后我马上找出纸和笔,写了一张又一张回信,但都被我揉成团扔进了废纸篓里。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表达我的特殊而又微妙的心情。我最终还是在那张尚未写满的信纸的下端用钢笔规规整整地写下了几个字:“春雁:破了相的佐罗可以做你的男朋友吗?春阳。”
这封信寄出去后几个月未见春雁来信。我揪着的心一直宽松不下来,成天叹息道:“完啦,冒犯她了,她不理我啦……”
一天中午,我无精打采地倚靠在床头上,突然听到门口有人喊:“春阳,在家吗?”
这不是春雁的声音吗?这细细的糯糯的声音几乎没有一天离开过我的耳鼓。我倏地从床上弹了起来,当我一把推开门时,春雁那早已刻入我脑子里的特有的笑脸真真切切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喊了一声“春雁”,说道:“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了……”
春雁说:“雁南归,回家了。”
我想伸手拉春雁进家,但伸出去的手半道上又收了回来,此刻的我却又偏偏不好意思碰触到她了。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明白了,怪不得你把自己的名字改叫春雁呢,雁南飞,回家,飞回家了……”
春雁进屋后就问我:“还抽烟吗?”
我回答说:“烟抽多了不好,偶尔抽抽。”
春雁听我这么说会意地笑了,说:“我爸老学究,就是那类不被待见的‘臭老九,他抽烟可厉害了,我妈和我就常劝他说烟抽多了不好。所以我那天对你无心地说了句习惯话。”
春雁说着把随手拎的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条大前门香烟递给我说:“我爸把烟戒了,这是他还没抽完的一条烟,送给你吧。”
我说:“那我也彻底戒烟,这条香烟就留着做个纪念吧。”
春雁“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说:“香烟放久了可要发霉的呀,你以为是古董啊……”
我的脸红到了耳根,也跟着“哧哧”笑了几声,说:“那我就慢慢抽,啊不,抓紧抽,抽完了就戒烟。”
我俩在一起不知不觉说了许多话。春雁从椅子上站起身,说:“我得走了。我随身带来了给你的回信。”
当她把信封塞进我手里时羞赧地说:“等我走了以后再打开。”
我点了点头,说:“那我送你回家吧。”
春雁说:“不用,我要去一个同学家,约好的。”
待春雁的背影从眼前消失后我急忙从信封里抽出信纸,还是原来那张已经差不多写满了的信纸。在信纸底端的空白处,也就是在我写的“破了相的佐罗可以做你的男朋友吗?”的下面跟进了两个秀丽的钢笔字:“可以。”
孙女托着下巴入神地听完了我讲的“爱情故事”,眨巴着眼睛说:“爷爷,奶奶,你们那一代人原来那么罗曼蒂克呀,那封信呢?还在吗?”
没等我回答孙女的问话,老伴在一旁插话道:“我们这一代人恋爱时知道害羞,话说一半。”
李世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政协报》《文艺报》《天津文学》《江南》《山西文学》《小说选刊》《海外文摘》《西湖》《文学港》《啄木鸟》《微型小说》《中国作家网》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共计一百多万字。已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四部。
责任编辑: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