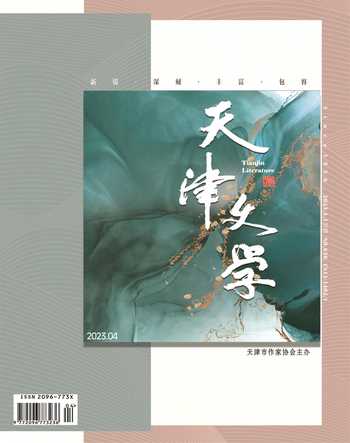制造陶渊明
栏目题解:唐传奇《古镜记》里写过一只神奇的镜子,能照出美女的原型是狐狸还是黄鼬。古代关于镜子的故事,是在完成现实生活中难以达成的愿望——照见对镜之人的本质。史传也曾被当作一面镜子:通过收集、整理、编排零散的材料,寻找过去事情变化的规律,成为未来的行为指引。在镜中反复观看、对比、自检,对镜之人假设自己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洞察力。再现一个古人的行止、思想、日常生活,观察一个遥远模糊的背影,真的能够在镜子呈现的无数面貌中分辨本质吗?
“获得关于一个人的清晰轮廓”是传记读者最基础的要求。可是,我们常常忽略被传记作者作为作品严肃性标志的“史料”也是一种完工之后的“历史叙事”。比如盖房子,我们常常以为的砖瓦,实际上是完成的房屋,而这间房屋的朝向决定于“史观”,梁柱则是“叙事方式”。不如试试拆掉依照“叙事方式”搭建好的积木(无论是故事的,还是史传的),去看看内部的样子。
陶渊明的诗怎样开始最初的流传始终是个谜。
有一种广为传播的都市传说——身前籍籍无名的作者死后忽然举世皆珍,以此来说明好作品的绝对审美价值,好像专门讲来鼓励郁郁不得志的作者。冷酷的是,文本的传播与保存的真相要扫兴得多。与我们的“常识”相反,一直到明末书籍生产最普遍的方式还是抄写,而非我们在教科书里读到的印刷。没有机器复制的时代,一个文本想被稳定地收藏留存,或者在藏书家之间抄写流传,或者是被官方持续不断地列为“必读”正典,成为考试的教材,因而被大规模地阅读。
陶渊明好像哪条都不沾。
比起他那些一边写着“狂歌五柳前”,大喊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边“奉和”“奉御”诗写了一堆,争相成为皇帝贵族酒宴座上宾的后辈,陶渊明对自己的观察过分诚实:“孤介”“贞刚”“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与子俨等疏》)。
在他的时代,陶渊明稍微有一点儿名声,地方性的,贵宾来了会被叫出去喝酒奉陪写诗助兴的那种。写过几首应酬诗,写得不错,但他既没有因此获得亨通官运,也没有因为无缘拔擢而失落。江州刺史王弘想要结识,陶渊明不理睬。多少说些心里话的诗篇里,讲他访友宴游的那些,写给庞参军、刘柴桑、郭主簿……“参军”“主簿”,姓庞,姓郭,连全名都没有留下来。“向上社交”这项技能,陶渊明零分。陶渊明死后,颜延之为他写诔文,明白说了:人的本性是“随踵而立”,因此,拒绝“向上社交”之人的下场是“菁华隐没,芳流歇绝”(颜延之作《陶征士诔并序》)。
既然话说到这分上,我猜颜延之做过一些让陶渊明的文集保存、流传的努力。在私人出版兴起之前,国家最大的出版商在秘书省(国家图书馆)和国子监(中央大学)。国子监负责抄印发行教科书,秘书省负责审查、收藏、销毁古往今来的文字作品。颜延之先后做过国子祭酒(中央大学校长)和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虽然如今声名不显,在南朝刘宋时代的数十年间,颜延之曾经同时掌握过官方的文化圈和知识圈影响力。他的朋友鲍照写过一首《学陶彭泽体奉和王义兴》,这是一个模仿陶渊明写诗的文字游戏,与鲍照一起玩的这位“王义兴”是王弘(就是那个陶渊明在江州时候爱理不理的上司)的小儿子,也是颜延之的朋友。也许就是因为颜延之,陶渊明的作品曾经被送到他们的手上,被诵读、赏玩、模仿。颜延之大概也给谢灵运看过陶渊明的作品,不过谢灵运什么也没说。
我们知道陶渊明去世接近一百年后,梁太子萧统的书桌上至少有两个版本的陶渊明集,以及《宋书·隐逸传》稿本中两千多字关于陶渊明生平的传记。萧统爱陶诗,决定编订一个最完善的《陶渊明集》(这个八卷本的“陶集”是后来我们看见的所有“陶集”的前身)。作为编订陶渊明的文集的配套,他要为陶渊明写作一篇传记。《宋书》主编沈约是萧统的太子少傅,萧统几乎面对着沈约曾经面对的相同材料;沈约又是个以“啰嗦”著名的史学家——《宋书》博通求真,动辄全文收录诏奏文章,是南朝四史中篇幅之最,《陶渊明传》又是《宋书·隐逸传》中最长的一篇……
但萧统依然决定重写。
萧统的《陶渊明传》实际上采纳了大部分沈约使用过的材料,但稍作改写,沈约的“陶渊明”与萧统的“陶渊明”如同折射率不同的两面镜子,映照出相异的神态——
萧统与沈约一样,全文抄录《五柳先生传》作为陶渊明性情的自白。沈约以此作为陶渊明“高趣”的证明;而萧统,尽管他承认陶渊明高逸不群的一面,但儒家的仁德修养依然是其更本质的底色。陶渊明做彭泽令,单身赴任,不过给儿子送去一名仆人,并附书:“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你日常花费,自给为难,如今派此人帮助你。但他也是别人的儿子,请善待他。这是儒家最根本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理。
萧统知道,他无法回避陶诗“篇篇有酒”的事实,但他想强调,酒不过是“志”的寄寓。在开始铺陈陶渊明著名的“琴与酒”的事例之前,萧统加入了一场沈约没有写进《宋书》的谈话。江州刺史檀道济拜访陶渊明,此时陶渊明病卧在床,饥寒困窘。檀道济问他,对于贤者,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仕,如今您生在文明之世,何必自苦如此?陶渊明只说,我不敢与贤人比较,志不在此。
在传记快要结尾时,萧统提到檀道济曾经邀请陶渊明在城中为学生讲《礼记》,顺便校勘。工作条件很滑稽——在马厩隔壁。萧统引用了陶渊明关于此事的一首五言短诗,陶渊明在诗中并没有谴责此举的斯文扫地,他只是做了一个幽默的对比“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
萧统特别把“马队校书”的事例安排在檀道济与陶渊明关于“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对话之后,以此作为对檀道济所谓“文明之世”的无言反讽,完成了对陶渊明“天下无道则隐”的动机塑造。传记最后,萧统再一次强调,陶渊明的妻子“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可是萧统又在前文采纳了陶渊明夫妻吵架的故事:陶渊明做彭泽令时分了地,妻子要种粳米,陶渊明要种高粱米酿酒,闹到最后对半分。
“贞志苦节”是萧统的《陶渊明传》贯穿始终的线索。萧统是品味高明的讀者,但他也有自己的私心。当他举起这面名曰“史传”的镜子去探究陶渊明的生命经验时,镜子里映照出的是在周围窥探的眼色中,萧统作为萧梁权力继承人的自白以及他对于未来臣民的感召:萧统为陶渊明的文集写序,通篇核心是“尚想其德,恨不同时”——对陶渊明道德修养的追慕。
哪怕萧统用漂亮的四六句赞扬陶渊明的文章“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但当他必须要给出热爱的理由时,话锋就转换成了“贞志不休,安道苦节”和“有助风教”。
有趣的是,作为“生育竞赛”的优胜选手,皇储萧统并没有采纳沈约在《宋书》里全文引用的两首“鸡娃”作品——《戒子》和《责子》。按道理,隐士是一种宣扬个人意志的行为艺术,在拒绝社会关系的同时,必然拒绝进入伦理关系的链条。不过,在沈约写进《宋书》的隐者故事里,每一个隐士传记的结尾他都要谈一谈主人公的儿子。沈约一定要告诉读者,这位贤人隐士的儿子最终官至何处。
在沈约这里,做官是代代相传的传统,做隐士只是这个传统里一个叛逆的例外。父亲彻底的醒悟也无法说服儿子,更无法打败读书做官的惯性。作为大家族的子孙,编撰《宋书》之外,沈约热心维持士族与庶族的婚姻隔离,特别弹劾过士族王家与庶族满家的一门婚姻: 当时的士族王源想要把女儿嫁给“士庶莫辨”的满璋之的儿子。因此,哪怕与隐士精神相悖,当沈约举起“隐士”这面镜子的时候,他也无法不反复调整角度,寻找其中一闪而过的父子人伦。
但对于萧统,父子与君臣的重叠让他对父子关系的每一次表述都像别有他意的寓言,而周围总有人在虎视眈眈,时刻不忘添油加醋地“解释”他的一言一行。在《梁书》的萧统传记里我们看见一个聪慧、善良、简朴、孝顺的完人,甚至在他重病快死时依然不忍父亲担忧,隐疾不报。三十一岁时过早到来的死亡为他的完美镀上传奇的光芒。
《南史》在复制了《梁书》塑造的这一完美形象之后,补叙一个故事,揭开作为臣与子的萧统面对“孝顺”的两难:萧统的母亲去世,将要下葬,皇帝身边的宦官为了吃回扣,对皇帝说如今选定的墓址对皇帝不利,不如另换。皇帝为了吉利,选了宦官兜售三百万的新地。结果就是皇帝得到吉利,宦官得到一百万回扣,萧统得到一个仓促改葬的命令。下葬之后,有道士对萧统说新地的选择不够谨慎,对长子不利,可用“厌胜”之术化解。另一边立刻有人将太子“厌胜”之事密告皇帝。《南史》以此作为萧统死后皇太孙没有继位为帝的解释。没有明说的,是一个儿子亦臣亦子时无法兼顾的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进退失据。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有一整段借“陶酒”浇自我块垒的议论:齐讴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骑之荣,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亦随之。
理论上来说,好的诗歌可以掩盖诗人的身世与名字。但在中国古诗的阅读传统里,传记从来是诗篇的影子。诗篇的情感、审美、德性,必须有诗人身世经历的参与才能获得完整的解释。作者和作者所创造的文学角色在读者的眼中高度统一,诗人的传记是完成他的作品的关键一环;相对应的,诗句描绘的情境也必得是作者的身世感怀。一段没有创作背景支撑的诗句不能满足后人要求作者经历与作品互动的愿望,因而无法凝聚词句之外更深远的意义。为了满足这样的愿望,不断有人试图为《古诗十九首》这类作者身世不知的诗歌找到苏武、李陵或者枚乘这些在史传里能够找到曲折身世的作者,他们认为这样的对应更能够彰显“十九首”表现的情感。但最终只能牵强附会,都失败了。
正如萧统和沈约在陶渊明传记中用几乎相同的材料描摹出更符合他们想象的陶渊明一样,早期的四份陶渊明传记(《宋书》,萧统的《陶渊明传》,《南史》和《晋书》)仿佛我们小时候常常去照的哈哈镜,每面镜中的陶渊明都不尽相同。不过,遵照隐士传记书写的传统方式,早期陶渊明的传记作者们依然统合了结构陶渊明传记的关键词——“拒绝”:拒绝做官的机会,拒绝向上社交。有关“拒绝”的事例被连缀起来,表现陶渊明的恬淡任真,高义峻节。
被史传裁剪省略的部分,是晋宋之交,陶渊明敏锐的腾挪辗转:
陶渊明写下“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时,东晋爆发了孙恩之乱。陶渊明的上司北府军将领刘牢之领命平叛,陶渊明离开刘牢之幕府。
刘牢之北府军与孙恩大战时,掌握东晋大半军权的桓玄是最安全的选择。不久,陶渊明转入荆州刺史桓玄幕府。不过陶渊明很快因为母丧去职。
这之后的三年,桓玄打败北府军,夺得东晋政权,逼迫刘牢之自杀,自立为帝,又被复仇的北府军旧将刘裕所杀。陶渊明为母亲服丧,远远旁观了他错身而过的朝廷变乱。
桓玄被杀的这一年,陶渊明写下“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拟古九首》)
晋宋之交的政权翻覆多半起于荆州、江州这些军事重镇,陶渊明生活在江州荆州附近,一直在风暴的中心。很奇怪,向来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传书写里,对陶渊明在晋宋之交间的仕宦经历都含糊其词。出尘忘俗的意志可以解释五次拒绝,却无法解释四次出仕。不过,史传着重描绘“弃官”这个彰显隐士之姿的戏剧动作时,经过深思的材料编织可以让读者忘记探问出仕与弃官之间不断转变的动机。
包括史传在内的传记作者的传统工作方式很像整形医生在顾客脸上动刀——他预想这个人应该拥有的个性、品德,而后在其一生杂芜的经历中选择最能彰显此类特质的事件。在他以强烈的色彩描摹被挑选的事件的同时,剩下的不能圆融地塞进如同乐高玩具一样片片相契的模型中的那些便自动沉入黑暗——这是塑造一个“跃然纸上”的形象最保险的方法。
“获得一个清晰的轮廓”是传记读者最基础的要求。作者显然必须满足这种要求,因而当发现互相排斥的事件、看法、可能性时,任何清楚的表述都会要求一种不再更改的结论,目标在于统合的削删几乎不能避免。
然而,以传记中的真实来对比我们所经历的人生,总有在什么地方显出轻微的不对。“全知的”认识论提供一种过于乐观的想象:读者总假设自己的“后见之明”具有穿透力。因而,已经过去的人与事,每一件都能被完整清晰地调查,人如同实验对象一般提供可被反复证明、毫厘不差的稳定的答案。传记的读者总是忘记,仅是在自己尚不能称之为“遥远”的个人经历中,就已经藏有足够多的“不可调查”了:分手的原因、老板的好恶、老爹老妈究竟为什么缴这么多“智商税”……如果“被记述的人”也拥有人的完整性,那么认识的盲区和不可被调查的部分,哪怕以后见之明,也不能看得更清楚。更何况,人的日常生活中,那些决定性的瞬间几乎总是犬牙交错地镶嵌在毫无意义的、生存性的、技术性的内容里,并不能界限清晰地切割开来。于是别人(甚至自己)回顾平生时总是虚构一场退潮:他虚构出关于“主次”的标准,命令无关紧要的部分潮水般退去,所谓“关键”的部分便水落石出般排列成条理清晰的动线——无论我们怎样保证材料来源的真实和动机的诚恳,当记忆里这场“退潮”发生时,“虚构”便已经开始。
稳定的结论、清晰的轮廓固然重要,但被削去的那些杂芜、模糊,指向另一种可能的碎片是否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假设“再现”是“传记”的目标,“再现”的标准究竟是一种“结案报告”式的唯一,还是证明这种“结案报告”之不可能?
史传作为一种意图展示“事实真相”的“再现”几乎天然地抵触这种“不可能”。阅读历史书写时,我们常常在两种观念之间反复跳跃:“真实客观的正史”和“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两种观念对史传书写都太有信心了:它假设有一个坚固的真相,有待书写者发掘、描摹、还原,整体平移到一个稳定的载体上,可以不被损耗地从此流传,而“对”和“错”全部归因于道德上的诚实与否。
然而面对人的反复、不彻底,人的行为的非理性、动机的暧昧,最正心诚意的史传作者在书写时也必得做出裁断。无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是某人的一生,某事的前因后果,史传作者收集、挑选、裁剪事件,串联成他雄辩的议论时,如同串珠成链,那一条串起珠子的线,始终来源于书写者所在的当下以及他为“再现”所选定的方向。
当然,作为一个有自己声音的作者,传主的作品总被作为他的传记“真实”和“确定”的证据。昆德拉把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掌握叫作“本质性原则”——当一个作者决定停笔(或者因为生命终了不得不停止),不再生产更多的作品的时候,当这个“总结时刻”到来时,那些会被作者首肯为代表了自己的美学规划的工作将会向世人显现一个作家最清晰、稳定、本质的意图。但对于古典作家来说,就连渴求一个稳定、唯一、代表了作者最终意图的文本也显得太奢侈了。世传《陶渊明集》有十几种,中国古文献专家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里收录了最有校勘价值的五个版本(“曾集刻本”“苏写本”“焦竑刻本”“莫友芝刻本”和“陶本”),注出了陶渊明诗在这几个主要版本中的异文。除去文意相近的异文,也有不少南辕北辙的版本:“悠然见南山”与“时时望南山”(《饮酒》),南阳刘子骥对桃花源是“欣然规往”还是“欣然亲往”(《桃花源记》)以及《游斜川》首句究竟是“开岁倏五十”还是“开岁倏五日”……
用文献学的方法,像逯钦立在《陶渊明集》里做的那样:把所有的异文收集起来,包括被作者划掉的句子、丢弃的草稿,后代文学领袖在别人字句里映照的自我,抄工复写时不能理解于是径改的字词……用昆德拉的话说,好像堆积“在一个巨大的公共墓穴中,一切安适美妙平等”。如此是否能还原一个古代诗人在他的“总结时刻”到来时(假设在生命最混乱仓促的结尾他能够有这样一个从容的时刻),所确定的那个最本质的自己?一个趋近理想状态的例子:最在意对作品的绝对统治的白居易晚年用功编订文集,在名山、宝刹和亲戚家里藏了五个副本,如同托孤一般要求亲朋永葆。不过,这几个副本从六十卷到七十五卷,不一而足——当诗人白居易进入这个总结时刻的时候,他依然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自己的结论。
网上曾经有一个热搜,李白《将进酒》的原句究竟是我们在课本里读到的“古来圣贤皆寂寞”,还是一份敦煌卷子上所写的“古来圣贤皆死尽”。论者辩论两者的美学成就,仿佛人人都是面对两份草稿裁决最终定稿的老李白。在这个二选一的问题里,没有给抄写、编辑与流传留下讨论的空间。在没有大规模印刷的世界里,抄写的过程也是文本内容不断被“完善”的过程,最有话语权的读者往往拥有“编辑”的双重身份。做编辑,以自己的学养以及当世的编辑规则赋予文本唯一的“正统”,裁判文本的道德、审美,甚至真伪,这都是权力。孔子编《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不能赞一辞”。
当一个人的某些特质被连缀成他最显眼的人格特点,“不连贯”的那些事迹和语言如同石膏粉墨被凿脱,拥有清晰线条的雕塑才能跃然眼前。可是,每一个编辑想象中的形象又并不相同,因而,意在呈现清晰的雕凿,最后却留下更多的模糊。这在文本上就是所谓的文集版本的“异文”。汲古阁藏的《陶渊明集》是陶渊明文集的一个重要的宋代刻本,其中留下了七百四十多处关于陶渊明文章的“异文”,也就是说,陶渊明的每一篇诗文,平均有六个不同的版本。
时间的消磨,不断地抄写、编辑、改动,作者的本质很难不转变成为最有话语权的那一批编辑的“本质”。苏轼见到的陶渊明《饮酒》,在多个版本中,最流行的版本是“采菊东篱下,时时望南山”。苏轼不能同意,大笔一挥,采纳了“悠然见南山”。没有版本源流的讨论,全靠读者心目中作者的形象——“见”是“境与意会”,“望”则“神气索然”。
我们今天看见的陶渊明,他的诗歌与形象,与其说是他本来的样子(如果还能够被识别的话),不如说是雄辩、有坚定信仰以及强大的编辑能力的一代代读者刀凿斧削后的陶渊明。被编辑“精选”后的“陶诗”,被用来证明陶渊明恬淡任真的个性,而被这样塑造成形的陶渊明居众处默、结志世外的个性又成为削删去取他诗句的证据。无穷无尽的循环。
最喜欢陶渊明的那批作家,欧阳修,苏轼……正是北宋最有话语权的文坛领袖。苏轼从五十七岁开始用同韵同字和陶渊明诗《饮酒二十首》,而后贬谪惠州、儋州,书箱里总带着陶渊明的诗卷。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同题同韵和“陶诗”,写了一百零九篇,编成四卷。他如此执着地在陶渊明的诗句里寻找难以安放的自我,有时候让我怀疑,照镜子的时候,苏轼会不会在镜中看见一张陶渊明的脸。
不意外地,陶渊明在此时成了最重要的古代诗人。胡仔编《苕溪渔隐丛话》,辑录周代到唐之前诗歌的七卷内容中,陶渊明独占三卷。
整合的努力并非止步于文学。从北宋起,绘画表现的题材经历过一轮筛选,去除了六朝至唐代依然能够看见的描绘战争、暴力、神怪故事、日常生活(甚至水磨的运转细节)转向文人诗意,强调与山水相连的超凡脱俗的精神世界。在这场关于题材的拣择中,以陶渊明为题材的画作兴起风靡。在这之前,表现“隐士”的题材是“商山四皓”“竹林七贤”,在这之后,陶渊明和他笔下的“五柳先生”与“桃花源”一道,成为长久流行的一种“类别”。
“陶渊明”成为一种象征,用来收纳人生进取之路上欲望不能满足的不平和怨怼。在元代的宫廷画家何澄和他的同事们那儿,当有高级官员退休,最得体的赠礼是以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为主题的画卷,如同除夕贴春联一样,成为一种应景。画家以及画家们的目标客户们把陶渊明挂在家中,标示恬淡任真的自我,向他人展示自己内在修养的静与定。
当后世介绍起这些有关陶渊明的画作时,总要用力于画家与画中人道德追求的共通。宋徽宗挂名编纂完成于北宋的《宣和画谱》,整理宫廷收藏的历代绘画与名画家源流,其中记载了画家与画中人的第一次互文。唐代郑虔画过一幅《陶潜像》。我们知道郑虔多半因为他有一个差不多穷的朋友杜甫。杜先生又穷又爱写,因而我们知道天宝十三载夏天的水灾中,杜甫和郑虔凑合着赈灾米喝酒的故事。在这首《醉时歌》里,杜甫描述郑虔的居住环境“石田茅屋荒苍苔”几乎是另一个版本“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的五柳先生。杜甫当然认识到这种类似的处境,他敲着碗对郑虔大喊,这个官做得不来赛,“先生早赋《归去来》”——学学陶渊明吧。往后,“学陶渊明”成为自嘲,也成为一种恭维。
言为心声,画为心印。传统画传以此标准寻找画家的个人品德、审美,笔墨风格与题材的相互辉映——这是判断一幅作品的真伪、决定作品价值的方法,也是区别画师与画家的重要标准。“位尊减才,势窘溢价”,画传的叙事逻辑是这样:当画家被描绘成一个拒绝“画师”职业的异类,当他不以画画作为谋生方式,当他成功地成为一个“业余”画家时,他才获得艺术的独立。他的画作,他选择的题材因而成为他道德追求的一部分,相反,画家任何的道德瑕疵也会成为他的笔墨缺陷——比如我们常常听见的,对于赵孟頫与董其昌的批判。
古代“制假团队”最懂艺术品升值的关键。台北故宫有一卷《归去来兮辞》,以画卷展现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意境,托名为李公麟的作品。李公麟是苏轼的朋友,北宋有名的画家。苏轼曾经写诗赞誉李公麟笔下的马寄寓了画家不受羁绊、意在万里的人格追求——“伯时有道真吏隐,饮啄不羡山梁雌。丹青弄笔聊尔耳,意在万里谁知之。”(《次韵子由书李伯时所藏韩干马》)拥有文学领袖首肯过的高尚情操,李公麟对陶渊明的描摹拥有了一种技艺之外的“道德血缘”,因而成为一种市场追逐的流行。李公麟暮年隐居龙眠山,自号“龙眠山人”,以行动次韵了文人心中的陶渊明。“制假团队”给了这卷《归去来兮辞》一个充满了文化圈认同的流传秩序——画卷后伪造了一排名人题跋钤印。通过虚构后代名人赏玩后的留念,聪明的造假团队给这幅画创造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前史”——它曾经被大画家沈度、文徵明展开在他们的书房,被赏玩、认可、膜拜。李公麟以“白描”人物为特点,以至于往后造假画的“团队”,但凡有墨色白描的人物山水画,多半托名李公麟。
明末清初的画家陈洪绶画过《陶渊明故事图》。他的画作最有名的特点是人物衣袂的线条:仿佛用中锋写篆字,拙朴劲硬。在《虢国夫人游春图》这类我们熟悉的宋代人物画里,线条飘逸,衣袂轻柔,仿佛飘飘欲仙,所谓的“吴带当风”。但在陈洪绶的一些人物画中,衣服的线条仿佛黏在人物的身上,很有下坠的“量感”。陈洪绶是明末清初的文人画家,不为清朝做官,因而,他的线条常被用来论证画家宁折不弯的性格。陈洪绶也画版画,他最有名的版画作品《水浒叶子》是画了四十个梁山好汉的一套纸牌。画好了,要刻板印刷复制售卖的。去除对技艺的道德判断,陈洪绶这种独特的线条可能也是为了方便刻版——一个经济的选择。其实,陈洪绶也画蓬松飘逸的线条,在他的《隐居十六观》中有一幅《缥香》,传说是鱼玄机的美人坐在平滑石头上读书,仕女的身旁有一丛竹叶,淡墨晕开,仿佛竹叶在微风中摇晃。在这张《缥香》中,画美人的衣袂、石头和竹叶,陈洪绶运用了多种不同的笔法。然而,这些笔法是无法统一在“宁折不弯”的人物个性之下的。
陈洪绶为他的赞助人周亮工画了十二年“陶渊明系列”(陈洪绶甚至为周亮工绘制一幅肖像,画成陶渊明的样子)。委托创作,自然要考虑雇主的喜好,货银两讫的时间,周亮工与友人宴游西湖,请陈洪绶画画。陈洪绶需要在这十天里,在朝廷官员与他满座宾客享受西湖晴雨时,为他仔细描摹“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
我家有一幅不知道哪来的水墨画,远景是郭熙《早春图》中那种苍莽高山,山下有茅庐、山涧、流水;近景是缓带轻裘的文士策杖行在曲折小桥之上,遥遥相对的是一个抱书小童。这是幅没有标题没有作者的三无画作,但是构图与题材都是传统绘画里常见的“隐士”主题。如果我愿意,也可以叫它“渊明逸兴”——如果陶渊明的形象是一场踩点给分的命题考试的话。
固定的艺术追求和主题观念,可以让不同的素材讲成同一个故事。反复细描一幅素描隐约的线条,会获得确定的轮廓。而后千万张脸在同一种审美标准下变得越来越相似。只是,我们怎样在画布上改变一张脸,但他依然是他自己?当对“本质”的追求,让一张脸被简化成一个符号,“我”不再是“我”的边界在哪里?
唐传奇《古镜记》里写过一只神奇的镜子,能照出美妖女的原型是狐狸还是黄鼬。古代关于镜子的故事,多少是在完成一个现实生活中难以达成的愿望——照见对镜之人的本质。在比喻里,史传被当作一面镜子:通过收集整理编排联零散的材料,寻找过去事情变化的规律,成为未来的行为指引。所谓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在有关镜子的比喻里,它的作用如同取景框,截取某个时空的一面,纤毫毕现,可以反复观看、对比、自检。在这样反复的自检中,对镜之人假设自己获得了一种强大的洞察力。“传记”试图完成的再现,正是对稍纵即逝的镜中影像一再的回顾,仿佛只要凝视够专注,那无法抓住的一瞬间蕴藏的确定本质便能再次浮现。不过,仔细想来,我们在博物馆看见的古代镜子总是背面,背面的镜铭提供一个稳定的故事,至少也是一个拥有稳定寓意的纹样。可是镜子的正面照见的是流动、变化、无法重复的瞬间,自然也无法提供一个确定的本质。
我们总是试图用镜子的背面去替换正面,希望有稳定的事实,坚固的解释,去弥补已经消逝的不可调查,不能检验。如果过去的人生如同我们在史传中看见的那样有线索清晰的可调查性,那么史传的作者理所应当拥有俯视和穿透现实世界的能力。
其实,大家都知道答案:望向镜中,也许见到陌生,见到惊讶,见到流逝,只是无法从中见到期待的清晰。古代居所中,壁、障、屏风,任何可以用来展示主人品位和志向的平面上,主人的选择往往是一幅寓意明确的图画:隐逸者的高山,纵放者的江湖,鹤与松,梅与兰……需要确定,需要清晰,需要提供价值和身份的认同。而他们多半不会选择一面镜子。
北溟鱼,南京人。清华大学哲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人类学硕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律博士。著有《长安客》《在深渊里仰望星空》等。
责任编辑: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