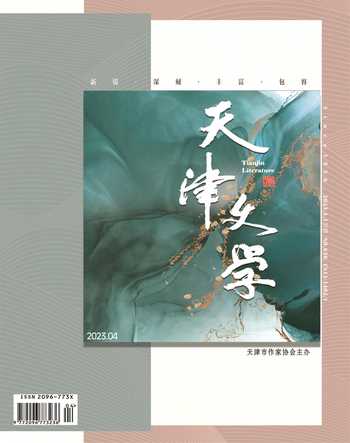川江隐语
吃带头
小时候在姑妈家看杀年猪,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请来的杀猪匠开膛破边时,用铁钩钩住猪肛门,倒挂起来操作。破完边,他不直接取下铁钩,而是连着钩周围的肉一起剜割下来,顺手丢在自己装工具的篮子里。钩上带着一坨肥肉,走时提走了。这番动作在不经意间完成。我问过很多同辈人与长辈,都没留意到这点,可能属于个别杀猪匠的习惯。肥肉拿回家可熬一两钱猪油。腊月里,请杀年猪的人户多,几天下来,得到一斤半斤猪油不成问题。在过去,这是有“油水儿”的事。
猪烫皮刨毛前,杀猪匠要把猪鬃扯下来,这归他,大家都晓得。猪鬃是猪颈背脊上又粗又硬的长毛,供销社门市收购,是制刷子的原材料,加工后出口。“川鬃”质优,远近闻名。民国时期,有外国商人在川江一带开商行,专门做猪鬃生意。猪鬃归属山货行业,其他诸如药材、皮毛、桐油等山货生意,因天时地利变化时而兴衰不定,唯独猪鬃销势一直都旺。有一年,姑妈对请来的范杀猪匠说,要扎一把洗衣刷子。范杀猪匠没全拿走,留下了一些猪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杀头年猪的工钱五至八角,仍要给,不会少,猪鬃和那坨肥肉算是主人家的“打发”,叫“吃带头”——吃,意为得、取;带头,顺带搭头。这是不成文的行规,也是乡俗。
旧时,烫灶房为猪贩子杀猪,除收工钱和留下猪鬃外,猪腰子也归杀猪匠,炒了下酒。那时候购买力低,一个县城一天杀不了几头猪,猪腰子并不多,不然吃不了。逢年过节会多杀几头,吃不完的猪腰子可卖给小餐馆。杀猪匠天不亮开始操刀,要点灯,也抠猪贩子的猪板油用或者捡碎碎儿肥肉。那是真正的土种猪,油脂肥腻,灯很亮。油脂灯为碗形,焊有一个手提的鋬鋬儿,提着走夜路,大家都晓得是烫灶房的杀猪匠来了。
川江走船,桡胡子会带一些私货,如:烟土、食盐、黄豆、糯米、大米等。桡胡子是川江船工的统称,其他江河喊“桡夫子”。有人认为,我们下川东一带因方言发音习惯,将唇齿音f与舌根音h的字混淆不分,如夫(fū)与胡(hú)、发(fà)与华(huá)等。的确如此,唯独“桡胡子”不是。我觉得“胡子”符合川江船工粗野的性格,“桡夫子”喊起来反倒斯文了。比如,我们称呼外公外婆“嘎嘎(gāgā)”,外婆叫“小嘎嘎”,外公为“胡子嘎嘎”。
桡胡子带私货和“吃带头”有些相似,他们自称“捎带”。1883年,有个英国人在沙市雇一只木舤船入川。船主是巫山人,拢巫山码头后,出其不意地从舱里搬出几匹土布和几袋大米、檀香,是在沙市悄悄装上船的,英国人一点没发觉。外国人包船,沿途各关卡免查,船主趁此躲脱了缴税。一个多月后,这位英国人返回时,在重庆又雇一只木船。船主也捎带货物,装的是鸭毛,用篾席包裹好,放在自己住的船尾舱里,运到上海销售。鸭毛最终可能会被卖到伦敦去。
过去船主雇桡胡子时,都要预付一些工钱,好让他们买货“捎带”,顺便挣点“外水”。但亏赚自己负责,这属行规。抗战胜利后,迁往重庆的人员纷纷返回武汉、南京及下江一带,因轮船运力紧张,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与家人、同事、亲友坐两只木船出川。五十多人等了两天,船一直不开,因船主没预发工钱。桡胡子们要等发了钱去买白术(中药材),每百斤进价一万多元,“捎带”去下游卖,价可达二三万元。
下川东一带县城,过去一般开设有米粮货栈,为商贩免费提供堆放、储存之地。少数大一点的货栈,还附设照看骡马、提供草料服务。当然也不完全是白帮忙,货栈采取“打角子”的方式“吃带头”。
介绍“打角子”前,先说说以前货物买卖怎样称重。那时候大宗货物买卖不用秤。比如,猪贩子到乡下买肥猪,没有秤,更没有称猪的大秤,一头猪的价钱,凭自己的经验,买卖双方当场议定,亏赚自愿,这叫“估砣砣”。牵牛送宰的牛贩子更要凭经验,甚至说是本事,牛的骨骼大,稍估偏一点,宰杀后肉的悬殊少则几十斤、多则上百斤,亏赚风险大得很。现在乡村耕牛买卖,很多地方仍是“估砣砣”。
汤溪河、东河一带的木船运煤,用“印子”计量,也没有秤。“印子”为四棱台形木板框子,上小下大,上无盖下无底,方便计量后取出。计量时,把“印子”抬到码头空地上,撮箕装了煤,一下一下往里倒。装满后向上抬起“印子”,煤堆留在原地,“印子”另放一空地处,重复操作。每堆“印子”的煤计量约两百斤。
然而像金银和烟土以及贵重药材之类精细物品买卖时,要用秤称。这种秤很小,最大单位为两,最小以厘计,精确度非常高,叫“戥秤”或“戥子”“戥子秤”都可。秤杆多为乌木或兽骨做成,粗细、长短和筷子差不多。铜质的秤盘非常薄、轻,大小如茶盏。秤砣是圆或方形的铜片,如铜圆或火柴盒大小。民间有拿戥秤做比喻的俗语:“家中有金银,隔壁有戥秤”,意思是你经济条件如何,瞒不过邻里乡亲;还有一句:“未必要拿戥子来称”,比喻对人斤斤计较,或苛刻。
回过头继续说“打角子”。商贩堆放、储存米粮在货栈,最终是要卖了赚钱。过去卖米也不用秤,用升、斗计量工具,借用货栈的,仍是货栈的人帮忙。升和斗,为倒过来的四棱台形框子,样式像量煤的“印子”,但下面封了底的,也小得多,一升只有六斤,一斗为六十斤。另有一斤和三斤的量具,分别被称为“合(gě)升”和“半升”。合也为旧时的计量单位之一。用量具卖米,卖到最后都可能剩下零头,不足一升,这就归货栈所得,算是报酬。此为“打角子”。
我岳母小时候读书,因物价涨得飞快,学费改交“尊师米”。她在家里拿了钱,自己去米市买,由卖米人帮忙送到学校。卖米人为挑担进城的农民,无秤,也没带升、斗,市场上有人专门出借,帮他量米。斗或升装满后,拿丁字形的木“趟子”推平升口或斗口,落下来的散米为出借量具人的报酬。卖米人肯定不会一股脑儿往斗或升里倒米,特别是快要满的时候,会悠着点慢慢倒。但不能有凹凼,不然买米人不干。因此,出借人就在这种平衡中得点“残羹冷炙”。
川东有一乡场,附近村民逢农历三、六、九日赶场,在文庙卖米。庙里和尚备有升与斗,统一由他量米,以示公平。升、斗满后,和尚不用“趟子”推米,用手抹,抹两次,第一次落下的米仍属卖米人的,抹第二次时落下的才归他,算庙里的收入。落下的米大约相当升、斗里的百分之一不足。
下川东一带桐油产量大,农民挑进城卖,桐油公会派人查验质量。此人用一截带圈的竹竿,样式有点像现在调搅鸡蛋的小用具,在油篓中慢搅,看里面掺假没有,是否有杂质。桐油非常稠黏,验毕提起竹圈时,往往粘有一二两,冬天时会更多。验质人专门用木盆搁放竹圈,粘的桐油滴在里面,要不了多久就滴满了,算他的回报,油帮公会不再给他开工钱。这叫“打勾秤”。
我听苏老先生说,他们县桐油公会“打勾秤”的人姓赵,每年须从得到的桐油中捐出一百斤来,为本帮端午节竞技的龙舟打二道防腐油。这与“船板凳”(船工)拿出部分“出秤”治滩差不多。澎溪河木船运米,交货时,多出的斤两为“升溢”,归船板凳得,叫“出秤”。当然,差斤少两也由他们赔。《开县交通志》载,1934年、1935年,各方集资整治猫爪子以下各险滩,其中运米船户捐出1934年4月至9月的“出秤”。同时,粮帮公会也将扣下的船户差秤米款三百元拿出,一同用于治滩。
“吃带头”并不“伤筋动骨”,在双方承受能力范围内。因此过去民间比较时兴、普遍,方法还有多种。
农村栽秧和挞谷叫“抢种抢收”,简称“双抢”,因体力用度大,农民需喝点酒解疲劳。打酒凭票的年月,供销社专门供应“双抢酒”,可不要票,也不收钱,用粮食斢。三斤高粱,或三斤半苞谷,斢换白酒一斤。按常规,一斤高粱或一斤苞谷可烤酒半斤至七两,多斢的粮食烤出的酒,赚的钱为供销社应得的利润。
贫困年代,家里来了客人,没什么好招待的。主妇会撮几斤麦子,让家里的细娃儿提到生产队面房,换回一把挂面。斢换标准是,一斤麦子斢七八两挂面。差缺是因为磨面粉时要产生麦麸,可做饲料和酒曲,归面房得,充当加工费。如果一斤麦子只能斢到半斤或六两挂面的话,那一定是好面粉擀的,产生的麦麸多,划得来。
合 脚
“咿哦——吔!”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二爸挑着百十来斤洋芋种回家,每次歇气完,担子再上肩时,都会这样长长地呼叫一声。
我问二爸:“气没歇够吗?”
“这是‘喊号子,做活路的人都要喊,”二爸回答,“上肩时,要使劲,长喊一声松口气。”一路都是上坡,二爸比较累,时不时又“嘿哟嘿哟”哼几声。
这种呼叫和哼气声也算是号子?一个人做活路也喊号子吗?
我第一次在川江上行走,是童年时跟着外公乘坐柏木帆船,当听到那一声声原汁原味的川江号子时,不明就里,问外公:“为什么要喊号子?”外公解释:“做活路才不累呀!”当时,整条船上的桡胡子都喊,各种曲调与音律交替,一会儿抑扬、清脆,一会儿粗犷、高亢。
川江与川渝及毗邻鄂滇黔地区大小河流上,船工的劳动号子统称“川江号子”,如今作为传统音乐项目,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官方定义:“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歌唱形式。”川江号子有词牌几十种,分上水、下水号子和杂号三大类。类别也可称为逆水、顺水(平水)号子和杂号,或叫推桡、拉船号子与杂号。
老桡胡子冉白毛吧嗒着叶子烟,慢悠悠地讲述:“拉纤使力气,肚子里憋到起的嘛,不喊号子要遭内伤。”这如我二爸说的“松口气”。冉白毛又举例子说:“人不舒服的时候,一边忍着,一边不停地哼,是不是觉得要松活一点?还有,你看那些抬二,都系紧了腰带的,抬石头的时候又吼得凶,就是不让肚子里憋气,要把气吐出来。石匠师傅开山(破岩)‘甩大锤,还不是一个人边甩边喊号子。”
“甩大锤”就是“打大锤”“抡大锤”“挥大锤”。平常,工匠们使用的二锤、手锤、榔头、斧头等工具的手把,有长有短,但一定是硬把子,唯独石匠的大锤手把拿细长的木棍儿做成,软的,有弹性。甚至有人破开南竹,直接用一块两指宽的篾片做手把。石匠挥舞大锤像是甩,很形象。冉白毛道出原理:“大锤用软把子使的是借力,也叫巧力,下大力气时才用,人没那么吃亏。硬把子的二锤,用的坠力,土话叫‘下死力,不花大力气的活路用。”冉白毛怕我不懂借力与坠力,打了个比方:“一百斤棉花和一百斤铁一样重,挑二都愿意挑棉花,肯定不想挑铁。”
冉白毛这番“气”与“力”的土俗道理,与外公“做活路不累”的意思差不多。川江号子的官方定义,看来只说了个半截话。
桡胡子拉纤喊号子,不都是由号工领唱,过去常以敲鼓的方式引导拉纤,用鼓声替代领唱。唐代,白居易《入峡次巴东》诗中有记。元和十四年(819年),白居易赴任忠州刺史途中,过三峡时,看到有人举旗击鼓,引导船只过滩:“两片红旌数声鼓,使君艛艓上巴东。”
白居易的诗只是一种诗意的描写,不知具体的操作。清代后期,敲鼓引导拉纤的情形普遍起来,尤其是西陵峡中常见。1868年,英国旅行家汤马斯·库柏入川时,清楚地记录,在茅坪镇上游不远处的獭滩,他看到“有时候需要纤夫们松开纤绳,或者突然停下来,所以在船头有一个敲鼓的人,用不同的鼓点来指挥岸上的纤夫们”。
敲鼓替代的只是号工领唱,桡胡子拉纤时仍要喊号子。一个名叫威廉·约翰·吉尔的英国人,不仅是位探险家,还是皇家工程兵团的上尉,他在旅行记中写得很明确。1876年3月11日下午,他乘坐的木船过獭滩时,小鼓以一种平常的节奏敲响,岸上的纤夫们喊起了号子,拉紧纤藤,听从变化的鼓点的指挥。
一路上,拉纤时都要敲鼓。敲鼓的人多为船上的烧火,也就是杂工,他和驾长深得船主信任,属“坐堂”(长工),而一般的桡工、籇工、纤工为随用随雇的短工。有的木船也由船主自己担任驾长。烧火不煮饭不买东西时,在船上帮这帮那,对各个工种熟悉,也都会一点儿,所以别称杂工。烧火敲鼓引导拉纤,船主可不请号工,节省开支。号工工资差不多和驾长一样高。
川江险滩长,纤藤更长,一般两三百米,有时岸边还有岩壁、石背遮挡,并且滩水湍急,声响还大,拉纤的桡胡子听不清号工的领唱。如果号工在岸上随行指挥,又摸不清船上的情况,不晓得驾长的号令,鼓声浑厚,穿透力强,传播很远,与周围环境声响泾渭分明,正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清嘉庆年间,陈明申的《夔行纪程》中记载:“船行江中,纤牵上顶,声息不能相闻,船上设锣鼓,以锣鼓声为行止进退。”这话解释为,船在江中行,拉纤的人在岩顶上,相互不知情况,听不到声音,便用锣鼓声指挥行止、进退。
1871年2月的一天,英国地理学家约翰·汤姆森过黄陵峡时,见船上的人敲一种小鼓,说“鼓声在河流的咆哮声和纤夫们的号子声中都可以听见”。
有鼓必配锣,时常锣与鼓并用,声响更铿锵有力。冉白毛说,下水放大滩时,我们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往河里撒大米,向河神报到,请求保佑平安。
进入民国,川江上航行的轮船逐渐多起来,船速快,掀起排排大浪,时不时撞沉、浪翻木船。重庆海关船务部门发布公告,规定木船必备锣与鼓,远远看到轮船,立即鸣锣击鼓,发出预警,轮船听到信号,必须慢船减速,避免事故发生。
脚蹬石头手扒沙,弓腰驼背把船拉。
穿的衣服像刷把,吃的苞谷面掺豆渣。
这是最有名的一首川江号子,大河、小河、沟沟河的桡胡子都唱。粗略了解川江号子的读者也知。严格说来,这不是川江号子的“正书”内容,称“书头子”。
什么是“正书”?什么又叫“书头子”呢?简单点说,“书头子”与“正书”分别相当于诗、文的题记和正文。过去茶馆的说书先生,开讲正书前,首先来一段开场白,内容雅俗共赏,幽默搞笑,达到预热、暖场的效果。开场白就是“书头子”,川江号子借用了这种形式及名称。
川江号子的书头子与正书有明显区别。书头子每句稍长,正书有长有短;正书词句都夹带助词、叹词,而书头子基本不带。书头子内容丰富,有趣、诙谐,听起来轻松、愉快,桡胡子们称“醒脑”,意思是让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
但书头子不是随时都唱。上水拉纤,过急流滩后是长流水,航道没多大变化,纤道也较平直,这个时候桡胡子轻松多了,要喊一种名为“数板”的号子,喊之前,号工便先唱一段书头子。下水或平水时扳桡,遇到水势平稳的航道,桡胡子不需出大气力,也喊数板号子,也先来一段书头子。桡胡子们在急流滩上奋力挣扎时,是喊抓抓号子,或叫招架号子,如果这时候突然冒出几句书头子来,他们一下子泄了气,下水船会乱窜,上水船要倒流,非出大事不可。
因此,书头子唱在数板号子之前,而上水、下水号子里都有数板号子。冉白毛说,活路轻松时,我们也会唱几句书头子。
书头子内容多少都有,少的四、六、八、十句,多的如《说江湖》五十八句、《川江两岸有名堂》八十句,还有更长的上百句。这么长的书头子,不可能一次唱完,不然等号工“开完音乐会”再拉纤、扳桡?往往是号工唱上一小段书头子后,桡胡子已做好准备,正等正书开场:
领唱:“呀呀嗬——嗨嗨!”
众答:“嗨!”
领唱:“要想夫妻哟——”
众答:“嗨!”
领唱:“不离伴呀!”
众答:“嗨!”
……
书头子和正书词句内容涉及风土风情、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最有趣的是号工现场即兴编唱,生动、有趣:
王村码头高又高,烧火称肉一坨泡。
吃一半,留一半,响水洞脚吃早饭。
词句旁敲侧击船主吝啬,昨天在王村买了一坨最差的泡泡肉不说,还只煮了一半,今天拉船到了响水洞,又才吃早饭。
冉白毛摆,有一次鲜辣椒刚上市,大家想尝新。那个时候没得大棚里长的反季蔬菜这回事。烧火按船主的吩咐,中午炒了青椒肉丝。吃饭时,船主半开玩笑说要算钱哟。桡胡子的伙食都是船主包了的,大家也不作声。下午拉滩时,喊号子的用节奏刚喊了句“中午的青椒肉丝要算钱”。船主听了,担心桡胡子暗中“整经儿”,马上高喊:“不算钱、不算钱,明天还吃。”
川江滩险浪高,桡胡子拉纤、扳桡要斗滩头、抢江流,拼尽全力,奋力抗争,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因此,川江号子的词句简洁、明快,而且众和词句除了助词、叹词外,几乎不含实质内容且基本上在四个字内:
领唱:“哦嗬!”
众答:“哦嗬!”
领唱:“吆哦嘿啦!”
众答:“哦嗬!”
……
领唱:“船到滩头哟!”
众答:“嗨!”
领唱:“水呀路开呀!”
众答:“嗨!”
……
一次,我看川江号子实景演出,激越高亢的音乐声中,桡胡子们一出场,领头的便高呼:“开——船——啰——”其实,真实情景是不喊“开船”的,有“破船”之讳,都称“开头”。船真的开头时,也只喊“退挡号子”——两边都停着船,要退着出去,此为退挡。属杂号类的一种。演出中,领唱、众合的那些川江号子词句,很大部分实属书头子范畴,声动梁尘、余音绕梁。
我含蓄地提出疑问:“船工拉纤时,喊这么长的句子,不好合脚哟!”合脚就是合拍的意思,川江号子不是要“统一动作和节奏”吗?我听冉白毛说过,合不到脚叫“碰龙”,乱蹦乱跳的,船上不了滩。
演出方负责人回答:“照你说的这样演出,没得几个人看了。”
原生态川江号子的词句,大部分比较土俗、口语化。有词唱道:“沟死沟埋,路死路埋,狗子就是肉棺材。”旧时,桡胡子和船主订有协议,路上病了,不做活路就不能白吃饭食,否则要遭撵下船去;死了,篾席裹起,扔上坡算数。在江边“桡倌栈房”雇用时就说清楚的,栈房老板或荐工的保人可作证。所以,哪里死了扔哪里,被野狗撕扯吃掉。土俗的词句里是没有苦难的。
“一床破席脸上罩,白骨奉还爹和妈。”这句是前句的翻版。古训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说法,即,身体、毛发、皮肤是父母给的,要保护好,不能损伤,这是孝的开始。结果只剩下白骨,忤逆不孝。也满是苦难的词句。
“使力的是我的老子!不使力的是儿子!”这是抓抓号子中的词句,我略去了众答和助词、叹词。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两个人摆龙门阵时,打赌、发誓的话。又如,“刘皇叔在白帝城托了孤,巴到墙边起的尽是半边屋”。刘备,人称刘皇叔,川江人有跟着晚辈喊的习俗;巴到,紧挨的意思;起,砌;半边屋,紧挨城墙的那面屋墙可不砌——牢固又省了钱,岂不是半边屋?这全是下川东人平时的口头话。再有,“清水洗来米汤浆”。过去,川江人把衣服洗干净后,要用煮干饭滗出的米汤浸一下,再晾干,衣服发硬、发挺,穿起平整,好看又耐穿。我姑妈说,细娃儿不爱干净,浆过的衣服穿脏了,下次才好洗。民俗与口语融入了川江号子。
1985年,我在云阳县志办公室工作时,看到航运志资料里的川江号子有这样几句词:“没有被盖睡,扯把黄金叶,没得枕头睡,石板都要得。”我认为记录有误,按下川东一带方言习惯,不会喊“被盖”,这是书面语,应该叫“铺盖”。于是,我做了几处修改,“被盖”肯定改为了“铺盖”;同时,前一句有“睡”,第三句又出现,累赘了,就把前一个改成“盖”;最后一句中的“石板”改为“石头”,“石板”是平的,不能当枕头,“石头”是砣砣,才可以。另外,没查到“黄金”这个植物,疑为乡下的黄荆树。
改好后的词句为:“没有铺盖盖,扯把黄荆叶;没得枕头睡,石头都要得。”并引用在我的散文《三峡船歌》中,于1988年8月21日刊发在《四川日报》副刊上。
我那时候想当然了。“铺盖”也许改得正确,但其他未必。词句中前后出现“睡”字,正是口语化的表达,而江边各种形状的大小石头,老百姓口头上至今仍喊石板……
川江号子的词句只有在江岸、河滩、峡谷喊唱才具魅力,舞台上的表演往往失去了生命力,缺少灵魂。四川地方史专家赵永康先生,对加工、整理的音乐作品《川江号子》这样论述:
与船工们航行时实际喊唱的“号子”(棹歌),已有相当大的差别,未能真正保留其本来形态……只余下未能深入了解人力木船船工劳动情况的音乐界专业人士加工、整理的音乐作品《川江号子》留存在人间。
陶灵,生于1964年,重庆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川江人文写作。在《散文》《散文海外版》《天津文学》《奔流》《延安文学》等刊发表散文多篇。出版散文集《川江记忆》《川江往事》《川江词典》《川江博物》。
责任编辑:杨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