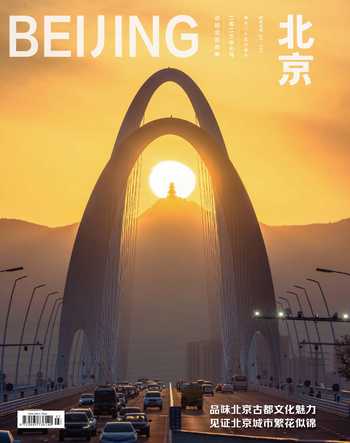最老的城 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
追溯一座城市的起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由于文字资料的缺失,在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之前,北京的城市起源一直是个“悬案”。直到多次大型考古发掘,让琉璃河遗址中埋藏的珍贵文物和遗迹走出“地下”,北京在距今3000多年前西周时就已建城的史实才得以确证。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镇区北侧,距北京市区38公里。现展陈在首都博物馆中的“堇鼎”,是目前北京地区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它于1974年发掘于琉璃河遗址253号墓,镌刻其内的铭文记载了这样一则史实:燕侯“克”身边的一位近臣“堇”,曾远赴周王都所在地奉献食物。堇回来后,专门铸造一件铜鼎来纪念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因做器者是堇,故该鼎被命名为“堇鼎”。3000多年前的堇可能从没有想过,他的“有心之举”会成为后人追溯北京城之源的关键所在。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曾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写道:“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然而,司马迁虽知晓“召公封燕”的历史,却不清楚“北燕”的具体位置和受封的具体内容。“堇鼎”的出现,证明琉璃河遗址曾是西周燕国的城址所在。随着“堇鼎”的重见天日,北京城之源的神秘面纱也随之落下。其后的考古出土成果和研究,让它的城市面貌和历史初源开始愈发清晰。
1986年,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再现两件重要的青铜器。经过清理,考古学者们认定它们曾是商末周初被用来盛酒与盛水的“罍(léi)”和“盉(hé)”。让考古专家们感到欣喜的是,这一“罍”一“盉”,不仅保存完整,设计精巧别致,而且还在它们的器盖和腹壁发现两篇所刻内容完全相同的铭文。“周王说: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命(你的儿子)克做燕地的君侯,管理和使用羌族、驭族、微族。”铭文在翻译成现代汉语后,一段在文献中缺失的历史得以还原:召公奭在灭商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周武王有感于召公的功绩,遂将位于西周北方的疆土燕地分封给他。不过,因召公此前已担任西周太保,位列“三公”,地位十分重要,就被周武王留在国都镐京,辅佐周王。因召公无法亲自就封“燕地”,周武王便令召公的长子克,子承父训,受命北疆,营建都城。克来到燕土后,受纳土地和臣民,成为第一代“燕侯”,开启了燕国800多年的历史。
为感念祖先、歌颂王业,克在到达燕地后,特铸一批青铜器。根据“克盉”“克罍”镌刻的铭文内容,不难发现,琉璃河遗址就是西周燕国始封地,第一代燕侯名叫“克”。一段失传的史实重现的同时,北京建城之源的历史谜团也得以正式“解密”。北京建城史由此被推算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年。
光阴流逝,琉璃河遗址一直在默默诉说着自己作为北京城之源的辉煌和威严。2019年,为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多家单位“联手”,重新启动对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2021年,M1902墓中出现的一件青铜卣(yǒu),再次给考古专家们带来惊喜。“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镌刻在青铜卣盖内壁和内底部的这段铭文,被翻译为现代汉语后,其大意为:“太保在匽筑城,遂后在匽侯宫举行祭礼。太保赏赐给作册奂贝,奂为他的父亲辛做了这件礼器。庚。”“太保”即“召公”,该铭文与1986年出土的克盉、克罍所刻铭文互为补充。铭文所载内容,证实召公曾亲自来过琉璃河遗址,并在此筑都。它的发现,也以无可争议的文字记载实证了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在世界城市史上独树一帜。
今天,琉璃河遗址已成为认识和了解北京在3000年前“城市面貌”的一个窗口。为保证这块遗址与当代生活的融合,北京已提出《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年-2035年)》,建设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正式进入“日程”。2023年春节,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再次有了重大发现。随着一座“东西超过25米、南北超过30米”的大型宫殿宫室建筑基址再现,北京“城市之源”的面貌更加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