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儒家文化视域下的善恶厕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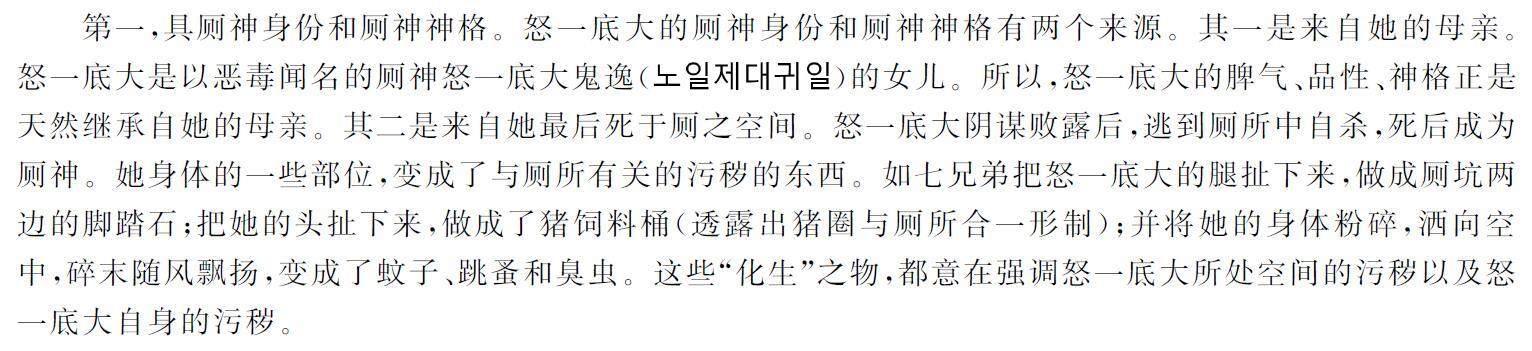


摘要:韩国厕神怒一底大和中国厕神紫姑是完全对立的形象。前者是个双重污秽的全恶形象,而后者则逐渐超越污秽,变为雅洁超拔的形象。不过,二者在诸多方面都相通,如都是女厕神,都司掌着厕之污秽空间,都是死而成神、身份卑微、与大妇对立等。尤其在更为原始的深层,都是对原始厕神生殖神格的继承。这表明她们是后经改塑才变得形象鲜明、单一并形成对立的。而且,怒一底大与曹姑,紫姑与骊山夫人,又可易位,足见两国厕神故事结构之类同。一恶一善,如此完全相反的厕神形象和评价,背后的价值准的出奇一致。这透露出东亚文化圈中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和性别视域局限。
关键词:厕神;怒一底大;紫姑;善和恶;叙事结构;儒家伦理道德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3.02.018
收稿日期:2021-12-21
基金項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皇五帝神话体系的文化基因研究”(21XZW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勤,女,四川成都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神话与民俗,E-mail: liuqin2023@163.com。
厕神信仰源自原始社会的粪肥崇拜、猪神崇拜和女性生殖崇拜(女性生殖崇拜具有统摄地位),并随着厕之空间的形成,神格被逐渐确定。进入文明时期以来,这类神灵在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国家中普遍兴盛,直至今天也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较多遗留,中国和韩国就是其中之一。中、韩厕神信仰,因地域和文化的密切关联而具有很多可资比较的地方。本文拟就韩国厕神代表怒一底大和中国厕神代表紫姑为例来进行探讨。
一怒一底大:对双重“污秽”的强调与“全恶”形象
韩国厕神怒一底大()的故事今天仍流行于济州岛。她不仅代表了韩国厕神的基本形象,也是迄今所见韩国各类厕神的主要来源。怒一底大的故事首末被记录在韩国古巫歌《门前本解》中,古籍中未曾有见。《门前本解》到底是何时产生的,不得而知。自从日本学者赤松智成和秋叶隆于1937年首次在济州岛采录该古歌之后,又有不少学者陆续进行采录。综观《门前本解》十多个版本,其故事结构、主要内容和感情倾向都基本一致,唯有某些具体细节不同。
《门前本解》篇幅较长,大意如下。南儒生家境贫寒,有七个儿子,荒年饥岁难以度日,于是妻子骊山夫人让他出去买米(一说让他出去做生意)。他驾船出航,三年未归。实际上,南儒生早已被梧桐国厕神的女儿怒一底大所引诱,输光了所有,并与她生活在了一起。日夜担心丈夫的骊山夫人终于到梧桐国找到了丈夫。怒一底大先假心与骊山夫人做好姐妹,后趁其不备将她推入池中淹死。之后,怒一底大假扮成骊山夫人蒙骗已瞎眼的丈夫,并处心积虑地要杀死七兄弟(取走他们的肝)。最后,怒一底大阴谋败露,逃到厕所中自杀而成了厕神。南儒生也在门前的横木上吊死了。七个儿子用倒还生花救活了母亲骊山夫人,并奉她为灶王娘娘。《门前本解》中的人物并不复杂,主要有骊山夫人、怒一底大、七兄弟和南儒生。骊山夫人善良、真挚、勤劳,七兄弟(尤其是小儿子)聪慧、勇敢、孝顺,南儒生薄情、轻信、无能,怒一底大伪善、狡诈、狠毒。其中,厕神怒一底大是最值得注意的形象。这一形象在韩国民间历来都被视为“全恶”形象,学者们也基本上是从这一角度去阐发的。她在巫歌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和象征意义大体如下。
第一,具厕神身份和厕神神格。怒一底大的厕神身份和厕神神格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来自她的母亲。怒一底大是以恶毒闻名的厕神怒一底大鬼逸()的女儿。所以,怒一底大的脾气、品性、神格正是天然继承自她的母亲。其二是来自她最后死于厕之空间。怒一底大阴谋败露后,逃到厕所中自杀,死后成为厕神。她身体的一些部位,变成了与厕所有关的污秽的东西。如七兄弟把怒一底大的腿扯下来,做成厕坑两边的脚踏石;把她的头扯下来,做成了猪饲料桶(透露出猪圈与厕所合一形制);并将她的身体粉碎,洒向空中,碎末随风飘扬,变成了蚊子、跳蚤和臭虫。这些“化生”之物,都意在强调怒一底大所处空间的污秽以及怒一底大自身的污秽。
第二,是索取、败家、穷困的象征。在梧桐国,怒一底大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当听到南儒生带着“银百两和钱百两”驾船来了,就飞快地跑去勾引他,并诱骗他下棋。南儒生输光了所有,无奈娶她为妻(实际上是连自己都输给了她)。南儒生与她一起生活后,也只能日日喝糠粥,最后连眼睛都瞎了。这些细节意在突出怒一底大贫困交加、道德败坏,并象征着索取、败家、穷困和使人穷困。
第三,善于伪装与欺骗,极度自私与凶残。怒一底大假装与骊山夫人关系亲密,口口声声唤她作“姐姐”,但骨子里一直盘算着如何谋杀她;怒一底大诱骗骊山夫人一起去洗澡,终将其推到池中淹死;怒一底大穿上骊山夫人的衣服,并假装她的声音说话,欺瞒瞎眼的南儒生和多年未见母亲的七兄弟;怒一底大(装扮成骊山夫人的身份)假装生病,并装扮成算命先生说一定要吃七兄弟的肝才能痊愈;怒一底大假装吃肝(小儿子悄悄用猪肝代替了人肝,但怒一底大不知情),暗中将其藏于垫褥,最后阴谋败露……巫歌以极大篇幅渲染了怒一底大善于伪装和欺骗的特点。此外,怒一底大引诱、占有、欺骗南儒生,害得他有家难回、穷瞎双眼;怒一底大诱骗、谋杀骊山夫人;怒一底大绞尽脑汁,借南儒生之手谋杀七兄弟……如此种种,又意在突出怒一底大自私、邪恶、狠毒、凶残的特点。
第四,是骊山夫人的对立面。作为“妾”这一身份的厕神怒一底大是作为“正妻”身份的灶神骊山夫人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她们俩是仇人关系。与骊山夫人的宽容、善良、真挚、诚恳相反,怒一底大自私、狠毒、邪恶、伪善;与骊山夫人(灶神)象征的赐予、富裕、丰产、多子相反,怒一底大(厕神)象征的是掠夺、贫困、饥饿和死亡。
由上可知,韩国古巫歌《门前本解》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否定了怒一底大,突出了其双重“污秽”和“全恶”形象。这里的“污秽”,不只是表示视觉、嗅觉层面的“肮脏”(pollution),而且可以说是一切严重的甚至偏激的否定性意义的浓缩——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当然,实际上这两个层面始终无法截然相分,因为我们在说一个层面的时候,必然会延伸或者跳跃到另一个层面。这里的“恶”同样如此,“恶”、“游”、“色”、“贱”四者总是浑然一体地浓缩于“恶所”之中的。而怒一底大,集此四者于一体,故名之为“全恶”。
在物质层面,首先,怒一底大是以恶毒闻名的厕神怒一底大鬼逸的女儿。怒一底大的厕神身份和败坏德性正渊源自此,甚至可以说,“污秽”属其天然本性。其次,厕之空间本就是至秽之处、卑下之地和死亡之所。她死于厕,并成为专司此地的厕神,自然是“污秽”的代言人。因此,她死后,身体的某些部位,变成了与厕所有关的污秽之物:脚踏石、猪饲料桶、蚊子、跳蚤和臭虫。这些都意在突出其所代表的空间之污秽。在精神层面,首先,她无子并杀子,是对“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的摧毁;其次,她代表着生产生活资料的匮乏,是索取、败家、穷困和使人穷困的象征;最后,她自私、伪善、恶毒、凶残等败坏品性,又是对精神文明之反动。毫无疑问,巫歌文本几乎全面否定了怒一底大,强调了她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污秽”和“全恶”形象。
二紫姑:对“污秽”的超越、转化与道德典范形象
中国厕神紫姑最早见载于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稍晚的南朝宋东阳无疑《齐谐记》、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等也有记载。到唐宋,紫姑信仰更甚,相关记录和歌咏也越来越多。笔记、散文如唐佚名《显异录》、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宋沈括《梦溪笔谈》、宋苏轼《子姑神记》与《仙姑问答》等、宋朱彧《萍洲可谈》、宋徐铉《稽神录》、宋洪迈《夷坚志》等,诗歌如唐李商隐《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宋陆游《新岁》与《箕卜》、宋方回《上元立春》等,异常丰富。明清以至近代,仍然不衰,如明佚名《道藏·搜神记》、清袁枚《随园诗话》、明刘侗《帝京景物略》、清施鸿保《闽杂记》等。当代田野调查资料中也多有所见,如白族的“青姑娘祭”、满族歌谣《笊篱姑姑》、达斡尔族“请笊篱姑姑”、土家族“请七姑娘”、闽台“关三姑”,等等。
与怒一底大不同,“紫姑”的相关异名、异文极多。本文主要以南朝宋刘敬叔《异苑》所奠定的故事线路为主。《异苑》云: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一作妒),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投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一作行年)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舞,恶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投,便自跃(一作穿)茅屋而去,永失所在也。
故事主要讲述了貌美的小妾紫姑为大妇曹姑所嫉妒,每每被役使做打扫厕所之类的秽事,于正月十五日愤懑而亡。后来人们在她的忌日奠设酒果,制作人偶,于夜晚在厕间或猪栏边迎祀之,并念祝词“子胥不在,曹姑亦归,小姑可出”。紫姑神位不高,但神格广泛,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十分灵验,并会惩罚不诚者。此后,紫姑故事在民间和文人士大夫中沿袭不同的道路发展。民间注重迎祀过程,多有“游神”环节,关心与生产生活相关的预占和问卜,如生育、婚恋、丰产、家庭琐事等;文人士大夫则不太注重迎祀过程,关注的是科考、仕途、才艺等主题,故多将紫姑发展为“言志工具”、“红颜知己”。经道教改造本已仙化的紫姑,又与文人士大夫的趣味相结合,便形成雅洁超拔的形象。到苏轼《子姑神记》、《仙姑问答》、《天篆记》等作品,紫姑命运悲惨、才华横溢、德行完美等被渲染得无以复加。现将紫姑的主要形象和发展路径做一梳理。
第一,从南朝文献记载到当代活态神话,《异苑》所奠定的基调一直未变,甚至愈演愈烈,如紫姑貌美,身份卑微(贱民、小妾),善良柔顺,遭遇悲惨,死而成厕神,令人同情等要素。苏轼的《子姑神记》增加了惨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前夫伶人被陷囹圄、紫姑被霸占为妾的经过。《仙姑问答》增加了紫姑的生活时代、父母情况、修学情况、嫁为人妇的缘由和经过、前夫伶人的具体遭遇及其被强娶为妾之细节等,又突出了大妇的“妒悍甚”和紫姑的恐惧感——死后为鬼仍畏惧丈夫和大妇,不敢为自己伸冤解恨,足见她的卑弱和平日所受之欺凌。此后无论是民间还是文人士大夫,大体都是沿着这条线路去发展的,并逐渐塑造了一类影响颇大的厕神形象——卑微凄惨的女儿神形象,如紫姑、如愿、戚夫人、三姑等。
第二,《异苑》所载的“(紫姑)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也是此后民间紫姑信仰的主要内容。在民间,紫姑的神格非常广泛,其中,职司生产(包括人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如生育、婚恋、丰收等)注定了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话题,自然也成了紫姑的重要神格。紫姑信仰之所以经久不衰,也与她和岁时信仰紧密相连不无关系。紫姑沟通“两种生产”,是“大母神”(the Great Mother)在新的历史时期之神显。至于“紫姑卜”在唐宋以后渐渐发展为“扶乩”,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第三,小妾紫姑与大妇曹姑是对立关系。紫姑卑微、柔顺、善良、受害,令人同情;而大妇位高(妻对于妾而言)、嫉妒、狠毒、施暴,令人憎恶。《异苑》中说大妇曹姑因嫉妒紫姑,役使她做打扫厕所之类的“秽事”,逼得她愤懑而亡。《显异录》则直接说是大妇将其阴杀于厕中。《子姑神记》、《仙姑问答》、《道藏·搜神记》等在此基础上,更渲染了紫姑的“冤屈”之感。如《道藏·搜神记》说紫姑死后“魂远不散。如厕,每闻啼哭声,时隐隐出现,且有兵刀呵喝状”。
第四,紫姑才华横溢、道德完美的特点主要是经由文人的推波助澜而奠定的,并反过来对民间巫俗产生影响。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引《洞览》说紫姑(帝喾女)“生平好乐”,颇具文艺天赋;唐佚名《显异录》说她知识宏通,“自幼读书辨利”。到宋代,更加踵事增华。沈括《梦溪笔谈》说紫姑文章清丽,有《女仙集》行于世;其书法“有数体,甚有笔力”,绝非世间篆隶可比,又“善鼓筝,音调凄婉,听者忘倦”;苏轼《子姑神记》和《仙姑问答》言其对诗赋、歌舞、佛道、棋艺、论辩等无不精通,并盛赞她具有“礼”、“智”、“贤”,是符合道德准则的典范形象。
第五,紫姑的仙道化和雅洁化主要是受道教的影响和文人的改塑,亦反过来对民间巫俗产生影响。汉代道教文献中已多房中女神,魏晋诸派也普遍继承。房中女神们貌美、降于人(通神、通人)、精通歌诗,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们的“白日梦”对象。南朝以来,就已见紫姑与房中女神合流。《荆楚岁时记》中喜好音乐的帝喾女(紫姑)与对黄帝陈五女之法的素女何其相似乃尔!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紫姑自称“蓬莱谪仙”,是“上帝后宮诸女”。这与《真诰》所载房中女神萼绿华“谪降于臭浊”一致。袁枚《随园诗话》则直接将紫姑描述为主“司云雨之事”、“愿荐枕席”的“上清仙女”。
由上可见,紫姑的信仰比较复杂,其形象也是逐渐发展的。在物质层面,紫姑成为厕神,无非也是因为她与厕之空间有关,或被役使做打扫厕所之类的秽事,或死于厕。人们在她的忌日当天晚上或者黄昏,在猪栏或者厕所旁祭祀她。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厕神紫姑司掌的是污秽之地,但她却又是超越“污秽”的,甚至是追求净洁的。不仅如此,沈括笔下的紫姑简直就有“洁癖”。闺中女子欲与紫姑云游,紫姑对她说:“汝履下有秽土,可去履而登。”于是女子脱掉鞋子,穿着袜子与之登云而游。在精神层面,首先,紫姑沟通“两种生产”,是“大母神”在新的历史时期之神显。民间巫俗中还继续保留着她的“生殖”神格——虽然并未说到紫姑“生子”的问题,但“紫姑”实际上是由“子姑”而来。“子姑”即商始祖母简狄(三姊妹),自然司掌着人的繁衍,只是南朝以来的紫姑信仰在这一点上已不甚明显。紫姑能预占众事、掌管蚕桑或行年,也是丰产女神。其次,紫姑美貌善良、身份卑微、遭遇凄惨、令人同情,出于幻想性的弥补,人们同情她并赞美她,将一切美好赋予她。最后,主要经过道教和文人士大夫的改塑,完成了紫姑“雅洁超拔”的形象塑造。她不仅才华横溢,还具有“礼”、“智”、“贤”的完美德性。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整体倾向一致,但民间和文人士大夫在“紫姑信仰”问题上的视角、侧重点、价值判断、目的等仍有诸多不同。“紫姑”产生以来一直受到道教的影响,如“紫姑”之“紫”,本就与道教尚“紫”密切相关。但是,士大夫和老百姓的关注点又十分不同。文人士大夫主要关注的是“形而上”层面或“司云雨”(男女性交隐喻)层面,与信仰无关;而老百姓关注的则主要是生产生活,信仰色彩浓厚。又如,同样是同情紫姑,二者也极为不同。底层劳动妇女将紫姑作为自身代言人,是生活“常态”。她们将身份卑微、遭遇悲惨的紫姑超度为锄强扶弱的神灵;文人士大夫则将紫姑作为失意后的“红颜知己”,在壮志难酬之时,将其作为代言人来“言志抒情”,是短暂的“非常态”,当他们恢复到“常态”之后,紫姑就成了被贬斥和疏离的对象。他们与紫姑“唱和”,虚拟对话,毫无信仰根基可言。
三从表层到深层:形象的对立、同源、易位与改塑
如上所述,韩国厕神怒一底大和中国厕神紫姑是完全对立的形象。前者是个双重污秽的全恶形象,而后者则逐渐超越污秽,成为雅洁超拔的形象。
在《门前本解》中,怒一底大是“施暴”的一方,是“恶”的代言人。她的“恶”表现在诸多方面。无论是对丈夫、正妻还是七兄弟,她都充满了残忍、邪恶和欺骗。一开始怒一底大就引诱、欺骗南儒生,后来处心积虑地要谋杀正妻和七兄弟。她这个“后妻(妾)”,完全没有中国紫姑那样的柔顺、卑微、可怜和令人同情,而是嚣张跋扈,令人生厌和痛恨。在《门前本解》中,人们同情的反而是正妻骊山夫人,尽管怒一底大生活贫困,被南儒生在感情上遗弃,最后自杀于厕,并被七兄弟将身体撕碎,也并不可怜,而是咎由自取,大快人心。人们在其身上所投射的感情是厌恶、惧怕和痛恨。
而中国人对紫姑却主要是同情、爱怜和赞美。与紫姑类似的厕神,还有如愿、戚夫人、三姑等。她们都是卑微凄惨的女儿神:具有“妾”的身份,地位卑下,命运悲惨,令人同情。她们的故事尽管各地版本有所不同,但是神话的重心无非都是在讲述这些女子的悲惨命运,表达人们的同情,体现了民俗事项中惯常的将弱者超度为神灵的走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卑微”、“可怜”的倾向在发展中相当稳定。民间底层妇女,常将其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唐宋之后的文人士大夫,也常将紫姑视为自己的“红颜知己”、“言志工具”。在道教的影响下,紫姑又被发展成为女仙、帝女、成道女师。这些显然都是同情、爱怜的同向极端发展。
另外,与此相应,正因为韩国人认为厕神是“全恶”的,所以绝对不会去主动招惹她,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语言和行为禁忌。韩国民俗学者认为,韩国的厕神算不上信仰,也没有祭祀仪轨。韩国人也普遍认为,别的家宅神都是避祸赐福,给全家带来安全保护的(如正妻灶神),但是只有厕神相反,她是造祸作祟的。所以人们并不把她作为崇奉的对象,而只是因为畏惧才姑且提及,也并没有祭祀的仪轨和观念。逢年过节,别的家神神案前总是摆满了祭品,但是在厕神那里,却不放什么祭品。有的地方只是点燃一盏油灯或是摆上一碗茶而已。别的家神也都有神体,唯独厕神没有。
但中国古代民间却盛行着“迎紫姑”的习俗,今天有些民族和地区还有类似的习俗遗存。迎祀的仪式过程,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简单的没有“游神”过程,直接由迎神者(包括参与者)扶着人偶进行占卜问事。较为复杂的基本都有“游神”过程。如江苏地区,立一支筷子在粪箕中,以香楮往迎于厕上,闻粪窖中有声则认为神降,再迎神入内室,执箕画米问事。浙江地区,用稻草一握,中扎桃枝为人形,披以衣裙,先置于荒郊废址或陈年坑厕迎神,后捧入家中,放置于方板之上,以桃枝敲打问卜;或将筷子插入溲箕前,绉帕围于箕缘边,由两童共举至厕,祝告后返室,设香烛果饵迎神,神降问卜,最后送神。安徽地区,在簸箕上插上花、蒙上乌帕代表厕神,于人日挂于内堂檐下,元宵日取至室内簸箕中。妇女举箕问卜,最后送神……这些都有“游行”过程,此不赘举。迎祀的基本结构都是:由一个空间(厕、井堰粪际、厩、圈和厕、茅厮、粪窖、废址、堂檐)或一个时间(元日、小除日、岁前、人日)转移到另一个空间(室内、炕桌、月下、小室)或另一个时间(十六日、元宵),有的还有“埋”和“取”的行为动作。有的地方甚至在迎祀时,还会辗转多个地方,并有送神的环节。此外,整个过程中还有念诵祝咒、装扮人偶、敬供祭品等环节。自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祭品也会与时俱进,如马粪、酒果、酒食、香烛、果饼、茶酒等,不一而足。神的需求即人的需求。在习俗的惯性之外,人们是根据自身所需,去调整祭品的。在这些仪式、习俗中,人们对紫姑神充满了“功能性”期待。这与韩国人对怒一底大的一味“避祸”态度大相径庭。关于二者形象的对立项,参见表1。
尽管怒一底大与紫姑是对立的形象,不过,二者也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就显而易见的层面来看:都是厕神、女神、身份卑微、死后成神(或自杀、或他杀)、与灶神(骊山夫人、曹姑)关系对立、祭祀地点多在厕所或猪圈(至少是“游神”的主要环节)、祭品相对随意而简单等。就隐性的层面来看:二者在“生殖”神格层面都继承自原始女性生殖崇拜,是“大母神”混沌神格之一分为二。怒一底大倾向于负面、“恶”的一面。她死后身体发生“化生”的變化,实际上正是“生殖”神格之体现,只是存在于隐性层面。文本所突出和宣扬的,反而是她对生殖和丰产的剥夺。而紫姑则倾向于正面、“善”的一面。
紫姑也有负面形象,但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主要的。汉代以来对恐怖厕神的记载并不少见,如《太平御览》引《白泽图》、东汉桓谭《新论》、晋干宝《搜神记》、南朝宋刘义庆的《幽冥录》、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唐李复言《续玄怪录》、《太平广记》所引唐牛肃《纪闻》等,都说到厕神具有相貌丑陋、神格恐怖的特点。唐以后,随着道教和传奇小说的发展,进一步将厕神发展为魅惑男子的女性鬼妖。唐代柳宗元《李赤传》、《太平广记》卷三四一引唐李冗《独异志》都记载厕鬼是个魅惑男性的妖娆女鬼。她能迷人心性,让人产生恍入仙境的美妙幻觉,实则是丑陋瘆人厕鬼在用巾带缢人或用粪坑污人、淹人而取人性命。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七“女鬼惑仇铎”与上述故事相类。一个死了五十三年的女鬼张氏三六娘乘着“紫姑”的名号被“请”来,迷惑仇铎长达一个月。她诈称为蓬莱仙,对仇铎威逼加利诱,扮演多人角色,狡狯之至。其“辞殊亵冗”、“写媟语诱铎”、“惑乱其心”,要与他为夫妇,致使仇铎发狂自残寻死。而之前的《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异疾附”也记载,迎紫姑时,有时会出现送不走而作祟的情况。这里紫姑也是“恶”的,是“污秽”的。紫姑的这些负面形象切实存在于民间信仰之中。它并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源自“大母神”负面特征,源自原始思维,并借由志怪而流行。只是在发展过程中,被正面形象所掩盖,而显得次要了。
如此看来,怒一底大与紫姑又不是全然对立的形象了,而是有很多相同、相通之处。而且,极有可能的是,最初她们的形象是比较接近的,都有正负,只是后来经由改塑而变成了矛盾对立的关系。那么改塑的标准是什么呢?此外,如果把怒一底大(小妾、厕神)与曹姑(大妇、灶神)的形象进行对比,会发现她们的形象极其类似,都是负面、施暴、无德、受鞭挞和令人憎恶的对象。而紫姑(小妾、厕神)与骊山夫人(大妇、灶神)的形象也极其类似,都是正面、受害、有德、受褒扬和令人同情的对象。可知,怒一底大的故事与紫姑的故事在结构上是一样的,是一个故事的變体,欲说明的也是一个道理。小妾、厕神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正妻、灶神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其善恶的评价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四善与恶:东亚视域下的儒家文化道德准的
无论是改塑的标准还是善恶评价的标准,实际上都是儒家的伦理规范。中韩文化具有一定的趋同性,是整个儒家文化圈(14-15世纪逐渐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中重视集体、家庭、秩序、礼法、伦理、稳定等特征,对两国的国民性都产生了极深的影响。毫无疑问,个人形象和国民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怒一底大和紫姑的形象自然也是受到国民性的影响的,因为叙事者的思想必然影响到所叙述的对象。
在儒家伦理规范下,男性是一家之主,是话语者。善恶评价标准都是“他”说了算,一切都是维护着“他”的利益群体。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门前本解》,善与恶主要分属给骊山夫人和怒一底大,南儒生虽然也是恶的,但却是个“无辜”者,因为他是被怒一底大引诱、蒙蔽、欺骗而变恶的,不是恶之源。怒一底大的恶,总的来说,是因为她对南儒生以及其“家”,造成了伤害——巫师唱《门前本解》常是在家祭场合,即是为了家庭的和谐、幸福而进行的祭仪、禳除,包括生育、婚恋、疗病、祈愿、安宅、除厄、丰产、安全等方面。怒一底大破坏了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为人妇却不安于人妇,居妾位却不安于妾位,想方设法要取代正妻,造出一系列恶果。与她相对应的正妻(骊山夫人、灶神)多生多育、持家有道、任劳任怨、宽容不妒、逆来顺受,正是儒家伦理规范的维护者。紫姑和曹姑的形象和关系正好是前二者的逆转。厕神紫姑美貌柔顺、多才有德、忍辱安命,是男人心目中的完美女性,是儒家伦理规范的顺应者和牺牲者,故苏轼对其大加赞叹:“余观何氏之生,见掠于酷吏,而遇害于悍妻,其怨深矣,而终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礼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终不言人之阴私与休咎,可谓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无闻于世,皆可贤者。”可见,忍辱、顺从、安命就是“礼”和“智”,得传佳名即为“贤”。“礼”、“智”、“贤”,最终剥夺了紫姑的一生。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广大妇女的命运和缩影。曹姑居妇位而善妒,不容小妾,造出虐待、阴杀紫姑的恶果。无论如何,“丈夫”是没有错的。与此同时,凡是顺应“丈夫”的(包括顺应他的错),都是对的,得到“善”的赞美和补偿;凡是不顺应的(包括不顺应他的错),都是错的,要得到“恶”的惩罚和鞭挞。故孟子对新嫁女子说:“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故事的善和恶分属于“妻”和“妾”,而无论是怒一底大的丈夫南儒生,还是紫姑的丈夫“子胥”(刺史、李景),表面上看是“失语”的形象,但实际上却是永恒的裁判者和监视者。在今天看来,所有的矛盾,“丈夫”才是“恶”之源;从制度上说,正是这种基于男权的一夫一妻多妾制才是“恶”之源。如此看来,怒一底大也好,曹姑也好,不过都是替罪羊;紫姑也好,骊山夫人也好,也不具有普遍的善。
因此,不难看出,中韩厕神故事是经过儒家伦理道德彻底改塑过的故事,去掉了很多巫俗的成分,而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无论是塑造怒一底大这样彻底反面的形象,还是塑造紫姑这样彻底正面的形象,无非是在不厌其烦地讲述同一个问题:男权社会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下的妇女抉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谈到男权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持续利于男性的单方面的“淫游制”,这“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淫游制,在口头上是受到诅咒的。但是实际上,这种诅咒绝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剥夺权利,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无条件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有学者已指出:“自进入男权社会以后,我国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封建社会对中国女性的影响最大、最深。传统中国女性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视封建伦理纲常为金科玉律,形成近乎本能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成为男权社会驯服的奴仆。”
儒家(或称儒教)认可现有的权威和秩序,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国之本在于家,所以尤其重视家庭关系。家庭和谐、稳定,尊卑、亲疏、等级秩序是根本。同样的道理,儒家伦理规范将性别的不平等定义为永恒真理。夫为天,妻为地,天尊而地卑;丈夫虽贱皆为阳,妇女虽贵皆为阴,阳尊而阴卑。所以一切都是围绕“丈夫”的利益和利益群体而展开的。同样是阳,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样是阴,讲究妻高于妾。因此,大妇曹姑虽为丈夫的“奴仆”,却又是“奴仆头”。她奴役、阴杀小妾,不过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罢了,而绝无反过来的道理。作为更卑贱的小妾,绝无谋杀大妇的可能,若如此,必然是大逆不道,必群起而攻之,这就是怒一底大的命运。因此,在儒家文化氛围下,“端正的行为就是顺应这种严格的等级社会的行为”,并且要“随时确定个人在这种排比中的位置进而确定其恰当的态度和行为,并由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左右其态度和行为,依靠教化纠正其乖戾和偏差”。
当然,这种基于血缘家庭、宗法制度的儒家文化所评价出来的“善”与“恶”,必然不是真正的、客观的“善”与“恶”,不具有普遍的法则性和规律性,并反对普遍的法則性和规律性。正因为如此,孟子必然会骂主张“兼爱”的墨子为“无父”的“禽兽”《。所以,尽管看起来紫姑和骊山夫人不仅具有伦理的美德(ethical virtues),还具有品格的美德(virtues of character),但是这些美德并不是普遍的、客观的、绝对的,而是因人而异和因社会而异的。它的受益者不是“人”,而只是“男人”。但是,真正的美德应具有普遍性,应是“人类善”或是对“人类繁荣”的贡献,也就是说,美德不应该是非正义的或是受压迫的,也不应该是与人类繁荣相违背的。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现实生活当下存在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和韩国的影响自然不尽相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怒一底大和紫姑的形象塑造上。带有否定性、禁忌性的怒一底大身上所体现的儒家教化色彩更浓厚。这是因为虽然中韩都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但相比而言,韩国更甚。韩国长期以来尊崇中国文化,接受、信奉儒家准则,再加上受到其他思想的挑战少,以及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在继承传统上的相当优势,韩国可以说是全盘接受了儒家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经过这样的洗礼,怒一底大自然被塑造为“全恶”的彻底反面,以示警诫。此外,韩国巫俗保留的完整性、巫歌传播的稳定性,也使得其形象少于变化。诚如学者所说:“中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巫俗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混种化,而韩国的巫俗文化却依然很好地保存和维持着它原本的形态,不断展现着民族及地区特性。”从这一点来说,怒一底大的形象也更为原始。她具备“恶所”的一切条件,是“全恶”(恶、游、色、贱)的。“‘恶之中存有一种放浪不羁的力量,它会破坏原有秩序,引起各种混乱纷争”,所以它正“象征了这深不见底的混沌(chaos)力量”。因此,日本民俗学家沖浦和光如是说:“我以为‘恶应该是逐渐侵蚀人类的本质属性的东西。而且出乎许多人的想象,‘恶与人类一同起源。”紫姑的神话传说故事,不是靠巫歌代代相传,而是被记载于典籍,后又经文人重塑,或民俗浸润,与诸俗神相杂糅。儒家文化虽原发于中华大地,但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非儒家之一家,更非一味奉其为圭臬,而是能不断地批判、继承、调适,遂能常新。因此,紫姑的形象相对而言更具包容性。其形象有正有负(负面为次要),又有民间和士大夫的不同抒写,体现出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开放性特点。
[责任编辑:唐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