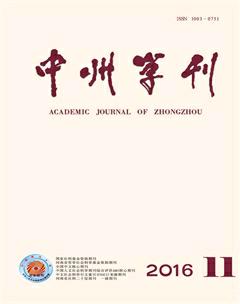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结构与功能
郭艳
摘要: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内容丰富,既有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空间,也有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超现实空间、魔幻空间和象征空间等,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主要有两类叙事结构:现实空间与非现实空间的穿越,空间秩序由混乱回复到平衡的过程。这些空间叙事具有实现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主题化,推进叙事视角转换和情节发展等重要功能,对于中国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志怪小说;空间叙事;叙事结构;叙事功能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151-07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虽然处于中国小说的初始阶段,艺术技巧还不成熟,但其空间叙事对于小说的情节推动、人物塑造具有重要意义。空间叙事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是叙事的“前景”和表现中心。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内容丰富,具有生活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文化空间等诸多特征。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许多空间叙事已经成为空间意象,出现在后世的许多作品中,对于我国唐代传奇、元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史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涉及的空间仅指文本再现世界的空间。
一、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类型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出现过许多空间,有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空间,也有阴间、梦境、仙境等与现实世界不同的非现实空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常常出现的空间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超现实的空间
在现实世界之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展示的空间还有一个“彼岸”世界,即超越现实的仙境、梦境和阴间等空间。
仙境。“仙境”一直是中国先民追求无灾无难、幸福生活的理想境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顿不堪、再加上佛、道两教的盛行,人们对于平安美好的生活更加向往,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出现了许多“仙境”故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仙境主要表现为神山洞窟、海洋等空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山这一空间,既有现实意义的山,又有神仙居住的“仙山”(仙境)。作为仙境之一的神山洞窟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对于“山”这一空间的夸张想象。王嘉在《拾遗记》卷十中介绍的昆仑、蓬莱、方丈、瀛洲、员峤、岱舆、昆吾、洞庭等神山仙岛,都属于仙境这种空间。
海洋也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仙境之一。海洋作为地球上最广阔水体的总称,本是一种现实的自然环境,但由于古代中国传统上一直是陆地国家,再加上当时航运并不发达,古人多不能亲见大海而极其向往。因此,海洋就被当作一种遥望、寻宝或想象的空间,极具神秘色彩。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海是连接天与地一个极为重要的空间。如《博物志·八月槎》中乘槎人由海通天。《拾遗记·贯月查》中巨查上有仙人居住。当然能在海上出入的
梦境。梦境作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一个常见空间,往往是阴阳两界进行对话的超现实空间,亡人可以在梦境中托付生者了却自己意愿。如《列异传·蒋济儿》中的蒋济儿就是通过托梦母亲完成谋个“得乐处”的愿望③。梦境有时是神人相恋的超现实空间,凡人可以在梦境中实现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完成的愿望和理想。如《搜神记·弦超》中的弦超梦遇神女并结为夫妇。梦境有时又是人物获知事态发展趋势的重要空间。如《搜神记·三王墓》中的楚王就是在梦中梦到眉间尺要杀他,后来楚王果真被眉间尺托付的怪客砍下头颅。《拾遗记·赵高受诛》中秦王子婴在梦中被天使告知“当有同姓名欲相诛”④,于是怀疑赵高并将他诛杀。梦境有时还是事态发展的另一“现场”,之所以说“现场”是指人物梦境中说的话或者做的事在现实中会产生相应的结果。如《幽明录·换头》中的贾弼之在梦中答应换头,起床后头就真被换了。梦境有时仅仅就是梦境,小说叙述的就是人物做梦的过程。《幽明录·柏枕幻梦》中的县民汤林在进庙祈福时入梦,后来“遭违忤之事”从枕中出来,才发现枕内的好几年不过是自己“俄乎之间”做的一场梦。
阴间。古人对于死亡充满了恐惧和神秘感,阴间作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超现实空间,充满神秘色彩。由于佛教的传入,“神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思想深入人心。人们认为死亡并不意味着终结,人的生命可以延续到来世。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有许多死而复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离不开墓穴这一空间。如:《列异传·蔡支》蔡支之妻死后三年被划回生录,挖开其冢就“坐起语,遂如旧”复活了⑤。《搜神记·河间郡男女》中河间男从军归来在河间女墓前哭诉,河间女就复活了。人鬼相恋的故事也离不开墓穴这一空间。如《陆氏异林·钟繇》《搜神记·紫玉》。墓穴里的物品有时则是检验亡人与当世人物关系的物证。《列异传·谈生》中睢阳王之女在临别时赠与珠袍并撕下谈生衣裾。后来,谈生售卖此袍子被识出,发墓检验找到谈生的衣裾,验证了谈生的话。《搜神记·崔少府墓》中卢充误入崔少府墓,与少府之女成婚,鬼妻赠其一金碗,卢生卖碗被崔氏亲姨母识得。冢还是人们辟谷服气的地方,如《异闻记·张光定女》中张广定女在大冢里模仿龟息功,三年不食竟未锇死。
2.魔幻的空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部分现实空间由于神奇怪诞的人物和离奇曲折的情节,使得这类小说具有光怪陆离的魔幻色彩。在这一空间里人鬼(妖)难分,虚实相生,有些鬼(妖)不仅没有令人恐怖、厌恶,反而有些可爱。
家宅。家宅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且饱含着情感和社会因素。人们对于“家”不仅有私密、舒适、安全的感知,也有对于家宅的黑暗角落、昏暗灯光等产生的恐惧心理。家宅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魔幻空间,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还多为异类出现的场所。《列异传·谈生》中的睢阳王之女夜半闯入谈生家里与其结为夫妇。家宅的地下、墙角等隐蔽的地方或者黑暗环境等处常常会出现一些妖魅鬼怪。如《列异传·细腰》中何文家宅中出现的黄衣人、青衣人、白衣人及细腰分别就是黄金、青钱、白银和杵棒,他们引起前主人张奋由巨富暴衰,程应“入居,死病相继”⑥。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家”很多时候是一个隐性空间,全文只字未提,但读者却明白故事发生在家里。这个隐性的空间——“家”的形成不只依靠作者单方面的描述,同时也依赖于根植于读者心中共享的中华民族关于“家”的文化传统和记忆。如《列异传·鲤魅》把“家”作为一个隐性空间,彭城妇就是在家里的床上捉住了化成自己的精魅——鲤鱼。《搜神记·吴兴老狸》的老狸幻化作吴兴人与其子在家生活多年。这类志怪小说中的家宅空间叙事多成为外来者——妖魅幻化成家人迷惑人的重要场所,充满了诡异的氛围。
深山。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有些“山”不再是现实中的普通山脉,而是精魅出没的区域,成为魔幻的空间。如《搜神记·白猿幻化》中幻化为老翁的白猿就是从主人公周群采药的岷山绝峰下来的。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有些“山”则是传说中的人物得道成仙的地方。如《神仙传·黄初平》中的黄初平和黄初起都是在金华山中学得仙道而成仙的。
亭。这也是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的一个魔幻空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亭常常是不祥之地,其中常常会发生一些恐怖的故事。《列异传·狸髡》中的刘伯夷夜宿惧武亭时,就有人说“此亭不可宿”,后来在楼屋间“见魅所杀人发髻数百枚”。⑦《列异传·安阳亭书生》描述“安阳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辄杀人”。⑧《搜神记·汤应》中“庐陵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辄死”。⑨《灵鬼志·嵇康》中的月华亭“此亭由来杀人”⑩。这类小说中的亭多为晚上妖魅鬼怪出现、杀人无数的场所,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人民生活缺乏安全感的现实。
3.象征的空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还有一类空间借助特定的具体空间来表现抽象的思想感情,强调隐喻、含蓄和隐晦。
泰(太)山。泰山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常见空间,“泰山”(有时作“太山”),多指与阳世相对的阴间。《列异传·蔡支》县吏蔡支拜见太守的路上迷失方向,进入岱宗山下的一个城郭即阴间,受太山神的委托向天帝递送书信,使亡妻复活。《搜神记·胡母班》胡母班经过泰山时被泰山府君委托送书信与女婿河伯,一年后返家途中路过泰山向泰山府君叙述传书之事,看到受罚的亡父。《幽明录·舒礼》巫师舒礼病死后被土地神送往太山。
桃花源。陶渊明在《搜神后记·桃花源》中描写了一个既真实又虚无的空间,这个桃花源其实就是古人向往的大同世界。这个空间除了具有“场景”的叙事意义之外,更多地体现了理想王国的象征意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象征着富足、美好的理想生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象征着男女老少和睦共处的平等社会;“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象征着无朝代更替的太平社会。志怪小说中的桃花源成为人们追求向往的理想社会。
4.现实的空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还有一些现实世界中的空间。本文所说的“现实的空间”不仅包括现实中实有其址的地理空间,也包括没有魔幻色彩的虚构空间。
如《搜神记·郭璞》中的“郭璞字景纯,行至庐江”,庐江就是实有其址的空间,郡治在今安徽庐江西南舒城。《搜神记·弦超》中“魏济北郡从事掾弦超”,济北郡治在今山东长清县。《搜神记·董永》中的“汉董永,千乘人”,这“千乘”郡治在今山东高青。此类篇目不在少数,不一一列举。这类空间大多作为小说中人物或事件发生的背景。另外,在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中也有许多现实空间。如张华的《博物志》中的《山》:“五岳:华、岱、恒、衡、嵩”;《水》:“四渎:河出昆仑墟,江出岷山,济出王屋,淮出桐柏。八流亦出名山:渭出鸟鼠,汉出嶓冢,洛出熊耳,颖出少室,汝出燕泉,泗出陪尾,沔出月台,沂出太山”。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还有一类未必能在现实地图中找到,但确为现实世界人们生活的世俗空间,如家宅、山林、集市等,这类空间与魔幻空间的区别在于是否有妖魅鬼怪的出现。如《卖胡粉女》中的富家男遇见卖胡粉女的那个集市就是现实空间。
二、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
表层结构及文化内涵小说文本是由一套可见的能指构成的有机结构,但其中的故事则是对能指的抽象,是无形的。通过复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可以把无形的故事表现出来,从而更好地分析作品的深层文化内涵。从空间视角来看,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表层结构主要有两大类:
1.现实空间与非现实空间的穿越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常出现人类现实生存空间与阴间、仙境、梦境等非现实空间的相互穿越。以文本中的俗世凡人为视角,许多作品中的世间凡人有时会由日常生活空间进入阴间、梦境或者仙境等异于现实世界的空间,演绎出许多精彩的故事。这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一是人间—阴间之间的穿越。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有许多篇目叙述人物从“人间—阴间—人间”的穿越过程,这种空间跨越与当时崇巫好鬼的民间信仰及佛教、道教的“轮回”观念有关。主人公从人间进入冥界地府,在同盟者的帮助下完成任务,重返人间,有的甚至让亡者再生。《列异传·蔡支》中的蔡支迷路误入死后魂魄的归所——岱宗山,在同盟者(泰山神)的帮助下,完成向天帝送书信的任务,不仅自己重返人间,而且使得已死三年的妻子复活,夫妻团圆。《搜神记·胡母班》与此类似。还有一类“人间阴间穿越”志怪小说的结构是主人公误入阴间,通过核查生死录确认阳寿未尽,又得以重返人间。如《幽明录·舒礼》《幽明录·康阿得》等等。
“空间总是社会性的空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阴间和阳间的穿越”这种空间叙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社会性。与现实社会一样,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阴曹地府里有草菅人命的事情和贪赃枉法的鬼怪。许多篇目里的人物按照生录还有阳寿,却无故被提前枉杀。《搜神后记·徐玄方女》中的徐玄方女“案生录,当八十余”,却在十四五岁就被枉杀。《幽明录·舒礼》的舒礼阳寿还有八年,就被索命。阴间的官吏也会徇私舞弊、贪污受贿。《搜神后记·阴吏受贿》的李除本已死去,因为许给鬼吏一只金钏而又复活;李除并不是个例,向鬼吏行贿的人不在少数,“为吏将去,比伴甚多,见有行货得免者”。《艺苑·章沉》中的章沉本已死去,却因为“天曹者是其外兄”而“断理得免”。与章沉一起来到冥界被录送的女子秋英,因把自己的金钏及臂上杂宝送与天曹主者也得以重返人间。《述异记·脱钏》的庾某也是寿数未尽就被俩鬼抓到阴间,在被遣送回人间的路上又碰到索要财物的门吏,一女子脱下三只金钏送给门吏,才使庾某得以重回人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阳阴两界穿越的空间叙事既反映了当时人们认为生与死是可以转化的观念,又表达了人们对社会黑暗的极度不满。
二是现实—梦境之间的穿越。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梦境虽然是一种幻觉,但梦中的人物事件又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表现。古人认为梦能预知吉凶,与现实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现实与梦境的穿越”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许多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人物从现实中进入梦境,在梦境中获知任务或者得到报偿如结婚、升官等,梦醒后完成任务或报偿消失。梦境叙事序列比较复杂,一类是人物在梦境中获知任务,醒后完成任务。如《列异传·蒋济儿》就是蒋济的妻子两次入梦,在梦中从亡儿那里获知了“任务”——即到孙阿那里为自己谋个“得乐处”,母亲醒来后就把任务转告蒋济,蒋济找到尚未去阴间赴任的孙阿求情,最终任务完成,其儿如愿以偿“转为录事”。有时做梦者是“任务”完成的阻碍者,“任务”有时可能与做梦者的意愿并不一致。如《搜神记·三王墓》中的楚王入梦,在梦中梦见了眉间尺报仇这一任务,梦醒后他力图阻止这一任务的完成,重金悬赏捕杀眉间尺,但最终在怪客的帮助下,眉间尺报仇的“任务”完成。另一类是人物在梦境中实现理想,得到报偿,中遇变故,报偿消失。《搜神记·弦超》中弦超在梦中遇到神女实现理想,结得良缘,后来因泄露其事,神女离开,虽然五年后再次相聚但终不得日日往来,弦超梦中得到的报偿——与神女结为夫妻还是没有真正得以实现。《幽明录·柏枕幻梦》中的县民汤林在梦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结婚升迁。后来遭遇意外,梦中醒来,报偿消失。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梦境不仅是人的一种生理现象,也成为人们表达理想、追求幸福的地方。
三是仙境—人间之间的穿越。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人民饱受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兵荒马乱中艰难地生活。加上当时风行清谈、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因此归隐山林,修道成仙成为人们逃避现实、追求幸福的一种方式。许多文人渴望进入仙境、修炼成仙。在这种形势下,以登山遇仙、修炼得道、拜会仙人为主要内容的游仙诗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涌现出张华、郭璞等游仙诗人,他们同时又是志怪小说的作者。在这种社会及文学风尚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大量的人间与仙境穿越的志怪小说。这类志怪小说中的人物偶入天界或仙山洞窟,遇仙不觉,归来醒悟。如《拾遗记·洞庭山》的采药石之人偶入灵洞,受到众女的热情款待,出洞返乡才发觉他入洞三天、人间已三百年了。《幽明录·刘晨阮肇》在天台山迷路,遇到二女并跟随回家,半年后返乡,发现“亲旧零落,邑屋改异,无复相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更是人间仙境穿越的代表作,从此之后桃花源就成为了理想社会的代名词。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现实空间与非现实空间的大跨度穿越使得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提高了小说这一文体的趣味性。
2.空间秩序由混乱回复到平衡的过程
以叙事文本中的俗世凡人为视角,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有些篇目中的俗世凡人并未穿越到非现实空间,而是由于异人异事的出现,从而打破了原有的空间秩序,人物在外力的帮助下或由于某种因缘,异人异事消失,空间秩序回复平衡。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妖魅鬼怪闯入—空间秩序混乱—英雄除异—空间秩序平衡。《列异传·鲁少千》由于蛇妖的闯入楚王少女屋舍,造成楚王少女生病,王宫以往的秩序被打乱;鲁少千得仙人符除死蛇妖,治愈了楚王少女的疾病,王宫恢复以往秩序。《列异传·细腰》由于细腰和黄衣、白衣、青衣的妖魅出现于巨富的旧宅,造成旧宅秩序混乱(“死病相继”),转卖给邺人何文后,他大胆破除妖怪(依次挖掘了黄金、青钱、白银,焚烧了杵棒),最终旧宅的秩序回复平衡(“宅遂清安”)。《列异传·鲤魅》《列异传·鼠冠》《列异传·狸髡》等篇目都具有类似的空间叙事结构。
二是女性神(怪)闯入—打破男主人公生活空间秩序—结为良缘—人神(怪)殊途。如《搜神记·董永》中的织女出现在董永行完三年守丧之礼回主人家的路上,打破了董永卖身为奴单身汉的生活秩序,织女与其结为夫妻,成就了一段良缘;但织女完成天帝交代的任务:织十天一百匹绢替董永还债之后,终究人神殊途,织女“凌空而去,不知所在”。《搜神记·猪臂金铃》中的美女出现在士大夫回家途中,搅乱男主人公的日常生活空间秩序(“呼之留宿”),结为一段姻缘(“解金铃系其臂”),但“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结果人妖殊途,美女是由猪幻化的(“因逼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甄异传·杨丑奴》《搜神后记·张姑子》等篇目空间叙事结构与此类似。在这类空间叙事结构中,作者更多地是表达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但由于当时社会对于人们情欲的束缚,人们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婚姻爱情自由。因此,这类人神(怪)恋往往以爱情无果为结局。
三是某种因缘导致空间秩序打破—因果报应—空间秩序回复平衡。如在《灵鬼志·蛊》中,一个世代以放蛊、收蛊来致富的人家,由于他们事蛊造成周边其他人日常生活空间秩序的混乱,后来这家里不知情的新媳妇独自在家时灌杀了大蛇,没多久这家人遭到报应(染上疾疫、死亡略尽)。整蛊的人死了,周边其他人日常生活空间秩序自然就回复了正常。在《列异传·猎人化鹿》中,由于彭姓猎人世代以捕鹿为业、猎杀过多使山中原有的生态平衡这一空间秩序被打破,在一次山中捕猎过程中,父“忽蹶然倒地,乃变成白鹿”,得到报应,儿子就“终身不捉弓”;但是到了孙子时,孙子又重新捕鹿,射中祖父,孙子幡然悔悟,停止捕猎,山中回复原有秩序。这一类空间叙事更多的是为了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
上述第一、二两种空间叙事模式与当时鬼神信仰的观念分不开。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作者大多相信神仙、妖魅无处不在,所以他们创作的小说中自然就会经常有妖魅鬼怪出现在人们的俗世生活空间。第三种叙事模式则与佛家的“因果报应”论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发展和繁荣,“因果报应”作为佛教一个基本的宗教观念深入人心。当时许多志怪小说的作者都是佛教信仰者或爱好者。因此,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形成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叙事模式。
三、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功能
空间叙事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使得小说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生动,提高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促进了小说这一题材的长足发展。具体来说,空间叙事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主要具有以下功能:
1.通过空间叙事来使时间呈现空间化
时间和空间作为叙事的两个基本维度,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巴赫金曾就二者关系提出“时空体”理论,“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时空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两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存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时间界限,使得时间叙事明显呈现出空间化、跳跃性特征。以梦境和地狱两大空间叙事类型为例,其自身既是与现实生活不同的空间,却也是对现实时间的重要突破。如:梦境既可以预知未来,又可以见到已故的亡者(亡者的隐喻是逝去时间),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空间载体;地狱则是鬼魂的所在地,体现了古人对于逝去时间的一种空间处理。这就形成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独特的时空体。在梦境这一空间中,现世生活中的人可以从现实时间进入到逝去的时间,可以与亡故的人进行沟通交流,如《列异传·蒋济儿》就是蒋济的亡儿两次在母亲的梦境中诉说心愿。现世的人还可以在梦境这一空间中预知事情的发展趋势,从而突破了以时间为轴线的叙事方式的局限,达到预叙的效果。如《搜神记·三王墓》中的楚王就是在梦境这一空间中得知自己将被眉间尺杀死为其父母报仇的结局的。在地狱这一空间中,人物不仅可以与亡人相见,而且还可以穿越地狱再次重返人间。这一空间穿越的过程也蕴含着现实时间与逝去时间的对接。如《搜神记·胡母班》就是胡母班在阴间遇到了自己亡故的父亲,并在完成任务后又返回人间。
2.通过空间叙事来塑造主题化的空间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有些叙事情境下,空间叙事取代了曲折离奇的情节,详尽描绘空间成为小说的主题。这时“空间就成为一个‘行动着的地点,而非‘行为的地点”。尤其是那些宣扬宗教的篇目最为突出。如《幽明录·康阿得》作者力图通过佛家弟子康阿得死而复生来宣扬信佛的好处,但文本并不以叙述他如何死而复生的过程为主,而是用重墨详细描述康阿得游历地狱的见闻。《冥祥记·赵泰》也是通过佛家弟子赵泰死而复生来宣扬信佛的好处,篇目细致地描述地狱的景象。通过地狱不同刑罚的详细描述,使得读者看后不由心生畏惧。与地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福舍,又通过“受变形城”这一空间描述,交代了地狱受刑罚者的转世报应。正是通过地狱和福舍两种空间的对比描述,显示出不信宗教、为非作歹的人与信仰宗教的人的死后不同待遇,从而说服人们要笃信宗教,为自己积累福报。
在一些仙山洞窟类的篇目里,空间叙事也呈现出主题化的特点。如《拾遗记·洞庭山》先是叙述洞庭山的传说,后又借采药石之人的视角描述了山中灵洞的奇美。小说极力突出洞庭山这一空间的美好,目的就是表达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搜神后记·桃花源》通过武陵渔夫误入桃花源,描绘出一幅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的生活图景。情节淡化,空间叙事成为一些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主题。空间的细节化描写对后世中国小说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通过空间叙事来转换叙事视角
法国结构主义叙述学家托多罗夫所说:“视点问题具有头等重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从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而是以某种方式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小说中提供给读者的人物形象和空间图象,最终都是由人物和空间被观察的方式即叙事视角所决定。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往往是叙事视角发生转换的一个拐点。“空间感知中特别包括三种感觉:视觉、听觉和触觉。所有这三者都可以导致故事中空间的描述。通常,形状、颜色,大小都是通过特殊的视角由视觉接受。声音可以对空间描述做出贡献,虽然是在较小程度上。如果一个人物听到一阵很低的声音,那可能仍距说话者一段相当的距离。如果可以一字一句清楚地听清说话的内容,那么它的位置就要近的多,比如一间屋,或一道薄薄的幕帐之后。”例如在梦境这空间叙事中,叙述者就像附在做梦者身上一样,借着做梦者的感官来进行视听。《幽明录·换头》中“河东贾弼之,义熙中,为琅琊府参军。”为外聚焦叙事模式,叙述者对于作品中的主人公官职、身份等了如指掌,并一一交代。接下来,进入梦境这一空间,叙事视角就转换为做梦者贾弼之的视角,“夜梦有一人,面皰甚,多须,大鼻瞷目”,又听这个人说“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通过贾弼之的视角,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梦中人的长相及言语。因为梦境是一个私人空间,只有叙事视角转换为做梦者身上才能具体生动地描述梦境内容,让读者产生如入其境的真实感。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一些篇目中,叙事空间的细微变化可以引起叙事视角的多角度变换。在《续异记·徐邈》中,“徐邈,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觉邈独在账内,以与人共语”,在徐邈独自处以帐中、外面站有左右人这一空间时,文本以“左右人”的视点出发进行叙述:他们总是听到徐邈与人谈话的声音。接下来,在帐中但又在屏风外这一空间中,叙事视角换为门生的:他发现了一只大青蚱蜢。“虽疑此为魅,而古来未闻,但摘除其两翼。”还在相同空间内,叙述视角又变为全聚焦模式,叙述者如同无所不知的神仙一样,洞察到门生的心理:怀疑大青蚱蜢是个妖魅。夜里一青衣女子入邈梦,叙事视角又转换为徐邈。叙事空间的不断变化有助于叙事视角在不同的人物间灵活自然地转换,为小说制造悬念提供了条件。这种托梦的表现手法为后世的长篇小说广泛采用。
4.通过空间叙事来推动情节发展
“情节被‘空间生成”。空间叙事对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情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一些空间叙事是某些特定情节发生的必要条件。如墓穴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人鬼恋的必要环境。而《谈生》中的情节用序列来表示如下:A.谈生四十无妻;B.谈生家中闯入一个女鬼,二人结为夫妻;C.谈生没到女鬼复活的期限就用火光照视,女鬼离开前赠与谈生珠袍,并裂取谈生的衣裾;D.谈生到集市卖袍;E.睢阳王发墓验证;F.谈生及其子受封。如果缺少了墓穴这一空间叙事E,前面的女鬼就失去出处,后面的验证身份进行加封也就无从发生。
有时空间叙事又是故事情节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与空间叙事是情节发生的必要条件有不同之处。当空间叙事作为情节发展的必要条件时,空间叙事则是贯穿整个情节的全过程;当空间叙事作为故事情节的一个组成部分时,空间叙事就成为情节发展的具体过程。如《灵鬼志·道人幻术》,从道人进担人的笼子中,到笼子中的道人口中吐一妇人,再到此妇口中吐一外夫,空间变换成为了小说的情节。托梦交代或预叙结局的梦境空间叙事也属于此类。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有时仅作为情节发生的背景,与故事情节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这些篇目多以现实中真实的地点作为故事发生的场域,如《灵鬼志·周子长》“周子长侨居武昌五丈浦东冈头。”《甄异传·杨丑奴》中“河南杨丑奴,常诣章安湖拔蒲。”五丈浦东冈头、章安均为历史中实有的地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以现实中的地点作为情节发展的背景与作者的写作目的有关。虽然今天看来,志怪小说充满了奇异怪诞的色彩,但作者并不是有意好奇,而是认为这些事件实有其事,按照史传文学“徵实徴信”的原则进行叙述。
注释
①②④〔晋〕王嘉撰,〔梁〕萧绮録,齐治平校注:《拾遗记·卷四秦始皇》,中华书局,1981年,第101、116、105页。③⑤⑥⑦〔魏〕曹丕等撰,郑学弢校注:《列异传等五种》,《列异传·蒋济儿》,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第10、25、29、32、29、26、88页。⑧⑨〔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十八·安阳亭书生》,中华书局,1979年,第229、230、37、16、14、15、225页。⑩李剑国辑释:《唐前志怪小说辑释》,荀氏:《灵鬼志·嵇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6、531、642、642、396页。〔晋〕陶潜撰,顾希佳选译:《搜神后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页。〔晋〕张华著,祝鸿杰译注:《博物志全译》卷一《山》,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23页。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晋〕陶渊明撰,顾希佳选译:《搜神后记·徐玄方女》,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3、40页。〔南朝宋〕刘义庆撰,郑晚晴辑注:《幽明录·卷一·刘晨阮肇》,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1页。[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74—275页。[荷]米克·巴尔:《叙事学:叙事学导论》,谭君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106页。托多罗夫:《文学作品分析》,张寅德《叙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5页。〔南朝宋〕刘义庆撰,郑晚晴辑注:《幽明录·卷一·换头》,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30页。[以色列]卓拉·加百利:《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责任编辑: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