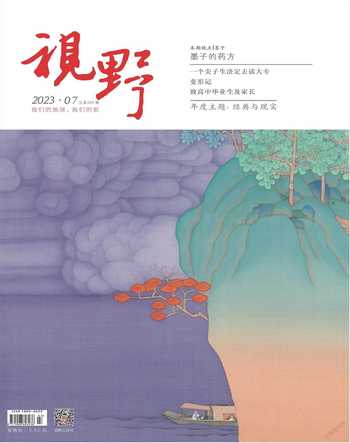向帝国挑战的剑侠
鲍鹏山

一个独行的身影踟蹰而来。那是一个独行客:他光着头,赤着脚,穿着粗布的衣衫,面目黧黑,焦虑急切。他腰中的短剑与眼神中的坚毅,使我们心中一惊:这是一个侠客!
是的,这就是墨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剑侠,最伟大的剑侠!
《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也就是说,墨子最初乃是儒家的门徒,学孔子的思想,但越学越不对胃口,越学越觉得儒学不是那么回事。儒者的礼那么繁琐而不切用,儒者提倡的厚葬浪费财富而使人民贫穷,长期服丧浪费生命而妨碍正事,所以他背弃儒家了!他当了儒门的叛徒了!这一叛,非同小可,这不仅仅是叛出师门,而且是政治上的背叛。我们知道,儒家是热烈礼赞周王朝,维护周王朝的文化的,他既叛儒,当然也就背叛了周王朝,成了周王朝的叛臣逆子了!
叛徒墨子自据山头,自立门派,自树旗帜,并且还真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的学派及思想,到了战国中期孟子的时代,已是弥满天下,压倒儒学。儒学眼看就不济了。所以孟子才有那么大的“道德愤怒”,骂杨朱为无君,骂墨子为无父,全是禽兽,必欲扑灭之而后快。但是,虽然儒学在战国中期又出现了孟子这样的大师,且这位大师又如此党同伐异,哓哓善辩,仍不能阻止墨学的传播与发展。
我一直把墨子称为向帝国挑战的剑侠,有两点依据:一、他是剑侠;二、他是在向一个有几百年赫赫历史与辉煌文化的古老帝国及其文化挑战。
韩非子曾列出危害国家的五种蛀虫,其中之一就是“带剑者”。这“带剑者”就是墨子后学的流亚。韩非子说他们都常常“以武犯禁”。后来汉代的公孙弘、班固也极力贬斥这类人。公孙弘用行政手段,借国家机器来杀这类人,班固则是借文化讲坛来骂这类人。但司马迁不同,他在《史记》中专列一章《游侠列传》,并对秦代以前游侠的“湮灭不见”感到极大的遗憾。
正是因了司马迁对游侠如此珍惜,认为他们有足够的值得肯定与赞扬的地方,他才记载了汉代的游侠朱家、郭解等多人,并给予深深的敬意。
这墨子学派,简直是一支敢死队,特别行动队!这些粗短服饰的“侠客”们一个个怒目圆睁,随时拔刃相向,与宽袍大服、风流儒雅、口颂诗书的孔门“君子”,真是大异其趣了!
这些勇士们关键时候是可以弯弓搭箭舞刀弄棒的。《游侠列传》中说游侠往往能为别人的厄困灾难而奔波,不爱惜自己的躯体——墨子听说楚国将要攻打宋国,便从齐国出发去阻止,这不是千里奔赴,为人解难吗?齐国与楚国,在交通极不便的那时,真是令人望而却步的遥远与坎坷啊!他一走便是十日十夜,这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躯体吗?最后墨子终于说服楚王,使之打消了进攻宋国的念头,弱小的宋国得以保全,这不是“存亡生死”吗?
墨子著作中,自第五十二篇《备城门》至第七十一篇《杂守》,现存共十一篇,都是谈防守。他反对攻,当然尽力研究守。司马迁就说他“善守御”。这十一篇完全是谈防守的技术,若和《孙子兵法》参看,是很有意思的。孙子能从哲学与政治角度讲战争,墨子却纯从技术角度谈战争。孙子颇重视战略,墨子却只留意于战术。看他这十一篇兵书,其实他的防守思想并不新颖,更不出色,新颖的是他的科学知识,出色的是他高超的技术。他的防守思路不新颖可以理解,因为他不是进攻的一方,只谈防守,并且是消极的被动的防守。敌方攻城门怎么办?敌方爬城墙怎么办?敌方挖隧道陷城墙怎么办?……凡此等等,都是消极应对,难怪后世“墨守”一词乃是贬意。看来墨子因为一味地反对攻,所以他不理解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彻底否定“攻”(注意,墨子讲“非攻”而不是讲“非战”,看来,他反对一切主动的战争),否定战争的一切正面价值,以至于也否定了主动进攻于防守的价值与意义。他自居于弱者一方,不想进取,只图保全,这就使他的防守思想很保守。他的防守之所以成功,只是他的工具先进,设计科学,禽滑厘等三百弟子在宋城上守御,使得楚国千军万马望而却步,乃是凭借他“守圉(御)之具”的先进,超过了公输般的“攻城之械”。从他这十一篇兵书看,他是一位专业木匠、科学家,看来他讲勇,更讲科学、讲技术。他挖隧道,其长度、宽度,他造器械,其尺寸、方圆,都一一标明,宛如现代兵工厂的兵器设计图。孔子是不谈战阵之事的,卫灵公向他讨教这方面的知识,他说他只学过“俎豆之事”(礼让揖节),而“战阵之事”不曾学过。孔子反战,乃不言战。墨子反战,却是以战反战以守反攻。这又是儒侠(墨)之间的大区别之一。
但墨子最锋利的剑还不是他的守城之具,而是他思想的锋芒。这思想锋芒的寒光直逼一个大帝国的咽喉,使本来就苟延残喘的周王朝,顷刻间就失去了苟活的依据。
墨子毕竟是孔门之徒,所以,有些思想与儒家还是一致的,这是他认为“理自不可异”的地方,如他的《亲士》《修身》《所染》诸篇,其思想、观点,与儒家如出一辙,不大有意思。有意思的是他与儒家不同的地方,这才是墨子自己的真创见。有些题目,一看就知道和儒家对着干,《非儒》不说了,《兼爱》《尚贤》直刺儒家的“亲亲”与贵族政治,《非乐》《节用》《节葬》直刺儒家的礼乐文化与厚葬靡费的传统,《天志》《明鬼》反对儒家的道德政治与敬鬼神而远之的观念,《非命》反对孔子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可以说,墨子由孔儒的思路,来个反向思考,从而别立一派,成一家之言,卓然而为一代大宗。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也正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大侠客作派。
那么,何处是墨子的剑锋所向呢?首先,他有意地忽略周王的存在,不把他看作天下共主,而是把他摒弃于天下政治之外了。这种冷处理尤其恶毒,清冷而落寞地苟存在洛阳的东周最怕的就是被人遗忘。墨子抬出一个有意志的“天”,来代替周“天子”,诸侯也只需对“天”负责,而没有什么“天子”值得去在意。墨子也反对战争,甚至钻牛角尖到反对一切战争,但他并不像孔子那样,从政治角度来考虑战争,而是从道德角度来考虑战争。战争的不义,在孔子看来,乃是由于不是出自天子而是出自诸侯,是政治的失序。而在墨子看来,攻打别国,正如同窃贼与强盗,其行为本身即当否定,不论什么身份的人都不能偷窃,所以,不论什么身份的人当然也就无权发动战争,哪怕是周天子,也不具有偷窃杀人的道德支持。
墨子否定周王朝,更主要表現在他对周文化的否定上。他的“兼爱”是反对“礼”的等级尊卑制度,“尚贤”是反对“亲亲”的贵族封建世袭制度。这两点实际上是周王朝政治运作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环节。他的“节用”“节葬”“非乐”又是反对周王朝的文饰,这正是孔子所倾心向往的“郁郁乎文哉”的王朝风范。墨子认定:“俯仰周旋,威仪之礼,圣王弗为。”显然,制礼作乐的周公在墨子这里决不是圣王了,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周王朝当然也就不是什么圣朝了。既如此,周王朝也就是可以被取代的。如何取代呢?在这里,墨子的思想放射出令人惊异的色彩,他提出了一个在后来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都没有人敢于响应的政治构想,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民主联合。
“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至乎乡里之长……”
在这里,天子是在“尚贤”的标准下民选的,天子而下则有三公,构成最高权力机关,然后是诸侯国君,左右将军大夫,直至乡里之长,相当于基层组织。现行的政治体制彻底被抛弃了,贵族特权被否定了。除了民主选举这一点外,如果把诸侯国改成郡、县,不极像后来的郡县制吗!而其通过民众选举,推举贤良、圣知、辩慧之人为天子、三公、诸侯国君、民之正长,则极易使我们想起卢梭。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思想啊!
(摘自《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