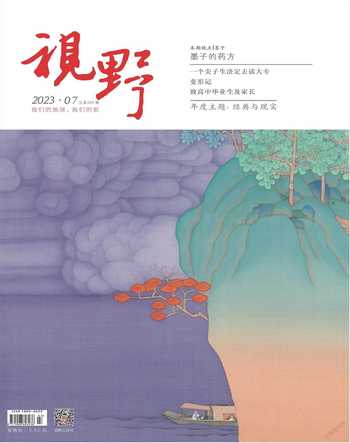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一个下午
时潇含

巴黎市区有一片巨大的墓地,叫做拉雪兹神父公墓,那里有三十多万座坟墓。
不过与其说这里是墓地,不如说是一个树影重重、雕塑林立的大公园。
这里的地形上下起伏,透过树冠的缝隙,星星点点的阳光洒在小径上。
没有一丝阴霾与消沉,风很柔软,人走在其中,感到巴黎变得温和了起来。
虽说这也是一个景点,但在相比之下这里人迹稀少,即使是在某个名人祭日,粉丝蜂拥而至的时候,也比不上卢浮宫或是凯旋门百分之一的热闹。
可能也是由于它十分庞大的缘故,在里面行走时只在很偶尔的时候,才会看到两三个闲人。
他们有的坐在树荫中读书,有的沉默地读着墓碑。
总而言之,这里没有充斥着整个巴黎的吵闹。
相比于埋葬的是被称为塑造了法国民族性伟人的先贤祠,而这里沉睡的名人就更为雅俗共赏了。
如今也埋葬在这儿的巴尔扎克称之为“一个按影子、亡灵、死者的尺度缩小了的微型巴黎,一个除了虚荣之外无任何伟大可言的人类眼中的巴黎”。
这里沉睡着的有莫里哀、拉封丹、巴尔扎克、普鲁斯特、王尔德、德拉克罗瓦、毕沙罗……
我去那里的本意是想看看他们的墓志铭,不过不知道是为什么,这里的墓碑只写最简单的信息,其余不著一字。
有的家族墓不是墓碑,而是一个一层甚至两层楼高的小亭子。
哪怕是名人也仅有肖像雕塑或代表作的雕刻来展示出他们最后的面孔。
没有墓志铭可读,我就当来逛了个公园吧。
除了名人之外,还有许多的普通人也葬在这里。
我在一个墓碑的缝隙里看到了一张被水沁湿的纸,上面写着“我十分想念你”。
说实在的,虽然这些名人是拉雪兹神父公墓出名的原因,不过除了一座光秃秃的墓碑,其实看不到太多的东西。
然而当我晃到了墓园的一个角落里之后,却发现了些有趣的东西。
那是一片集体的纪念性雕塑,有的是为了纪念在巴黎公社运动中被集体枪杀的人们。
有的是为了纪念被德国迫害的犹太儿童,他们的石碑上刻着:“你的记忆是他们唯一的葬礼。”
还有为在二战中战斗的法国或是在法国战斗过的别国士兵所建的雕塑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他们承受痛苦也承载了希望,请你也为你的自由战斗。”
不过让我产生好奇的,是这些关于二战对犹太人迫害的纪念碑透出了一丝微妙的、复杂的情绪。
首先让我困惑的是一个反复出现的词——déporté。意思是驱逐。
那些石碑上反复提到,有很多犹太人被驱逐出境。这让我挺好奇的,为什么不是“被抓走”或者“逃离”,而是驱逐呢?
有一个石碑上刻了歪歪扭扭的一行字,写着“我们是900个法国人”,下面写着1944年900个法国人从法国被送往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一年后只有22个人回来。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驱逐”说得还是委婉了。
法国北部曾被德国人大规模地占领过,不过即使是在没有完全被占领的南部,法国政府都曾大规模将犹太人遣送至德国纳粹集中营。
这样的痕迹很深刻。在我家附近有一条废弃的铁轨叫做Train de Loos,原来就是在这条法国国营铁路上,源源不断的法国犹太人被送进了德国集中营。
1995年,当时的法国总统首次公开承认,法国曾协助纳粹德国将犹太人运往纳粹集中营,“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

2009年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裁决中表示,法国维希政府在没有受到德国占领军胁迫的情况下,驱逐犹太人,应该对这种“允许并协助把反犹迫害活动的受害者驱逐出法国”的行为造成的伤害负责。
这并不是被人逼迫的“平庸之恶”,而是有主观意识的行为。
在一个石碑上写着一句话:“Tous avons sonde des abimes en nous-mêmes et chez les autres .”意思是“所有人都探索了自己和他人的深渊”。
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在欧洲我所看到的大部分纪念馆,都是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很少有人站出来说,我们承受了痛苦,我们战斗过,但同时我们也是帮凶。
这样的承认本身已经意味着共同的记忆,而就如石碑上所写的那样,“记忆是他们唯一的葬礼”。
我看过一位教授讲述主权与人权的关系。
他说:“对内争人权,对外争主权才是有意义的,主权是为了维护国民的人权。因为争主权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侵害本国人民,但如果国民受到来自国内的伤害比国外更甚,那就失去了争主权的立足點。”
有了主权,才不会出现德国人在欧洲各地建集中营这样的事。
但是光有主权并不足够,因为法国政府可以主动发起反犹运动,自己在境内建集中营,他们甚至不需要德国人的指导,他们可以自主自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地建起集中营。
不过不论如何,承认这段历史已经意味了很多。
共同的记忆是责任,也是权利,如果连记忆都不被允许,那么不单放弃了这个权利,而且是放弃了正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