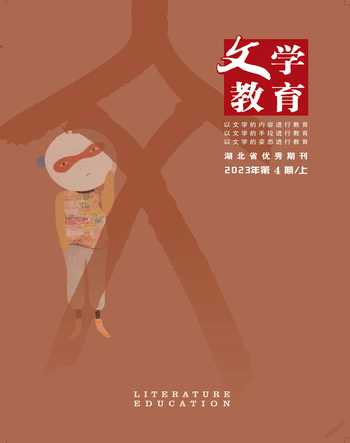叙述视角下太宰治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周豆
内容摘要:太宰治是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作家,本篇论文主要研究太宰治四部作品在不同的叙述视角下的女性形象,《人间失格》和《GOODBYE》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描写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而《维庸之妻》和《斜阳》是以女性独白的形式从女性自己的思维和所见所感出发描写女性。叙述者视角的不同往往影响读者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太宰治喜欢从女性独白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同时也不乏有很多自传性质的作品是从男性的视角去感受世界,不管视角如何变化,这些人物身上多多少少带有太宰治自身的性格特质。所以本文从叙述视角出发,去分析太宰治本人所见到的女性或带有自身特质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太宰治 女性形象 叙述视角
太宰治是日本无赖派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虽然无赖派文学有一定的消极和病态表现,但在当时日本战后文坛引起了极大反响,也为日后日本文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在生活中找不到希望,内心颓废却只能从文学作品中去找寻共鸣,太宰治的颓废主义写作正是在当时出现,给处于困顿中的日本民众以精神上的共鸣。太宰治的审美是病态的,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在太宰治的一生中,女性对他的影响很大,他作品中的女性都与他现实中所遇到的女性有重合,在这种病态的审美下,女性多半是以悲剧收场。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就像是自我认知和他人的评价。在当时的日本,女性地位十分低下甚至完全沦为男子的附属品,她们自己或许有良好的教养、敢于反叛的革命精神或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好品质,可这些品德在男性的视角下又显得不那么重要甚至根本不会在意,他们通常喜欢美丽、善良,温柔、纯洁的女性。在太宰治的作品中,女性数量和所占篇幅也十分多,这与太宰治本人生活密切相关,很多作品中的女性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并且记忆深刻的女性,还有一些女性身上被赋予了他自己性格的某些特质或他眼中理想化女性的特征。太宰治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女性众多的家庭,从小便对女性有一种独特的情感,在文学作品中展示出来就是大量描写女性。此外,太宰治从小与母亲、乳母、叔母分离,使得他对女性产生了一种渴望、恐惧及嫌恶的矛盾心理。所以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基于这种特殊的情感与矛盾心理,写作了大量女性题材的作品,甚至在多篇小说中通过女性独白体的写作手法对作品进行创作。所以在不同的叙述视角下去分析和认识他的女性题材小说可以更好的认识和理解他对女性的矛盾心理。
在当前男性作家比例远高于女性作家的情况下,文学史上令人记忆深刻的女性也常常出自男性之手,她们通常代表着美和超脱,这些女性多半是男性作家理想中的女性形象。不可避免的,文学创作中不可能没有女性的存在。太宰治一生创作了许多典型的女性,甚至在他晚年直接用女性独白的方式进行剖析理解,渴望探求她们内心深处的痛苦以此来反映社会现实。
这样,在太宰治的作品中,就有独特的从女性独白和男性叙述两个方面展开的小说,在本文中,要对比分析太宰治笔下的女性形象就不得不从不同性别叙述者出发,找到他文中男女性视角下女性形象的特点。
一.半自传体私小说的写作
私小说是日本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日本地域狭小,民眾与外界交流不便,导致多关注自身,文学也开始探求人的内心世界,于是出现了第一人称手法叙事的私小说,正如久木正雄所说:“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暴露出来的小说”,个人的思维只能了解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创作中,作家笔下的人物不仅仅是作品中的形象,也是内在的作家。太宰治是私小说领域的重要作家,他笔下的女性也不是理想的美好形象,更多的是他在生活中见到的女性的异化,甚至许多女性身上还带有太宰治自己的颓废、忧郁及不幸的遭遇。太宰治的许多作品是他自己生活的写照:《人间失格》以“我”看到大庭叶藏的三张照片后的感想开头,中间是叶藏的三篇手记,而三篇手记与照片对应,分别介绍了叶藏幼年、青年和壮年时代的经历,描述了叶藏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丧失为人资格的道路的。作品中太宰治巧妙地将自己的人生与思想,隐藏于主角叶藏的人生遭遇,藉由叶藏的独白,窥探太宰治的内心世界——“充满了可耻的一生”。在发表该作品的同年,太宰治自杀身亡;《Goodbye》是太宰治生前最后一本小说,在他自杀后这篇小说也以未完成的状态存在,完全不敢相信这篇小说是太宰治在绝望的面对死亡时所写下的作品,《Goodbye》作为绝笔,行文故事却很幽默。不像是自杀前的文章,甚至不像是太宰治的文章。诚然,太宰治也有《御伽草纸》这类滑稽有趣的小文,却都不像《Goodbye》这般冷静明快。太宰治用这种冷静的幽默笔调与过去的种种道别,他借用田岛的口吻与自己的情人说再见,向世人说着自己最后的爱,用这样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笔调反而有一种爱与释然;在《维庸之妻》中,太宰治用维庸来指代文中的男主人公太谷先生,维庸是法国中世纪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对现实世界失望,通过放纵自己的欲望来达到思想的升华,维庸与太谷先生的融合同时更加是与他自己融为一体,本文以女主人公小佐的视角写了丈夫太谷的战后颓废、绝望,这也是太宰治自己生活的写照;如果说《人间失格》是人生绝望的吟唱,那么《斜阳》就是繁华落尽最后的一抹明亮。《斜阳》从和子视角出发用一种近乎释然和超脱的姿态,表现了日本战后混乱背景下没落贵族的斜阳般的生活。太宰治把自己的经历加到直治与上原两个人身上,直治有贵族气却不得不在社会变迁中成为平民,渴望在放纵与浪荡中建立与民众交往沟通的桥梁,上原从小说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家庭责任感,并且从酒馆的人的对白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他的评价很恶劣,在现实生活中与女人有着诸多纠葛,这和作者太宰治自身很像。这些作品中的人物或多或少带有太宰治自己生活的影子,看到过别人对他的评价:“当他戴上那面滑稽的假面时,他就是你们眼中文学上的巨人。当他摘下那张假面时,他就变成了你们眼中社会的废人。”文学就是太宰治的面具,撕下面具的他就是他笔下那些在无奈、绝望中挣扎的破落不堪的人物。太宰治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私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故事异化写下来,在当时的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反映了战后日本集体的迷茫、失望心理。
二.男性视角下的女性形象
女性以其独特的美和勇于反抗的精神成为文学作品中最常描写的人群,而在男性作家居多的情况下,女性形象又和现实有所偏颇。如:《雪国》中的驹子和叶子是美的象征和符号,是作家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女性形象;《悲惨世界》中善良却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芳汀,是作家对底层人民悲惨命运同情的产物;《边城》中天真善良、活泼灵动的翠翠是爱情和大自然的产物,是沈从文“天人合一”思想的代表。纵观古今中外的男性作家作品,他们眼中的女性形象总是带有自身理想或作品要求的特质的,太宰治的小说也不例外,他笔下的女性常常生活不幸却还是坚强、善良、面对悲痛的人世间积极向上渴望活着,他笔下的男性充满颓废厌世思想,尽管想融入社会却被排挤被丢弃,当然,他的作品中也有尘世中少有的安逸、幽默和冷静,足以可见在厌世文学的面具下的太宰治尽管充满颓废思想,也期待成为别人眼中的“神一样的好孩子”[1],死亡是他自我的超脱,颓废是他生存的面具。在这种浓重的半自传男性视角下的颓废气息中的女性形象也是畸形病态的美与丑的结合体。
《人间失格》中的女性形象较多,基本囊括了叶藏一生中遇到的所有女性,重点集中在恒子、静子和祝子身上。恒子是一个陪酒女,诈骗犯的妻子,在社会的底层艰难的活着,在叶藏穷困潦倒时施恩于他。叶藏对恒子的描述也很少,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她本身给人的印象,也是完全遗世独立的女人,仿佛身旁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随风狂舞”[2]尽管是处在底层社会的一个丑陋、穷酸的陪酒女,她作为女性所散发出来的独特气质也如影随形。在恒子身上也有美与丑的矛盾,她在丈夫入狱后以陪酒女的身份艰难的生存着,面对生活的重压她反而是善良的去帮助落魄的叶藏,丈夫入狱后她也每天给丈夫送吃的,就是这样一个温顺又善良、落魄又卑贱的矛盾形象是叶藏一生中最初的爱,也许仅仅是因为与她相似的落魄感、或者是因为约定跳海却独自活下来了的愧疚,但不管是哪种爱,都对叶藏后来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静子是一家报社的记者,丈夫去世三年和女儿相依为命,在叶藏离家出走的时候接纳了他,给他介绍漫画的工作,静子在叶藏的眼中是离家时的救星,是善良、质朴且可靠、稳重的,她值得拥有简单的幸福,可是叶藏又同时认为静子是丑陋的,认为她的睡相“活像四十多岁的男人”[3]。祝子是叶藏人生中遇到的女人中对他影响最深刻的,唯一可以称得上是妻子的“天使”与“魔鬼”并存的人,是信赖他人的天才。祝子的出现如天使般拯救了处于迷茫困顿中的叶藏,他将祝子比喻成一朵鲜花。叶藏眼中的祝子是纯洁可爱、活泼灵动的存在,是第一个劝他不要喝酒的女人,在叶藏心中完美得如天使一般的女人。生活的戏剧性转折总是来得太快,就在叶藏以为自己已经慢慢变成一个普通人时,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小小新娘被别人玷污,祝子也是在那晚之后变得战战兢兢,失去了她的纯洁完美变成了一个可怕的魔鬼般的存在。《人间失格》是带有半自传性质的一本小说,其中的许多人物是有原型的,这些叶藏见到的、想到的事大部分都是太宰治自己经历过的。他能够清楚地记起崛木“五官端正,肤色黝黑,穿笔挺的西装,领带的花色十分朴素,打了发蜡,梳着整齐的中分”[4]的样子,可是那些在他生命中起重要作用的女人们他却没有正面描写,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式的回忆,甚至连名字都记不清楚却记得一个毫不相干的寿司店的老头的模样。也许叶藏不是不记得而是主观的不愿意想起,作者也不愿意去描写这些女性,希望通过遗忘來减轻自己内心对这些女人的愧疚,所以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把她们的样子抹去以减轻负罪感。
《Goodbye》是太宰治未完成的遗作,描写的是田岛请永井娟子假扮妻子来与情人告别的故事,其实这也是太宰治对自己的情人、对这世间所有人的爱的告别,这篇作品一改太宰治小说中的颓废厌世情绪,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冷静幽默。通过田岛的角度塑造了永井娟子这样一个美与丑并存的女性形象,她高贵优雅,在路上引得人们频频回头,声音却如乌鸦一般难听;在社会底层做着行商的活计,为了生存在努力,工作时力大如牛,十分卖力气,作为一个年轻女孩子没有娇气,表现了太宰治之前的作品中都不曾有的对生的渴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可是她同时又是贪得无厌、食量惊人的,在田岛眼中她的美是超凡脱俗的可是她同时又是贪婪、凶狠的。娟子与之前太宰治笔下的女性形象都不一样,她是真实又不真实的,却最为有血有肉的存在,比起一心求死的恒子、处事稳重的静子和敢于信赖的祝子来说,她更像是当时处于日本底层中无奈却又积极努力生存的人。用这样生机勃勃的方式与他眼中的不会饶恕他的世人告别,他就这样自私的离开了,留下自己破败的人生和“气弱”[5]的文学,希望世人在读到他的告别时能记得他曾经也是那么渴望爱与被爱;他曾经也有这样生机勃勃的时刻;他也曾渴望撕下丑陋自私的假面具以真实的自己面对人们;希望人们在谈到他时能说上那么一句“我们认识的太宰治,个性率真、幽默风趣。只要不喝酒,不,就算喝了酒……也是一个像神一样的好孩子”。在《Goodbye》还未完成他就等不及的离开了这个让他充满憎恶的人世间,他太想死了,甚至连‘Goodbye’都来不及说完。
在男性视角下选取《人间失格》和《Goodbye》两个基调完全不一样的作品,一个是颓废的太宰治、一个是热爱的太宰治,但这两个作品中的女性都有着男性视角下女性的独特美和她们表现出来的男性无法忍受的丑陋。女性形象通过叶藏和田岛的心理独白和所见表现出来,男性视角下的女性都是两面性的,许多经历、遭遇、思维各异的女性,她们在常规中又有错位,不只是片面的美或丑,善或恶。
三.女性独白下的女性形象
从女性自身来认识自己和周围的女性,这样的角度相当于是男性作家将自己化身为女性存在于文学作品的人物中,无异于我们平时对对方思想的揣摩,只不过文章更加具体细腻。太宰治晚年热衷于女性独白体小说的创作,仿佛只有把自己的思想投入到他笔下的女性中才能获得写作的动力,从女性心理出发,寻找隐藏在她们心灵最深处的恐惧和欢乐,运用独白体的,很大程度上在于避免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让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而单独强调女性,是由于女性在主流社会的评价标准下,一直被视为弱者,处于从属地位,用他们的视角来叙述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感悟则更能激起读者的共鸣。战争失败后,男性陷入了集体的失望期,他们不关心一切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那么女性在彼时又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和状态生存着的呢?太宰治借由女性独白的方式探求女性真正的内心想法,用最底层女性的角度去感知社会,也更能感受到战争结束的萧条和社会集体的无望。
《维庸之妻》是太宰治女性独白体的代表作,在小说的标题《维庸之妻》中,维庸指的是法国中世纪的抒情诗人,他可谓当时社会的怪胎,集许多矛盾的因素于一身。死亡的主题,在维庸的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一生中,他每时每刻都感到死亡的威胁。死亡的恐怖如同一个巨大的魔鬼,紧紧地纠缠他。小说中的诗人大谷与维庸有着很多类似的地方:懦弱、彷徨、游手好闲,所以作者借“维庸”影射懦弱无能且无所事事的人。然而,大谷的妻子小佐与他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热情善良面对生活的重压一直维系着家庭,出门做女佣为丈夫还清债务。在《维庸之妻》中起初,映入读者眼帘的是一个逆来顺受、相夫教子的传统妇女。丈夫大谷出身于落魄的贵族家庭,虽名为诗人,实则终日酗酒作乐,毫无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感。当她在为儿子生病的事情烦恼时,小酒馆的老板夫妇却因为大谷拖欠酒钱找上门来。为了替丈夫还清欠款,大谷的妻子取名为小佐,带着孩子在酒馆打工。通过这个情节,我们能看到女主人公坚强勇敢的一面。可从一个传统的妇女转变为一个招待女对小佐来说仿佛只是一瞬间的事,她去小公园坐了坐就完全没有心理负担的开始了自己的酒家女生涯,这是一个充满无奈和悲剧的抉择。但是,这部作品是很特殊的,成为女招待之后,女主人公反而得到一种解脱,不是再像以前那样和丈夫毫无精彩可言的生活,而对于主人公而言,她可能更喜欢现在的生活,不但没有丝亳的伤心和悲怆,反而觉得比以往更加快乐,这种独特的心理也体现了一定的颓废和自我破坏的精神,原本温柔贤淑的女主人公,在一步步的堕落。原本其对于丈夫的堕落,充满着无奈,但是现在她却以一种比丈夫更快的速度在跌落,而且也更为彻底。但是给人一定冲击的是,女主人公有一种完全积极乐观的心态,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其完全摆脱了道德的枷锁。在这方面上,女主人公比丈夫更为勇敢,使得女主人公也逐渐变得强势起来。在文中,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小佐和儿子相依为命,应该是很爱自己的儿子的,可是她却常常用一些难听甚至可以说是感到厌恶的话来形容她的孩子:“虽说是自己的孩子,可这样的表情的确让人觉得他有些愚蠢。”“说不定是脑子出了什么问题。”在文中,她经常用愚笨,脑子有问题这样的词来形容他,单看这些句子恐怕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说的话,可见她虽然爱自己的孩子但在内心深处却是拒绝这样天天带孩子的毫无热情的生活的,所以在逃离时她比大谷先生显得更快速、从容。
文如其题,《斜阳》描写的是封建贵族家庭斜阳般的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颓废和无奈与此同时还表现了一丝生活的光彩照人和人性的生机勃勃。就我看来,《斜阳》与太宰治其他作品都是不一样的,尽管它也同样表现了浓重的阴郁、颓废气息,但刻在人物身上的与众不同的生命力是太宰治对生活努力的象征。读了很多太宰治的文章,母亲的形象一直很少出现,就算出现也只是虚无缥缈的影子般的存在,而在《斜阳》中,太宰治塑造一个在行为和精神上都可以称为贵族的母亲形象。在《斜阳》的开头,太宰治就借直治之口称母亲为“真正的贵族”:“真正的贵族大概只有妈妈了吧,她是名副其实的,让我等之辈望尘莫及。”文章主人公和子把生下喜欢的人的孩子成为妈妈作为她的道德革命,如果是直治的反抗是激烈的以生命为代价的无奈,那么和子的反抗就是另一个角度的通过为自己的热爱而像太阳一般活下去的信念。和子离婚后与母亲生活,在家道中落后搬到农村,相比于之前有佣人照顾的日子,在农村的生活处处需要她自己动手。《斜阳》中的和子是个坚韧的女性。一个对金钱毫无概念的落魄的贵族,一个胎死腹中又与丈夫离婚居住娘家的女性,这样的一个女子,即便在当今的社会,也不免遭受周围人的非议。然而在经历家道中落后,她勇敢的面对新的生活。下田劳作,经营小店,坚持不论之恋,这是她对生活对伦理的反抗。作为一个贵族阶级的大小姐,她完全没有压力的下地干活、服侍母亲,显示出了一个贵族小姐娇生惯养之外的坚韧和勇敢。这样的和子,在充满颓废的灰色地带中成为一抹光亮,尽管她的做法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可是这是她对自己生活的热切追求。在母亲离开后,贵族社会消亡,和子对道德革命的追求却刚刚开始。文章由和子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母亲、弟弟和情人,同时审视自己的道路,读者从中也可以感受到和子对自我的认识和肯定,把生下孩子成为私生子的母亲活下去作为自己反抗社会救赎灵魂的开头。母亲的死代表贵族阶级的消亡、直治的死是不能融入社会却渴望脱离身份的贵族人的陨落、和子的斗争代表了选择面对社会并积极找到自己人生目标的贵族的新生活。“斜阳”是没落贵族的黄昏也是新兴阶层的朝阳。
从女性视角下感知女性形象,选取了《维庸之妻》和《斜阳》两篇文章,小佐在绝望的生活中之渴望能活着就好,和子却在所有人都离开她的情况下,希望带着自己的道德革命像太阳一般活下去,作为太宰治笔下的女性,他们却意外的都渴望活着,与男性的颓废、死亡相对,她们在面对社会普遍低气压的环境下,找到自己活着的意义并且积极与社会抗争。从女性视角来看,她们不局限于表面或言语,更多的是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在社会集体失去希望时,这些女性却表现出了独有的属于女性的坚强。
我们可以看出太宰治描写的女性经典形象,女主人公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甚至比男人更为坚强。而这些女主人公的共性,基本都是一开始是温柔贤淑的完美女性,但是由于生活的逼迫,而逐渐走向堕落的道路。并逐渐摆脱道德的枷锁,可以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世俗,在堕落的过程中体会到快乐。不管是从男性视角还是女性心理独白来看,她们都不是单纯的片面的符号,而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有血有肉的女性,从女性这一日本社会中的独特人群的迷茫堕落中也反映了社会现状,体现了太宰治对迷茫不知所为的社会的批判。对爱的渴望以及对女性厌恶的心理。正是由于太宰治在一生中受到过几次女人的伤害,所以在其创作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描写出的基本上都是表现女性的残忍和勇敢。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对自己理想中的女性追求,所以其他作品中又会塑造很多温柔贤淑的女子形象,正是这种又厌恶又向往的矛盾心理,使太宰治作品中刻画的女性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6]
注 释
[1]太宰治.人间失格[M].烨伊,译.湖北:武漢出版社,2018.
[2]太宰治.人间失格[M].烨伊,译.湖北:武汉出版社,2018.
[3]太宰治.人间失格[M].烨伊,译.湖北:武汉出版社,2018.
[4]太宰治.人间失格[M].烨伊,译.湖北:武汉出版社,2018.
[5]三岛由纪夫:太宰治"气弱",人也很讨厌。
[6]孟德林.浅析太宰治斜阳中和子的感情世界[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03)
本论文为吉首大学校级科研课题《核心素养下的高中语文课堂导入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Jdy22169。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