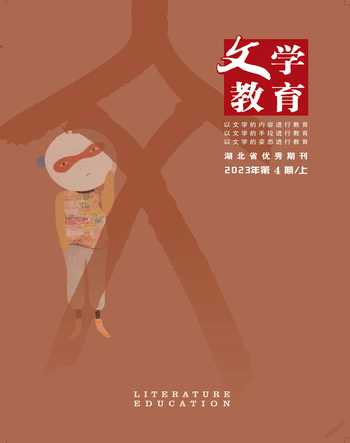朱山坡小说集《萨赫勒荒原》中的存在之思
内容摘要:《萨赫勒荒原》中,朱山坡的写作空间由乡村转向都市乃至国外。“荒原”意象是朱山坡新的创作标识,它是现代人在世的生存体验,主要的表征是孤独与悲伤。《萨赫勒荒原》中的主人公踟蹰在世界上,面对的是精神之困、存在之痛。此处的孤独与困顿,促使主人公们逃离到别处寻求希望与崇高。当别处变为此处,崇高随即呈现残酷的一面,理想与现实之间有巨大断裂与偏差。但朱山坡的“荒原”不仅是颓废的,在荒原中寻找本真存在与自我蜕变,是朱山坡对世界的新塑形,也是《萨赫勒荒原》的存在启示。
关键词:《萨赫勒荒原》 荒原 存在
从颇具辨识力的米庄、蛋镇到萨赫勒荒原,朱山坡写作的空间在进一步扩大,收集在《萨赫勒荒原》中的九篇短篇小说中,除了《香蕉夫人》承续了其之前南方地域特征外,其他的故事发生地均没有明显的地域性,有的故事涉及到非洲、美国。地域性的淡化或改变意味着写作焦点的转移,在《萨赫勒荒原》中,主人公是援非医生、城市自由艺术家、公务人员,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乡村小镇的逼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缺失,但他们面对的是“荒原”。在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中,朱山坡说:“‘荒原’辽阔、寂静、苍凉、孤独,是最接近苍穹宇宙的地方。但在我的小说里,更多的是指‘内心的荒芜感’吧。”可以说,“荒原”意象是朱山坡新的创作标识。作为南方写作的拥趸者,朱山坡转向了更普世、更阔大的生存体验领域。《萨赫勒荒原》中的主人公面对的是精神之困、存在之痛。此处的困境,导致对别处的追寻,于是远到异国他乡,近到别人家的阳台、一张床、一把椅子,都成为主人公的精神寄托,它们寓示着一种对乌托邦的、希望的追寻,而别处的虚无与崇高,未必能够与理想完全契合。正是在此处与别处的落差中,生命的韧性得以彰显。
一.此处:困境与孤独
“对于乡村命运的深切关注,是朱山坡小说创作的核心所在”[1]。从朱山坡在文坛崭露头角开始,边地、乡土、底层就成为理解其创作的关键词,其笔下的米庄、蛋镇是“新南方写作”的地理标识。但边陲村镇的故事也是世界之一角,朱山坡本人也认为,南方写作是面向世界的。在文学空间上,米庄的故事是关于乡村的,蛋镇的故事是关于小镇的,《萨赫勒荒原》中的故事则是关于都市的,这其中似乎也暗合着作者的生活轨迹:从乡村出身,到城镇工作,再到区首府工作。作者的眼光从乡村看到城市,发现身陷生存困境与迷惑的人无处不在:《索马里骆驼》中才华横溢受绯闻影响夫妻感情破裂的女舞蹈家,《卢旺达女诗人》中功成名就却夫妻离心的援非医生,《闪电击中自由女神》中为父复仇却陷入更深悲怆的记者,《夜泳失踪者》中为世俗功名富贵所累的夜泳者,《一张过于宽大的床》中孤身迷茫独守空床的公务员等等。
《萨赫勒荒原》中貫穿着“荒原”意象,其中有在《萨赫勒荒原》《索马里骆驼》《卢旺达女诗人》中真实的非洲荒原,这里地域广阔,人烟稀少,与茫茫宇宙浑然一体;有《一张过于宽大的床》《午夜之椅》中主人公梦里、感觉中的精神荒原。在文学史上,荒原是一个重要的意象,最有代表性的荒原是英国诗人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1922年创作的长诗《荒原》。荒原上满目萧瑟、生机寂灭、混乱、倾塌,荒原上的人则精神恍惚、萎靡不振。一般认为,艾略特的荒原是当时西方精神价值崩溃与幻灭的象征,也是他对人类存在的探问。艾略特本人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说这首诗只是个人对生活的感知。因此,也有研究者认为,“荒原”是艾略特“内心深处的荒原”。《荒原》诞生后很快就传到中国,由于和当时中国社会背景相契合,30、40年代的现代派和九月派诗歌中也涌现了荒原意象,反映了诗人对荒谬与黑暗现实的批判,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对于朱山坡来说,“荒原”也是一种精神象征,是现代人在世的生存体验,无尽的孤独与悲伤是其主要表征。
《卢旺达女诗人》中,玛尼娜爱上身为援非医生的“我”,俩人同甘共苦,“我们见过荒原。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尽头。平坦荒凉的地面上经常孤零零地站着一棵棵树。玛尼娜说,那些树,将孤独终老,死得悄无声息。像没有经历过爱情的人类”[2]。后来,玛尼娜追随我来到中国。作为一名医生,“我”事业成功,住着宽敞的房子,妻子漂亮,女儿可爱,一切仿佛完美无缺,但玛尼娜一眼就看出“我”与妻子之间没有爱情。对于“我”来说,没有爱情也可以生活,现实的考量要比爱情重要,面对玛尼娜真诚的爱,“我”以不能背叛妻子拒绝了她,一方面是顾忌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另一方面是对玛尼娜的感情超越了友情却没有到达爱情(“我”对她的肉体是向往的,这从“我”关注她性感的身体可以看出来)。因此,“我”在精神上是孤独的,玛尼娜走后,“我”彻底陷入了没有方向的荒野。《午夜之椅》中的“我”是一个怀才不遇的画家,在长春与莹相遇后不听劝告,一心想着挣钱谋生最后却负债累累,生活无以为继,换了几个城市生活,“每次都像一只鸟掠过荒原,世界越来越苍茫”[3]。到了M城,遇到了芳,因为是个“好人”,芳与“我”结婚。婚后琐碎困顿的现实使得两人心生嫌隙,“我”不时从床上跑到自己买来的单人椅子上睡觉,那是属于“我”的唯一的财产,芳认为“我”不属于床。“我”在街头为人画肖像时遇到之前的主顾琼,琼认为“我”不属于街头,琼做生意一般把“我”从芳手中买了回去,供“我”食宿。“我”专心画画依旧不被认可,猜忌很快又代替了开始的甜蜜。在一次争吵后琼说“你不属于这里”,“我”又被赶了出去。于是,“我”扛着唯一的财产——那把灰色椅子走进了黑夜中,“此时此刻,她脸上的决绝应该慢慢变成了忧伤,孤独感和巨大的悲怆会迅速将她击倒。这是人类必须承受的情感。她要承受,我也同样承受着”[4]。他人即地狱,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却彼此伤害彼此疏远。“我”意识到自己既不属于这个时代,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就如尼采一样。尼采这个形象本身就具有一种荒原色彩:脱出生存常规,没有现实职业,没有生活圈子,没有结婚,在他乡游荡,永远在寻找未曾找到的东西。文中结尾“我”放下了椅子,很多行人坐到椅子上,每个人都痛哭流涕,“我”再也挤不到椅子跟前,丢掉了最后的归处。《一张过于宽大的床》中,“我”带着父亲遗留给我的床,孤身一人从镇政府到小县城到省城,因种种机缘与很多女人男人一起睡过这张床,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人生:表姐,蒋虹、流氓、妓女、流浪汉——,“我”软弱善良,怜悯众生,被人所用却无怨无悔,体验到“孤独和痛苦都是身体的组成部分,是无法割掉的,更不能归咎于床过于宽大;两个孤独的人未必能睡到一张床上——”[5]《夜泳失踪者》中,即使结伴而游,每个人仍感到深入骨髓的的孤独。“我不明白他的深意,但此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同时,我想,惠江也应该感到孤独。还有拥有日月繁星的天空,不也应该感到孤独吗”[6]。《闪电击中自由女神》中,了解真相后的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和苍凉感;《索马里骆驼》中,行走在非洲荒原的人与骆驼都是孤独而忧郁的;另外在《萨赫勒荒原》《野猫不可能彻夜喊叫》《香蕉夫人》中,“我”都体验体验到孤独与悲伤。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指出,孤独是人生的常态,越文明越孤独。现代文明中,生活日新月异,人类的身体与心灵却裹上了厚厚的包装,焦虑、异化。《萨赫勒荒原》中的九个故事诠释了现代社会里人孤独痛苦的存在状态,主人公们不断追问:世界变了吗?无处安放的自我在大地上游荡并竭力要找到归处。《午夜之椅》中芳下岗的父亲与母亲吵架后离家出走,母亲追随父亲也开始在外流浪不归,明明有家,他们却每夜睡在银行屋檐下或某个地方,芳的父亲短暂归家后,与芳不断争吵,又重新开始流浪生活,这寓示着世俗的家不能带来安定,流浪却能冲淡心灵的荒芜。海德格尔认为人是没有选择被抛在世界上的,在浩瀚的世界中,微小的人类有着各式各样的烦恼,像小说中的爱而不得、夫妻离心、怀才不遇、抑郁症等等。但作为被抛在世界上的个体,人渴望成为自己希望的样子,成为本真的存在。“本真的生存并不是任何漂浮在沉沦着的日常生活上空的东西,它在生存论上只是通过式变来对沉沦着的日常生活的掌握”[7]。
二.别处:希望与崇高
“如果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卑贱,逃到哪里才能避开呢?只有逃向崇高借以逃避堕落!”[8]别处是想要到达的地方,是远方与梦想,它脱离现实的束缚,直面内心的渴望。
朱山坡的小说中经常有诡异的失踪与人间蒸发,比如《蛋镇电影院》里的售票员凰、随着洪水想要漂流去美国的胖子、在电影屏幕上消失的贼荀滑等。这种失踪有时是生死未卜,一直想偷渡去美国、过自由幸福生活的胖子,大概率是死在路途中。但“我们”怀抱希望与信心,并在美国电影里见到了胖子的身影。凰堅信已牺牲的爱人凤会回来,有一天凤竟然真的回来了,他们在夜里一起离开了蛋镇。这种荒诞、仁慈的描写或许是不忍心看到美好希望的破灭,是对别处的信念。《萨赫勒荒原》中也有此类的消失,这类消失出现在此处生活无路可走的时候。《闪电击中自由女神》中,潘京目睹父亲在闪电中消失,父亲因被逼做伪证陷害“我”父亲,“他后悔了,没脸见人,所以跟随闪电走了……他不是被闪电掳走,是自愿,他自投罗网,他必须要换个地方生存”[9]。《索马里骆驼》中,父亲援非时身为舞蹈家的漂亮的母亲被绯闻中伤,父亲回来后猜疑不断又远走非洲。后来父亲骑着一头骆驼回来,在“我”的注视下,父母骑着骆驼消失,从此音讯全无。他们离开了是非之地,“我”作为一个曾被怀疑与引起争吵的符号一起被抛弃。
最耐人寻味的是《夜泳失踪者》中樊湘的失踪。大学毕业后在博物馆工作的樊湘才华横溢却整日对着文物无人问津,后来凭借对名士谢布衣或真或假的研究以及贿赂(他把所绘谢布衣的《惠江夜泳图》以真品的名义送给了闵市长),他当上了博物馆的馆长。他带着“我”等三人吃饭夜泳,自得其乐。四人同样的人生失意,夜泳“是一个人远离尘世纷扰、排除内心杂念安静地享受孤独的过程,是思考人生的过程……”[10]在江中,人摈弃了现世,面对自我真心。随着闵市长被检察院带走,博物馆文物全被偷梁换柱的真相被揭露,一次夜游之后,樊湘失踪了。因为对女儿的爱,樊湘置换了博物馆的所有文物,包括谢布衣的《惠江夜泳图》,得来的钱据说全堆在女儿的床底下。樊湘留言说随谢布衣去了,颇具意味的是,在他自己及“我”等的眼里,他不是一个坏人,他仰慕谢布衣,甚至具有谢布衣的某些高洁品性。然而在世俗价值观的挤压下,他与谢布衣背道而驰,铤而走险。樊湘的失踪是此处矛盾的无解,别处或许有一个能够容忍他的地方。
同理想中的乐土一样,别处是对平庸现实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香蕉夫人》中的堂姐秀英希望嫁得远一些。身为家境贫困的农村姑娘,长相端正漂亮是她唯一的本钱,因此她千挑万选,最终嫁给浦北种香蕉大户,成为香蕉夫人。同名小说《萨赫勒荒原》中的医术精湛的“老郭”隐瞒自己有心脏病的事实去援非,“我最后一次问他,非得要去吗?他依然坚定地说,要去”[11]。这句“要去”,是对现实的遮蔽与崇高的向往,老郭用去异域救死扶伤实现自身精神的救赎与升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即使没有远方,一种具象的物体也足以与现实拉开距离,完成对别处崇高的臆想。《一张过于宽大的床》中,父亲倾其所能给“我”制作了一张堪称奢华的大床。在爱慕的少女唐小蝶消失之后,“我”曾与各式各样的女人、男人在这张床上共眠,但我对近在咫尺的女人毫无兴趣,心里一直挂念着唐小蝶,唐小蝶此时已成为一种理想的执念。“我”踞于宽大的床中一隅,做着精彩的梦,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大。在晚年“我”重新遇到唐小蝶,她已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与她结婚并应她的要求换了床后,“我”的梦境消失了,“只有现实没有梦境的生活是坚硬的、冰冷的,身体和灵魂都无处安放”[12]。床是承载梦想的地方,是此处的别处。同样,《午夜之椅》中,“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处处被挤压、忽视,与莹分手,被芳收留结婚,又被琼以10万元买走,在芳及琼的家里,“我”没有大声说话的权力,只有被安排的命运,唯独一把自己买来的灰色的单人椅子让“我”有归属感,“我”经常躲到椅子上做梦,像一个梦游症患者,椅子是“我”能拥有的脱离现实的别处。《野猫不可能彻夜喊叫》中,“我”独居在家很少与外界联系以求“大隐于市”,而“我”家阳光充足的阳台是抑郁症患者闫小曼的别处。
三.别处与此处的断裂与错位
“真正的生活在别处”[13]。别处是人生的希望,但如果真的到达了别处,一切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生活在别处”这句话是从法国诗人兰波的诗句中转化而来的,因米兰·昆德拉的同名小说闻名。兰波一生不断走向远方,做过各种职业,但他所体验到的并不只是异域风情与诗意,更有贫穷与琐碎,甚至为了生存放弃写诗,在他贫病交加去世时,理想与诗意已经离他很远了。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中通过诗人雅罗米尔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当向往的此处变为别处,崇高感会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这是人类追求本真存在所必须面对的困境。
《萨赫勒荒原》中的主人公们面临同样的悖论:离开荒原来到别处,发现这里是另一片荒原,现实与理想之间有着巨大反差与断裂。《香蕉夫人》中的堂姐如愿远嫁到浦北,一时风光无限。随着香蕉园的破产,丈夫远走广东打工并有了情人,她生了5个孩子,容颜坍塌,负债累累,成为村里耻笑的对象,曾经向往的别处成为她另一个更悲惨的此处。《萨赫勒荒原》中的援非医生也面对着严峻事实:荒原的凄凉穷困、疾病众生,坚持崇高信念要付出的代价——老郭因超负荷的工作量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男孩尼可因父亲萨哈所坚持的大公无私而病死。《卢旺达女诗人》中“我”与“玛尼娜”都没有在别处得到自己想要的,“卢旺达,那是我的梦境,却是玛尼娜的现实;而中国,是我的现实,却是玛尼娜的梦境。”[14]玛尼娜追随“我”来到南宁企图得到爱情,“我”被现实所困,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玛尼娜在南宁游荡,吟诵写给“我”的情诗,用酒填满心中的空虚。她历经几次恋爱,身体与心灵都受到伤害。
在别处,人并不能完全找到自己,别处之后依然是别处。《一张过于宽大的床》中“我”在老年遇到了朝思暮想的唐小蝶,此时她已面目全非,“我”已衰老到愿意把任何自称是唐小蝶的人当成她。“我”与唐小蝶结了婚,她真实地填补了床的空隙处,婚后,唐小蝶开始介意很多女人睡过这张床。于是“我”知道她所经历的一切并没有让她对人生有所醒悟。“我”感到失望了,因为爱(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对曾经梦想的别处的执着),我妥协了,卖了陪了我几十年的床。最终,唐小蝶发现还是旧床好。“我”呢,床卖了后,连梦境也消失了,身体与灵魂都处在悬浮状态。最后我疑惑着,去哪儿再找回那张床?梦想的东西似已到来,“我”却依然需要梦境。
朱山坡显然意识到别处的生活与此处相比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因此,人永远处在追寻亏欠的路上,有些追寻终于半完成或疲竭,有些追寻只能终于死亡。《索马里骆驼》中,饱受诽谤的母亲金灿英跟着父亲张健中来到索马里柏培拉,“躲在世界的角落里与世无争,地球另一边的人和事不再与自己有关,这样很好。唯一的遗憾是让人变得慵懒、孤独、健忘、不思进取,甚至忘记自己还有一个儿子”[15]。如同在《蛋镇电影院》中小镇人在困顿生活中对电影院的向往一样,金灿英需要电影来充实背井离乡内心的空虚。后来张健中帮她盘下了电影院,但张健中与印度女人之间的暧昧,她在中国的绯闻却还影响着两人。之后金灿英专心经营电影院,为了“善”,为了改变他人的崇高信念,不顾张健中的劝阻,骑着骆驼跋涉荒原给索马里一些部落放电影,最终在旷野中死于流产。以生命为代价,金灿英完成了由“比发情的母骆驼还骚”的淫荡形象到人人称赞的勇敢顽强、美貌与美德兼备的“母骆驼”形象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对成为此处的别处的反抗,她如同倔强的骆驼,坚定而悲壮地走向心中的目的地。
我们也看到,朱山坡的“荒原”不仅是颓废与凄凉的,还有爱与牺牲,有追问与反思。《萨赫勒荒原》中,“我”明知援非条件的艰辛还是选择来到尼日尔,接替殉职的老郭继续救死扶伤;《索马里骆驼》中,“我”接替母亲,继续骑着那头骆驼给索马里部落放电影,结婚时,在部落借来的上百头骆驼中,“我”再次见到了盛装而来的母亲;《野猫不可能彻夜喊叫》中,“我”愿意为闫小曼敞开我家的阳台;《香蕉夫人》中,堂姐依然在为重建香蕉园而努力。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塑造了超人形象,超人是勇敢的荒原进军者。在荒原中,人的精神有三段变化:由任劳任怨、以“我应该”为信念的骆驼转变为质疑茫茫宇宙、向广阔沙漠大吼“我要”的狮子,并最终成为“我是”的本真的婴儿。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末人、高人、超人,当生活由自己掌握,价值由自己创造,伟大的超人就诞生了。在这个意义上,《萨赫勒荒原》中的主人公与我们都在路上。
张燕玲认为,朱山坡“寻求在地方性和世界性的融会中,建构自己的小说样貌和美学个性,确立独特而闪亮的文学自我,成长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灵魂捕手’”[16]。我们不难在《萨赫勒荒原》中看到朱山坡一贯具有的写作特性:想象奇诡,文笔辛辣诙谐灵动。比如,《索马里骆驼》中父亲回国听到关于母亲的流言蜚语,“像掉进了粪坑里”,“我”看着母亲发呆,担心“她变成狗尾巴草”等让人忍俊不禁的语言。另外,小说中不时有对名篇名言的戏仿,《闪电击中自由女神》中,潘京带我去断桥拍照片让我们看到《廊桥遗梦》中男主罗伯特·金凯抓拍曼迪逊桥的场面,《午夜之椅》中借用尼采“凝望深渊久了,深渊必予以回望”来形容已婚的我在街头给琼画肖像时两人间的眉目传情,而“一想到莹,后悔的雪便堆积如山”[17]是对张枣“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的实景模写,等等。这类戏仿让我们看到同样幽默而深邃的朱山坡,他以極具个性的写作,对世界进行塑形。朱山坡重新确立了文学史上“荒原”的意象,生活在荒原上,从一个荒原到达另一个荒原,在荒原中寻找本真存在与自我蜕变,这是《萨赫勒荒原》的存在启示。
注 释
[1]黄发有:《边地乡村的宿命与寓言——朱山坡》,《南方文坛》,2010年第1期。
[2]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107-108 页。
[3]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252页。
[4]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251页。
[5]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236 页。
[6]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193 页。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版,第208页。
[8]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袁筱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71页。
[9]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161-162页。
[10]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180页。
[11]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23页。
[12]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242页。
[13]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袁筱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234页。
[14]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112页。
[15]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55页。
[16]张燕玲:《朱山坡新作<萨赫勒荒原>及其创作:在地方性和世界性中寻求个性》,《文学报》,2022年11月12日。
[17]朱山坡:《萨赫勒荒原》,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9月版,第274页。
(作者介绍:赵娜,文学博士,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