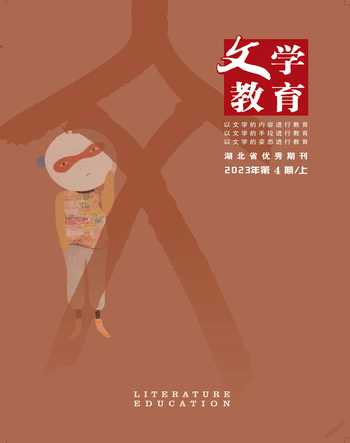空间视域下《女佣的故事》的自我救赎
孙衍各
内容摘要:《女佣的故事》讲述了斯蒂芬妮作为单身母亲,女佣和社会福利救助的对象,通过教育和写作与现实抗争,最终涅槃重生,翻转生活的故事。作品有明显的空间特征,从流离收容所到租赁公寓,再到前往米苏拉,斯蒂芬妮借助空间的变换来书写故事。因此,本文将借助空间理论分析作品的艺术价值,认为它也为身处美国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提供了一条改变生活的现实途径。
关键词:斯蒂芬妮·兰德 《女佣的故事》 空间 女性 救赎
《女佣的故事》是美国作家斯蒂芬妮·兰德的处女之作。作品一经出版,便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知名媒体的畅销榜和推荐榜上大放异彩。虽是文坛新秀,但初出茅庐的斯蒂芬妮凭借自己真实的经历和独特的叙事方式,收获了一大批读者。社会学家芭芭拉·艾伦赖希为其撰写序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将它列入2019年的个人阅读书单。本书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以个人型叙述声音讲述故事经历。所谓个人型叙述声音,就是热纳特所谓“自身故事”的叙述者,即斯蒂芬妮在讲述故事的同时,也担任故事里的主角。故事里的主人公是她以往的自我。[1]这种新颖的叙述方式,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感距离,使读者身临其境。作品主要以她和女儿米娅的日常生活为主线,记叙了处在社会底层空间的单亲妈妈如何通过教育和写作,与命运抗争,最终摆脱生活的困境。此外,文本主题涉及美国的住房、医疗、结业、教育和社会福利制度。斯蒂芬妮和女儿米娅的生活状况是当代美国边缘人物的一个缩影,在不健全的政府救助机制下,有千千万万的人正处在和她們一样贫苦的环境里。
全书共27章,分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不是相互独立的篇章,是以场所的变换和空间的转移来展开故事的情节,不同的片段在空间层面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作品里斯蒂芬妮和女儿米娅经历了多个场景的变化,从寄居收容所到租赁公寓,拥有自己的住处;再到最后更换生活的城市,前往米苏拉。在这个过程中,空间不仅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所,女主人公成长的陪伴者和见证者,更是与她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密切关联。因此,本文将借助空间理论,探讨作品的写作特色和艺术价值,认为作品也为身处美国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提供了一种改变生活的新的范式。
一.流离收容所:社会底层空间的他者
故事以当前居住的收容所日子到期,斯蒂芬妮和女儿米娅要搬去其他过渡居所开篇,虽然作者并未直接点明处在如此境况的原因,但接下来通过闪回和倒叙的叙事方式,斯蒂芬妮向我们呈现了发生在她和米娅身上的遭遇。和米娅的父亲杰米分手后,斯蒂芬妮带着九个月大的米娅,没有工作,也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只能靠着政府的“食品救助券”和收容所来支撑母女的生活。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的国家里,利用政府福利政策维系生活的人会遭到大众的鄙夷,在他们看来这些“穷人偷取美国公民辛勤上交的税金去买垃圾食品”。[2]36正如杰夫里克在《看不见的孩子》一书中所说:“只有伤病人士、老人和儿童被认为是‘值得同情’的穷人,而那些身体健全的穷人是‘活该受穷’,社会不欠他们什么,也不会提供什么帮助”。[3]49所以每当斯蒂芬妮去超市购物时,收银员会面露不悦,一些傲慢的中产阶级在经过她的身边会大声地说“不用谢”。[2]186因为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观念让他们觉得穷人应该为自己的境遇负责。
空间总是文化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是为社会关系所建构的。因为,“空间不是单纯的社会关系演变的舞台,反之它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又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结构和转化”。[4]所以,随着环境场所的变换,人与人之间也建构了不同的空间关系。收容所里人鱼龙混杂,里面有从戒毒所出来的瘾君子,有小偷,还有一些饱受精神疾病困扰的人。斯蒂芬妮和这里的住客,一同构成了社会底层空间的他者,他们与繁荣的美国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不被其接纳,是被漠视和忽略的存在。所以,在这狭小的生存空间内,他们会遭到严苛的对待:要保持房屋整洁,不准留宿客人;要随时配合尿检。因为在大众眼里,“贫穷总是和龌龊脱不了干系。声名狼藉的的便签越垒越高。”[2]47
空间的范围广大,既有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分,也有社会空间与家庭空间之别。如果说社会这个大空间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依托,那么家庭无疑是个人成长更为直接和亲密关怀的空间。[5]82虽然依靠政府的救助,斯蒂芬妮和女儿暂时有了寄居之处,但是她却始终游离在家庭空间外。离婚后的父母都有了各自的家庭,他们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爱护她。母亲怕再婚的丈夫不开心,甚至拒绝了斯蒂芬妮索要一个她们独处空间的请求。父亲的收入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生活拮据,无法为她提供庇护。原生家庭给予的情感支撑是个体生命中不可替代的财富。可悲的是,在她陷入生活的窘境时,她的父母为了维护各自所建立的新的家庭空间,不是向她给予“羊跪乳”般的疼爱,而是选择舍弃她。尽管她现在也是位母亲,可是在向米娅提供爱时,她也渴望自己能够被别人疼爱。
怀孕后,她和男友杰米的家庭关系也急剧骤降。生下女儿米娅后,杰米更是对她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虐待、威胁以及高声辱骂”。[2]33如此恶劣的家暴行为对她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导致了斯蒂芬妮的抑郁。而后来,杰米又以抑郁为由,在法庭上对她恶言相向,以此获得米娅的抚养权。这段创伤记忆让她经常身体和心理处于警戒状态,整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好在一连串情感上的重创与生活上的拮据并未让她就此沉沦。她把教育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武器,踏上了攻读学位的旅程,因为她清楚地知道:“上学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件让我们获得地位的事情”。[2]209
在流离收容所的这一部分,斯蒂芬妮通过回忆和倒叙的方式,将主观空间与现实空间并置,记述了她沦为社会底层人物的悲惨遭遇,在不健全的救助机制下,她要在冷眼中生存,艰难度日。然而,她选择迎难而上,借助教育在社会层级的梯子上慢慢攀爬。
二.一居室公寓:重新出发建构生存空间
离开杰米后,斯蒂芬妮在婚恋网站上认识了她的第二任男友特拉维斯,这个新男友不仅填补了斯蒂芬妮一直以来情感上的空缺,也给了米娅慈父般的宠爱。她们一起搬去了他的农场,为即将到来的生活共同努力。沉浸在恋爱的喜悦中,斯蒂芬妮一度觉得有特拉维斯在,她和米娅会安定下来,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情况还是发生了变化。特拉维斯是一个有着传统男性逻各斯思想的人,在对待斯蒂芬妮的态度中,更是有着明显的表征。在他们新组建的家庭共同体里,他占据着主导地位。明明是一起劳作获得的收入,经济大权却被特拉维斯牢牢掌控着。这让她常常感觉到束缚,惶恐与不安在她的心里与日俱增。就连斯蒂芬妮向他索要加油钱,特拉斯维都会面露愠色。在他看来斯蒂芬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家庭和农场里,她的女佣工作是“去和读书会一样的消遣,觉得它妨碍了她在家和农场里干正事”。[2]80但斯蒂芬妮越发清醒地知道“工作能力和安全能力是她唯一的‘安全网’”。[2]80很快这段感情也走向了终点,她和米娅也不得不重新寻找住处。在高速公路旁,斯蒂芬妮租赁了一间一居室公寓。可就是这么一间脏兮兮的屋子,她也得缓交押金。
列斐伏尔说过:“空间从来不是各种事物中的一物,也不是各种产品中的一个产品”,相反它不仅包含物,也包含它们之间的关系,[6]更重要的是人们常常以自己所处的空间为参照去和其他的空间作对比。但是空间的层级是与人们的社会等级相对应的,每个阶级有其适配的居住区域。[7]50雇主们豪华的房子让斯蒂芬妮羡慕,“一张有我车子那么贵的地毯收据,可以买下我半个衣柜的衣服的干洗账单”。[2]172
空间也是社会性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7]48斯蒂芬妮和她的雇主们形成了建立在雇主关系基础上的具有差序性特征的纵向空间,他们在这个空间里的鸿沟和差距与经济水平和阶级差距有密切关系。[8]108她的雇主们构成了富裕的上流阶层,处在这个社会大空间格局的顶部,而斯蒂芬妮是靠着“食品救助券”维系生存的底层女性,“每个马桶都要用双手擦上二十几遍,才能拿到10块钱的小费”。[2]90有时候,雇主还会安装摄像头,或者把财物放在显眼的位置来考验她的人品。过度劳累和超负荷的工作让斯蒂芬妮的脊柱神经严重受损,她常常疼痛难忍。但是因为收入不在医疗资助的范围内,她只能靠服用大剂量的布洛芬来缓解,而雇主家里的阿片类药物一直都是满瓶。她用辛勤的双手把别人的生活打磨得光鲜良丽,而自己的困顿却无人发觉和在意。
幸运的是,她的真诚和努力也换来了一些客户的尊重和赏识,他们摒弃阶级的偏见,向她传递温暖。在雇主亨利家的日历上,她以斯蒂芬妮的身份存在。并且亨利一直将她视为“值得爱与欢笑,偶尔也该享受一顿龙虾大餐的人”。[2]125客户温迪更是将斯蒂芬妮视作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人,她会给辛苦清洁的斯蒂芬妮做一顿午餐;也愿做她不开心的倾听者。无论是亨利还是温迪,他们都并没有因为斯蒂芬妮清洁工的身份,而戴着有色眼镜对她。
与等级鲜明的纵向空间形成对比,作品也让读者看到了女性群体的力量,她们互帮互助相互扶持,构造了一个温暖的“横向空间”,为主人公辛酸的经历增添了人文主义色彩。[7]109服装店里的女老板萨迪,同意斯蒂芬妮以清扫店里的卫生间来换取购置新衣的抵扣积分;斯蒂芬妮的上司帕姆在得知她的公寓空间狭小时,也愿意把自己的阁楼借给她存放物品;朋友在得知斯蒂芬妮要更换住所时,更是送上了新碗筷、婴儿床等生活必需品。
在这些爱意的包围下,斯蒂芬妮又重拾了自己的写作爱好。她在网上建立了自己的博客,日记将斯蒂芬妮从烦闷的生活中抽离出来。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人因为她使用“食品救助券”而歧视她,也没有人因为她清洁工的身份而觉得她低人一等,她可以放松长期以来一直紧绷的神经,敞开心扉,甚至咒骂不公的生活。在这里她是自由的,可以卸下平常坚强的伪装,书写自己的悲伤。生活的压力,工作的疲惫,霉菌丛生的公寓,几乎把她掏空,而写作是她苦难生活里的精神支撑,“也有只有在这些时光里,我的心神才会安定下来。我不用再去纠结自己是否应该去工作,或是思考自己是否做得不到位。我不用去想是否有人会把我们看做占尽政府便宜的‘低保户’”。[2]197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社交网络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团结的纽带”,不只在美国,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也有和斯蒂芬妮一样经历的女性,网络将拥有不同背景的她们联结在一起,她们在里成为了同舟共济的伙伴,网络为他们提供了互相安慰的空间。[5]86斯蒂芬妮的故事鼓舞了很多人,人们在日记下方留言称赞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钦佩她的果敢和坚毅。
在作品的这一部分,斯蒂芬妮和米娅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虽然它只是一间狭小的一居室公寓,但是在它给予了她们缺失已久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斯蒂芬妮也坚信以这个公寓为起点,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会开始变好。
三.前往米苏拉:涅槃重生 踏上寻梦之旅
写作一直以来都是斯蒂芬妮的梦想,很早之前她就仰慕蒙大拿大学的创意写作课程,但是遇见杰米以后,对家的向往让她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在互联网创作的这段时间里,梦想的火苗再一次点燃起来,网络日记“成了一道不停雕琢的生命线”,[2]257记录了她的迷茫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利用假期前往米苏拉后,她更加坚定了在那里生活、重拾梦想的决心。这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容,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友好的氛围。多年来,因为“救助受领人”的身份,斯蒂芬妮一直活在自卑当中,她不敢与别人太过亲近,和自己的亲朋好友一度处在断联的状态,她觉得自己是一個麻烦制造者,除了增加困扰,她向别人提供不了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她害怕他人一旦发现自己长期使用“食品救助券”后会疏远自己。但是米苏拉的人们不同,他们向她表达了前所未有的善意,“我们可以和所有人打成一片。没有人会像华盛顿州的人那样用余光瞄我们”。[2]314米苏拉之行也让她清楚地知道,女佣的工作仅能让她不再被打回收容所,而教育才是扭转自己和米娅的处境的最佳路径,自己才是自己的救赎,这件事不是靠某个男人或者家庭,那个人只能是我自己。
在作品的最后,她们如愿去了米苏拉,斯蒂芬您的创作也被当地的一家杂志机构刊登出来,米娅也继续在学前机构读书。她们做到了,美好的生活在前方等着她们!
在作品《女佣的故事》中,斯蒂芬妮用辛酸的笔调书写了一个处在社会空间底层的单亲妈妈的生活图景。跟随她的文字,读者了解了被社会忽视的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同时,它也向读者展示了身在不堪中的强大女性力量。从流离收容所,到租赁公寓,拥有自己的住所,再到决定前往米苏拉,继续写作梦想。空间不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与她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相关。场所的变换也是她命运转折的重要节点,它们记录了她的成长与成熟。
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强国,提起美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繁荣”,鲜有人将它与“贫穷”、“苦难”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然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人都享受到它经济迅速发展的福利,还有许许多多的像斯蒂芬妮一样的边缘人物,被生活的困顿,工作的疲惫掏空了自己。庆幸的是,她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让底层人物的声音被听到。她负重前行的英雄主义也给其他“小人物”送去了生活的希望靠着教育和写作,她最终翻转了和女儿米娅的生活,实现了涅槃重生。她的故事鼓舞了和她有着一样遭遇的人,激励着他们去讲述自己的故事,让越来越多的人被看到,被听到。她的成功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实现自我救赎!
参考文献
[1]朱晓映.毒瘾难戒的女性主义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07(02):119-124.
[2]斯蒂芬妮·兰德.女佣的故事. [M].孟雨慧,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3]杰夫·马德里克.看不见的孩子:美国儿童贫困的代价.[M].周长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4]陆扬.空间转向中的文学批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05):66-72+1
59-160.
[5]朱荣华.难民小说《西去》中的后国族伦理共同体建构[J].当代外国文学,2020
(04):80-87.
[6]Henry L.The Production of Space[M].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1991.
[7]包亚明.现代性空间的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8]王迪.空间、命运与抗争:《温柔之歌》的空间叙事与女性主题[J].当代外国文学,2022(01):106-111.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