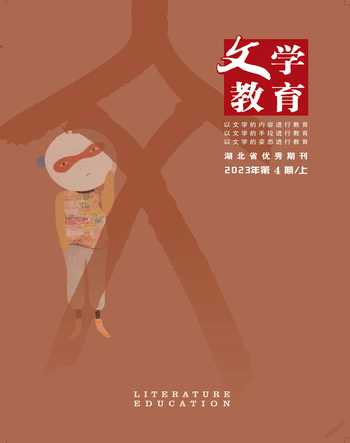论毕飞宇新世纪中长篇小说创作
钟子龙
内容摘要:进入新世纪,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发生变化,小说所需要承载的使命随之发生变化。毕飞宇以新的文学使命探索文学创作,脱离唯形式的路径,从社会问题和边缘人中切入人的日常书写。在其新世纪中长篇小说中,他不但书写存在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节点下乡村的自然人性和权力欲望,还关注生存于都市缝隙中人的异化及尊严,以重返现实主义的姿态,深入生活细节的描写,从人性维度去重新发现人,揭示着平淡生活背后的精神隐痛和人性欲求。
关键词:毕飞宇 新世纪中长篇小说 人的再发现 乡村和城市
随着上世纪90年代我国市场化的加速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在国家经济、文化上的巨大影响不可避免地作用到了文学上,这是一个集合了复杂思想文化的宏大转变,笔者只能粗浅的梳理文学特质的大概发展路径,以及进入新世纪以来,从小说角度瞥见的文学新变。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市场和新媒体成了文学的重要元素,根据雷达在《新世纪小说概观》中对新世纪小说的定性:“近十多年的‘新世纪文学’,则是以日渐成熟化的市场经济机制为运行基础的新媒体时代的文学。”[1]2在未进入新世纪的过渡期,大概从1993年到2000年,大批受西方现代主义滋养的先锋作家,在经历了漫长的模仿后,对外来文化的心态进入了调整阶段,逐步在社会环境变化中反思本土化的路径,他们开始认识到对形式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形式高于一切,真正“有意味的形式”并不以消除小说的故事、情节、细节等基本元素为代价,而应该是与之相互渗透、有机融合[2]。然而进入新世纪,网络文学在数量上出现爆发式增长,却没有质量上的保证,大批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涌进大众生活空间,而新世纪生活节奏的加快,导致大众越来越缺乏阅读的精力,因而接受者还是乐于从类型化的作品中寻找娱乐消遣而不加区分,导致先锋转型的成果被大众市场催生的网络文学所遮蔽。聚焦于乡土叙事和人性日常,新世纪以来很多当代作家依然耕耘在纯文学创作的土地上,就如毕飞宇的新世纪中长篇小说,他用自己切肤的体会去感受社会,感受底层群体,致力于写出真正属于笔下人物最真实的精神状态,无论是乡村中人性权利的角逐,还是都市里尊严认同的获取,都体现着一种对于人的命运和生存境遇的关注,如果说网络爽文宣泄了个人的一般欲望,那么毕飞宇新世纪对人的书写,对人的 再发现,则填补了大众的精神空虚。
一.创作转向与日常发掘
新世纪写作中的人不同于二十世紀80年代“理性”的人,也不同于二十世纪90年代原生态或欲望化的人,新世纪小说中的人是“日常的人,个体的、世俗的、存在的人”[1]12。而把毕飞宇小说纳入新世纪写作的视野,即需要将视野缩小到个体精神状态或一类群体的社会遭遇上,同时扩大作家对于当下文化生活的感受能力,去发掘人性,发现个体欲求的受阻过程。
作为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他并非一开始就走向现实主义书写,在毕飞宇的前期创作中,受博尔赫斯影响,他在创作中追逐一种文化的乌托邦和拟历史,透露出博大的历史悲悯和深邃的哲学气息[3],如《孤岛》和《叙事》,而且其明显的先锋叙述,交融着历史的回溯和文化想象,表现出一种汇入时代大潮的小说书写风格。而从1995年到新世纪,《哺乳期的女人》《生活在天上》《男人还剩下什么》等文章的发表,毕飞宇的注重点逐步从叙述形式转向生存在社会中的人,进入新世纪后,毕飞宇的中长篇《青衣》《玉米》《平原》《推拿》陆续问世,一种属于作家自己的写实风格从作品中建立起来,不仅是修辞方式、语言节奏方面,毕飞宇还表现出一种隐秘的书写格调,他用戏谑的语言在消解人物身份的严肃性,如《平原》中的知识分子顾先生;用民间的陋习来改变乡村留给人的美好印象,如《玉米》中玉米的私密信件被所有人拆开观看;用特别的视角去感受群体的生存境遇,如《推拿》中盲人的先天盲人和后天盲人的不同心态。
而在日常生活中要塑造人,首先得要理解人,如果不通过人物动态去体现日常,会使日常难以散发魅力[4],因此在毕飞宇新世纪的中长篇中最亮眼的地方即为对人的再发现。在五四时期,五四启蒙意识所倡导的人的觉醒和个性自由,打破了长久以来旧文学“文以载道”的创作向度,通过揭露国民性问题和批判吃人的封建礼教,意图实现中国民众的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高举现实主义大旗的作家,对社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但这种批判性的写作发展到后来,变成了一种脱离社会基础的发号施令,是站在知识分子精英立场上的单向批判。在毕飞宇这里,他恪守的准则是去了解人物真实的生活,他摆脱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姿态,从不以审视的态度看待农村社会与生活,而是将浅露或深蕴其中的迷信、谣言和暴力组合成一种生活日常,去具体观照生存于城市或者农村的人的心灵状态,在平常平淡的叙述中,以人的转变或人文关怀,实现人的再发现。
我们把毕飞宇的新世纪中长篇小说可以笼统归为乡村和都市两个层面,明显《玉米》和《平原》属于前者,而《青衣》和《推拿》属于后者,但这样的分类并非是在二元对立中去看待两类小说的区别,而是探究在乡村和城市都体现的人性问题和权力意识,同时观照现代社会转型中,乡村人口大量融入城市的背景下,乡土叙事与城市小说的交互。
二.权力欲求与生存状况
从《玉米》开始,毕飞宇对乡村的称谓由“我们村”转变成了“王家庄”,这表明王家庄从此和莫言的东北高密乡一样,成了他笔下具有精神寄托功能的文化故乡。在《玉米》和《平原》中,毕飞宇对于乡村的描写并未致力于史诗性的建构,他没有将重心放在宏大的村落布局构想和农村改革的历时性变化的描绘上,而是聚焦于权力角逐、灵肉关系,去展示上世纪70年代生存于广袤的农村大地上人的生命意识和感性悲剧。
对《玉米》的描写,刻画了乡村中人的第一个欲求——权力。从小说叙事逻辑上看,玉米的父亲王连方仗着村支书的权力在村子里肆意寻找肉体的狂欢,破坏他人家庭。导致村民积怨已久,后来王连方偷情被抓,因为女方是军婚使其无奈遭遇双开,玉米的家庭境遇瞬间落魄,这时权力的反噬便引来了家庭成员的痛苦,即玉米爱情梦破碎,玉秀被强暴。玉米在经受爱情受挫、妹妹被侮辱、家庭条件一落千丈后,意识到手握权力重要性的她迫切想脱离被欺压的现状,通过当老男人的补房,最后把自己卖了出去。因而玉米成了权力的追求者,甚至说是奴隶。而在这个乡村场域中,所有人都是权力的奴隶,相对于玉米,毕飞宇对于村民的权力欲求的叙述是暴力性的,他们因为得不到权力,所以施暴于曾经掌权的人,通过折磨权力掉落者而获得快感,用行为和语言上的暴力来获得“人在人上”的幻想,以发泄积压的权力欲求。这里的乡村从来就不是一个令人恍惚而追寻自我的地方,而是一个真实厮杀的斗场,是一个拷问人性的地方[5]。
再看《平原》,毕飞宇在《平原》历史瞬间的抉择上,选择了“大革命”结束前的阶段,描述黎明前的黑暗和农村青年在彷徨中的绝望宣泄,而即将到来的光明时代又预示着人性的希望[6]。毕飞宇特地选择这样的时代节点,是为了消解“文革”带来的时代伤痛记忆,更重要的是为了将人物置与明暗之间,关注人物在灵肉之间、政治之下的生存状态。
从三个人物的特性上看,王端方是回乡知青,是一个有知识理想抱负的青年,但他在爱情上的处理是混乱的,他所认为的爱情比较粗浅,只是一种肉体的占有,在情人三丫死后,端方忘记了其长相,只记得情人的身体和呼吸,正说明二者朦胧的感情只是性的交涉,对于王端方来说,忘记三丫的样貌或许是一种心理上对死亡的应激反应,但深层的因素还是:三丫只是端方在无聊的革命年代里因性饥渴无处释放的宣泄对象,他们的“爱”只涉及肉,而没有灵的交流。
而在女支书吴蔓玲身上,则表现出在政治力量的控制下人的压抑,吴蔓玲为了深入民众,从小女生转变成了粗糙地道的农民,力图用工作的诚恳去改变村庄现状。在政治面前,她永远把集体利益摆在自身利益之前,闭口不谈爱情婚姻,她压抑着对王端方单向的爱慕,而这份爱慕随着王端方下跪事件、无奈把本应该是王端方的参军名额让给混世魔王,导致两人之间的误解越来越深,最后引发吴蔓玲的痴狂结局,也让本来拥有梦想的端方永远留在了养猪场,最后两人都成了被乡村捆绑的对象。小说把城市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生活融汇在同一时空下交替描写比照,弥补了文学历史长廊中缺失形象的塑造,其本身就充满着人生的况味,同时,又呈现出极大的历史张力[5]。这张力就是王端方和吴蔓玲之间压抑着的、无法言说的误会,在小说的叙事逻辑中,他们的命运环环相扣,一个事件导致另一个,代表着想逃离农村和想留在农村的两种人在同一场域的悲伤结果。
而在顾先生身上显现的对知识分子严肃身份的解构,更加表现了乡村秩序下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村民注视下的顾先生,并不是知识的传播者,而是强加枷锁给学生的罪犯,他所犯的错误不仅仅是教条主义,还有教育方式的错误,他未考虑到乡村的实际情况,光单方面灌输,使得顾先生带有启蒙色彩的唯物论成了王家庄人们厌恶、憎恨的对象。从文本意义上看,顾先生的做法在无形之中达成了一种反神圣化、反启蒙主义[1]225,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而回到内容上,固守着自己文化思想的顾先生,虽然拥抱着革命建设、指导思想武器,能够一字不落的复述,甚至倒背如流,但他脱离了实际,理论性的观点无法在文化水平低下的乡村得到吸收,导致顾先生的晦涩理论犹如鬼神,人人敬而远之。他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吞噬的幽灵,始终漂浮在乡村话语之外,知识分子的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村民的尊敬。
以上便是乡村中的人的第二个发现,即大时代环境下情感认识的混乱、肉体的压抑,以及对知识分子与场域的隔膜,这曾隔膜解构了所谓的严肃知识分子。
在毕飞宇的乡土叙事中,他用一种常见的“村落叙事”方法[7],把人物活动场所固定在“王家庄”里,竭力去刻画乡村中“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命哲学,然而将故事放置于“文革”这一时间节点上,他并非要从宏大的角度去揭开民族的集体伤痕,而是娓娓在讲述具体的土生土场在农村大地上的俗人,他们的日常可以脱离时代而存在,站在新世纪高度对过去的回望其中的生活细节,在今天的习惯日常里仍具有一些共同性。
三.异化问题与边缘群体
《青衣》开启了毕飞宇新世纪小说的现实主义风格,而《推拿》则把这种关注具体到生存于现实社会缝隙中的群体,展现他们对于社会的感知。在城市中,作家把存在于乡村里的政治权力的欲求,转变成了一种现代性的资本力量,在资本的控制下,他们无一例外为了能改变个人命运而奔波,而生存的压力和对社会认同的寻找,又将他们排斥在社会边缘,只能在失语状态中目睹着自己的悲哀。对于城市中的“人”的刻画,作家善于站在他们每个人的角度去感受世界。
对于生活于城市的琐碎生活书写而言,由于缺乏陌生化图景的勾勒,对于冲突制造的把握程度不够——比如说像存在于乡土中的死亡叙事和复杂族群关系引起的矛盾——导致故事往往会陷入一种庸俗、流水式的平淡,缺乏张力。而毕飞宇的新世纪小说中,这种弊病被作家用深入主体的心理描写巧妙化解,这种叙述不是通过暴力性来呈现冲突,而是通过视角切入,去除标签化,形成小说内部的叙事张力及外部的社会响应。
先谈内部异化问题,近来有学者发文提到:《推拿》中盲人群体遭受着三重异化,分别是盲人和自我、盲人和健全人、盲人和主流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8]。从盲人和自我看,小马因为失明,变得沉默寡言和易怒,通過玩弄“时间”来发泄精力,他渴望获得小孔的爱,像是一种对缺少的母爱的补偿,但最后性的压抑把自己送进了洗头房,这是一种源于失明的精神折磨或者说自卑带来的个性的的异化;从盲人和主流社会看,盲人这一群体需要的并不是同情,而是尊重。然而主流话语常常把盲人定义为弱势群体,是需要被照顾被怜悯的对象,这种同情只会加重盲人心理的不平衡,盲人被社会建构被异化;而从盲人和健全人这一点看,盲人和健全人始终处于对立状态中,虽然故事把盲人摆在中心位置,而将正常人作为灰色的陪衬,但小说将王大夫和弟弟并置,一个盲人和一个健全人,盲人可以自食其力挣钱养家,而弟弟四肢健全,却只能做家庭的吸血鬼,说明生理上的差别并没有成为盲人“躺平”的借口,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对于盲人的刻板印象,盲人和正常人之间的鸿沟是可能跨越的。盲人不“盲”,正常人反而堕落,这是一种错位的异化,小说以一种讽刺和对比的构思,去写盲人本就不易的生活背后家庭的冲突,发现城市底层人需要面对的多重压力。《推拿》有一处细节写到王大夫戴着一块手表,对于无法看见时间在指针上流逝的王大夫,这块手表是融入主流社会的通行证,也能够达成王大夫的心理安慰。这种来自于主流社会的规训力量,在无意识之中建构着盲人的边缘身份。
这样一种异化现象在《青衣》中也同样存在,主要表现在筱燕秋因为年老色衰无法再继续承担嫦娥身份而导致的身份焦虑,这种舞台身份的缺失引起了筱燕秋无法正确看待自我和他者,紧接着在个人混乱夹杂着来自社会、家庭、权利的压迫后,曾经台上的嫦娥丢失了自己的身份,无限的焦虑导致了人的异化悲剧。上述所说异化,所表现的其实是在社会生活中人的一种精神状态,毕飞宇在人的异化中,希望传达的是一种平等观念,还有正确对待人的态度。
再谈外部社会因素,新世纪“文学都市”,其实是物质化、欲望化、日常化、实利化的“世俗都市”[1]11。这背后的社会原因,是都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应该注意到,从新世纪以来,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的迅速发展,让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涌入,这种变化使得文学创作中的乡下人进城小说成了一类重要的文学作品,在进城小说中,乡下人对于城市的奔赴已经由过去的被动驱入变成了主动奔赴,他们常常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梦想,却被城市的文化和节奏搞得焦头烂额,只能迫于生计勉强维持生活。这类叙事,在雷达的文章中归结为“亚乡土叙事”[9],呈现着城市内容的新变,而正是由于人口密度的增加,城市工作岗位无法承载基数过大的人口,导致不可避免的就业困难,在这样逐渐内卷化的社会里面,物质和欲望便滋生得越来越庞大。
《推拿》中的盲人是进城打工的主体,他们基本都是从底层走向都市,大城市的机会和薪水对作为典型打工人的他们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在城市他们享受着的“大夫”这种高尚称谓,却区别于医生,只是服务行业的一种说辞,具有一定自我安慰性。而生理缺陷也导致对世界的认识产生极强的差异性,他们既厌恶自身也永远无法脱身被看的状态。因此他们主动地闯进人海里受人凝视,却只能被动地顺着城市的逻辑,靠物质和财富去武装自己。盲人群体在大城市人群的缝隙中就像是一座座烂尾楼,是城市的伤疤,他们的幻想被城市的文明和财富高高垒起,而进入城市后却发现举步维艰,没有让生活更富足的前路,只能像烂尾楼一样保持现状,身体的缺陷要求盲人更加上进和拼命,作为打工的主体,他们需要用财富来填补内心空洞,也需要社会的支持。
《青衣》并不具有进城小说的范式,却同样对应着这样一种“世俗都市”的气息,在“人”的方面,体现为乔炳章对烟厂老板的谄媚,烟厂老板对“嫦娥”的占有欲,前者体现为一种金钱支配下的附和,是为人性中被资本力量支配的一面,而后者,烟厂老板不是为了筱燕秋的肉体,只是一种对“嫦娥”身份下筱燕秋的间接占有,这体现为人性中扭曲欲望的另一面。
毕飞宇的都市书写是紧紧贴着时代的,戏子和盲人都是职业工作者,在飞速发展的当下,他们身上所弥散出相同的边缘气质,一方是逐渐没落的传统戏剧现状,另一方是充满神秘感的盲人推拿。作者将视野直接安插进个人,通过人物的遭遇来更直观的呈现都市的残酷,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书写并非是要批判都市的乱象,而是把关注点放在像筱燕秋和王大夫所代表的这类边缘人上,撕扯掉属于他们的标签,把职业、身体、阶级等因素全部剥离,平等看待。
丁帆在评论《平原》的文章中说:“《平原》更有人性的张力,而《推拿》就时时可以看出作者过于注重潜在的市场需求。”[5]6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毕飞宇其实很好的把握了市场性和文学性之间的平衡,它所带来的人性思考依旧震撼人心,因为《推拿》中展示的人性是和时代相连的,它区别于乡村小说70年代的人性存在。毕飞宇新世纪的四部中长篇小说,对“人”的再发现,其实也就是注重在平淡的日常中去发掘人性,围绕人及其处境进行思索,关注人的精神状态和个人欲望,从历史瞬间去挖掘人性的张力,比如在权力欲求下人的转变,在政治力量下人的压抑,或者是将目光聚焦到现代社会中,以人文关怀去书写正挣扎在焦虑中的边缘化的个人或群体。
参考文献
[1]雷达.新世紀小说概观[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
[2]臧晴.先锋的遗产与风格的养成——论毕飞宇的小说创作[J].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01):95.
[3]葛红兵.文化乌托邦与拟历史——毕飞宇小说论[J].当代文坛,1995,(02):45.
[4]毕飞宇,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167.
[5]陈子诺.毕飞宇苏北小说的独特文学价值探究[J].汉字文化,2020,(14):38.
[6]丁帆.《平原》:一幅旧时代文化梦遗的地图——兼论长篇小说的“保鲜度”[J].当代文坛,2021,(03).
[7]王春林.乡村、历史与日常生活叙事——对新世纪长篇小说一个侧面的考察[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03):16.
[8]杜姣.毕飞宇《推拿》的异化现象[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2,36(02):68.
[9]雷达.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J].文艺争鸣,2010,(03):11.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