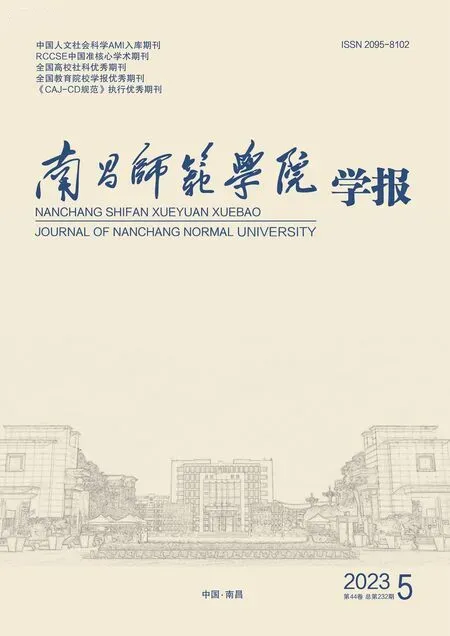禅宗时空观的哲学意涵及其现代意义
李 满
(南昌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32)
禅宗的时空观与常人的时空观迥然不同。其“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芥子纳须弥,毛孔呑巨海”之类的空间观念和“一念万年”“三际无别”“时序倒转”的时间观念,常常令人莫名其妙。禅宗为何秉持这样的时空观?禅宗时空观有何道理可言?禅宗时空观对于现代哲学具有什么意义?这就是本文要集中讨论的问题。
一、禅宗时空观的具体表现
(一)不可思议的禅宗空间观
A.芥子纳须弥,毛孔呑巨海
空间是事物的存在形式。物体的内部空间叫做体积或容积。物体容积或体积的大小是可以通过测量来确定的。大的物体可以容纳小的物体,小的物体不能容纳大的物体,这是常人的共识。然而,禅宗空间观与此迥异。
傅翕大士云:“须弥芥子父,芥子须弥爷。”[1](P234)百丈怀海道:“破须弥为微尘,摄四大海水入一毛孔。”[2](P128)东山云顶曰:“须弥、铁围、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3](P357)
芥子、毛孔皆属体积极小之物。须弥山、铁围山、大地、大海,俱属体积巨量之物。说高山大岳能装入芥菜子里,大地大海能装入一毫毛孔中,岂非疯人之语!然而,禅宗大师皆如是说,禅宗典籍里此类说法无以数计。可见禅宗空间观与常人空间观迥然不同。
B.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
世界由万物共同构成,其中任何物体与整个世界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作为万物之一的某物,不能等同于整个世界。不同事物形状性质各异,物与物之间界线分明,甚至相差悬殊,因此不可以混同为一。这是常人的共识,是常人坚持的空间观念。然而,禅宗空间观与此迥异。
洞山梵言上堂:“一尘一佛土,一叶一释迦。”[3](P1154)“佛土”和“释迦”在这里都是指无量广大的世界。因为,以禅宗立场来看,世界之大,无非佛土;万物之众,无非法身。全句意思是:一粒微尘等同于无量广大的世界,一片草叶等同于无量广大的佛陀法身(万物)。
九仙法清偈曰:“万柳千华暖日开,一华端有一如来。”[3](P1204)此处“如来”意同洞山梵言语中“释迦”,指无量广大的佛陀法身,即无量广大的世界万物。全句意思是:万柳千花中的任何一花一叶都等同于整个世界,一物与万物没有丝毫分别。
黄檗希运道:“果满菩提圆,花开世界起。”[2](P186)此处“菩提圆”意为“整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豁然显现”。全句与前几位语意相同,意思是:一颗圆满的果实将世界万物的本来面目显现出来,一朵盛开的花将整个世界呈现出来;也就是说,一花一果与整个世界无别。
如此奇特的空间观念就是禅宗典型的空间观念,同类禅语在禅宗典籍中无以数计。
(二)不可思议的禅宗时间观
时间是单方向流逝的,时间一去不复返。在单向流逝的时间之轴上,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三者之间界限分明,颠倒和混淆是不可以的。这是常人共识。
时间是外在于人的意识和行为的存在。无论人是否意识到它,时间总是无情流逝,分秒不停。无论人做什么、怎么做,时间总是无情流逝,一去不返。故古人曰:“时不我待,时不再来。”现代人则常说:“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此看来,时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这也是常人共识。然而,上述种种常人共识,禅宗都给颠覆了。
A.禅宗时序倒转的时间观
关于时序的倒转错置现象禅籍中有许多记载:
僧问如何是禅?志端禅师答:“今年早去年。”[3](P490)去年与今年的时序在这里被倒转错置了。僧问如何是青悍境?青悍如观禅师曰:“三冬华木秀,九夏雪霜飞。”[3](P845)无独有偶,玄沙师备禅师道:“三冬阳气盛,六月降霜时。”[1](P226)春夏秋冬的时序在这里被倒转错置了。僧问悟到什么?投子禅师答:“丫角女子白头丝。”[3](P299)白发覆盖在小女孩头上,年齿时序在这里被倒转错置了。问得道的人年岁多少?守昌禅师曰:“千岁老儿颜似玉,万年童子鬓如丝。”[3](P903)其所言与投子禅师法语异曲同工,年齿时序在这里被倒转错置了。
B.禅宗“一念即万年”“瞬刻即永恒”的时间观
关于一念万年、瞬刻永恒的时间观念,禅籍中有诸多记载:
僧璨《信心铭》道:“宗非延促,一念万年。”[3](P50)晦堂禅师曰:“从容一觉华胥梦,瞬息翱翔数百年。”[1](P227)清远禅师诗云:“春日春山里,春事尽皆春。春光照春水,春气结春云。春客春情动,春诗春更新。唯有识春人,万劫元一春。”[1](P227)云居文庆禅师偈曰:“道本无为,法非延促。一念万年,千古在目。月白风恬,山青水绿。法法现前,头头具足。”[3](P1013)
禅宗这种“一念”与“万年”没有差别、“瞬刻”与“永恒”同一不二的时间观念,与常人的时刻清晰、长短分明而绝对不容混淆错乱的时间观念,迥然有异。
C.禅宗“三际无别”,过去、现在、未来浑然一体的时间观
这种三际无别、过去现在未来浑然一体的时间观念在禅籍中有诸多记载:
问佛法在于三际否?大珠慧海曰:“现在无相,不在其外。应用无穷,不在于内。中间无住处,三际不可得。”[2](P157)大珠慧海“三际不可得”的说法出自《金刚经》:“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4](P37)意思是:禅者心性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无别,皆无碍于禅者之心;禅者之心并不分别过去现在未来。也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在禅宗的时间观中是浑然一体无差别的。
幽州宝积道:“法本不相碍,三际亦复然。”[2](P152)黄檗希运道:“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本既无物,三际本无所有故。”[2](P186)玄沙师备道:“无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际。”[2](P344)浮山法远道:“十方通摄了无遗,三际全超在此时。”[2](P437)四位禅宗大师法语异曲而同工,意思都是:过去现在未来在禅宗的时间观中是浑然一体无差别的。
二、禅宗为何秉持这样的时空观
禅者的终极目的就是了空得道,得道成佛,获得人生的大自由大自在。禅宗的时间观、空间观、乃至一切人生价值观,都是为实现人生的大自由大自在这个终极目的而存在的。
而在禅宗看来,常人的空间观是达到自由人生境界的根本障碍。
禅宗以为“心外无物,法由心生。”也就是说,常人以为确切实在的事物,禅宗认为皆属人心所现之象。山岳、海洋、芥子、毛孔都属人心所现之象,皆非实在之物。
既是人心所现之象,其大小又有何实在性可言?而常人毕竟认定山岳、海洋为极大之物,芥子、毛孔为极小之物,大小迥异,皆属实在而不可通融。在禅宗看来,这只是证明常人“我执”“法执”[4](P98)。也就是说,常人的心念固执,固执地以为自己眼前物象是铁定不易的实在。
因此,禅宗的第一要务就是破除常人的固执型空间观。“芥子纳须弥,毛孔呑巨海”这种说法的首要作用,就是以极端的手法来破除常人固执的空间观念。而这种说法的更深含义则在于:既然一切物象都非实在,都属人心所现之象,则物象与物象之间相含互容、相互通透叠合,就纯属自然了。
常人心执,固执地以为眼前物象属实在之物,且固执地以为物体形状性质各异,物与物之间界线分明,绝不可以混同为一。而禅宗却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同样,这种说法的首要作用就是以非常手段来破除常人固执的空间观念。而其更深含义则在于:既然万象皆属心象,其根本性态即无别异。恰如东山云顶所言:“入得我门者,自然转变天地,幽察鬼神,使须弥、铁围、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众生,不觉不知。我说此法门,如虚空俱含万象,一为无量,无量为一。”[3](P357)意思是说,人心犹如虚空,一切物象都蕴含在心中,而随缘显现出来就成为眼前异彩纷呈的万象。一心生万象,万象归一心;因此“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也就是说,一象与万象,其性不二,皆为心现之象,故而道通为一。
在禅者看来,常人的时间观同样是达到自由人生境界的根本障碍。
常人以为时间的长短是客观存在的,时光匆匆流逝、从来不曾停留,这是客观事实,是谁也无法改变的铁定实在。然而在禅宗看来,常人所持的时间观是痴人的自困自缚。因为,将时间视为外在于人的铁定实在且谁也无法改变,则人必然被时间制约、支配、主宰,因此成为时间的奴隶;在时间面前,人必然完全丧失自由自主和独立自在性。要获得人的自主自由和独立自在性,就必须推翻常人这种时间观念,而代之以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于是禅宗就发明了“一念万年,瞬刻永恒”的时间观,并坚定地加以秉持。
清远诗云:“唯有识春人,万劫元一春。”[2](P227)意味着在清远这位识春人眼里,万劫与一春没有区别;而万劫之所以与一春没有区别,就在于人有识春的心。人若有一颗自由自在的心,便能不被时间制约、支配、主宰,眼前之春光就等于万劫之中任何一段时光,任何一段时光与万劫也就没有区别。也就是说,时间对禅者之心没有影响,时光的流逝不能使悟者之心受到骚扰,不能使禅者之心被时间所役使而处于不由自主的状态。时光自然流逝,每一寸时光完全一样,人又何必执着于一时一刻,纠结于时光的流逝呢?如此,则时时是春光美景,日日是快活好日。这样的时间观念,这样的禅心状态,真正是大自由大自在的境界。
云居文庆偈曰:“道本无为,法非延促。一念万年,千古在目。月白风恬,山青水绿。法法现前,头头具足。”[1](P1013)
在文庆眼里,一念与万年没有区别。所以没有区别,因为悟者秉持禅道,而禅道本来就是自然无为之道。时间自然流逝本无所谓快慢,分分秒秒都一样;禅者秉持禅道,即是顺其自然,分分秒秒一视同仁。如此,则每时每日都自然而然,怡然自得。分分秒秒一视同仁,便是念念一如,万年无别。如此,便是一念万年,瞬刻永恒。
自然时间无快慢,而常人却谓“时不我待,时不再来”,感觉时间匆匆逼人、促人。在禅宗看来,不是时间出了错,而是常人时间观念出了错。常人惜时如命,爱财如奴,使自己完全丧失了自由自在的佛性。若能幡然省悟,便可时时悠然自在而怡然自得,不受时间催逼。如此,则日日所见都是“月白风恬,山青水绿”的好时光。
常人以为过去、现在、未来三际分明,不可混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定实在。然而这样一来,自然时间的圆融一体性就被人为地分离割断了。人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倒逼自己。所谓“今日事今日毕,莫将今事待明日。”若是今日事未今日毕,这事就横梗在心里。若今日事今日毕了,则“明日又有明日事,莫将明事待后日。”如此,则时间分分秒秒在逼迫人,则人完全被时间所支配和主宰,完全丧失了本来具足的自由自主性(佛性)。
禅宗以为时间并无过错,是常人的时间观念出了错。时间日日自然流逝,天天都是一样的。常人非要把日子分别为昨日、今日和明日,坚持以为过去、现在、未来不同,目的无非是为了完成确定的任务。将事情与时日绑定在一起,于是,人就这样被每时每日地绑架了。
如前所述,禅宗的终极目的是达到大自由大自在的境界。因此,常人这种三际有别的时间观念必须予以扫除。
玄沙师备道:“佛道闲旷,无有程途。无门解脱之门。无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际。”[3](P344)其意为:禅者求佛之道闲适旷远,自然无为而已;若将自然流逝的时间刻意分别为过去现在未来,由此而划定昨日今日明日必须完成的事,这便背离了自然无为之道,这便使自己被时间所绑架,而丧失了本来具足的自主自由性。去除人为刻意的功利之心而复归自然平常之心,则三际自然无别,日日自由自在。
浮山法远道:“十方通摄了无遗,三际全超在此时。”[3](P437)其意为:东南西北上下左右本无分别,过去现在未来本无分别,是常人刻意地作出分别。此分别之心其实是执着之心,将心执着于种种人为的分别,则人心便丧失了本来具足的自主自由性,人生便丧失了自然自在的生态。若是一念省悟,便“十方通摄了无遗,三际全超在此时”;也就是空间复归于本来具足的自然圆融一体,时间复归于自然而然的三际圆融一体,禅者则达到了自由无碍的至高境界。
黄檗希运道:“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本既无物,三际本无所有故。”[3](P186)其意为:世人刻意将时间分为昨日今日明日,将事情绑定于过去现在将来,然后对自己形成倒逼的形势,使人被时日完全绑定而丧失自身本来具足的自由自主性。这叫做庸人无事生非。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然本无事,人为刻意造作而成纠结事”。若能一念省悟,自然了知“三际本来无别,人生自然无事”,如此便可自然度日,不受时间逼迫,而得自由自在。
在禅宗看来,常人所持的时间观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必须坚决打破而完全颠覆。在常人看来,时节有序,四季顺延;怎么可能“三冬华木秀,九夏雪霜飞”呢?同理,时间有序,年齿分明;怎么可能“千岁老儿颜似玉,丫角女子白头丝”呢?而如此这般的偈语在禅籍中海量存在,其最明显的意义就是通过颠倒自然物候现象来颠覆常人固执的时间观念,从而使人获得大自由大自在。而其甚深意义则在于:在常理看来不可能,而站在佛法禅理的立场上来看却没有什么不可能。
以常人时间观念来看,“一念万年”绝不可能,“三际无别”也不可能。而禅宗看来,常人之所以说不可能,纯属执着于自身刻板的时间观念。彻底超越和颠覆刻板的时间观念,则分分秒秒自然无别,念念同于万年;则三际本来无别,时时自然度日,自由无碍。
如前所述,常人的时空观之所以阻碍人心,使之不得自由自在,是因为“我执”和“法执”[4](P98)。禅宗的时空观之所以能让人获得大自由大自在,是因为禅者之心了无执着。禅心无执,则物象皆空灵圆融无碍。同理,物象皆空灵圆融,相互间通透穿越而了无隔碍,则禅者之心便得大自由大自在。
三、禅宗时空观的现代哲学意义
用现代哲学话语来解读禅宗的时空观,就会发现其中蕴藏着极为深刻而宏远的哲学意义。
自然本体是无在而无所不在、无时而无时不至的绝对实体。无在而无所不在,即无空间限定性;无时而无时不至,即无时间限定性。无时空限定性的东西属于非现实性存在,现实性存在必然具有时空限定性,故而自然本体不属于有限现实性存在,而属于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自然恒常变化而变化恒常,因无限能动,故无限可能。
人是自然的产物,故而本来具足自然性、自然大化性、恒常变易而变易恒常性、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禅宗称之为佛性或自性。佛性、自性即自然性,即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禅者修行的根本目的是获得人生的大自在、大自由”[5](P52),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认为人是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者。
然而,人出生入世,也就意味着走出绝对无限境域而进入相对有限境域,从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转换为相对有限现实性存在,从无在而无所不在、无时而无时不至的绝对存在转换为时空相对有限性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禅宗认为人是相对有限现实性存在者。
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让人出生入世,进入现实环境。在现实环境中人被自然生成为三维时空性存在物。人本能地将眼前的一切看成三维时空性存在,由此而生成了三维时空性的人类现象世界。(万物也是自然的产物,故而同样本来具足自然性、自然大化性、恒常变易而变易恒常性、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禅宗谓之“佛性遍在于万物”。)这种自然生成的三维时空性的人,是相对有限现实性存在者,是绝对无限时空性的自然本体的相对有限现实性体现。这个三维时空性的人类现象世界,则是自然本体绝对无限时空性(通过作为相对有限存在者的人而造就)的相对有限现实性体现。
禅宗认为,人生在世难免“我执”而“法执”[4](P98)。“我执”即执著于自身本能的三维时空性存在意念,“法执”即执著于人为造就的三维时空性现象世界。换言之,“我执”而“法执”,即执相对有限时空性存在以为绝对实在。如此,则自然本体的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便被自身的相对有限现实性所遮蔽;同时,人类佛性、自性(人的绝对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亦被人的相对有限现实性所遮蔽。
众所周知,人是一种善于发明和使用工具的生物。用禅宗的话来说就是,人是一种善于发明和使用方便法门的生物。时间和空间本质上是一种人造的坐标尺度和测量工具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在禅宗看来,时空坐标尺度或测量工具就是人所发明和使用的方便法门之一。
任何尺度、工具或方便法门都是人类的发明。当然,人的发明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深深地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性。
康德认为时间与空间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存在,而是内在于人类心灵的东西,是心灵天然就有的两种实用理性范式。人类感官接触到的一切现象都会经由人类实用理性范式被赋予时空形式,由此生成为时空定域性存在,这也就是现实性存在。对于人类而言,无时空确定性的东西等于不存在的东西。而事实上,事物的时空形式是人类赋予它们的。禅宗时空观与之不谋而合,禅宗同样认为时空形式是人类心识在识认外界事物时赋予事物的。
人类的任何发明根本上都源于天赋本性。自然让人出生入世,将人类生成为三维时空存在物,因此人类本来具足三维时空性。于是,人类便本能地以自身的存在方式看待和对待一切。人类以此来审视测量感官所接触到的所有东西,于是所有东西在人类看来都必然具有三维时空性质。换言之,没有三维时空性的东西对于人类而言就是不存在的东西,非时空定域性现象属于非现实性存在。而其实,对象的时空规定性或现实存在性恰恰是意识测量时人类赋予对象的。所以禅语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3](P232)。也就是说,整个世界一切现象都是经由人类心识而获得现实存在性和时空规定性的。
人类先是本能地将一切看成三维时空性存在物,然后又有意识地发明了时空坐标测量工具,有意识地用时空坐标工具来测量和定位一切,从而建构起整个人类现象世界。恰如霍金在《生命的意义》这篇讲演中所说:“人类是高度复杂的生物机器,行为举止全根据自然法则。大脑得以创造并延续人的意识,有赖于奇妙的神经元互动网络,而人的意识创造了外在世界的三维模型,这种最适模型就是我们所谓的现实。这种现实的范围,比日常生活中周遭所见还要广大。当我们探索宇宙时,我们认知中的现实世界拓展得愈来愈大。我们回顾过去,一直到宇宙自身的起源,这一切,这整段137亿年的宇宙历史,都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模型。”[6](P34)
需要强调的是,人类建构起来的这个世界并非本然存在的自然世界,而是人类现象世界。整个人类现象世界都属于时空定域性存在或相对有限现实性存在,而自然本身则属于绝对无限存在。自然恒常变化而变化恒常,故属于非时空定域性存在,属于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
经由时空坐标系统测量和定位所造就的现象世界,必然是时空定域性存在,也即相对有限性存在。自然本属于非时空定域性存在、绝对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一经人类实用理性工具的测量定位,绝对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便被人为地转换为相对有限现实性存在。而人类本能地将此时空定域性存在和相对有限现实性存在视作绝对实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类也就因此被自己造就的相对有限现实性存在禁锢成了相对有限性存在者。
当人将三维时空性本能发挥到极致,用依据本能发明的三维时空坐标工具测量定位了整个宇宙,将宇宙定义为有137亿年历史、直径为930亿光年的东西,并认定这个自己定义的东西是铁定的实在,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绝对存在时,人是被自己的三维时空性本能所主宰了,是被自己发明的三维时空坐标工具所主宰了,进而被自己用三维时空坐标工具测量和定义的人类现象世界所主宰了。人就这样沦为了人为造物的奴隶。
在禅宗看来,时空定域性存在或相对有限性存在是常人的存在状态。这种存在状态是常人将方便法门当成终极真理,视相对有限存在为绝对无限存在,由此造成自蔽自障自困自役所导致的存在状态。禅宗称之为“我执”而“法执”[4](P98)。我执而法执,在这里是指人类自我中心偏私执著于时空坐标测量工具这种方便法门,进而执著于由方便法门所造就的人类现象世界(执相、著境)。常人因此必然陷于画地为牢而作茧自缚的境地,由此迷失人人本来具足的佛性或自性。禅宗所谓佛性或自性,即绝对实体性、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恒常变易而变易恒常性、自然大化而圆融无极性。
在禅宗看来,人类将自己经由时空坐标测量工具建构起来的世界视为客观不易的绝对实在,是出于人性的痴愚和蒙昧。人类本能地以实用工具理性跑马圈地而建构自己的世界,最终导致人类的自蔽自障自困自役。人类发明工具使用工具,随后将自己异化成为工具;人类造就世界占有世界,随后将自己物化为自造的现象世界的奴隶。是所谓始而画地为牢,继而抱残守缺,然后故步自封,最终坐井观天;以为自己经由时空坐标测量工具看到的那片天就是无垠的天空,就是自然的本来面目;最终将人自身陷于固执不化的相对有限境地而不得自由。
禅宗立意将人从相对有限境地解脱出来,达到绝对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的存在境界,即大自在大自由的人生境界。大自在,即返璞归真而回归自然,对万物一视同仁而与万物共生同在。大自由,即人以自身的自由给予宇宙万物以自由,从而达到人天合一而物我两忘,与天同运而与道同化的自然境界。
在禅宗看来,自然本身属于非时空定域性存在、非相对有限现实性存在,属于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即绝对时空性存在。
而禅宗的时空观似乎在现代宇宙物理学研究者那里得到了共鸣。继牛顿物理学的三维时空观被爱因斯坦物理学的四维时空观替代之后,随后又产生了五维、七维以至于十一维时空理论,更有论者提出了宇宙时空具有无限多维性的观点。这也就是说,自然本身属于绝对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就其时空性质而言,自然本身具有无限多维性。无论是三维、四维、七维、十一维时空以至于N维时空,都是人类用自己发明的测量工具所造就的,都属于时空定域性存在、相对有限现实性存在。唯有无限多维性时空,才是自然的本来面目,才属于绝对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
当人超越三维时空性本能,站在自性、自然大化性、无限能动性的立场来观测世界的时候,世界便不再呈现为固定的三维时空性,而是可以呈现为四维时空性、七维时空性、十一维时空性以至于N维时空性面貌。
在三维时空不可能的事情,在四维时空就可能了。在四维时空不可能的事情,在七维时空就可能了。也就是说,前文禅语所描述的所有那些不可思议的时空现象在高维时空中就都成为了可能。而时空的维度是无限的,因为自然本体属于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佛性、自性属于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也就是说,在无限多维时空中一切皆有可能。无论是多少维度的时空观,在禅宗看来都属于人类发明的方便法门权宜之计。唯有在各种时空维度之间自如转换无限变化,方便法门权宜之计才会升级为无穷妙用之微妙法门。当此时刻,人便由相对有限现实性存在升级到无限能动而无限可能性存在的境界。
从现代哲学意义上说,是禅宗的时空观敞开了人类时空理论发展的无限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