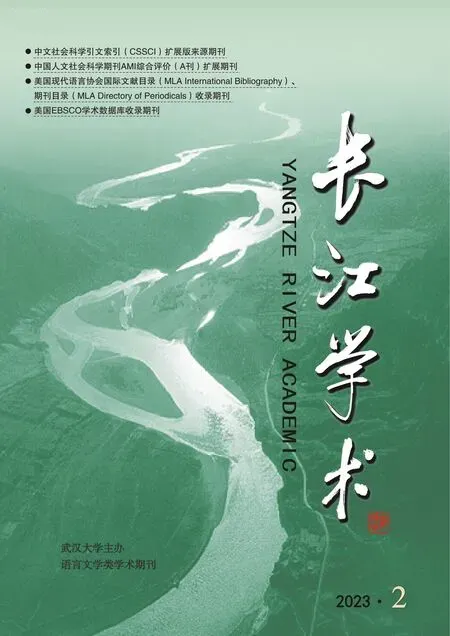试论语音史研究框架的转型
刘晓南
(复旦大学 古籍所,上海 200433)
汉语语音史几乎是伴随着上古音研究而开始的。随着上古音研究的成长,在经过了宋元明清诸代漫长的酝酿之后,语音史从上古历经中古、近代以达现代的研究框架终于在20 世纪初成型,随之而来的是上古音、中古音和近代音的纵向研究全面展开。但随着时间的推进,研究的步步深入,语音史各个时代的研究在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经常遭遇到来自历史上的共时层面复杂语音现象的挑战。这些新的挑战,一次又一次地提示我们是否应当对不同时代平面上丰富多彩的语音现象作出多视角的考察,把历史语音的空间差异纳入研究框架之中来?毫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形形色色的挑战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能量已经将语音史推向了一个十字路口,是沿袭已有的依时间线索单向推进的路径继续前行,还是迅速调整,引入空间维度以促使语音史框架作出历史性转型,已经成为语音史学科进一步发展的一道绕不过的必答题。有鉴于此,我们将简要地回顾语音史学科的萌生与百来年的发展进程,展望发展的方向,尝试给出我们的答案。
一、语音发展观和语音史
音韵学研究古汉语语音,就是要在语音发展观的指导下,对不同历史时代的语音状况及其发展变化作出详实的考证和科学的论述,以建构语音史的框架与体系。通常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但语音史的研究却先有行动,后有思想。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语音发展观的形成有一个从偶然涉及古音进而到有意识地揭示古音的漫长探索过程,随着古音材料逾益丰富,对古音的了解愈益深入,有关语音古今变化的思想越来越清晰,语音史才逐渐得以成型。
(一)汉唐人偶说古音



(二)宋人的古音研究实践




(三)古今音变思想与语音史
1.宋人的古今音变思想萌芽
在语言学史上,叶音是宋儒研究古音的主要方式,其代表人物是吴棫、朱熹。自明末以来,对宋儒“叶音”开展了广泛的批评,可以说充分地批判了其消极的一面,但对其积极的一面关注不够。我们认为,“叶音”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萌生了宋儒的“古今音变”思想。
以今所见,最早显现“古今音变”思想的是吴棫。吴棫早期的古音学著作《毛诗补音》里其实就有了比较清晰的古今音变思想。因《毛诗补音》已佚,故而后世学者仅据其《韵补》来论其古音学。看到他的取证古今杂糅,字无定音,故而不为采信。如麻韵所收的一组从“叚”得声的字,《韵补》上平声九鱼洪孤切小韵收“霞瑕鰕騢豭”、下平声七歌寒歌切小韵收“霞瑕蝦遐”,一会儿入鱼部,一会儿入歌部,给人大道多歧之感,颇有疑惑。但在《毛诗补音》中,“瑕”等字的论说就大不相同,甚至可以说精采:

这段话中的点睛之笔就是:“秦晋以前凡从叚者,在平则读如胡,魏晋之间读如何,齐梁之后读为胡加切。”看到这段话,才明白《韵补》为什么要将这批字一会收入歌部,一会收入鱼部。原来他是要说,这些字在秦晋时归于鱼部,并引述先秦两汉的例据证之,到魏晋之间转归歌部,同时引魏晋时的例据证之,时代之音与例证若合符契。试将吴氏此意,以音标图示如下:






“讼”是个多音字,有平、去二读,《广韵》钟韵“祥容切”、用韵“似用切”。宋代常用去声一读,而《诗经》该段韵文从声律上看,当取平声一读入韵方可和谐,朱子在“讼”字的平去二读之中选定非常用音平声一读入韵,故注为叶音。然而为了注释从简,朱熹在《诗集传》《楚辞集注》中一般都不给出自己叶音的根据,后人难以理解,甚至以为臆说。
陈第与焦竑等人批评叶音的正面意义,并不是反对前人提出的古音说,究其实只是反对叶音表现出来的纷歧繁芜,以及由此引出的主观臆断。强烈的怀疑,使他们全盘否认了“叶音”的音注,进而确认了不但古代字有本音,而且字音随时而变的观点。陈第的名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将“古今音变”升华为一种势所必然的历史规律。学术思想的升华,引领并促成了他超迈前辈的学术成就。
3.语音史框架形成
陈第既然认识了古代字自有本音,就从《诗经》等先秦韵文考古音,作《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对先秦韵文中许多韵脚字的古音作了考定。用充足的证据证明了古音是确定的,力纠“叶音”一字多叶的偏差,其中已经隐含了古音系统不同于今音的意涵。清初音韵学家顾炎武考证先秦古音,离析《唐韵》,得出古韵十部系统。顾炎武有浓厚的复古思想,他要摒弃今音,以返淳古,这是不对的。但他由此而进入到古韵系统,开始了古音系统的研究,这是他对古音学的重大贡献。后来的学者循此以进,随着古音系研究的逾益深入,语音史的观念和框架逐渐形成。
清朝乾隆间编《四库全书》时,收集了一大批包含古音著作在内的音韵之书,依类编排,分别列为古音之书、今音之书和等韵之书三类。其中古音、

二、单线研究模式及其困难
(一)单线模式的语音史


单线模式继承了音韵学古音研究传统。前文我们已经看到,从吴棫到段玉裁逐渐形成的正是语音从一个时代到下一个时代连续不断演变的思路。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古音系列研究,强化了这个思维模式。高本汉以《切韵》研究的辉煌成就建立了中古音在语音史上的核心地位,他明确提出从《切韵》上推古音,下溯今音的研究思路。有了中古音的立足点,有利于语音史单线发展模式的确立。
按照单线发展的思路,除王力先生晚年写的《汉语语音史》之外,其他语音史都将从《诗经》用韵和《说文》谐声系统考求的音系确立为上古音系,以《切韵》音系代表中古音系,以《中原音韵》音系为近代音的代表,三点确立,然后将三点之间的空隙填充补足,语音史的全景画卷就大功告成了。

(二)单线模式的困难
单线发展的语音史研究模式着力于每个时代建立一个音系,可以名之曰:时代音系。正因为一个时代只有一个音系,因此,时代音系也就被寄予了解决本时代的所有语音问题的殷切期望,但在实施中却遇到了许多困难,有时甚至左支右绌,可以概括为四点。
1.诗文押韵存在大量的跨部通押
通过归纳韵文押韵所得的每个时代的韵部系统,都无法全部解释本时代诗人的用韵现象。以《诗经》用韵为例,江有诰构建了古韵21 部系统,后出转精,超越先贤,然美中不足的是,仍有很多出韵通押。他自己曾有一个统计,《诗经》韵段1112 个,跨部通押有70 来个,约占总数的6.2%。但细数其《诗经韵读》,实际上他的通押韵段多达119 个,占总数的10.7%。如此之多的跨韵部通押,对其古韵部系统的合理性、严谨性等等无疑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我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绝对不是一个特例,古音学史上无论哪一家,无论其立韵是如何精严,都无可奈何地留下不少的跨韵部通押。推展开来,无论是从《诗经》等先秦文献中所得的上古韵部,还是从汉魏以下各个时代韵文获得的韵部系统,跨韵部通押都如影随形,无法消除。足以显示出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作者之间,押韵的差异有多大。这些都不是一个音系所能解释的。
2.音近通假大量存在
通假现象,是古代文献中的常例,几乎可以说没有哪一部历史文献不存在通假。但只要稍微有一点古文阅读常识,我们都会惊讶在时代音系的背景下,古音通假居然是以“音近通假”为多,而少见“音同通假”。我们常说,古通假类似于现代人写错别字。可是,现代人写别字都是同音别写,如“阴谋诡计”误写成“阴谋鬼计”之类,一般不会写成“阴谋贵计”或“阴谋归计”等等,说明两字读音不同而别写是很困难的,即算是读音差异很小的字之间写错也很少见。也就是说,音近字“通假”其实是极不自然的。然而,当我们采用“时代音系”来考察文献中的通假现象时,却正好与之相反,音近通假占绝大多数,成为自然现象,同音通假反而是少数,变得不自然了。很难理解为什么古人放着音同的不别写,专挑读音不完全相同的字来别写?恐怕更有可能的是,写别字的人所操语音并非标准的时代音系,他的同音别写,在时代音系看来,就不同音而是音近了。
3.古音注材料不合时代音系


4.诸韵书音系往往不同
韵书是记录某一时代音系的专书。如果韵书所记都是时代的代表音系,那么同时代韵书所记之音一定相同,至少其音系主体相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早期韵书,即《切韵》以前的韵书大多不传,我们今已难知其详,但颜之推早有评述曰“自兹厥后,音韵锋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亦可见其差异甚大,互不认同。
《切韵》一出,风行天下,音韵定于一尊,但数百年来的持续修订,也说明内中有所差异。元明以降,《蒙古字韵》与《中原音韵》几乎同时,但二书音

三、转型:时空结合的语音史
(一)时间与空间、通语与方言
历史语音的高度复杂性向语音史研究的单线模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其凸显出来单线模式的重大弊端,就在于强调时间推移的同时,忽略了空间变化的差异。所谓空间变化,至少有两个内涵。
1.通语基础方言的变换。
汉语从先秦到现代,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约五千年,一直存在一个全民通用的共同语,可以称之为通语。



2.古方言语音的歧异
这种歧异最早表现在《诗经》用韵研究中的跨韵部通押的例外之上。处理这些例外,前修常作两种处理,一是目为合韵,看作临时从权的音近通押现象,如段玉裁;一是看作古方音差异,如顾炎武、江永等。后者由于缺乏充足的证据来加以证实,故而长期不被采信,而前者又难以圆满解释为什么临时合韵的数目如此之大,如江有诰韵谱的占总数百分之十以上。近年来,随着语音史研究的深入,新材料的拓展,人们越来越多的发现,不但《诗经》、先秦群经用韵有例外,汉赋乐府、魏晋古诗以至唐诗宋词元曲传奇等等用韵莫不如此。唐宋以下传世文献相对丰富,从中可以考得诗词用韵的例外属于方言的可信证据。证据确凿,完全可以肯定,大多数的用韵例外,正是当时使用方言特异语音造成的,当然也有极少数可能是用韵偶疏。近代如此,中古上古亦可类推。
这样看来,陈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名言应当要做新的诠解:“原则上大概地理上看得见的


(二)两个研究层面
时至于今,通过文献研究汉语的历史语音,必须面对复杂的方音。毫无疑问,语音史的“一线制”框架有必要作出相应改造,要在时间维度之外,确认并引入空间维度,以改变长期以来仅关注时间推移之变异而忽略时代共时层面语音差异的传统研究态势,形成由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或通语、方言两个研究层面组合而成的新型语音史。在这个新的架构中,反映特殊语音现象的历史方音将与时代音系和谐共存,各司其职,时代音系只需要说明时代的代表语音,解释民族共同语语音的应用及表现,再也不必期望它去完成那个不可能完成的诠释纷繁复杂的方音现象的任务了。
因此,新型语音史构架必须确立两个研究层面:上位层是研究通语音系,下位层是研究历史方音。在这个二位层级结构中,由空间维度引入的历史方音研究,不但不会与传统的“时代音系”发生冲突,反之,恰恰由于有历史方音的介入,时代音系的性质与价值才得以清晰的确认。
1.上位层的性质
所谓上位层研究是要聚焦于语音史的代表音层面,其目的是获取某一历史时期文献中所有语音现象的共性成分,并将它们有机组合起来,作成一个时代的代表音系。这个音系是某一时代全民通用的共同语音,即通语语音。通语音系一般有强势的首都方言作为基础方音,有广泛通行的韵书详细记录,符合大多数文献语音的共同特征。如果基础方言尚不明朗,那么,通语音系就应当由时代文献语音中的全部共性因素构成。所谓“共性因素”泛指不同地域的不同作者,都按照同一种音类规则使用文字,比如同样的押韵,同样的同音字组等等。造成文献语音具有共性因素的原因,是记写文献的汉字具有超方言性和“文言”用语有要求规避俚俗口语的传统。在传统文献的话语环境下,通语语音有足够的空间来展示自身。通语的共性可以通过文献有意无意的记载,得到充分的表现。这也就是为什么通过海量文献归纳的语音系统一般都属于通语音系的原因。要之,通语音系是时代广泛使用的,普遍认可的,有极大的共同性的成系统的语音。通语音系不但具有全民通用的共性,同时也提供了区域方音沟通的桥梁以及描写和说明方音差异的参照系。
在新型语音史构架中,通语音系作为全民共同语的语音,必然是研究的主体。上位层研究必然聚焦于时代通用的各种共性的语音现象,而不必囊括作为不同区域变异的特殊语音现象于一身,更不必寻求构建一个包打天下的超能音系。同一时代的地域性方音特征的研究将留待语音史的下位层来实施。
2.下位层的性质
新语音史下位层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复杂的历史方音,这个研究必须要囊括所有的文献中特异语音现象,加以古今方俗的比较、考证,以论证其方音特征与属性。
汉语的方言自古而然,任一历史时代都广泛存在与通语相对的方言。方言的语音即“方音”虽然自成体系,但对于通语音系而言,绝不是异质的系统。方音与通语之异只是同质前提下的大同小异,有同有异。因其大同,故属于汉语大家庭,因其小异,故能有别于通语。任一时代的历史方音都以其有别于通语共性的特异语音为标志,在文献语言中表现为语音现象的个性成分、特异成分。它们在各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但在历史文献中却大多以特殊方式出现。因此,处于语音史下位层的历史方音研究有“细碎性”“散点性”和“依附性”三大特点。
所谓细碎性是指语音文献中的历史方音现象不显著、零碎而不成系统。这是因为受汉字文献超方言性以及文言排斥俚俗用语的传统的制约,大多数方音在文献中被“磨损”,被“转化”,成为一些隐而难显的遗迹,成为文献中特异的、枝节的现象。虽然细碎,但决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它们,因为它们细碎而独特,但并不少见,广布于文献之中,如点点繁星遍布昊天,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它们其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量,足以对语音史的研究发生重大影响。



四、新型语音史:两个层面的有机结合
语音史研究设立通语、方言两个层面,这是从研究的方便立说的,绝不是要将语音史割裂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当然,研究中可以有所侧重,完全可以就某一具体对象或材料,侧重于通语的或方言的层面研究,无论是哪个层面,必然都是语音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仅就某一时代的语音文献而言,完备的语音史研究是既要进行通语语音的研究,又要进行方音的研究。两个层面的研究不可分离,侧重点不同,效能各异:前者是主体的,全面的,后者是辅助的,补充的;前者是共性的,是所有文献展示的共同语音现象,后者是个性的,只是某一区域文献中特殊现象;前者是系统的,以建立音系为目标,有完整的韵部系统和声母系统等等,后者通常是特征式的,表现为某韵与某韵通押或某声母与某声母通用等等;研究的材料往往前者是多数的,大量的,后者是少数的,小部分的。最后,从史的角度来看,前者以时代音系为其主线,完全可以也必须通过前后时代的串联作纵向发展,形成不间断发展的语音史;后者散播于某一历史时代的广袤区域之中,星罗棋布,呈现散点多线的等征。它们游移于主线周围,以其绚烂多彩的语音表现,作为主线的补充成分,极大地丰富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语音,也成为语音史纵向发展的原因或动力之一。因此,两个层面的研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两者全备,才是完备的语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