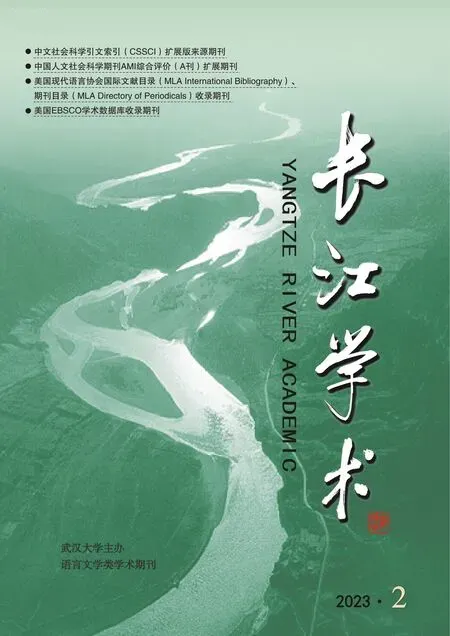欲望和想象的莫比乌斯圈
——从赫西俄德、安徒生到福楼拜的包法利综合征
涂险峰 曹晓龙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镜中之灯”与包法利综合征











二、“潘多拉瓶”与希望的理念










这一理解,与赫西俄德文本中关于潘多拉的细节裁剪颇为一致。她显得像人偶一样被创造,却又被众神赋予了魅力、狡黠、巧言加谎言等主体能力,而唯独没有智慧。耐人寻味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偏偏只负责为她配备服饰。她被赋予了一切迷人的品质,只为直接激起欲望,而她作为欲望的对象,本身也具有不可遏制的欲望。她的欲望体现为没有特别恶意的好奇心,缺乏洞见的好奇心。欲望、好奇、缺乏智慧再加上对人类本无恶意,才是潘多拉先放出灾祸后又永远闭锁希望的情形。她对瓶中封闭的希望完全缺乏理解,而且,连她这位掌握瓶盖开阖者也不能理解希望的具体含义,更不指望无缘窥其一瞥的人类能够找到答案。她让希望永远留在想象之中存在,并成为纯粹而凝固不灭的神往对象。
由于希望在潘多拉这里被永远封禁,于是失去了前述诸多其他含义,例如,相信某事必定发生的“信念”和“预感”,以及“凶兆”“担忧”和“焦虑”等。希望本身变得纯粹而绝对,变成了不可到来、不可认知之物的“能指”。因其不可认知而不断想象,因其不能到来而持久渴望。至于潘多拉最终封闭的所谓“希望”的所指究竟是什么,是否真有什么,我们均不得而知。甚至可以说,此时希望就是如此定义的。无论它是什么,凡是被封闭的“瓶中之物”甚或“瓶中之无”,均可定义为“希望”。或许还可以认为,被潘多拉释放出来的万千灾难,当它们尚在瓶中时,与叫做“希望”的东西并无区别。当然,无论“希望”一词有多少语源学含义,其意义最终由其具体用法决定,而潘多拉决定性的闭瓶行为,锁定了希望的最终定义,即“关闭在瓶子里的东西”。因为永久关闭,希望剩下的主要特质便是“不可企及”,希望的结构则是对不可企及者的欲望和想象。
潘多拉将希望永久性地封禁在瓶中的行为,意味着希望与它的实现变得不可调和。总之,如此界定希望的逻辑能够成立,需要依赖对人生虚妄本质的洞见,而这种虚妄的现实,正是赫西俄德第一个版本中所发生的情形:婚姻的三种状况都不幸福,单身、幸福或不幸的婚姻概莫能外。因此,赫西俄德精心裁剪出的第二个版本,其实仍与第一版本的逻辑内在契合。这正如莫比乌斯圈的奇特拓扑结构:沿着条带的中轴线纵向剪断,仍是一个且仅只有一个闭合的圆环,而这个闭合的圆环,由一体一面的欲望与想象构成。
潘多拉提供了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希望”的理念,但她本身却对其中的深意无知无觉。那么,谁是故事中洞悉希望之谜的知觉者?是事先不断发出警告的普罗米修斯吗?埃斯库罗斯在自己的普罗米修斯故事中,曾谈到了人类的悖谬处境以及希望的性质。



三、安徒生的“瓶中童话”与姿态性迷狂








四、福楼拜的“自我祛魅”与想象和欲望的莫比乌斯圈
生活在苏联强盛期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极致的现实主义氛围中,虚构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故事,阐述文学如何介入生活,告诫不要将想象用于哀伤。吊诡之处在于,这部作品却因其动人的浪漫特质,成为少数至今仍广为流传的苏联作品。相较于现实中的安徒生,帕乌斯托夫斯基对安徒生圣徒般的纯洁刻画,更符合人们的期待,想象之于现实,我们不知不觉倾向了前者。但是,正因为众人对于艺术作品的浪漫特质充满期待,甚至追随模仿,想象世界对真实人生的介入变得难以避免。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等诸多人物,正是这方面的典型体现。
福楼拜以“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冷漠叙事风格著称,其实他的书写充满情感张力,他以这种方式与自己青年时代的白日梦倾向激烈鏖战。他对欲望与想象的交织状态具有切身体验,更能意识到它的强劲存在、巨大威力和潜在危险。当梦幻介入真实生活,潘多拉瓶便被不断打开,甚至成为常态,正如包法利夫人的人生境遇。
《包法利夫人》第二部第十五章的歌剧院情节,是小说中一个重要转折点。剧院虚实交融的场景,让爱玛反思了此前的情感关系,也使她重燃了激情和想象,然后她又与莱昂重逢。同时,福楼拜也用“剧中剧”的结构,再次提醒我们与爱玛之间的模进关系。









福楼拜为什么要写作这样一个绝望到毫无出路的人物?他是在借爱玛表露自己内心的痛苦吗?抑或是试图刻画人不得不面对的两种选择,成为庸俗的奥梅,或是绝望的爱玛?福楼拜并未给我们提供答案,他只是以这部“镜中之灯”,烛照了人的普遍处境。
正如不少读者所感,这是一部没有希望存在的小说。其间“潘多拉瓶”不断开合,“希望”昙花一现,相互错位的主体追求,伴随着欲望和想象的此起彼落。福楼拜的书写呈现出一个虚妄充斥的世界,唯有存在的勇气可以直面。


——谈《包法利夫人》的包法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