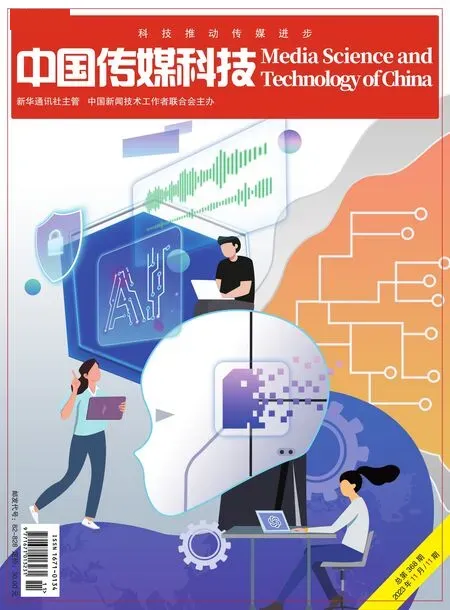从互动到交易:从后现象学到历史人类学审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
袁慕晗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英国 伦敦 SE146NW)
导语
当人类和技术的关系成为讨论的主题时,人们往往会认为:人类是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我们控制技术,并利用技术控制我们周围的环境。这种关于人类与技术关系的假设似乎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且二元对立的,我们人类往往误以为自己与众不同,是当今文明的唯一创造者。在这个以技术快速发展和人类与机器之间前所未有的相互作用为特征的时代,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本文深入探讨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深层动力,剖析了体现、意向性以及人类学历史的细微差别,这些都是人类与技术互动的基础。通过哲学探究、艺术创作和社会人类学分析,笔者将深入探讨定义现代人类与科技关系的多层面因素,重点关注人类的感知力、能动性和我们的社会结构。也将通过自身的艺术实践,从技术和意向性的后现象学论点,以及技术和社会技术的人类学历史这两个角度探讨人类与技术的关系。
1.人类是会思考的机器
对人机关系的好奇似乎出现在笛卡尔 “第一次明确尝试确定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别”。[1]笛卡尔认为,人由身体和心灵组成。身体是有形的机器,总有一天会腐朽,而心灵则是非物质的、不朽的物质,具有理性,因此能够思考。[2]事实上,笛卡尔的观点似乎将人类的理性和智慧置于神坛之上,对非人类(机器和动物)系统不屑一顾,因为他衡量理性存在与否的标准是基于语言的使用和发明创造的能力。[3]机器可以用机械术语来解释,尽管可能与人类(人体)相似,但它们完成的是人类交给它们的任务,并没有自己的能动性或意向性。尽管笛卡尔的二元论方法在今天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但后来的学者们对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更多的假设和理论。
2.传统与可穿戴设备、体现与意向性
1945 年,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出版了《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一书,他在书中摒弃了传统二元论以及“人是一个超脱的客观观察者”的笛卡尔思想,并认为身体不仅仅是世界中的一个客体,更是一个塑造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的具身主体,强调知觉者与被知觉者之间的动态互动。[4]
这位法国现象学家研究了身体、感知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认为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是由我们的体化认知所塑造的。身体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而感知则是这种具身互动的结果。他举了一个有趣的管风琴演奏家的例子,说明感知不是一个孤立的心理过程,而是从身体与环境的动态互动中产生的。当一位经验丰富的管风琴演奏家被要求使用一架他们从未演奏过的管风琴进行演奏时,他们只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适应它,而这是一个相对较短的练习时间。现象学家在寻找这一现象的可能解释时,排除了新的条件反射成为旧条件反射替代物的假设,“ 除非两者形成一个系统,而且变化是全方位的,这就使我们脱离了机械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乐手的反应是以对乐器的全面掌握为中介的”。[5]对于陌生的管风琴,演奏者并不进行分析和规划,而是将自己的身体几乎当作一把量尺,来熟悉相关的尺寸和方向。管风琴演奏者体现了运动意向性的概念,即身体不仅是一个物理的、物质的对象,而且还影响着人的感知和行动。通过强化练习和训练,管风琴演奏家形成了精细调整的身体图式,使他们的手指能够轻松地在键盘上移动。他们演奏的音乐是他们有意识动作和手势的结果。
同 样 , 维尔贝克 (Verbeek) 的 “ 赛 博 格 意 向性 ”(cyborg intentionality)概念提出,技术作为一种体现性中介,影响着人类的意向性和感知。技术成为我们与周围世界之间的中介,成为身体的延伸,增强了人类的能力。2008 年,维尔贝克在期刊《赛伯格意向性:重新思考人类与技术关系的现象学》(Cyborg intentionality:Rethinking the Phenomenology of Human–technology Relations) 中提到:人类与所处现实之间不可避免的纠缠关系是由于“人类经验的意向性结构”。[6]“由于人类经验的意向性结构,对人类的理解永远无法脱离他们所生活的现实。人类总是指向现实。他们不能简单地‘想’,但他们总是在想些‘什么’;他们不能简单地‘看’,但他们总是在看些‘什么’;他们不能简单地‘感觉’,但他们总是在感觉些‘什么’。作为体验者,人类不能不面向构成其世界的‘实体’”。[7]
维尔贝克接着介绍了唐·伊德(Don Ihde)对人类与周围环境关系的现象学观察,重点介绍了人类与技术层面的互动。人与技术之间存在四种关系,即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诠释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他者关系(alterity relation)和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智能手机是人类与技术之间具身关系的一个例子,因为它成为了我们感官知觉的延伸。智能手机的物理形状和大小被设计为 “亲密的机器”,根据特克尔的说法,它通常“既被体验为自我的一部分,也被体验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 ”。[8]当我们用智能手机的摄像头拍照或录音时,它将我们的感知转化为有形的人工制品,从而保存了我们的视听体验。在诠释关系中,“技术提供了现实的表征,而这些表征需要诠释才能构成感知”。[9]技术产品作为中介,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体验。这种关系模式凸显了解释和意义生成在我们与技术互动中的重要性。在他者关系中,人类与技术互动并将此举动视为人类意向的最终目标。第四种背景关系,是指技术并不被人类直接体验,而是 “为我们的感知创造了一个环境”。[10]背景关系的例子可以在我们对熟悉物体或地点的感知中找到。当一个人在熟悉的房间里看到桌子上的咖啡杯时,有一种隐含的、预先反映的背景关系在起作用,影响着这个人的体验。[11]在这种情况下,人对咖啡杯的感知是由放置咖啡杯的桌子和咖啡杯周围的房间所提供的空间背景促成的。这些提供了我们理解和认识物体、其位置及其在我们生活经验中的意义的背景。[12]
为了深入探讨人类与技术的关系,维尔贝克提出了 “赛博格意向性”(cyborg intentionality)这一概念,描述了部分由技术构成的人类意向性。[13]他认为,在人类与技术建立体现关系之前,存在着一种“仿生生命”,它是有机物与技术的混合与融合。[14]当一个人接受手术,用微型芯片取代受损的视力,或用假肢取代截肢的腿时,具身关系就不能再准确地描述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了。人类与假肢和微型芯片等技术增强装置之间的关系被称为 “赛博格意向性”。赛博格意向性表明,“这种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联不是人类与非人类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在物理上改变人类”[15]维尔贝克将伊德总结的四种人类与技术的关系归结为 “介导意向性”(mediated intentionality),并在人类与技术关系的基础上扩展了两种赛博格意向性:混合意向性(hybrid intentionality)和复合意向性(composite intentionality)。混合意向性发生在 “人类与技术融合而非仅仅被具身化”的情况下[16],而复合意向性发生在 “技术制品本身的意向性与使用这些制品的人类的意向性合作发挥核心作用 ”的情况下。[17]在艺术实践中,笔者试图研究音乐和声音表演中技术与人类的不同关系。笔者在受到古典音乐训练后,不仅用大脑演奏,还用动作演奏。大脑并不是单向地发送信号,指示身体做什么。相反,身体动作也在影响着笔者的认知。笔者发现,影响演奏者认知处理的身体动作是他们与乐器(技术)互动的结果,而不是他们对乐器的操作,因为乐器的存在也会影响演奏者。调整演奏者与其乐器之间的关系的灵感就来源于这一观察。笔者想创造一种可穿戴的乐器,它能消除人类演奏者的重要性,将乐器技术与演奏者融为一体。为了理解传统乐器和可穿戴乐器与演奏者之间关系的不同,需要研究这两种技术的意向性,以及演奏者与这两种技术分别结合时的意向性。就传统乐器而言,演奏者与技术之间存在着他者关系,因为演奏者的意图是与乐器互动。另一方面,穿戴式乐器一旦穿戴到表演者身上,它就改变了表演者的动作和行为方式。可以说,可穿戴乐器是具身关系的一个例子,但我想创造的这种身体乐器的概念更接近维尔贝克的混合意向性概念。乐器一旦穿戴上身,就不应只是“以技术为媒介的人类意向性形式”[18],而应是与表演者融为一体的东西。通过这种融合,一种新的身份被创造出来,表演者和他们身体上的乐器共同成为一种超人类的存在。换句话说,乐器的概念消失了,成为表演者的一部分。[19]
3.技术和社会技术系统的人类学历史
在制作和改装可穿戴仪器的过程中,笔者将人类与技术关系的现象学视角应用于音乐和声音表演领域,但仔细观察后发现,这种视角主要局限于个人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因而没有完全涵盖更广泛的背景框架。这促使笔者思考人类与技术之间互动的起源和基础。特别是,笔者试图解决几个问题: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最早的技术人工制品的诞生?这些人工制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及其所处的社会? 此外,只讨论人工制品和技术本身,而忽略它们所诞生的以及后来由它们产生的系统是否足够?
布莱恩·普法芬伯格(Bryan Pfaffenberger)提供了一种社会人类学观点,进一步强调了在研究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时,系统和物质参与的重要性。为了更全面地研究技术与人类之间的联系,有必要重新审视技术的定义。罗伯特·F·G·斯皮尔(Robert F.G.Spier)将技术定义为 “人类试图改变或控制其自然环境的手段”。[20]这一定义只有在人类 “固有的目的是统治或控制自然 ”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而普法芬伯格认为“在塑造人类适应性的过程中,技术和人工制品对于社会劳动协调来说是次要的”这一说法这是不对的。[21]因此,仅仅依靠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的视角来全面理解人类的适应性问题似乎是片面和不全面的。普法芬伯格指出,“技术”一词很快就会让人联想到“仅仅是技术性的”活动,而剥离了其社会背景,他认为,研究技术的社会人类学更有内涵的方法应该包括3 个基本主题:技术、社会技术系统(sociotechnical system)和物质文化。技术是 “在物质人工制品的制造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资源、工具、操作顺序和技能、语言和非语言知识以及特定的工作协调模式的系统”。[22]另一方面,社会技术系统”指的是源于技术和物质文化与社会劳动协调之间联系的独特技术活动”。[23]
普法芬伯格认为,社会技术系统的概念源于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关于现代电力系统兴起的著作。休斯认为,新技术的发展不应该是孤立地追求技术和物质工艺品的改进和发明, 相反,他们还应该“对技术的社会、经济、法律、科学和政治背景进行工程设计”。[24]休斯在对爱迪生成功创办电灯工业的研究和分析基础上,归纳出发展富有成效的社会技术体系的模式,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他在模型的第一阶段强调了 “发明家—企业家 “相对于普通发明家的重要作用。[25]发明家—企业家 “居于一个从发明构思到开发再到发明的系统可以使用的过程之中。”[26]
约翰·劳(John Law)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以葡萄牙混装帆船的发明为例,这是 14 世纪和 15 世纪早期出现的一种前工业技术,强调了在社会技术背景下研究技术的必要性。[27]正如劳[28]所说,这项重大成就不仅仅是包括混装帆船的制造和其载货能力的提高和在风暴中的稳定性。成就葡萄牙航海业同样重要的其他元素还有磁罗盘,它能确保在多云条件下保持航向一致;简化的星盘使文化水平较低的水手也能确定纬度;有目的地探索产生了用于位置评估的数据表;对大西洋信风的掌握为不同季节的航行提供了便利。
在研究技术的人类学历史和审视过去与现在的技术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种的模式。很明显,我们不断发明和改造技术的倾向与现行标准的不断变化交织在一起,促使社会、政治和文化建构发生转变。因此,这种互惠关系引发了人类进一步完善和改变现有技术的干预,从而再次受到最新发明的影响。这种辩证关系意味着无限的反馈循环,很难追溯到这种关系的最初形成。
在当今互联互通的数字环境中,社交媒体与审美标准之间的关系是科技与人类相互影响的一个引人入胜的例子。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加和自下而上的强化并存的复杂动态对个人的自我认知、社会规范和心理健康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造成这些影响的显然不仅仅是技术本身,因为每个个体使用社交媒体的实践也导致了这一技术的发展。当人们打开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滚动浏览时,他们会看到无数精心制作的图片,这些图片展示了完美无瑕的皮肤、苗条的身材和轮廓分明的五官。这些视觉呈现往往伴随着光彩照人的代言和时髦的标签,体现了当前的美丽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对个人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一些精心挑选的图片能够塑造和强化人们普遍的审美理想。然而,在技术助长人们追求单调的审美标准的同时,使用社交媒体的人们也通过参与这些平台上的内容来强化这些标准并改变这种技术。由于人们渴望在网上被认为是美丽的, 滤镜和编辑工具应运而生,并且成倍增加。这些用户友好型滤镜和编辑工具的出现,进一步激发了人们遵从这些标准的欲望。只需点击几下,瑕疵就能被刷掉,颧骨就能被凸显,肤色就能被改变,这样人们就能变成他们心目中的 “完美 ”形象。社交媒体技术与追求美丽理想之间的这种共生关系,说明了数字平台与狭隘的审美标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不断互动。正如上述例子所描述的那样,技术的发展和演变、人类、他们对技术的实践变化以及他们对自身的认知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玛蒂娜·海斯勒(Martina Hessler)在她的期刊文章《对技术历史人类学的申辩》(A Plea for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Technology )中认为,“我们必须在不陷入本质主义、二元论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情况下,但又不要求以科学技术研究的分散性和对称性为前提,寻求对人类变革的理解”。[29]如果想了解科技史,不研究科技与人类的关系,就不可能全面掌握科技的发展和演变。换句话说,在研究技术时,讨论 “在技术文化中人类意味着什么 ”也同样重要 。[30]她强调的一个特别有趣的观点是,在探索技术的人类学历史时,“技术化的实践、常规、观念总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它们随着技术本身的变化而变化和发展。[31]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思考”的定义,它一直受到计算机和 “机器智能”领域的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定义。[32]
海斯勒以当今“技术化足球”[33]中采用的球门线技术为例,以人类裁判为重点探讨了这种技术如何影响了人类在比赛中的角色,(海斯勒在这个例子中有意指男性裁判)。根据海斯勒的说法,这一情景围绕着人机关系的动态变化展开,因为它涉及到裁判的 “失权或权威;混杂或替代——取决于从谁的角度来看”。[34]自 2000 年以来,关于是否应在足球场上使用技术作为判定进球的辅助工具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这一直是一个争议性话题。直到2012 年,国际足联才最终采用了这项技术,并在国际足球比赛(2012年国际足联世俱杯、2013 年联合会杯和 2014 年世界杯) 中实施。[35]在过去的十年中,门线技术不断发展,如今鹰眼技术已在比赛中用于辅助裁判判罚。一些人认为门线技术提高了人类的能力。支持门线技术的一方认为,鹰眼技术可以帮助人类看得更清楚,因此可以提高裁判员的准确性,克服人类的局限性,增强他们的能力。裁判们自己也表示,这项新技术对于帮助他们重新获得权力地位非常重要。[36]在采用这项技术之前,观众可以观看回放和慢动作,而裁判却不拥有技术的辅佐,这使观众们获得了比裁判更多的比赛信息。采用门线技术后,失误和幻影进球变得不可能,反过来,裁判也不会受到认为裁判判罚不公的愤怒球迷的攻击。现在,裁判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并重新获得权威地位,因为技术提高了他们的能力。技术被视为扩大裁判感官的工具,可以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另一些人则对技术削弱足球运动中人性化的因素表示担忧。他们认为,技术贬低了裁判的价值,并威胁到了比赛的情感和刺激性,因为足球堪比“人类生活——而不是机器——它富有情感、刺激、不公平”。[37]这项技术的反对者担心机器会取代人类。
然而,仔细观察进球过程,在引入门线技术后,决定进球是否成立的做法创造了一种新的人机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人的主宰或技术的接管那么简单。与以往不同的是,以前是裁判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进球情况,然后宣布自己的判罚,而现在则是摄像机、计算机和裁判的行动形成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导致进球的判罚。现在正朝着 “人机 ”混合的方向转变。[38]换句话说,鹰眼技术不仅是人类训练机器系统的一个例子,而且当裁判在球场上时,他也变成了被机器训练的人类,因为他会根据摄像机和传感器改变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进程。海斯勒得出的结论是,这是裁判和门线技术的共同进化。然而,如果从人类的自我认知角度,特别是裁判的自我认知角度来观察,论点就会发生变化。它强调了裁判在做出最终决定中的作用,并声称技术只是充当了为裁判工作的助手。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是一种假象,它试图帮助人类重新获得控制权,但却很容易被反驳,因为进球的实际决定过程是由机器完成的,裁判只是宣布机器提供给他的最终裁决。因此,技术的引入自相矛盾地既剥夺了裁判的权力,又赋予了他们权力。有趣的是,由于观众认为机器计算出的决定比传统裁判富有人性特质(无能、欺诈和腐败)的决定更客观,因此裁判们重新获得了公共权威。总之,社交媒体和门线技术这两个案例都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技术化的实践、常规和观念不断被其所接受的技术所塑造,从而导致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适应和进步。
从人类学历史的角度对人类及其自我认知以及技术和技术化实践的研究,启发了笔者的概念艺术作品“训练学习二重奏”(duet of a training session)。在这个作品中,笔者的目的是实验笔者自己与笔者用代码语言构建的技术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该技术是笔者用Max MSP 构建的生成音乐算法,Max MSP 是一种可视化编程语言和开发环境,用于音乐创作、声音合成、交互式多媒体和其他视听项目。笔者的算法生成音乐作品,而笔者则用笔者的声音与之配合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作用是什么?我们都是表演者,还是我的算法是我的助手,就像裁判们认为鹰眼技术是他们的助手一样?在我们舞台上的动态关系中,笔者的算法是否有自己的意图?此外,当在舞台上引入算法时,我作为表演者的舞台实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笔者选择从后现象学和 “物质参与理论”(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人与技术的关系。
4.后现象学与物质接触理论:从互动到交易
与笔者使用可穿戴设备进行的表演类似,“训练学习二重奏”也是我与技术之间的合作表演。在对这两个项目进行反思时,笔者注意到,把笔者使用这两种技术的表演描述为一系列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并不十分准确。相反,在这些情况下,技术中介似乎是交易性的。伊德和马拉佛瑞斯(Malafouris)在他们的研究文章《重新审视Homo faber:后现象学与物质参与理论 》(Homo faber Revisited: Postphenomenology and Material Engagement Theory)一文中写道,为了在当代新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框架内拓宽他们的论述,他们主张从单纯的 "互动 “(interaction)方法转向更全面的 “交易”(transaction)视角来看待技术中介的意义。[39]伊德和马拉佛瑞斯反对一种普遍存在的错误观点,即把人类及其技术中介看作是参与互动对话的本体分离的实体。传统的达尔文观点认为,人类相对于其自然和人造环境的进化是单向的,而“最近的进化——生物共同进化框架和生态位构建理论则承认其中的因果互惠和相互作用”。[40]然而,这些观点仍然坚持人类进化与技术进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这意味着两个或更多预先形成的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使一个实体适应另一个实体,而不是交易或相互关系。这种假定给人的印象是,人类的进化和技术的进化是两个独立的过程,在某些时候可能会相互作用或相互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各自独立的系统。此外,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即否定新达尔文主义关于生物体及其环境分别先于其关系构成的观点。[41]后现象学和物质参与理论都反对将人类的“自然”物种繁衍与“文化”技术变革区分开来,认为人工制品作为关系的积极媒介,塑造着人类的体验,并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改变着人类的体验和经验。因此,技术发展并不总是线性或可预测的。根据伊德和马拉佛瑞斯的观点,“扩展和增强会带来依赖和替代”。[42]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进化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持续的和永远不完整的。技术中介的变革潜力成为后现象学与物质参与理论的交汇点。将创造性的物质参与放在首位,消除了人类进化与技术和文化进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挑战了将达尔文原理应用于技术发展的还原论。伊德和马拉佛瑞斯认为,与其仅仅依赖自然选择,不如将重点转移到研究 “人类意识的创造能力、物质参与的多样性和不断变化的机会,以及这些过程嵌入特定社会和历史环境的方式 ”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43]通过“后现象学”和 “物质参与理论”的视角,笔者开始思考算法设计和编程中蕴含的意图本质。虽然算法不具备人类的意识,但它的代码和功能却塑造了一种有目的的意向性。人类与算法意图之间这种独特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合作表演的基础。算法的引入将我带入了一个人类表达与复杂技术共舞的境界。这种转变与伊德和马拉福瑞斯的论断不谋而合,即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依赖性和替代性,为人类进化的动态和持续叙事做出了贡献。
结论
总之,对传统乐器和可穿戴乐器、体现、意向性以及技术人类学历史的探索揭示了人类与技术之间深刻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无法简单地归类。梅洛·庞蒂对 “体现 ”的见解强调了身体与感知的融合;维尔贝克的“赛博格意向性 ”概念扩展了这种互动,揭示了技术如何成为身体的延伸并影响人类的意向性和感知;普法芬伯格强调了形成人类与技术动态关系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从前工业技术的兴起到当代的共生关系,技术的演变与人类的实践、认知和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结合后现象学和物质参与理论的观点,人类与技术的交易关系挑战了仅仅是两条独立进化路线之间互动的传统观念。对人类与技术关系的这些不同方面的探索,凸显了人类与其技术创造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从体现到社会技术系统,从传统工具到生成算法,人类与技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揭示了一种复杂而相互依存的共同进化,这种进化塑造了人类的经验和技术进步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