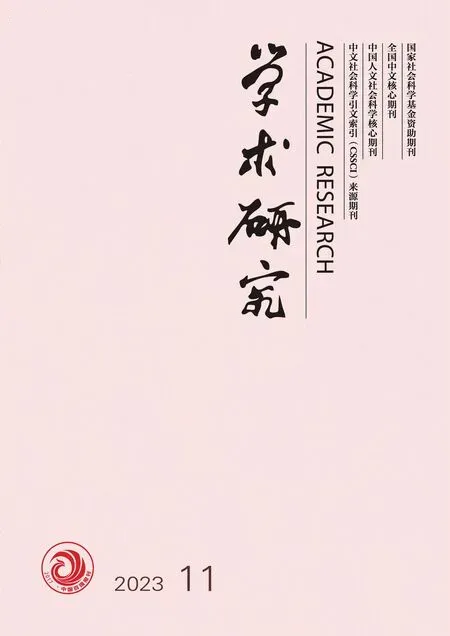景图在文学传播中的生成机制与意义
——以刘禹锡《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及其“涵碧”意象为例*
戴一菲
刘禹锡《答东阳于令涵碧图诗》(以下简称《涵碧图诗》)较少有人关注,其诗是对于兴宗所赠《涵碧图》的应答之作,虽源于《涵碧图》而并非题画诗,画源于“涵碧亭”景观而先于诗歌存在。在景图诗三者彼此相承的线性关系中,能看到景观、绘画在文学意象传播过程中的特殊意义,而景观的加入也突破了以往诗画关系研究中的对象限定,呈现文化生态链条中更多艺术形式的融合样态,有助于还原文学圈层的真实景象。
《涵碧图诗》云:“东阳本是佳山水,何况曾经沈隐侯。化得邦人解吟咏,如今县令亦风流。新开潭洞疑仙境,远写丹青到雍州。落在寻常画师手,犹能三伏凛生秋。”①[唐]刘禹锡撰,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877 页。从诗歌中可见刘禹锡对东阳山水之仙境多有赞赏,虽为“寻常画师”所作,却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涵碧”包孕的凛冽秋意。这种以景述情的表达在传统山水题诗中并不少见,但刘诗前还有一序,交待了于兴宗其人及其建涵碧亭之旨,特别是提示了“涵碧”原初的艺术形式,为我们考察“涵碧”意义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材料。刘禹锡并非眼见实景,却能凭图构想;于兴宗只是一位县官,却能凭借“涵碧”留名;刘禹锡、于兴宗之后,“涵碧”被后世广泛地用于景观命名。“涵碧”作为文学意象,在其生成与传播过程中,于景观和诗歌二者间勾连,其对后世影响到底更多缘于文学作品的加持,还是景观本身样式的特殊性?其中,复现景观的涵碧图又起着什么作用?这些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第一次传播:从景到画的图像生成——“涵碧”审美的视觉呈现
过去,人们关注文学意象,多将其放入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相关文字文本中,考察其始源,训诂其流变,探究其影响。很多文学意象往往通过诗歌等文学作品,实现意义增殖,成为经典意象,历久而不衰。其中不少意象突破了文学的界限,在其他艺术门类中被赋予美学价值和文化意义。这一类意象无论在历史生成还是自身意蕴上,都殊于他类,“涵碧”即是其中之一。“涵碧”在唐以前较少出现在诗词作品中,《说文》曰:“涵,水泽多也。”①[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366 页。“碧,石之青美者。”②[汉]许慎:《说文解字》,第10 页。可见,“涵碧”一词形象而具体,具有较强的审美特性。除此之外,它还具备区别于其他文学意象的特点,并为传播带来特殊性。
首先,“涵碧”审美意象的视觉因子为由景到画提供了可能,更便于传播。《涵碧图诗》序中说东阳县令于兴宗“因构亭其端,题曰涵碧”,所谓涵碧,即水色碧绿深沉的意思。同样形容水之倒映,古人还用“涵虚”“涵空”等,意谓水映天空所呈现的空茫之感,如孟浩然《望洞庭湖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③[唐]孟浩然撰,李景白校注:《孟浩然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233 页。温庭筠《春江花月夜》“千里涵空照水魂,万枝破鼻团香雪”。④[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268 页。古人还有“涵碧落”,碧落指天空,“涵碧落”常形容天映在水中。唐陆龟蒙“古岸涵碧落”,⑤[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七九三,第8930 页。元丁存“百顷澄波涵碧落,一行归雁渡青冥”,⑥杨镰主编:《全元诗》第8 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436 页。明冯惟敏“浸青峰兮影倒,涵碧落兮光浮”⑦[明]冯惟敏:《冯惟敏全集》,济南:齐鲁书社,2007 年,第131 页。等即是。由此可见,“涵碧”与“涵虚”“涵空”“涵碧落”相比,着重强调了包涵之“碧”。这个“碧”字,表现了一种由色彩包裹有如碧玉般的质感,从而使“涵碧”独具魅力。刘禹锡《涵碧图诗》序中将“涵碧”描写为“碧流贯于庭中,如青龙蜿蜒,冰澈射人”,虽是简单几笔,但“碧流”“青龙”二字明确了“涵碧”的核心审美内容。
除去“涵”字,上述“涵碧”“涵虚”“涵空”“涵碧落”的区别,就在于所涵之物的特点。“虚”“空”表示的是虚无空渺之感,是只能意会而无法触摸的;天空虽为实物,但与“碧”相比,缺少具体的形象表征。换言之,只有“碧”因其色彩上的绿,可以用具体的画面表达,给人以视觉上的感知。这种视觉因子为画家描摹“涵碧”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对景的这种图像转换才能使刘禹锡尽管未见景却如在目前。柳宗元《永州八记》创作心境与于兴宗相类,本无其景,开拓成景,其中多以诗心画意写成,可谓绝佳风景画,但未见有“图之”之说,多少有些遗憾。于兴宗“图之”虽粗,出于“寻常画师手”,但从传播的角度看,以图存景的绘画作品便于携带,为“涵碧”的传播带来了便捷,使人不用亲临,便能欣赏绝佳风景。
其次,景与图的视觉审美特性使“涵碧”在审美过程中具有确定性,使传播内容不产生偏差。古人以山水为审美对象,将其形诸文字是诗歌史上一重要内容,从而完成了从“景”到“诗”的审美过程。其中一部分山水诗为画家所摹写,作为诗意图留存于世,又形成了由“诗”到“图”的审美转换。但以诗为中介,很多时候囿于古人意在言外的审美追求,无法直接呈现形象,读者和画家只能借助文字进行想象,“图”与“景”基本无法做到复刻。即便是有明确指向的一些图文转换,都很难达到图景一致,比如绘画史上的传统母题“辋川图”,王维本人作《辋川别业诗》二十首,又自作《辋川图》。从宋代到清代,无数画家对此进行复现,包括文征明和王原祁这样的大家。但展开他们的画卷,很难看出他们绘画对象的一致性。如文征明《辋川别业图》是一种江南水乡般的辋川意象,王原祁自己说“未见粉本不敢妄拟,……以我意自成,不落画工形似”。⑧[清]王原祁:《王原祁集》,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 年,第270 页。可见,古人作画再现诗意,更多的是融入自我体悟,追求神似。那自然地,“景”与“图”之间常常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同为融合景图诗三者的刘禹锡《涵碧图诗》中涉及的图、景却和上述图、景有明显的区别。这种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绘画主体的追求,二是创作序列的先后。前者表现在涵碧图创作主体身份上,据刘禹锡诗云:“落在寻常画师手”,那就意味着“涵碧”风景的描摹者是寻常画师,相较于后代文人画对神似的极致要求,唐代画师还处在对形似的审美追求中。彼时流行的山水画在青绿两色上的高超技法,与“涵碧”的色彩特征相呼应。虽图已失佚,但不难想象画师对“碧”的客观状写。而刘禹锡发出“犹能三伏凛生秋”的感叹,仿佛该画师有远超形似的技艺,拥有让人身临其境的能力,当然,此句亦可能缘于刘禹锡对于兴宗之褒奖。同时,《涵碧图诗》是对东阳县令于兴宗所献“图”之描绘,该“图”是对“景”的直接临摹,从而构成了从“景”到“图”再到“诗”的审美序列,区别于惯常所见 “景—诗—图”的艺术创作先后环节。尽管《涵碧图》以“图”的形式对“景”进行了二次创作,但因图直承于景,略去了诗这一中间环节,且与景同为视觉呈现,具备直观性特征,使得“景”“图”之间的转换能基本保持一致,从而使得“涵碧”在传播内容上具有限定性,不易产生偏差。
由此,“涵碧”意象以其“碧”之特殊性,即色彩的呈现而区别于其他相似意象,使得审美对象在景与图之间实现了较为准确的复制,而由于景图二者的直观性特征,亦使得“涵碧”意象的呈现具有特指性,即必有含绿之水。这种图像生成和视觉呈现对“涵碧”意象在后世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为其文化意义的输出限定了范围。
二、第二次传播:从图到诗的文化意义——“涵碧”意象生成的双重主体
通常人们会习惯性地认为,对于文学史或艺术史上的经典性意象,审美创作主体对其意涵的建构是第一位的,在“涵碧”内蕴的生成过程中,刘禹锡的书写确实不可忽视,但同时,通过刘禹锡的阐释,作为原初以景观形式出现的涵碧亭,其建造者于兴宗本人的影响在对后世“涵碧”意义的传播中有所体现。
首先,由普通景观到名胜古迹来源于审美创作主体的传播能力。刘禹锡在《涵碧图诗》序中交待了写作的缘由:“惜其居地不得有闻于时,故图之来乞词,既无负尤物。”涵碧亭所在之地并不出名,所以于兴宗令人图景,并请刘禹锡赋诗。刘禹锡也不吝溢美之词,不仅在序中说“不负尤物”,更写自己“予亦久翳萝茑者,睹之慨然”,表达目睹涵碧图时的感慨,其在诗中说:“新开潭洞疑仙境,远写丹青到雍州。”东汉时光武帝定都洛阳,设立过雍州。于兴宗为东阳令在宝历二年(826),时刘禹锡由和州刺史奉调回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刘禹锡作此诗时正是从和州调至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的时期,无论是身份地位,还是心境,都和“居地不得有闻于时”的于兴宗截然不同。以刘禹锡的身份地位,虽可帮助于兴宗扬名,但后人在提到“涵碧”时似乎都忘记了于兴宗,只言刘禹锡诗。如宋王铚《游东阳涵碧亭刘梦得所赋诗也明日过中兴寺游览终日记所见》:“我游东阳城,隐侯昔所制。山川无古今,城邑有存废。梦寐涵碧亭,草间得遗记。飞流落天明,喷洒寒玉碎。停车风雪中,岂特生秋意。李杜到韩刘,峥嵘相品次。景因真赏见,遗句细吟咏。”①[宋]王铚:《雪溪诗集》卷四,清冰蕸阁钞本,第9-10 页。宋强至《寄题殊公禅老黄云阁》云:“还如梦得闻涵碧,谁写丹青复寄予。”②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五九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6988 页。元陈樵《涵碧亭(刘禹锡题涵碧亭:犹能三伏凛生秋)》:“涵碧池头夏气清,我从三昧起经行。移樽近树传杯绿,向日看山入户青。人似亭前花不语,诗如江上草无名。山中水调知何限,不入熙宁水乐声。”③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8 册,第358 页。可见,名人效应在涵碧亭从一处普通景观转变为名胜古迹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景变为图固然在传播中更加便捷,但名声更大的刘禹锡以诗写图的举动更为“涵碧”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助力,这一点从其与方干的对比中更见端倪。同时代人对“涵碧”的吟咏极少,方干有《涵碧亭(洋州于中丞宰东阳日置)》一诗,由题目可知正是于兴宗所建之涵碧亭,方干此诗注云“洋州于中丞”,于兴宗为洋州刺史应在大中后期(847—860),晚于刘诗。诗云:“高低竹杂松,积翠复留风。路极阴溪里,寒生暑气中。闲云低覆草,片水静涵空。方见洋源牧,心侔造化功。”④[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四八,第7444-7445 页。与刘禹锡面对的是画作不同,方干之诗虽无序,但大致可以看出是游观的创作。从写作姿态上看,方干与刘禹锡的差别也很大。刘禹锡一言“远写丹青到雝州”,再言“落在寻常画师手”,高居其上,俯视对象;而方干“方见洋源牧,心侔造化功”,仰瞻对象。方干一生活动在社会下层,未有一官半职,对时任洋州刺史的于兴宗钦慕实属自然。尽管两首诗因涵碧亭而发生了关联,但在后世文献中言及涵碧亭者,很少提及方干诗。在“涵碧”意象的传播过程中,审美创作主体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传播的效果,另一方面,诗人作为“涵碧”意象的阐发者,亦是“涵碧”意象生成的主体之一。
其次,涵碧内在意蕴的固化与其建造者于兴宗有密切关系。刘禹锡《涵碧图诗》尽管面对的是画中之景,但和一般的山水诗一样,对景物的描述很细致,而其于一般写景诗不同之处就在于序开头叙于兴宗事迹,并在诗歌中对于兴宗做了“如今县令亦风流”的评价。
一方面,于兴宗其人,正史载录不多,而刘禹锡这首诗序成为了解于兴宗不可多得的材料。另一方面,于兴宗建造涵碧亭这一事件,通过刘禹锡诗使“涵碧”得到文化意义上的确认,风流县令与地方景观浑然一体,成为政治清明的一种表征,为文人士大夫所向往和称许。序开头云:“东阳令于兴宗,丞相燕国公之犹子。生绮襦纨袴间,所见皆贵盛,而挈然有心如山东书生。前年白有司,愿为亲民官以自效,遂补东阳。及莅官,以简易为治,故多暇日。一旦于县五里偶得奇境,埋没于翳荟中。于生自以有特操而生于公侯家,由覆荫入仕,常忽忽叹息。因移是心,开抉泉石,芟去萝茑,斧凡材,畚息壤,而清溪翠岩森立坌来。因构亭其端,题曰涵碧。”序叙作诗缘起,述诗之本事,刘禹锡诗序不吝笔墨,详细描述于兴宗为东阳令之缘由及其建涵碧亭的过程,字里行间勾勒出一个生于公侯之家却为政简易的清明县令形象。同时,于兴宗在刘禹锡的笔下也是一个善于自我调节之人,“惜其居地不得有闻于时”,含有不为世用之意,但他能于荒野中开辟胜景,并构筑涵碧亭,懂得寄情山水排遣内心苦闷。经刘禹锡建构,于兴宗的为官遭际通过涵碧亭的建造而具象化,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范例,即为官一方,开拓风景为养其性之助,有利于政治清明。
宋《宝祐重修琴川志》载:“于东阳啸咏于涵碧亭,李虞城游憩于蠡丘馆,世率谓其游亭馆而废事,然观柳子厚论作邑者,以为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常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虚,则夫啸咏游憩之地,所以养其清明,而为政之助也。若夫杨炯为盈川令,多治亭台,书榜美名,则非为政之所急矣。”①[宋]孙应时编纂,[宋]鲍廉增补:《宝祐重修琴川志》卷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9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289-290 页。这段文字以于兴宗建涵碧亭为例,纠正了人们对文人建亭馆废于政事的认知偏差。后《咸淳临安志》记载了关于“涵碧”的另一则故事:“涵碧桥,孤山路中。桥非名不足以润色,以雅易郑署曰涵碧,盖出于揽景而生乎?自然也。且将图以归。好事者或思见之,当出以示,或曰启塞之说,实由古之训山水之乐,未达予之志,曰:今朝廷有道,区宇无事,能敏其政,又适其性,则斯人也。庶几不为妄矣。别作五言律诗一章,章四韵,刻于他石,率大雅者和之,以永涵碧之说。”②[宋]潜说友纂:《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490 册,第254 页。涵碧桥并非涵碧亭,桥在西湖孤山路上,与亭同取“涵碧”之名,是为“润色”之举,原因在于古人“山水之乐”与“敏其政”的正向关联,并认为题咏“涵碧”之诗是雅正之言。可见,亭桥建造者对亭、桥之名的传播作用亦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建造主体的为政清明通过亭桥之助得以确立和显现,二者之间的联系以“涵碧”意象得以勾连,并为后人所继承。因为“涵碧”之“碧”的限定性,这种对“涵碧”意蕴的承接并非源于“涵碧”自身的审美意义的阐发,而是对建造主体——风流县令与风景客体——涵碧亭间的联系做了引申,从而引出士人为政之“山水之助”,赋予“涵碧”文化意义。
由此,刘禹锡与于兴宗作为“涵碧”的双重创造主体,对“涵碧”的流传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当然,如果没有刘禹锡,建造者于兴宗与亭之间无法发生联系,也不能因涵碧亭留名,两个主体在传播效用上有所区别。
三、广泛传播:从一处景观到广泛采用——“涵碧”图像背后的文人雅趣
现今留存的不少古迹,皆因文人题咏闻名。从唐人漫游所到之处的肆意题写,到宋人赏玩山水的墨迹留痕,及至元明清,山水皆因文人赋诗而雅趣横生。其间,诗歌成为山水声名的传播者,但反过来,景观亦是诗歌传播的媒介,甚至成为文人情趣的物质遗存,帮助固着其文化意义,增强其传播效能。以“涵碧”为例,唐人诗作中较少有对“涵碧”及其景观的描写,唐之后,特别是有宋一代,不少的诗词作品中都出现对“涵碧”的歌咏,这些作品大概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唐人所建“涵碧亭”及其周边景观的描摹及追忆,二是对其他以“涵碧”命名景观的描绘。由此可见,“涵碧”意象在传播过程中,不仅以文本的形式再现,更存在于景观这种可视化的图像中,且呈现以下特点:
首先,广泛传播的物质载体以景观为主。涵碧亭为唐于兴宗所建,经由刘禹锡的题咏,得以扬名。东阳涵碧亭后世犹存,“来者未知秀老,观荆公所赠六诗,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择刻六诗于扬州禅智寺真觉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又欲刻之东阳涵碧亭。嘉其伯仲清尚,故书。”①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一一二,济南:齐鲁书社,2015 年,第3144 页。而到了南宋绍兴年间,涵碧亭不存,杜绾《云林石谱》载:“涵碧石,婺州东阳县之南五里有涵碧池,唐令于兴宗得其胜概,……刘禹锡有诗在集中。”②[宋]杜绾:《云林石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年,第13-14 页。涵碧原址已无涵碧亭,但有涵碧石,且宋人将此与于兴宗和刘禹锡关联。东阳人曹冠有《兰陵王·涵碧》《蓦山溪》(乾道戊子秋日游涵碧)《满江红》(淳熙丁酉六月十三日浙宪芮国瑞巡历东阳招饮涵碧)《喜迁莺》(上巳游涵碧)《夏初临(并序)》(淳熙戊戌四月既望,游涵碧)等诗词作品,其中提到“刘郎何在玩石刻”③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1536-1537 页。“游涵碧,登生秋、冲霄二亭”,④唐圭璋编:《全宋词》,第1532 页。可见,南宋时唐于兴宗所构筑涵碧亭已不存在,景区统名“涵碧”,而另有生秋亭、冲霄亭,“涵碧”命名亦来自于兴宗、刘禹锡二人。王铚《游东阳涵碧亭刘梦得所赋诗也明日过中兴寺游览终日记所见》:“梦寐涵碧亭,草间得遗记。”⑤[宋]王铚:《雪溪诗集》卷四,清冰蕸阁钞本,第9-10 页。金华人王象之《舆地碑记目》中载《婺州碑记》有“涵碧亭碑”,⑥[宋]王象之:《舆地纪胜》附录:舆地碑纪目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19 页。东阳涵碧亭虽至南宋已为古迹,但后人为其立碑,可见其影响。除此之外,宋代亦出现了不少以“涵碧”命名的景观。如《(景定)严州续志》:“故地之侧为亭曰:南昌胜境,亭之南,植木为表,榜曰:屏山第一峰。又南放舟为亭曰:涵碧。庶几续旧观云。”⑦《(景定)严州续志》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7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585 页。《宝庆四明志》所载:“普济寺县东北一里……寺之前德润湖之心有亭,旧名清音。天圣九年,余姚县令孙籍记。大观二年,令唐昌期改名涵碧。”⑧[宋]胡榘修、[宋]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7 册,第284 页。《咸淳临安志》载杭州孤山路中有涵碧桥。⑨[宋]潜说友纂:《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0 册,第254 页。《舆地纪胜》载连州有涵碧轩。⑩[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九十二,第2270 页。除方志外,诗歌中也多出现涵碧亭、涵碧轩和涵碧寺,如宋冯山《阆中蒲氏园亭十咏涵碧亭》,⑪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七四一,第8646 页。文同《蒲氏别墅十咏·涵碧亭》,⑫傅璇琮等:《全宋诗》卷四三三,第5315 页。刘安上《甘露亭二首其一》中所云:“涵碧轩前甘露亭”,⑬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一三一六,第14950 页。喻良能《再游东阳》有“寻幽已访涵碧寺”⑭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二三五二,第27012 页。句。无论是公共景观,还是私人营造,“涵碧”在宋代以实地景观形式得以存留,成为传播链条上重要的一环。
宋之后,以“涵碧”为名的景观层出不穷,如元成廷圭《宁境寺涵碧轩》,⑮[清]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683 页。陈颢《涵碧池》,⑯[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三四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9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652 页。明陈爟《文用更新涵碧亭病起游览不遇》,⑰[明]曹学佺编:《石仓历代诗选》卷三六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91 册,第983 页。祝允明《沧洲姚家涵碧阁》。⑱[明]祝允明:《怀星堂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年,第179 页。多地亦有涵碧亭,如无锡涵碧亭,“池右有‘涵碧’‘湿云’及‘漱香’诸亭,皆可坐以观泉”。①王继宗校注:《〈永乐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常州府五,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272 页。扬州有涵碧楼,“水次设小马头。逶迤入涵碧楼。楼后宣石房。旁建层屋。赐名致佳楼”,②[清]李斗撰,汪北平、涂雨公点校:《扬州画舫录》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217 页。“堂后开竹径,水次设小马头,逶迤入涵碧楼”。③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乾隆朝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1164 页。西湖有涵碧楼等名胜。潮州有涵碧楼,亦有涵碧堂,如“寺僧导余上,入涵碧堂小坐,启右扉而北度石桥,过绿云楼。”④[明]王临亨:《粤剑编》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97 页。涵碧轩,“江道士《涵碧轩》:‘飞阁环流水,层轩面面开。虚澄涵倒影,净碧绝浮埃。镜里闲云度,潭心爽气来。道人能有此,还似小蓬莱。’”⑤[明]薛瑄:《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六,《薛瑄全集》,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 年,第249 页。庐山有涵碧池,“有十老堂、濯缨亭、涵碧池、芙蓉径、古木陂诸胜。二百年来殆亦消归何有”。⑥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康熙朝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860 页。涵碧由一处景观的命名开始,经由刘禹锡诗歌的推广,逐渐成为闻名遐迩的文人胜迹,在历代延续中,不仅有涵碧亭,还广泛推及到楼、堂、轩、池等其他景观。
其次,传播中不断强化文人雅趣与山水景观的历史积淀。古人历来有寄情山水之作,题咏“涵碧”也不例外,如宋冯山《阆中蒲氏园亭十咏·涵碧亭》云:“日影摇吟笔,烟光落酒杯。犹嫌池外俗,移入镜中来。”⑦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七四一,第8646 页。文同《蒲氏别墅十咏·涵碧亭》曰:“轩窗晓吹清,枕簟晴光冷。亭上逍遥人,满身摇水影。”⑧傅璇琮等:《全宋诗》卷四三三,第5315 页。“涵碧”之景集日影、晴光、水影为一身,有清冷脱俗之感,充满文人赏玩之雅趣。但从刘禹锡《涵碧图诗》以来,“涵碧”不仅拥有现时的抒怀意味,更带有历史感,从而使“涵碧”更具人文意味,表现出传统文化的深厚。如东阳人曹冠《兰陵王·涵碧》云:“晚云碧。松巘飞泉翠滴。双鱼畔、疑是永和,曲水流觞旧风物。波光映山色。时见轻鸥出没。壶天邃,修竹翠阴,虚籁吟风更幽寂。登临兴何极。上烟际危亭,彩笔题石。山中猿鹤应相识。对远景舒啸,壮怀豪逸。刘郎何在玩石刻。感往事陈迹。还忆。少年日。帅旗鼓文场,轩冕京国。如今老大机心息。有陶令秫酒,谢公山屐。闲来潭洞,醉皓月,弄横笛。”⑨唐圭璋编:《全宋词》,第1536-1537 页。曹冠词是对涵碧景观的整体描绘,不仅有对碧水山色修竹亭石的细致描摹,更追忆刘禹锡当年题诗涵碧的情景,用陶潜、谢灵运的典故,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其另一首《夏初临(并序)》中说:“淳熙戊戌四月既望,游涵碧,登生秋、冲霄二亭,觞咏竟日。……佳山句在,我思古人,对景兴怀,视今犹昔,何异乎兰亭之感慨也。”⑩唐圭璋编:《全宋词》,第1532 页。亦承袭于古人登临咏景之情怀。刘宰《东阳道旁涵碧亭》云:“斯亭作者谁,俯仰四百年。栋宇有兴废,篇章足流传。”⑪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二八〇八,第33391-33392 页。在时空差异中写尽文章千古不废的历史事实。强至《涵碧阁,东阳山水佳处。予闻且久,独未能往。近得进士与邑官唱和诗,读之景物依然,如暂经目,因次元韵附诸篇之末云》中说“吟恐昔人精魄笑,到疑盛夏骨毛寒。流觞已往双鱼在,怀古探奇两事干”,⑫傅璇琮等:《全宋诗》卷五九二,第6978 页。亦是今昔对比。元胡助《和方韶卿游涵碧韵》中写“拂袖高吟梦得诗,缓探陈迹扣林扉。古亭禅刹自兴废,野水闲云无是非。一沼净沉秋树影,数峰长带夕阳晖。风流县令今何在,唯有苍苔满钓矶”,⑬杨镰主编:《全元诗》第29 册,第79 页。不仅表达对刘禹锡题诗之向往,更点明风流县令之典。
古代文人士大夫眼中,山水景观可供赏玩,源于其绝佳的外在形态。可能是位置经营的巧妙,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可能是景色的奇绝壮丽,如“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亦可能是色彩的绚烂多姿,如“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等等。但另一方面,正如“涵碧”这样的景观,不仅有其自然美的一面,亦因历史沉淀而有了人文韵味。通过代代诗人的再阐释,“涵碧”意蕴脱离了单纯的写景,其所附带的名人印迹不再仅限于兴宗和刘禹锡,更多富于文人情怀的典故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叠加,其内蕴不再局限于寄情山水的自得自洽,而被赋予了文人修身立言的终极意义。因“涵碧”以物态的景观形式存在,使得其间的文人情趣得以固化,更增强了其在文人群体中的显性传播。
四、结语与余论
古代诗歌传播的载体多为文本化的文人诗歌全集、选集,再加上历代诗文评注本、选本等等,建构了线性的诗歌传播路径。实际上,诗歌传播属于文化生态圈层的一个方面,必然受多类型、多样式的传播形式和模式的影响。当传播对象的外在特征和内在意蕴在审美性上产生交集时,传播主体的类型就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意象的传播并非单一线性,而是多角度叠加的晕圈模式,多角度即包含文学、音乐、书法、绘画、景观等。以“涵碧”为例,景观和绘画先于诗而成,后又不断重建与命名,加强了诗歌的美学特征和文化意义。唐东阳令于兴宗于县五里处发现一山水佳处,结亭其端,因其碧水澄澈,命名为“涵碧”。于兴宗请画师将此景绘成,使“涵碧”完成从景观到图画的转变,也是“涵碧”得以传播的优势条件。涵碧图呈于大诗人刘禹锡手中,刘禹锡作《涵碧图诗》融情感和议论入景。同时,刘禹锡在序中点明涵碧亭的由来,褒扬了于兴宗身为县令之亲民和为政的简易,从而建构了“涵碧”的深层意蕴,即从审美角度往文化角度转变,从可观性的“碧”之风景到文人为政清明的象征,体现了传统文人寄情山水之乐的内在理趣,并以从图到诗的方式完成了“涵碧”的第二次传播。“涵碧”本身的可视化特征以及其“景—图—诗”的传播路径为传播带来了确定性和广泛性,后世对“涵碧”的容受不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还以景观为中介广泛运用于文人群体,并以其深厚历史感所带来的文人化雅趣得到进一步传播与再塑。
值得注意的是,“涵碧”以其在文人圈的广泛传播而闻名,但在明清两代,却出现了从文人雅玩到俗文学和宫廷景观的些微变化,如俗文学中出现涵碧庄,“听秋馆里足勾留,涵碧庄前恣步游,自怡轩小适名楼(原注:俱园中楼馆名)。几多秋,一半儿梧桐一半儿柳”。①凌景埏、谢伯阳编:《全清散曲》,济南:齐鲁书社,2006 年,第1659 页。宫廷也出现以“涵碧”命名的景观,如“内苑涵碧亭苑入黄金坞,桥回碧树湾。龙池观九岛,鳌禁觅三山。溜转云车急,花深月殿闲。从来人罕至,御榻在中间”。②[清]钱谦益撰集:《列朝诗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3740 页。“乐成殿,从椒园南,循水过西苑门半里,有闸泻池水,转北别为小池,中设九岛三亭。一亭名涵碧,藻井斗角,十二面丹槛碧牖,尽其侈丽。中设御榻,外四面皆梁槛”。③[清]张怡:《玉光剑气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17 页。出现此变化的原因一是可能与“涵碧”的色彩之美有关,另一方面,也缘于其时文化艺术的时代背景。对“涵碧”这一经典范例的梳理,是对古代诗图关系研究的一个补充。“涵碧”的由来以及传播,可见古代文化生态的存在形式。其并非一个孤立的个体,也不是单一的文学艺术样式所能包含的,文学、绘画和景观三者之间彼此影响,接受容纳,共同塑造出传统文化的存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