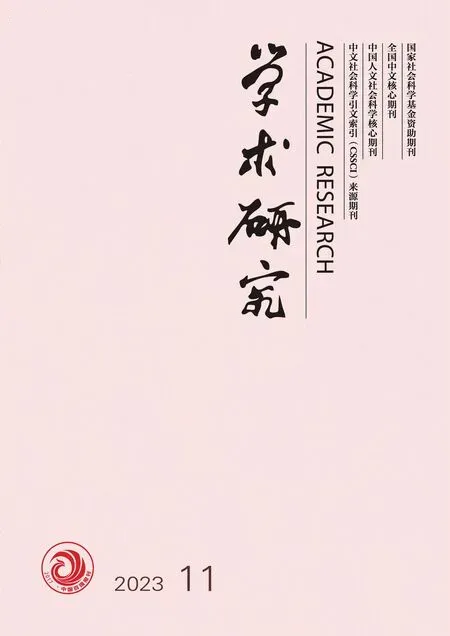两个桃源的对话
——《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关系的再探讨
李光摩
《桃花源记》(以下简称《记》)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也可以说是陶渊明最具知名度和代表性的作品,而《桃花源诗》(以下简称《诗》)则相对逊色不少。但在《陶渊明集》里,《诗》和《记》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以《桃花源记并诗》的名目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诗》的重要性未必就在《记》之下。那么,《诗》与《记》到底是什么关系,《诗》与《记》是否可以独立单行,它们的思想是否一致?如果《诗》与《记》作为一个整体,算是文体的创新吗?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一一进行审视。
一、关于《桃花源记》与《桃花源诗》关系的种种说法
《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在陶集、陶诗注本及古诗文选本里的存在形态迥然不同。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以李公焕本为底本,并用曾集等本对校,桃源诗文题作《桃花源记并诗》。其他如杨勇、龚斌和袁行霈等笺注本也都参校多种古本,题作《桃花源记并诗》,入卷六“记传赞述”类。这样看来,陶集里的桃源诗文基本上是以记为主,以诗为辅。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却一改成规,将桃源诗文移置编年诗内,以诗为主,改题《桃花源诗并记》。当然还有更特别的,如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中《陶渊明集》,桃源诗文被一分为二,记是记,诗是诗,各不相干。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四卷,是现存最早的陶诗注本,其中《诗》却以《记》的附庸形式出现,题作《桃花源记并诗》,附在卷四之末。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四卷,突出了《诗》的地位,题名《桃花源有记》,列在卷四之末。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参照黄文焕做法,列《诗》于卷末,题作《桃花源诗并记》。丁福保《陶渊明诗笺注》、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亦是如此处理,题作《桃花源诗并记》。古诗选本如明人冯惟讷《古诗纪》、陆时雍《古诗镜》和清人沈德潜《古诗源》由于编选内容的限制,皆题作《桃花源诗并记》,《记》只是附带性质的存在。而在古文选本中,一般是把诗删去,只保留一篇记,《古文观止》即是如此。这也影响到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并通过教材影响一般社会大众,认为《记》是独立成篇的。那么,《诗》与《记》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第一,视诗文各自独立。其一,认为《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1918 年,胡适发表《论短篇小说》一文,认为《桃花源记》是一篇用心结构的短篇小说。①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第4 卷第5 号,1918 年5 月15 日。1929 年,梁启超说:“这篇记可以说是唐以前第一篇小说,在文学史上算是极有价值的创作。……至于这篇文的内容,我想起他一个名叫做东方的Utopia(乌托邦),所描写的是一个极自由极平等之爱的社会。”②梁启超:《陶渊明》,《饮冰室合集》第8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1 页。把《记》视作一篇小说,这个说法自然有其根据。因为在《搜神后记》里可以找到《记》的雏形,而《搜神后记》在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当中属于子部小说类。其二,认为《桃花源记》是一篇古文。如明贺复徵编《文章辨体汇选》就将《桃花源记》与柳宗元“永州八记”等编为一卷,明显是将其视为古文。传统的古文选本如吴楚材、吴调候编纂《古文观止》,限于选文体例,单选记,不录诗,完全将《记》视作古文。
第二,视诗文互为一体。其一,认为《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四库全书总目》“搜神后记”提要云:“旧本题晋陶潜撰,中记桃花源一条,全录本集所载诗序,惟增注渔人姓黄名道真七字。”③[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说家类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1208 页。四库馆臣把《搜神后记》当作伪托之作,且把《记》当作《诗》的序言看待。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将《桃花源记》降为与“诗序”同列,是《诗》之附庸。④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年,第92 页。施蛰存也认为《记》是《诗》的序,后人裁篇单行,题作《桃花源记》,可以说是游记文的嚆矢。⑤施蛰存:《漫谈古典散文》,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 年,第30 页。诗序这个说法太不确切,首先要破掉。什么是诗序呢?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尔雅》云:‘序,绪也’。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⑥[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第42 页。一般诗序,大都“自述写作缘起、主旨和阐释创作背景,是对诗题的补充,是读者了解作品的重要依据”。⑦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文学遗产》1996 年第5 期。陶渊明的作品,如《停云》《时运》《游斜川》《饮酒》等作均有序,也都是交待写作缘起、背景,而《记》却没有这些类似的交待,与诗序迥不相类。其二,认为二者属于对话关系。蔡瑜曾论及陶集不同文体之间的对话,认为《诗》与《记》也是如此。“《桃花源记》……再加上与诗组合,并列《记》的客观叙事,《诗》的主观抒情两种声音,形成文体结构本身虚实主客的对话张力与多重声音。”⑧蔡瑜:《陶诗与对话》,《中华文史论丛》2010 年第2 辑。
其三,认为《诗》与《记》是一个整体,属于文体的创新。张伯伟认为陶渊明是文学史上少有的文体大师,兼采不同文类,熔铸新体。《桃花源记》由一文一诗构成,以两种不同的体裁处理同一主题,亦文亦诗,互相映衬,正是陶渊明在文体上的一种新尝试。⑨张伯伟:《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新论》,莫砺锋主编:《程千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年,第289-291 页。顾农认为《桃花源记并诗》在思想上是复古的,在艺术上是创新的,其一文一诗的成组配合,同时又各具相对独立性。⑩顾农:《〈桃花源记并诗〉新论》,《中原文化研究》2019 年第4 期。如果《记》与《诗》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那么可以把《诗》视作《记》的隐括。如果思想倾向不一致,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记》是陶渊明独创,抑或记录润色?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回溯作品的诞生过程。
二、《桃花源记》的诞生与思想倾向
《桃花源记》的故事显然不是作者杜撰,而是有所借鉴。陈寅恪认为桃源故事系据传闻而写成,《搜神后记》中桃源故事乃《桃花源记》之初本。“《搜神后记》卷一之第五条即《桃花源记》,而太守之名为刘歆,及无‘刘子骥欣然规往’等语。”其第六条即刘子骥入衡山采药事。“据此推测,陶公之作《桃花源记》,殆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二事牵连混合为一。”①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195 页。唐长孺也有类似的主张,他说:“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陶渊明根据所闻加以理想化,写成了《桃花源记》。”②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186 页。逯钦立也认为《桃花源记》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③逯钦立:《关于陶渊明》,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附录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256 页。
除《桃花源记》外,魏晋六朝在南方存在着不少类似的遇仙传说。如刘敬叔《异苑》卷一载:“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遂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斫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④[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4 页。唐长孺评论说:“刘敬叔与渊明同时而略晚。他当然能够看到陶渊明的作品。然而这一段却不像是《桃花源记》的复写或改写,倒像更原始的传说。我们认为陶、刘二人各据所闻的故事而写述,其中心内容相同,而传闻异辞,也可以有出入。敬叔似乎没有添上什么,而渊明却以之寄托自己的理想,并加以艺术上的加工,其作品的价值就不可同日而语了。”⑤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87 页。任昉《述异记》卷下“武陵源”条载:“武陵源在吴中,山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末丧乱,吴中人于此避难,食桃李实者,皆得仙。”⑥[梁]任昉:《述异记》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19 页。这个故事基本上是桃源故事的简写版。类似的还有刘义庆《幽明录》所载“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故事。⑦[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年,第1 页。这些传说的出现在时间上与《桃花源记》相距很近,也间接说明桃源故事在当时广泛流传,陈寅恪、唐长孺等人的说法是可信的。
我们发现,这些传说大致有着共同的要素,即沿水而入的路径,经过山洞进入平旷的地方,有桃树等。这里涉及三个道教之象,即山洞、桃树与溪水,它们构成了遇仙故事的基本要素。仙界往往需沿水路而入,这个特点如果往前追溯,还有几个有名的故事。如周密《癸辛杂识》引《荆楚岁时记》载,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至天河,得织女支机石。⑧[宋]周密:《癸辛杂识》,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29 页。其他如张华《博物志》卷三、《太平御览》卷八引南朝宋刘义庆《集林》所载应为同一故事,传闻异辞而略有差异。其共同点是凡人皆经水路而达仙界,这与桃源渔翁沿溪而行颇为相近。而桃树作为仙界的代表植物,在《桃花源记》及同类故事中多有出现。其出现可以追溯更早。《风俗通义》《搜神记》俱引《黄帝书》云,黄帝做桃人以立门户,画神荼、郁垒以象之,借之驱鬼。《初学记》卷二十八引《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服邪气,制百鬼。故今人作桃符著门以厌邪,此仙木也。”⑨[唐]徐坚等:《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674 页。由此看来,桃树作为仙木有着悠久的历史。桃源的山洞,也和道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陶弘景在《真诰·稽神枢》中有关于洞府的详细描述,至唐代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道教洞府基本定型。道教认为,在天地之间,除了仙岛之外,名山之中还有诸多的洞天福地。那里虽是仙人世界,世俗凡人亦可出入。
张松辉认为桃花源的原型就是道教茅山洞天,且拿桃花源与《真诰》描写的洞天做了比较,得出几个共同特点。其一,二者都是经过山洞进入洞天。《真诰》卷十一云:“中茅山东有小穴,穴口才如狗窦,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阔……便朗然如昼日。”其二,洞天里的山水田园与人间无异,虽是神仙福地,世俗凡人也能偶尔进入。《真诰》卷十一云:“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觉是洞天之中。”陶弘景注曰:“世人采药,往往误入诸洞中,皆如此。”其三,《真诰》提示,山洞即是洞天的便门,专门为世人准备的,因为神仙根本用不着。但不是谁都可以进入洞府的,只有纯真之人才可以。《真诰》卷十一云:“愚心鄙近,亦以肉人秽浊,精诚不恳,无能上达。”陶弘景注曰:“今南便门,外虽大开,而内已被塞,当缘秽气多故也。”①参见张松辉:《十世纪前的湖南宗教》,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116-120 页。陶渊明笔下的渔翁,第二次想要带人进入桃源,由于落了机心,遂不能如愿了。
《桃花源记》作为遇仙的故事,在类书中也可得到佐证。如《太平御览》卷六六三“道部五·地仙”引“陶潜《桃源记》曰”云云,可以说是一个简化版的《桃花源记》。由此可见,《桃花源记》原本就是遇仙的故事。唐代诗人大多视《桃花源记》为一神话故事,如王维、韩愈、刘禹锡诸人的相关诗作,皆是如此。宋代以后,风气转变,则视《桃花源记》为一世俗故事,其中居民即为隐居避难之人。苏轼、洪迈、方回等人皆作如是观。②关于宋代以来对《桃花源记》现实维度的解读,可参见李光摩:《〈桃花源记旁证〉发覆》,《学术研究》2012年第6 期。即便在宋代以后,在部分词曲作品中,桃源故事依然保留着神话性质。如韩元吉【六州歌头】:“前度刘郎,几许风流地,花也应悲。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元杂剧《误入桃源》第四折【殿前欢】:“这时节武陵溪怎喑约,桃花片空零落,胡麻饭绝音耗。”《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赚煞】:“春光在眼前,争奈玉人不见,将一座梵王宫疑是武陵源。”我们发现,在这些作品里,桃源往往指代刘阮天台遇仙故事,天台和桃源合而为一了。这一点甚至在词牌上亦有表现,如【阮郎归】,宋以后又名【醉桃源】【碧桃春】等,隐约透露了其中消息。其实,桃源与天台合而为一,至迟在唐代即已出现,如曹唐的游仙诗《刘晨阮肇游天台》云:“树入天台石路新,云和草静迥无尘。烟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梦后身。往往鸡鸣岩下月,时时犬吠洞中春。不知此地归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③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下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2772 页。天台与桃源为什么会合流?首先,二者的性质是一致的,都是遇仙故事。其次,牵涉到诗歌的用典问题。陈永正解释说:“同姓之典,如‘刘郎’之典,‘桃源’与‘天台’之典,亦经常合用。”自杜甫以来,宋代诗人作诗也喜欢合用典故,并视之为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法。④陈永正:《诗注要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第128 页。这一用典方法后来又逐渐渗透到词曲创作之中了。
也许有人说,桃源的世界实在太像人间了,说是仙境有点牵强。袁行霈对此解释说:“此仙境乃渔人偶然发现,且不可再觅,所谓‘一朝敞神界’,‘旋复还幽蔽’。此亦无甚奇者,一般神仙故事多如此。桃花源与一般仙界故事不同之处乃在于:其中之人并非不死之神仙,亦无特异之处,而是普通人,因避秦时乱而来此绝境,遂与世人隔绝者。此中人之衣著、习俗、耕作,亦与桃花源外无异,而其淳厚古朴又远胜于世俗矣。”⑤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483 页。这个解释不尽如人意,其中蕴含着一个矛盾,既然是仙界,却长期住着一群凡人。也许潘雨廷的解释更为合理,他说:“道教的仙境与其他宗教的彼岸世界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个纯粹空虚死寂的世界,而是和充满了活力的人间相似。”⑥潘雨廷:《道教史丛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59 页。综上所述,《桃花源记》叙述的是一个遇仙故事,其所表现的思想,是当时一般社会大众的道教信仰,即追求洞天福地、长生久视的思想。问题是,陶渊明是否认可这一思想倾向?
三、《桃花源记》符合作者的思想吗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归属,历来众说纷纭,儒释道三家标签都曾被不同的学者分别标在陶渊明身上。其一,认为陶渊明属于儒家思想。如真德秀说:“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⑦[宋]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104 页。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云:“渊明之学,自经术来。《荣木》之忧,逝水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饮酒》末章,东周可为,充虞路问之意,岂庄老玄虚之士可望耶?诗中言本志少,说固穷多。夫惟忍饥寒,而后存节义也。”⑧[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年,第101 页。钟泰说:“渊明慨想大同,于诗文屡发之,不独《桃花源记》云尔也。”又说:“盖自孔子作《礼运》以来,儒者言治,惟及三代。其跨三代而思跻于黄虞者,渊明一人而已。”“渊明之学,迹近老庄,而实本之孔氏。”①钟泰:《中国哲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年,第157-159 页。朱光潜也认为陶公一再引“先师遗训”,处世近于人情,富于热情,故得力所在,“儒多于道”。②朱光潜:《诗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第330 页。其二,认为陶渊明属于佛教思想。如葛立方认为《形影神》三篇,皆寓意高远,盖第一达摩也。③[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575 页。熊十力《存斋随笔》云:“渊明学杂道佛,而佛之成分尤多。”又说:“陶渊明诗,有旷远冲淡之趣,而杂染佛徒西来意。览其诗集,《归园田居》有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又曰,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王船山嫌其颓废,卓哉睿识。千载来论陶诗者,未见及此。”④熊十力:《存斋随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第77、75 页。其三,认为陶渊明属于道家思想。如朱熹说:“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陶渊明,古之逸民。”⑤[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3243 页。朱自清从古直笺注引注情况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49 次,《论语》第二,37 次,《列子》第三,21 次,说明陶诗里的主要思想还是道家。⑥朱自清:《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第288-289 页。
中国在宋代以来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思想格局,几乎每个士大夫都会受到三教的沾溉。在陶渊明时代,三教合一还没有最终完成,但许多人已经程度不一地受到三教的影响。所以,我们探讨陶渊明的思想,主要是指他在三教之中更倾向哪一家,而不是说,除了此一家,他的思想中再没有受到其他两家的任何影响了。那么,陶渊明在儒释道中到底更倾向哪一家呢?首先可以排除佛教。慧远在庐山精舍与同道立誓共期西方,周围名流云集,如刘遗民、周续之、毕颖之、宗炳、雷次宗诸人,皆一时之选。而当时与慧远比邻而居的陶渊明却未参与,说明诗人对其思想的不认同。汤用彤曾说:“靖节诗有赠刘遗民、周续之篇什,而毫不及远公,即匡山诸寺及僧人亦不齿及,则其与远公过从,送出虎溪之故事,殊难信也。”⑦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264 页。前揭熊十力举“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之语来证陶渊明沾染佛教颇深,似不贴切。“幻化”在道教亦为常谈,“空无”虽有佛教色彩,但单词孤语,很难坐实。
陶渊明更倾向儒家吗?他曾说:“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赠羊长史》)⑧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第65 页。本文所引陶诗皆出此书,不另注。“跨三代而思跻于黄虞”,钟泰以此为陶渊明为儒家之一证。然而,黄虞是儒道两家共同想象的黄金时代,单指儒家,显然不合理。朱光潜也以陶渊明屡引“先师遗训”,谓其为儒家信徒。这个证据也不够有力。陶渊明诗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之二)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对此说法,诗人显然不认同。“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他说,孔子的理想太高远了,不切实际,还不如下地劳作。而孔子对劳作的态度,以及对樊须的批评,是众所周知的。陶渊明还曾借古隐士来表达对孔子的态度。“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这两首诗涉及长沮、桀溺和荷蓧等三位古隐士,而他们对孔子是颇不认同的。在《论语·微子》里,长沮、桀溺耦而耕,他们对子路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荷蓧丈人对孔子之徒的评价也很低,即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陶渊明欣赏的古隐士对孔子颇不以为然,从中我们自然可以窥见其倾向。《饮酒》之二十,也是一首能够表现其对儒家看法的作品,其中云:“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陶渊明追求羲皇时代的真与淳,显然对当下颇为失望,孔子即使有复真还淳的愿望,但时移世易,也很难有所作为。况且,从“弥缝”二字,诗人看出孔子迁就时势勉强推行儒道的窘态,其结果自然不会乐观。观此,陶渊明非孔子之徒可知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陶渊明更倾向于道家思想。陈寅恪认为《形影神三首并序》最能代表陶渊明的思想。“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陈寅恪按语云:“谓长生不可期,神仙不可求也。”“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陈寅恪按语云:“此非主旧自然说者长生求仙之论”。“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陈寅恪按语云:“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概括言之,“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他对所谓名教也是有所批评的,“但其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盖主新自然说者不须如主旧自然说之积极抵触名教也。又新自然说不似旧自然说之养此有形之生命,或别学神仙,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即与大自然为一体”。①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29 页。陈寅恪标举“新自然说”,借此使陶渊明与嵇康等人区别开来。但陶渊明既不养生,又不求仙,只是委运任化,恐怕与天师道这种宗教信仰相距甚远。
其实,陶渊明的道家,似老庄,又不同于老庄。清人方宗诚说:“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②[清]方宗诚:《陶诗真诠》,《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第254 页。不离人事人情,又有行动的能力,说明陶渊明信崇的道家不是魏晋之际清谈的玄学,也不是修仙的道家,而更像是战国至汉初的黄老道。黄老之学在先秦汉初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范蠡、张良是其重要代表人物。司马谈对黄老道家评价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于道家曾著录《老子》《黄帝四经》等书,也说黄老道学是“君人南面之术”。这说明黄老道学是有大行动力的,远非魏晋玄学可比。黄老所谓的“无为”,不是完全不为,而是顺自然而为,汉初的文景之治就是落实黄老之学的结果。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黄老之学并未消歇,而是潜入民间,时隐时现。到唐代,《黄帝阴符经》被发明,和《道德经》相配,依然是黄老之学。在陶渊明诗文中比较明显表现黄老思想的作品是《咏二疏》:“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此诗表彰汉代疏广叔侄,功成身退,散尽千金,颇有范蠡、张良之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诗,表现了陶公对仕隐的看法,亦可注意,诗云:“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踠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清人温汝能评曰:“孔明初出茅庐,便有归耕南阳之想;渊明始作参军,便有终返故庐之志,其胸怀一而已。至于一返一不返,时势不同,所遭各异也。”③[清]温汝能:《陶诗汇评》卷三,《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第117 页。黄老强调适时顺势,时来则仕,时去则隐。即便成功,也要功成身退。陶渊明此诗差可表现此意。陶渊明侧重黄老思想的另一表现是珍惜现实生活,而非避世出尘。“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饮酒》之六更是完美呈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南山飞鸟,一派澄明,世界在诗人面前打开,万象在旁,目击道存,何必言语?有此境界,又怎会追求什么仙境?对现世生活的热爱,使诗人远离了一般社会大众的道教信仰。
陈沆认为,读陶应力避二蔽,一为闲适,一为忠君。“早岁肥遁,匪关激成;老阅沧桑,别有怀抱。”④[清]陈沆:《诗比兴笺》卷二,《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第237 页。可谓知言。陶渊明既不是闲适的田园诗人,也谈不上激愤的忠君诗人。正如鲁迅所言,“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反而内心有一种平静。他对刘裕不抱什么希望,对东晋也未必有太多的向往。总之,他对这个时代彻底失望了。然而,尽管失望,诗人并未自暴自弃,而是坚定地站在大地上,用劳作证明生命的价值,用劳作呼唤人性的本真。沈德潜引陶诗曰:“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并进而指出:“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异于晋人如此。”①[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63 年,第170 页。《劝农》就是这样一首作品,举舜、禹、稷、周作榜样,以劝君相之重农;举冀缺、沮、溺作榜样,以劝仕隐之重农。陶渊明为什么如此重农?黄文焕道出个中原因:“《劝农》,情理深远。绎其首末,光怪万状。开口曰‘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巧最伤朴者也。欲广用奢,财之不足,岂必智巧,愚者同有之。而必归罪智巧者,智巧生而百姓之心坏;心不坏,则欲不广。智者不作,则愚者不效也。坏风俗莫若智巧,赡民生又必须哲人。下欲愚,上欲智,上与下不同道,小智与大智不同用也。杜民智巧,惟在劝农。民农则必朴,移风易俗,返朴在是。历代作用本领,由虞至夏、周,莫不同意。此《劝农》大渊源,非独为疗饥计。”②[明]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3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第169 页。不但《劝农》如此,陶渊明的多首农耕诗也是如此,皆有用世之意。面对浇薄的人世,他渴望有一个大回归,“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于是有羲皇之想。
通过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考索,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和清静无为的玄学无关,和修仙养性的道教也无关,而是以积极入世的黄老道学为主。而《桃花源记》所表达的长生久视思想与诗人是有冲突的。那么,我们就需要具体考察诗人的创作意图何在,《诗》与《记》的关系如何。
四、《诗》与《记》的对话
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诗》与《记》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现象很多学者也看到了。如雒江生认为,《诗》与《记》存在着三个矛盾:五百年与六百年的矛盾;《诗》与《记》所描写的历史环境与时代特点不同,有些情景是相反的;《诗》与《记》的写作旨趣不完全相同。这之中除了第一个矛盾可以忽略之外,其他两个矛盾是确实存在的。那么,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呢?雒江生认为《诗》与《记》不是一篇作品,而是作者在不同时期,不完全相同的写作旨趣下,所写的各自成篇的诗文。③雒江生:《略论桃花源记与系诗的关系》,《文学遗产》1984 年第4 期。但这并没有解决矛盾。因为这毕竟是同一作者就相同题材所作的诗与文,不会因为把二者分开各自成篇,矛盾就自然消解了。还有部分读者认为《诗》与《记》是一体的,其思想倾向也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对于其中的矛盾之处,极尽弥缝之能事。然而,这些努力也不尽如人意。这就提醒我们,不妨转变思路,正视矛盾的存在,且视之为诗人的有意为之。因为像陶渊明这样的大诗人不可能对如此显豁的矛盾认识不到,处理不了。
前揭陈寅恪引述《形神影》论证了陶渊明对修仙养性道教的排斥,在陶渊明其他诗文也有类似的表述。如“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闻”(《连雨独饮》),“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这些诗句体现了诗人对神仙的不信或不屑。《读山海经十三首》,诗人以现实起,以考史终,立意所在也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此外,众多的田园诗也表达了诗人对现世生活的热爱。以陶渊明这样的思想,他对追求长生久视的道教思想应该是排斥的。而《桃花源记》如前所述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追求洞天福地、长生久视思想的体现,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诗人把这一故事勾勒出来,再以一首诗来回应,其意图很明确,就是对话与批评。既然不认同,既然是批评,两首作品呈现出来的内容和旨趣当然会有差异。《诗》既然是对《记》的批评,脱离了《记》就成了无的之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把《记》与《诗》看作一个整体,缺一不可。
下面就《诗》与《记》逐条疏解,以呈现二者的对话关系。对其矛盾之处,读者尤需留意,这正是诗人命意所在。(1)“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记》的开头先讲渔翁发现桃源的过程,这个过程几乎是遇仙故事的一个套路,而《诗》却略而不言,直陈世人入山避秦,桃源之人亦是如此。此与仙境拉开距离。(2)“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记》云:“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诗》说路径荒废了。二者说法相似,都是说桃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3)“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记》中只是闲闲带过,所谓有“良田桑竹之属”、有人“往来种作”,显得过于恬静。而《诗》中所述,桃源人肆力农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种秋收,自足自乐。无王税之可交,无王官之可瞻,三代不过如此。《诗》强调了力耕的快乐。(4)“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记》云:“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不同之处在于“暧”字,此字有昏暗不明之义,亦有掩蔽之义。“阡陌交通”是指交通便利。而“荒路暧交通”却是指交通不便利,即便有路,不常走,也荒废了,即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诗》强调了“不相往来”的一面,因为大家生活富足,不需要往来相互帮衬。(5)“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记》中无俎豆之事。两个对句,说明《诗》中桃源礼制、衣裳皆旧时之制。《记》对衣裳的表述:“男女衣著,悉如外人。”“外人”为何,历来聚讼纷纭。按照常理,一个与世隔绝了几百年的地方,其服饰不可能与外界完全一样。不管“外人”是指桃源之外的人,或是世外之人,都说明《记》中所写应是仙境,否则解不通。而《诗》写的是带有复古气息的理想人间。(6)“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记》云:“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诗》则更生动具体,是鲜活的人间。(7)“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记》勉强对应的是:“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强调的是没有历史感,对世事的茫然。而《诗》强调的是,桃源无历志,叶落而知秋。无历志,即无王权,此殆所谓羲皇时代。(8)“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记》无相关表述。《诗》渴望返璞归真,是对尔虞我诈的现世的批判。陶诗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瞻之,实赖哲人。哲人伊何?时维后稷。瞻之伊何?实曰播植。”(《劝农》)(9)“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记》文所述,自秦至晋太元间,五百多年。一朝被渔翁撞破,显露于世。自此以下,是对《记》所写桃源故事的评论。(10)“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记》中渔翁再寻,不复得路。即便有这样的仙境,也不可能向浇薄的世俗世界敞开。《诗》强调桃源关闭的原因,淳薄不同世。(11)“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记》之末尾,刘子骥欲寻而未果。《诗》显示了对方士的不屑。(12)“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最后卒章显志。自己不会像刘子骥那样想去寻找一个世外桃源,也许在这个尘嚣的世界里,在自己的脚下,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
细读文本,我们发现《诗》与《记》有重合,有差异,差异多于重合。重合是认同,这是二者相似的地方,都是避难入山,都生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里,其中的生活非常美满。差异是商榷,是对话,重要性远在重合之上。差异之中包含着忽略与增补,忽略是否定,增补是强调。一损一益之间,诗的主旨凸显了。其中最重要的忽略是桃源发现的过程,诗人有意避开,其目的是否认其神话性质,显示了桃源的人间属性。增补的是桃源人肆力农耕,以及桃源世界无王税、无历志的无政府状态。其对劳动的赞美,是诗人站在大地上面对浇薄人世的批评,希望能借此移风易俗,返璞归真。既然是对话,当然蕴含了两个迥然不同的桃源。一个是《记》中呈现的无历史感的仙境桃源,一个是《诗》中所写带有复古气息的人间桃源。仙境桃源所表述的是那个时代一般社会大众的思想,而人间桃源则表达了作者的愿望。仙境桃源是静谧的、被动的,其所表现的是世俗的仙界想象。而人间桃源,则是主动的、有为的,其对仙境桃源有所修正,有所批评,其所表现的是淳朴人世的劳作与快乐。通过对话,诗人否定了仙境桃源,表明其所向往的桃源是一个虚君主义的、无为而治的世界。那里不需要智慧,不需要王权,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最后归宗于“羲皇上人”,所谓“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种以不同文体对话构成的新体裁,可视为陶渊明的一次文体实验。陶渊明把世俗的遇仙故事加工润色,成就了《桃花源记》这一千古名篇。但它代表着世俗的意见,作者并不认同。陶渊明最终以诗的形式对这种世俗意见作出了回应,把一个清幽恬静的桃源仙境,成功地改造为脚踏实地的人间乐土。这种文体创新也为后学开启无限方便法门,为文学体裁的丰富多样提供了可能。如果这个结论可以成立,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效法王瑶的做法,将《桃花源记并诗》改题《桃花源诗并记》,并在陶集中将其置入适当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