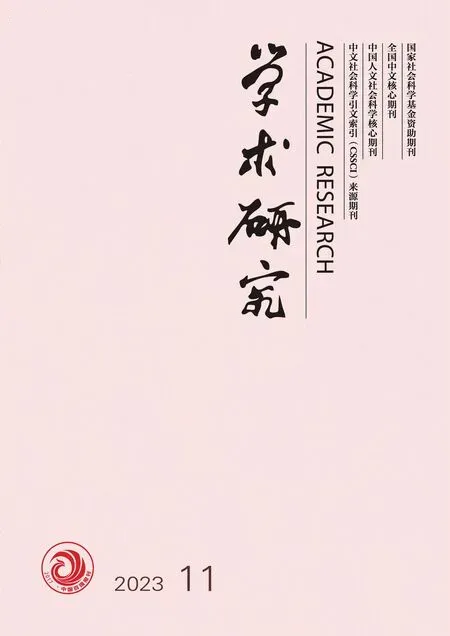清末官制改革与丞参兴废*
林浩彬
以尚书、侍郎(合称堂官)与郎中、员外郎、主事(合称司官)为主的六部官制,是隋唐以后中国历代王朝的重要官制,并与卿寺、翰林院、都察院等一并构筑起整体的内官制。上述官制由于清末丞参兴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丞参为左、右丞与左、右参议的合称,二者是清末新政以后各部普遍新设的职官。丞参兴废贯穿了清末新政的各个关键阶段,展现了不同阶段官制改革的新特点。该问题不仅决定了清末新政以后各部官制改革的成效,同时与卿寺、翰林院、都察院等其他内官制改革的整体进程密切相关。丞参兴废作为清末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不仅改变了既往各部官制的立意、体系、架构,更成为改变整个内官制立意、体系、架构的关键,对于近代中国的官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清末丞参兴废的问题,此前学界主要在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部的研究中有所涉及,侧重于介绍特定部院丞参的设立时间、人员组成、职能等基本内容。①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208-209 页;王奎:《清末商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63-77 页;杨帆:《清末度支部机构及职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s1 期;苏全有:《论清末邮传部的人事管理》,《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6 期;鞠方安:《中国近代中央官制改革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103-104、232 页。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到清末设置丞参对部院职官专门化的影响。其中,李文杰注意到清末外务部设置丞参与总理衙门的渊源关系,并重点考察了外务部丞参人员的来源与去向。②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第373-428、435-445 页。刘文华则从部院内部官职调整的角度,介绍了清末丞参设置、职掌与存废之争的大体过程,提出其职掌“大致是承上启下,统筹全局,辅佐堂官处置部内事务”,认为设置丞参“符合了行政近代化的潮流”,而丞参存废争议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选任中的“腐败行为”。①刘文华:《丞参设置与清末官制改革》,《宁夏社会科学》2023 年第2 期。总体而言,学界对于丞参兴废中起源、讨论、定制、裁撤过程的梳理仍有不足。本文拟重点关照丞参兴废与清朝原来的部院官制、内官制以及日本中央官制的立意、体系、架构的关系,考察丞参兴废与裁撤书吏、裁撤九卿②清代的九卿有大小九卿之分。此处主要是指小九卿,一般指宗人府府丞、詹事府詹事、翰林院学士、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鸿胪寺卿、通政司通政使及顺天府尹。等相关问题的关联,展现清末官制改革寻求专门化的曲折过程,探讨其对于近代中国官制转型的长远影响。
一、改设外务部与设置丞参的起源
在庚子议和期间,由于北京公使会议要求清政府设立专门负责外交的机构,其开始筹划将总理衙门改设为外务部,由行在政务处、在京政务处与吏部商订外务部官制。③[日]川岛真著,薛轶群译:《晚清外务的形成:外务部的成立过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1 期。其中,按照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鹿传霖的设计,外务部的官制方案先由行在政务处拟稿,再交在京政务处商定。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初,行在总理衙门提出外务部官制草案,强调其升转等方面“均照六部旧章”的原则。不过,行在总理衙门章京刘宇泰等人对此并不认同,指出外务部相比六部存在“事繁责重,额缺应多”的特殊情况。因此,相比于旧的六部,外务部官制更应注重拓宽司官的升途,“以资鼓励”。假设外务部变通六部郎中、总理衙门章京保送四、五品京堂的旧制,不仅无法拓展外务部司官的升途,甚至不如六部司官的升转待遇。在其看来,外务部既然无法额外设置京卿以提供出路,就应在六部与总理衙门升转旧制基础上拓宽升途,“在京出路,自以郎中升转京卿及同员外保送御史为定”。④《本署拟改官制额缺应多并宽予出路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档号:01-14-032-06-008。
与之不同,五月初七日,京师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瑞良、顾肇新等拟订外务部官制九条方案,强调外务部“有总核之事,有分任之事”,讲求熟悉部务,这与六部的运作模式不同。因此,瑞良、顾肇新等强调,外务部的职官设置必须特殊对待,在仿照六部定例的基础上,“仍应参酌总署成规”,⑤《据总办等酌拟改外务部章程九条钞录咨会一并核议具奏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档号:01-14-032-06-007。使其同时兼具总核与分任的功能。由此奠定了外务部官制杂糅总理衙门与六部官制的设计基调。
其中,瑞良、顾肇新等提出“请酌设卿缺”的方案。在他们看来,改设为外务部后总理衙门章京由差遣改为实官,依照六部的升转体制已不合适。为此,瑞良、顾肇新等建议在该部添设职官,“拟请照内务府三卿之例,添设同文馆四品卿、五品少卿,满、汉各一缺,提调馆务,即充总办”。该项职官从原来的总办章京等人中“请旨简用”,使得熟悉部务的郎中、员外郎“迁转不出一途”,⑥《据总办等酌拟改外务部章程九条钞录咨会一并核议具奏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档号:01-14-032-06-007。符合各国外务部用人专门化的取向。按清朝旧制,寺卿等京堂是六部郎中、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等后续升转的重要对象,因此新设“卿”与“少卿”等职官,实际有将原先作为升途的寺卿移植、嫁接到外务部体制之内的意味。
不难看出,上述方案的实质是将总理衙门的提调、总办章京合二为一,变通总理衙门提调、总办章京的机制并移植到外务部之内。新设的四品卿、五品少卿负责原来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处理的事务,并从后者之中选择。编制与原来总办章京的人数相同,品级则分别与郎中、员外郎或总理衙门章京的升途对应。可见,上述设计实际便于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等直接改为外务部职官,实现本职与差遣合一,促使其成为事实上新增的职官层级。
六月,行在政务处已经议定,外务部“在侍郎以下、章京以上又设三、四品参议二员,体制如京堂。遇本署侍郎缺出,固可充补,即六部侍郎缺出,亦可升补”。⑦《外部新章续志》,《新闻报》1901 年7 月21 日第1 版。新设职官的品级与实质与前述方案截然不同。新的“参议”与侍郎的品级更加接近,更便于司员在本部直接、迅速升转,并且“体制如京堂”,愈加贴合此前京师总理衙门提出的仿效内务府三卿的方案。同时,外务部的“参议”可以升补各部侍郎。可见,该项设置更多是为了拓展该部职官的升途,而非出于简单的职官专门化的考虑。
由于外务部事属初创,各方对于该部新设职官的名称、级别、编制、升途等存在分歧。行在与在京的政务处大臣围绕此事反复讨论。此后,有消息称,外务部官制已由行在政务处将方案送京,规定“侍郎以下又设三品左、右丞各一员,四品左、右参议各一员,以本署总办升补斯缺”。①《外部额缺述闻》,《申报》1901 年7 月26 日第1 版。和此前的各种方案有别,新方案开始明确设置“丞”与“参议”的名称、品级与编制。
分设“丞”与“参议”进一步体现了不同品级职官的区别。对应清朝九卿职官的品级来看,设置三品“丞”比三品“参议”更加名正言顺,并能与堂官、司官的品级上下衔接,构筑起上下贯通的部院职官体系。此外,政务处确定“丞参四员以总办充补”,实际上等于正式承认将总办章京由差遣改为实官。随着外务部官制日渐清晰,政务处进一步规范丞参承上启下的地位与升途,“体制在堂官之下、司员之上,可升本部侍郎”,②《外部事宜汇闻》,《新闻报》1901 年8 月23 日第1 版。使其与六部堂司直接、大小相制的职官体系截然不同。
按罗惇曧的《宾退随笔》所载,外务部设置“丞参”的方案由京师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肇新提出。在设计外务部官制的过程中,顾肇新因其郎中的身份,“自揣必不能得侍郎”。设置丞参可在品级差别悬殊的郎中与侍郎之间架设升转的桥梁。顾肇新为个人的前途考虑,“乃建增设丞参之议”。可见,该方案实际是顾肇新为个人的前途所设的。不过,该提议虽被外务部“长官纳之”,却遭到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会办外务部大臣王文韶的抵制,按照该说法,王文韶认为外务部设置丞参弊大于利。各部堂官与司官品级相差悬殊是基于职官“大小相制”的设计。二者虽然区分尊卑,但可以堂司直接,“本无隔阂”。设置丞参作为总核职官,只会在二者之间增加职官层级,对政务运转“徒生障碍”。为此,王文韶主张采取倚重司官的举措,维持旧有的部院官制以代替设置丞参。据该笔记称,外务部设置丞参的进程一度受阻,直至王文韶去世之后才得以实施。③《记各部丞参》,[清]罗惇曧著,孙安邦、王开学点校:《罗瘿公笔记选》,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222-223 页。
实际上,上述说法存在不符史实之处。一方面,盛宣怀早在七月初二日就向在京的政务处大臣李鸿章通报清廷在外务部设置丞参的决议,“丞参照办。本日具奏,奉旨依议”。④《盛宗丞转西安来电》,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年,第 397 页。为此,李鸿章还就外务部丞参的选任对象提出意见,“外务部丞参应在总办、帮办各员内,择其尤为勤能者”,符合丞参“以资熟手”的功能要求与设计初衷。⑤《寄西安行在军机处》,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8 册,第399 页。另一方面,王文韶在商定外务部官制过程中实际扮演着重要角色。据其日记所载,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他“午后到外务部,随同庆邸核定丞参并章京二十四缺”。⑥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1052 页。可见,王文韶至少未对外务部设置丞参展现出明显的反对态度,甚至还亲身参与制订丞参的具体编制。
十一月,政务处大臣奏定的外务部章程决议“拟设左右丞各一员,正三品;左右参议各一员,正四品”。明确外务部职官在本部升转,“左右丞缺,以左右参议开列奏请简放。左右参议缺,先尽郎中,次用员外郎。由该部堂官保送引见,请旨录用。遇有该部侍郎缺出,先尽左右丞开列”,体现对外务部职官“以专责成”与“优予升阶”并举的宗旨。此举改变了六部郎中与总理衙门章京升转到其他机构的惯例,“所有郎中例应保送四、五品京堂员缺,即无庸开列”,⑦《具奏遵旨会议总署改设外务部酌拟章程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宗》,档号:01-14-032-06-008。开始打破原来的内升外转的体制。如果说外务部的司官设置是仿效六部、体现“分任”的宗旨的话,丞参设置则是在原先总理衙门的运作机制下改头换面,体现“总核”的要求。
综上可见,外务部设置丞参是结合总理衙门、六部与九卿体制的产物,主要目的在于拓宽官员升途、职官专门化以及沿用总理衙门总办章京旧制,并非仅仅只是职官专门化的考量,这也为后续该问题产生的一系列困扰埋下伏笔。在外务部率先设置丞参之后,新设的商部亦仿效其设立丞参。随后,户部等开始“请设参丞”。①《会议》,胡思敬:《国闻备乘》,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94 页。在清朝旧的六部中,户部与刑部是特别讲求熟悉部务的机构。二部的重要事务分别汇总于北档房与秋审处,并选择熟悉部务的司员充当总办、领办等差遣,新旧部院体制有别。户部提议设立丞参,无疑提出了六部是否设置丞参的命题。
二、整顿部务与关于六部设置丞参的讨论
清代六部原先以依据例案办事为基础,在说堂、画稿等方面大体形成堂官、司官、书吏之间区分尊卑又大小相制的运作体系。各部堂官、司官由于频繁迁调等原因通常无法熟悉部务。书吏则往往凭借对各部例案的熟悉而掌握其解释权,进而出现舞弊。清末新政开始之后,裁撤书吏、删订例案等成为时人主张整顿部务的主要方针,而裁撤书吏等无疑会改变旧有的部院体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受吏部裁撤书吏事件影响,御史王诚羲奏称六部书吏舞弊的根源,在于司官无法久任而不熟例案。因此,在六部裁撤书吏之后,部务需要责成司官,如何保证六部“官皆久任”是下一步整顿部务的关键。为了实现六部官员久任的目标,王诚羲提出了两套方案:一是完善旧制。此前六部通常从郎中、员外郎中选择资深人员,充当各司掌印、主稿或各部领办、总办等差遣,由其处理主要事务。在其升转时则由堂官通过奏留以保证熟手。因此,需要保证该部有重要兼差的司官久任,“期以数年不调”。二是新设职官。仿照外务部、商部的事例,在郎中以上“添设参议、左右丞各缺”。以此为司官提供升途,“使各部自堂至司在署办事常有始终行走之员”,②王诚羲:《奏为吏部裁革书吏统筹无弊之法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440-006。解决其在本部久任的问题,实现以专责成的目标。可见,其将设置丞参视为裁撤书吏后整顿部务的一大抓手或进一步举措。
不难看出,王诚羲提出的两套方案存在逻辑关联,与此前外务部设置丞参的方案大同小异,主要目的还是为处理重要部务的职官寻求新的出路。正因如此,有说法称,王诚羲的上奏背后有人事的影响,“此事发端由于吏部”,“所谓吏部建议开办,明指张玉叔(指张检,张之洞之侄,时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而言。有人谓此事为张玉叔所运动者,颇近是”。③[清]徐兆玮著,李向东、包岐峰、苏醒标点:《徐兆玮日记》第1 册,合肥:黄山书社,2013 年,第498 页。与之前外务部设置丞参的事例相似,提议六部设置丞参似因吏部官员考虑自身升途而推动。
吏部在清朝六部体制中地位显要,该部是否设置丞参对六部官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加之同期朝野裁撤六部书吏的呼声高涨,裁撤书吏以后的六部官制如何调整成为现实问题。政务处认为六部设置丞参与“官制攸关”,奏请清廷通咨各衙门“各抒所见,开具说帖,以凭汇核”。④奕劻:《奏为请旨会议添设各部丞参官制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442-057。最终该请求“奉旨依议”。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68 页。
需要指出,上述问题虽因裁撤书吏而起,但实际牵扯的问题已经超出六部官制,涉及到内官制的整体。在清朝的内官制中,九卿是六部司员后续升转的重要对象。裁撤九卿则意味着部员原有的重要升途被打断,以及内升外转体系被打破。另一方面,被裁的九卿将面临着安置的需求,而新设职官的六部无疑将是去处之一。因此,是否裁撤九卿成为制约六部普遍设置丞参的关键问题。
正因上述问题关系重要,在各方上呈说帖之前,政务处已先行商议如何处理裁撤九卿与六部设置丞参的关系问题。有消息称,政务处曾规划解决两个问题的先后次序,分清轻重缓急,提议六部先行“添设丞参”,再讨论裁撤九卿问题。⑥《裁撤九卿再志》,《大公报》1905 年5 月28 日第2 版。此后,政务处又筹划通过将六部丞参与九卿的人事对接,“九卿衙门之堂官由各部出身者仍回本衙门,授以丞参”,①《议设六部丞参详述》,《香港华字日报》1905 年7 月5 日第4 版。实现新设职官与裁撤旧署并举。尽管如此,政务处仍未就该问题作出决议,而需根据各方说帖的总体情况再做决定。
随后,各机构的人员陆续就六部设置丞参一事展开讨论并上呈说帖。六部设置丞参无疑会改变原来堂司直接的体制,引发堂官与司官权力关系、架构的重组。由于新设丞参对自身权力、利益的影响不同,六部堂官、司官对于设置丞参的意见有别,“闻各司员以为然者多,各堂官不以为然者较多”。②《各部添设丞参问题》,《时报》1905 年7 月7 日第6 版。其中,户部主事徐士瀛认为六部设置丞参有两大益处:一是丞参能完善旧的堂司直接体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可使各部职官的权责更加明确,乃整顿部务的关键所在。二是便于各部司员在本部升迁,有利于各部职官专门化。不过,六部设置丞参需要两个配套举措:一是仿照外务部、商部酌减堂官数额,减少相互牵制。二是专以本部司员升补,保证丞参来源的专门化。③徐士瀛:《上户部书》,《绶紫集》,出版者不详,1926 年,第123-125 页。
前面提到,设置丞参的本意是方便本部司员久任与升转。实际上,清朝旧的官制体系遵循内升外转的设计,六部、翰林院、卿寺、都察院等机构的职官因此存在升转的关联,“皆不能不出衙门”。④张亨嘉:《添设丞参议》,《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583 页。清朝通过职官在各个机构之间升转,既能在某种程度上保证职官之间的流动,又使得职官不断历练以积累行政经验,还可防止其在固定职位上结党营私。设置丞参则体现了各部上下贯通的用人专门化趋向,无疑会对清朝原来内升外转的官制产生强烈冲击。为此,翰林院编修陈伯陶在回复户部侍郎戴鸿慈的书信中,就对戴鸿慈赞同六部设置丞参的说帖提出异议。陈伯陶分析了内升外转与上下有序官制之间的矛盾,认为清朝内升外转的官制讲究总揽与综合,而基于专门化考虑而设置的丞参不适合讲究综合的官制,“今议以丞参升尚侍,盖冀其有益部务耳。然但知一部之益,此非惟不足任秉钧之重,即于所管部亦恐有覆餗之虞”。⑤[清]陈伯陶:《复戴少怀前辈书》,卢晓丽校注:《陈伯陶诗文集校注》,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329-330 页。
另一方面,清末新政开始之后,翰林院、卿寺、都察院等机构面临裁改的危机。在此情境下,各部官制的变革更加引起上述机构职官的担忧。在设置丞参之前,翰林院官员是各部堂官的主要来源。对此,时人总结称:“未设丞参以前,各司而上则侍郎矣,尚书、侍郎皆为翰林坐致之地,部曹无与焉”。在各部设置丞参之后,各部堂官的选任来源随之发生剧变,各部司员与翰林院官员的升途乾坤颠倒,“设丞参,取部曹之资深或外官之道府擢之,于是部堂始易人”。⑥《记部曹》,[清]罗惇曧著,孙安邦、王开学点校:《罗瘿公笔记选》,第254-255 页。翰林院官员的升转空间被各部司员挤压,导致“清望顿减,极盛而衰,亦其变也”。⑦《京官变局》,胡思敬:《国闻备乘》,第33-34 页。由于设置丞参对仕途升转的利害关系各异,翰林院与各部官员之间的意见截然对立,“闻翰林院开坊诸人均极力运动不设,以既设丞参,则翰林院升途更窄也”。⑧《翰林院阻设六部丞参》,《香港华字日报》1905 年8 月4 日第4 版。
其中,大学士孙家鼐就声称政务处会议“不以设丞参为然”。他认为,六部改造升转旧制就可实现所谓的官员久任与专门的目标,“郎中独不可径升侍郎邪”,不必有所更张。换言之,六部官员的专门、久任、升转与新设职官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受其影响,翰林院官员对六部设置丞参之事也是集体反对。在领会孙家鼐的意见之后,翰林院官员就如何写作说帖展开商议,其中“鞠农(指李傅元)欲作一总说帖,嘱恽薇生(指恽毓鼎)以此意叙入”。⑨[清]徐兆玮著,李向东、包岐峰、苏醒标点:《徐兆玮日记》第1 册,第499 页。而据翰林院侍讲恽毓鼎所述,此后翰林院的说帖是孙家鼐指令其撰写。恽毓鼎所写的说帖主要对设置丞参“设四说以驳之”,并且据说该说帖“寿州(指孙家鼐)颇赏其骏快”。①[清]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274 页。
光禄寺卿、大学堂监督张亨嘉则列举了设置丞参的三大问题:一是设置丞参以革除书吏旧弊并非对症下药。二是丞参的品级与部分京堂相同,体制则介于各部的堂官与司官之间,地位尴尬。在改变堂司直接体制后,丞参难以与堂官、司官划清权限,无法各司其职,只会给各部的运作制造障碍。三是设置丞参会改变内升外转的体制,阻碍内阁学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官升任六部堂官。如若实行兼顾各方的补缺利益的措施,则有违六部设置丞参的初衷。所以,张亨嘉提出参考刑部秋审处人员内升外转的旧制,实现六部用人专门化的目标,舍弃另外设置丞参的举措。②张亨嘉:《添设丞参议》,《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65 册,第583 页。
不同于上述观点,都察院兵科则认为,六部添设丞参是基于整顿部务考虑,并且外务部、商部已设丞参,必须要求各部官制整齐划一。不过,全由部员升任丞参有损京官之间升转的平衡。为此,都察院兵科提出了结合上下贯通与内升外转旧制的变通方案,六部设置的丞参“其叙补半取之本部郎中,半取之九卿”,③《兵科会议添设丞参呈都察院说帖》,《申报》1905 年7 月12 日第3 版。将丞参补缺的机会向九卿等其他职官开放,从而提升六部设置丞参的可行性。
事实上,此前御史与六部郎中同时可以保送四、五品京堂。各部设立丞参无疑会打破旧有京官升转体系的平衡,对于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续的升转难免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此,有说法称:“且各部设立丞参,皆自郎员以渐跻卿贰,惟御史终身沉滞,皓首台郎,才智之士视为畏途矣。”④[清]赵炳麟:《请改给事中为殿中侍御史疏》,黄南津等点校:《赵柏岩集》,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433-434 页。因此,都察院兵科新旧杂糅的方案,实质是协调用人专门与疏通仕途的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谋求自身的补缺利益。如此考虑周全,据称政务处王大臣“佥以为然”。⑤《兵科会议设丞参事》,《大公报》1905 年7 月23 日第2 版。
金钻明,长得白白净净,待人谦逊有礼。他一开腔说自己是上海人时,一楞后一喜,我们赶紧问他是上海哪里人?答曰:浦东杨家宅。坐落于如今浦东最繁华地段陆家嘴地区的杨家宅属浦东沿江地带,这和上海的开埠历史几乎是同时的。1986年出生的小金回忆,从懂事起,耳畔不时传来的就是机器的打桩声,以及拆房者、建楼者的身影。谈及儿时的成长,他最大的感受是自己居住地周围的环境一直在变,念书学校的场地也换了几次。这就是当年浦东大开发的速度。这段经历也让金钻明成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亲历者。
综上可见,由于设置丞参的利害关系各异,围绕六部是否设置丞参,不仅翰林院、寺卿、都察院与六部之间存在分歧,各部之内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总的来说,各方的意见可分为三类:一是赞成六部设置丞参,认为其有利于各部职官专门化。同时主张应该裁撤九卿,保证丞参只由部员而非九卿等升任。此外,需要裁减各部堂、司官员数量,取消满汉复职,以及厘清丞参与堂、司官员的权限,以此真正实现各部官员久任与专门的目标。二是反对六部设置丞参,认为设置丞参只是为部员提供升阶。其与堂司权责不明,反而增加行政层级,降低行政效率。并且会破坏原来的部院职官升迁以及内升外转的制度。为此,主张沿用或改良六部设置各司掌印、主稿或领办、提调的旧制,代替设置丞参以实现专门化的目标。三是提出折衷意见,认为六部在设置丞参之余,需要平衡九卿等与各部司员的补缺利益作为配套措施,平衡专门与升阶、内升外转与上下贯通之间的关系。
对于说帖中支持与反对六部设置丞参的总体情况,媒体的报道则有所不同。有媒体称,支持六部设置丞参的说帖占据多数,“统计说帖分为三类:(甲)主添设者;(乙)主不添设者;(丙)主添设丞参,请裁尚、侍各一缺,不分满汉者。甲类约占十之六,乙类约占十之四,丙类不及十之一”。⑥《添设丞参议分三类》,《新闻报》1905 年7 月19 日第2 版。不过,由于各机构针对六部设置丞参问题的说帖数量众多,媒体也难以探知其中准确的比例。与上述报道相反,有媒体则声称,反对六部设置丞参的人员占据多数,“大约主不添设者约十之七,主添设者十之四,丙类则不及十之一”。⑦《记政务处添设丞参之说帖》,《时报》1905 年8 月2 日第6 版。可见,各机构针对该问题的态度存在着明显分歧。结合现有材料以及后续政务处的行为来看,官员中反对六部设置丞参的比例应该占据多数,导致政务处无法根据说帖的总体意见立即作出决策。
总体而言,各种意见分歧的实质,在于六部职官是否需要专门化以及如何保证专门化。是设置丞参增加职官层级实现上下贯通以保证专门化,还是沿用并改良堂司直接、大小相制、差遣与实职分离以及内升外转的旧制以保证专门化。设置丞参需要哪些配套举措,尤其是如何确保丞参来源的专门化,其背后很大程度是各机构职官的升迁利益问题。这也成为此后丙午官制改革亟待回应的问题。
三、丙午官制改革与各部设置丞参
清末预备立宪,清朝确立了仿照日本进行官制改革的方针,首当其冲的是内官制改革的问题。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初六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会衔上奏,二人认为清朝六部与日本的中央官制相比缺乏“辅佐官”的角色,“至新设各部特置丞参,尚有辅佐之意,他部则惟有郎、员。郎、员分掌各司,实如日本诸省之各局局员、各课课长,不可谓为辅佐官也”,由此导致各部书吏弄权。为此,改变满汉复职、大小相制的职官体制而设置辅佐官,是彻底解决书吏弊端的最佳方式。二人提出改革各部官制的两套方案:一是完全仿效日本的中央官制,将各部尚书、侍郎改为大臣、次官。二是仿效新设各部的事例,设立一尚书、两侍郎,并改变堂官相互牵制的权限、职能,“以尚书为主任官,而侍郎为之辅佐,受其指挥”。在此设计理念的基础上,“更设丞参各官”,将丞参等与日本中央官制的职官逐一对应,并据此划定职权,“丞如日本之参事,专主审议、立案;参议如日本之局长;郎、员如各课”。①戴鸿慈、端方:《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胡绳武主编:《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第3 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372 页。
事实上,日本中央官制各省由上到下一般分为省、局、课三个层级。参事官则是设置于内阁官房、大臣官房或各局的政务官,起到辅助长官的作用,与各局局长等事务官并无明确统属关系。如此一来,该方案“丞”的定位与此前新设各部左右丞的作用不同,其与参议、司官的权限关系也存在差别。该方案通过中外、新旧制度的杂糅,在清朝没有彻底仿效日本官制的情况下,向日本等立宪各国的中央官制靠拢,促使各级职官上下有序、权责分明。“内而丞、参、郎、员”,“凡就任者必先策其悠久之功,始不致有置棋之诮”,进而实现用人专门化的目标。在附上的“中央政府官制”办事权限大略中,二人强调,新旧各部“按部务繁简,各设丞参、司员等,分理庶务”。②戴鸿慈、端方:《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胡绳武主编:《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第3 册,第382 页。其对各部丞参的编制未做划一要求,而是提议根据各部的实际情况处理。
随着七月官制改革的展开,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模式下,无法妥当安置的九卿等机构面临裁撤的问题。在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被正式并入礼部的情况下,裁撤寺卿的目标部分得以落实,从而为各部设置丞参扫除了重要的外围障碍。另一方面,该时期的官制改革方案确定保留翰林院、都察院等机构。已设丞参的各部,也向卿寺、翰林院等机构的官员提供选任丞参的机会,③参见拙文《丞参选任与清末部院用人专门化问题》,《清史研究》2021 年第4 期。平衡专门与升阶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落实了上阶段讨论六部设置丞参的折衷方案。各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上述机构官员反对各部设置丞参的压力。
清朝随后的内官制改革方案,主要是在戴鸿慈、端方奏议的基础上讨论修订的。据媒体披露,厘定官制大臣在此期间反复讨论“汰尚书、侍郎之缺额,裁冗员,设丞参”等官制改革之事。④《会议厘定官制要闻》,《大公报》1906 年9 月10 日第2 版。其中,编纂官制大臣载泽更是力主在各部设置丞参,对此起到重要作用。据称,各部设置尚书一人以及左右侍郎、左右丞参,不分满汉,该方案由载泽“领班奏明两宫先行办理”。⑤《部缺议定纪闻》,《大公报》1906 年9 月18 日第3 版。有消息则称,在讨论各部官制的过程中,载泽积极主张仿效新设各部官制,“拟编各部两侍郎,外设丞参”。⑥《本馆特电》,《香港华字日报》1906 年9 月22 日第4 版。
期间,各方围绕设置丞参问题主要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各部仿效外务部等新设部院的官制,改为一尚书、二侍郎,并且设置左右丞与左右参议,取消满汉复职的职官设置。⑦《电报一》,《时报》1906 年9 月27 日第3 版。二是部分仿效日本的内阁官制,将各部尚书、侍郎分别改为大臣、副大臣,同时保留丞参设置,新旧、中外制度杂糅。①《各部尚书侍郎改为大臣下设丞参》,《香港华字日报》1906 年9 月27 日第2 版。三是全盘仿效日本的内阁官制,各部职官除了改设为大臣、副大臣以及各局局长之外,取消丞参设置,转而仿照日本各省大臣官房的规制。②《京师近信》,《时报》1906 年9 月28 日第2 版。
九月,清廷正式颁布《各部官制通则》,在“分职以专任”的原则下,规定各部设置的职官包括左右丞、左右参议以及参事等。同时指出,外务部等设立的丞与参议“阶级虽分,事权无别”,应进一步为二者设置专门的办事机构,“故特设承政厅,使左右丞任一部总汇之事;设参议厅,使左右参议任一部谋议之事”。在此基础上,更加明确划分各部丞与参议的权限、职能,改变新设各部中二者“事权不明,尚多窒碍”的局面,作为对上阶段丞参与堂官、司官权责关系争议的回应。上述举措可使丞与参议的功能更加实际、专门,而非主要为升途所设,符合各部官制改革权责明确与专门化的取向,“此分职专任之大要也”。⑤《庆亲王奕劻等奏厘定中央各衙门官制进呈折》,胡绳武主编:《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第3 册,第515 页。
对比《阁部院官制节略清单》可以看出,左右参议的权责由原来制定各部规章制度的“立法之事”改为“谋议之事”,⑥奕劻:《呈拟厘定阁部院官制节略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284-044。与戴鸿慈、端方奏议对应日本中央官制确定丞与参议的功能不同。可见,厘定官制大臣对于丞参的权责划定仍存分歧,并且期间曾作出调整。为此,各部甚至试图按照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模式划定内部职官的权限,“本部大臣司法,丞参行法,郎中以下立法”。⑦《各部官制权限纪闻》,《大公报》1906 年10 月17 日第2 版。实际上,各部丞与参议原先的职能区分,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部院职官内部“行政”与“立法”的权力分别。后续的修改方案则更多体现了二者在“行政”下的配合。此举应与官制改革将各部定位为三权分立体系中的行政机构相关。正因如此,有说法称,各部承政厅兼有“行政、司法之性质”,而参议厅则兼有“立法、行政之性质”。⑧《会议改定官制详确情形》,《香港华字日报》1906 年10 月25 日第4 版。上述现象体现了丞参设置并未直接对应日本的中央官制与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设计,而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清朝此前官制偏重行政的设计理念。相比于日本基于分类的扁平化职官设计,清朝的丞参由于其提供升阶的作用,更多是基于分层的垂直化职官设计,同时承担了更多行政的功能。
《各部官制通则清单》则明确了丞参的编制与具体职责。规定左右丞各一人,“承尚书、侍郎之命,总核承政厅兼考核各司重要事务”。具体负责的事务包含各部原先由各司掌印、主稿以及堂主事、司务厅、档房等负责的人事、文书、财务等庶务。实际是将原来分散到部内各机构的重要事务,以及清末新政后各部新的人事、财务自主权集中管理,收归于上。另一方面,左右参议各一人,“承尚书、侍郎之命,总核参议厅事务兼审议各司重要事务”。⑨奕劻:《呈各部官制通则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284-043。主要负责处理各部的章程条文。实际上由丞参代替各司主稿、书吏等担负制定章程等权责。
上述条例实际是根据此前新设各部的相关章程、实践,同时结合日本中央官制中“参事官”“秘书官”的权责而定,在各部新增兼有总汇、辅佐功能的职官与机构。某种程度上来说,上述举措是调整各部的内部架构与相互关系,将原来各部之内与各司平行的机构、职官或差遣,整合为承上启下的机构与职官,使各部职官体系由大小相制转为上下有序。
值得注意的是,《各部官制通则清单》还借鉴此前学部的做法,在丞参之外设置了参事一职,规定参事“承尚书、侍郎之命,佐左右参议审议拟稿”,而且参事“可视各该部情形,由尚书派令助理承政厅及各司事务”,①奕劻:《呈各部官制通则清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9284-043。主要起到辅助丞参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丞参与参事皆“承尚书、侍郎之命”,可见参事与丞参三者虽然品级存在差别,相互之间却无统属关系,甚至职能还存在交叉与重合。其相互关系更多是品级的上下有序,而非职能上的明确统属。“参事”在清代以前主要是一些特殊官职,此处是借鉴日本中央各省所设的参事官一职。前述的戴鸿慈、端方奏议是以各部的左右丞对应日本的参事官。与之不同,此时各部则是在丞参之外另设参事,而且其与丞参并无统属关系,显示清朝有意进一步仿效日本分类设置的官制内容与设计理念,与自身现有分层设置的制度相辅相成,体现了中外、新旧官制杂糅的特点。
在清廷颁布《各部官制通则清单》后,各部基本以此为基础设置丞参,作为清朝无法彻底仿效日本内阁官制的折衷举措。只是,各部对于丞参权责的规划不一,实际的职能有别,因而丞参机构的设置亦不同。②参见刘文华:《丞参设置与清末官制改革》,《宁夏社会科学》2023 年第2 期。其中,陆军部、礼部等甚至起初在其官制草案中并未规划设置丞参。该过程中清朝为了划一官制而忽略各部的实际情况,成为影响此后各部丞参不同命运的重要因素。设置丞参新旧、中外制度杂糅的特点,也为清季试行新内阁官制而出现裁撤丞参呼声埋下伏笔。
四、新内阁官制与裁撤丞参的纠葛
在光绪三十二年各部普遍设置丞参后,因认为设置丞参无用,御史黄瑞麒、赵熙等人曾先后奏请裁撤丞参。此后,陆军部拟订的新官制使丞参存废问题成为焦点。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宪政编查馆等厘订的陆军部暂行官制,强调该部相比于其他各部讲求运作效率的特殊性,“务使阶级较少、事类相从,一洗从前牵制、推委之习”。陆军部由于职官“责任宜专”,必须改变此前的官制,原设之尚书、左右侍郎、左右丞参“均拟一并裁撤”。③《为厘订陆军部暂行官制大纲列表呈进一折尚书侍郎左右丞参各缺着即裁撤改设陆军大臣副大臣等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全宗》,档号:05-13-002-001002-0078。该部转而全盘仿效日本陆军省的官制,改设为陆军大臣、副大臣各一员。言下之意,设置丞参只会使该部职官层级过多,出现上传下达不顺畅以及运转效率低下的问题。增加职官层次与讲究专门、高效的官制要求并不相符,需将职官由分层的垂直化设置改为分类的扁平化设置,进一步追求专门与高效。
陆军部的新官制随后被海军部效仿,并引发了舆论的关注以及各部的恐慌。随着清朝修订新内阁官制被提上日程,在丙午官制改革的基础上,清朝试图进一步仿效日本的内阁官制,由此开启了内官制新一轮的改制。其中,各部是否仿效陆军部官制而裁撤丞参,职官由分层设置改为分类设置,进一步追求专门化与效率,成为改制的重要议题。
受制于新内阁官制的不同设计方案,关于各部是否裁撤丞参以及如何裁撤丞参,清朝内部存在不同声音。除了部分官员主张丞参等职官仍旧之外,总体来说,各方裁撤丞参的方案主要有二:一是将各部丞参全部裁撤,但为其安排出路。其中,地位显要的左丞借鉴日本官制“即改为本部秘书官”,而右丞与左右两参议则听候考试,再根据考试结果予以不同安排,合格者降级“以郎中补用”,不合格者“概作为裁缺之员,不再任用”。④《京师近事》,《申报》1910 年12 月9 日第6 版。该方案无意中调整了丞参原先的权责关系与内部架构,使其在贴近日本官制设计的同时,又保留了某些清朝原来部院职官的设置特点。二是全盘仿效日本的内阁官制。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李家驹提出的方案,各部的丞参与尚书、侍郎等“一律在裁撤之列”。裁撤上述职官之后,各部的尚书、侍郎“改为大臣、副大臣”,郎中、员外郎等则改为“一、二、三等科员”。①《京内外新官制内容纪要》,《申报》1911 年1 月3 日第5 版。各部的其他职官可在新内阁官制中改换名目,重新定位。而由于无法与日本官制的职官对应,丞参被裁撤之后如何安排则无明确方案。
不难看出,上述各方案的核心区别在于,在新内阁官制中是否为丞参保留位置以及如何安置,其背后则是各部官制的体系与功能的定位区别,即职官是垂直化的分层设置或扁平化的分类设置。
不过,裁撤丞参在清朝高层内部阻力重重。据媒体报道,宣统二年十一月,政务处在会议各部新官制时,对于裁撤丞参问题,“泽公(指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沈云沛(时任邮传部右侍郎)、那相(指那桐,时任军机大臣)均不认可”。②《政务处会议纪闻》,《申报》1910 年12 月22 日第4 版。有媒体则披露了具体的消息,针对裁撤丞参的问题,载泽主导的度支部“反对最力”。作为丙午官制改革力主各部设置丞参的主要人物,度支部尚书载泽反对裁撤丞参,与度支部丞参的职能特殊以及丞参上行走人员众多密切相关。与普通部院的丞参不同,度支部丞参还兼充清理财政处、币制局的提调、帮提调,并与外务部丞参同时兼充税务处提调、帮提调等。③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119,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3454、3450 页。清理财政处作为清朝清理各省财政的关键机构,币制局则是负责币制改革事宜的机构,可见该部的丞参权责重要。受其影响,其他一些部院也纷纷反对裁撤丞参,“而外、邮、农三部因亦随同附和”。④《京师近事》,《申报》1911 年1 月7 日第6 版。尤其是此前被御史胡思敬弹劾与舆论指摘的邮传部,“其于丞参一缺保全之甚力”。在上述部院的抵制之下,各部尚书“亦因此见好,决不加以裁抑”。⑤《新官制竟有如此阻力》,《申报》1911 年2 月24 日第5 版。
日本的内阁官制讲究职官的分类与精简。不过,对于上述各部而言,在新内阁官制可能诱发新一轮人事变动的背景下,尽可能避免所在部院的人员被裁撤,减少因人事变动导致内部出现混乱,从而维系行政事务的正常运转,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由此可见,如何在新内阁官制中平衡整体改制与特殊需求之间的关系,避免过分损害各部的具体利益,尤其是丞参人员众多的部院的利益,成为新内阁官制裁撤丞参能否凝聚共识、顺利推行的重要因素。
宣统三年(1911)四月,清朝成立暂行内阁,并由其主持修订新的内官制。经过一番讨论,新内阁官制规定将各部尚书改设为大臣,而各部大臣与总、协理大臣均为国务大臣,成为内阁成员。各部长官之间的权力关系进一步发生转变,并且由于中央集权的需要更加注重行政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的内阁官制中各省只设副大臣一人作为行政次官,而清朝原先各部则设有侍郎二人。丞参则作为丙午官制改革时期清朝无法直接仿效日本内阁官制的折衷举措,无法在日本的内阁官制中找到直接对应的职官。因此,该时期影响丞参等是否裁撤以及如何裁撤的关键,在于采用何种内阁官制方案。具体而言,即是否将丞参与尚书、侍郎等作为旧制视为一体,从而与后者的改制一并进行。同时,改变上述职官的职能,重新理顺各部职官之间的权限关系。另外,此前各部设置丞参更多是为了安置官员以及为官员提供升途,而非出于简单的专门化职官考虑。因此,在新的内阁官制实施后,如何平衡各部职官精简与功能充实的关系,妥善安置各部丞参,也是影响丞参是否裁撤以及如何裁撤的重要因素。
不过,对于新内官制中各部裁撤丞参一事,度支部、外务部等“已决计不认裁汰丞参办法”。度支部尚书载泽与外务部尚书邹嘉来讨论,认为两部事务繁难,必须受到特殊对待,⑥《外务、度支两部均拟添设顾问》,《大公报》1911 年4 月19 日第5 版。以此作为共同反对裁撤丞参的理由。在此期间,相关各部相互联络,集体行动,以此向清廷施加压力。正因度支部、外务部与邮传部极力反对裁撤丞参,导致此事成为新内阁官制中“实为极难解决之问题”。为了平衡部分部院的特殊诉求与新内阁官制整体改革的需要,清廷高层被迫提出“变通办理”的折衷方案,对应日本内阁官制的职官名称,将丞参一律改为“参事”,改换门面,并准许其照常办事。在新内阁官制中暂时保留该项职官的权力与地位,仅在形式上作出改变,以此向相关各部作出让步。作为临时举措,“此制即附订于暂行章程之内”。①《略更名称之新内官制》,《大公报》1911 年5 月19 日第2 版。
实际上,对于新内阁官制是否裁撤丞参、右侍郎等事,清廷高层内部存在严重分歧。据称,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副大臣寿勋对裁撤丞参“主张尤力”,而陆军大臣荫昌则“极力折驳,以为非宜”。针对各方争执不下的局面,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只能“从中调停”,该问题因此“卒未决议”。②《要电》,《时报》1911 年5 月26 日第3 版。此后,裁撤丞参等问题虽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核定为“必行之件”,但是各国务大臣对此“仍多不置可否”。其中,邮传大臣盛宣怀继续奏调丞参,“以表示其不裁汰之意”,借此展现出抵制裁撤丞参的态度。不仅如此,盛宣怀还准备联合此前一直反对裁撤丞参的度支大臣载泽,共同“与内阁抗议”。③《邮部不认新制之裁汰》,《大公报》1911 年6 月7 日第3 版。正因如此,尽管总理大臣奕劻与协理大臣那桐皆主张裁汰丞参,但由于邮传大臣盛宣怀、度支大臣载泽“仍主张保存”,该问题“故极为纠葛”。在此情形下,奕劻等人被迫将该问题提交摄政王载沣决断。对于该问题,载沣认为各部应在精简机构与充实职官之间寻求平衡。针对部分部院极力反对裁撤丞参等事,载沣提出“所有政务较难之各部似可通融办理”。实际上默认新内阁官制对于特定部院可以特殊对待,根据各部具体需要而定,不必强求各部一律裁撤丞参。由于摄政王载沣态度暧昧,“惟一时尚不知有何调停之法”。④《监国对于新官制之调停》,《大公报》1911 年6 月10 日第2 版。是否裁撤丞参以及如何裁撤丞参的问题仍悬而未决。
在此期间,针对裁撤丞参问题仍争执不下的情况,各方又主要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改易丞参的名目。其中,由于陆军部设有参事,而海军部参照日本官制设有参事官、秘书官。因此,有人提出,将各部丞参对应日本官制改为“参事”“秘书官”等名目。使其仅是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于权利毫无损失”。⑤《本馆专电》,《新闻报》1911 年6 月14 日第5 版。与上述方案相似,有人则提出,将各部丞参分别改设为“一、二等参事”,与各部副大臣等新职官“同理部务”。以上作为暂行章程,“候各部务清理就绪,再行裁撤”丞参。⑥《各侍郎有仍得保存之耗》,《大公报》1911 年6 月25 日第5 版。实际上,日本内阁官制中的“参事官”“秘书官”等职官建立在政务官、事务官的区分基础之上。二者与各局局长皆属于“荐任”官,相互并无上下统属关系。其区别更多是职能的分类而非级别的高低,其级别、权限、职能与清朝各部的丞参并不相同。因此,上述方案强行将丞参与日本内阁官制的参事官等职官对应,并不讲求二者在整体官制中地位、作用与性质的差别,实际上是寻求其在新内阁官制存在的合理性。二是将各部的丞参与右侍郎一并裁撤,但妥善安置上述裁撤的职官。其中,有人提出,保留各部裁缺的右侍郎、丞参原先的品级等待遇,“拟暂赏原俸,以对品行政官简放”。⑦《本馆专电》,《新闻报》1911 年6 月23 日第5 版。有人则提出,裁去左右丞而保留两参议,在新内阁官制中寻求其合适的位置。借鉴原来各部承政厅、参议厅的设置,在各部新设总务厅,“即以各该部参议充参议,各该部丞之一充厅丞”。⑧《改订官制之大意》,《申报》1911 年8 月14 日第4 版。从而避免全部裁撤丞参引起反弹,减轻改制的压力,使得新内阁官制得以顺利实施。
可以看出,由于丞参等官员品级较高,影响较大,能否事先设计妥善的安置方案成为制约裁撤丞参问题的关键。随着吏部、礼部等被裁撤机构的丞参得到安置,该问题一度出现进展。此后甚至有消息称,清廷要求各部官制原则上不设丞参,“均暂按海、陆军部成例办理”。不过,在辛亥革命爆发的现实情况下,丞参等“亦暂行参赞”。⑨《谕交各部暂照章办事》,《大公报》1911 年11 月22 日第5 版。清朝的新内阁官制并未彻底完成改制,裁撤各部丞参的问题被迫搁置,直到民国肇建之后才真正完成。
在南京临时政府新的《各部官制通则》中,规定各部分别设立总长、次长、参事、司长、秘书等职官。其中,各部设参事二至四人,“承总长之命,掌拟订及审议法律命令案事务”。此外,各部设秘书四人,“承总长之命,分掌总务所事务”。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政治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11 页。原先各部丞参的职能被新的参事、秘书等职官代替,在某种程度上落实了此前清朝新内阁官制裁撤丞参的方案。虽然此后受政治体制变动的影响,北洋政府一度在政事堂中恢复了丞参的设置,并且不时有声音传出,北洋政府还有意在各部取消参事、秘书等职官,转而恢复原先丞参的设置。即职官从分类的扁平化设置,改回分层的垂直化设置,但上述想法一直未能实现。丞参作为清末官制改革寻求专门化的过渡,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结语
清末丞参设置兼具升阶与专门的功能。在清末官员众多而不少机构的官员面临裁撤的情况下,丞参提供升阶、安置的功能愈加突显。如此一来,机构精简与充实职官如何平衡始终困扰着清政府。该问题也是此后丞参兴废的过程中,清朝始终无法直接仿照日本中央官制的重要原因。
清朝六部各司的“掌印”“主稿”与其他司官存在实际地位差别,户部、刑部的北档房、秋审处等机构的总办、领办等更是如此。上述差遣与各司官员之间并无统属关系,形成了各部官制的差遣与实职、权重与品级分离的格局。各部通过上述差遣,在保障“熟手”之外可以体现官员的资历差别与某种升转,是“阶官化的过程”。②郑小悠:《清代刑部司官的选任、补缺与差委》,《清史研究》2015 年第4 期。丞参兴废无疑是各部职官体系“阶官化”变为实职化的重要过程。同时,也是将原先各部内部的机构、职官、差遣以及各部之外的临时机构、差遣,整合为新的机构、职官的行为。以此使其从原来的权限模糊变为职能明确,从叠床架屋变为结构清晰,从大小相制变为上下有序,从堂司直接变为承上启下。
上述过程的背后,是从传统的六部体制到近代仿效日本等实行新的各部官制的过渡。只是,在丞参兴废的过程中,清朝未能完全处理好中外、新旧制度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改变原来堂司直接的体制之后,是仿照清朝原来设置各种领办、总办的旧制,还是借鉴日本的参事官、秘书官的设计理念;丞参设置与裁撤是建立在职官分层的垂直化体制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政务官、事务官分类的扁平化体制基础上,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由于丞参提供升阶以及更多承担行政功能,丞参设置无法完全对照日本参事官、秘书官等政务官。丞参的层级、架构与职能、效率难以协调。同时,在丞参兴废的过程中,清朝未能处理好丞参整体改制与各部不同情况的关系,尤其是平衡新设、改设与旧有各部之间对于专门化的不同需求。在清末对改制的迫切需求之下,清朝为了从整体寻求改制的声势或象征性意义采用一刀切的举措,而未能在其中找到适合不同部院的精准差别化方案,导致官制改革专门化的进程充满曲折。
在内官制的整体改革下,各部丞参的兴废还涉及部院与卿寺、翰林院、都察院等机构职官的关系、地位问题。清朝旧的内升外转体制是建立在防弊、历练以及现实中官员众多迁转需时的基础上,同时其升转次序也体现了不同机构、职官之间的地位差别。在讲求实用、专门的上下贯通体制中,各部丞参迅速、直接升转则对该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原来翰詹、科道与部员内升京卿、外放道府的体制亦被打破。其本质是内官制的架构、职官地位、升转体系的重新划分。在丞参兴废的过程中,与卿寺、翰林院、都察院等偏务虚的机构地位衰落不同,具备实用功能的部院在内官制的地位则不断提升。传统的建立在皇朝体制下的六部官制与内官制,随着近代的政体变迁,其立意、体系、架构随之发生不可逆转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