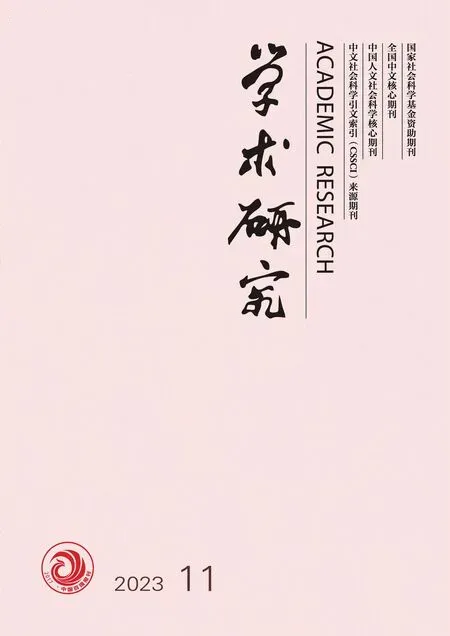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田 澍
尽管“晚明”是明史研究中常用的一个术语,但使用较为混乱。其中,影响较大的观点是把张居正去世的万历十年(1582)作为晚明的起点。如果此论成立,那首先得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幼主神宗的即位和张居正的病逝哪一个事件对神宗政治的影响更大?换言之,张居正去世所造成的政治震荡是万历初政的正常表现还是异常反映?如果说是正常表现,那就无关紧要;如果是异常反映,那就说明张居正根本没有尽到顾命辅臣之责,没有使已经20 岁的神宗有能力正常行使皇权。换言之,张居正没有将神宗培养成“圣君英主”,未能完成穆宗的遗愿。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转移话题,一味地放大张居正“改革”成效和去世的负面作用,很少顾及张居正如何结束顾命时期的非正常状态。被张居正架空的神宗皇权需不需要恢复常态,这是认识万历初政的首要问题。只有以神宗即位后皇权的弱化为视角,才能认清张居正与晚明政治的关系和把握晚明政治的走向。
一、“晚明”:一个具有争议的概念
“晚明”在中国历史演进中具有独特性,晚明史是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之一。在不同时代,学者根据自己面临的问题,各取所需,截取其中的一点或一个方面对晚明史进行不同的解读。如有的学者从亡国的角度来认识晚明,有的从政治腐败的角度来考察晚明,有的从生产关系变化的角度来解析晚明,有的从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的角度来认知晚明,有的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审视晚明,有的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观察晚明,有的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解读晚明。正如高寿仙所言:晚明“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充满了张力和矛盾。从中既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可以看到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既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又可以看到结朋结党的宗派混斗;既可以看到改革志士的励精图治,又可以看到官僚群体的腐败无能;既可以看到个性的空前张扬,又可以看到欲望的极度膨胀”。①高寿仙:《变与乱:明代社会与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333 页。正是由于解读晚明的视角不同,故观点各异,认识不一。周明初就此论道:“晚明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它的划分依据是什么?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晚明就不是一个确切的时间概念。一般学术界把万历到明代灭亡前这一段时期看成是晚明时期。但是,晚明是不是就从万历元年开始,万历之前的某段时期,如隆庆时期和嘉靖后期算不算晚明时期?谁也不能作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因此,所谓晚明又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时间概念,它没有明确的时间断限。”②周明初:《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年,第1 页。解扬亦言:“晚明是个难以一言以蔽之的时代,相信科学地深入其中的研究者都会感到头绪纷乱。不少概念工具用于研究现代社会尚能清晰有效,一旦用于解释晚明,研究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有言不尽意,甚至文不对题的困惑。”③解扬:《话语与制度——祖制与晚明政治思想》,北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1 年,第2 页。
晚明之“晚”,既指明朝政治腐朽、衰败之意,标志着当时皇权的弱化和政治的混乱;又指明朝经济与思想文化等方面兴旺、蓬勃之意,代表着明朝的生机与活力。换言之,就是晚明政治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极不适应,互不匹配,政治上的腐败无能与具有新因素的社会转型形成了明显的错位。而晚明经济结构的新变化、商业的空前繁荣、白银的大量流通与国家货币银本位的确立、工商业城镇的勃兴、消费的奢华、早期启蒙思想的萌芽、以人性解放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实学思潮的兴起、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与反应等全新的现象,与历史上各朝各代亡国时期的政治景观明显不同,故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并从多方面予以审视。如王天有认为:“从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算起,到天启七年,仅仅四十五年。四十五年中,明王朝由振兴到衰微,进而趋于崩溃,国势急骤转变。东林党人顾允成在万历时已称‘天崩地陷’的时期已经到来。清代史家论及明朝衰亡时,也往往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可见这一时期是攸关明朝存亡的重要时刻。”④王天有:《王天有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5 页。樊树志认为:“王阳明的大声呼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此后,人才辈出……思想界流派纷呈,讲学之风盛行,互相辩驳诘难。有了这样的氛围,使得西方科学文化得以顺利地传播、弘扬,培养出了一大批放眼世界的先进中国人。”⑤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6 页。张春树、骆雪伦则认为:“晚明的社会经济变化给明代社会制度结构带来转变,同时转变的还有生活在其中的不同人群的行为和态度。而且随着这些变化,属于明代社会的儒家基本构造的某些文化和道德操守也逐渐遭到破坏。”⑥张春树、骆雪伦:《明清时代之社会经济巨变与新文化——李渔时代的社会与文化及其“现代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116 页。
正是由于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晚明,故在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述这一特别而复杂的问题,而起始的时间自然也就各不相同。如沈定平用“明中叶以后”“明中叶后”“明末”“明朝末年”等概念来称呼正德以后的明代历史,将王阳明的“心学”与明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⑦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第525-527 页。赵轶峰认为:“自明代中叶书院讲学之风盛行,知识分子普遍喜好游学、结社,至明末为最甚。但晚明党社中人,或以才学,或以道德相标榜,其所关切的实际仍是庙堂中事。”⑧赵轶峰:《明代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年,第82 页。周振鹤以“晚明”为大时段,“明末”为小时段,说道:“晚明社会是黄宗羲所谓的‘天崩地解’的时代,追求人的正常生活以至于个性解放成为文人的生活目标,因此许多文人不再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头,而是走向大自然,走向气象万千的社会,将自己融合在天地人群之中,有人并且以己为宾,以自然与社会为主,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形成多种多样的、超越前人的精彩游记。这些游记有相当大的普遍性,而且越到明末,这类游记的数量越大。”①周振鹤:《晚明文人与旅游风气》,郑培凯:《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170 页。徐泓将“嘉靖至崇祯122 年”称为“明代后期”,也称为“明末”。②徐泓:《明代社会转型之一——以江浙为例》,郑培凯:《明代政治与文化变迁》,第108-109 页。巫仁恕将“晚明”与“明中叶以后”“明朝后期”“明季”混用,但通观全书,其所指的“晚明”应该是指嘉靖以来的明代历史。如言:“明代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约当16 世纪以后,各地的方志中都反映出平民服饰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改明初朴素守制的情形,而走向华丽奢侈,甚至逾越礼制。”③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125 页。张显清在《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将明代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从洪武至天顺(14 世纪中叶至15世纪中叶)为前期,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时期;从成化至正德(15 世纪中叶至16 世纪初叶)为中期,是社会转型苗头出现时期;从嘉靖至明末(16 世纪初叶至17 世纪中叶)为后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并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并明确指出:“在本书中,有时也将明中期称之为‘明中叶’,将明后期称之为‘晚明’。”④张显清:《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3 页。刘志琴明确指出:“晚明时期,一般是指嘉靖末年、隆庆、万历、天启和崇祯王朝,为时不足一百年,其中尤以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朝最令人瞩目。”⑤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年,第3 页。陈宝良也说:“追溯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变动,尽管已经萌芽于明代中期,但还是以万历以后最为明显。”⑥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410 页。王家范则认为“万历后期至崇祯末”是晚明时代。⑦王家范:《晚明江南士大夫的历史命运》,《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396 页。高寿仙在梳理晚明研究后认为:“‘晚明’并非一个严格的断代概念,有人将其收得很窄,仅限于天启、崇祯两朝,也有人将其放得很宽,从成化、弘治一直延续到南明。较为通行的用法,是指万历至崇祯这一时间段。当然,历史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没有明显的起点和终点,晚明时代呈现的诸多现象和变动趋势,的确可以上溯到明代中叶,下延到清朝时期。”⑧高寿仙:《变与乱:明代社会与思想史论》,第333 页。但一味地上溯晚明的开始时间,并无多大意义。
在晚明史的早期研究中,主要聚焦于探究明朝亡国的原因。《明史》的作者认为:“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光宗潜德久彰,海内属望,而嗣服一月,天不假年,措施未展,三案构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⑨[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神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294-295 页。此论是否有理,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和不同解读。孟森认为:“神宗的怠政,是晚明政治败坏的根源,从万历十年起,神宗深居简出,和外廷隔绝,有几十年不上朝听政。”⑩李文治:《晚明民变》,北京:中华书局、上海:上海书店,1989 年,第1 页。李光璧论道:“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从万历十七年后就不上朝,在宫中吸食鸦片,纵情声色,直到万历四十三年才因为‘梃击’事召见群臣一次,以后仍旧不上朝。”他在描述“万历天启间的城市市民反抗矿税监的斗争和白莲教起义”时则使用“明末”或“晚明”,大概以万历二十年以后为开端。⑪李光璧:《明朝史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135、148 页。韦庆远则明确指出张居正的去世标志着明朝政治进入混乱状态,说道:“如果说,隆万时期为期十多年的大改革运动,曾经扭转了明代自正统年间以来由治入乱的趋势,一度出现过由乱入治的兴旺前景,那么,自张居正死败,大改革运动戛然停顿,各方面政策截然倒退,政局陷入混乱,又进入了由治入乱的恶性循环之中。”⑫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859 页。神宗在位48 年,万历前期又有所谓的“张居正改革”,故一些学者认为要说明朝“亡于神宗”,那只能说是亡于张居正之后的神宗时期,以便突出张居正功绩,否则就无法讲述“张居正改革”,更无法凸显张居正“改革家”的作用与地位。
假如“万历至崇祯”为晚明时期,那就必须搞清楚“万历”是指神宗称帝后的时代,还是改元后的时代。谢国桢将神宗即位至崇祯亡国划为明朝“已经由衰微逐步趋于崩溃”的阶段,认为“万历四十余年间,社会的情况,是由于统治者的‘好货成癖’贪婪无厌,就从暂时的小安,很迅速地转变为外患纷起,社会动荡极不稳定的局面”。①谢国桢:《南明史略》,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年,第6 页。章嵚认为党争是明亡的一大主因,“其祸要自居正当国始之”,“居正以前,言官所争者为公是非;居正以后,则所争者为私是非矣!”②章嵚:《中华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年,第1229 页。黎东方也认为:“党争的根源,是内阁与六部的权力问题。张居正当国之时,把六部的实权归入内阁。张居正一死,六部便颇想从内阁手中,取回原有的实权。而六部之中,对内阁首当其冲的,便是吏部。”③黎东方:《细说明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309 页。司徒琳也认为:“这个首辅位置连对最柔顺谦和的在职者都是座烤炉,而且得随时充当皇帝过失的替罪羊。有谁试图经过那个公职向政府施加真正的影响,必受弹劾,理由不外是乘危篡取特权,或把皇帝引向堕落。的确,它就是首席大学士张居正(1525 ~1582)果断的行政改革由高涨到激起‘反行政机构’运动的同一理由,后者是由明末‘东林’社团所领导的。”④司徒琳:《南明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年,《引言》第10 页。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明季党社考》中认为,虽然在万历初年不存在成为东林党的团体,但是,“抵抗要把权力集中到内阁的张居正的势力逐渐形成,顾宪成等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批判的是,张居正的夺情,以及张居正为了确认行政、财政改革而施行的考成法。”⑤[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李庆、张荣湄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370-371 页。尽管以上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将张居正与晚明政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明亡于万历”中的“万历”,既可以理解成万历时代,也可以理解为神宗时代。一般而言,人们将其理解为万历时代。如樊树志在《晚明史》中直言:“本书论述的晚明史,起自万历元年(1573 年),迄止崇祯十七年(1644 年)”,认为“晚明中国在经济、文化上融入世界之际,一个固步自封的王朝不仅不可能把握机遇,反而是加剧了自身内在矛盾,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中几乎没有不争之时。”⑥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 年)》“内容摘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何宗美也说:“晚明指从万历初年(1573)到崇祯末年(1644)这一历史时期,包括七十二年,它是明王朝在衰落中挣扎并走向灭亡的最后阶段。”⑦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71 页。这些说法均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神宗即位的时间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而不是万历元年正月。很显然,将隆庆六年六月至十二月不计入神宗时代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二、“顾命”与“专擅”:张居正辅政的特点
以大历史观来认知某一时期的历史,在不割断历史联系的前提下,更应关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但在具体研究中,可以根据某一关键事件来划分出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晚明而言,尽管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晚明的历史特点,但首先必须要正视政治的因素。无论晚明呈现多么新奇的现象,必须承认的是,明朝的社会性质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仍然是高度强化了的君主专制制度,不能因为有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或“市场经济萌芽”,或“早期工业化”,或“近代早期中国”,或“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等现象而忽略了这一基本事实。讨论晚明时代在局部或个别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是必要的,但不能以点概全,更不能无视政治因素的制约而津津乐道于晚明的“新气象”。
就社会矛盾激化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激烈程度而言,明朝在正德时期即在建国150 多年后亡国也是有可能的。而之所以没有出现这一结果,就在于正德、嘉靖之际出现了较为彻底的人事更迭,并在这一阵痛中扭转了衰亡的局面,使明朝在世宗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的过程中实现了重生。一些学者将嘉靖朝政治描绘成漆黑一团,腐败透顶,对世宗与张璁等人的革新活动和因此对明朝历史走向所产生的独特而又积极的作用视而不见,其结果是既没有讲清楚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也没有搞明白所谓“张居正改革”的前因后果,自然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张居正施政的得失和晚明历史的走向。①参见田澍:《嘉靖革新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事实上,张居正对嘉靖朝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指出严嵩因弄权而导致政治弊端丛生的同时,又在整体上肯定了嘉靖政治,并明确指出“孝莫大于尊祖”,再三表示自己要切实效法祖宗之制,“率由旧章”,明确说道:“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②张居正:《张太岳集》卷37《谢召见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464 页。他曾严厉地批评非议祖制的言行,说道:“近时迂腐之流,乃犹祖晚宋之弊习,而妄议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识治理者也。”在评价“二祖”(明太祖和明成祖)之后诸帝的作用与地位时,张居正特别突出了嘉靖皇帝的巨大影响,认为世宗“承正德群奸乱政之后,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纲,饬法纪,而国家神气为之再扬”。③张居正:《张太岳集》卷18《杂著》,第211、212 页。他还明确表示要效法世宗之行政,说道:“正德年间,政体紊乱,至世宗皇帝以聪明至圣入继大统,将以前敝政一切改正,以复我祖宗之旧,正今日所当遵守者。”④张居正:《张太岳集》卷45《议外戚子弟恩荫疏》,第572 页。谈迁就此论道:“张居正既柄政,慨然任天下之重,专尊主权,课吏实。尝言高皇帝真得圣之威者也,世宗能识其意,是以高卧深宫之中,朝委裘而不乱。今上,世宗孙也,奈何不法祖!”⑤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68,隆庆六年六月庚辰,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4193 页。
不可否认,张居正在万历十年的去世,绝对是影响万历政局走向的一件大事,但简单地将张居正与其生前的政治行为截然分开,并一再放大张居正去世的影响,则是值得商榷的。正是由于张居正十年的“专擅”,使亲政后的神宗力图洗刷其“顾命”政治的痕迹,并极力清除张居正的各种影响。王锡爵认为:“皇上天纵神明,近者事事惩张居正专权之辙,章奏亲览,处分亲断。”⑥《明神宗实录》卷267,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壬辰,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 年,第4969 页。正由于此,由张居正亲自选任的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等人也势必与张居正划清界限,力图消除顾命政治的历史痕迹,以开启神宗亲政的新局面。《明史》所谓张四维担任首辅时,“知中外积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故“力反前事,时望颇属焉”,⑦[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9《张四维传》,第5770、5771 页。以及申时行“务为宽大”,“罢居正时所行考成法”,“以次收召老成,布列庶位,朝论多称之”,⑧[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8《申时行传》,第5747 页。凡张居正“诸所引用者,斥削殆尽”⑨[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3《张居正传》,第5651 页。等现象,就是这一转变的具体体现。申时行对此毫不掩饰,他在《张文毅公神道碑》中说道:
自江陵柄国,以刑名一切痛绳海内,其治若束湿,人心嚣然。既没,而亲信用事之人尚据要地,与权珰 为表里,相与墨守其遗法,阁中议多龃龉不行。公燕居深念,间为余言:“此难以显争而可墨夺。今海内厌苦操切久矣,若以意示四方中丞直指,令稍以宽大从事,而吾辈无深求刻责。”会皇嗣诞生,而公喜可知也,曰:“时不可失。”乃手疏,劝上宜以大庆施惠天下,省督责,缓征徭,举遗逸,恤灾眚,以养国家元气,而出诸司所拟宽条属余损益,凡数十事以进。上欣然命行之。⑩申时行:《张文毅公神道碑》,张四维撰,张志江点校:《张四维集·条麓堂集》卷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872-873 页。
张四维、申时行行政风格的遽变,既是其同张居正划清界限的必然选择,又是适应神宗亲政局面的必然要求。明人夏允彝所谓“继之辅政者,多避怨趋时,鲜能负荷”的批评显然不符合实情,但所谓“上既壮盛,明习庶事,不复委柄于下,操切之后,继以宽大,人皆乐之”⑪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83,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丙申,第5154 页。则有一定的道理。而《明经世文编》的编辑者认为申时行等人“尽反江陵之政者为身谋,非为国谋耳”⑫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69,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5154 页。的说法,并没有考虑结束张居正顾命政治所必然带来的政治阵痛。
《明史》的作者极力贬损申时行等后继阁臣,试图要把他们与张居正区分开来。其言:“神宗之朝,于时为豫,于象为蛊。时行诸人有鸣豫之凶,而无干蛊之略。外畏清议,内固恩宠,依阿自守,掩饰取名,弼谐无闻,循墨避事。”①[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8,赞曰,第5768 页。同时认为“四维等当轴处中,颇滋物议。其时言路势张,恣为抨击。是非瞀乱,贤否混淆,群相敌仇,罔顾国是”。②[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9,赞曰,第5782 页。事实上,张四维、申时行等阁臣都是张居正一手挑选任用的,是张居正利用顾命身份组阁以维持自己“专擅”的产物。如果非要说是这些阁臣集体反水,那只能说明张居正用人失察,应对其严重失职进行反思,而不是一味地讥讽张四维等阁臣。万历十九年(1591),吏部尚书陆光祖对神宗说道:“自大学士张居正用事,阁臣进用,始有不由会推者,意在市恩蔑弃成法,天下共言其非矣。”③陆光祖:《覆请申明职掌会推阁臣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374,第4058 页。从张居正夺得首辅之后,“内而内阁、六部、都察院,外而各省督、抚,没有一个不是居正推荐的人,言官之中,御史、给事中也几乎没有一个不听居正底指挥。”对于张居正选用的阁臣,朱东润做了很有意义的考察,认为善于“潜伏”的张四维于万历三年(1575)入阁后,表面上对张居正恭谨谦顺,使张居正“只觉得四维是一个恭谨的同僚”,但张四维很清楚,“在居正当国的时候,谈不到争权。吕调阳入阁三年了,除在内阁公本照例署名,以及每逢庆典,照例进官、蒙赏以外,还有什么?四维知道自己只是‘随元辅办事’。这是圣旨,也不妨说是一个条件。大学士固然名为大学士,其实只是居正底一条尾巴。在这一点,居正和四维成立一种默契。但是居正没有看清忠厚的人和才华的人究竟有些不同。忠厚的人如吕调阳,也许可以遵守这个默契,并不感觉痛苦;才华的人如张四维,便完全两样了。他遵守这个默契,但是心里却充满怨愤。他不甘做尾巴,然而他只能做尾巴。他底恭谨,只能增加他底仇视。这便成为居正身后,四维极力报复底张本。”④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345、199-200 页。为何张居正如此招人痛恨?黄仁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⑤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70 页。所以,在考察申时行等人的政治行为时,不能将其与张居正截然分开,否则,就无法理解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谢国桢所谓“继任张居正的首辅,像申时行、王锡爵之流,他们的威望远不如张居正,手段也不如张居正老练,他们只知道唯诺因循,来取媚于皇帝,想尽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造成党羽养成自己的势力”,⑥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 年,第13-14 页。看到的只是张居正顾命和神宗亲政两个不同时期首辅权势的不同表现状态,申时行等首辅权势的明显弱化是神宗亲政后的必然要求,他们不可能拥有张居正式的“专擅”,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张居正。
当然,神宗亲政后的行政并非一无是处,就其本意来说,他试图有所作为,有所成就。如神宗起用被张居正长期排斥的清官海瑞并为刘台等人平反,就是向天下昭示自己惩治腐败和纠正冤案的决心,也是在表示对张居正执政时政治腐败和专权的不满。但总体而言,神宗未能弄清清算张居正的真正目的,既没有详细的清算内容,又没有可控的清算范围。所以,在清算张居正时,势必涉及张居正效法嘉靖政治的敏感话题。如万历十六年(1588),阁臣王锡爵对神宗说道:“闻张居正擅权时,要钳人口,故将世宗晚年遗札尽行进御,名虽效忠,其实有导皇上刑辱言官自为己地之意。今皇上必欲法祖,则自有良法美意可师,而居正乃万世罪人,岂可既发其奸,而又行其志也?”⑦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庚寅,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728 页。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阁臣方从哲、吴道南改变了这一认识,明确要求神宗向世宗学习,说道:
自昔帝王敬天,必先法祖,臣等不暇远引,即我世宗肃皇帝,非卓然中兴之主哉?彼其用贤图治、虚怀纳谏之芳规,乃皇上耳闻而目击者。夷考其时,有九卿多缺、都宪全空如今日者乎?有考选不下、候补散馆不下、言路寥寥如今日者乎?有各科无印、各差无人、虚封驳之司、废巡方之任如今日者乎?使是数者而无妨于祖制,无害于国家,以世宗英明神圣,何不当先为之,而必至于皇上始有此异常之举动也?夫人主,语之以敬天,谁不悚然惧?语之以法祖,谁不欣然喜?况我皇上聪明睿知,有为尧为舜之资,岂其于世主之所能为者反有让焉?是不过一深思、一奋发间,便可转因循为振作,易壅滞为疏通,纾海内郁结之心,辟贤士登庸之路,太平之盛将煌煌乎与世宗肃皇帝比隆较烈矣。①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丁未,第3328-3329 页。
不难看出,在清算张居正时的舍本求末和矫枉过正是亲政后神宗最大的政治失误,而放任朝臣毫无节制地攻讦张居正更是神宗政治最大的自我伤害。
明代政治体制的核心在于权力制衡,以确保皇权的绝对安全。在神宗即位后,明代政治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象:一方面张居正权势显赫,神宗皇权被“侵夺”,皇权与阁权的错位,导致皇帝可有可无;另一方面出于清算张居正的需要,阁权被全面打压,皇权与阁权又出现了新的错位,阁臣可有可无。其结果就是皇帝视阁臣如无有,阁臣难有作为,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弱。从神宗即位开始,张居正生前的“专擅”和死后的反“专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万历十二年(1584),申时行对神宗说道:“今议者徒见前任阁臣之擅专,往日铨部之阿意,不论黑白,并以疑臣。不知昔年,皇上犹在冲龄,故彼得操权罔上。今皇上春秋鼎盛,总揽权纲,凡有票拟,必经御览,凡有处分,必奉宸断,臣何敢毫发擅专?臣不擅专,部臣何所忌惮而曲为阿媚?”②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四月一日庚寅,第465-466 页。后来,阁臣叶向高也指出:“盖当主上冲年,江陵为政,一切政事不相关白,至于起居食息,皆不自由,上心积愤不堪,深恶臣下之操权矣。”③叶向高:《答刘云峤》,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61,第5049 页 。离开了神宗被张居正架空的基本事实和由此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就无法理解晚明政治的基本特征。
在张居正和万历初政的研究中,首先必须要正视张居正的顾命角色,也必须要把这一阶段视为非正常的政治状态。同时,只有把神宗亲政看成常态,而不是变态,才能理性地认识神宗政治的走向。也就是说,晚明的政治走向与年幼的神宗有关,与顾命时期“专擅”的张居正有关,与张居正未能顺利移交皇权有关,与张居正没有把神宗培养成明君有关。于慎行就此论道:“万历丁丑,江陵奔丧辞朝,上御文华殿西室,江陵墨缞入见,泣涕陈辞,上亦为之抆泪,一时相传以为古今宠遇,而不知贾似道故事也。似道平时尊礼,至于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避席目送殿廷始坐。已而称疾乞归,人主涕泣拜留,至命大臣、侍从传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赐,日十数至。此何礼也?江陵晚节礼遇,亦略相仿,至称‘太岳先生’,又过于往代矣。嗟夫!君上宠荣出于迫胁,大非人臣之福,有识之士以为惧,不以为荣也。”④于慎行撰,吕景琳点校:《谷山笔麈》卷4《相鉴》,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44 页。张居正所侍奉的皇帝是“小孩子和他的学生”,而“环境和才能加在一起,造就了张居正的权威”。⑤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5 页。高寿仙就此认为:“张居正并不是皇帝,而且他所担任的首辅职位也不享有前代宰相那样的法定行政决策权,因此他全权处理国家事务的行为便不可避免地会视为‘专擅’。”⑥张显清:《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第373 页。
如果以张居正的去世来分割万历时代,那将无法理解清算张居正“专擅”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也无法理解神宗内阁权力弱化的来龙去脉。只有将张居正的辅政与其去世后所遭受的清算联系在一起,才能认清神宗初政对晚明政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三、神宗皇权的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学界所谓晚明时期神宗怠政、思想混乱、党争激烈、吏治腐败、矿监税使横行、土地兼并等现象,只是明朝走向衰亡的一般表象,而非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不应视为进入晚明的主要标志。明朝的衰亡既有封建王朝亡国的一般特征,又有其特殊的内在表现。而要想弄清后者,观察的起点只能从神宗即位的那一刻来探寻。尽管明穆宗去世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但与幼主即位相比,其他所有事件都处于次要地位。张居正一人顾命现象的出现本身就是这一巨变中的一个特例,人们越凸显张居正的个人作用,就越说明万历初政的异常。尽管神宗的即位没有像“大礼议”那样带来君臣更替的全新格局,但皇帝因年幼而被阁臣、太后和宦官联合架空,则反映着“大礼议”之后明朝政治的又一巨变,并对此后的明代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穆宗临终前的安排是阁臣的集体顾命,而非张居正一人之顾命。时任吏部尚书的杨博对集体顾命的安排寄予厚望,他希望“查照累朝故事,内外章奏应票拟者,不拘大小,悉令阁臣票拟;中外传帖应视草者,无论巨细,悉令阁臣视草。既有未惬圣心,不妨召至便殿,面相质问,务求至当,然后涣发。二三阁臣世受国恩,新承顾命,必不忍负先帝,必不敢负陛下。惟愿陛下推心委任,始终无二,庶几明良庆会而新政有光,上下志同而成宪无爽,固皇祖磬石之宗,慰先帝凭玉之望,天下生灵不胜幸甚,臣等不胜幸甚”。①杨博撰,张志江点校:《杨博奏疏集·杨襄毅公本兵疏议》卷28《会请端政本以隆新治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1272-1273 页。但不久因高仪去世和高拱被逐,顾命之臣仅剩张居正一人,政局为之大变,出现了“江陵承顾托、辅幼主,身伊周之任,宠眷稠渥,前古未有”②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71,万历十年六月丙午,第4415 页。之奇特现象。对此,张居正也毫不掩饰地对神宗说道:“仰窥皇上之心,不过以数年以来,举天下之重,尽属与臣……故臣得尽其愚耳。今在廷之臣,自辅臣以至于百执事,孰非臣所引荐者?”③张居正:《张太岳集》卷41《三乞守制疏》,第520 页。柄政之后,张居正“对中央则力求提高相权,使政权集于内阁,阁权集于首辅,而以大部隶诸内阁,俾收指臂相助之功”。④佘守德:《张江陵》,梁启超:《中国六大政治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757 页。正由于此,被他提拔任用之人都想方设法地回馈张居正,这让张居正应接不暇。他在万历八年(1580)对四川巡抚张士佩说道:
仆生平好推毂天下贤者。及待罪政府,有进贤之责,而势又易以引人,故所推毂尤众。有拔自沉沦小吏,登诸八座,比肩事主者矣。然皆不使人知,不望其报,盖荐贤本以为国,非欲市德于人也。乃今为仆所引拔者,往往用馈遗相报。却之,则自疑曰:“何疏我也!”及不能殚乃心、任乃事,被谴责,则又曰:“何不终庇我也!”⑤张居正:《张太岳集》卷32《答张巡抚澽滨言士称知己》,第408 页。
又如万历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晚,神宗在乾清宫与宦官夜宴放纵时差点将其中两人杖毙,事发后,张居正对涉事宦官进行了处理。但是所处理者“不过冯保不悦者而汰去之,则此举适所以阿保之好恶而已”。对于这一处理结果,神宗明知其由,但“迫于太后,不得已皆报可,而心颇嗛居正及保矣”。⑥[清]夏燮著,沈仲九标点:《明通鉴》卷67,神宗八年十一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2685 页。
毋庸置疑,张居正的“专擅”是以架空皇权为前提的。“江陵柄国”“江陵当国”“江陵秉政”“政权由己”等表述都是架空皇权的代名词。黎东方论道:张居正“生平颇爱权力,而且定要全部权力。神宗从十岁即位,到二十一岁张居正死,始终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已。两宫太后,神宗的嫡母仁圣太后陈氏与慈圣太后李氏,由于有司礼太监冯保替张居正左右其间,也一直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又言: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之中,由于皇太后“管教甚严,张居正大权独揽,司礼监冯保又颇与太后及张居正合作,神宗除了读书以外,无所作为”。⑦黎东方:《细说明朝》,第282、294 页。朱东润亦言:张居正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认定惟有自己,才能担当国家底大任。因此从居正看来:攻击居正,便是攻击国家;摧毁居正,便是摧毁国家”。又说:“内阁里面,安静到没有一点波浪,更是嘉靖、隆庆以来没有的现象。”⑧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226、266 页。神宗即位后出现的这一现象,与嘉靖、隆庆时期皇权的强化正好相反,是皇权弱化的表现,暗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于慎行认为:
江陵自失臣礼,自取祸机,败在身家,不足深论,而于国家大政,有一坏而不可转者,何也?凡天下之事,持之过则甚,则一发而溃不可收,辟如张鼓急则易裂,辟如壅水决则多伤。即以内使一事言之,人主在深宫之中,以醉饱过误,断一奄人之发,不为非过,而未至大失,辅弼大臣,付之不问,则犹有惮而改,即欲规正,亦当从容陈说,使之自解,何至假太后之威,中外相应,制之股掌之间,使之藏怒忿志,蓄极而发,从此惟所欲为,无复畏惮。数年以来,诛戮宦者如刈草菅,伤和损德,无可救药,视一奄人之发,相去何如?则持之太急故也。嗟夫!以善为之,而不知其陷于太过,则不明于《春秋》之义者矣。①于慎行撰,吕景琳点校:《谷山笔麈》卷2《纪述二》,第20 页。
孟森就张居正的权势论道:“综万历初之政皆出于居正之手,最犯清议者乃夺情一事,不恤与言路为仇,而高不知危,满不知溢,所谓明与治国而昧于治身,此之谓也。”②孟森:《明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256 页。谢国桢明言:张居正“令人失望的地方,就是大权独揽,用高压的手段,权威都归到内阁,言官等于木偶,来取媚于内阁。居正到了晚年,位高望尊,傲慢的态度,更觉暴露无遗……冯保与他勾结,通行贿赂,官职的升降,都由他的爱憎,他的儿子嗣修等都中了高第,居正的势力,真是炙手可热,气盖一世,但他的积怨,就潜伏其中了。言官的舆论,表面上看来,似乎已被削夺,里面更是膨胀。而一般无耻士大夫,借着机会来弹劾正人君子,以取媚时相……到万历十年,张居正死了,遂为众矢之的……言官被张居正压制了十年,至此如江河千里,一泻直下”。③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2-13 页。樊树志认为:“张居正掌权之时,权势显赫,举国上下仿佛风中芦苇,随风而倒。”④樊树志:《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180 页。这些评论深刻揭示了张居正担任首辅时期的“专擅”实情和由此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张居正的“专擅”既非阁臣的权力,亦非明代之前宰相的权力,而是万历初政皇权弱化的直接反映。特别是张居正通过借助宦官冯保来强化自己的权势,明显违背了明朝政治的基本精神,故不可能成为效法的榜样。万历三十四年(1606),礼科给事中汪若霖论道:“皇上御极以来,阁臣变态亦略可睹矣。万历初年,权相勾珰擅政,天下股栗,盛满不戒,卒受诛灭之祸。嗣是宵人观望,于是一切变为侧媚险邪之行,以牢笼一世,门户甚坚,气脉不断。苟有正类,立见倾挤,以私灭公而不顾。天下之大,使天下之人,亦瞒心涂面以附之,而不知有公家之急,遂至今日,可为太息!”⑤汪若霖:《朝政因循可虑辅臣单匮难支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69,第5154 页。朱东润论道:“高拱、张居正当穆宗在位的时候,在最后的阶段里,已经不能并存,神宗即位以后,居正利用政治机会,撇开高拱,成为实际的独裁者,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史实。”⑥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345 页。也正因为如此,张居正一死,神宗便将其身边的徐爵等人视为“楚党”,认为其与冯保等“奴辈盗我威福久,其亟诛之”。⑦申时行:《张文毅公神道碑》,张四维撰,张志江点校:《张四维集·条麓堂集》卷34,第873 页。不难看出,当时神宗对张居正及其依附之人侵夺皇权的行为极度愤慨。正如申时行于万历十二年所言:“窃见故臣居正,虽以苛刻擅专,自干宪典,然天威有赫,籍没其家,则国法已正,众愤已泄矣。”⑧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六月四日己酉,第475 页。
政治晚明是晚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制约经济晚明、社会晚明、文化晚明等晚明“新气象”的关键因素。不论人们如何发掘晚明的新因素,也不论如何认识晚明新因素的积极意义,当晚明政治中枢极度疲软、吏治愈加腐败、政局激烈动荡、区域发展严重失衡且自我无力变革之时,明朝只能在民怨沸腾中土崩瓦解。汪若霖认为:“臣惟天下理乱,在于朝政得失,而国家内阁之地,号曰政府,谓皇上心膂所寄,天下机务之所从出也。今天下大势,似强实弱,似安实危,百孔千疮,仅存象貌,则惟是二十年来政府之内,懦啮渐靡,以至于此,识者伤之。”⑨汪若霖:《朝政因循可虑辅臣单匮难支疏》,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469,第5153 页。当神宗无法组建自己可信可控的集体内阁及神宗内阁不能与皇帝进行有效的沟通时,神宗政治的失控是必然的。万历三十六年(1608),入阁不久的叶向高鉴于上下隔绝、内外离心而自己难有作为,要求辞职,并言:“受事数月,莫展一筹。政本何地?辅弼何官?而可苟且度日!铨臣问臣曰:‘庶官旷矣,职何以修?’计臣问臣曰:‘边军噪矣,饷何以处?’台臣问臣曰:‘宪署空矣,要紧各差,急何以应?’诸如此类,臣皆不能置对。举天下至危至急之事,尽责之臣等,而臣等实无以副。”①《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壬午,第8452 页。同年,利玛窦就自己的所见所闻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神父的报告中说道:“当今皇帝从不离开皇宫,很多年才在宫中上一次朝,而朝臣们也只能从很远的地方见到他:他们在一个院落中,面对着居于高台之上的皇帝。”②[意]利玛窦著,文铮译,[意]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利玛窦书信集·致罗马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神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321 页。要理解这一极不正常的现象,就不能不把观察的视角聚焦于张居正身上。在张居正看来,“只要他取得万历皇帝一人的暂时信任,就可以为所欲为,对于任何不同的意见,尽管罚不当罪,也要重处,这样的确可以取得暂时的效果,没有人敢反对他了,但是在积压新的社会矛盾,为日后的矛盾暴发准备了条件。”③陈生玺:《张居正与万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604 页。通过清算张居正,神宗明白其他人与张居正一样,一身兼有“阴”“阳”两重性,“有‘阴’则有‘阳’,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的。于是他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并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④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76 页。可以说,神宗对阁臣的不信任,主要源于其对张居正“专擅”的不理解和不认同。朱东润认为:“居正当国,便等于神宗失位,首辅大学士和皇帝,成为不能并立的形势。在这一个情态之下,居正头脑糊涂一点,便可以做王莽;气魄大一点,也可以做曹操。但是居正不是王莽、曹操,而且在那个提倡忠孝的环境之下,也不容许王莽、曹操的产生。居正以忠孝自负,而忠孝自负的主张,又和专权当国的现实,不能融洽,心理遂陷于极端的矛盾状态。”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第345 页。
正是由于张居正未能在神宗成年后自觉地结束顾命政治,没有在生前将皇权顺利地移交给神宗,没有组建能够担当大任的内阁团队,便直接导致了万历内阁的疲软,使后张居正时代无法构筑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明人冯时可认为张居正的事功不容抹杀,“惟是好揽权而喜附己,则于贤者若掷沙遗沈而莫之恤,于佞者若嗜醴悦膻而莫之厌。故一时举措多拂人意。又其交内竖以固位,进珍玩以希宠,甚非大臣之道。至于夺情拒谏、鼎甲其子,而名行大坠,人心大失矣。所谓君子有大道,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于斯验矣。”⑥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71,万历十年六月丙午,第4415 页。张居正事实上的“专擅”和神宗应有的“独断”之间的冲突是神宗即位之后最大的政治矛盾,这一矛盾不仅仅存在于张居正生前,而且在他死后依旧延续着,对神宗心理所造成的影响是极大的。王其榘认为张居正得祸的主要原因是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在明代特别突出,“皇帝要躬揽庶政,内阁辅相只是做顾问、代言(草拟诰敕),超过这个界限,就是专恣擅权”。而张居正“这个名相,还总揽了朝政。他自己也意识到‘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提出要‘归政’于朱翊钧,但又受阻于慈圣皇太后。以一个内阁辅臣,公然要提出归政,表明是他在‘摄政’,这在皇帝成年之后,是绝对难以容忍的。居正死后不久即遭惨祸,关键问题就在这里”。⑦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260 页。但让神宗君臣始料不及的是,清算张居正不仅未能强化阁权,反而使其越来越弱。面对言路的攻击,朝臣“皆人人自危,重足而立,侧目而不敢言”。首辅申时行甚至发出了“孤单寡与”⑧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四月四日庚戌,第469、470 页。的感慨,并认为“今之论者,皆不惜国家之体统,不知臣子之分义,此风不息,为患非轻”。⑨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六月十日乙卯,第476 页。阁臣许国也认为自己身处“国是摇夺,朝议混淆”⑩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六月十二日丁巳,第477 页。的乱局之中,故连连上疏辞职,直言:“彼私党已成,气焰渐盛,稍侵其类,则群起交攻。或居中密图,或扬言鼓众。不得于此事,则籍明口于他事。不得于此人,又假手于他人。盖有鳞可批、颜可犯,而言官不可少指者;命可违、法可乱、而弹章不可少议者。将来大臣拱乎(手)听命,重足屏息,人人自危,接迹求去,又不独臣一人而已。”①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庚申,第478-479 页。一年半后,许国又与王家屏联名疏言:“臣等既不能将顺皇上之美,又不能匡救皇上之过,伴食窃位,分毫无补,使天下后世追臣等而数其罪,复何颜面参于帷幄之中,立于臣僚之上乎?”②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丁亥,第566-567 页。将张居正的权势与其顾命的身份联系在一起。所谓张居正改革“不仅必然是短命的,而且在此之后不可避免会出现两种趋势:其一是政治权力失衡后的反弹,造成各种势力的纷争不休;其二是思想被禁锢后的回拨,形成以讲学、清议为核心的士人运动。而此二者恰为晚明党争兴起的重要原因”。③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79 页。阁权弱化必然导致政治功能紊乱,明朝的衰亡不可避免。万历三十九年(1611),叶向高说道:“臣见近来朝纲国政日以陵迟,世道人心日以嚣竞,而又到处灾伤,连年荒旱,考古准今,必成祸乱。”④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辛酉,第2809-2810 页。五年多后,方从哲直言:“年来水旱相仍,盗贼时有,民生困敝,国计空虚,吏治日窳,边防渐弛,纪纲坠而不振,法守废而不存,人心之郁结未纾,朝政之壅淤日甚。”⑤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第3332 页。《明史》的作者认为在朱赓一人在阁时,明朝已经是“朝政日弛,中外解体”⑥[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219《朱赓传》,第5780 页。的状况了。
在认识晚明政治时,如果抛开首辅张居正,就无法认清其时代特点和政治走向。只有从神宗即位开始来认识晚明政治,才能较好地把握晚明政治演变的内在特点。毫无疑问,首辅张居正绝对是认识晚明政治的关键人物。万历十年,尽管张居正离开了人世,但他仍然活在人间,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着万历政局。无论生前的“专擅”,还是死后所遭受的“清算”,张居正的荣辱变化集中反映着神宗皇权畸变的时代特点:神宗年幼之时,暂时需要张居正;神宗长大明理之后,则要抛弃张居正。而要树立亲政后的良好形象,神宗必然要设法消除张居正顾命政治的印记。换言之,以“专擅”名义清算张居正的目的在于使皇权和阁权向常态化转变,只是由于神宗君臣全面否定首辅张居正,未能把握好分寸,才使清算失控并走向反面。
晚明的起点应从隆庆六年六月神宗即位算起,历时73 年,作为探讨明朝衰亡的时间已经够长了。而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是以皇权的弱化来表现的。表面上看是张居正在“尊主权”和“强君威”,实际上是在侵夺神宗的皇权,造成了神宗对阁臣的不信任。首辅张居正的独特权势是神宗年幼即位的特殊产物,既不可能延续,也不可能复制,故在万历十年以后绝不可能出现像张居正一样的强势阁臣,使神宗无心膂股肱可寄。从叶向高、方从哲等人连连上疏要求神宗增补阁臣而不敢提及张居正的情形来看,他们不敢拥有张居正式权势的想法,而是一再强调集体内阁的重要性。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方从哲所言:“窃惟国家设内阁之臣,匪徒备顾问、供代言之役而已,凡军国大事,咸得与闻,故密勿之司,号称政本。祖宗朝多至五、六员,少亦三、四员,使之谋断相资,协恭共济,从来未有以一人独任且至数年之久者。”⑦南炳文、吴彦玲辑校:《辑校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二日丁未,第3790 页。此类话语在后张居正时代不绝于耳。只有正视张居正辅佐幼主的独特性,并以皇权的弱化为中心来认识神宗政治的特点,才能认清晚明政治的特点与走向。
四、结语
穆宗去世后,神宗年幼且一时难以行使皇权是客观事实,如何将神宗培养成贤君英主,才是张居正首要的政治任务。如何在恰当的时机将皇权顺利移交到神宗手中,才是张居正首要的政治使命,也是对张居正极大的政治考验。只有以神宗即位为起点来审视晚明的历史,才能认清因皇帝年幼而出现的皇权弱化对晚明政治的特殊影响,才能洞悉张居正对神宗政治生态的深刻影响,才能看清晚明政治的实际走向。
不论是张居正“专擅”所导致神宗皇权的被动弱化,还是神宗亲政后因“怠政”而引起的皇权的自我弱化,都是神宗即位后皇权弱化的不同表现形式,这是隆庆、万历之际明代政治的重大变化。穆宗的临终托孤、幼主的即位、顾命首臣高拱被逐、张居正夺得首辅并成为顾命孤臣,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是神宗皇权弱化的集中表现,故晚明政治的起点应从神宗即位的隆庆六年六月算起。只有将“万历”等同于“神宗”,赵翼所谓明朝“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①[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卷35《万历中矿使之害》,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797 页。才与《明史》的作者认为明朝“亡于神宗”的论断是同一个意思。
只有把幼主神宗即位以后的皇权和阁权的失衡联系起来并以此为视角来认识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才能看清晚明政治的走向并把握晚明社会的特点。过分突出张居正的个人作用而无视内阁“同寅协恭”的集体功能,显然背离了明朝设置内阁的基本精神。后张居正时代既有清算张居正“专擅”而树立神宗亲政形象的主观要求,也有结束顾命局面而恢复内阁常态的客观要求。张居正的权势既不可复制,也不能再现,神宗绝不会允许出现第二个张居正,后来的阁臣也不敢成为第二个张居正。神宗时代皇权的弱化和阁权的疲软势必引发政治的衰败,而政治的迷乱又与活跃的社会经济之间找不到契合点,明朝只能在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失衡中走向灭亡。
将神宗即位作为晚明政治起点的标志,旨在强调这一特殊历史时刻对明代政治的特殊影响。幼主神宗的即位标志着明朝皇权的弱化,对此后明朝的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顾命辅政之时,一方面继承了嘉靖、隆庆时期革新的遗风,使神宗初政得以平稳发展;另一方面又隐藏着巨大的危机,使神宗初政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神宗对皇权弱化的极度不满,才使清算张居正毫无理性可言。在神宗君臣甚嚣尘上的清算之中,张居正在顾命时期所遵循的法祖崇实、综核名实、精核吏治、讲求实效等政治理念也一并被抛弃,万历政治因此而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