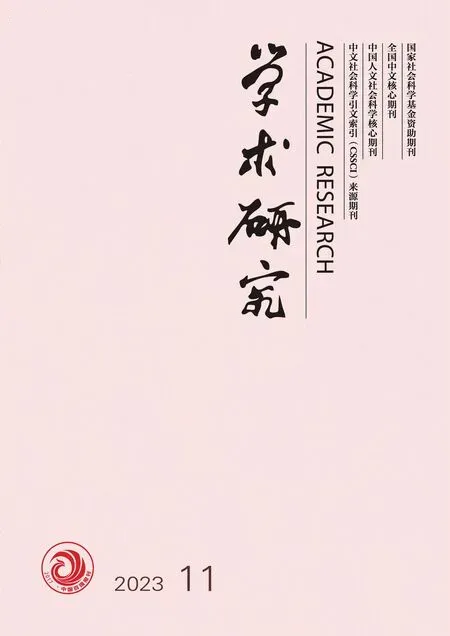卫生法基本理论的困局与方法论的重构*
肖平辉
一、问题的提出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当年6 月,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第一部“牵头管总”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施行。上述卫生领域重大事件引起了学术界对卫生法的关注。近些年,国内也出现一批卫生法学者,并已经出现一批卫生法立项课题,显示卫生法愈发成为学术界热点研究问题。而学术界对于卫生法的法学理论建构的探讨尚处于初级阶段。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卫生法出现基本理论的困局,需要突破传统法学理论构建,应吸收理论界新近提出的领域法学视角进行方法论的重构。①解志勇:《卫生法基本原则论要》,《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3 期。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卫生法基本理论的困局
21 世纪初,有学者提出中国法学分阶段演进为政法法学、法教义学、社科法学三派。②尤陈俊:《不在场的在场: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之争的背后》,《光明日报》2014 年8 月13 日第16 版。虽然纯粹的政法法学已不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作为传统法学、部门法学的方法论,在学术界仍具有强大生命力,二者逐渐形成中国法学基本理论构建的基座。法教义学强调实然法的语义分析、对法条的解析和诠释以及稳定性、可预期性,而社科法学强调法条之外的学科探讨,具有应然法的批判张力。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的区别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为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方法论上的取向不同而已。相比而言,以社科法学来研究构建卫生法已胜于法教义学,具有进步意义。因为法教义学建基于传统部门法的话语体系,更接近法学科内的话语体系内循环。而且如前所述,法教义学是部门法体系构建下的法解释学,若教学研究过程中,仅仅从法教义学展开卫生法,或许会步入“机械卫生法条主义”窠臼而不能自拔。①赵敏、胡亚林等:《“5+3”一体化模式下卓越中医师的卫生法治素养培养研究》,《医学与法学》2020 年第6 期。而且目的上“法教义学是关于现行有效法律或者实在法的学问,它并不致力于探讨理想之法或应然之法”,法教义学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和可预期性”,以解释法条核心工作为司法提供裁判基准,较少思考“法应该如何”这样一个应然法维度的问题。而社科法学不同,它强调开放性,主动进行对非法律语言即其他社会科学的吸纳,达到法律学科大社科的外循环。“法教义学可能更多地关注法律后果,而社科法学更注重对事实后果的分析与考量。”②孙海波:《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的方法论反省——以法学与司法的互动关系为重点》,《东方法学》2015 年第4 期。在法律实践运作方面,“社科法学更注意现代治理术的灵活运用,因此视角更多扩展到新兴法律部门,以及法律与其他公共政策交织的运作技术。”通过社会科学的介入,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能够更好回应社会中的新问题。③李晟:《实践视角下的社科法学:以法教义学为对照》,《法商研究》2014 年第5 期。
以卫生法中的医疗纠纷为例。大量医疗纠纷都由医疗损害衍生而出。如果从法教义学的角度,医疗纠纷来自于医疗损害,而医疗损害应该直接定位到民法教义学中的侵权损害赔偿,也就是过去的侵权责任法到现在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医疗损害责任条款,将法律事实与相关民法规范涵摄,进而完成司法裁判。从法律及语义逻辑来看比较完备,但实际上上述民法教义学在现实中遭遇了困境。大量的医疗纠纷无法仅仅通过医疗损害的法教义学分析得到解决,即至少民法教义学在卫生法面对某些问题时失去了解决问题的张力。医疗损害是医患问题的燃点,具有更深刻的社会纬度,“医患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具有契约性质、消费倾向、经济伦理和法律内容的特殊的不对称的专业关系,具有综合性的特点”。④李正关、冷明祥:《医患关系研究进展综述》,《中国医院管理》2009 年第3 期。我国长期存在医疗资源地区性不平衡、过度医疗、医生收红包等不当行为。⑤张文娟、郝艳华等:《我国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对策》,《医学与社会》2014 年第4 期。而这些问题的叠加带来的医疗纠纷问题,通过民法以教义学的教条的方式难以解决。对医患关系应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法律多维层面进行思考,“其改善的途径应是全方位”。⑥宋华、宋兰堂等:《对医患关系现状的多维思考》,《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3 年第9 期。这些更深刻的社会纬度问题,使得医疗纠纷不能仅仅只看“法律后果”,更应关注其扩大性的社会影响的“事实后果”问题。正因为如此,对于医疗纠纷,国务院出台《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强调加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同时司法、公安、财政、民政、保险监督管理等部门通力做好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⑦《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8 年第26 期。本条例实际上是对我国既有医疗损害民法教义学的有力扩张。先前的医疗损害民法教义学以解释法律为工具,仅仅对实然法进行诠释,缺乏应然法的社会性张力,对解决卫生法中医疗纠纷这样一个较具社会开放性的问题已经开始力不从心,所以才有《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在后的以一种全方位多社会视角介入医疗纠纷进行补位。这也契合了有学者对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进路差异高度总结:前者是“作为自治体系的法律”,后者是“社会语境中的法律”。⑧宋旭光:《面对社科法学挑战的法教义学——西方经验与中国问题》,《环球法律评论》2015 年第6 期。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中国对现行卫生法中医疗纠纷问题的解决思路不是仅仅限于法教义法,而是某种程度上契合社科法学,在超越法条教义语义维度上展开。此时社科法学视野的展开,也即大社科的外循环分析,即前面提到的“现代治理术的灵活运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科法学在卫生法方法论上的优势。
本质上,社科法学以法律交叉为研究进路,形成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认知科学研究等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交叉的学科。⑨侯猛:《社科法学的研究格局:从分立走向整合》,《法学》2017 年第2 期。相较于法教义学,社科法学虽然强调不拘泥于教义,法外学科展开并形成相对独立的新的学科,有其进步意义,但对于卫生法中的医疗纠纷问题,可能需要解决前置发生的地区医疗资源不均衡等相关问题,这些通过经济财政手段也就是社会科学维度可以得到解释和解决。因此,对于卫生法中的医疗纠纷问题,社科法学似乎提供了某种解决路径,但社科法学在卫生法的展开仍有缺陷。
卫生法大量涉及医学、公共卫生等自然科学。这些问题通常又以法的形式展开技术内容,比如形式意义的立法条款中却含有大量的技术内容。例如《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不得泄露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该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故意泄露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密切接触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的,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规定实际可以分两段进行分析:一是“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等先发行为,这是公共卫生医学问题;二是这些先发行为可能引发个人隐私信息的泄露等后生行为,而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先发行为与后生行为实际上是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一个卫生法问题,也就是传染病防治过程中的隐私保护问题。先发行为都是具有高度技术性的工作,涉及医学公共卫生等自然科学领域。这些先发行为因为是针对个人展开,直接从上述先发技术行为中伴生隐私问题,所以上述法条实际上同时涉及医学、法学高度交叉的现象,显然缺了任何一条腿都无法解决由此带来的卫生法责任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以什么进路去理解卫生法中以法的形式展开的技术内容?社科法学的交叉研究只强调社科领域,社科法学只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依然有学科跨度不够的问题。有学者在反思社科法学研究进路时,提出了法律与自然科学交叉怎么办之问。①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法商研究》2014 年第5 期。法律与自然科学交叉之问虽然只是以此质疑“社科法学”这一称谓的逻辑合理性,却无心插柳抛出了当今法学研究一个正在显现的命题:法学不但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叉,其实也在大量地与自然科学交叉集结。出现了一些新兴的文理交叉强调问题实践导向的领域,如前论述卫生法中有关医疗损害、传染病防治等具体问题,除了涉及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维度知识遁入法学,大量涉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也通过立法进入法学界域,此时社科法学研究进路在应对类似卫生法等新兴交叉法学科时开始力不从心。
上述分析显示了以法教义学、社科法学为中国法学基本理论构建的基座,在卫生法的法学知识的逻辑生成中,呈现方法论的不足。而卫生法遭遇的理论困局,亟待新的方法论的理论重构。
三、卫生法方法论的重构
(一)传统法学的破局与领域法学兴起
近20 年以来,一些新兴领域如卫生法、环境法、网络法等出现高度整合性、交叉性、动态性的特点。从传统法学角度,难以按当前传统部门法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标准划归任何一个既有部门法,这也呼唤以学科交叉和法学内部交叉进行研究的路径来解决这些领域的法律问题。有学者将上述有别于传统部门法的新兴领域的法学现象统称为“领域法”。该学者进一步认为,卫生法是典型的领域法,其调整对象具有很强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包括调整人体生命健康权益保护关系,跨公法、私法。涉及个体及群体健康安全,调整与人体生命健康相关的各种传统和新型特殊关系、调整卫生安全保障关系、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关系等,在实践中无法划归任何法律部门。②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政法论丛》2016 年第5 期。
领域法的出现克服了法教义学、社科法学在新兴问题领域的方法论上的研究缺陷,又在吸纳传统方法论的基础上形成自身独有的研究进路。有学者指出,有着浓重法教义学的传统部门法发展到现在受到三大挑战:一是部门法交叉,如刑法和行政法交叉形成行政刑法;二是传统法律因新的价值体系的遁入而带来全新塑造,如生命法原来归入民法或刑法,后来随着后器官移植、人工辅助生殖等现代生命科技的诞生,生命法开始对生命伦理纳入研究范畴;三是科技发展伴生出来的新兴领域天然的有别于任何传统部门法,如网络法、环境法等。第一种只需要加强传统部门法的教义交流便可以周延解决;后两种都是传统部门法建构“不敷用于新兴社会领域”的情形下,领域法可发挥的空间和价值的体现。①耿颖:《现代社会转型与领域法话语的展开》,《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6 期。前面提到法教义学、社科法学具有相通之处,则可视为传统部门法逻辑框架下的方法论。但以上述两方法论适用卫生法学教学研究都具有一定局限性。法教义学不免落入教条主义,“是法律与事实之间的公式化联系,至于法律背后的公义,通常不是其关注的重点。”社科法学偏重社会科学交叉下的理论建构,将关注法律规则的整体性价值,并不重视规则本身的形式圆满。②熊伟:《问题导向、规范集成与领域法学之精神》,《政法论丛》2016 年第6 期。虽然社科法学强调跨学科思维,需要遁入其他社会科学寻找解决问题的支点,但是卫生法是一门医学专业背景下的交叉法学。它无法回答医学等理工科学在卫生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更进一步说,社科法学无法解决法律人如何对医学等自然科学完成知识谱系的法学化建构问题。
(二)领域法学视角下的卫生法研究进路特点
领域法学一定程度上对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等合理元素兼收并蓄,并在前述理论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进路。随着学者研究的深入,领域法法学学科属性、定位愈加清晰。传统部门法更关注抽象、形式的正义;而领域法则对复杂的问题做具体和实质性的审思。当然领域法作为新型法学,并非完全颠覆既有的传统方法论,而是借鉴融合。领域法融合了部门法思维下的法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工具和手段等要素,但方法论上强调问题意识,强调法学研究的经世致用。领域法与传统部门法同构互补,但前者相对后者又有法社会张力的异质性,领域法突破传统部门法的形式主义,在认识和方法上对传统法律部门加以拓展和超越,弥补其应对新兴领域法律问题的研究进路的不足。按通说,领域法是以问题为导向,以特定经济社会领域法律相关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具有包容和开放的特征,融合部门法、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实现法学内部乃至其他学科之间整合互动,具备新型法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③刘剑文、胡翔:《“领域法”范式适用:方法提炼与思维模式》,《法学论坛》2018 年第4 期。
长期以来,我国“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甚至学科内部也沟壑纵横”,形成学者以传统部门法教义学为壁垒的“饭碗法学”思维。④王利明:《“饭碗法学”当休矣》,《法制资讯》2011 年第6 期。领域法作为法学研究方法论,实际上是对打破“饭碗法学”论的积极回应。领域法往往涉及新兴行业或技术等领域,作为新问题,其所体现的规则和法律范式往往无法被传统部门法框架所涵括,此外新兴行业或技术往往还有法律之外的知识体系架构。这些或都导致研究者需要重新学习、系统探究法学之外相关学科逻辑。而这也揭示了以部门法为基础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等其方法论在特定场域里的局限和领域法的发展空间。⑤耿颖:《现代社会转型与领域法话语的展开》,《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6 期。简言之,并非具备部门法学科知识,就可以将某一领域法研究好;领域法具有高度跨学科性,要想深入某一领域法,还必须对领域法所涉及的行业及技术背景也即法学之外的学科知识有系统了解。卫生法就是典型跨学科的法律,长期在法学、医学等学科中徘徊,一方面是两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研究的,另一方面也存在同时被两个学科边缘化的尴尬局面。如公共卫生法就尚未成为主流法学学科体系,并“长期在医学和法学领域内处于双重边缘化境地”。⑥李广德:《我国公共卫生法治的理论坐标与制度构建》,《法学》2020 年第5 期。这其实是对领域法的挑战,也是其魅力所在。“健康中国”的实施,新冠疫情的肆虐为卫生法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卫生法学者也有了更多的研究空间,而中国卫生法学术圈也尚在成长中。
(三)卫生法的领域法学实践与展望
从领域法学视角研究卫生法,学术界已有响应。法学院的卫生法学研究者开始进入领域法学,在卫生法方法论上作出了积极回应;医学院卫生法学者对领域法学在卫生法研究进路方面也进行了省思,如有医学背景的学者著书立说提出如何从领域法视角解构卫生法。领域法应该作为卫生法基本的理论范式,是因为领域法有效地避免了传统部门法划分研究导致的割裂性。领域法以问题为导向提取研究“公因式”。①乐虹、赵敏:《中国卫生法发展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75-79 页。
目前卫生法初步形成体系化教学,进入国内部分法学院、医学院。学术界现在普遍认为卫生法学是一门集法学、医学、公共管理学、伦理学等交叉学科。②王晨光:《时代发展、学科交叉和法学领域拓展——以卫生法学为例》,《应用法学评论》2019 年第1 期。不过一部分学者也对卫生法实际现状和地位产生忧思,卫生法的这种交叉跨学科,也使得它在医学和法学教育方面异化边缘化。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发生相互轻看冲突的“斯诺命题”现象;而破解这个问题,应该在医学院的卫生法学教学中用“以问题和案例为导向”的方法来提升医学生的医师职业精神,使医学生形成法律思维模式,进而形成学科良性交叉互动。③王岳:《医学专业卫生法学教育的“异化”现象探析》,《医学与哲学(A)》2017 年第6 期。
四、余论
本文探究了卫生法基本理论上的困局,即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等法学理论在卫生法上的局限性。④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并非因此否认传统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等法学理论在法学研究中的工具价值,事实上,法学界如部门法研究依然自觉不自觉运用法教义学作为理论证成工具和路径。秦天宝:《〈民法典〉背景下环境保护禁止令的法教义学展开——基于人格权禁令制度的考察》,《政法论丛》2022 年第1 期;王海军:《自杀行为规范属性及刑事归责的法教义学诠释》,《政治与法律》2023 年第4 期。提出对于卫生法这样一个跨法学和医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高跨度的学科,领域法更具有学术张力,因此卫生法研究者应打破传统部门法研究格局,主动进行跨学科知识体系的方法论重构,回应时代需求。中国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形成了包括疫情监测预警、领导决策、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等核心机制运转的重要经验,疫情也对中国卫生法进行了一次全面检视。⑤鲁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的多主体合作机制研究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学术研究》2020 年第4 期。但是,国内卫生法学还在建构起学科独有的知识体系的路上。⑥张怡:《欧洲卫生法学学科建设现状与发展路径》,《中国卫生法制》2021 年第4 期。借鉴美国主流学说中的卫生法学体系,卫生法分为以下模块:公共卫生相关法律(疾病预防、传染病防治法等);医疗相关法律(医疗卫生服务的许可、管理等);食品和药品相关法律(食品安全法、健康相关产品生产和营销、药品安全和记录保存等);生物伦理等。⑦上述模块中,是否将食品法纳入卫生法存在一些争议,比如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卫生法和政策创新中心(Center for Health Law and Policy Innovation)和食品法律及政策诊所(Food Law and Policy Clinic)联合主任艾米丽·莱布(Emily Broad Leib)教授认为食品法一方面具有维护人类身体健康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其具有卫生法属性。但另一方面由于食品来自于农业生产,其具有卫生法研究不能涵盖的特性,她本人于是更倾向于将食品法独立于卫生法。参见Emily B.Leib and Baylen J.Linnekin, “Food Law & Policy: An Essential Part of Today’s Legal Academy”, Journal of Food Law and Policy, vol.13, no.2, 2017。关于美国卫生法概况,参见Wang Zhengzhi, Tran Djung, Xu Fenglei, et al., “Health Law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Chinese Law Schools: Results of a Pre-SARS Survey”, Temple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Journal,vol.18, no.1, 2004。上述卫生法模块化内容充分体现了卫生法学与传统部门法的异质性和自身的高度交叉性。法学作为传统文科,法学研究者如何进行法科之外的学科如医学自然科学的构建?如何跨法学外部学科构建卫生法所需的知识体系?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